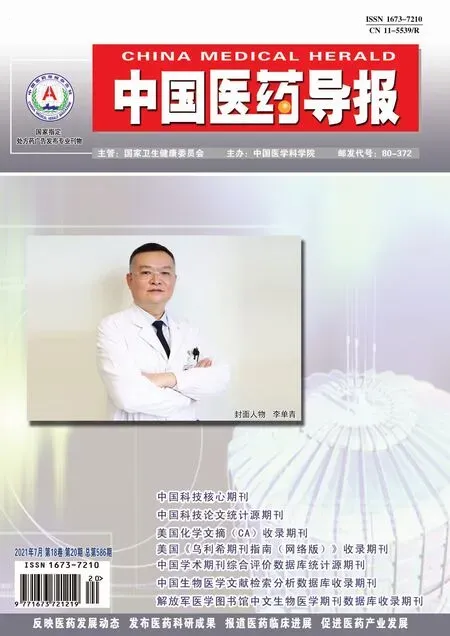賀豐杰教授順期而治談“調經重在滋陰”
王海靜 賀豐杰 朱虹麗 李 楠 李小寧 陳 梅 白 俊 龐 羽
1.陜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婦科,陜西咸陽 712000;2.陜西省寶雞市中醫醫院婦科,陜西寶雞 721000
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生活壓力日益劇增,生活方式及飲食的改變導致臨床上“閉止傾向性月經失調”發病率逐年升高,并呈年輕化趨勢,治療難度大。西醫學上“閉止傾向性月經失調”多由于卵巢功能低下甚至早衰、甲狀腺功能低下、高催乳素血癥、多囊卵巢綜合征、宮腔粘連等疾病引起,治療大多是針對其原發病,用外源激素調整體內激素的分泌,但治療周期長、預后欠佳等一系列問題始終存在。賀豐杰教授多認為“閉止傾向性月經失調”多以陰血津液虧損為主要病機,或兼它證,治療當以滋陰為主,調整月經當以“全周期滋陰養血,后半周期補陽以溫陽”為綱,臨證合理加減用藥。
1 調經以順期為本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人部·婦人月水》[1]中云:“女子,陰類也,以血為主,其血上應太陰,下應海潮,月有盈虧,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與之相符,故謂之月信、月水、月經。”月經周期的時間特點和大自然的“陰陽變化”密切相關,夏桂成教授曾提出月經周期按照“天人相應”的理論符合陰陽消長轉化的規律,與年、月、日、時相的節律均有一定的關系[2]。月經周期分別經歷行經期、經后期、經間期、經前期,這四期從陰陽節律變化角度看,分別為行經期重陽必陰、經后期陰長陽消、經間期重陰必陽、經前期陽長陰消,直至行經期月經來潮,又開始新的周期[3]。月經病順期而治的療法也稱為中醫周期療法,是在辨證辨病的基礎上,根據月經周期的不同時期,針對不同時期的陰陽變化,分別調方用藥,整體調節腎-天癸-沖任-胞宮軸的功能,為月經如期而至或受孕奠定良好的基礎[4]。
2 調經以滋陰為重
2.1 陰精為月經之根本
《素問·上古天真論》[5]“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其中二七和七七涉及女性生殖,即月經與胎孕。月經是女性生理特點之一,其與天癸關系密切,“天”言其來源于先天,“癸”言其本質屬天干中的癸水,天癸在生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月節律與月經的周期性相合[6],是促進生殖功能的一種物質,就其物質性而言,顯然天癸屬陰,為陰精(元陰、元氣)。然朱丹溪認為,日為陽,月為陰。天大于地,太陽始終如一,而月亮卻有陰晴圓缺,從這個自然現象來說,就是“陽盛陰衰”的體現,在人的生命過程中,多處于陽有余陰不足。《靈樞·五音五味》[7]云:“婦人之生,有余于氣,不足于血,以其數脫血也。”故月經以陰精為本,具有“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的體質特點,月經病從陰陽論則為“陰虛”,從氣血論則為“血虛”,常以陰不足為病機根本。
2.2 陰長為月經之始端
傳統中醫學認為[8]月經是天癸、臟腑、氣血、經絡協調作用于子宮產生的生理現象。腎與胞宮關系密切,《素問·奇病論》云:“胞絡者,系于腎。”腎在月經生成中起著主導作用,腎藏精,主生殖,生成、貯藏、施泄精氣;精生髓,髓充腦,作為元神之府,主宰包括月經在內生理活動;腎主一身陰陽,陰血充足,胞宮滿盈;腎乃天癸之源,天癸乃天之水也,又為月經之本;腎主沖任,沖為血海,任為陰脈之海;腎為氣血之根,月經物質基礎是也。現代醫家大多認為腎在整個中醫生殖軸中,具有類似于下丘腦的調節功能,參與卵巢排卵及性激素分泌的調節調控[9]。
天癸即元陰、腎精。明·張景岳《類經》:“夫癸者,天之水,干名也……故天者,言天一之陰氣耳。”就其功能性而言天癸乃動力,為元氣之來源。源于先天,為先天之陰精,受后天水谷精微的滋養成熟泌至,促進人體生長發育、維持胞宮行經及生殖機能,與下丘腦-垂體-性腺軸功能異曲同工[10]。其最主要是與下丘腦、垂體、卵巢分泌的激素類物質的功能相似[11]。這些理論可作為《內經》中“月事以時下”的現代科學解釋。羅元愷[12]認為天癸是與生殖密切相關的精微物質,即促進卵泡生長發育成熟、破裂的卵泡刺激素和黃體生成素。天癸在女性的生殖中,具有類似于西醫生殖軸中垂體前葉產生的促性腺激素的作用,因此天癸可能有類似垂體的調節功能[13]。雖然古籍中沒有相關“補天癸”的記載,但天癸源于先天,藏之于腎,可以通過滋補腎精腎陰以調節天癸盛衰[14]。
沖脈為十二經氣血匯聚之場所,是全身氣血運行的要沖,故稱“血海”。與腎脈相并而行,腎中真陰滋于其中。婦女以血為本,月經以血為用,沖脈充盛則月事以時下,故沖脈為月經之本。任脈乃“陰脈之海”“謂之任脈者,女子得之以妊養也”,任脈與全身陰脈匯于膻中穴,主一身之陰經,故為“陰脈之海”,凡精、血、津、液皆屬任脈所司,對女性的生理起著極其重要的調節作用,為婦女妊養之根本,故稱“任主胞胎”。十二經脈氣血充盛流注沖任,沖任二脈相滋,腎氣下傳,天癸下行,通過沖任二脈下注氣血于胞宮胞脈[15],使卵泡正常發育、成熟,而沖任通盛、氣血調和,才能順利排出卵子,保證正常的生殖功能。不論是元陰、腎精,還是天癸、血液均屬陰精范疇,均與卵泡的發育、成熟密不可分,因此說陰長為月經之始端。沒有良好的增生期子宮內膜,無言良好的分泌期子宮內膜。“子宮內膜分泌不良”往往基于增生不良。此期的“陰長程度”直接影響卵泡卵子的發育,特別是子宮內膜的增生程度,“陰長不及”也許就是臨床中“薄型子宮內膜”導致的月經過少及不孕癥的癥結所在。
2.3 滋陰為調經之法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說明決定人體生理活動的是陰氣而不是陽氣,滋陰極為重要。朱丹溪在《格致余論》中明確提出了“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的觀點,認為“陰氣難成易虧”,認為精血是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不斷消耗,易損難復,故陰常不足,同時還提出“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故氣常有余,血常不足”[16]。后世醫家也有相似觀點,如明代醫家劉純在《玉機微義》[17]中指出,天為陽,地為陰,天大于地,日明于月,在自然界存在著“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女子一生以血為用,經、孕、產、乳等特殊生理過程均與血有關,故常處于陰血相對不足的狀態,因此滋陰為女子調經之法,其貫穿在整個月經周期中。
行經期以“重陽轉陰,排出經血”為特點,根據陰長陽生、互根互長之理,重陽必須依賴陰的支持,陰不足則重陽的基礎不實,轉化時必有影響,轉化后陰長不及可導致病理變化,如卵泡募集數量不足、卵泡生長發育緩慢,激素水平不夠,則使子宮內膜修復延緩而出血延長,引起月經紊亂。《黃帝內經》云:“陽盛則陰虛”。婦人經血下泄必易耗血傷陰,有學者[18]認為“行經期腎陰癸水下泄,要適量加入滋陰養血之品”,在行經期“泄”時,以養血滋陰之品促陰長,協助重陽的順利轉化。
經后期“陰長陽消”,經血已下,胞脈空虛,胞宮藏而不瀉,促使“陰長”,是“補陰”的最佳時期,陰長奠定了其物質基礎,推動月經周期的演變[19]。《傅青主女科》所制養精種玉湯主要運用滋陰補血的藥物達到血中補陰,陰中養精,養精才能種玉,從而達到治療效果,同時又把血、陰、精聯系在一處,這一理論與西醫學上月經期后進入卵泡期,依賴雌激素促進卵泡發育,正反饋下丘腦垂體分泌黃體生成素,完成排卵之論相同,因此“滋陰養血、陰中育精”是貫穿整個經后卵泡期的主要治法。
經間期即“氤氳之時”,是重陰必陽的結果。“重陰”是指經間期癸水之陰達到整個周期的最高水平,具有癸水之陰的物質如卵子、血海內膜、周身氣血達到充盈的過程[3]。現代醫學此期是子宮內膜經歷從增生到分泌的過程,卵子成熟、內膜增厚開始轉化,這與中醫理論中氤氳之時陰陽轉化,陰精化生陽氣“不謀而合”。此期臨床病理特點主要是陰虛癸水不足。卵泡的發育依賴于腎陰癸水的滋養,如不足則影響卵泡發育,或長勢緩慢,或卵泡雖長大,但張力不佳、形狀欠圓,甚至無法順利排出,因此調理腎陰癸水極為重要。
經前黃體期的主要特點是“陰消陽長”,但陽長需建立在陰長至極的前提下,與陰密不可分,陰精生長而精卵發育,重陰必陽,排出卵子,從而分泌孕激素,開始陽長,故陽長是在陰長的基礎上產生的,陽長賴陰,陽長極,所需更多的陰液物質來支持,如陰有所不足,則陽長亦受影響。正如張景岳提出的:“善補陽者,必于陰中求陽,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此期類似于黃體期黃體分泌孕激素,孕激素相當于“陽”能夠幫助子宮內膜在增生的基礎上轉化為分泌期,從而排泄經血。
3 調經當以“全期滋陰養血,后半周期陰中求陽以溫陽”為綱
中醫認為閉止傾向性月經不調的病機分虛實兩種,虛者多因經血虧少,沖任虧虛;實者多由瘀血內停或痰濕阻滯,壅塞沖任,血行不暢所致。臨床以虛證或虛實夾雜者多見,尤以腎虛、血虛、血虧為主,夾雜他證。基于“腎氣全盛,沖任流通,經血漸盈,應時而下”“月經全借腎水施化,腎水既乏,則經血日以干涸而閉也”等理論,賀豐杰教授認為治療此類病癥首先要重視填補腎精,以“全期滋陰養血,后半周期陰中求陽以溫陽”為綱,兼化瘀通絡,臨證之際在溫潤填精,通澀互用。
賀豐杰教授臨證中自擬方——滋腎養血湯,此方以四物湯補血養血為基礎,加之健脾、補腎、疏肝、行氣之藥,同時順應月經周期加減用藥。滋腎養血湯主要組方為:熟地、山萸肉、山藥、赤芍、川芎、當歸、枸杞子、菟絲子、雞血藤、石楠葉、香附、砂仁。方中熟地、山萸肉、枸杞子補腎益精養血。菟絲子溫腎補陽,陽生陰長,陰中有陽,源源不竭,張錫純謂之補益之功能生肌肉。方中當歸、赤芍、雞血藤滋陰養血活血,能增加內膜生長的速度。石楠葉養腎氣、補陰衰,有學者研究[20-21],石楠葉為女子起陰之良藥,能夠喚起性興奮,對治療女性性冷淡有良好的效果。川芎為血中之氣藥,上行頭目、下行血海、中開郁結、旁通絡脈,與當歸相伍則暢達血脈之力益彰,靜中有動。香附之氣平而不寒,香而能竄,為疏肝理氣、調經止痛之良藥,李時珍稱其“氣病之總司,女科之主帥”。同時加之山藥、砂仁健脾益氣開胃,補而不滯。全方共12 味藥配伍滋腎陰、養精血,補腎陽溫而不燥,兼調肝腎脾三臟,動靜結合,補而不滯,以達到促進卵子生長發育成熟、改善子宮內膜血流、增加內膜厚度的作用。研究表明[22-23],以益氣養血活血、補腎填精為主,佐以溫補腎陽、理氣之劑,可明顯改善子宮內膜厚度,增加子宮血流量,并促進子宮內膜相關生物活性因子的表達,改善子宮內膜容受性。
月經期——滋腎養血縮宮湯:經期以疏泄為主,在滋腎養血湯基礎上加桃仁、紅花、澤蘭、益母草等活血化瘀之藥祛瘀生新,行氣活血,使精血瀉下順暢,除舊則新生。經期損耗陰精,祛瘀而不忘乎補陰精,以促進陰長,協助重陽的順利轉化,為新周期的開始奠定基礎。
經后期——滋腎養血育泡湯:經后期經血下泄,胞宮胞脈相對空虛,此時期以陰長為主,維持腎之陰精增長,為陰長的最佳時期,“陰”涵蓋了精、血、津、液等物質,并不單單指腎陰。《道德經》[24]云:“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折之,不足補之。”此時當養陰而助“陰長”。因此“滋陰養血、陰中育精”是貫穿整個經后卵泡期的主要治法,使天癸充盛,血海依時滿盈,為卵泡發育提供物質基礎。此期在滋腎養血湯基礎上常酌加紫河車、阿膠、黃精、女貞子、旱蓮草、何首烏、炙龜甲、炙鱉甲等血肉有情之品滋補精血。清·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中寫道:“阿膠是‘血肉有情之品,滋補最甚’。”滋養胞宮脈絡、充盈血海,促使卵子發育成熟、子宮內膜生長,為重陰轉陽奠定物質基礎,為孕育做好準備。
經間期——滋腎養血促排湯:在經間期則“重陰轉陽”,陰精化氣,氣屬陽,氤氳之候,陰陽互相轉化,陽氣蒸騰,鼓動卵子排出;《女科準繩》“天地生物,必有氤氳之時……凡夫人一月經行一度,必有一日氤氳之侯……順而施之,則成胎也”,此期是種子的最佳良機。此期機體通過重陰轉陽,排泄陰精(卵子)以糾正此時的陰陽不平衡關系,《黃帝內經》記載“無陰則陽無以化”,因此此期應當滋補陰精之品以助陰陽轉化。“女子以肝為先天”“滋腎必疏肝”,同時加以疏泄、理氣、活血等藥物鼓動卵子排出,為種子育胎提供良好的基礎。在滋腎養血湯的基礎上酌加肉蓯蓉、肉桂、柴胡、急性子、皂刺、澤蘭、路路通等溫補腎陽、疏肝理氣、活血調經之品,促卵子順勢排出。
經前期——滋腎養血促黃湯:經前期是在陰長至重的基礎之上,陽氣漸生至重陽的階段,此期陰陽俱盛,為孕卵著床提供良好的微環境。張景岳在附子、肉桂等補陽藥中加入大補陰精、滋腎水的熟地黃、枸杞子等補陰藥,使其補陽而不傷陰,陽氣得陰相助,化生無窮,水火既濟,創立了后世應用極為廣泛的右歸丸,此方益火之源,培右腎之元陽,為陰中求陽的代表方劑,迄今依然為婦科最為重要的基礎方劑之一。故此期在前方補腎填精基礎上溫補腎陽,治療酌加巴戟天、仙茅、鎖陽、淫羊藿、肉蓯蓉、續斷、補骨脂等以使黃體功能正常甚至增強[25],維持基礎體溫高相狀態,即維持陽長至重,重陽延續,才能順利轉化,排出精血,為行經期做好準備。且臨床研究發現[26]補腎藥如菟絲子、淫羊藿、鎖陽、枸杞子等可以顯著改善下丘腦-垂體-卵巢生殖性腺軸的功能,調節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的分泌,從而促黃體生成素及促卵泡激素的生成,改善卵巢的激素水平,提高生殖能力[27]。
4 結語
月經周期是一個陰陽、動靜轉化和氣血變化的過程,月經產生如季節之變化、海之潮汐、月之盈虧。這一周期變化的基礎是腎氣,動力是天癸,表現在血海。賀豐杰教授臨證中順應月經周期規律變化,不同時期用藥側重點不同,但仍強調滋補陰精之重要,在調經整個過程中全周期滋陰,在后半周期陰中求陽以溫陽,這一理論與現代醫學治療薄性子宮內膜、卵巢功能早衰或閉經所運用的人工周期治療方法相類似。
經后期滋養胞脈胞絡、充盈血海,補陰精、促陰長、助重陽,為重陰轉陽變化奠定物質基礎,精血源足充盛,血脈通利,沖任胞宮精氣血液灌注改善,從而促進胞宮內膜充盈生長、卵子成熟泌至、胞宮內膜由增生向分泌開始轉化;經前期因重陽至重較快,陰雖有消,但消中有長,而且長達到中高水平,若有消無長或是長不能達到中高水平,則陰虛及陽,必導致陽長不足,因此繼續補腎滋陰,陰中求陽以溫陽,陰中補陽,水中補火,以促進后半周期孕激素水平達到一定水平,并維持足夠時限,使子宮內膜充分轉化,為孕育胎兒或經期完全脫落做好準備,此法對于治療閉止傾向性月經失調性疾病效果較為明顯,然臨床亦不可完全拘泥于此,需結合現代醫學檢查手段,審時度勢,選方用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