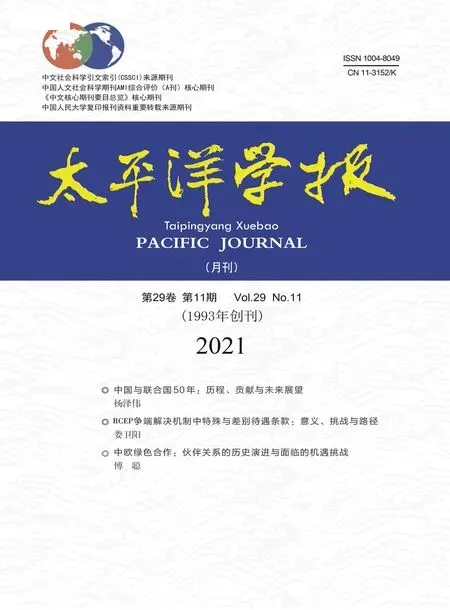北約新一輪變革趨勢與影響: “北約2030” 改革報告評析
郭籽實 洪郵生
(1.南京大學,江蘇 南京210023)
建立于冷戰初期、旨在抗衡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北約組織,在蘇聯解體、外部威脅消失后經過數次轉型而延續至今。北約的存續與轉型一直是學術界和戰略界研究的熱點課題,有學者認為,北約轉型成功得益于其制度化的約束性、靈活性與開放性等多重因素。①參見:Kirsten Rafferty, “An Institutionalist Re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Alliance Systems:Insights for Alliance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6,No.2,2003,p.342;鄭維偉、漆海霞: “聯盟制度化,自主性與北約的存續” ,《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第87-125頁。然而,近年來國際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大國競爭態勢仍然嚴峻,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的命題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探討。在這種背景下,作為美國全球霸權主要軍事工具的北約組織也面臨新的挑戰,并醞釀其戰略概念的更新和新一輪變革,北約近期發布的 “北約2030” 改革報告正是反映了這種變化。對此,有學者指出, “作為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安全基石,當前北約周邊局勢緊張,新冠疫情給各國安全風險帶來了不確定性,北約需要繼續調整以保持自身凝聚力和效力” 。②Andris Sprūds,Mārtin?Vargulis, “Transatlantic Futures:Towards NATO 2030,” The Rīga Conference Papers 2020,Rīga:Latv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Nov.13,2020,pp.9-10.與此同時,北約的轉型也面臨著與歐盟分工不明確、責任分擔爭議和職能范圍擴大帶來的更多內部問題和外部挑戰。①參見:Michael Scrima and Jurgis Vedrickas, “Non-Traditional Threats and NATO:A Look Toward an Expanded Role for the NATO Alliance,” Eastern Europe Studies Centre report,p.16;Si?nanülgen,A Long-Term Perspective on NATO and the Multinational Order,Dec.24,2019,www.jstor.org/stable/resrep19662,訪問時間:2021年6月9日;Peter Viggo Jakobsen&Jens Ringsmose,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How NATO’s Difficulties are Caused by the Absence of a Unifying Existential Threat,” Journal of Transatlantic Studies,Volume 16,Issue 1,2018,pp.38-58.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將首先考察冷戰以來北約戰略概念的演變及其面臨的新挑戰,重點以其 “北約2030” 改革報告為依據論述其新一輪軍事戰略變革的內容和性質,評估其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障礙,最后分析北約戰略新變化對中國的影響,提出作者對中國與北約關系的看法和判斷。
一、北約 “戰略概念” 演變及其面臨的新挑戰
冷戰結束后發展至今,北約組織先后通過1991年、1999年、2010年三次聯盟 “戰略概念” 的更新實施 “履行新使命、吸納新成員以及擴大新功能” 三大任務,實現了聯盟變革和轉型。然而,隨著后疫情時代的到來,北約面臨著盟國關于責任分擔的爭議、傳統大國競爭的回歸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及周邊安全環境的復雜嚴峻挑戰,因而對其 “戰略概念” 進行更新以適應形勢的變化勢在必行。
1.1 冷戰后北約三次 “戰略概念” 的出臺回顧
在冷戰結束前夕,北約就將其戰略轉型問題提上議程。1990年7月北約各盟國在倫敦峰會簽署《倫敦宣言》,開始了自身由軍事聯盟向政治—軍事聯盟的轉型進程。1991年北約羅馬峰會通過《聯盟的新戰略概念》(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這是冷戰結束后它出臺的第一份 “戰略概念” 文件,提出北約的軍事戰略由冷戰時期的 “前沿防御” 轉向新階段采取更廣泛的安全措施,在保留集體防御功能的同時,減少軍事力量規模、提高機動性以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國際危機事件的發生。
1999年北約開始了其冷戰后的首次東擴。面對冷戰后地區性危機和沖突頻發的形勢,同年4月,北約各國在華盛頓峰會上通過冷戰后北約的第二份戰略文件即《同盟的戰略概念》(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它們一致認為,北約在堅持既有的共同安全與互助合作外,將處理地區危機作為其主要職能。至此,北約確立了集體防御與危機處理兩大使命,也即 “第五條” 和 “非第五條” 使命。②朱立群: “北約的變化及未來發展趨勢” ,《歐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3頁。
2001年 “9·11” 事件突顯了恐怖主義襲擊的嚴重威脅,之后反恐成為北約及其盟國的主要安全使命。2010年11月北約里斯本峰會在評估新戰略環境后,出臺了題為《積極接觸,現代防務》(Active Engagement,Modern Defence)的冷戰后第三份北約 “戰略概念” 文件,它認為新形勢下北約本土遭受常規攻擊可能性大大降低,但強調仍面臨著恐怖主義襲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網絡攻擊以及能源、貿易、通訊等關鍵供應中斷的諸多新威脅。對此北約提出 “以合作促安全(Promot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Cooperation)” 的新概念,③Ian P.Rutherford, “NATO′s New Strategic Concept,Nuclear Weapons,and Global Zero,”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66,No.2,Spring 2011,pp.463-482.堅持門戶開放原則,與一切符合條件的歐洲民主國家建立廣泛的合作伙伴關系以應對新挑戰。
1.2 冷戰后北約體制的調整與轉型
作為北約的行動指南與綱領,其戰略概念文件在冷戰后的不斷更新,反映了北約試圖通過機構調整和戰略轉型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形勢。④張健: “北約新戰略概念解析” ,《現代國際關系》,2010年第12期,第19-21頁。縱觀這一改革進程,北約的轉型趨勢大致有二:
(1)在新的安全環境和外部威脅形勢下,北約旨在精簡優化其軍事指揮系統和部署,突破域外行動限制,提高軍事反應靈活性,以應對恐怖主義威脅、宗教與極端勢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網絡空間安全等多重安全挑戰。
在精簡軍事機構方面,北約設立盟軍作戰司令部,取代過去的歐洲盟軍司令部和大西洋盟軍司令部,其所轄各級司令部亦減至9個,另外設立了盟軍轉型司令部負責監督和完善盟軍的軍事改革。①許海云: “冷戰后北約體制改革的反思” ,《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2期,第45-48頁。此外,為了應對新階段其外部威脅的多樣化、威脅來源和地域范圍擴大化以及威脅的不確定性,北約于1992年奧斯陸外長會議后開始參與域外維和行動,在1993—1995年波黑戰爭中,北約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第816號決議支持聯合國維和部隊。1996年,北約組建波黑多國穩定部隊(SFOR)維護該地區和平與穩定。2002年北約各盟國于布拉格峰會一致同意建立快速反應部隊(NATO Response Force)以保障歐洲-大西洋區域的和平與安全。②“NATO Official text:Prague Summit Declaration,” NATO,Nov.21,2002,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9552.htm,訪問時間:2021年4月5日。
(2)在加強內部凝聚力和協商一致性的同時,擴大北約的戰略視野和行動范圍,強化北約在雙邊和多邊安全事務中的政治合作效能,從而構建全新的歐洲政治與安全體系。冷戰時期,作為針對蘇聯陣營的前沿防御力量,北約與華約等中東歐國家處于軍事對峙狀態。蘇聯解體后,為了提高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構建一個更加團結與穩定的歐洲大陸,北約開始向東歐國家伸出手來。③“NATO Official text:Declaration on a Transformed North At?lantic Alliance,” NATO,Jul.5,1990,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3693.htm,訪問時間:2021年5月10日。1991年12月北約成立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NACC),它成為東西歐洲首次進行協商的平臺。1994年,北約啟動 “和平伙伴關系計劃” ,與前蘇聯和中東歐27個國家建立雙邊關系。1997年,北約成立歐洲-大西洋伙伴關系委員會(EAPC)常設機構取代了之前較為松散的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充實并成為 “和平伙伴關系計劃” 的固定機制。
北約東擴是北約實現更廣泛的歐洲-大西洋政治與安全合作進程的嘗試,但隨著越來越多新成員國的加入,各方對域外行動等諸多問題出現分歧,安全構想經常淪為空談。對此,北約一方面通過大西洋理事會進行政治磋商,另一方面拓展深化與歐盟、歐安組織、西歐聯盟等北約架構外安全協商機制合作,從而強化自身的組織職能。④同①,第49頁。在北約2010年新戰略概念文件《積極接觸,現代防務》中,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將集體防御承諾、軍事能力和政治協商共同列為北約的三大持久性支柱。⑤Anders Fogh Rasmussen, “The New Strategic Concept:Active Engagement,Modern Defence,” NATO,Oct.8,2010,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66727.htm?訪問時間:2021年4月5日。
1.3 當前北約安全形勢新變化與 “戰略概念” 更新的需要
冷戰后北約出臺的三份 “戰略概念” 文件針對的外部威脅主要是域外地區性沖突和國際恐怖主義襲擊,而當前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北約面對的安全形勢日趨復雜化,一方面各盟國面臨著東部烏克蘭危機爆發后俄歐斗爭范圍擴大、南部恐怖主義威脅依然存在以及各種非傳統安全的挑戰,另一方面,2020年全球性新冠疫情引發的盟國經濟衰退正在進一步影響北約凝聚力和戰斗力。具體來說,與北約現行指導性文件2010年戰略新概念所針對的安全形勢相比,當前北約外部安全環境所面臨的主要威脅、包括所發生的顯著變化主要體現在:
(1)北約東部和南部防區爆發的新型非傳統混合戰爭方式,呈現出了新特征和危險性。在東部,2014年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并對烏克蘭東部進行軍事干預,與傳統常規作戰方式不同,俄羅斯此次采取了多種作戰方式,戰爭界限也更加模糊。在南部,近年來日益惡化的西亞、北非局勢和敘利亞內戰、利比亞沖突引發的難民危機挑戰著歐洲國家的非傳統安全。與此同時,歐洲盟友飽受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的侵襲, “ISIS” 極端勢力肆虐,盡管之前北約已經開始關注恐怖主義活動威脅,但仍缺乏具體的作戰目標和戰略部署。
(2)大國競爭持續加劇。近年來,由于美俄關系轉冷,2019年雙方分別暫停履行《中導條約》導致地區軍備控制遇阻,軍備競賽趨勢顯現,核武器競爭加劇。與此同時,中國軍事現代化快速發展,積極參與對北極和太空領域的開發并與俄羅斯頻繁展開軍事合作,引起了北約的擔憂。長期以來,北約一直視俄羅斯為主要敵人,2014年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的《俄羅斯軍事學說》總統令視北約為俄頭號軍事威脅①Russia Security Paper Designates NATO as Threat,” BBC News,Dec.31,2015,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5208636,訪問時間:2021年6月15日。, “北約2030” 改革報告也將俄羅斯視為北約的主要軍事威脅。
(3)聯盟內部政治分歧加大、美國領導力下降等因素引發自身凝聚力下降。近期以來,包括匈牙利歐爾班(Orbán Viktor)政府、波蘭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Law and Justice party)和土耳其在內的多個成員國的國內政治動向引起北約精英的關注和擔憂。與此同時,北約領導者美國在特朗普任期內國內右翼民粹主義盛行,日益分裂的美國社會和種族問題使得新任拜登政府短時間內也疲于應對,而美歐在經貿和對華問題上一直爭議不斷,諸多因素使得北約內部凝聚力持續下降。
針對以上新變化和新威脅,北約組織認為現行的北約2010年戰略概念關于 “歐洲-大西洋地區局勢和平,北約本土遭受常規安全威脅程度較低”②“NATO Official text:Active Engagement,Modern Defence,” NATO,Nov.19,2010,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68580.htm,訪問時間:2021年1月4日。的判斷已顯過時;北約對非常規作戰方式、戰后復原能力、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威脅關注不夠;對北約東部和南部防區動蕩缺乏有效應對。另外,北約及其盟國在情報共享、態勢感知、快速決策和東翼防御等方面都認識不足。冷戰后北約各成員國在不斷變化的戰略環境中尋求新共識,制定 “戰略概念” 來應對新的安全挑戰,因此 “戰略概念” 的更新對于重塑北約,以不斷應對未來威脅、明確未來走向具有重大指導性價值。鑒于此,2020年10月,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在 “全球安全論壇2020” 中公開提出,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安全環境,現在應該為北約制定新的 “戰略概念” 。③Jens Stoltenberg, “Keynote Speech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t the Global Security 2020 Bratislava Forum,” NATO,Oct.7,2020,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78605.htm,訪問時間:2021年6月10日。
二、 “北約2030” 改革報告關于北約新一輪變革的思路
2020年11月25日,北約組織發布了 “北約2030:團結面對新時代” (NATO 2030:United for a New Era)改革報告,旨在審視北約今后如何加強聯盟內部團結、政治協商和自身的政治角色。2021年3月25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談到這份報告的背景時指出: “世界正在變化,我們面對著更多的網絡攻擊,更殘暴的恐怖主義和核武器的擴散,隨著中國崛起、全球力量平衡的轉移以及復雜安全環境的挑戰,北約需要適應這種變化” 。 “北約2030” 改革報告出臺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謀劃更新北約戰略概念,即為醞釀升級版北約新戰略概念做準備。④見2021年3月25日斯托爾滕貝格與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師生交流時所發表的講話《關于 “北約前途” 的談話》(Conversation on “The Future of NATO” with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nd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NATO,Mar.25,2021,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82812.htm,訪問時間:2021年4月15日。2021年6月召開的北約布魯塞爾峰會同意了該報告,并稱其為北約應對 “現存的、新的和未來的威脅和挑戰” 提供了清晰的 “指導方針” 。⑤North Atlantic Council,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Issued by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in Brussels,” NATO,Jun.14,2021,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訪問時間:2021年6月10日。
“北約2030” 改革報告由北約組織多領域專家共同參與的研判團隊(Reflection Group)起草,分為 “愿景及主要論斷、政治與安全環境和政策建議” 三部分,具體來看, “北約2030” 改革報告所涉及的北約新一輪變革的思路如下①“NATO 2030:United for a New Era,” NATO,Nov.25,2020,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pdf,pp.22、53-55、16-17,訪問時間:2021年4月15日。:
2.1 進一步強化北約的政治角色
冷戰時期,北約作為集體防御的軍事聯盟組織旨在對抗蘇聯陣營的入侵。然而,成立不久北約就開始試圖擺脫純粹軍事聯盟的性質,1956年北約組織三人委員會(Wise Men Group)就如何改善和擴大北約在非軍事領域的合作提出建議,旨在發展規模更大的大西洋共同體。冷戰結束后, “9·11” 恐怖襲擊使得北約試圖在軍事和政治議程中超越傳統防區歐洲-大西洋地區的防御任務和政治穩定。2014年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后,北約在擴大聯盟內部磋商機制、加強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東部伙伴的接觸等政治領域均取得了新突破。在阿富汗問題上,北約也一直在行動規劃、預算發展和后勤保障方面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隊和維和任務。
可以說北約在后冷戰政治安全環境下一直試圖通過預防沖突、危機管控和維和行動將自身重塑為政治、軍事雙重同盟。 “北約2030” 改革報告對北約政治性改革也給予高度關注,指出當下北約一方面面臨著恐怖主義帶來的南部及外圍地區的不穩定,另一方面面臨著諸多人為和自然風險帶來的非國家行為體威脅。盟國威脅認知的不同使得各方就戰略優先事項難以協商一致,北約堅定地追求通過政治協商減少各盟國威脅認知上的差異、最終達成戰略共識。因此,當下北約迫切需要加強政治融合,尤其是在其所謂的俄羅斯和中國帶來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 “雙重挑戰” 的形勢下。
組織機構改革是北約政治性改革的重要環節。北約是當今制度化程度最高的聯盟行為體,但特朗普任期內美國外交政策與北約盟國缺乏戰略協調,美國與土耳其和歐洲盟友在諸多領域存在分歧。 “北約2030” 改革報告強調各盟國必須重視北大西洋理事會,使之成為重大戰略和政治問題磋商的真正平臺。隨著地緣戰略競爭的加劇與威脅形式多樣化發展,北約內部需要更頻繁地舉行北約部長級會議,并在適當時擴大這些會議的規模。各盟國要努力使其外交政策與北約保持一致,各盟國外交部長可以定期會晤以評估當前階段北約的健康和發展。
2.2 強調非傳統安全因素和新興顛覆性技術研發,突出應對中俄安全 “挑戰”
“北約2030” 改革報告指出,2010年以來北約的外部安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恐怖主義到全球大流行病、氣候變化和移民問題帶來的跨國威脅和風險繼續對北約構成重大安全挑戰,網絡空間和太空技術成為國際競爭新領域。對此,北約一方面呼吁加強自身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大流行病等新風險的能力,并將這些挑戰納入其危機管控規劃。另一方面北約明確了未來十年,包含生物科技、太空技術、量子技術和人類增強技術在內的新興顛覆性技術(EDTs)將在全球安全環境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新技術將會廣泛應用于超高音速導彈、太空作戰和混合作戰中。隨著中、俄在這些領域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北約國家要在新技術研發方面繼續保持優勢。
除了應對新出現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和加大投入新興顛覆性技術研發以外, “北約2030” 改革報告認為當前全球安全環境的主要特征仍是地緣競爭的重新崛起。在歐洲-大西洋地區,新的安全挑戰以俄羅斯軍事入侵的形式出現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對此北約要繼續增強東翼防區的威懾和防御力量。報告進一步指出由于當前的地緣戰略競爭呈現出混合作戰和灰區作戰新特征,傳統的沖突邊界逐漸被侵蝕、私營軍事公司的加入模糊了平民與軍事人員的界限,虛假信息和顛覆活動分布廣泛,北約不得不花費越來越多的精力發展對抗混合作戰的政治和非政治性工具。
長期以來,俄羅斯一直被北約視為最大的威脅對手,北約早在 “2010戰略新概念” 中就意識到俄羅斯將以 “混合化” 的入侵手段影響北約成員國。2019年隨著美俄相繼退出《中導條約》,美俄雙方對立局勢進一步加劇。 “北約2030” 改革報告重申了對俄威懾和對話的雙軌模式,即一方面要提高俄羅斯冒險主義和侵略行為所付出的代價,另一方面擴大與莫斯科的政治接觸,尤其在軍備控制和降低風險領域。與此同時,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構成了北約所謂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 “挑戰” ,本文第4節將對此進行專門論述。
2.3 以亞太為重點發展全球伙伴關系①
“NATO 2030:United for a New Era,” NATO,Nov.25,2020,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pdf,p.57,訪問時間:2021年4月15日。
北約自成立以來一直堅持 “門戶開放” 政策,即任何有潛力為北大西洋地區安全做出貢獻的國家都有資格成為北約成員國。現階段隨著2017年黑山共和國和2020年北馬其頓共和國的加入,北約會員國數量增至30個,組織結構也不斷擴大。與此同時, “和平伙伴關系計劃” 是北約在傳統防區之外更大范圍進行合作和政治磋商的重要途徑,北約試圖借此協助伙伴關系國提高自身防御能力,同時提升后者與自身的軍事互操作性。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6月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 “北約2030倡議” 中強調北約要發展亞太伙伴關系,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志同道合的國家展開密切合作以維護利于自身的全球規則和制度,包含制定網絡和太空領域、全球軍備控制、裁軍和新技術的規范標準以及推廣自由民主價值理念。②Jens Stoltenberg, “NATO2030-Strengthening the Alliance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world,” NATO,Jun.8,2020,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76197.htm,訪問時間:2021年4月15日。實際上,北約既有的 “全球合作伙伴倡議” 可以追溯至2006年里加峰會提出的 “全球化北約”③Ivo Daalder and James Goldgeier, “Global NATO,” Foreign Affairs,Vol.85,No.5,2006,p.110.,當時北約試圖通過構建亞太地區伙伴關系將歐洲和亞太地區連成一片。鑒于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和日本都參與了北約的互操作性架構(Interoperability Platform)、能夠更便捷協調地參與北約主導任務,以上國家均屬倡議國家。除此之外,與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地中海對話和與海灣國家開展協作的伊斯坦布爾合作倡議也是北約確保其南翼安全的重要制度性安全合作框架。
由此可見,當下北約正試圖在歐洲和亞太地區利用和平伙伴關系參與地緣政治競爭。在此過程中,北約不斷拓寬盟國與伙伴關系的戰略協商,審慎、積極地通過和平伙伴關系塑造地區安全環境,履行其核心任務及使命。
三、北約新一輪變革的制約因素
2018年7月北約布魯塞爾峰會是北約歷史上分歧最大的一次會議。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熱衷于極限施壓的談判風格逼迫下,美歐雙方在貿易關稅、對伊 “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 、巴以和談、德國進口俄羅斯天然氣、氣候變化等諸多領域和問題上陷入分裂,美歐關系趨于歷史低點。2021年初民主黨拜登政府上臺后提出重新加強跨大西洋關系,并尋求在G7、北約等既有西方制度框架內與歐洲盟國取得共識。然而,美歐分歧難以掩蓋,其所反映出的雙方結構性矛盾也為北約新一輪變革帶來種種挑戰。
3.1 北約改革與歐盟機制重疊,形成潛在競爭關系
自冷戰形成以來,北約一直是歐洲安全和美歐關系的主要平臺,冷戰后北約和歐盟的雙東擴進程給彼此帶來了多重壓力,盡管雙方努力構建伙伴關系、共同推進歐洲安全合作,但在有關該領域的職能和主導權等諸多問題上彼此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潛在競爭關系,④馮存萬: “北約戰略擴張新態勢及歐盟的反應” ,《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2期,第24頁。這是新一輪北約變革所難以回避的一個障礙。
首先,北約和歐盟的機制重疊體現于成員國的重疊。冷戰結束后,北約和歐盟都進行了擴張行動。截止今日,在北約的30個成員國中加拿大、美國、英國、冰島、挪威等9個國家不屬于歐盟成員國,在歐盟的27個成員國中奧地利、塞浦路斯、芬蘭等6個國家不屬于北約成員國。北約和歐盟成員國的分離性重疊使得二者選擇偏好產生分歧,安全合作成本提高。
其次,現階段應對政治、外交、經濟等混合模式威脅成為北約和歐盟面臨的共同問題①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se and Security(ICDS)Report, “A New Era of EU-NATO Cooperation:How to Make the Best of a Marriage of Necessity,” ICDS,May.13,2017,https://icds.ee/wp content/uploads/2018/ICDS_Report_A_New_Era_of_EU-NATO.pdf,訪問時間:2021年6月15日。,這引發了兩者的功能性重疊。2007年10月歐盟各成員國批準的《里斯本條約》試圖通過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CSDP)綜合使用民事、軍事手段進行域外維和行和預防沖突,并根據《聯合國憲章》實施聯合裁軍、人道主義救援、軍事咨詢與援助、危機處理等國際安全行動,②Johan Andries, “The 2010 Belgian EU Presidency and CS?DP,” Egmont Security Policy B rief,No.21,April 2011,pp.1-7.而 “北約2030” 改革報告也強調通過軍事、政治、經濟與外交手段履行集體防御、危機管理、合作安全三大核心任務,二者在安全方面的界限已逐漸模糊。
最后,二者的機構重疊。1999年科索沃戰爭使得歐盟意識到自身防務力量的缺乏,歐盟理事會一致通過組建快速反應部隊,2003年10月北約也成立了快速反應部隊,二者作戰目標幾乎相同。與此類似,歐盟理事會政治與安全委員會與北約理事會都執行相似的政治軍事職能。因此可預見,隨著北約的進一步政治性轉型,其與歐盟的機構重疊的強化也似乎在所難免。
3.2 對中、俄安全認知難以協調一致
共同的威脅與安全認知是聯盟形成、轉型的基礎,雖然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多次表示應對俄羅斯與中國崛起已成為北約戰略目標的重中之重,但其呼聲仍然掩蓋不了北約內部的安全認知裂痕。
在對俄安全認知上,北約內部立場不一。與波羅的海三國視俄羅斯為威脅不同,德國、法國始終保持與俄羅斯的密切接觸。德國與俄羅斯簽訂的 “北溪二號” 天然氣管道項目讓歐洲對俄羅斯產生了能源依賴,這為歐洲能源供給帶來安全隱患。2019年12月,土耳其拒絕批準北約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的軍事防御計劃,以威脅北約承認其認定的 “庫爾德人民保護部隊” (Kurdish People’s Protection Units)為恐怖主義組織的立場。③Patric Wintour, “Turkey Denies Blackmailing NATO Over Baltics Defence Plan,” The Guardian,Dec.3,2019,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dec/02/turkey-denies-blackmailingnato-over-baltics-defence-plan,訪問時間:2021年1月4日。在此階段,俄羅斯與土耳其達成雙邊協議對土敘邊境展開聯合巡邏,并就出售S-400地對空導彈防御系統和引進蘇-35戰機進行談判,俄土關系的進展進一步強化了北約盟友的擔憂。
在對華認知上,與中美關系日益緊張相比,歐洲雖然總體上保持與美戰略同盟關系,但仍視中國為歐洲的重要貿易伙伴,歐中雙方緊密的互利經貿關系使歐洲對中美戰略競爭中的立場充滿不確定性,這也引發了歐洲內部對華認知難以協調的難題。例如,旨在維持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波羅的海國家刻意幫助美國渲染 “中國威脅” ,而希臘與意大利等東歐與南歐國家則對中國投資抱有較大期望。④Tim Rühlig, “Exposing the fragility of EU-China Rela?tions,” East Asia Forum,May 23,2020,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5/23/exposing-the-fragility-of-eu-china-relations/,訪問時間:2021年9月6日。2018年美國發布《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宣布美國將對華戰略競爭列為主要優先事項,通過地緣政治、金融、經貿、意識形態與軍事等方面全面打壓中國。⑤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May 15,2018,https://www.congress.gov/115/crpt/hrpt676/CRPT-115hrpt 676.pdf,訪問時間:2021年8月20日。歐洲在對華立場上雖然整體上視中國為 “系統性競爭對手” ,⑥Luis Simón,Linde Desmaele and Jordan Becker, “Europe as a Secondary Theater?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s European Strateg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Vol.15,No.1,Spring 2021,pp.90-115.但隨著中歐經貿與基礎設施投資的合作,雙方依賴程度逐步加深。因此,當美國不斷要求北約歐洲盟國與中國保持戰略距離甚至脫鉤時,多數歐洲國家不愿在科技與經濟生態上與中國徹底脫鉤,相反,視中國為聯系緊密的合作和磋商伙伴。
3.3 聯盟范圍擴大,軍費分擔問題難以解決
隨著北約追隨美國以亞太為重點發展全球伙伴關系,聯盟范圍的擴大可能會對北約自身團結與合法性造成不利影響,①吳昕澤、王義桅: “北約再轉型悖論及中國與北約關系” ,《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10期,第33頁。北約的軍費分擔問題也因此變得更加困難。雖然在2014年北約威爾士峰會期間,北約各盟國就軍費分擔問題達成一致,即: “各成員國將國內生產總值(GDP)2%用于國防開支,其中20%資金用于大型設備等軍事能力建設” ,②Kristina Daugirdas and Julian Davis Mortenson, “Trump Ad?ministration Criticizes NATO Members for Failing to Meet Defense Spending Guidelin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11,No.3,2017,pp.756-64.但近年來美歐雙方圍繞聯盟內部責任分擔問題的爭端愈演愈烈。2018年7月北約布魯塞爾峰會召開前夕,特朗普指責 “美國承擔了北約90%的經費,而歐洲眾多盟國在享受每年對美貿易順差的同時,軍費支出還未達到國內生產總值2%的最低標準” 。③Jon Harper, “U.S.Spending About$36 Billion on NATO,” National Defense,Vol.103,No.778,September 2018,p.13.隨著北約的重心一定程度上趨向于向亞太地區轉移,鑒于歐洲國家除英、法之外幾乎在亞太地區沒有防務利益需求,軍費分擔矛盾勢必再次加劇。
為了安撫長久以來一直負擔著大約70%的北約軍費開支④“Defence Expenditure of NATO Countries(2013-2020),” NATO,Mar.16,2021,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0/pdf/pr-2020-104-en.pdf,訪問時間:2021年6月15日。的美國,歐洲盟國試圖調整它們對北約共同預算的貢獻以實現更公平的責任分擔。例如在北約共同基金問題上,根據2021—2024年成本分攤公式,北約計劃將美國共同預算份額從大約22%降至16%與德國持平,以此增加歐洲和加拿大的分攤份額。⑤“NATO summit:What does the US Contribute to NATO in Europe?” BBC News,Jun.15,2021,https://www.bbc.com/news/world-44717074,訪問時間:2021年6月15日。但美國仍然認為北約共同防御政策使得歐洲對自身防務缺乏足夠重視,指責歐洲盟友 “搭便車” 。特別是在當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北約國家可能會重新調整財政優先事項,國防支出難以達到2%的標準,甚至維持目前水平都將變得更加困難。此外,經濟因疫情而停滯造成各國國內生產總值萎縮,即使履行了滿足2%的承諾,實際軍費支出仍將縮減。如果北約成員國繼續以2%標準來要求各盟國,勢必會進一步加劇防務分擔糾紛,損害北約內部凝聚力,最終危及其應對外部安全威脅的能力。
四、北約戰略轉型對中國的現實意涵
近年來,隨著北約參與阿富汗維和、伊拉克安全部隊培訓與亞洲反恐行動,其勢力已遍布地中海、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等中亞地區。北約東擴及全球伙伴關系進程和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日益增長使得雙方安全利益發生交叉和重合,逐漸成為彼此關注的焦點。 “北約2030” 改革報告中將中國設置為北約新戰略重點,而2021年6月的北約布魯塞爾領導人峰會會議公報又直指中國對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與聯盟相關的領域” 造成了 “系統性挑戰” ,⑥North Atlantic Council,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Issued by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in Brussels,” NATO,Jun.14,2021,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2021年9月6日。毋庸置疑,它們發出的信號具有深刻的現實意涵。
4.1 北約對所謂 “中國挑戰” 的認知程度不斷提高
“北約2030” 改革報告中對中國崛起進行了詳細論述,認為中國近年來在洲際導彈、核潛艇、航母以及太空領域取得了競爭優勢,并且從北極到地中海和大西洋區域與北約產生了全面接觸。⑦“NATO 2030:United for a New Era,” NATO,Nov.25,2020,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pdf,p.27,訪問時間:2021年8月23日。鑒于此,該報告將中國界定為北約戰略新重點,這反映出北約成員國對中國崛起這一地緣政治變化及日益增長的海外投射能力的擔憂。具體而言:
(1)擔憂中國軍事、科技發展削弱北約軍事優勢和內部凝聚力。雖然中國對任何北約盟國都不存在安全威脅,但近些年中國在5G和人工智能領域的先進水平使其逐漸占據了歐洲某些領域產業鏈、供應鏈主導地位,北約擔心這會對聯盟凝聚力和互操作性帶來影響。2018年中國年度研發支出為4620億美元,已超過歐洲所有研發預算的總和。①“Gross Domestic Spending on R&D 2000-19(indicator),” OECD,Apr.2,2020,https://data.oecd.org/rd/gross-domesticspending-on-r-d.htm,訪問時間:2021年4月2日。北約擔心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發支出和關鍵技術的投資日益侵蝕北約現有的軍事技術優勢。此外,美歐雙方也擔心在與中國技術競爭中采取不同的評估標準和規則,將會導致北約內部的技術系統脫鉤問題。例如,如果部分北約國家選擇華為通信設備部署其5G網絡,北約可能會將其排除在聯盟通信和情報系統之外。最后,北約擔心中國憑借其供應鏈對北約武器系統造成影響并削弱其作戰能力,2019年6月美國部分媒體就質疑其F-35戰機的核心電路板來源于中資公司是否會引發安全隱患。②Zak Doffman, “U.S.and U.K.F-35 Jets Include‘Core’Circuit Boards from Chinese-Owned Company,” Forbes,Jun.15,2019,https://www.forbes.com/sites/zakdoffman/2019/06/15/chine?se-owned-company-supplies-electronics-on-u-s-and-u-k-f-35-fighter-jets/,訪問時間:2021年9月12日。
(2)擔憂中國在歐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影響北約作戰機動性和行動力。鑒于中國投資希臘比雷埃夫斯港(Port of Piraeus)后,2017年6月希臘反對歐盟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一份批評中國人權記錄的共同聲明,③Robin Emmott and Angeliki Koutantou, “Greece Blocks EU Statement on China Human Rights at U.N.,” Reuters,Jun.18,2017,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u-un-rightsidUSKBN1990FP,訪問時間:2021年9月12日。北約擔心中國通過中東歐國家的17+1合作項目和 “一帶一路” 倡議與歐洲各國政府雙邊談判,利用其對歐洲成員國(例如黑山和意大利)的經濟影響力,迫使后者不加入北約共識,進而影響北約內部團結。近年來隨著中國海軍開始在地中海和波羅的海地區開展軍事訓練并參與聯合軍演,中國在歐洲航道沿線和港口廣泛進行基礎設施投資。除了地中海沿岸的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意大利瓦多利古雷港(Port of Vado Ligure)、西班牙瓦倫西亞諾圖姆港(Noatum Port in Valencia),大西洋海域的西班牙畢爾巴鄂港(Port of Bilbao)和比利時安特衛普港(Port of Antwerp),中國最近也推動了在波羅的海立陶宛的克萊佩達港(Klaipeda Port)的投資建設和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至匈牙利布達佩斯(Belgrade-Budapest)的高速鐵路項目。美國《外交政策》刊文認為,當下中國持有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區大約10%的歐洲港口運輸能力,中國通過港口、鐵路與公路將中歐緊密連接在一起推行其 “一帶一路” 倡議,勢必會削弱北約在該地區的作戰能力。④Keith Johnson, “Why is China Buying up Europe’s Ports?” Foreign Policy,Feb.2,2018,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2/02/why-is-china-buying-up-europes-ports/,訪問時間:2021年9月12日。
(3)擔憂中俄之間特別是在安全和軍事領域的密切合作。自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引發俄歐關系惡化以來,俄羅斯加強了其 “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 戰略。2017年中俄首次在波羅的海展開聯合軍演,2019年6月,中俄雙方將兩國關系提升為 “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這些都引起了北約國家的警覺和單方面解讀,可以說北約一直以來對中俄雙方的國防和安全合作 “耿耿于懷” 。⑤Janka Oertel, “NATO’S China Challenge,” Whitehall Papers,Vol.95,No.1,2019,pp.74-75.除此之外,北約也擔心中俄雙方未來可能通過情報共享或者利用中國在歐洲的經濟影響力和基礎設施建設影響北約成員國遏制俄羅斯侵略的立場。⑥Andrea Kendall-Taylor and David Shullman, “A Russian-Chinese Partnership Is a Threat to U.S.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May 14,2019,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5-14/russian-chinese-partnership-threat-us-interests,訪問時間:2021年7月19日。
4.2 未來北約對中國及所謂 “中國挑戰” 的定位與應對
在當今國際戰略環境下,中美大國競爭很大程度上主導著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對于北約的新一輪變革,值得警惕的是,隨著中美關系持續緊張,北約是否會論為美國參與大國競爭的工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未來北約如何看待中國及其所謂的 “中國挑戰” 值得探討。
(1)伴隨著中國 “一帶一路” 倡議的實施,北約將不會視中國為俄羅斯那樣的直接威脅,而是既非 “敵人” 也非 “伙伴” 的競爭對手。一方面,中國的 “一帶一路” 倡議為歐亞大陸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和中歐貿易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部分東歐和南歐國家受益于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波蘭、羅馬尼亞等國家均視中國為重要的貿易和投資伙伴。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在歐洲通信、港口、橋梁等諸多核心領域投資,北約對自身傳統勢力范圍愈加警惕,應對中國成為塑造北約當前安全認知的重要外在變量。北約期望通過呼吁關注中國崛起帶來的 “挑戰” ,讓聯盟內部更加團結,為新一輪變革找尋出路。應對中國崛起也逐漸成為北約下一輪戰略轉型和擴大的重要依據,鑒于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分量,其與全球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北約將不再以歐洲和北美為中心,而是朝著全球化的方向,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通過多種靈活方式協調合作,共同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所謂 “挑戰” 。①Jens Stoltenberg, “Strengthening the Alliance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World,” NATO,Jun.8,2020,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76197.htm,訪問時間:2021年8月5日。
(2)由于中美競爭關系的加劇,北約在新地緣政治環境中的角色和作用會得以增強。拜登執政以來美國試圖憑借北約這一跨大西洋關系核心紐帶獲取應對中國崛起的政治支持,而應對中國崛起也是北約同亞太地區國家開展廣泛合作,從而推動北約力量 “全球化” 的重要契機。基于此,美國試圖在多領域聯合北約的歐洲盟國、協調對華政策,其國內不乏制定跨大西洋路線應對中國崛起的聲音,即通過修復美歐雙邊關系,在貨貿服貿協定、多邊出口管制、商業情報共享和尖端科技領域持續保持對華優勢。②Luis Simón,Linde Desmaele and Jordan Becker, “Europe as a Secondary Theater?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s European Strateg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Vol.15,No.1,Spring 2021,pp.90-115.
(3)美國試圖聯合北約盟國在5G通信領域和高新軍事技術對華出口管控實現區域產業鏈和供應鏈的 “去中國化” 。當前5G已經成為中美競爭的戰略優先項,美國以國家安全威脅為由先后對中國華為和中興公司的5G通信設備施加禁令,并公然要求歐洲等盟友將中國投資公司拉入黑名單,在重要通信領域擺脫對中國的供應鏈依賴。2019年2月,時任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推動北約將5G列入議程,并呼吁美國所有安全合作伙伴警惕中國通信公司對北約通信技術和國家安全造成 “挑戰” 。③Jens Stoltenberg, “Speech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NATO,Feb.19,2021,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81696.htm,訪問時間:2021年8月8日。5G技術是北約試圖保持技術優勢以維護其價值觀念和規范,團結協作擺脫中國技術影響力的首場較量。美國將經貿和科技問題政治化、安全化的做法實質上就是推進區域發展的 “去中國化” 進程,這顯然威脅著中國和北約關系的健康發展。
4.3 中國的應對之策
2021年北約布魯塞爾峰會聯合公報聲稱的中國對北約造成 “系統性挑戰” 是北約領導人首次集體表明對中國的強硬立場。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對中國長久以來和平發展的詆毀,讓人不得不懷疑其堅持事實基礎之上與中方開展坦率對話的誠意。習近平總書記近期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和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中多次指出,面對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統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保持戰略定力與戰略自信,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④“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2018年6月2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4060074048442582&wfr=spider&for=pc,訪問時間:2021年6月8日; “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新華網,2021年2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2/20/c_1127120082.htm,訪問時間:2021年6月8日。這為我們思考如何應對北約新一輪變革對中國的影響指明了方向。
從近年來的跨大西洋關系來看,無論是特朗普任期內的北約責任分擔爭議、美國對歐戰略收縮,還是拜登上臺后追求重振美歐關系、修復聯盟合作,美歐關于北約變革和轉型的謀劃都繞不開中國議題。同時,北約自身也不斷加強對中國的防范意識。斯托爾滕貝格強調盡管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為歐洲各國帶來了發展機會,但由于雙方意識形態差異,北約對中方不斷增長的國防預算和軍事能力表示擔憂,中國與北約在高新科技和人權領域的諸多分歧也使得雙邊關系充滿挑戰。①Deutsche welle, “Joe Biden,Jens Stoltenberg Meet Ahead of NATO Summit,” NATO,Jun.8,2021,https://www.dw.com/en/joe-biden-jens-stoltenberg-meet-ahead-of-nato-summit/a-57809195,訪問時間:2021年9月4日。因此,我們對于北約與中國關系的復雜性和矛盾的長期性應該具有清醒的認識和理性的預判。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應始終不渝地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在爭取穩住中美關系的基礎之上積極運籌好中美、中歐的多領域合作和多層級良性互動,在明確美國試圖利用北約獲取大國競爭優勢、北約視中國為 “系統性競爭對手” 的雙重前提下強調雙方合作共贏的必要性。長期以來,中國堅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與北約也不存在直接的地緣政治矛盾,中國可以通過與北約各盟國深化合作,強化彼此的積極認知。北約現在還未將中國視為敵人,而且不是所有北約盟國都愿意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工具,也不排斥對華接觸,這為中國與北約及其相關盟國在國際事務的合作上留有余地和空間。近些年來北約通過打擊索馬里海盜和執行國際維和行動為中國能源進口、海上貿易航線和海上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中國也意識到北約是當今全球安全的供給者和維護者,雙方應繼續在應對全球疫情、打擊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國際軍控和裁軍領域展開對話與合作。此外,也要敦促北約在中美大國競爭中以積極、客觀、開放的態度看待中國,同中國一道堅持和平發展之路,多做有利于地區穩定和國際安全的努力,警告其冷戰思維違背人類共同利益,沒有前途。
五、結 語
自北約2010年 “戰略概念” 出臺以來,其外部環境日益復雜嚴峻,內部矛盾交織,在北約精英看來,改革已經刻不容緩,而 “北約2030” 改革報告的出臺為其新一輪變革提供了 “指導方針” 。總體來看,美國及其歐洲盟國仍將作為冷戰產物的北約視為跨大西洋安全的基石,在大國競爭趨于激化的背景下, “北約2030” 改革報告強調北約必須進行戰略目標與組織機構的改革以適應國際政治和安全形勢變化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北約繼續將俄羅斯視為歐洲乃至全球安全的威脅并不斷加以強化,這是北約為自身存續尋找合法性的借口;另一方面,在將俄羅斯當作未來十年的主要對手之外,北約還首次提出中國崛起對其造成了 “系統性挑戰” ,主張通過政治協商凝聚共識、廣泛聯合所謂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實現北約的亞太和全球轉型。顯然,北約的這一動向與美國拜登政府上臺后恢復和加強與歐洲盟國的關系有著密切聯系,其極力拉攏盟友試圖共同對中國進行封鎖和打壓以維持其世界霸權地位。
因此,我們在考察北約新一輪變革時需要保持應有的防范意識,警惕未來一段時期內美國會不斷施壓北約盟友在中美競爭中選邊站,與中國保持距離甚至全面脫鉤。近期一些北約國家頻繁派遣艦船穿航臺灣海峽或來南海水域活動、罔顧事實真相以新疆人權為借口單方面向中國個人和實體提出制裁,北約的對華姿態似乎越來越強硬。我們對此要保持高度警惕,未雨綢繆,關注北約的亞太化發展態勢。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此次北約布魯塞爾領導人峰會仍然聲稱與中國保持建設性對話,期待中國與北約就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反對恐怖主義等議題進行廣泛接觸,提高各自外交政策透明度以增進互信,消除分歧。①North Atlantic Council, “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issued by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in Brussels,” NATO,Jun.14,2021,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訪問時間:2021年9月18日。總之,我們需要 “不畏浮云遮望眼” ,關注北約新一輪變革將對國際格局演變的影響,在戰略和戰術層面上做好充分應對準備,力爭中國與北約的關系能夠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