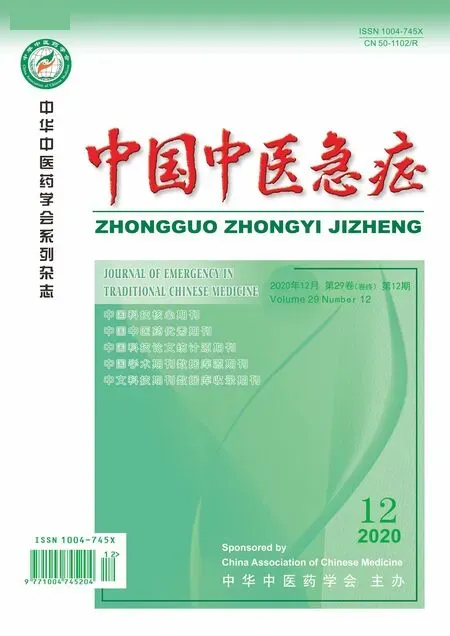“動留針術”治療危重癥患者合并腹腔高壓的臨床觀察*
姚 瑤 張 彥 趙 慧 李 莉 廖焦魯 樊 藝△ 王毅剛
(1.重慶市中醫院,重慶 400021;2.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 長沙 410208)
腹腔壓力(IAP)是指腹部封閉腔隙內穩定狀態下的壓力,主要由腹腔內臟器的靜水壓力產生,隨著呼吸節律和腹壁阻力而改變[1]。腹腔高壓(IAH)若持續發展,可能會發展為腹腔間隔室綜合征(ACS),導致患者出現嚴重的并發癥,甚至死亡[2]。世界腹腔間室綜合征聯合會(WSACS)在2013版最新的專家共識和診治指南中將IAH定義為持續或反復的IAP病理性升高≥12 mmHg[3]。1項包括了5個國家13個ICU的前瞻性研究報道,在ICU中IAH和ACS的發生率分別為32.1%和4.2%[4],并且還有研究顯示危重癥患者合并IAH/ACS后病死率明顯升高,可達30%~80%[5]。重癥患者IAP升高在臨床很常見,被認為是危重癥患者繼體溫、血壓、心率、呼吸及血氧飽和度之后的第6大生命體征[6],也是評估預后的重要指標之一,是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7-8]。現將本院重癥醫學科采用中西醫結合治療危重癥患者合并IAH情況報道如下,以探討“動留針術”在治療IAH中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1)納入標準:由各種原因導致腹腔高壓,且符合WSACS中IAH標準[3];APCHEⅡ評分高于15分;年齡≥18周歲且≤70周歲;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2)排除標準:有壓力測量禁忌證(神經性膀胱、膀胱損傷、膀胱痙攣等)者;癲癇患者;已進行外科手術干預如開腹減壓、腹腔鏡治療者;腹腔或腹膜后巨大占位性病變(占位腫塊直徑>10 cm)者;妊娠或哺乳期女性;針灸或電針禁忌證者;就診時已進行針灸治療者。3)分級標準:本次研究以膀胱壓來表示腹腔內壓(IA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