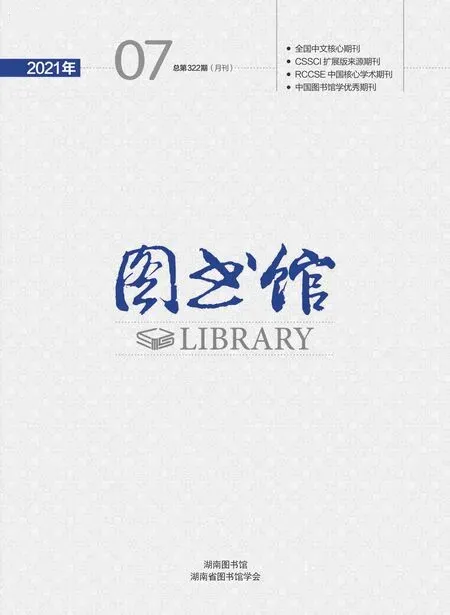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發掘的探索與實踐*
耿洪利
(河北師范大學 石家莊 050024)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史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史學資料開始進入學者研究視野。然而,對于有限的史學資料來說,在研究不斷深入的情況下,不少學者感嘆可供史學研究的材料,特別是新的史學材料日益匱乏。對此,孫繼民先生在其《公文紙本:傳世文獻最后一座待開發的富礦》一文中曾指出:“我們還有一筆非常豐厚卻基本不為人所知而處于待開發狀態的文化遺產和文獻資源,這就是蘊藏于我國傳世典籍文獻中的公文紙本文獻。”[1]
有關公文紙本的概念,在版本學界和目錄學界已有界定,孫繼民先生在此基礎上又對其進行了補充,“對‘公文紙印本’概念的使用還需要有一個補充說明,即除了‘公文紙印本’之外,還應該有‘公文紙抄本’的概念,即古人利用公私廢舊紙張背面抄寫的古籍,公文紙抄本雖然極少,但畢竟存在(詳下),應視為‘公文紙本’之一類。”[1]然,筆者偶見《〈文苑英華〉版本裝幀拾遺》一文,文中提到:“在參與點藏和鑒定沈陽師范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時,發現其中的明隆慶元年(1567)刻,隆慶六年(1572)、萬歷六年(1578)、萬歷三十六年(1608)遞修本《文苑英華》,具有鮮明的特色和重要的版本裝幀價值……其重要發現是,這部《文苑英華》是利用明代萬歷年間,福建官府當時廢棄的公文紙作書皮襯紙托裱印制而成的。”[2]2015年6月,筆者隨同孫繼民先生赴沈陽進行了實地查閱,得以見到該書真相。類似的情況在重慶圖書館藏《冊府元龜》亦有體現,故孫繼民先生在公文紙本已有概念的基礎上,又再加入“公文紙托裱本”這一特殊概念,即古人利用公私廢舊紙張來托裱古籍,這種現象雖極少,但已然存在,亦應列入“公文紙本”中的一類。在此基礎上,先生《古籍公文紙背文獻學的內涵與外延》首次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公文紙背古籍,即古籍紙背文獻這一特殊典籍的深層含義,推動了該項工作的整理與研究[3]。
1 公文紙本古籍的類型
前文談及公文紙本的概念時,除了先前學界早已擬定的“公文紙印本”這一定義,孫繼民先生又增加了“公文紙抄本”這一類型。另外,筆者曾見過封面封底用公文紙進行托裱的古籍文獻實物,且孫先生又對其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延伸。由此看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可大致分為三類,即“公文紙印本”、“公文紙抄本”和“公文紙托裱本”。
1.1 公文紙印本
所謂公文紙印本,是指古時用廢棄官私文書、賬簿(極少數文書、賬簿內容與古籍內容位于同一面)等紙背來印刷的書籍。公文紙印本是公文紙本古籍文獻中最為常見也是目前發現最多的類型,周廣學曾在其《古代的公牘紙印書》[4]一文列舉了16 種,日本學者竺沙雅章的《漢籍紙背文書研究》[5]一文對國內和日本的公文紙印本古籍進行統計,共有35種,而瞿冕良的《略論古籍善本的公文紙印、抄本》[6]一文中羅列出各代公文紙印本共計81種。近年來,孫繼民先生致力于宋、元、明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工作,據其不完全統計,包括藏地不明確的在內,公文紙印本古籍達86種之多[7]。據《中國古籍善本總目》[8]和《中國古籍總目》[9]記載,同時結合國內外學者的相關論著統計,公文紙印本的古籍約有160余種,其中明代公文紙印本古籍130余種,極具文獻開發和整理研究價值。
1.2 公文紙抄本
前文述及,所謂“公文紙抄本”就是古人利用公私廢舊紙的背面抄寫的古籍。這類公文紙本古籍存世較少,前文談及的瞿冕良《略論古籍善本的公文紙印、抄本》[6]一文中曾列有15種公文紙抄本古籍,沈津的《明代公文紙抄本二種》[10]一文中重點介紹了《明文記類》和《觀象玩占》這兩個公文紙抄本。孫繼民先生曾就公文紙本古籍流傳和存佚寫過專文論述,統計在內的公文紙抄本古籍亦為15種。近一年多以來,由于筆者一直在進行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撰述,期間查閱了大量相關資料,據實際查閱,公文紙抄本的古籍共有20余種。在這20余種公文紙抄本的古籍中,明抄本有13種,宋本僅有2種。公文紙抄本的古籍雖不如印本多,但其紙背所保留的原始公文內容仍具有豐富的史料研究價值。目前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明抄本的《明文記類》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問世。
1.3 公文紙托裱本
“公文紙托裱本”古籍因其稀見,目前學界尚未有統一的認識和定義,筆者所知所見總共不過7種,其中有1種于2008年被拍賣,具體下落不明。從目前所見到的幾種來看,所謂的“公文紙托裱本”是指古時人們利用廢棄的官私公文作為書皮襯紙來托裱的古籍。需要說明的是,“公文紙托裱本”古籍不同于前文談及的公文紙印、抄本古籍,托裱的古籍可能在時間上與公文紙所書時間相差更遠,如清代的時候用明代的廢棄公文來托裱印刷的書籍等。另外,用于托裱書皮的公文紙有多層托裱的情況,即書皮用多張公文紙層層托裱,同時也有多張殘缺公文紙共同托裱的情況出現。較為明顯的便是沈陽師范大學圖書館所藏《文苑英華》和重慶圖書館藏《冊府元龜》,書皮均用明代廢棄公文紙托裱。《文苑英華》封皮裱紙相對更為復雜,既有單張亦有多張多層托裱,同時還有多張殘缺公文紙拼合托裱;且其內容更為豐富,主要為萬歷年間福建各府縣官府檔冊,反映的是明代官府的行政支出[11],另有部分為“憲票”和各類“申文”。《冊府元龜》裱紙均為明代訴訟文書,所涉多為民間民事糾紛,真實地反映了明代基層百姓的生活現狀。
2 公文紙本古籍的特點
目前,國內學界對公文紙本古籍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特別是在圖書館、博物館等收藏領域分歧甚大,使得公文紙本古籍的收藏極不規范,同時缺乏系統性的數據庫。僅筆者所了解的情況來看,大多數圖書館界人士對公文紙本古籍并不了解,甚至表示不曾聽聞,加上公文紙本古籍本身的一些特性,導致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收藏呈現出隱蔽性、分散性和多樣性的特點。
2.1 隱蔽性
前文述及,目前圖書館界對公文紙本古籍仍缺乏足夠的認識。因此,在著錄館藏古籍目錄或建立數據庫時,對本館所藏的公文紙本古籍并未進行詳細的錄入和說明,大多仍舊簡單地著錄為刻本、抄本等。這就使公文紙本古籍這一特殊文獻深藏于眾多典籍當中,增加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收集難度。另外,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由于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紙張較厚且紙背文字墨跡較淺,再加上某些公文書寫字體較小,如不仔細翻閱很難發現紙背存有文字;再者,“公文紙托裱本”的古籍因其是用舊時公文紙對古籍進行托裱,紙張大小、文字多少等均不統一,且存在多層裱糊和多張拼合現象,很容易被忽略,僅將其視為對現存古籍的一種保護,并無太大價值。除上述所言之外,還有更少見的一種是用公文紙加襯古籍,其目的也是保護古籍以免破壞受損,這種情況的公文紙大多已經和原書用紙粘連在一起,更難被世人所發現。以上種種原因,導致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在收集和發掘上較為困難,也使得其收藏呈現出隱蔽性的特點。
2.2 分散性
公文紙本古籍除了上文提及的隱蔽性特點外,另一特點便是分散性。由于公文紙本古籍多為不同時代、不同機構、不同人員,或印刻、或抄寫、或托裱而為,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散藏于國內各個圖書館、博物館。同時,因這些古籍文獻本身又可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導致散藏在國內外各個圖書館、博物館等處的公文紙本古籍藏身于各類典籍當中,如二十五史、各類政書、地方志、詩歌類編、雜記等。
另外,除上述提及的各圖書館、博物館等處外,另有部分公文紙本古籍散藏于民間。筆者曾在國內各拍賣公司的古籍拍賣專場幸有所聞,如2012年北京德寶夏季拍賣會中,其一件拍品《通典》便是明嘉靖十七年(1538)方獻夫刻嘉靖二十五年(1546)南京府衙公文紙印本;2015年北京德寶拍賣公司秋季拍賣會中,其拍品《前漢書》殘卷,便是明嘉靖最樂軒刻公文紙印本;2015年天津國拍秋季古籍善本拍賣會中,其拍品《王氏存笥稿》為明嘉靖公文紙印本。
正是由于以上種種,現存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被湮沒在浩如煙海的世界各地圖書館、博物館等處的傳世典籍當中,給學界人士的整理和研究增加了難度。加之前文述及的館藏界普遍缺乏對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認知,更是加重了學者在對其進行搜集、整理和研究時的不便,導致公文紙本古籍文獻鮮有人知,更少有人對其進行整理和研究。
2.3 多樣性
所謂多樣性,是指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在版本、語言、內容和書寫形式上有著豐富的多樣性。在版本形式上,除有前文述及的“公文紙印本”“公文紙抄本”“公文紙托裱本”,還有為數不多的“公文紙襯本”,即古人用公文紙加襯其中以保護書籍;在語言上,除了人們熟知常見的漢字版外,另有蒙古文出現,使公文紙本古籍文獻變得更加豐富;在內容上,從目前所知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來看,其紙背公文有魚鱗圖冊、都察院憲票、各級官府公文等,內容極其豐富;在書寫形式上,就筆者所見有小楷、行書、草書等。
豐富多樣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無疑極具開發和研究價值,對其進行深入的發掘和整理勢在必行。近幾年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逐步進入學界視野,愈發受到廣大學者的重視,已有多個相關課題成功立項國家社科基金,同時也相繼有一批研究成果問世。
2.4 真實性和唯一性
公文紙本古籍除了具有隱蔽性、分散性和多樣性的特點外,還有更為重要的特征,即真實性和唯一性。公文紙本古籍是用廢棄官私文書舊紙印刷、抄寫、托裱的新編新著書籍,為避免紙張正反面內容相互干擾,造成閱讀困難,原有的文書內容往往被封存在葉面內里(托裱的被粘在書皮之上)。書籍一旦生成,原來的文書內容便被鎖定,其再次轉抄、轉印以致發生改動的可能性極低,使得原有的公文內容基本保持原貌,其真實可靠程度要比一般的傳世典籍文獻更高。同時,正面印、抄本文獻可化身千萬,往往流傳存世的不只一本,而公文紙本古籍紙背(或托裱的襯紙)原有的文獻大多為當時的實用文獻,如政府公文、賬簿冊紙、公函啟札等,往往只有一份,屬于孤本,因此具有極高的文獻史料價值。
3 公文紙本古籍的收藏和分布概況
如前所述,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具有分散性的特點,這種分散性的直接體現便是其收藏范圍廣泛,國內外均有收藏。從筆者所了解的情況來看,大部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藏于我國大陸各省市及高校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中,另有部分藏于臺灣省,除此之外,在美國、日本等其他國家也有收藏。對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收藏分布情況進行研究,有利于對其進行深入的發掘、搶救、搜集與進一步的整理和研究。
3.1 國內各地收藏情況
就目前學界所發現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藏地統計情況來看,國內各公藏機構的收藏量占有絕對優勢,其中以北京、上海、江浙和臺灣的收藏最為豐富和集中。因此,這些地方往往也是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搜集與整理的重點地區。在研究領域同樣如此,其典型案例便是2015年的“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古籍公文紙背文獻整理與研究”重大招標項目,引起了學術界廣泛關注。
3.1.1 北京
北京作為首都,在各個方面均占有一定優勢,也就使得其成為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收藏最豐富、最集中的地區。以國家圖書館為例,其館藏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有30種,如宋淳熙二年鎮江府學刻公文紙印本《新定三禮圖》、宋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魏書》等,都是公文紙本古籍文獻中的精品,孫繼民、杜立暉等國內學者也開始著手對其進行有效的整理和研究。除國家圖書館外,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北京市文物局等亦有少量收藏。據筆者統計,整個北京地區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藏書量多達44種,在時代上涵蓋了宋、元、明、清四個朝代,內容極為豐富。
3.1.2 上海
國內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收藏的第二大地區是上海。上海的公文紙本古籍收藏,在數量上僅次于北京,其中以上海圖書館為最。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公文紙本古籍共有26種,時代上涵蓋了元、明、清三個朝代,其中元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已由南開大學王曉欣先生整理研究,明代部分由孫繼民先生牽頭,通過與上海圖書館合作的方式開始著手對其進行整理和研究,這也是學界僅有的最為集中、最為廣泛的對公文紙本古籍的整理與研究。目前,相關的整理工作已近尾聲,成果出版工作正在推進,亦有諸多研究成果問世,如《后湖黃冊悄然現身》[12]、《北京黃冊填補空白》[13],《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黃冊的發現及意義》[14]、《明初小黃冊中寄莊戶初探》[15]等,而眾多明代賦役黃冊尤其是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黃冊的發現更是明史學界的重大發現。另外,上海博物館和復旦大學圖書館分別藏有公文紙本古籍5種和2種,加上海圖書館所藏,上海地區的公文紙本古籍藏書量達到了33種。這些公文紙本古籍文獻,除了孫繼民先生所致力于研究的上海圖書館所藏之外,上海博物館和復旦大學所藏尚待深入發掘。
3.1.3 江浙
江浙地區自宋代以來便是我國最為富庶之地,也是文人豪客的聚居之地,這也使得這些地區得以保留諸多古時之物。江浙地區是國內除北京、上海之外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收藏最多的地區。據筆者統計,僅江蘇省所藏公文紙本古籍就有20種,其中南京圖書館藏有11種,另外9種分別藏于蘇州大學圖書館、無錫市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博物院、蘇州市圖書館、蘇州博物館以及南通市圖書館等地;浙江省所藏略少,僅有6種,分藏于浙江省圖書館和寧波天一閣。江浙地區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所藏總量為26種,僅次于北京、上海地區。
目前,江浙地區所藏的這26種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正逐步進入學界視野,其中寧波天一閣所藏《國朝諸臣奏議》已被宋坤先生立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且相繼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問世。如《明代五城兵馬司公文的發現及意義——明正德二年南京南城兵馬指揮司呈文考釋》[16]、《略論明代衛所余丁的差役——以天一閣藏〈國朝諸臣奏議〉紙背文獻為中心》[17]、《紙背文獻提供南京倉場新史料》[18]。
3.1.4 臺灣
國內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收藏數量較多、較為集中的除北京、上海和江浙地區外,臺灣地區所藏也十分豐富。臺灣地區所藏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多是當年國民黨內戰失敗后,退守臺灣時從大陸地區運走的古籍,其中很多是當年北平圖書館所藏之書。臺灣地區所藏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據筆者統計共有14種,其中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有11種,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3種。這些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同樣涵蓋了宋、元、明三個朝代,特別是其元代公文紙本古籍,更具極高的史料文獻價值。
3.1.5 國內其他地區
國內公文紙本古籍的收藏,除上述所言四地區之外,在其他地區也或多或少有所收藏。筆者通過對各類館藏書目進行檢索、翻閱,加之實地調研和網上搜尋,對國內其他地區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收藏情況進行了粗略統計,大致數據結果如下:
遼寧省藏有5種,分藏于遼寧省圖書館、沈陽師范大學圖書館、沈陽市圖書館和大連市圖書館;山東省藏有4種,分藏于山東省圖書館、山東省博物館和曲阜師范大學圖書館;河南省藏有4種,均藏于河南省圖書館;吉林省藏有2種,分藏于吉林省圖書館和吉林大學圖書館;重慶市和安徽省各藏有2種,分別藏于重慶圖書館和安徽省博物館。除此之外,四川、湖北、黑龍江各藏有1種。
據此來看,這些散藏于國內其他地區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共有22種,其中不乏有十分珍貴的元代史料,其明代史料更為豐富,是亟待開發的文獻史料富礦。
3.2 國外收藏情況
國外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收藏情況相較于國內并不豐富,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知的國外藏有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國家僅有日本和美國。目前,日本是國外藏有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最豐富的國家,共藏有公文紙本古籍6種,其中4種藏于東京靜嘉堂文庫,其余2種分藏于東京東洋文庫和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這些藏身于日本的公文紙本古籍,涵蓋了宋、元、明三代,具有豐富的史學價值,特別是元代公文更具開發價值。
美國的公文紙本古籍藏量略少于日本,僅有4種,其中3種藏于哈佛大學的燕京圖書館,另1種藏于美國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美國藏有的這4種公文紙本古籍均為明代文獻,其中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重刊并音連聲韻學集成》已由山東大學的杜立暉申報為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并且有了一些初期的研究成果,如《哈佛大學藏公文紙本〈重刊并音連聲韻學集成〉等紙背明代文獻初探》[19]、《新見明代黃冊中匠戶相關問題研究——以哈佛大學藏《韻學集成》等紙背文獻為中心》[20]。另外,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的《明文記類》也有學界人士開始著手整理和研究,如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的馬春香,曾就《明文記類》紙背的《到任須知》撰文論述[21]。
3.3 收藏地不明的情況
目前,除上述所言藏地明確的167種文獻之外,尚有60余種藏地不明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這60余種藏地不明的公文紙本古籍僅在學界人士的論著中有所涉及,但具體藏地無從得知。如瞿冕良曾在其所編著的《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中提到,“《疑獄集》十卷,明嘉靖刻本,用公文紙本。”[22]329《湖南近現代藏書家題跋選》第一冊中提到,《謝疊山批點〈陸宣公奏議〉·郎曄注》十五卷,元公牘紙印本[23]169。諸如此類的情況還有很多,均是在一些學者的論著中有所提及,然其現今的具體藏地卻無從得知,這無疑是非常遺憾的。更為可惜的是,一些曾見諸于世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已毀,再也無法窺知其內容,如:明代王鏊著《震澤紀聞》,嘉靖公牘紙所印。原鄧之誠藏書,后贈予王君九,疑毀于火劫[24]1084。這些藏地不明或久已失傳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尚待更多學界人士介入搜尋,在豐富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同時也是對傳世典籍文獻的一大貢獻。
綜上所述,公文紙本古籍文獻藏地較為分散,在國內外均有收藏,對這些古籍紙背的公文內容進行整理和研究勢在必行。特別是紙背所存的元代公文紙,由于元代史料存世較少,這些公文紙本古籍文獻中的元代文獻更應引起學界注意。對其進行整理和研究,不但能豐富元代史料,同時還能為學界提供難得的史學資料。然而,由于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藏地分散,對其進行整理和研究首先要解決搜集難的問題,對這些藏之于海內外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進行搜集,以便日后的整理和研究。
4 公文紙本古籍的搜集方法與實踐
近幾年,業師孫繼民先生致力于宋、元、明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在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筆者有幸讀研期間師從孫繼民先生,參與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先生的悉心指導下,筆者通過翻閱各類館藏古籍書目、善本書目,閱讀相關論著,并隨同先生親赴全國各地進行實地調研等方式方法,先后新發現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60余種;同時,在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搜集方面積累了一些寶貴經驗,也在日常的整理和寫作當中,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和經驗。筆者就自身經驗,結合實際中的具體問題和方法來探討在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收集和實踐中存在的諸多問題。
4.1 通過版本目錄學進行搜集
版本目錄學是目前檢索、搜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最為常用的方法,也是最直接、最便捷的方法。目前,國內各地均已陸續整理出版了各類館藏的古籍書目、古籍善本書目以及珍貴古籍名錄等。迄今為止,筆者先后翻閱了《中國善本書提要》[25]、《中國古籍善本書目》[26]、《中國古籍善本總目》[8]和《中國古籍總目》[9],其中《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統計在冊的各類型公文紙本古籍共有75種[27],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僅著錄有17種,《中國古籍總目》中著錄的共有54種。另外,這三大書目中的公文紙本古籍著錄又各有一些出入,如:明崇禎間刻公文紙本《郭弘農集(郭景純集)》二卷,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不見有載,而是著錄于《中國古籍總目》[9];宋刻明初公文紙印本《忠文王紀事實錄》五卷,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總目》中均不見有載,之前一直傳聞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明確著錄其藏于國家圖書館[8]。除上述三大全國性古籍書目之外,筆者又陸續翻閱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28]、《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明確書目》、《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和近幾年編錄的珍貴古籍名錄,由此發現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綜合統計為84種,其中有9種之前未見有學者提及。
近年以來,隨著國家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各類型的古籍逐漸受到學界追捧,特別是近幾年由文化部牽頭推動的珍貴古籍名錄普查行動,各級地方政府紛紛積極響應,各省隨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浪潮先后推出若干批珍貴古籍名錄。全國范圍內古籍普查逐漸走向熱潮,有關各類古籍版本知識的推廣和相關工作人員的培訓,無疑為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搜集和進一步挖掘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在各省相繼推出的珍貴古籍名錄中或多或少均有所著錄。因此,翻閱各個類型的古籍書目是搜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首要策略,是搜集和發掘公文紙本古籍的第一步。
4.2 赴全國各地進行實地訪談、調研
如前所述,翻閱各類古籍書目是搜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首要策略。然而,由于目前圖書館界對公文紙本古籍的認識層次不夠,很多著錄的館藏古籍書目并未對此作出相應說明,這就需要有針對性地到各藏書地進行實地調研。近幾年,筆者實地調研了國內諸多省、市及其各高校圖書館、博物館,通過與其工作人員進行交流、翻閱其館藏書目和索書卡等,獲得了有關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多種信息,發現了一些未曾見諸學界著錄、統計在冊的新公文紙本古籍。
親赴各地進行實地的訪談、調研必然能夠獲得更多、更直觀、更詳細的相關信息,但在實踐當中需要注意一些小的細節性問題。在實際的訪談和調研當中,首先,要注意在充分尊重對方的情況下詳盡說明來意,便于工作人員給予幫助。其次,目前國內各個館藏界工作人員對公文紙本古籍文獻仍未形成足夠的認識,因此,在與各圖書館、博物館工作人員進行交流和溝通時,要將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典型特征和主要價值進行重點說明,便于進行下一步的古籍調研工作。再次,要注意在實際調研當中充分利用其館藏的各種能夠提供古籍版本的書目以及索書卡等,要將跟工作人員的訪談溝通與自己的實際查閱相結合,不僅限于從工作人員口中獲得信息,同時要注意在方便的情況下留下聯系方式,便于以后的進一步交流。
實地訪談和調研是一項較為繁瑣的工作,既要細致入微地當面詳盡解釋、詢問,又要不厭其煩地翻閱、查詢館藏的各類古籍書目和索書卡,同時還要注意盡量地留下聯系方式,以便后續進一步地跟蹤了解。如2015年7月,筆者隨同孫繼民先生等前往哈爾濱考察,期間對哈爾濱市圖書館調研時,筆者與該館古籍部一位林姓老師進行了詳細的溝通交流,經過反復的說明得知,該館所藏的古籍中有一部情況類似公文紙本古籍,其紙背疑似存有文字,紙張為格子紙。后經過進一步協商,林老師同意帶我到書庫查閱具體內容,遺憾的是當時古籍保管部主任不在,沒有鑰匙,無法查閱。最后,林老師答應在保管部主任上班后,她再進入書庫進行查閱并告知于我。為便于聯系,筆者留下了電話并加上了林老師QQ。另外,筆者拍下了所要查閱的檢索卡片,確定所要查閱的書為:唐代杜佑撰《杜氏通典》,明刻本。回來后不久,林老師打電話告訴筆者,其館藏《杜氏通典》書高29cm,寬17.3cm,其紙背為紫紅色格子紙,有白邊,無公文內容,其中最后一冊的整個版葉均為兩部分拼接用紙,在拼接處存有殘朱印,經林老師辨認為某縣朱印,具體縣名不知,且不止一縣朱印,疑為嘉靖年間刻本。
實踐調研當中,除上述情況之外,還有一種情況使得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搜集更為困難,即工作人員無法提供較為有效的相關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則需要翻閱該館館藏古籍書目和索書卡,特別是對之前已經統計在冊的公文紙本古籍,要進行重點查驗。這種重點的針對性查驗,主要有兩個看點:一是版本,主要看其是否注明公文紙本;二是在未注明公文紙本的情況下,看其古籍的印書出版時間是否與之前統計在冊的公文紙本古籍相同,若相同則可能是同一批次的公文紙本古籍,特別是同一種書的不同殘存卷數,即可協調工作人員提書進行查驗。如2020年10月筆者隨同孫繼民先生到山東師范大學開會,期間到山東省圖書館進行調研,在與該館古籍部主任溝通交流后,并未得到有價值的信息。隨后,筆者與一同去的孟月、田琳翻閱其館內的索書卡柜,發現有三種古籍注明為公文紙本。其中一種為《錦繡萬花谷》,其索書卡正面信息顯示“存前集三十五卷,續集四十卷,明嘉靖十四年徽藩崇古書院刻本”,背面注有“封面封底用萬歷五—六年還糧票據”。經過與主任協商對其進行調閱,查得該書與索書卡信息基本一致,為萬歷年間的公文紙托裱,但筆者認為其并非還糧票據,疑為萬歷五、六年間巡按御史按察地方的照刷文卷。
4.3 相關研究論著中的信息提煉
公文紙本古籍最早是在版本學界和目錄學界提及,稱為公文紙印本,也稱公牘紙本、文牘紙本、官冊紙本等。因此,在一些版本學和目錄學的論著當中對公文紙本古籍有所提及,為對其進行搜集和整理提供了重要信息。其中較為典型的便是前文提及的周廣學的《古代的公牘紙印書》,瞿冕良的《略論古籍善本的公文紙印、抄本》,日本學者竺沙雅章的《漢籍紙背文書研究》,沈津的《明代公文紙抄本二種》《公文紙印本〈重刊并音連聲韻學集成〉》,以及孫繼民的《公文紙本:傳世文獻最后一座待開發的富礦》、《近代以來公文紙本古籍的流傳和存佚——兼議公文紙本原始文獻與次生文獻的價值比較》和《古籍公文紙背文獻: 中國古文書家族的新丁》。另外,筆者在其他論著中獲得了一些之前未聞的新信息,如瞿冕良編著的《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提及“李崧祥,明正德間貴池人,字時望,號恭川。嘉靖十四年(1535)任浙江按察使時,刻印過晉和凝、和蒙《疑獄集》十卷,明嘉靖刻本,用公文紙本”[22],遺憾的是,該種公文紙本古籍現藏地不明,無法窺其真相;張拱卿的《館藏古籍善本版刻舉隅》提及重慶圖書館所藏《冊府元龜》時言,“書皮用嘉靖中榮河、夏縣、蒲圻、臨汾、長樂、安邑、鹽池、平陽府等州府州縣公牘紙裱褙而成”[29]43,該書經重慶圖書館工作人員證實,確有此書且裱紙為公文紙無疑;前文述及的《〈文苑英華〉版本裝幀拾遺》[2]一文,則提供了沈陽師大所藏公文紙托裱本的《文苑英華》。
相關研究論著中的信息提煉,除了翻閱一些明確的書籍、文章之外,還有一種更為便捷的方法,即網上檢索。在信息技術發達的今天,很多東西都可以通過網絡來獲取,筆者在日常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搜集、整理當中,通過網上檢索關鍵詞的方法發現了諸多新的尚未統計在冊的公文紙本古籍。通過網上檢索關鍵詞來搜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目前據筆者實踐而言讀秀是比較準確且方便快捷的主要網站。在讀秀網站進行公文紙本關鍵詞的檢索,可以直接檢索諸如“公文紙”“公文紙本”“公文紙印本”“公牘紙”等,經此類關鍵詞檢索能夠搜尋到涵蓋這些關鍵詞的大部分論著。筆者據此方法檢索到的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有幾十種,如有錢傷輯《城守籌略》五卷,崇禎刻本,用縣署公文紙印刷[29]505;宋朱申撰、明顧梧芳校正的《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五卷,四冊,明刻本,該書封面、封底用紙,均以隆慶六年察院憲票裝裱(憲票主要內容:為廣積貯,以杜吏弊,以裨國計事,對大梁道儀封縣呈報人犯處理意見)[31]92;《謝疊山批點〈陸宣公奏議〉 ·郎曄注》十五卷,元公牘紙印本[23]169。
4.4 關注各拍賣公司古籍拍賣
除了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外,民間尚有大量的古籍文獻,其中不乏珍本、善本,而部分民間文獻則隨著各拍賣公司的古籍拍賣為世人所知。因此,搜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除了上述所言方法之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各拍賣公司的古籍拍賣。據筆者所知,每年的春、秋二季各主要拍賣公司都會推出自己的古籍拍賣專場,在眾多的拍品當中就可能會存在公文紙本古籍。關注一些主要拍賣公司的古籍拍賣專場,如嘉德、雅昌、德寶等可獲得一些相關的信息。筆者通過網上搜尋獲得了不少有關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資料,如2004年北京瀚海春季古籍拍賣專場,其拍品《呂氏家塾讀書記》為明嘉靖十年傅鳳翔刻本,明公文紙印本;2008年中國嘉德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其中的拍品《王諫議集》,為明崇禎間婁東張氏刻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公文紙印本。筆者曾遵師囑有幸參加了北京德寶拍賣公司2015年北京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其拍品《前漢書》殘卷,共計17頁,為明嘉靖最樂軒刻公文紙印本,最后以5 000元的起拍價成交。
古籍善本拍賣中的公文紙本古籍遠不止上述所及,天津國拍2015秋季古籍善本拍賣會專場中,其拍品《王氏存笥稿》便是明嘉靖公文紙印本。隨著民間文獻大量被發掘,越來越多的古籍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公文紙本古籍文獻隨之而出,使得學界得以窺知其一二。雖然由于種種因素我們無從得知這些公文紙本古籍拍出后藏于何人何地,但至少能夠為學界提供更多的重要信息,豐富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數量和種類。筆者有理由相信,隨著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整理與研究的興起,這些被拍賣的公文紙本古籍勢必會重新回到學界,使其得以整理和研究。
5 結語
搜集、挖掘和整理公文紙本古籍文獻,能夠為學界提供更多的傳世典籍中所未載的新的史學資料。目前,據筆者所知,這些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在時間上涵蓋了宋、元、明、清四個朝代,在內容上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個領域,“是我國傳世典籍中一座極具珍貴價值,富于開發遠景而又亟待開掘的文獻資源富礦”[27]。近幾年,隨著越來越多的新史料被發掘和開發,學界感到很難再有新的大規模史學資料顯現,而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無疑為學界開辟了一個新的學術整理研究領域。古籍紙背文獻學的不斷推進,使得眾多史學新文獻資料逐漸進入學者視野,諸如元代湖州路戶籍冊、元代肅政廉訪司文書、明代南京倉場文書、明洪武三年處州府小黃冊及眾多的明代賦役黃冊等,在為學界提供新的文獻資料的同時也進一步豐富了我國傳世文獻的文化價值,具有雙重的傳統文化價值。另,現有的傳世典籍多為中央或是地方高層的史學資料,極少涉及古代基層領域,公文紙本文獻作為基層公文文書無疑彌補了這一缺憾。因此,搜集、發掘公文紙本古籍文獻,能夠進一步充實現有的傳世典籍文獻體系,保障我國傳世典籍藏書的完整性、系統性,同時也為進一步整理和研究公文紙本古籍文獻提供極有價值的文獻寶庫。公文紙本古籍文獻的發掘,是一項極為復雜、煩瑣的系統工程,需要學術界內外諸方面的廣泛關注,更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投入。筆者在此呼吁,各版本學界、目錄學界以及文博界人士,共同關注公文紙本古籍文獻,同時在研究中給予學界人士一定的方便,進一步豐富我國傳統文化當中的重要載體——傳世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