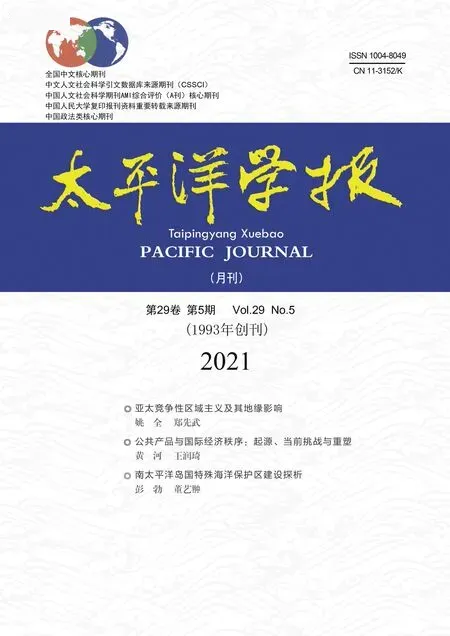公共產品與國際經濟秩序:起源、當前挑戰與重塑
黃 河 王潤琦
(1.復旦大學,上海200433)
近年來,美國在二戰后主導建立起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正面臨嚴峻挑戰。 霸權的相對衰落與新興力量的不斷崛起引起了一系列結構性變化,國際公共產品作為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最主要手段之一也受到大國“私物化”影響而處于供給不足和分配不均的狀態,國際經濟秩序單靠原有機制安排已經無法維持。 與此同時,各行為體將重點轉向了區域間經濟合作以彌補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帶來的利益損耗。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英國和美國借助 “自由主義優勢”(liberal ascendancy),先后主導和建立了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①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1.但世界經濟先后經歷了20 世紀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兩次失序。 本文認為,國際經濟秩序的失序與國際公共產品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當下國際經濟秩序再次遭到質疑和挑戰的背景下,以公共產品理論剖析世界經濟秩序的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這為全球經濟參與者如何理解未來世界經濟的發展及自身定位提供了獨特視角和理論工具。
一、問題的起源
1929 年爆發的大蕭條是資本主義世界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1929 年10 月24 日,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價暴跌,金融危機爆發并持續擴散,工業生產萎靡不振、持續蕭條,與此同時,大批企業宣布破產,失業人數暴增。 美國工業生產下降了55.6%,工業生產指數從10 月份的110 降至 12 月的 100,新興工業嚴重受挫。①[美] L.S.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698 頁。美國的經濟蕭條隨后迅速地席卷了資本主義世界,國際經濟出現困境,各國貨幣紛紛貶值,英國試圖投入大量資本避免危機的蔓延,卻無力回天,世界工業生產大幅倒退,農產品與初級產品價格暴跌。 工農業危機繼而引發國際貿易的嚴重萎縮,各國紛紛采取短視政策,妄圖以損害別國經濟來挽救國內經濟,從而導致資本主義世界貿易總額大幅下降。 20 世紀20 年代末至二戰結束期間的國際經濟秩序便處于此種狀態,英國作為昔日霸主已失去主導能力,難以承擔維持國際秩序的成本,而正在崛起的美國則欠缺意愿和能力承擔恢復世界經濟秩序的職責。 因此,當時的國際社會出現了一段較長時間的領導空位期。
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分析這一階段的全球經濟大蕭條時指出,經濟危機出現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國際層面領導者的缺失,經濟體系的運轉需要某個國家成為“穩定器”(stabilizer),②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The Penguin Press, 1973, p. 305.當貨幣制度停滯失靈時,該國作為主導者愿意建立某種再貼現機制,提供一定程度的貨幣政策合作,可以負責為虧本產品(distress goods)提供開放市場、設立經濟體系的行為準則,并主動承擔系統內的“公共成本”(public cost)。③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254.金德爾伯格隨后明確提出了國際公共產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的概念,強調其在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穩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④Charles P. Kindleberger, “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6, No.1,1986, pp.1-13.
國際經濟秩序是世界經濟領域中基于一定的實力結構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國際行為規則體系。⑤徐秀軍:“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秩序:實力結構、規則體系與治理理念”,《國際政治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82-101 頁。承擔維系國際秩序的成本是國際關系主導國的必要義務,20 世紀30 年代開始的國際經濟秩序“失序”的根本原因是在英美霸權交替的背景下,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國際公共產品出現“斷供”。 這一“斷供”現象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當時的國際資本流動形成了一個較固定的循環支付鏈條。 由于戰債問題,一戰后德國的賠款通過英法等國大量流向美國,美國再以貸款方式重新投入德國經濟,以投資方式將資本大量注回歐洲,這使歐洲的金融體系形成了對美國資本的高度依賴,這意味著英國正逐漸失去維持資本穩定流動的主導權。 其次,各國貨幣匯率的過度浮動影響了貨幣價值穩定,打亂了國際貿易秩序。⑥袁偉華:《權力轉移、國家意志與國際秩序變遷》,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年,第204 頁。1929 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迅速引發全球經濟危機,英國曾嘗試通過自身力量防止危機的進一步擴大但已于事無補。 在此之前的歷次國際金融危機中,英國作為國際公共產品的穩定供給者往往能起到緩解危機的重要作用,但在此時,英國的“斷供”使英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徹底喪失了合法性。 與此同時,在1933 年召開的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上,當各國把重建國際經濟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美國之時,羅斯福政府卻選擇了退縮:在恢復國內經濟的首要目標面前,美國并未準備好承擔起國際經濟秩序領導者的責任和義務,因而拒絕了會議中提出的穩定貨幣、取消戰債等穩定經濟秩序的要求。 總而言之,世界經濟在大蕭條之后經歷了漫長的經濟霸權更迭期,英國無力發揮領導作用,而崛起中的美國則不愿承擔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成本,因而放棄了在國際經濟秩序中進行主動的角色轉變。①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34.
在國際經濟的“失序”狀態下,新的經濟霸主是否能夠接受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的責任,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經濟實力,另一方面是將這種經濟實力應用于公益生產的意愿。②[美] 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著,高祖貴譯:《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 370 頁。顯然,美國由于較弱的意愿并未第一時間承擔起主導重建國際經濟秩序的重任,但長時間的國際經濟失序使美國政府意識到其影響早已超出單純的經濟范疇。 當國家間關系的惡化開始損害美國的自身利益,美國逐漸產生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想法:1934 年美國國會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1936 年通過同英法合作的《三國貨幣協定》(Tripartite Agreement),1941 年又通過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這些法案的出臺,改善了國際貿易的環境,推動了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堅定了美國建立多邊機制的信心。 在此之后,美國將經濟實力用于穩定世界秩序的意愿逐漸顯現。 二戰行將結束之時,羅斯福政府在組織籌建聯合國的同時也積極設計了一系列金融、投資和貿易的國際制度安排,以主導者姿態參與到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塑中。 為了實現其目標,美國政府經過長期醞釀,于1943 年4 月7日正式推出“懷特計劃”,并最終替代英國成為新的全球霸主。③王玨:“英美不同霸權體系下的債權國地位”,《教學與研究》,2009 年第 6 期,第 56 頁。
“在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過程中,諸多環節和因素導致其具有極大的可變性。 然而,并非所有可變的因素都可以進行主觀塑造,只有部分因素具有不同程度的塑造性。”④呂虹、孫西輝:“國際經濟秩序變遷的理論與現實— —基于結構化概念的分析”,《太平洋學報》,2019 年第9 期,第89頁。基于自身一騎絕塵的綜合國力,美國在1944 年領導各國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這是一個“以美元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⑤孟憲揚:“淺析布雷頓森林體系”,《南開經濟研究》,1989年第 4 期,第 3 頁。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簽訂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以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為世界經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制度安排,成為美國作為國際經濟秩序主導者的合法依據。 戰后作為國際公共產品而出現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保障了成員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公共利益訴求,這成為區別于以往大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一個重要特征。 自此,美國通過“設計”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方式,建立了以貿易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為核心的國際經濟秩序,世界經濟在漫長的混亂狀態后終于重歸穩定。
二、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困境和挑戰
二戰后在美國主導下建立的“國際經濟秩序”被定義為治理國際經濟活動的關鍵行為體所設立的一系列規則、基準及制度規范。⑥Hal Brand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the Liberal Order: Continuity, Change, and Options for the Future,” Rand Cooperation Report, 2016, p.2;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23.查爾斯·金德爾伯格作為“霸權穩定論”的首創者,構建起國際經濟秩序與國際公共產品之間的互動關系并指出領導國供給國際公共產品在維持國際經濟秩序穩定中的重要作用。⑦樊勇明:“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政策”,《現代國際關系》,2000 年第 9 期,第 20-23 頁。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等“霸權穩定論”者對這種霸權供給模式做出了理論解釋并將這種行為合理化。⑧[美]羅伯特·吉爾平著,楊宇光譯:《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5 頁。他們指出,美國通過“設計”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得到了國際影響力,使自身和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之間產生了權力關聯,其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便化作謀取政治利益和權力的產物,從而使美國成為世界單極霸權。 這意味著國際經濟秩序從建立之初便帶有“結構性權力”色彩,主要反映了霸權國的利益。 隨著美國實力的衰減,這種霸權體系逐漸演變為“集體霸權”,但美國仍然領導著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體系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中國也不例外。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霸權穩定論”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具有較強的解釋力,然而面對21 世紀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嬗變,這一理論卻顯得愈加蒼白無力。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實力的削減及霸權的衰落使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意愿和能力大幅下降,國際經濟再次失序。 正如約翰·伊肯伯里所說:“后霸權國際秩序的一個特征就是美國在公共產品供應、穩定市場、促進合作等功能性服務提供方面的核心作用將會下降。”①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 7, No. 1, 2009, p. 80.這種變化不同于20 世紀的國際經濟秩序變遷,進入21 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社會意識到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已無法依賴于國際公共產品的單一霸權供給模式,而美國等西方國家也無法僅靠小團體合作以實現國際公共產品的充足供給。 國際經濟秩序面臨的重重挑戰凸顯了國際公共產品霸權供給模式的局限性,全球化背景下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難以適應全球公共產品大范圍外溢的出現,公共政策的制定方式表現出排外性與片面性,導致全球性公共劣品(global public bads)現象出現并揮之不去。 霸權式供給非但維護不了世界經濟的穩定與有序發展,還會干擾到其他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發揮作用。
上述問題產生的根源是美國對國際公共產品的“私物化”傾向。 當霸權國建立的國際經濟治理機制作為公共產品為國際社會提供正面效應時,體現了國際公共產品“公”的屬性;而當霸權國將應盡的責任轉化為剝削榨取利益,運用權力產生更有利于自身的結果時,國際公共產品便體現出“私”的屬性。②李巍:“國際秩序轉型與現實制度主義理論的生成”,《外交評論》,2016 年第 1 期,第 31-59 頁。私物化現象的愈演愈烈意味著國際公共產品的強排他性越加突出,最終喪失其“公”的屬性。 美國對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貿易體系的私物化行為正在逐漸侵蝕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對國際經濟制度運行產生的“交易成本”的衡量是霸權國首要考慮的問題,交易成本是霸權供給意愿的最重要影響因素,這也是美國私物化行為發生的根本動機。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概念源于交易成本經濟學。③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4, No.16, 1937, pp.386-405.隨后,經濟學家對交易成本這一概念進行了進一步闡述。④有關交易成本的概念和交易成本經濟學可參考:[美]奧利弗·威廉姆森、[美]斯科特·馬斯滕著,李自杰、蔡銘譯:《交易成本經濟學》,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美]邁克爾·迪屈奇著,王鐵生等譯:《交易成本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9 年版;[美]約翰·康芒斯著,趙睿譯:《制度經濟學》,華夏出版社,2009 年版;盧現祥著:《新制度經濟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盛洪:《現代制度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2009 年第2 版;張五常著,易憲容、張衛東譯:《經濟解釋》,商務印書館,2001 年版。馬修斯(R.C.O. Matthews) 給出了一個沿用至今的交易成本的定義:“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履行該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它們區別于生產成本,即為執行合同本身而發生的成本。”⑤R. C. O. Matthews,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96, No.384, 1986,pp.903-918.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國際關系學者開始將交易成本概念運用于政治領域,他們認為交易成本在政治交易中也同樣重要,交易成本政治學應運而生,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礎性概念。⑥黃新華:“政治交易的經濟分析——當代西方交易成本政治學述評”,《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5 期,第5-13 頁。
根據交易成本政治學,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與穩定運行同樣需要支付交易成本,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安排所形成的非必要交易成本將嚴重制約世界經濟的繁榮。①有學者將交易成本分為兩類:一類是必要的交易成本,如談判、簽約、履約、監督經濟績效等費用,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條件之一;另一種是非必要交易成本,如機會主義、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外部效應、不確定性、搭便車等所導致的交易成本,這種是制度中存在的應予以消除的。 參見周春平:“民營經濟發展的交易成本約束——兼論交易成本視角的市場經濟中政府職能”,《現代經濟探討》, 2005 年第 6 期,第 27 -31 頁。例如,霸權國在“設計”國際公共產品之初需要投入一筆固定交易成本,隨著國際公共產品的消費者增多及國際公共產品涉及的領域拓展,霸權國就需要承擔巨大的額外交易成本。 只有當霸權國認為其收益超過(或至少足以彌補)相應成本時,才有動力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才能保持其穩定國際經濟秩序的意愿。②Robert A. Past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ericas: Unfilled Promise at the Century’s Turn,” in Robert J. Lieber, ed., Eagle Rules?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Pri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entice Hall, 2002, pp.133-152.而過高的交易成本有可能導致霸權國放棄或降低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意愿,其利用國際公共產品服務于自身利益的私物化行為就越強烈,從而導致全球秩序陷入再次混亂。
美國在最初建立戰后國際經濟秩序之時,所承擔的總交易成本并不高,具體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 一方面,當時的美國擁有強大的綜合國力,為其在設計和創立國際經濟制度和提供一系列國際公共產品時所花費的固定交易成本提供了雄厚的財力保障:美國的經濟實力在二戰后急劇增長,其經濟總量(GDP)超過了世界的一半,占到了世界的56%,美國工業生產占資本主義世界的54.8%,黃金儲備占48.5%,出口額占50%,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債權國。③曹廣偉:“世界經濟秩序的歷史變遷”,《國際展望》,2012年第 5 期,第 72-97 頁。隨后的20 世紀50—60 年代,美國經濟增長迎來了“黃金時代”,完成了從工業經濟的發展期到發達期的飛躍,成為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 另一方面,美國為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消費群體”規模并不龐大,國際公共產品所涉及的領域也十分有限。 例如,1944 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一共只有44 個與會國,關貿總協定最初成員國也只有23 個國家和地區,而后在冷戰時期,世界經濟劃分成兩大陣營,美國所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主要局限在其盟友體系內,隨交易數目或規模變化所形成的可變性交易成本尚在美國可承擔的范圍內。 然而,現今的國際格局顯然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維持國際經濟秩序所需的可變性交易成本開始大幅飆升,具體仍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 一方面,2008 年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陷入財政赤字和軍事過度擴張的泥潭之中,導致美國霸權的內部衰敗④Josef Joffe, “ The Default Power: The False Prophecy of America"s Decline,” Foreign Affairs, Vo1.88, No.5, 2009, pp.21-36.。美國的綜合國力早已不復當年,經濟實力的相對衰弱意味著美國支付能力的降低。 另一方面,交易數量和交易規模正不斷擴大。 依據集體行動理論,全球化下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難度較大。 當博弈的參與者數量增多時,合作性博弈將面臨更為復雜的阻礙,相應的“搭便車”“公地悲劇”和“囚徒困境”問題也更加凸顯。⑤張建新:“國際公共產品理論:地區一體化的新視角”,《復旦國際關系評論》,2009 年第 1 期,第 31-49 頁
步入21 世紀以來,國際經濟治理主體更加多元,治理平臺不再僅依賴于美國戰后所建立的核心機制。 例如國際金融治理主體不僅涵蓋了二十國集團(G20)等新興國家、國際清算銀行等既有政府間國際組織,也包含了全球金融市場協會等非政府間國際組織、跨國企業和公民社會組織等,從而導致美國的影響力相對減弱。 美國非但不積極參與各類治理新平臺,而且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條件惡化時(例如發生全球金融危機),通過雙邊協議網絡臨時替代國際組織,收縮國際公共產品的惠及范圍,增強國際公共產品的排他性,捍衛霸權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隨著美國霸權的衰落,公共產品的“公共”屬性或者供給量會顯著下降。
其二, 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WB)等國際公共產品自成立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美國烙印,這為日后美國的私物化行為提供了便利條件。 其私物化行為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實現:
一方面,美國自始至終在組織運行與決策機制方面占據主導地位。 實際上,關于各國投票的配額分配問題早在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之前便通過政治途徑得到了確定。 雷蒙德·邁克塞爾作為配額分配計劃的參與人員曾寫道:“我試圖讓整個過程盡可能表現得比較具有科學性,但是各國代表團都很精明,他們知道整個國際組織決策程序的政治性要高于其科學性。”①Raymond F. Mikesell, “ The Bretton Woods Debates: A Memoir, International Finance,”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192,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pp.35-36.雷納托·魯杰羅在就任世貿組織總干事時曾承認“多邊貿易制度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處于美國結構性權力的領導之下”。②Renato Ruggiero, “Keynote Opening Address,” in Jeffrey J.Scott, ed., Launching New Global Trade Talks: An Action Agenda,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p.12.世貿組織是美國霸權下創立的核心國際公共產品之一,其規則的不同階段的演變體現出不同時期美國的國家利益,由此帶來的收益又使得美國得以繼續維持其國際經濟統治地位,掌握國際貿易規則的主導權和定制權。③黃河:“貿易保護主義與國際經濟秩序”,《深圳大學學報》,2019 年第 3 期,第 63 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也是維持國際金融穩定最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美國同時作為這兩個組織的最大股東,掌握著決策過程的主導權,成為實現其政治利益的有力工具。④劉嵐雨、陳琪:“國際經濟組織如何思考”,《暨南學報》,2017 年第 10 期,第 13 頁。目前,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是16.74%,而該組織規定:涉及提升份額、分配特別提款權和接收新成員等重大事項時必須有84%的同意票才可通過,這意味著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沒有任何一國或集團可對其進行有效制衡,新興國家的份額提升問題更是得不到有效解決,中國投票權提升的方案在經歷長達5 年后才由美國國會批準。⑤周帥著:《全球金融治理變革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版,第 87-93 頁。
另一方面,美國不斷利用自己在國際金融機構的主導權力實現其政治目的,造成國際金融公共產品的不公平供給。 例如在2008 年金融危機中,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資金已無法發揮作用時,美國為維持其金融體系改革的主導權,僅與其有意拉攏的國家簽署貨幣互換協議,那些不被美國重視的國家則很難得到有效救助,這也使得巴西和韓國主持的二十國集團峰會的會議議程和政策協調受到美國很大程度的影響。⑥劉瑋、邱晨曦:“霸權利益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形式的轉換——美聯儲貨幣互換協定興起的政治邏輯”,《國際政治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78-96 頁。“當工業化國家政府和市場參與者支持改革時,這些改革政策就能得以實施;而發展中國家支持改革時,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出現。”因此,國際層面的決策結果往往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其金融部門的壓力和偏好所決定的。⑦Stephany Griffith-Jon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Market Efficiency as a Global Public Good”, in Inge Kaul et al.,ed.,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Managing Glob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35-455.
其三,私物化行為造成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困境使得新興力量對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產生質疑,而美國已無力支付打消這些質疑所需的成 本。 約 翰 · R · 康 芒 斯 ( John Rogers Commons)曾指出建立經濟組織的目的是協調交易雙方的矛盾,從而避免實際的或可能發生的各種沖突。⑧黃立君:“康芒斯的法經濟學思想及其貢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 年第 5 期,第 92-96 頁。美國倡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之所以持續,是因為它曾經為其他國家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收益,并在國家間互動中具有可預測性。⑨Rebecca Friedman Lissner, Mira Rapp-Hooper, “ The Day after Trump: American Strategy for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1, No.1, 2018, pp.7-25.對于美國而言,“設計”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是其獲得政治影響力和維持霸權的最主要方式,對于其他國家行為體,“參與”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是獲得這些利益的重要途徑。 當現行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已無法解決雙方矛盾和緩解沖突時,國際經濟組織的合法性也必然遭受質疑,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參與國的收益也會大幅下降,一旦收益受損,這些國家的參與積極性必將大打折扣。2008 年金融危機后,各國除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增加非西方國家的代表權等一些問題中擁有較為明確的共識以外,對于如何塑造一個既能代表新興國家等更廣泛行為體的利益又可得到西方國家贊同的國際秩序似乎較少提及。①Hans Kundnani, “What is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Policy Essay of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United States, No. 17,2017, pp.1-10.正是缺乏危機管理機制及糾正對外經濟不平衡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才使得國際金融公共產品的霸權供給能力大幅下降,金融危機得以傳播與擴散,加劇了國際經濟秩序的紊亂。然而,哪怕意識到國際經濟治理結構亟需重塑,美國也并未展現對這種重塑所需的成本的支付意愿,美國能力與責任感的缺失引起了國際經濟秩序的嬗變。 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在經濟增長方面的表現逐漸分化,世界經濟的權力中心逐漸擴散,國際經濟秩序已經進入一個深度調整和變化的時期。
由此可見,國際公共產品的霸權供給機制的可持續性取決于霸權國對成本與收益的考量,一旦維持現行秩序所需的成本與獲益失衡后,霸權國便會出于自身利益考慮而削減支出,減少或中斷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使得私物化問題更加凸顯。 這導致當前國際經濟秩序中存在著大量的、明顯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做法和偏向,并沒有實現戰后國際秩序構建的最初目標。這種游離于解決國際經濟活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以維護和促進西方國家的利益為目標的經濟秩序,勢必遭到其他國際經濟行為體的質疑與挑戰。
三、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塑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通過對1500—1990 年中世界經濟現象的研究指出,國家同人一樣有生命周期,國家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也經歷著世界地位的興衰,從而決定著其在世界經濟中所處的地位。②[美]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著,高祖貴譯:《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 349 頁。2008 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昭示了霸權的衰落和西方世界“黃金期”的落幕。 2016年特朗普上臺執政后,美國開始試圖親手打破這個戰后由自己打造的國際經濟秩序。 由于認為在此秩序下已無法充分維護既得利益,特朗普政府時期曾多次發生大幅中斷承擔國際義務的行為,如2017 年以來,美國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巴黎協定》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還揚言退出世貿組織。③朱劍:“特朗普政府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背棄抑或支持?”《國際論壇》,2020 年第 3 期,第 80-99 頁。西方世界“黃金期”的落幕伴隨著新的國際經濟力量的崛起,新興經濟體已成長為世界經濟活動的重要參與者,正在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推動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深刻的變化,全球經濟的“新”“舊”力量正在發生激烈碰撞,全球進入了全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探索期。④佟家棟、何歡、涂紅:“逆全球化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開啟”,《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2 期,第 1-9 頁。
從歷史上看,國際經濟秩序的構建過程就是各行為體經過協商,在世界范圍內通過參與國際公共產品“設計”“創造”和“供給”形成符合自身理念和經濟利益的國際行為規則的過程。 雖然國際經濟秩序正處于一個混沌分裂的探索期,這并不意味著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會立刻出現。 國際社會并不能找到一個具有絕對經濟優勢以及政治優勢的國家替代美國充當國際經濟秩序引領者的角色,新興力量仍舊沒有足夠強大的實力顛覆西方國家長期堅守的“自由主義”經濟秩序觀。 在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和分配不均背景下,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對供給與需求的差異深化促使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積極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經濟機制和規則創新,推動國際經濟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變革。
3.1 通過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優化區域經濟秩序
區域合作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參與經濟秩序重塑的突破口,區域性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夠為全球經濟秩序的變革提供更大動力。 與國際公共產品相比,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有幾點獨到之處:其一,區域性公共產品由于參與成員數量較小、溝通更為方便從而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更容易實現供應;其二,區域內的對話與合作機制只發生在一定區域內,交易成本大大少于國際公共產品并更易平攤,可避免大國“私物化”問題;其三,由于范圍相對較小,各參與方的成本收益更加清晰,責任也更為透明,更利于避免國際公共產品的“搭便車”現象。①樊勇明、薄思勝著:《區域公共產品理論與實踐——解讀區域合作新視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8 頁。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國際經濟秩序產生了巨大沖擊,經濟全球化出現了許多新的發展趨勢。 其表現之一就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載體開始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全球性的國際經濟組織轉向區域性的多邊合作機制。②樊勇明:“從國際公共產品到區域性公共產品”,《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 年第 1 期,第 144 頁。這意味著區域性公共產品在促進區域合作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創新變革中具有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隨著區域合作的深入,其發展趨勢將與全球化更加同步,最終對全球化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③黃寧、酆佩:“經濟區域化與全球化發展及其關系分析”,《經濟問題探索》,2015 年第 9 期,第 133 頁。
因此,地區間國家合作供給區域性公共產品將是未來的趨勢。 區域經濟合作的興起源自于各行為體在共同利益基礎下對解決域內存在的經濟治理問題的需求。 對中國而言,應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中歐投資協定》(BIT)的落實,保持對《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談判的開放態度,掌握地區經濟合作規則變革的主動權。 RCEP 和BIT 是區域多邊主義在逆全球化浪潮中的最新勝利成果,是中國參與主導未來多邊主義的國際貿易體系的重要經驗。 RCEP、BIT 和 CPTPP 等地區合作協議也有助于地區成員對接國際高水平規則,加快國內經濟轉型及經貿規則創新,提高各成員國參與國際經濟秩序重塑的能力,繼而逐步破除有關發達國家對中國在貿易規則制定領域的“規鎖”。④任琳、彭博:“全球治理變局與中國應對——一種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視角”,《國際經濟評論》,2020 年第1 期,第108-123 頁。可以看到,中國正用實際行動在開拓區域經濟合作的新高度,在未來的合作中,中國在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大環境下,將關注與合作方共同利益的拓展,繼續創新提供而更多的區域性公共產品,通過主導重塑區域經濟秩序增加未來國際經濟秩序變革的自身分量。
3.2 重視金磚國家、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平臺建設,在平臺改革中起到領導作用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間的相互依賴也逐漸深化復雜,越來越多的問題需要區域間或區域內國家的集體行動才能有效解決。 由此產生的最緊迫問題體現在現有國際經濟體制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區別對待的“雙重標準”和全球發展融資面臨的巨大缺口上。 例如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具的方案非但沒有幫助陷入困境的各國,反而惡化了各國的經濟政治環境。 又如2008 年經濟危機爆發后,現有國際金融機制暴露出嚴重的問題,受到許多國家的質疑。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的領導位置大多由西方國家所占,這意味著在這些重要的國際機構中,西方國家掌握著重大事項的否決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被動位置,并無足夠的話語權。 盡管中國是以上這些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重要成員,但影響力仍十分有限,中國仍難以順利推動相關改革的進行。
近年來,中國逐漸意識到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在體現發展中國家經濟利益訴求方面的缺陷,開始逐步采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提出“中國式”解決方案。 中國參與提出并主導構建了金磚國家開發銀行(NDB)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并積極準備籌建上合組織開發銀行(SCO Development Bank),這些措施逐步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也傳遞出中國特色的經濟治理理念。 中國在國際層面的對話平臺中,需要加強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合作與交流,為發展中國家謀求更多的話語權,團結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中用同一個聲音說話。中國更應該利用自身經濟大國的優勢來推進區域性和國際性經濟合作平臺的構建,這樣其國際公共產品和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者的角色才會得到更多認可。 在今后,中國應繼續加強金磚國家、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等經濟治理平臺建設的參與力度,同時通過這些平臺倒逼世界銀行等全球機構治理規則的調整,將中國所秉持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逐漸替代長久以來盛行的西方片面“自由”觀念,成為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格局的核心關鍵詞。
3.3 通過“一帶一路”向沿線國家提供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打造中國國際經濟秩序觀
2013 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中國一直積極倡導利益共同體的理念,“一帶一路”逐步成為滿足各國現實經濟利益的合作構想。 中國政府也公開表示:“‘一帶一路’構想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歡迎各國、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都能參與到具體的合作中來。”①王毅:“‘一帶一路’構想是中國向全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中國新聞網,2015 年 3 月 23 日,http:/ /www.chinanews.com/gn/2015 /03-23 /7151640.shtm。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創造了多種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倡議中包含政策溝通、貿易暢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板塊,側重于從供給的角度改善當地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準備,進而促進當地經濟進入持續增長的良性發展周期。
“一帶一路”倡議的要點是促進區域間合作,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無法解決個體間巨大差異的情境下,中國推動并合作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成為勢在必行的舉措。 從供給角度來看,全球治理模式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往往受制于供給主體的結構性權力,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均強調了物質性權力對秩序建構的重要性。 從需求角度來看,國際區域間巨大的偏好差異性成為造成國際公共產品供給陷入困境的一大原因,自由主義者雖然強調國際制度對國家間合作的重要性,但卻并未將權力失衡會對合作產生制約的問題納入重點考察范圍。 中國已經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了豐富的經貿交流與合作,也制定了更長遠的公共產品供給規劃,這表明了中國借助“一帶一路”在未來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重要作用的決心。
當前中國正在引領發展中國家進行一場國際經濟新秩序變革。 基于區域間經濟合作,“一帶一路”倡議、亞洲投資發展銀行等相繼推出了各項經濟舉措,構成了中國國際經濟秩序觀的重要內容。 以上舉措有別于以往的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有利于中國主導開創區域經濟秩序重塑的新局面,向世界展示中國國際經濟秩序觀。 正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所體現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是達成其他各項目標的基礎。②胡鞍鋼、周紹杰、任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 2 期,第 17-22 頁。羅斯瑪麗·富特指出:塑造中國國際秩序觀的重要因素在于其經濟發展與國內穩定如何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國際體系內主導國家的影響。③Rosemary Foot, “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2, No.1, 2006, pp.77-94.作為一種全新的國際關系模式,中國與鄰國通過構建區域核心競爭力實現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有助于實現有關國家對經濟秩序供需差異的良性匹配。 通過重塑所在國經濟發展模式、提高要素流動的物流效率、降低要素運輸成本等方式促進同其他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的對接,繼而增強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重塑中的地位。④黃河:“公共產品視角下的‘一帶一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 年第 6 期,第 138-155 頁。中國應當繼續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為國際貿易新秩序的塑造貢獻中國力量。
3.4 深化亞投行的金融性區域公共產品的供給與創新,促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由于現有全球性或區域性多邊開發銀行主要由發達國家籌資興辦,內部決策往往反映出發達國家的偏好。 盡管更多的落后地區或國家迫切需求的是基礎設施建設,在多邊開發銀行內更受到重視的卻是如環境、人權、教育等議題。 以亞洲開發銀行為例,由于主導國日本更加關心有關環境凈化保護的議題,因而拒絕增加對煤礦基礎設施的投入①Smita Nakhooda, “Asia,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and Energy Governance,” Global Policy, Vol.2, Special Issue, 2011,pp.120-132.。 但一些落后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缺乏相應的資金和技術,在其他產業尚未得到充分發展的時期,對自然資源的開采與出口在其經濟結構上仍占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因為投票權占比較少而難以得到表達。 這方面的矛盾導致經濟落后的國家在基礎設施發展上得不到應有的援助。 亞投行的組織結構決定了發展中國家的需求是亞投行關注的重點,而亞投行內部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也因為設立了以下兩個部門而得以彰顯:其一是亞投行特別設立的負責解決投訴、評估所有業務項目和實施反欺詐、反腐等廉潔調查的合規局(CEIU),由董事會直接管理,部門成員有機會直接向董事會成員報告工作;其二是國際咨詢小組(International Advisory Panel),成員由行長任命,任期為兩年,小組成員獲得小額酬金并不會收到薪水,銀行支付與小組會議相關的費用。 亞投行成立此小組的目的是支持高級管理人員就亞投行的戰略和政策以及為一般性業務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亞投行作為中國自發領導建立的國際金融機構,是中國向世界貢獻的符合新興國家利益訴求的國際金融公共產品。 亞投行是中國在國際制度領域探索新型合作的嘗試,滿足了亞洲各國的發展與合作要求,填補了現有國際性或區域性金融機制存在的薄弱環節。 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例如印度、孟加拉國、菲律賓等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安排與機制,鞏固各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將他們與中國未來的發展緊密聯系起來,實現亞洲共同繁榮發展的新局面,成為促進亞洲經濟區域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
3.5 探索大國合作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可能性與具體路徑
為應對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嬗變,中美可以通過合作的方式進行國際公共產品和區域性公共產品的共同供給,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做出貢獻。 于美國而言, 將新興經濟力量納入國際經濟機制,分擔該體系的一定義務,可降低交易成本并擴大按現有主導規則行事的主導國數量;于中國而言, 與美國合作供給國際公共產品,有利于世界經濟穩定發展,體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訴求,亦是國內經濟發展對于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的內在需要。 中美可通過構建提高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大國協調機制,將重點放到資金籌集這一核心問題,解決當下嚴重的“搭便車”行為。 具體而言,可在這一機制下關注托賓稅、特別提款權、官方和私人資金的投入三方面,主導行為體參與國際合作,從而改善國際公共產品供應。②黃河、朱適:“論中美‘共主’的可能性”,《現代國際關系》,2008 年第 2 期,第 28-32 頁。
大國依舊是全球性和區域性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和維護者,大國在公共產品領域的互動博弈對全球治理實現的影響最為深刻。 因此,積極斡旋世界主要大國關系仍是構建未來全球經濟秩序的關鍵。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仍需要通過實現與大國的雙邊有益互動來規避沖突,構建良性競爭關系,增進大國互信,縮小主要大國對國際公共產品的供需差異,并推動各方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的關鍵領域達成共識。
隨著中日間關系的緩和,日本逐步改變了對“一帶一路”的消極態度,并表達了與中國共同參與推進在沿線國家的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意愿,這種態度轉變是伴隨其國內在經濟上尋求更多自主性的訴求出現的。③王競超:“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日本的考量與阻力”,《國際問題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81-93 頁。2018 年5 月,中日雙方簽署了《關于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 這意味著中日間經濟合作出現新的可能,是基于兩國日益密切的貿易往來和產業內和產業間的優勢互補。 自第三方市場合作由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以來,在2015 至2019 年間,中國同法、英、日、德等15 個國家開展了第三方市場合作,有關成果接連涌現。 這成為中國探索大國合作途徑的最新進展,也成為中國同大國合作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全新模式。 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形式促進了大國間經濟的緊密合作,有助于緩解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中的矛盾,也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重塑過程中的影響力。
3.6 以“擴散性互惠”為理念同發展中國家實施更深層次的經濟合作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正在國際經濟秩序重塑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以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方式不斷深化為特征,中國的外交實踐出現了新的理念變化。 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建立在擁有更多的觀念共性基礎上,雙方在發展模式和自主權等議題上觀點一致,而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相互需要和依賴關系正為合作的深化打下堅實基礎。 中國正以“擴散性互惠”為理念進一步建立“非對等”價值交換的國際經濟合作體系。①黃河、戴麗婷:“‘一帶一路’公共產品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太平洋學報》,2018 年第 8 期,第 50-61 頁。羅伯特·基歐漢區分了國際合作中兩種互惠類型,一種是“特定型互惠”(specific reciprocity),另一種是“擴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特定型互惠”的特點是即時性的利益交換,通常價值對等。 “擴散性互惠”,不刻意追求及時的利益對等,而是關注長時間內總體利益的均衡。②Robert O. Keohane, “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0, No. 1, 1986, pp. 1-27.“擴散性互惠”的經濟合作理念具體體現在中國創建的符合發展中國家經濟利益需求的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上。這種互惠有助于維持經濟合作的可持續性,繼而促進合作參與國的和諧共處,實現多領域的利益均衡。 在今后,中國應繼續秉持這種理念,在世界經濟合作體系的規則重塑過程中,拓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經濟合作范式和規范,促使國際經濟秩序朝向更加公平的方向演變。
四、結 論
霸權的相對衰落與新興力量的出現引起了一系列國際經濟行為體實力結構的變化,國際公共產品作為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主要手段也面臨供給不足和分配不均的現狀,國際經濟秩序單靠慣性已經無法維持。 當下的全球格局告訴我們沒有一種國際經濟秩序可以永恒存在,它會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結構的演變及國際重大事務的發生經歷不斷地調整和變遷,國際公共產品同霸權國的存在也不具有直接因果關系,非霸權國家也可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供給方案,以參與到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塑中。
2020 年12 月,習近平主席在《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一文中指出,“全球治理體系只有適應國際經濟格局新要求,才能為全球經濟提供有力保障。”③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求是》,2020年第24 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全球治理體系作出一系列重要闡述:“當今全球發展深層次矛盾突出,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思潮抬頭,多邊貿易體制受到沖擊,世界經濟整體發展環境面臨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這些都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需要各國協作共同治理”。 “人類社會要持續進步,各國就應該堅持要開放不要封閉,要合作不要對抗,要共贏不要獨占”,“開放合作是促進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時代要求”。 這說明,推動開放合作的國際治理是我國新時代的重要使命,面對當前國際治理面臨的諸多挑戰,構建更為開放合作的國際治理體系是中國參與甚至引領國際經濟秩序重塑的必然選擇,同時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 全面開放是中國向世界的承諾,同時也是中國積極參與和促進全球治理發展的宣言書。
中國推進開放合作的全球治理體系建設與完善,從理論視角看其關鍵就是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通過全球治理理念、規則和制度的改革與完善,構建開放合作的全球經濟新秩序。 隨著全球公共產品霸權供給模式的日漸式微,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所倡導與踐行的統籌合作供給模式正日益成為全球治理的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帶一路”、亞投行、絲路基金、上合組織貨幣互換機制等皆是中國通過提供公共產品來參與全球治理、彰顯大國責任的良好范例。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而言,樹立開放合作的國際治理體系、推進國際經濟秩序的完善要求更多的新興力量加入到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合作中去。 不同于霸權供給方式,中國在這一過程中正在統籌國內和國際供給、政府和市場供給、實體和數字供給、單邊和多邊供給、多元和多方供給。 這種國際公共產品的統籌供給模式是相較于霸權供給模式的更優選擇,也體現了中國在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中的模式創新。
現今國際經濟秩序面臨的多重挑戰對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提出了更高需求。 在未來,中國如何引導塑造國際公共產品的統籌供給這一創新模式,構建開放合作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推進世界秩序朝著更加公平、更具廣泛代表性的方向發展,是值得學界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