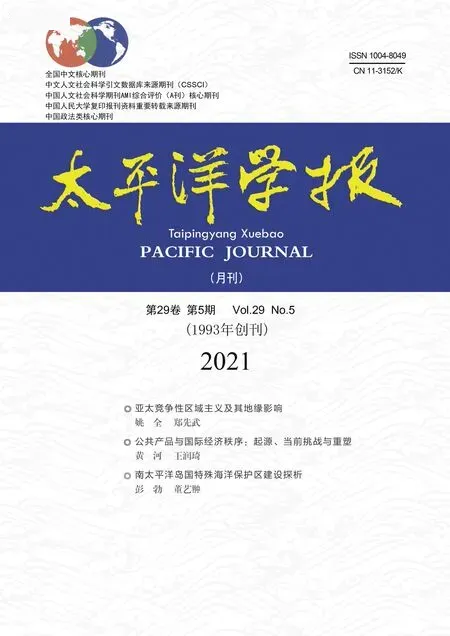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探析
彭 勃 董藝翀
(1.浙江海洋大學,浙江 舟山316022)
隨著人類海洋開發活動的持續加劇,全球海洋生態系統正遭受污染加劇、棲息地喪失、氣候變化和過度捕撈等一系列人為破壞。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 年提出建設“海洋命運共同體”倡議,期望各國共同保護海洋生態文明,超越人類不顧氣候變化和自然資源枯竭等傳統利用海洋、開發海洋的模式,從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從包括人類在內的地球生命的角度,均衡、全面地認識海洋。 雖然太平洋在世界四大洋中最為浩瀚、寬廣,但諸多海洋國家同樣面臨海平面上升、漁業資源短缺、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生存問題。 尤其是南太平洋島國①本文主要研究對象南太平洋島國是指大洋洲除去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之外的14 個島嶼國家,分別是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基里巴斯、庫克群島、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瑙魯、紐埃、帕勞、薩摩亞、所羅門群島、湯加、圖瓦盧和瓦努阿圖。 “大洋洲”,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訪問時間:2021 年 1 月 9 日。承受的生存壓力最為突出。 南太平洋地區的海洋生態系統極為復雜、脆弱,加之南太平洋島國均為典型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既對海洋資源極度依賴,又對海洋生態環境變化十分敏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系統成為南太平洋島國的首要任務。 基于這種現狀,南太平洋島國在《2021 年藍色太平洋海洋報告》中強調,南太平洋地區各國應積極參與海洋治理,繼續維護和改善藍色太平洋的健康、生產力和復原力。①“Blue Pacific Ocean Report 2021: A Report by the Pacific Ocean Commissioner to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Leaders”, Office of the Pacific Ocean Commissioner(OPOC), 2021.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諸多南太平洋島國通過建立眾多的保護區域,有效解決了棲息地退化和漁業資源衰退的世界性難題,一躍成為全球海洋保護區建設的主力。②鄭苗壯:“全球海洋保護區建設呈現新趨勢”, 中國自然資源報,2020 年 6 月 18 日。 http:/ /www.iziran.net/shendu/202006 18_125086.shtml。因此,分析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的現實動因、建設模式與未來走向,借鑒其建設經驗,對于中國把握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未來走向及制定相關的海洋保護區政策,從容應對全球海洋生態環境的深刻變化具有重大意義。
國內學術界關于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的研究并不多見,主要集中論述南太平洋區域海洋治理。 有學者關注區域海洋機制,對南太平洋區域海洋機制形成的歷史和特征作了進一步的討論;③曲升:“南太平洋區域海洋機制的緣起、發展及意義”,《太平洋學報》,2017 年第 2 期,第 1-19 頁。也有學者從治理客體出發,分析了南太平洋地區的區域漁業資源治理現狀,并對中國的漁業資源保護提出了對策建議;④應曉麗、崔旺來:“太平洋小島嶼國家漁業資源區域合作管理研究”,《太平洋學報》,2017 年第 9 期,第 70-77 頁。還有學者從海洋合作治理的角度出發,分析各國參與南太平洋島國區域海洋治理的邏輯動因;⑤梁甲瑞:“中法南太平洋地區海洋治理合作:內在邏輯與現實選擇”,《海洋開發與管理》,2021 年第 2 期,第 41-48 頁;余姣:“人海和諧:中國與南太平洋島國海洋治理合作探析”,《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19 年第 1 期,第 96-102 頁;梁甲瑞:“德國參與南太平洋地區海洋治理:方式、動因及意義”,《國際論壇》,2019 年第 1 期,第 127-142+159-160 頁。更有學者從全球海洋治理的角度出發, 結合南太平洋區域海洋治理同全球海洋治理理論,論證南太平洋地區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處于“先行者”的地位,并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活力;⑥梁甲瑞、曲升:“全球海洋治理視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區海洋治理”,《太平洋學報》,2018 年第 4 期,第 48-64 頁。此外,全球海洋治理進程也推動了南太平洋島國地區主義的進一步發展;⑦陳曉晨:“全球治理與太平洋島國地區主義的發展”,《國際論壇》,2020 年第 6 期,第 119-136,159-160 頁。但也有學者指出南太平洋區域海洋治理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各治理主體之間聯系亟待加強,綜合性海洋治理仍任重而道遠。⑧陳洪橋:“太平洋島國區域海洋治理探析”,《戰略決策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3-17+103 頁。相較于國內,國外對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的研究相對豐富。 有學者認為在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需要最大限度地平衡生態效益和社會經濟效益,提高社區居民的參與熱情;⑨Robertson, T., Greenhalgh, S., Korovulavula, I., Tikoibua,T., Radikedike, P., Stahlmann - Brown, P., “ Locally Managed Marine Areas: Implications for Socio-economic Impacts in Kadavu, Fiji”, Marine Policy, Vol.117, No.3, 2020, pp.103-114.也有學者認為南太平洋島國旅游業帶來的巨大經濟收益是推動海洋保護行為的重要動因;⑩Mangubhai, S., Sykes, H., Manley, M., Vukikomoala,K., Beattie, M, “Contributions of Tourism-based Marine Conservation Agreements to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Fiji”,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171, No.2, 2020, pp.106-114.還有學者提出西方國家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經濟援助為許多南太平洋島國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提供了經濟支持。?Bos, M., Pressey, R. L., Stoeckl, N., “Marine Conservation Finance: The Need for and Scope of an Emerging Field”,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Vol.114, 2015, pp.116-128.可以說,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對于我們進一步分析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提供了諸多啟示。 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認為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是指通過法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建立,一定程度上限制海洋漁業捕撈等人類商業活動,對島國周邊重要水體及相關的動植物群落、歷史及文化屬性等進行半封閉保護的特定區域。 其特殊性體現在島國政府、部落酋長、宗教及非政府組織等建設主體多元化,傳統管理手段與西方先進技術疊加的建設方法耦合化,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復合化,以及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殖民文化等相互滲透的建設理念融合化。 同時還要看到,現有研究對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特征仍然缺乏一個有效把握,也未詳細闡述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發展的現實動因與實際效果。 因此,本文在現有基礎上,著重分析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特征和現實動因、模式與措施、建設效果,并研判其未來發展動向。
一、建設概述
“小島國、大海洋”是南太平洋島國的基本特征。①陳曉晨:“小國研究視域下太平洋島國的外交策略”,《國際關系研究》,2020 第 2 期,第 108-131+157-158 頁。南太平洋島國陸地面積較小,全部島嶼國家的陸地面積不到60 萬平方千米,在廣泛分布的幾千個島嶼之中只有7 個島嶼陸地面積超過700 平方千米。②Tutangata, T., Power, M., “The Regional Scale of Ocean Governanc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Vol.45, No.11, 2002, pp.873-884.這些島嶼的面積自東向西增加,超過75%的陸地位于巴布亞新幾內亞。相較于較小的陸地面積,14 個南太平洋島國宣布的專屬經濟區(EEZ)面積達2200 萬平方千米。 廣闊的海域面積為其提供了豐富的海洋資源,同時也意味著南太平洋島國人民的生存和發展嚴重依賴海洋。 可以說,海洋保護是南太平洋島國發展戰略中重點考慮的事項。
鑒于此,南太平洋各島國積極進行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建設工作。 截至目前,南太平洋島國的特殊海洋保護區數量為430 個,總面積超過300 萬平方千米,約占全球海洋保護區面積的11%。③數據來源為 WDPA, https:/ /www.protectedplanet.net/en,訪問時間:2021 年1 月17 日。 世界保護區數據庫(WDPA)為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聯合項目,是使用IUCN 和CBD 定義陸地和海洋保護區最全面的全球數據庫。 不過南太平洋一些地方保護協議和社區管理海域未被納入統計范圍,但這些特殊海洋保護區的保護效果往往超過一般的海洋保護區,也是本文研究對象之一。其中,斐濟的特殊海洋保護區數量為122 個,是南太平洋島國中建設特殊海洋保護區數量最多的國家;庫克群島和帕勞都建立了覆蓋整個專屬經濟區的特殊海洋保護區,且庫克群島特殊海洋保護區的面積達197 萬平方千米,居14 個島國最高;而瑙魯則是眾多南太平洋島國中唯一沒有建立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國家。 從管理上看,南太平洋島國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已經從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轉向更具包容性的多元主體管理模式,部落社區、政府、宗教及非政府組織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保護區的建設與管理工作,不少保護區因其基于社區的管理模式(CBM)而被世界各國仿效。
二、現實動因
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已經初具規模。 旅游業和漁業的需求、非政府力量的影響,以及西方國家和企業的訴求成為特殊海洋保護區的驅動力。 本文基于內部動因和外部動因二元視角分析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的現實動因。
2.1 內部動因
(1)經濟驅動:旅游業和漁業影響
南太平洋島國積極的海洋保護行動與其特殊的經濟結構密不可分。 南太平洋島國大多為群島國家,人口廣泛地分布在各個島嶼,國內交易和供應成本很高。 受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當地居民的生計與發展嚴重依賴海岸帶和海洋資源。 南太平洋島國經濟主要包括旅游業、漁業、農業、養殖業、小規模制造業和相對較小的自給自足經濟,其中旅游業和漁業是大多數南太平洋島國的支柱型產業。 但過度捕撈、海洋污染等問題嚴重威脅了這些產業的發展,更威脅了這些島國的生存與發展,因此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建設顯得十分必要。
以帕勞為例,旅游業是帕勞島國的第一大產業,是其收入和就業的主要來源,約占國內GDP 總量的50%。 帕勞擁有著太平洋地區最好的海洋生態系統,其中鯊魚潛水作為旅游特色,為當地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④Vianna, G. M. S., Meekan, M. G., Pannell, D. J., Marsh,S. P., Meeuwig, J. J., “ Socio-economic Value and Community Benefits from Shark-diving Tourism in Palau: A Sustainable Use of Reef Shark Population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145, No.1,2012, pp.267-277.但是,傳統的商業捕鯊行為曾一度導致帕勞的鯊魚瀕臨滅絕的困境。 2009 年帕勞宣布成立世界上第一個鯊魚保護區,禁止一切商業捕鯊活動以保護瀕臨滅絕的鯊魚。 時至今日,帕勞的鯊魚保護區成功地保護了大錘頭鯊、豹紋鯊、海洋白鰭鯊和其他130 多種鯊魚和鰩魚。 同時,禁止商業捕鯊這一行為并沒有造成國內經濟的嚴重損失,反而通過旅游業的發展為帕勞人民帶來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業崗位,得到了國內民眾的廣泛支持,并促使當地居民積極參與到鯊魚保護區的建設與治理中。 此后,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基里巴斯、薩摩亞和馬紹爾群島也先后在專屬經濟區內建立鯊魚和鰩魚的指定特殊海洋保護區。
(2)政治推動:非政府力量影響
南太平洋島國的政治情況復雜多樣,既有類似美國的聯邦政府,也有正式的“威斯敏斯特式”政府。 長期的殖民歷史和財力單薄導致許多南太平洋島國的政府管理能力薄弱,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往往落到非政府主體的身上。 社區居民、酋長、宗教和非政府組織都是與海洋具有特殊聯系的群體,是海洋生態環境破壞的直接受害者,對海洋有著獨特的理解和關注。 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推動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詮釋對海洋的保護。
南太平洋島國長期以來深受土著部落歷史、文化和價值體系的影響。 除了正式的“威斯敏斯特式”政府之外,許多島國的政府成員本身可能擁有部落社區的身份,甚至是部落社區的領導人,他們在國家政治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此外,傳統領導人由于在地方上具有極高的威望,是一些國家政府管理地方的得力助手。①趙少峰,于鐳:“太平洋島國酋長制的演化及其走向簡論”,《世界民族》,2020 年第 3 期,第 11-20 頁。傳統觀念傾向于海洋所有權歸部落社區所有,這極大地激發了民間部落社區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熱情。②“State of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2020 Regional Report”, Apia, Samoa: SPREP, 2021, pp.59-60.部落社區作為治理主體參與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建設管理,成為南太平洋島國海洋生態環境治理能長期進行和維持的關鍵因素。
傳統宗教組織,主要是基督教會對南太平洋島國的特殊海洋保護區管理具有重要影響。盡管部落社區在最初創建和擴大保護倡議方面是熱情的支持者,但其支持力度會根據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突發情況而增減。 同時,不同社區和部落在傳統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導致海洋保護行為只是孤立片面地進行。 基督教會本身擁有巨大凝聚力,可以有效協調各個社區和部落。③Lyons, K., Walters, P., Riddell, E., “The Role of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Case of Forestry in Solomon Island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Vol.18, No.3, 2015, pp.342-360.不同的社區、部落因為相似的傳教歷史而擁有同一宗教信仰,讓原本沒有交互的部落和社區之間產生聯系。 此外,宗教領袖在地方上具有極高的威望,可以團結各個社區和部落,使之從零散的保護行為上升為有組織、規模化的保護網絡。
非政府組織也是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的重要一環。 其獨特的影響力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 首先,非政府組織擁有制定管理計劃所需的人員、資金和技術,能夠有效彌補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中資金和技術的匱乏,為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建設提供支持。其次,非政府組織能夠積極引導和組織社區居民開展各項保護活動,在活動中提高民眾對于海洋生態保護的認識。 最后,非政府組織通過自身渠道廣泛吸引更多的權威人士關注南太平洋地區海洋生態環境問題。
2.2 外部動因
(1)資本推進:西方國家訴求
南太平洋島國有著400 多年的殖民史。 雖然二戰結束后各國相繼宣布獨立,但由于長期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和價值體系的沖擊,許多島國并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 西方國家在南太平洋島國仍具有較高的話語權,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參與了南太平洋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 而且南太平洋的海洋戰略部署是西方海洋強國的現實需要,特殊海洋保護區因其特殊的戰略作用,成為各國的關注點。
西方國家的援助計劃推動了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 澳大利亞、美國、日本和新西蘭是南太平洋島國的主要援助國,自身海洋安全或經濟利益訴求是援助國為南太平洋島國提供海洋保護資金的主要原因。 澳大利亞2017 年發布的外交政策白皮書中指出,維護南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穩定對于共處于同一片海域的澳大利亞極為重要。 美國、日本、新西蘭等國家也期望通過與南太平洋島國共建特殊海洋保護區,提升本國在太平洋海域的影響力。2008 年—2017 年近 10 年來,澳大利亞、美國、日本和新西蘭等國家為南太平洋島國提供7 億美元官方援助資金用于海洋環境和漁業資源保護,①數據來源:OECD, https:/ /stats.oecd.org/,訪問時間:2021年 1 月 23 日。為諸多特殊海洋保護區提供建設和管理所需的資金和設備。 可以說,西方國家提供的援助資金和項目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南太平洋海洋生態環境,但也導致南太平洋島國的海洋資源政策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國家。
(2)技術拉動:西方企業訴求
西方企業訴求影響著南太平洋島國政府的海洋資源開發保護政策。 南太平洋島國海洋資源豐富,但各島國資源開發保護能力薄弱,同西方企業合作建設特殊海洋保護區成為“雙贏”選擇。 2008 年,新英格蘭水族館、英國海洋中心與基里巴斯政府共建菲尼克斯群島保護區就是一個典型案例。②Rotjan, R., et al., “Establishm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hoenix Islands Protected Area”, Advances in Marine Biology, Vol.69, 2014, pp.289-324.新英格蘭水族館和英國海洋中心利用海洋潛標、自治式水下潛器、無人遙控潛水器等觀測設備,以及衛星遙感技術和無人機等近地遙感技術,依托覆蓋“航空航天、海面、水體、海底”的全方位、立體化海洋數據監測系統,在位于夏威夷和斐濟之間海域建立菲尼克斯群島保護區。 新英格蘭水族館、英國海洋中心獲得基里巴斯海洋油氣資源的優先開采權,并在保護區決策上具有直接的影響力。③Mallin, M. F., Stolz, D. C., Thompson, B. S.,Barbesgaard, M., “In Oceans We trust: Conservation, Philanthropy,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hoenix Islands Protected Area”,Marine Policy, Vol.107, No.2,2019, pp.1-12.
三、建設模式
在諸多現實因素的推動下,南太平洋島國積極推進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 在眾多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實踐中,以斐濟、所羅門群島、帕勞和庫克群島四個南太平洋島國最具代表性,它們對于闡明政府和宗教以及社會因素如何影響特殊海洋保護區功效等問題提供了充分的解釋力。 因此,解析這四個島國獨特的海洋保護區建設模式和具體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3.1 斐濟模式——酋長驅動
位于南太平洋拉美尼西亞群島的斐濟,是覆蓋332 個島嶼的群島國家,其中100 多個島嶼有人居住。 地方集權和社會分層是斐濟政治體制的顯著特征,酋長是社會政治生活的核心,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和權力。④Mills M., Jupiter S. D., Pressey R. L., Ban N. C., Comley J., “Incorporating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in a National Marine Gap Analysis for Fiji”, Conservation Biology, Vol.25,No.6, 2011, pp.1155-1164.斐濟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極具特殊性,斐濟是本地管理海洋區域(LMMA)的發起者,也是基于社區管理的海洋保護區建設典型。
斐濟的酋長驅動模式經歷四個階段的演變。 上世紀90 年代以前,斐濟沿襲著“百日哀悼酋長”活動。 當一個部落社區的酋長去世時,部分漁場劃為禁漁區,以此表達對酋長的尊敬。100 天后該海域重新開放,社區收獲魚類舉行宴會并結束哀悼活動。 這種暫時性的禁漁行為使得100 天禁漁期結束時捕獲量增加,通常被社區民眾視為酋長的“超自然力量”。 隨著“百日哀悼酋長”傳統活動的世代傳承,社區民眾逐步認識到較長或永久封閉部分近岸水域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禁漁區的溢出效益。⑤Elodie Fache, Annette Breckwoldt, “ Small-scale Managed Marine Areas Over Time: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in a Local Fijian Reef fishe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220,No.3, 2018, pp.253-265.到了90 年代中期,一些科研人員開始在斐濟進行各種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護區項目,“百日哀悼酋長”這一傳統的保護活動很快被他們視為項目的關鍵。科研人員開始與各個社區的酋長進行商討,希望能進一步推廣這種傳統保護模式。 在他們的努力下,本地管理海洋區域模式產生,酋長與社區居民簽訂聯合協議,永久劃定一部分漁場(約10%~20%)作為特殊海洋保護區,其余部分留給社區成員捕撈作業,將最初臨時性、不確定性的保護行為常態化。 2000 年,考慮到各個社區之間信息的閉塞,斐濟政府聯合酋長、非政府組織和科研機構建立了本地管理海洋區域信息平臺,旨在讓各個社區可以在平臺上相互學習并改善其特殊海洋保護區管理效果。 平臺的搭建吸引了更多的成員關注斐濟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并且數量在隨后的十幾年里呈指數增長。①LMMA, https:/ /lmmanetwork.org/, 訪問時間:2021 年 1月27 日。更多的管理方法也在平臺中得到推廣,包括限制破壞性漁具、減少陸上威脅、適應氣候智能解決方案、備災應急方案等。 到了2009 年,超過250 個社區已經建立了本地管理海洋區域,覆蓋了斐濟超過25%的近岸地區,②“State of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 2020 Regional Report”, Apia, Samoa: SPREP, 2021, p.60.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初具規模。
目前,斐濟所屬島嶼已有420 多個社區酋長和居民協定的特殊海洋保護區,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為社區提供現代化管理技術和資金支持,目的是通過特殊海洋保護區的溢出效應提高捕撈量;保護區外的近岸海域留給社區成員捕撈作業,保障漁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各個特殊海洋保護區遵循傳統創建儀式,不僅對封閉水域進行標記,而且舉行正式集會并通知周邊部落居民。 由于保護區給當地居民帶來巨大的收益,越來越多的社區開始對這一模式進行效仿。
綜上,斐濟的酋長驅動模式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自治,酋長在特殊海洋保護區管理過程中發揮著主要作用;同時,保護區的建設還有賴于當地政府、非政府組織、研究人員等的現代化管理技術和資金支持。 可以說斐濟的本地管理海洋區域模式是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的成功范本,為世界各國的海洋保護區建設提供了指導方針。
3.2 所羅門群島模式——宗教驅動
同樣位于拉美尼西亞群島的所羅門群島是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國內大多數人依靠捕魚為生。 沿海漁業和海洋資源對于所羅門群島人民來說極為重要,不僅供應蛋白質和微量營養素,也是為數不多的現金收入來源之一。 和斐濟不同的是,受定居模式和利益分配的影響,所羅門群島鄰近的村莊形成區域性部落群體。這些部落群體具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特征,且部落首領的海洋保護區建設意愿會根據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緊急情況而增減,但由于類似的傳教經歷,所羅門群島部落首領和民眾的信仰呈現高度一致性特征,基督教為國教。 由于缺乏人力、技術和財政能力,政府和地方的聯系并不緊密,各個島嶼對海洋資源和環境的保護更多依靠宗教組織,形成了特殊的跨部落水域的保護區管理模式。
基督團契教會(CFC)在所羅門群島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教會成立于20 世紀50 年代末,是一個將基督教教義和當地傳統民俗結合起來的組織。③Shankar Aswani, Simon Albert, Mark Love,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Critical Insights for Effective Community-base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Melanesia”, Marine Policy, Vol.81, No.6, 2017, pp.381-391.雖然部落擁有陸地和海洋的傳統占有權,但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的教會領袖,在當地海洋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方面擁有強大的話語權和巨大的影響力,成為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實際管理者。 教會領袖引進西方專業知識和技術管理特殊海洋保護區,同時保留當地部落的傳統民俗,并將其與基督教的重要節日相結合。 每年的感恩節,教會領袖帶領部落群體進行禮拜,感恩海洋的饋贈并為海上捕撈作業的親人祈福;復活節期間,各個部落之間相互贈送復活節彩蛋,預祝部落民眾的健康和海洋生物群體的繁榮;在最為重要的圣誕節,各個部落不僅為耶穌慶生,還在特殊海洋保護區內開展一系列聯合保護行動,主教、部落首領和民眾進行珊瑚礁的培育和魚苗的放生。 此外,不同部落之間出現海域所有權分歧和爭議時,教會領袖常會出面協調,運用教會教義和海洋保護理念緩和部落間的矛盾沖突。 因此,所羅門群島的宗教驅動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方式既借助“上帝”的影響力、又注重現代管理技術的運用,還關注傳統海岸管理方法的恢復,實現了三者的動態平衡。 通過宗教組織在各部落之間的協調,所羅門群島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不再局限于單一部落所擁有的海域。 目前所羅門群島已建立了超過70 個跨部落水域的特殊海洋保護區,覆蓋了接近2000平方千米的近海海域。
3.3 帕勞模式——政府驅動
位于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帕勞,從1885 年開始,相繼被西班牙、德國、日本和美國的殖民政府統治。 帕勞擁有著與美國高度相似的政治體制,國家憲法以美國的民主思想為基礎,同時也嘗試賦予習慣法和成文法平等的權力來振興風俗習慣,①Tom Graham, Noah Idechong, “Reconciling Customary and Constitutional Law: Managing Marine Resources in Palau, Micronesia”,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Vol.40, 1998, pp.143-164.地方具有高度的自治權。 海洋資源的所有權屬于州政府,《帕勞共和國憲法》授予各州“12海里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資源(高度洄游魚類除外)的專屬所有權”。 同時《帕勞共和國憲法》還授予國會“管理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勘探和開發的權力”。 在州政府和國家政府的推動下,帕勞的特殊海洋保護區網絡得以建立。
各州政府在20 世紀80 年代開始行使海洋資源自我管理權,到了90 年代中期,各州政府都通過立法的形式確立特殊海洋保護區并對區域內的漁業捕撈進行管制。 但是,1998 年的大面積珊瑚礁白化事件導致各州政府和國家政府開始反思現有的保護區體制的弊端。②Golbuu, Y., et al., “Palau’s Coral Reefs Show Differential Habitat Recovery Following the 1998-bleaching Event”,Coral Reefs,Vol.26, No.2, 2007, pp.319-332.一些議會成員指出,各個州政府互不連通的管理模式是問題的根源,并提出要建立連通各州保護區的特殊海洋保護區網絡以推進帕勞海洋的可持續發展。③Gruby R. L., Basurto, X., “ Multi-level Governance for Large Marine Commons: Politics and Polycentricity in Palau ’ s Protected Area Network”,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Vol.36,2013, pp.48-60.帕勞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上作出的保護承諾也是推動特殊海洋保護區網絡構建的重要原因。
2015 年,帕勞總統簽署了《國家海洋保護區法案》,確立一個面積約50 萬平方千米的大型海洋保護區,除20%的海域向當地人開放,剩余海域嚴格禁止漁業捕撈,尤其是外國漁船的商業捕撈行為。 國家政府設立專門機構進行管理,并將原本保護區的州政府管理機構嵌套在國家機構之中,標志著帕勞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由“點狀式”步入“網狀式”。 同時,政府認識到僅憑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無法實現保護的預期效果。 因此,在特殊海洋保護區網絡建立之初,政府就通過州政府管理機構開通專門的渠道,鼓勵社區居民針對特殊海洋保護區網絡的建設相互交流、提出建議,這極大地激發了社區居民的參與熱情。 在當地社區居民的呼吁下,許多傳統漁業管理舉措被特殊海洋保護區網絡所使用。 例如,帕勞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名為“布爾”(bul)的傳統,在魚類產卵和進食期間留有足夠數量的礁石區,以減輕漁業捕撈帶來的損害。 目前,國家政府正在特殊海洋保護區網絡內推廣這一舉措。
3.4 庫克群島模式——聯合驅動
位于波利尼西亞群島的庫克群島是世界上海洋與陸地面積之比最高的島國之一。 國內對海洋資源的開發與保護極為重視。 在庫克群島,除了政府是特殊海洋保護區的有力推動者之外,非政府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當地居民的資源保護意識。 例如島內的Te Ipukarea Society(TIS)組織成員信奉“土地和海洋資源是當代人留給子孫后代的寶貴財富”。④“We Do Not Own Our Land and Marine Resources but Borrow Them from Ou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Need to Leave Them in Good Condition”, TIS, https:/ /www.tiscookislands.org, 訪問時間:2021 年 1 月 21 日。傳統領導人在庫克群島同樣具有較高聲望,島內設有酋長院,由分散在各島嶼的20 位酋長組成,經常就海洋資源使用和傳統習俗向議會和政府提出建議。 早在2012 年,庫克群島總理亨利·普納在第43 屆太平洋島國論壇領導人會議上就提出建立大型海洋公園的目標。 隨后的幾年中,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傳統領導人成立聯合委員會積極開展行動,調查有人居住島嶼的產權歸屬,以確保國家對海洋公園的所有權。
2017 年,在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傳統領導人等主體的聯合推動下,庫克群島建設了世界上第一個涵蓋整個專屬經濟區的特殊海洋保護區——馬拉·莫阿納(Marae Moana)海洋公園。①Henry Puna, “Rights of the Ocean Need to Be Explored,”SPREP, 2017Marae Moana 意為神圣的海洋,覆蓋了國內接近200 萬平方千米的專屬經濟區,是世界上最大的由單一國家保護和管理的特殊海洋保護區。 如何在廣闊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內達到預期的保護效果成了庫克群島亟需面對的挑戰。聯合委員會希望通過協商和空間規劃等包容性進程實現海洋綜合管理和養護的模式。 馬拉·莫阿納定位于多功能型海洋保護區,特殊海洋保護區借鑒澳大利亞大堡礁分區管理辦法,根據庫克群島人民的需要和經濟、文化、社會和環境需求來劃定具體功能區,覆蓋保護敏感珊瑚礁的“禁錨”區域、允許動物繁殖的庇護所、保護魚類家園或保護海龜筑巢海灘的棲息地保護區、可持續漁業區、禁止捕魚區、錳結核采集區或禁采區,以及瀕危物種保護區。 明確規定功能區必須經過當地社區、聯合委員會及其技術咨詢小組的同意才能建立。 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建立保護了境內61 個瀕危物種,并制定海底礦產資源開發與保護規劃,明確禁止開采的區域。②“Biodiversity,” Marae Moana, https:/ /www.maraemoana.gov.ck/, 訪問時間:2021 年 1 月 22 日。政府、非政府組織、傳統領導人等不同主體的聯合管理,極大激發了當地居民參與保護區建設的積極性,有力推動了庫克群島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
2.1 職業足球 英格蘭職業足球俱樂部運動員培養體系基本上分為社區足球、進階訓練中心、精英訓練組、發展訓練組、足球學院和職業一線隊6個層次。
3.5 效果評估
(1)建設成效
首先,經濟效益明顯。 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有效增加了鯡魚、鱈魚、鮭魚、鯖魚、沙丁魚、金槍魚及比目魚等經濟性漁業資源,斐濟、帕勞、庫克群島等島國的漁獲量平穩增長,南太平洋捕撈漁業發展進入良性循環;近年來島國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3%以上,漁業經濟發展穩健。 另外,特殊海洋保護區的溢出效應進一步豐富海洋生物多樣性,催生了休閑觀光、旅游度假、漁家民宿等各種涉漁新業態,促進南太平洋島國旅游業發展。 2013 年斐濟德拉瓦卡島和納維蒂島之間的曼塔島(Manta)被打造成蝠鲼旅游勝地,海水、珊瑚和熱帶魚成為島國海洋旅游的標志性元素,2015 年,訪問這里的游客人數超過5000 人,在半年內給當地居民創造了超過10 萬美元的收入。
其次,海洋生態環境效益顯著。 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不僅保護海洋珍稀物種和提升生物多樣性,而且防止了大面積珊瑚白化的再次發生。 目前,南太平洋諸多島國的主要污染物入海量持續減少,近岸海域水質基本穩定,海洋生態系統穩定性顯著增強,海洋環境風險得到有效控制。 尤其是斐濟、帕勞等島國,通過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根據島嶼和特殊海洋保護區網絡建設的逐步推進,帕勞和斐濟再未發生過由于海洋氣候變暖、海洋酸化及污染等因素造成的珊瑚大面積白化。 2018 年,南太平洋區域的珊瑚覆蓋率達到26%,而這個數字在最新的報告中達到了30%左右,③“State of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in the Pacific Islands:2020 Regional Report,” Apia, Samoa: SPREP, 2021, pp.46-49.海洋生態環境系統已具備對氣候變化的強大復原力。
最后,文化效應突出。 南太平洋島國通過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保護了海洋圖騰文化。 鯊魚和鰩魚一直是南太平洋島國土著文化中的圖騰象征,但由于所羅門群島、庫克群島等島國的鯊魚和鰩魚瀕臨滅絕,導致圖騰文化也難以延續。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建立恢復了南太平洋海域鯊魚和鰩魚的種群,不僅讓圖騰文化在島國繼續傳承,更讓世界各國游客體會和了解到圖騰文化蘊含的生態環保理念,在潛移默化中傳播了特殊海洋保護區圖騰文化獨特的信仰力量。
許多南太平洋島國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模式被世界上其他各國所仿效。 其中以斐濟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建設模式最為明顯。 本地管理海洋區域模式被認為是基于社區管理的海洋保護區建設的成功范本,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推廣,尤其是在東非、印度洋等地被廣泛應用。①Kawaka, J. A., et al., “Developing Locally Managed Marine Areas: Lessons Learnt from Kenya”,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Vol.135, 2017, pp.1-10; Rocliffe, S., et al., “Towards a Network of Locally Managed Marine Areas (LMMAs)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PLoS ONE, Vol.9, No.7, 2014, pp.1-14.
(2)存在不足
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建設有其不足之處。 一方面,許多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是當地社區發起成立,監測和管理力量薄弱且需要依托外部力量提供的資金和技術支持。 社區內部的不平等現象也阻礙了特殊海洋保護區的發展,斐濟的社區體系問題尤為突出;同為社區原住民的斐濟裔和印度裔在地位上具有明顯的區別,社區的海洋屬于斐濟裔原住民,印度裔斐濟居民作為弱勢群體缺乏對社區海洋保護的積極性,造成在特殊海洋保護區治理過程中出現矛盾和沖突。
另一方面,部分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受大國影響明顯。 帕勞明確規定嚴禁國外捕撈漁船在其特殊海洋保護區網絡中的商業捕撈行為,但日本作為帕勞的主要經濟援助國,取得了在特殊海洋保護區捕撈的特權。2019 年,帕勞政府決定為日本沖繩縣的漁船提供作業水域,②“Palau Changes Ocean Sanctuary Plan to Allow Japan Fishing”, Phys.org, June 17, 2019, https:/ /phys.org/news/2019-06-palau-ocean-sanctuary-japan-fishing.html.既影響了特殊海洋保護區的海洋生物種群恢復,又打擊了國內民眾的熱情和信心。 類似的情況許多特殊海洋保護區都有發生,庫克群島的馬拉·莫阿納特殊海洋保護區建立之初,聯合委員會希望能夠頒布禁令保護以錳結核為主的海洋礦產資源,但遭到了以澳大利亞為首的諸多國家反對,導致計劃最后難以實現。
四、未來走向
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走在全球海洋保護區建設的前列。 可以預見,未來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建設與管理會呈現大型化、多元治理、區域合作等特征。
4.1 海洋保護區規劃:大型化
大型海洋保護區是指保護面積大于15 萬平方千米的海域。③AN Lewis, JC Day, A Wilhelm, et al., “ Large-Scale Marine Protected Areas: Guidelines for Design and Management”, IUCN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WCPA) and IUCN,Global Protected Areas Programme, 2017.早在2009 年召開的第40屆太平洋島國論壇會議期間,基里巴斯就在其提出的“太平洋大洋景觀框架”概念中提到大型海洋保護區(又稱太平洋弧)。④Jit, Joyti, and M. Tsamenyi, “ Evaluation of the Pacific Oceanscape to Manage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Ocean Environment”,Oceans, 2011.此后,帕勞和庫克群島先后建立了大型海洋保護區,并有效保護專屬經濟區內的海洋資源。 斐濟和薩摩亞也承諾將保護其境內30%的專屬經濟區,⑤“Protecting Fiji’ s Most Important Marine Areas”, IUCN,2020.其他諸多南太平洋島國正規劃建立大型海洋保護區網絡。 由此可見,相較于小型海洋保護區,大型海洋保護區依托寬闊的棲息場所,將保護區內的物種數量和生境質量維持在較高水平,能夠提供更多的“外溢”生物量并降低區域內物種受到邊緣效應的影響,⑥De Santo, E. M., “Miss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Targets: How the Push for Quantity Over Quality Undermines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Vol.124, 2013, pp.137-146.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因此,海洋保護區大型化是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的未來趨勢。
4.2 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多元治理
南太平洋島國人民長期以來依靠海洋維持生計,人們對海洋環境及其保護有著深刻的理解。 部落社區管理海洋的制度,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護了南太平洋島國的漁業資源和海洋環境。①Patrick, Christie, et al., “Trends in Development of Coastal Area Management in Tropical Countries:From Central to Community orientation”, Coastal Management, Vol.18, No.11, 1997, pp.2271-2276.盡管在殖民主義、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沖擊下,傳統的海洋管理制度面臨挑戰,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海洋資源管理制度日漸強化,但單一的政府主導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和管理模式并未完全見效。②Timothy R, McClanahan, et al., “A Comparison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Coral-Reef Management”, Current Biology, Vol.16, No.14, 2006, pp.1408-1413.前文中,所羅門群島將傳統的海岸管理制度和現代管理制度相結合的嘗試,已成為眾多國家、地方利益相關方、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捐助者探索的方向。 將注重社區和部落力量保護海洋資源的傳統習慣模式與注重政府力量的現代管理模式進行有機結合,既運用現代管理技術,又傳承行之有效的傳統習慣做法,形成政府、社區、部落、宗教、非政府組織等多主體的治理模式,是未來南太平洋特殊海洋保護區的發展方向。③Rohe, J. R., Govan, H., Schlüter, A., Ferse, S. C. A., “A Legal Pluralism Perspective on Coastal Fisheries Governance in Two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Marine Policy, Vol.100, 2019, pp.90-97.
4.3 公海保護區建設:區域合作
公海屬于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域,由于捕魚行為不受任何國家的管制,導致海洋“公地悲劇”現象愈演愈烈。④侯芳:“分割的海洋:海洋漁業資源保護的悲劇”,《資源開發與市場》,2019 年第 2 期,第 209-215 頁。南太平洋地區存在四個帶狀公海,這些區域是高度洄游魚種金槍魚、劍魚、馬林魚等的重點棲息地,也是國際漁業捕撈的重災區,各島國均希望限制公海的過度捕撈行為,實現漁業資源的長期養護與可持續利用。
區域化合作管理公海是未來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的重點工作。 第一,南太平洋島國是一個整體,公海使他們連結在一起。水體本身的流動性和海洋的整體性導致單一國家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與管理在保護海洋生態環境方面存在局限性,容易受到周邊海域的影響,共同管理公海可以推進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一體化進程。 第二,南太平洋島國在公海區域合作管理方面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2013 年召開的第十屆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上,各與會國已經就減少公海水域金槍魚幼魚的捕撈達成了共識,為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合作建設奠定了基礎。
隨著各國保護意愿的加強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南太平洋地區公海保護區建設將逐漸提上進程,有望成為繼國內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之外,能夠有效保護海洋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舉措。 同時,公海保護區建設也是打造南太平洋區域海洋保護區網絡的關鍵所在。
五、結論與啟示
進入21 世紀,全球海洋仍面臨著巨大危機。 2010 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提出的“在2020 年前將海洋保護區面積增加到10%”目標至今無法實現,且單一的保護面積占比目標設置也使得全球諸多國家對海洋保護區規劃與管理關注不足;但不可否認的是,世界各國對海洋保護區的建設熱情仍不斷高漲。 南太平洋特殊海洋保護區的建設既是各島國基于自身生存發展需要做出的選擇,也是以澳新為主的西方國家在南太平洋地區維護自身利益的戰略決策。 未來的南太平洋島國的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將朝著大型化、多元治理和區域合作的方向進一步發展,并不斷為全球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提供動力。
總體而言,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工作的進一步展開,不僅對南太平洋地區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具有重要意義,更能推動全球海洋保護區網絡的加快成型。 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的經驗對于共處同一個太平洋的中國突破海洋保護區的管理瓶頸、把握海洋保護區的未來走向以及制定相關的管控政策具有重大借鑒意義。 借鑒南太平洋島國海洋保護區建設經驗,本文得到以下啟示:
(1)生態補償機制建設。 建立海洋保護區生態補償機制,通過運用行政和市場的手段平衡相關利益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勢在必行。 海洋保護區數量和面積的不斷增加,一方面保護了海洋生態環境,另一方面也對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當地居民、企業和政府在海洋保護區的建設和保護過程中承擔了額外的保護成本或喪失了經濟發展機會,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參與海洋保護區建設與管理的積極性,阻礙了海洋保護區的長期發展。 目前,我國海洋保護區生態補償機制還處在起步階段,僅在部分海洋保護區有試點工作。 且相關立法體系并不完善,缺乏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配套支撐。①趙玲:“中國海洋生態補償的現狀、問題及對策”,《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1 期,第68-74 頁。因此,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國海洋保護區生態補償機制,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者受益、使用者付費、破壞者賠償的利益導向機制,既是中國海洋保護區建設和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激勵公眾參與海洋保護區治理的重要手段。
(2)公眾參與保護區建設。 基層群眾自發的海洋管理是降低海洋保護區建設成本,增加保護效率的重要途徑。②高陽、馮喆、許學工、段曉峰、崔艷智:“國際海洋保護區管理經驗及其對我國的啟示”,《海洋環境科學》,2018 年第3 期,第475-480 頁。在過去幾十年中,世界各國的海洋保護區管理方法已經從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轉向更具包容性的多元主體管理模式,斐濟保護區建設采用的就是部落社區酋長主導、其他主體參與的管理模式。 近些年來,中國的海洋環境不斷惡化,海洋資源日益衰退。僅靠政府部門進行的海洋保護區管理工作難以實現其保護目標,將公眾參與引入海洋保護區管理成為必然選擇。 新時期中國的海洋保護區建設要格外注重公眾參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拓展公眾參與的渠道,激發公眾參與的熱情。應當積極引導當地居民以個人或組織的形式參與海洋保護區的建設和管理過程,通過提高居民的生態保護意識,推動當地居民的保護行為由自發走向自覺,③Jones, P. J. S., Qiu, W., De Santo, E. M., “Govern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Marine Policy, Vol.41, 2013, pp.5-13.形成政府主導,多方參與的保護形式。 在發揮政府在海洋保護區的主體作用的同時,建立健全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保護的長效機制。
(3)注重當地特色。 南太平洋島國特殊海洋保護區建設還著重強調了當地傳統民俗在海洋保護區建設中發揮的作用。 在我國的東南沿海地區,海洋保護行為常以宗教民俗等形式呈現。 以舟山群島為例,舟山市內有兩大國家級海洋特別保護區,即嵊泗馬鞍列島國家海洋特別保護區和浙江普陀中街山列島國家級海洋生態特別保護區,兩大保護區總面積約752 平方千米。 當地漁民歷來靠海吃海,對于海洋有著獨特的情懷和歸屬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海洋文化。 同時,舟山宗教文化極具多元性,兼容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其他民間宗教。 宗教文化與海洋文化交織,產生了獨特的海洋宗教信仰。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如“漁民開洋、謝洋節”等獨具特色的傳統民俗,加深了當地漁民對于休漁期的認同感。 在我國海洋保護區建設的過程中,注重對傳統宗教民俗的傳承,對于海洋保護區的建設有著推動和促進作用。
(4)加快海洋保護區體系建設,構建海洋生態環境綜合管理網絡。 由于海洋的高度關聯性和系統性,海洋保護區應該嵌套在大型、多功能、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網絡中。 目前,我國海洋保護區實際管理工作由諸多責任機構負責,且相關職能部門缺乏宏觀統籌授權,難以對各類海洋保護區的空間、職能進行實質整合。 2019 年6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④“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新華網,2019 年6月 26 日,http:/ /www.xinhuanet.com/2019-06/26/c_1210171088.htm。因此,成立國家專門管理機構,統籌海洋保護區體系建設頂層設計,采用統一分級與部門協作的管理機制,加強不同類型、不同級別海洋保護區的跨區域協同聯動管理,進一步完善生態保護紅線等剛性約束制度,搭建配套的信息平臺,有效推動各個保護區的自我學習和改進,改變原有海洋保護區建設和管理中呈現出的碎片化、零散化傾向,是推動海洋保護區由“點狀式”步入“網狀式”、由“數量建設”步入“質量建設”的關鍵所在。
(5)區域合作共建保護區網絡。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動區域合作共建保護區網絡不僅對保護我國專屬經濟區內的生態環境具有重要意義,更是緩解國家沖突和維持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手段。 隨著我國保護區建設能力的不斷提升,未來海洋保護區建設必然會從近岸向遠海進行拓展,從管轄內向管轄外延伸。①匡增軍,徐攀亞:“南海海洋保護區建設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分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2 期,第151-159 頁。所以需要在加快本國專屬經濟區內海洋保護區建設的同時,在爭議區域積極尋求合作、達成共識,共同制定和實施養護措施。 通過構建海洋保護區網絡,增進與周邊海上鄰國技術與教育的交流互助,擴大資金支持,強化共同執法力度,提高海洋保護的默契性,最終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