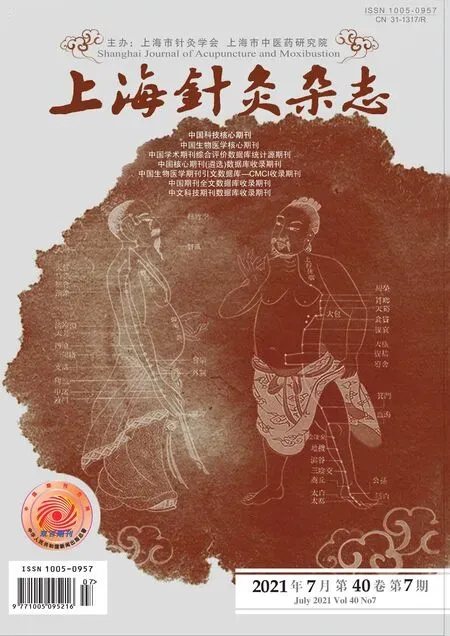關于英國婦產科雜志“妊娠期針灸的安全性: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的分析與思考
郝鳴昭,楊會生,鄭晨思,尹雅倩,劉思雨,房繄恭,2
(1.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北京 100700;2.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醫院,北京 100700)
英國皇家婦產學院的官方期刊——英國婦產科雜志(BJO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是國際婦產科領域的頂級期刊。2019年9月20日,該刊發表了“妊娠期針灸的安全性: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其研究成果來自韓國自生漢方醫院的H-Y Moon團隊(以下簡稱“該研究”)[1]。該研究數據來源于 2003年至 2012年韓國醫療保險數據庫(Korea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NHIS),共納入 20 799例患者,其中針灸組 1 030例(4.95%),對照組19 749例。其結論是兩組間生育結局無顯著差別,故針灸是一種無不良反應的可緩解孕婦不適感的安全的治療方法。該研究是本領域第一個大型的國家范圍的回顧性研究,為孕期針灸的安全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盡管細節、分析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但其首創性與重要性不言而喻。
藥物致生殖毒性作用及遺傳毒性效應受到醫學界廣泛關注,絕大多數藥物可通過胎盤進入胎兒體內,故孕期用藥需慎之又慎。尋求一種有效且安全的非藥物療法對于提高孕婦生活能力、改善其生活質量很有必要。隨著針灸熱在全球的盛行,針灸療法的功效及作用被海內外廣泛接受,然而其安全性仍有爭議,尤以孕期針灸為甚。近年來,國內外多項臨床試驗和系統評價證明了針刺能治療妊娠期面癱[2]、腰背和骨盆疼痛[3]、失眠[4]、妊娠劇吐[5]、圍產前期抑郁[6]等,可改善妊娠結局,提高孕產婦生活質量,且不良反應較少。歐洲的兩個研究[7-8]顯示,4%~13%的婦產科患者會尋求針灸的幫助。英國針灸醫學學會(BMAS)[9]在其治療規范中指出,一般針刺治療對妊娠無不利影響,但妊娠早期及“妊娠禁穴”等應謹慎使用。美國[10]、新西蘭[11]等國家也曾展開妊娠期針灸安全性的討論。該研究是第一個國家性的大型隊列研究,其得出的孕期針灸安全性的結果將令國際醫學界對孕期針灸更多一分信任。筆者將結合針灸相關理論和妊娠期安全性相關標準并綜合目前的研究成果,以期為妊娠期針灸的安全性研究提供幾點建議與思考。
1 該研究概述
①納入標準,2003年至2013年NHIS數據庫中婦產科符合妊娠相關診斷(第10版國際疾病分類);初次妊娠;孕期為診斷日到孕38周。②排除標準,錯誤診斷和亞臨床診斷;有妊娠相關診斷但無妊娠結局(足月生產、早產、死產)。③暴露因素,針灸。④研究類型,回顧性隊列研究。⑤結局指標,孕期足月生產、早產、死產的發生率以及高危妊娠和多胎妊娠的發生率。⑥結果,共納入20 799例患者,其中針灸組1 030例,對照組19 749例;早產方面,針灸組及對照組兩組總體及高危妊娠無差異;死產方面,針灸組無死產,對照組死產率為0.035%。⑦結論,兩組間生育結局無差別(早產和死產),因此針灸是一種安全的無不良反應的緩解孕期不適的治療方法。
2 針對該研究的意見與建議
2.1 結局指標
①該研究未明確孕婦的生產方式,其中是否涉及人為因素導致的主觀性早產未可知,近年來臨床上孕產婦選擇主動早產的并不少見。②談及妊娠安全性,不僅關系到本代健康,更關系到子代的生命安全性問題,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匡延平教授團隊在BJOG發表評論文章[12],建議將子代安全性如出生體質量、致畸等納入評價范圍。
2.2 暴露因素的限定
①該研究設定的暴露為針灸,而針灸本身是個大概念,包括有毫針刺法、灸法、耳穴貼壓、穴位貼敷、穴位注射、綜合治療及其他療法,不同的干預方式有其迥異的特征,因此也是影響妊娠結局的重要因素。②疾病、治療方案、頻次與時間該研究均有涉及,然而疾病是否妊娠相關、是否涉及“妊娠禁穴”、接受針灸治療的時期等診療細節均是安全性的考量因素。
2.3 妊娠禁穴
針灸治療往往涉及一套完整復雜的處方,其穴位組成多樣、可變,作用靶點和機制較為復雜,且穴位間相互作用難以預測,然而個別“妊娠禁穴”因其特殊性,應當以單獨因素作為評價依據。
3 結果解讀
該研究的結果顯示,①人口學特征,兩組年齡、收入無差異;多胎率、高危妊娠無差異;與對照組相比,針灸組孕期長 20 d,且針灸組婦產科就診次數更多。②早產與死產,針灸組無死產,兩組早產率無差異;針灸組10個多胎均為足月妊娠無早產。③妊娠的終止,與針灸時間相近的妊娠終止病例相對較少。④治療與診斷,針灸組中早產和足月生產診斷無差異;足月生產常見診斷為功能性消化不良,腰痛,腰扭傷;早產常見診斷為功能性消化不良。⑤各組高危妊娠診斷代碼中最常見的為妊娠糖尿病。
匡延平教授針對針灸組孕期婦產科訪視次數更多提出可能是更頻繁的監測和更及時的治療導致結果產生偏移,建議將訪視次數作為混雜因素進行調整。后續該研究作者[13]針對評論給予回答,絕對危險度降低率為 0.015(95%CI,0.002~0.033),可能因孕期短或有住院等情況,若將訪視次數作為混雜因素可能會對結果造成較大的影響,但依據建議計算比值比為1.12 (95%CI,0.89~1.4)。筆者建議深入探討針灸組孕期婦產科訪視的診斷和處方,以進一步判斷是否需調整訪視次數,從而尋求針灸組孕期較長的合理原因。
“妊娠的結果是健康的嬰兒”是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生殖健康概念中的重要內容,因此合理的結局指標應當據此相關。臨床上妊娠期用藥關注點主要為流產以及畸胎率、低體質量兒出生等,限于醫療保險數據庫的數據限制,僅可提取診斷類數據。該研究未涉及干預的暴露劑量、時間和妊娠時期,這3點均可影響妊娠結局,對針灸的干預效果有很大影響。相關研究[14-15]顯示,身體的狀態與刺激參數是決定針灸是否導致流產的主要因素,而穴位的墮胎效應需滿足一定條件才會產生,否則即使是“妊娠禁穴”也不會輕易導致墮胎。筆者建議進一步做亞組分析,如根據孕前中后期、療程的長短、針刺的次數等,跟進探討是否會有更深入的結論?
4 討論
孕期針灸的安全性一直以來頗有爭議,我國古代對于妊娠期針灸的安全性問題已有認識,西晉王叔和《脈經》記載:“妊娠者,不可灸刺其經,必墮胎。”宋代《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記載:“昔有宋太子性善醫術,出苑逢一懷娠婦人,太子診曰:是一女也。令徐文伯亦診之,此一男一女也。太子性急欲剖視之,臣請針之,瀉足三陰交,補手陽明合谷,應針而落,果如文伯之言,故妊娠不可刺也。”后世書籍相繼轉載,合谷、三陰交穴也就成為妊娠禁忌穴之代表。邱茂良的《針灸學》[16]記載:“婦女懷孕三月者,不宜針刺小腹部的腧穴;懷孕3個月以上者,腹部、腰骶部腧穴也不宜針刺;三陰交、合谷、昆侖、至陰等通經活血的腧穴應禁刺。”妊娠期這些穴位是否必須禁針?為何禁針?是否妊娠特定階段有所不同?近年來的一些研究對“妊娠禁穴”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1項機制研究[17]發現針刺合谷可通過環氧化酶-2抑制孕鼠子宮活性,從而預防早產;另1項研究[18]則發現針刺三陰交可使未孕家兔子宮運動的強度和頻率明顯加強;而針刺早孕大鼠合谷、三陰交使其子宮收縮波幅明顯升高而頻率明顯減慢,從而有效地抑制子宮的無強力收縮,提高流產率[19];50例不同妊娠月份的孕婦,以電針合谷、三陰交為主進行流產、引產,結果顯示針刺只對末期妊娠有催產作用[14]。綜上所述,“妊娠禁穴”的臨床運用和作用機制仍有待進一步驗證,運用這一類穴位時應當謹慎。
該研究以其大研究范圍、大樣本量所得的結論為孕期針灸的安全性提供了一份保障,針灸不良反應的臨床表現較為復雜,如該文作者所述“短暫且輕微”,故該研究將不良妊娠結局與針灸時間間隔作為衡量安全性的重要指標。因回顧性研究的局限性,患者信息不全面或不詳細導致偏移較多,孕期的隨機對照研究面臨倫理困境較難實施,因此后續前瞻性注冊登記研究應彌補該研究的缺陷,充實詳細資料,以提供高質量的安全性證據。該研究數據來源于韓國醫療保險數據庫,提取的標準數據為診斷碼,因此該研究中探討的結局指標為保險數據中常用的基本信息及診斷,不良反應、孕產史及后代安全性等方面未能納入。這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安全性的概念與范圍,因此筆者呼吁更多的醫療機構、研究機構關注該領域。
醫者往往是造成不良反應的最基本原因[20],國外妊娠期的針灸從業者多為助產士與理療師,Tiran D[21]在1項研究中指出醫生的能力應是衡量安全性的一個重要指標,且針灸應當作為一種專業知識并質疑助產士在此領域的專業性。因此,加強針灸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認識對臨床和研究人員都是非常必要的。本課題組不孕患者多接受輔助生殖技術,房繄恭主任醫師臨床上建議患者于移植胚胎后繼續針灸至 B超見胎心胎芽(孕 40~60 d),尤其對妊娠早期子宮內環境較差的患者提供支持,臨床實踐數年尚未有報告不良反應,有患者反饋針刺治療后移植引起的下腹部不適感有所減輕。Paulus WE等[22]認為足太陰脾經和足陽明胃經的穴位有助于增加子宮的血流灌注,配以內關、百會、太沖等鎮靜安神,因此同樣選擇胚胎移植術后進行針刺。相關研究表明,針灸治療對于先兆流產[23]、胎動不安[24]、反復生化妊娠[25]等均有較好的臨床療效。近年來隨著中藥在全球范圍的流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著手構建妊娠期中藥安全性評價體系[26]以適應中醫藥特色的藥物療法,針灸界是否也應構架相應的非藥物療法評價體系以方便針灸進一步推廣與應用?
安全性及有效性是評價藥物及其他醫療手段的首要標準。藥物對人類的生殖危害是深遠的,不僅對畸形兒本身的生理、心理成長造成障礙,對患者家庭甚至整個社會都是沉重的負擔,因此一種安全有效的孕期非藥物療法對于提高人類生殖健康、人口質量均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建立符合針灸自身特點的生殖及遺傳安全性評價技術與方法,規范、優化妊娠期針灸的運用,在保障安全性的基礎上發揮針灸的療效,幫助更多的孕期婦女提高妊娠期生活能力,改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