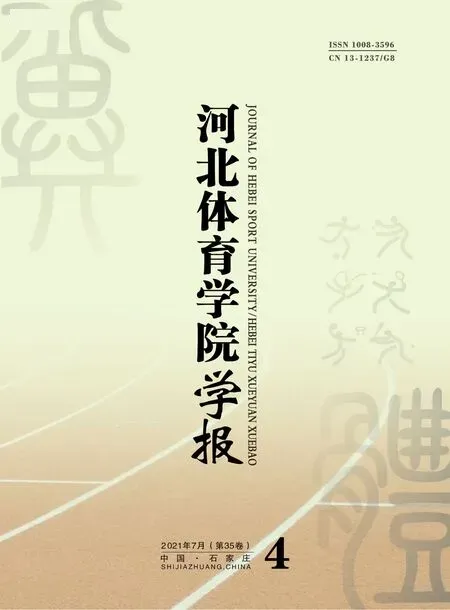傳統(tǒng)武術(shù)的非體育屬性
——馬保國現(xiàn)象的喜劇性
路云亭
(上海體育學(xué)院 傳媒與藝術(shù)學(xué)院,上海 200438)
就自然時間而言,2020年的5月17日并無任何特殊性,但是,這一天傳統(tǒng)武術(shù)鐘情者馬保國脆敗于王慶民,給很多中國傳統(tǒng)武術(shù)關(guān)注者帶來了一定的心理沖擊。馬保國事件看似簡單,其實(shí)不然,它幾乎將原先隱藏在傳統(tǒng)武術(shù)世界中的諸多不為人關(guān)注的信息和盤托出。中國武術(shù)界部分人士認(rèn)為馬保國敗壞了傳統(tǒng)武術(shù)的名聲,而年輕一代的網(wǎng)民則展示出了更為豐富多彩的觀念,他們認(rèn)為馬保國以68歲高齡參加比武活動未必合乎社會性、日常性與國情性邏輯,賺錢不要命說、蹭取新聞熱度說、博取觀眾眼球說、提升自己知名度的江湖行為說等觀點(diǎn)開始浮升出來。不難看出,馬保國現(xiàn)象已然構(gòu)建出一種武林迷思,若以社會學(xué)、人類學(xué)以及武術(shù)傳播學(xué)的角度來綜合研判、考察、解讀馬保國比武事件,則又可以得出全新的結(jié)論。
1 馬保國事件充滿喜感的戲劇精神
大而言之,中國民間比武和競技體育領(lǐng)域的格斗并不相同,競技格斗是一種非贏即輸?shù)母偧蓟顒樱耖g比武更多是一種無功利性的自然社交活動;競技格斗是剛性對抗,民間比武是以武會友;競技格斗是決絕之悲情展示,民間比武是喜感十足的情感交流行為。僅從幾則發(fā)生在近幾年的民間比武事件中即可看出,類似的比賽并無太多的體育性可言,卻有很強(qiáng)的娛樂性。筆者注意到,馬保國比武事件中的參賽者、裁判乃至主辦方并非專業(yè)的體育人,他們旨在捍衛(wèi)傳統(tǒng)武術(shù)的內(nèi)在精神,或多或少都體現(xiàn)出一種對體育精神的漠視、小覷乃至挑戰(zhàn)的意味。傳統(tǒng)武術(shù)一向擁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傳統(tǒng)武術(shù)的習(xí)練者都擁有一種心理上的優(yōu)勢。“在當(dāng)今的傳統(tǒng)武術(shù)練習(xí)者中,存在的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diǎn)是傳統(tǒng)武術(shù)是世界上最強(qiáng)的武術(shù),也是最科學(xué)最高深的武學(xué),其他現(xiàn)代搏擊術(shù)與國外武術(shù)都是‘小兒科’。許多人主觀地認(rèn)為,國外武術(shù)以及現(xiàn)代搏擊術(shù),永遠(yuǎn)無法與傳統(tǒng)武術(shù)相提并論,并用一些看起來高深莫測的理論來駁斥現(xiàn)代武術(shù)與國外武術(shù)的‘膚淺’。”[1]然而,時代在前進(jìn),人們的觀念也在發(fā)生變化,這里需要說一說觀眾對傳統(tǒng)武術(shù)的判斷,普通的武術(shù)觀眾大體可以分為民傳派與體育派。兩派人士從各自的立場出發(fā),對馬保國事件的態(tài)度呈現(xiàn)出一定的差異性。體育至上論者極易生發(fā)對馬保國的嘲弄之欲,而捍衛(wèi)民傳精神的網(wǎng)民則直接將馬保國事件看成戲劇表演。由于馬保國事件涉及多個學(xué)科,在權(quán)威學(xué)者會診暫時缺位的情況下,網(wǎng)民的立場便會上升為主流觀念。
中國是非宗教國家,中國人也早已習(xí)慣以道德代宗教。漢代以后,中國尊崇儒家道德觀。儒家道德的核心是禁忌,側(cè)翼是儒巫思維,儒巫思維的側(cè)翼則是喜劇精神,三者共同構(gòu)建出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文化結(jié)構(gòu),其中的禁忌學(xué)制定主體是儒巫合一的史官或巫師,而社會流行價值觀是道德,百姓日常倫理精神則是追求圓滿、喜慶、吉祥之類的喜感元素。古代儒巫思維的積極性很明確,儒巫思維融含了一種追求戰(zhàn)無不勝的意愿、理想與結(jié)果,充滿了積極用世的思想。于是,道德與儒巫思維、喜劇與禁忌,構(gòu)成了中國文化的四角關(guān)系,四者相互支撐,相互倚重,營造出一種中華文化的基本生存理念。馬林諾夫斯基在闡釋巫術(shù)與道德的關(guān)系時曾說:“道德之所以為道德而不同于律法與風(fēng)俗者,乃在道德系由良心來制裁。蠻野人不犯禁忌,并不是因?yàn)榕律鐣奶幜P或輿論的制裁。他所以不這樣,一部分因?yàn)樗律耢`見怪,但主要則因?yàn)樗牧夹呐c個人責(zé)任不允許他這樣。禁忌中的圖騰,亂倫常的交通,不準(zhǔn)吃的物品與不準(zhǔn)作的事,都使他自然而然地相遠(yuǎn)。”[2]馬林諾夫斯基極為重視巫術(shù)在人類日常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其實(shí),巫術(shù)在特定的語境中的確有存在的必然性,而在極端的環(huán)境下,它也會成為一種優(yōu)化人的心理環(huán)境的要素。在馬林諾夫斯基看來,道德和巫術(shù)的聯(lián)結(jié)媒介為禁忌。先民的禁忌學(xué)的開創(chuàng)者是巫師,而禁忌的執(zhí)行標(biāo)準(zhǔn)則是道德,儒家文化被禁忌掉的內(nèi)容是包括競技體育在內(nèi)的所有類型的暴力行為,于是,中國文化孕育出來的體育也便失去了其暴力文化的常態(tài)身份,最終只剩下了喜感文化,而喜感文化的大眾性、表演性和舞臺性形式則是喜劇。
馬林諾夫斯基講述的巫術(shù)文化融含了所有民族史前社會的思想與行為本貌,其中自然包括中國文化。由于儒家長期的統(tǒng)治地位之作用,中國文化中的儒巫元素顯然帶有更多的普適功能。中國文化也有禁忌,但大多將其設(shè)計(jì)為一種喜感很強(qiáng)的禁忌,如喜喪、做惡夢是反的、吐唾沫可以化解不吉利之事等。具體到武術(shù)的領(lǐng)域也是如此,傳統(tǒng)武術(shù)受中華傳統(tǒng)文化影響至深,中國的比武活動往往帶有濃郁的喜感,對很多秉持傳統(tǒng)武術(shù)信念的人來說,比武就等于表演,相當(dāng)于一種儀式化的社交活動,其所折射出來的是一種喜劇精神。僅從格斗品階而言,馬保國與王慶民的比武格斗更像一場由鄉(xiāng)村、街道、市郊、城鄉(xiāng)接合部相關(guān)人員組織起來的自然約架,存在技術(shù)含量低、規(guī)則不嚴(yán)格、競技規(guī)范性差之特點(diǎn)。但是,馬保國事件的反常性十分突出,其不僅引發(fā)了媒體和觀眾的強(qiáng)力反應(yīng),且在長達(dá)數(shù)月的時間內(nèi)都是媒體和網(wǎng)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對此需要作出合理的解讀。
馬王比武的失范性非常明顯。先說兩者的身體條件。馬保國68歲,王慶民50歲,皆屬中老年人,兩人的約架行為既違背了中國武術(shù)界“拳打少壯”的傳統(tǒng),也背離了世界上各種徒手格斗須經(jīng)專業(yè)機(jī)構(gòu)嚴(yán)格檢測的做法。賽事主辦方在賽前并未公布參賽者的身高、體重、臂展、戰(zhàn)績等數(shù)據(jù),亦未通報兩者徒手格斗的技戰(zhàn)術(shù)流派、風(fēng)格、特色等情況。其實(shí),從比武的事實(shí)看,兩人都屬于格斗素人,網(wǎng)民對兩人的定位也是業(yè)余武術(shù)玩家。拋開兩人各自未必可靠的關(guān)于體重的描述,僅從視頻資料目驗(yàn),王慶民的體重和肌肉發(fā)達(dá)程度都超馬保國。
馬王比武的場地也不規(guī)范。比賽場地是一個室內(nèi)開闊地帶,既無圍繩鎖定,亦無高出地面的擂臺,地面還有各種黏合劑的黏合痕跡。本場比賽的現(xiàn)場秩序也很混亂。賽場呈高度開放性,觀眾可以自由出入。當(dāng)馬保國第一次被擊倒后,還有一位觀眾試圖上前攙扶,比賽之混亂可見一斑。參賽者的行為也不規(guī)范。賽前乃至賽后,兩人對比賽規(guī)則皆不熟悉。馬保國每次演示其動作之前總要先說一段話,既像在講解理念,又像在暗示結(jié)局,似乎又是一種誘導(dǎo)或威脅,充滿了暗示、詛咒、日常表演等巫性元素。
馬保國在賽前還反復(fù)向裁判龐皓天講解他的一個習(xí)慣動作,并說此動作有可能傷及裁判,且用手戳點(diǎn)龐皓天的后頸部,此舉已涉嫌語言挑釁、巫術(shù)詛咒及肢體威脅問題,同時也展示出馬保國對競技體育規(guī)則體系的無知和漠視。其實(shí),馬保國的語言威脅是擺在口頭的,在很多場合都使用過。在回答歐洲學(xué)生的問題時,馬保國堅(jiān)定地認(rèn)為點(diǎn)穴術(shù)不僅存在,而且威力巨大。“我的西方入室弟子們也都十分贊賞中國的點(diǎn)穴功夫,要求我教他們點(diǎn)穴秘訣,我視情況教了他們一些點(diǎn)麻穴的方法,如:在教他們奪匕首時,就教他們點(diǎn)內(nèi)關(guān)和虎口兩個麻穴。同時,也教了他們誤點(diǎn)大穴后的急救方法,并一再告誡他們,不到生死關(guān)頭不準(zhǔn)點(diǎn)大穴。”[3]233然而,馬王比武極富喜劇性,或者說就是一場未曾彩排的即興表演的戲劇。比賽中,馬保國穿球鞋,王慶民赤腳,畫面充斥著一種極為鮮明的滑稽元素。而從競技體育的角度看,其所展示出來的亂象本身更值得解讀。
2 馬保國的武術(shù)來自民間雜藝
還要說到本場比賽的合法性。雙方的格斗未經(jīng)過任何體育管理部門的認(rèn)證,屬于民間私斗行為。盡管如此,馬王比武所引發(fā)的后續(xù)效應(yīng)仍然非常強(qiáng)烈。在很多人看來,馬保國偽武者的表演性人格開始凸顯,從而將個體的馬保國當(dāng)成了傳統(tǒng)武術(shù)人士整體的代表。然而,當(dāng)事物演進(jìn)到極端的時候,會呈現(xiàn)出一定的超越性。人們最終發(fā)現(xiàn),馬保國的知名度一路攀升,人們似乎用一種接受喜劇的方式接受了馬保國的所作所為。這里需要說明,中國文化是喜感文化,這種文化對競技體育很排斥,因?yàn)楦偧俭w育有輸有贏,但喜感文化只接受贏的信息。中國文化中一直存在一種傳統(tǒng),某人參加比賽,一定代表的是某個群體,于是,人們習(xí)慣上認(rèn)為,霍元甲代表中國人,霍元甲就只能勝利而不能失敗,因?yàn)橐坏┦。愦砹恕爸袊恕备拍畹氖 R虼耍袊烁矚g看人為設(shè)定的武打電影,而不愿意觀看充滿不確定性的格斗比賽。
對中國觀眾而言,代表自己一方的競技者即使失敗,也要盡量回避有關(guān)失敗的信息,借以維持一種祥和氣氛。馬保國事件之所以觸動了很多傳統(tǒng)武術(shù)熱愛者的神經(jīng),也是因?yàn)轳R保國輸?shù)袅吮荣悾^眾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馬保國的失敗是傳統(tǒng)武術(shù)的失敗。于是,觀眾盡力將馬保國排除出傳統(tǒng)武術(shù)體系,也就出現(xiàn)了馬保國非傳統(tǒng)武術(shù)人士的說法,甚至還有一些人將馬保國當(dāng)成職業(yè)演員,旨在以一種戲劇性語境來化解尷尬。其實(shí),馬保國、王慶民所習(xí)練的武術(shù)既非傳統(tǒng)武術(shù),亦非競技武術(shù),而是一種社會武術(shù),它是一種以言談、說笑、講敘為核心的武術(shù),從不涉及身體的極限性、對抗性與生命本體的風(fēng)險性。馬保國被連擊三拳而毫發(fā)未傷,至少可以說明王慶民的擊拳質(zhì)量很低。武術(shù)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占有特殊地位,中國人大都有過傳統(tǒng)武術(shù)夢,且此夢又很難徹底別離于人們的記憶深層。面對馬保國的脆敗,更多中國觀眾僅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已,但是,哀其不幸的動機(jī)也會構(gòu)建出一種攻擊力,并在短期內(nèi)將馬保國乃至所有傳統(tǒng)武術(shù)項(xiàng)目送到審判臺。
毋庸置疑,馬保國事件并非有意上演的超能鬧劇。很多觀眾觀看到馬保國脆敗后都會詫異,在一種糾結(jié)矛盾的復(fù)雜情感的促動下,一些人會產(chǎn)生一種激烈的情感沖動,從而否定馬保國的武功,進(jìn)而厭惡馬保國自言之代表傳統(tǒng)武術(shù)精神的各種言論,一些人將馬保國看成了演戲者之輩,其實(shí)隱含著一種解脫之道,認(rèn)為馬保國僅僅是在表演傳統(tǒng)武術(shù),而非真正的武術(shù)家,甚至不是真正的傳統(tǒng)武術(shù)習(xí)練者,正因如此,其不堪一擊也會變成為一種積極信息。
真實(shí)的情況是否如此,仍值得探究。坦率說,中國的武林本身就有其復(fù)雜性,武俠小說及影視劇只是過濾掉了其中有關(guān)勝負(fù)的偶然性元素,卻將其動作形態(tài)保留了下來,而馬保國試圖展示一種屏蔽勝負(fù)走向后的武林儀式,描繪一幅中國武林的以武會友的美好圖景,而王慶民并未心領(lǐng)神會,將馬保國簡單看成純?nèi)坏母偧紝κ郑瑥亩Τ鋈Y(jié)果造成了馬保國脆敗之結(jié)局。馬保國或許還在小說或影視劇的情境中沉迷,其對中國武林諸多感知的觸點(diǎn)、深度和維度皆源于小說或影視作品。就現(xiàn)階段而言,由一部分篤信超自然能量的傳統(tǒng)武術(shù)人員構(gòu)建出來的武林只是一個自娛自樂的社會表演者麇集的社團(tuán),他們沒有現(xiàn)代競技場域內(nèi)的實(shí)戰(zhàn)力,然而,仍有不少人認(rèn)為他們是一種堪稱無敵的強(qiáng)人符號,對其充滿了爛漫的想象。這里再度展示出了道德、儒巫思維、禁忌與喜劇的四角關(guān)系。四者合力打造出帶有某種準(zhǔn)宗教性質(zhì)的信仰實(shí)體。其實(shí),這是一種刻板印象,并非中國武林的本真風(fēng)貌。馬保國事件發(fā)生后,中國觀眾炸鍋般反應(yīng),體現(xiàn)的是一種精神崩潰后的情態(tài),在此意義上說,馬保國事件的負(fù)面性很明顯,因?yàn)樗蚱屏酥袊说奈鋫b夢。
真實(shí)的情況也是如此,馬保國事件不僅輕易地解構(gòu)了既有的武林規(guī)則,還急速消解了中國武林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一些理性人士已然看到中國傳統(tǒng)武術(shù)存在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便是現(xiàn)代性元素高度虛白化,原因很簡單,當(dāng)隱蔽性、神秘性的傳統(tǒng)武術(shù)演化為公平性、透明性的體育競技之后,傳統(tǒng)武術(shù)自身的生命密碼、史前基因、原始風(fēng)貌也會急劇異變,于是,人們可以輕易感受到馬保國事件締造出來的戲劇性效果,但是,人們依然不會感到滿足,因?yàn)閭鹘y(tǒng)武術(shù)本身具有永不失敗的信仰性元素,而永不失敗只能是宗教性、信仰性或巫術(shù)性概念,并非體育概念,因此,傳統(tǒng)武術(shù)要想成為一種真正的體育項(xiàng)目不僅困難重重,而且充滿風(fēng)險。
按照西方競技體育的傳統(tǒng),任何一種競技類型都應(yīng)有充足的悲劇性,然而,馬王比武缺失了這樣的悲劇性,這也導(dǎo)致兩人的對壘無果而終。從傳播學(xué)的角度看,馬王比武稱得上是中國近期民間比武活動亂象之巔峰。面對兩種截然對立的文化,人們對馬王比武的評價也呈現(xiàn)高度對立狀態(tài),民間人士開始以諧謔的方式解讀馬保國失敗的原因。“阿魁方言配音”直接推出了《馬大師輸拳的真正原因》的抖音短視頻:“馬保國大師那次比賽被KO,完全是另有原因的。第一,聽說馬大師是騎洋車子來的,別說五六十歲的大爺騎洋車子,就算騎摩托,幾百里地也累得夠嗆。第二哩,大師穿的是長袖,長袖兜風(fēng),嚴(yán)重影響了出拳速度。第三,大師賽前喝了幾口水,比賽時水在肚子里晃蕩,影響身體平衡。第四哩,俗話說光腳不怕穿鞋哩,但穿鞋哩害怕光腳哩!剛好比賽時大師穿的是千層底,王慶民則是光著大腳板子。第五哩,馬大師平時都是空手發(fā)功,但比賽時帶上了手套,這就嚴(yán)重影響了功力的正常輸出。所以說,大師輸了比賽,并不是自己功夫不行,最后大師還以筆直的倒地姿勢來證明自己功力不淺。”[4]“魯生可畏”制作的《渾元形意太極拳山東馬大師》短視頻對事件的評價則更具批判性。“魯生可畏”開場定性:“馬大師就是個打著‘傳統(tǒng)武術(shù)’各種招搖(旗號)搶爛錢的騙子。最可氣的是呢!他還對自己的功夫深信不疑,騙人,騙著騙著連自己都信了。”[5]隨后還將馬保國與閆芳、王林、張悟本等“大師”放在一起進(jìn)行整體批判。這里已然呈現(xiàn)出一種超體育的表演譜系,當(dāng)此之境,馬保國完全失去了體育人的身份,也漸次喪失了武者的符號性,而蛻變?yōu)橐环N新型的喜劇演員。
準(zhǔn)確定性馬保國事件有相當(dāng)?shù)碾y度。先說賽制,類似的比賽很難說是正規(guī)的格斗賽。“之前王慶民所在俱樂部發(fā)表公告,表示王慶民已經(jīng)回歸了正常生活,未來也不會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訪和約架。”[6]這里提到的“約架”一詞已經(jīng)完全脫離了體育精神。其次,比賽之后出現(xiàn)了大量的表演性叫罵現(xiàn)象。“值得一提的是,日前,一位名叫侯友勝的武術(shù)演員,公開叫囂KO馬大師的王慶民,希望嘗一嘗外國拳的滋味,同時也諷刺馬保國,認(rèn)為他不能代表中國傳統(tǒng)武術(shù)。”[6]這不僅違反體育道德,還觸及社會道德問題。其三,馬保國事件發(fā)生后,網(wǎng)絡(luò)世界竟然出現(xiàn)了冒充馬保國徒弟散布不實(shí)信息者。“關(guān)門弟子的視頻在網(wǎng)絡(luò)上被傳開之后,馬保國也出面怒噴其是假冒,要求這名‘關(guān)門弟子’道歉。并且聲稱如果假冒者不道歉,馬保國將會利用法律武器追究其責(zé)任。然而在網(wǎng)上冒充馬保國弟子的人遠(yuǎn)不止這名關(guān)門弟子,還有‘大弟子’等,大弟子則是說要為師報仇。其實(shí)這些所謂的弟子都是騙子,只是在利用拍段子來蹭馬大師的熱度而已。”[7]如此亂象在正規(guī)的體育比賽中不可想象,但在當(dāng)下中國武林中則是常事,可見,中國傳統(tǒng)武術(shù)世界存在著豐富的花絮,這些花絮時而會超越競技本身,成為一種高度娛樂化的文化元素。往深里說,馬王比武只有輸家,而沒有贏家。王慶民在賽后說,裁判并沒有根據(jù)國際慣例舉起他的手,宣告他為勝利者,王慶民為此而困惑。這樣的細(xì)節(jié)也再度體現(xiàn)出本場比賽的獨(dú)特性,其中的戲劇性、表演性、戲耍性、喜劇性要大于其體育性、競技性、嚴(yán)肅性與悲劇性。
馬保國事件還折射出一些其他情況,人們至少通過此類事件看清了經(jīng)典的戲劇表演與競技比賽并不完全相同,競技體育的競賽雙方地位平等,而戲劇中不僅有主角、配角之分,還有正角、反角之別。假如說馬王比武是一場真實(shí)的戲劇表演的話,那么,裁判龐皓天則是第二主角,其戲劇性地位超過了王慶民。無論是否有意,龐皓天從始至終都沒有宣布比賽結(jié)果,使得比賽更像戲劇而不像體育。或許是受到?jīng)]宣布比賽結(jié)果的影響,馬保國始終不承認(rèn)自己失敗,這也再度為賽事增添了值得繼續(xù)探討的分化性議題。其實(shí),本場比賽的很多問題都出在馬保國的身上,馬保國大體可以稱為本場演出帶有反角元素的主角,因此,要想徹底解讀龐皓天不宣布比賽結(jié)果之謎,就要了解馬保國的參賽動機(jī)和心理特征。
3 喜劇的游戲性可以降解所有類型的精神紛爭
新媒體時代到來后,海量信息可以暢通傳遞,為全方位追索、展示馬保國的個性特質(zhì)提供了方便。當(dāng)前中國的草根傳統(tǒng)武術(shù)人士大致有三種類型,其一,爭取非遺待遇者。此類人士兢兢業(yè)業(yè),甘于寂寞,靜候機(jī)會到來。其二,各大院校的武術(shù)教師。此類人士將自己設(shè)計(jì)為力爭進(jìn)入體育界的人,試圖以一技之長贏得社會尊重。其三,以出賣武技及相關(guān)能力的生活者。此類人大多不在乎武技術(shù)水平,而著意于傳播一些想象性、傳說性、超異性信息,以便吸引民眾的關(guān)注力。他們更像一群布道者,致力于擴(kuò)大信眾規(guī)模,直接或間接地培植粉絲群,辦班賺錢,維持生計(jì)。馬保國以及人所熟知的雷雷、閆芳、丁浩等,大體屬于此類。
作為一個自然的江湖人或超異派思想的篤信者,馬保國長期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他或許從來都不愿意認(rèn)可格斗項(xiàng)目的體育特性,亦從未深刻領(lǐng)會和正視公平競爭的合理性,所以才會在古稀之年參加這場毫無公平性可言的比賽,且未想到自己的失敗,因?yàn)樗冀K秉持超人不敗理念。但是,競技體育是一種真實(shí)的對抗行為,其以科學(xué)性為前提,馬保國的巫師般的想象力最終敗在了科學(xué)主義的場域,人們對此不應(yīng)感到奇怪。
馬保國的思維亦有其合乎理性的一面,那便是他對民間比武規(guī)則的高度信賴。中國的民間比武一向自成規(guī)則。沈喬生曾講述過中國民間比武的合法性,“民間比武,從來就是一件盛事,在中華大地上,已經(jīng)有幾百年歷史了。雖然現(xiàn)在當(dāng)局不提倡,但私下里也沒有禁止,現(xiàn)在中央臺也播出武術(shù)散打的節(jié)目。”[8]馬王比武尚不屬此類,因?yàn)橥鯌c民一度試圖捍衛(wèi)體育的規(guī)則,問題在于馬保國早已放棄了公平競技理念,兩者的比武失去了對稱性。然而,如以儒家文明的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西方格斗帶有與生俱來的文化“原罪”,這種文化原罪帶有多方面的內(nèi)涵。首先涉及中國人常提及的面子問題。儒家文化圈中的人好面子,而純?nèi)坏谋任湟獩Q出勝負(fù),就一定要傷面子,于是,為了維持溫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之做人準(zhǔn)則,民間武者往往在心理上更樂意接受中國式比武方式,而排斥西方的體育規(guī)則。馬王比武的裁判至今未舉起王慶民的手,最主要的原因或許正在于維護(hù)失敗者的面子。在中國獨(dú)特的以和為貴的文化精神影響下,馬保國事件的連鎖性作用還在持續(xù),貌似獲得勝利的王慶民也心情沉重,王慶民對媒體聲明,因?yàn)槠涓改改赀~,他今后不再參加任何比賽了。王慶民試圖還給傳統(tǒng)武術(shù)界一個面子。眾所周知,中國傳統(tǒng)武術(shù)界并未進(jìn)入體育領(lǐng)域,在接受悲劇理論之前,面子循環(huán)機(jī)制仍在起作用。這便涉及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
馬保國事件再度將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凸顯了出來。儒家文化講人性善,而比武現(xiàn)象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身體對抗,屬于人性之惡,于是,中國武者便確立了“點(diǎn)到為止”的規(guī)矩,借以維持人性之善。這里需要解讀一下“點(diǎn)到為止”的學(xué)理價值。只要熟知幼年時代的貓科和犬科動物參與打斗游戲的情況就會知道,點(diǎn)到為止是那些小動物們的本能做法,它們在游戲的時候不會真的傷害對方,它們本能地知道什么時候是在做游戲,什么時候是在參與狩獵。由此也可以推導(dǎo)出,中國式比武的“點(diǎn)到為止”是一種兒童游戲規(guī)則,而非成人世界規(guī)則。可以這樣認(rèn)為,傳統(tǒng)武術(shù)之所以未能發(fā)展成為現(xiàn)代體育,就在于其帶有兒童游戲的特質(zhì),這便推演出悲劇性和喜劇性的對立問題。競技體育是悲劇,中國傳統(tǒng)武術(shù)是喜劇。傳統(tǒng)的中國人講大團(tuán)圓,追求一種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和氣境界。這便說明,中國文化有一種迥異于西方文化的特質(zhì),這其中既包含禮儀教化之學(xué),還包括待人接物之道。中國人的日常人倫文化中有一種隱性的強(qiáng)制規(guī)則,人們一旦越出此規(guī)則,就會失去安全感。馬保國也一樣,他將點(diǎn)到為止看做是武德的特定組成元素。馬保國在《我在英國教功夫》一書中專門講述到武德問題:“一、愛國愛民,遵紀(jì)守法;二、尊師重教,勤奮好學(xué);三、團(tuán)結(jié)同門,情同手足;四、擇良而教,關(guān)愛學(xué)生;五、比武切磋,點(diǎn)到為止。”[3]241由此可知,馬保國的武學(xué)重心是個體的修煉、修養(yǎng)、道德、倫理之類的非體育元素,傳統(tǒng)武術(shù)的非體育屬性在馬保國的身上有較為完整的體現(xiàn)。
其實(shí),以武會友的待人之道的確是中國傳統(tǒng)比武活動的默認(rèn)規(guī)則。有過武術(shù)人類學(xué)考察經(jīng)歷的徐皓峰曾說:“武術(shù)要傳承下去,有很重要的一關(guān)叫‘過門子’,師傅要通過實(shí)戰(zhàn)把看中的徒弟培養(yǎng)出來。要帶著徒弟,或者讓徒弟自己去其他門派比武。以前民間比武要有公證人,要立約,有嚴(yán)格的場地,比前要休息好調(diào)養(yǎng)好,現(xiàn)在不允許這樣了。所以現(xiàn)在的比試往往不是真正的比武,而是在受約束的情況下,局部性、兩個人打那么兩三下,或者在家里就比了。”[9]類似的比武帶有禮俗性,大體可以體現(xiàn)儒家文明傳統(tǒng)。于是,中國式比武從本質(zhì)上講一定是一種喜劇,即便因故出現(xiàn)了悲劇結(jié)果,裁判、主辦方、媒介乃至對手也都會利用各種機(jī)會,將其設(shè)計(jì)、描述或矯正為一種喜劇。王慶民賽后一直聲稱自己練的是傳統(tǒng)武術(shù),而非自由搏擊,其實(shí)就是想抹平由于不和諧因素造成的消極后果,其唯一的價值觀依據(jù)便是以武會友之宗旨。
4 結(jié)語
馬保國事件的爭議面很大。就來自自媒體的信息而言,有人認(rèn)為馬保國事件是個悲劇,與此同時,亦有人像對待喜劇演員一樣議論馬保國。有人從競技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認(rèn)為馬保國打的是假太極,馬保國由此也便成為一種“偽武術(shù)”的代言人。馬保國在賽場上多余的語言很多,但這也是一種中國文化,中國人在文化選擇上有其獨(dú)特性,中國人并不太喜歡純而又純之物,更喜歡一種混成式語境。很難想象成龍的電影中兩位武者孤獨(dú)地格斗而無臺詞之局面,如果出現(xiàn)那樣的場景,中國觀眾就會覺得很孤獨(dú)。成龍的電影是中國儒家文化的縮影,兩位武者一定會亦戰(zhàn)亦言,有聲有色,呈現(xiàn)出一團(tuán)和氣、喜氣洋洋之大團(tuán)圓格局。馬保國也一樣,馬保國事先用語言威脅裁判,看似一種惡性,其實(shí)更容易催生出喜劇元素。由此不難看出,中國式比武和儒家文明本體一樣,其終極價值體現(xiàn)在對喜劇性的追求層面。傳統(tǒng)武術(shù)的喜劇性還有自身的擴(kuò)張能量,當(dāng)它與極富原始感的草根群體融合之后,更容易爆發(fā)出超強(qiáng)的喜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