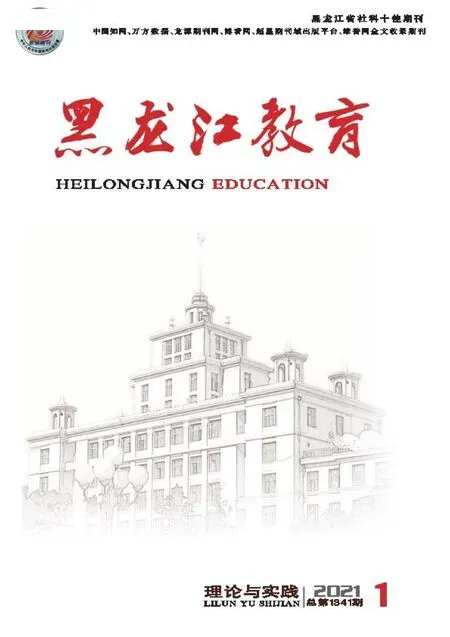地方高校慕課翻轉(zhuǎn)課堂混合式教學(xué)的適宜性探析
魯建輝
(寶雞文理學(xué)院,陜西寶雞721013)
當(dāng)前在一些高校的教室里,“后排課堂”“手機(jī)課堂”“睡覺課堂”等現(xiàn)象讓人憂心。究其原因,其課堂內(nèi)容不能及時反映“互聯(lián)網(wǎng)+”等科技和社會發(fā)展的新興學(xué)科內(nèi)容,內(nèi)容嚴(yán)重重復(fù),人文通識教育內(nèi)容薄弱,真問題關(guān)注不足。因此,大學(xué)教學(xué)改革迫在眉睫,其中教學(xué)方法的改革已成為突破點。慕課、翻轉(zhuǎn)課堂、混合式教學(xué)等方式最為流行。它們是以課堂教學(xué)系統(tǒng)四要素“教師”“學(xué)生”“教學(xué)內(nèi)容”和“教學(xué)媒體”為抓手,提升教學(xué)質(zhì)量與效果的一種現(xiàn)代措施。
一、作為教學(xué)改革著力點的慕課、翻轉(zhuǎn)課堂、混合式教學(xué)
慕課(MOOC)是大規(guī)模在線開放課程教育平臺(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簡稱的音譯,它的“新”在于其規(guī)模和革命性的發(fā)展?jié)摿Γ瑢崿F(xiàn)了過去的教師本位向?qū)W生本位轉(zhuǎn)變,學(xué)習(xí)過程的趣味性和學(xué)生話語權(quán)相協(xié)調(diào)。翻轉(zhuǎn)課堂(Flipped Classroom)教學(xué)模式2007年率先在美國出現(xiàn),短短幾年內(nèi)得到了世界范圍內(nèi)的熱烈響應(yīng)和廣泛實踐,特點是課堂教學(xué)內(nèi)容精簡,質(zhì)量和效果得以提升,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能力和學(xué)習(xí)興趣得到加強(qiáng)。在我國(2000年),“跨越式教學(xué)”(中國式的“翻轉(zhuǎn)課堂”)進(jìn)入了小學(xué)和中西部的廣大農(nóng)村。混合式教學(xué)是以“B-Learning”為標(biāo)志的混合式教育思想指引下的教學(xué)觀念,它是兼取“傳遞—接受”和“自主—探究”這二者之所長而形成的一種全新觀念,強(qiáng)調(diào)“有意義的傳遞與教師主導(dǎo)下的自主探究相結(jié)合”為標(biāo)志的教與學(xué)活動[1]。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混合式教學(xué)是指在適當(dāng)?shù)臅r間,通過應(yīng)用適當(dāng)?shù)拿襟w技術(shù),提供與適當(dāng)?shù)膶W(xué)習(xí)環(huán)境相契合的資源和活動,讓適當(dāng)?shù)膶W(xué)生形成適當(dāng)?shù)哪芰Γ瑥亩〉米顑?yōu)化教學(xué)效果的教學(xué)方式。”[2]整個教學(xué)過程可以劃分為課前、課中、課后三個階段。
慕課、翻轉(zhuǎn)課堂與混合式教學(xué)三者之間既有聯(lián)系又存在區(qū)別。首先,三者原本互相獨立,以各自的模式為主體,在產(chǎn)生的時間上有先后,操作內(nèi)容上各有側(cè)重,應(yīng)用于各教學(xué)領(lǐng)域。如慕課強(qiáng)調(diào)可達(dá)“數(shù)十萬人”的大規(guī)模效應(yīng),在線的多重深度互動,學(xué)教資料的海量累積與加精置頂。翻轉(zhuǎn)課堂則因有面授環(huán)節(jié),所以班級人數(shù)與傳統(tǒng)課堂無二,它強(qiáng)調(diào)“教師”“學(xué)生”“教學(xué)內(nèi)容”和“教學(xué)媒體”四要素地位和作用的深度變革。如“教學(xué)媒體”要求網(wǎng)絡(luò)化教學(xué)環(huán)境(或其網(wǎng)絡(luò)教學(xué)資料的變形),“學(xué)生”“教師”變“先教后學(xué)”為“先學(xué)后教”。翻轉(zhuǎn)課堂開始由教師自制視頻,后來吸收了慕課的大量視頻資源。混合式教學(xué)則融合了慕課、翻轉(zhuǎn)課堂、傳統(tǒng)課堂及其他教學(xué)方式,力圖使它們的優(yōu)點重疊,獲得最佳的教學(xué)效果。其次,三者又相互關(guān)聯(lián),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可以兩兩聯(lián)系,又可以另外兩者為輔助,實現(xiàn)共存。最后,從今天的國內(nèi)教學(xué)實踐看,混合式教學(xué)是主體,慕課、翻轉(zhuǎn)課堂是它的兩種次級形式,它可以根據(jù)課程性質(zhì)對慕課或翻轉(zhuǎn)課堂有所側(cè)重。并且與傳統(tǒng)教學(xué)模式相似度最高、最便于對接,吸取精華,培養(yǎng)批判性思維與創(chuàng)造性思維。
二、地方高校進(jìn)行混合式教學(xué)改革的發(fā)力處與側(cè)重點
地方高校進(jìn)行混合式教學(xué)改革的優(yōu)勢是:人數(shù)絕對值大,師生專注度高,能夠吃苦耐勞,改變落后的期望值大,支持教改的意愿強(qiáng)烈,針對性突破的可能性大。劣勢是:教科研經(jīng)費少,網(wǎng)絡(luò)教學(xué)環(huán)境較差,圖書資料量少,參與國家和省部級項目少,師資薄弱,師生觀念相對落后,教科研的積極性不高,經(jīng)濟(jì)困難生比例大,課程迭代慢。本研究的適宜性問題實際就是在有限條件下爭取教學(xué)改革最大的成功,如何發(fā)力與側(cè)重點的選擇問題。
首先,落實到慕課、翻轉(zhuǎn)課堂、混合式教學(xué)、傳統(tǒng)教學(xué)效果的比對與評價上。要正確評價慕課、翻轉(zhuǎn)課堂、混合式教學(xué)、傳統(tǒng)教學(xué),第一必須搞清楚慕課與翻轉(zhuǎn)課堂的優(yōu)勢與缺失。慕課的優(yōu)勢與對它的質(zhì)疑有以下四點:一是為求學(xué)者(師生)提供了非實時學(xué)習(xí)的窗口,充分利用碎塊時間,對整個教學(xué)過程的調(diào)控非常精密。高校學(xué)生實際上不存在非實時學(xué)習(xí)困難。二是提供了針對性學(xué)習(xí)的窗口,它是該領(lǐng)域“最優(yōu)秀”研究者的思想結(jié)晶,避免求學(xué)者“坐井觀天”。然而,慕課是單向度的信息傳遞,最大的盲區(qū)在于師生不能對癥下藥,教師無法及時了解學(xué)生的需求。三是提供了在線交流的平臺,比較強(qiáng)調(diào)討論、交流與互動,涉及“人機(jī)交互”“師生交互”和“生生交互”的多重深度互動,有基于“大數(shù)據(jù)”的技術(shù)支持,有資源共享和優(yōu)化積累的優(yōu)勢。如撰寫課程wiki,有明確的指導(dǎo)理論支持。然而,如果師生面對面交流得到恢復(fù),此項便利與優(yōu)勢就難以立足。資源眾多會帶來選擇困難。四是慕課平臺、課程數(shù)量眾多。在平臺上獨立學(xué)習(xí),抽象與虛擬提供迅捷與便利。然而,如果過度提倡此等方法,對高校師生則有“喧賓奪主”的感覺。抽象與虛擬的模式使得課堂上鏡頭外的大量隱性信息散失,師生舉手投足、音容笑貌、慷慨激昂的情境難以體會,“親炙”之感無從談起。翻轉(zhuǎn)課堂最大的優(yōu)勢是為求學(xué)者(師生特別是學(xué)生)提供了經(jīng)過初步消化或本土化的學(xué)習(xí)資源,方便求學(xué)者的消化吸收,提升學(xué)習(xí)質(zhì)量。它堅持“以學(xué)生為中心”的教育思想,教學(xué)觀念以“自主—探究—合作”為標(biāo)志。它有兩大施行前提:一是翻轉(zhuǎn)課堂的實施要有網(wǎng)絡(luò)化教學(xué)環(huán)境的支撐。二是教學(xué)者(師生)具備一定基礎(chǔ)、較高學(xué)習(xí)能力與自覺性。對它的質(zhì)疑:一是通常會面臨管理上、技術(shù)上、學(xué)術(shù)上、心理上的較大困難。二是求學(xué)者的教育思想、教學(xué)觀念更新為“以學(xué)生為中心”,教師如何盡力于教學(xué),教學(xué)質(zhì)量真的會提高嗎?三是課前在線學(xué)習(xí)時間和課堂面對面教學(xué)時間(20分鐘+20分鐘+n分鐘)是否能夠調(diào)整或變通?與當(dāng)前的課堂體制難以協(xié)調(diào)一致。四是實施翻轉(zhuǎn)課堂的學(xué)段能否向高低兩端擴(kuò)展?高校能做,職校、高中、初中和小學(xué)能做嗎?
其次,由于混合式教學(xué)既不是傳統(tǒng)教學(xué)的“以教師為中心”,也不是建構(gòu)主義的“以學(xué)生為中心”,而是以Blended-Learning為標(biāo)志的“混合式”教育思想。它不是教師或?qū)W生的單輪驅(qū)動,而是師生的雙輪驅(qū)動。既要發(fā)揮教師啟發(fā)、引導(dǎo)、監(jiān)控教學(xué)過程的主導(dǎo)作用,又要充分體現(xiàn)學(xué)生作為學(xué)習(xí)過程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與創(chuàng)造性。分述如下。
從經(jīng)濟(jì)角度來說,在當(dāng)前的混合式教學(xué)的實踐中,有一種“降低教學(xué)成本”的認(rèn)識誤區(qū)。理由是:其一,引進(jìn)“大師”的慕課比引進(jìn)“大師”成本低得多。其二,管理慕課與本校師生比管理“外援”要容易,成本低。其三,師資培訓(xùn)本身要花錢,引入混合式教學(xué),培訓(xùn)本校師資,一舉兩得,降低了成本。然而,這種“降低教學(xué)成本”的認(rèn)識是淺層次的。實際上,要想將混合式教學(xué)辦好,管理、技術(shù)、學(xué)術(shù)、心理上的困難是巨大的,必須做好師生的能力準(zhǔn)備才能成功開展,其成本花費遠(yuǎn)遠(yuǎn)大于傳統(tǒng)教學(xué)。就混合式教學(xué)本身來說,它最大的特點是既有慕課等在線教學(xué),又有翻轉(zhuǎn)課堂等面授環(huán)節(jié)。此教學(xué)法的復(fù)雜性遠(yuǎn)遠(yuǎn)大于兩者以及它們的簡單加和。對地方高校廣大師生來說,一種陌生且復(fù)雜的教學(xué)方式的施行,減少浪費而取得良好教學(xué)效果的要點是:選擇建立師德高尚、精明強(qiáng)干的課程團(tuán)隊,按學(xué)科分類,選擇少量代表課程進(jìn)行試點,加強(qiáng)相關(guān)理論研究與動態(tài)跟蹤。
從教學(xué)方法本身來說,人們對混合式教學(xué)有一種簡單的“優(yōu)+優(yōu)=更優(yōu)”的認(rèn)識誤區(qū)。如“混合式教學(xué)模式,在‘教與學(xué)’的活動中,充分結(jié)合了網(wǎng)絡(luò)學(xué)習(xí)和對分課堂學(xué)習(xí)的優(yōu)勢”[3]。混合式教學(xué)既吸收了在線學(xué)習(xí)的優(yōu)勢,又具有傳統(tǒng)教學(xué)的優(yōu)勢,教師當(dāng)面引導(dǎo)、啟發(fā)、傳授。從辯證法來講,世間萬事萬物都有優(yōu)長與缺陷,某事物最大的優(yōu)長往往也就是它的最大缺陷所在。例如慕課學(xué)院Coursera宣稱“在網(wǎng)上學(xué)習(xí)全世界最好的課程”,但是它的受眾卻沒有定位為在校大學(xué)生。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優(yōu)勢在于“從頂級大學(xué)免費學(xué)習(xí)技能”。然而,在經(jīng)濟(jì)社會,人們常說“免費的就是最貴的”。“頂級大學(xué)”并不是所有課程都是“頂級的”,跟著世界上“最好的老師”學(xué)習(xí)不一定適合自己,“技能”并不是大學(xué)生“唯一重要的”。翻轉(zhuǎn)環(huán)節(jié)也是為了解決師生不能面授、課堂教學(xué)效率下降時,采取的彌補(bǔ)措施。在實際的教學(xué)過程中,混合式教學(xué)既然要具備慕課、翻轉(zhuǎn)課堂乃至傳統(tǒng)教學(xué)的優(yōu)勢,那么就必須正視三者糅合后產(chǎn)生的復(fù)雜狀態(tài),也必須做出三倍甚至更多倍的努力,從而提升教學(xué)質(zhì)量。
教學(xué)理念就是將各門課程、各種教學(xué)方法、各樣技術(shù)支撐、各項管理服務(wù)貫穿起來的邏輯“紅線”。其一,教學(xué)理念中“師”或“生”孰為中心。古人“以教師為中心”最大的一個現(xiàn)實客觀條件是,那時師資普遍不足,學(xué)生求學(xué)若渴。今人則相反,工業(yè)化進(jìn)程使社會趨于無限復(fù)雜,掌握專門技藝以應(yīng)對社會需求成為燃眉之需。人們處于知識加工處理能力急劇增加的年代,已經(jīng)不苦于沒有東西可學(xué),而是困于面對海量信息無所適從。因此,今人“以學(xué)生為中心”則力圖抓住學(xué)習(xí)容易迷失、積極性不足、深度不夠這一關(guān)鍵問題。這是時代發(fā)展的必然現(xiàn)象,社會生產(chǎn)力升級的必然結(jié)果。同時,“師”的社會化、系統(tǒng)化、數(shù)據(jù)庫化、抽象化,在德性的成長上,幾乎是中性的。《資治通鑒》載:“經(jīng)師易遇,人師難遭。”[4]今天能以其淵博的學(xué)識,高尚的人格修養(yǎng)去教人如何做人就顯得很難。因此,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科技如何進(jìn)步,網(wǎng)絡(luò)教學(xué)都不可能取代面對面的課堂體驗和真實的人際互動;大學(xué)校園的學(xué)術(shù)氛圍和優(yōu)秀教師的人格魅力是任何先進(jìn)技術(shù)和網(wǎng)絡(luò)都無法替代的。所以,今天的地方高校教育工作者,既不要視慕課、翻轉(zhuǎn)課堂、混合式教學(xué)為洪水猛獸,也不必簡單認(rèn)為它們完美無缺。其二,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從它的結(jié)果來說,就是圍繞教學(xué)理念有所取舍,培養(yǎng)出高質(zhì)量的人才。宏觀上,兩千年來“傳統(tǒng)儒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yǎng)社會的管理者,因此,特別重視‘道’的教育,形成了‘重道輕器’的不良傳統(tǒng)”;鴉片戰(zhàn)爭以來,國人深感“技不如人”,力求“師夷長技以制夷”,以至于“當(dāng)前的教育矯枉過正,走到了‘輕道重器’的另一個極端”[5]。微觀上,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完成了一個完整的恢復(fù)、上升、高漲過程,在整體上保持進(jìn)步的同時,也暴露出教學(xué)質(zhì)量與教學(xué)數(shù)量相對嚴(yán)重滑坡的問題,特別在一些地方高校更是如此。其中的緣由,就是對教學(xué)理念定位不清。如今,國內(nèi)高校分為研究型大學(xué)、研究教學(xué)型大學(xué)、教學(xué)研究型大學(xué)、教學(xué)型大學(xué)、應(yīng)用型大學(xué)、高等專科學(xué)校等六大類。不同類型的大學(xué),教學(xué)理念既要有“大學(xué)”的共性,也要有各自的個性。就共性來說,“立德樹人”是當(dāng)今最鮮明時尚的要求,即“道器并重,道為根本”。綜觀當(dāng)前對慕課、翻轉(zhuǎn)課堂、混合式教學(xué)的研究,實際仍是集中在“授業(yè)、解惑”兩個層面。盡管后兩者有面對面的過程與環(huán)節(jié),但是師生間“傳道立德”所用的時空絕對值實際上在縮減而不是擴(kuò)增,教學(xué)的“傳道立德”職能實際在減弱。其三,教學(xué)理念是當(dāng)代社會生產(chǎn)需求的反映。從社會生產(chǎn)的現(xiàn)實來說,中國經(jīng)過四十年的追趕,在諸多領(lǐng)域承擔(dān)了“世界工廠”的職責(zé)。然而,各行業(yè)的生產(chǎn)力水平仍處于中低端,簡言之,就是“大而不強(qiáng)”。探究世界上的高端制造強(qiáng)國,要實現(xiàn)“重器”的制造必須有該領(lǐng)域的“大德大道”的強(qiáng)有力支撐。再具體一點,對制造者來說,業(yè)要精至極致,道、德也要同步提升,否則就難以達(dá)至巔峰。“中國制造”目前進(jìn)入瓶頸階段其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自傳統(tǒng)書院教育土崩瓦解后,中國一心模仿西方大學(xué)教育理念培養(yǎng)“工業(yè)化專才”,卻沒有解決精神歸宿問題的宗教信仰等自救機(jī)制。
三、結(jié)語
通過以上分析得出,混合式教學(xué)是傳統(tǒng)教學(xué)的有益外延和補(bǔ)充。秉持“技術(shù)提升教育的教學(xué)觀”,能對慕課、翻轉(zhuǎn)課堂、混合式教學(xué)的定位達(dá)到適宜。混合式教學(xué)的資源共享與優(yōu)化積累無疑是最值得稱道的。訓(xùn)練大學(xué)生在高校里養(yǎng)成利用網(wǎng)絡(luò)等資源進(jìn)行終身學(xué)習(xí)的能力與習(xí)慣,是它最有價值的地方。然而,在任何教學(xué)改革中要做到“知己知彼”,這樣改革不會因為對阻力估計過高或過低而陷于停滯。就三者自身而言,目前最大的危與機(jī)在于,它們既是新生事物,有無限發(fā)展的可能,又還沒有經(jīng)過時間的沉淀,可能忽焉而亡。它們都以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為自身特點和著力之處,這也表明了今天的人們對“教”沒有那么擔(dān)心,而是唯恐求學(xué)者在知識大爆炸的環(huán)境中迷失與怠惰。然而,當(dāng)學(xué)習(xí)者在知識訴求得到階段性滿足后,對德性成長的渴望就會日趨濃烈,那時,人們會再次去尋覓“人師”的親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