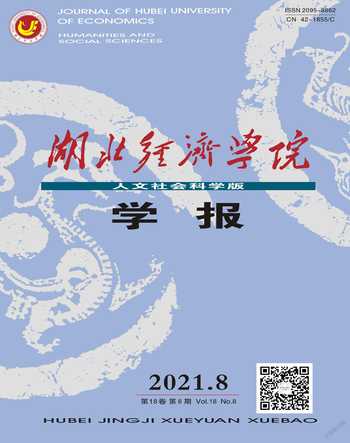民間趣緣組織自主性的生成機制研究
游松梅
摘要:自十八大以來,社會組織日益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社會組織是連接國家與個人的重要載體,在協商民主、社會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基于此,針對地緣下的民間趣緣組織,從組織行動、組織服務、組織資源三個維度和地方民情土壤、地方治理網絡兩個變量搭建趣緣組織自主性生成機制的解釋框架。案例研究發現,地方民情土壤主要通過在地內生和關鍵群體作用影響趣緣組織的人力資源、社會認同和支持資源等的獲得,地方治理網絡則通過屬地管理和協同治理機制影響趣緣組織的合法性身份和組織發展資源獲取,同時促進組織認同。民間趣緣組織正在成為基層治理的重要參與主體,對于民間趣緣組織自主性進行研究有利于我們了解在基層治理中,不同類型社會組織對其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社會組織;自主性;地方治理網絡;民情土壤
一、文獻回顧及問題的提出
長期以來,學界對于社會組織自主性的研究是不同學科關注的重要議題,在此之下形成了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多種視角。總的來說,學者們大從結構性視角和能動性視角來展開進行討論。結構性視角下的組織自主性研究主要關注在宏觀制度背景下社會組織自主性的獲得,認為社會組織自主性是國家權利讓渡的結果,國家對社會組織的態度和管控程度和政策環境下所釋放的空間是社會組織獲得自主性的關鍵。俞可平通過對我國多種類型的社會組織進行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組織面臨著政策制度下的“宏觀鼓勵與微觀約束”,社會組織的自主性有賴于國家政策制度下的所釋放的空間[1]。康曉光、韓恒通過考察國家對多種社會組織的控制,認為國家對社會組織采取了“分類控制”策略,而在此制度背景下,部分社會組織能夠獲得相對的自主性[2]。唐文玉認為在“分類控制”基礎上,中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是“行政吸納社會”,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在于政府對其的“控制與支持”。劉鵬在對地方治理實踐進行研究中發現,政府在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方面正逐步從分類控制轉向“嵌入型”監管,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取決于國家嵌入程度的高低[3]。鄭曉華、于瑞川對上海兩個社會組織的生存策略進行分析后認為,在政府“選擇性支持”下,社會組織能夠獲得一定的自主性和獨立性[4]。總體而言,結構性視角下社會組織的自主性主要來自國家宏觀的制度環境,強調國家掌控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影響。
能動性視角下社會組織的自主性主要關注社會組織的“策略性自主”,即社會組織在國家制度環境下并不是被動接受,社會組織能夠通過自身的一些“策略性”行動獲得自主性。唐文玉、馬西恒認為具有“合法”身份的民辦組織通過“去政治化”的策略實現自身的自主性[5]。黃曉星表示在街區強權力結構下,社會組織發展出直接嵌入策略、權變性策略和專業維持策略三種類型以實現自身的自主性獲取[6]。管兵通過對政府購買下的社工組織進行研究,發現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通過“反向嵌入”性活動獲得發展空間[7]。紀鶯鶯認為我國國家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是一種“雙向嵌入”與“雙向賦權”,在這種關系下,社會組織能夠能動的嵌入國家治理體系,以提升自己的自主性[8]。“結構—能動”視角下社會組織的自主性的研究使得現有研究處于“制度—策略”的二元論困境,因而近年來有學者開始關注國家政策制度與社會組織策略下綜合性分析,從而發展出一種整合性的視角。黃曉春表示中國社會組織自主性生產是嵌入在一系列的不同層次互動過程中的,需要超越“結構—能動”視角,提出了“非協同治理”的解釋框架[9]。郎曉波通過對多邊合同執行下的社會組織自主性進行了考察,提出“剩余控制權”框架作為從結構到行動的中間變量分析,延長了制度分析的解釋鏈條[10]。
可以看出,結構性自主認為社會自組織實現自主的前提是獲得自身的獨立性,即合法性,是國家政策制度下的依附型自主,而能動性自主認為其自主性的獲得是通過去政治化以擺脫行政制度對社會組織的干預和掌控,并能夠對國家權力進行一定的約束,防止權力濫用。然而不論是結構性自主,還是能動性自主,都是基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的理論價值前提下對社會組織的自主性進行分析,認為國家與社會是二元對立,政治依附性強的社會組織自主性較弱,反之則自主性強。但是,近年的研究已經證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并非此消彼長,政治依附能夠使社會自組織獲得更加系統性的支持方案,使其納入國家基層治理的體系當中,實現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有機聯動部分,同時,社會自組織自身的內在自主性能夠推進國家治理的善治。可見,“結構—能動”單一視角下的社會組織自主性隨著近年來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已經不能完全解釋現有的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全部樣態。在中國的具體語境下,社會組織并非只有單一的結構性自主或能動性自主,又非單一的內在性自主,而是多種自主性交互的結果,是一個兼具多樣自主性的組織。基于此,本文試圖構建一個綜合性的分析框架,試圖分析在現代城市的基層治理中,以興趣愛好形成的社會趣緣組織的自主性的來源有哪些,其生成的機制如何?
二、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內涵及維度
在西方的背景下,早期社會組織主要指的是非政府組織,即“在地方、國家或國際間組織起來的非營利的自愿的公民團體”[11],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社會組織的概念和外延也不斷深化。薩拉蒙從學理層面對社會組織進行了界定,認為非政府組織包括了非營利性、自愿性、組織性、自治性以及民間性五個維度,它能夠天然的與政府進行區隔,并能夠不受外界影響而實現自身的活動[12]。社會關系以及結社生活具有制度化的,相對于國家的自主性,萊維特則反向提出“第三部門”的概念,從邊界上區分非政府組織,即將“政府”和“企業”視為非政府組織的邊界[13],部分學者還從政治結構視角出發,認為社會組織自主性是“社會關系以及結社生活具有制度化的,相對于國家的自主性”[14]。在中國語境下,對社會組織的自主性有著更為多樣的解釋。黃曉春認為社會組織的自主性是多層次的,包括了政治層面的結構性制度安排和行動策略層面的日常性生活運作,并在這兩個層面下提出了社會組織在活動領域、活動地域和運作過程三個維度的自主性[15]。費迪、王詩宗認為組織的自主性意味著組織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標來行事,其目標設定和自身運作過程中的決策方式都是自己確定的,并將組織的自主性操作化為組織目標認同度、人事安排權、主營業務權三個維度[16]。本文同樣認為包括趣緣組織在內的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存在多種層次與結構,呈現出不同的維度,通過對以往文獻的不同梳理,發現社會組織的自主性主要包括組織外部的制度性土壤也包括了組織內部治理結構、行動安排、自我決策等內部因素。通過操作化的定義,將社會組織自主性劃分為行動自主、資源自主和服務自主三個方面。
首先,行動自主是指組織能否以合法的身份進行活動,能否按照自我的意愿行事,其主要包括身份獲取和認同兩個方面。其中,合法性身份的獲取代表著組織身份被法律所認可,這是社會組織開展各種活動的基礎[17]。實際上,有許多社會組織在成立之初并沒有得到法律承認,因為其在最開始沒有進行注冊,尤其是對于基于共同興趣愛好而組成的趣緣組織來說,而對于這種情況來說,能否獲得有效的身份是決定其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認同是指社會共識,指社會組織能夠獲得它所在地方的支持,從而實現自身的自主活動,這是其根基。這種“社會合法性”不僅對那些民間會社是至關重要的,而且也是其他一切社團開展活動的基礎[18]。其次是資源自主。資源自主的指標主要包括人力資源以及其他資源兩部分。作為趣緣組織來說,其本身就是因為共同愛好而組成的,組織成員是其自主性的重要標準之一,長期存在并保持穩定的共同興趣愛好的成員是組織不斷開展活動的重要因素,穩定且具有向心力的人力資源能夠穩定組織內部的結構,同時促進組織不斷發展狀態。Pfeffer和Salancik提出的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一切組織都不能獨立發展,需要借助外部環境的資源來減少自身的不確定性[19],因而除了基本的人力資源外,社會組織的自主性還與資金、渠道、場地等諸多資源相關。最后,服務自主是指社會組織服務的服務領域和服務地域自主兩方面。服務領域是指社會組織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自主決定提供服務的范圍,即組織所進行的活動或提供的產品是否符合社會需求與公共價值。而服務地域則是指社會組織能否突破地域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圍內實現自己的活動,它代表了社會組織的組織規模、社會動員能力、競爭水平[20]。
三、分析框架
(一)地方民情土壤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影響
社會組織的發展依托于其所在地的地方民情土壤,但人們往往遺忘了社會組織結社自由的“民情”土壤,即組織結社所秉持的公共性價值承諾,這些公共價值承諾是社會組織發展過程中對責任、道義、專業水平等的秉持[21]。在地方民情土壤下,在地內生是社會組織自主性的重要影響因素。在地內生性是指組織的產生和發展內嵌于特定區域,符合特定地域群體的文化和利益,其從特定地域的微觀社會力量中[22]。在地內生要求我們從社會與社會的角度去思考,一個社會組織是否能夠滿足其所在地方基層的需求,獲得地方基層群眾的支持與認可,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其自主性的高低,這要求社會組織必須參與到地方的實踐中,并在實踐中切實滿足需求。除此之外,作為一個組織,尤其是以共同興趣愛好而形成的組織,其人員是重要組成要素。在組織中,“關鍵群體”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奧斯特羅姆指出在人際網絡中能夠產生信任、合作、聲譽,而組織中的關鍵群體通過社會互動,能夠加深組織與社會網絡的聯系,在這當中產生出組織與地方的關系互動,提高社會組織的社會資本存量。另一方面,組織的政治關聯也會為組織提供一定的自主生存空間,政治關聯主要指非盈利組織高層曾擔任或現擔任政府職位[23],這就將組織行為與關鍵群體的行動邏輯聯系在一起。可以看出,一個組織內部關鍵群體知識觀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組織自主性的獲得。
(二)地方治理網絡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影響
作為現代基層治理的重要體現,地方的治理制度對社會組織自主性具有重要的影響。隨著政府治理能力轉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將社會組織納入社會治理體系,各地方政府也不斷響應號召,紛紛出臺相關文件,完善頂層制度設計,社會組織有了長足的發展。制度環境的結構性轉變為社會組織創造“增速發展”的契機和條件的同時,制度中蘊含的各種有意識或非預期的制度邏輯同樣會作用于社會組織[24]。在這當中,“地方屬地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組織帶來了發展的空間,在屬地管理下形成了政府對所轄地區的特殊信任機制,能夠穩定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長期關系,拓展社會組織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隨著協同治理的不斷發展,地方治理強調分權化和自主管理,同時倡導政府間、地方政府與民營企業之間、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廣泛合作[25]。協同治理要求將社會主體納入治理體系,強調多主體的協同參與,在這過程中,社會組織在地方治理中參與地方政策、公共議題等的討論,逐漸形成參與協商機制,不斷擴大組織的影響力,獲得長足的發展。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社會組織的自主性獲得及包括其外部制度環境、社會環境,也包含著其內部的組織稟賦,但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一個大的前提是社會組織要考慮其所在的地方場景下去如何獲取自主,尤其是對于趣緣組織這類本身就依賴于地方土壤的組織,基于此,構建以下分析框架(如下圖1)。

四、案例分析
(一)案例選取與介紹
接下來本文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對地方基層中的趣緣組織的自主性生成機制展開進一步的分析,以期實現更深層次的剖析。本文主要聚焦于民間趣緣組織自主性受到哪些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以及如何影響的,是為什么和怎么樣的問題,因而欲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本文主要研究地方背景下的社會趣緣組織的自主性生成機制,所以主要選擇的是具有趣緣組織特征和參與了地方基層治理的社會組織作為研究對象。本文選取了C市H編織隊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其原因如下:一是其具有典型性。首先,H編織隊具有典型的趣緣組織色彩。H編織隊最早是由幾名手工編織愛好者在一起相互學習而組成的,是單純的因為共同的興趣愛好而形成的社會志愿組織。該編織隊于成立于2009年,在社區民政局備案,經過10余年的發展,目前共有核心骨干成員30余名,興趣學員2000余人。其次,H編織隊參與了地方基層治理。與一般的趣緣組織不同,H編織隊在自我活動的同時,也作為地方基層治理的重要參與主體,其積極參與社區治理的各種議題,承擔著基層治理功能。二是其具有代表性。H編織隊的社會影響力較強,受到多次表彰,被評為C市學習型團隊,經常進行對外的經驗交流活動。除此之外,H編織社作為城市基層地域下的趣緣組織,與同類型的因興趣愛好而組成的城市基層社會組織具有相似性,能夠成為我們觀察趣緣社會組織自主性生成了一個窗口。
(二)案例分析
1.地方民情土壤下的自主性生成:在地內生與關鍵群體
在地內生的第一個影響是實現服務領域和服務地域的自主。一方面,在社區內部的服務不斷增長。H編織隊首先是趣緣型的組織,首要滿足的服務是成員共同的興趣愛好,H編織隊每周星期二下午都會舉辦固定的交流會,組織成員在會上進行相關編織技藝的傳授和交流。通過這樣的方式,編織隊的名氣不斷擴大,是其所在社區的典型。除此之外,編織隊組織愛心義賣、愛心扶助等公益活動,進行志愿服務,這已經超越了其已有的服務,逐漸將組織服務由服務組織內部轉向服務社區,更加凸顯出組織的公共精神,使得組織的服務領域不斷擴大。另一方面,H編織隊影響力擴大,成為該社區多外宣傳的重要素材。如C市每年12月份的冬日志愿大型文化活動啟動儀式都會在該社區舉辦,“市文明辦的市委宣傳部的都會來,我記得14年的時候市委宣傳部的嚴部長來看到我們做的絲網花,都大力稱贊我們,那個時候我們編織隊在整個C市都是很有名氣的。”(訪談資料20190413A)通過這種方式,發源于地方,但不僅限于地方,讓編織隊的服務范圍不斷擴大,獲得了更多的發展途徑。除開服務領域的自主,在地內生還是使得H編織隊在服務地域上不斷突破。在地內生要去組織不斷滿足需求,在滿足需求的同時,H編織隊也逐漸超越社區地域范圍,與社區外的各類組織展開交流與合作。例如參與冬日志愿者活動,H編織隊會將圍巾、手套等編織品以送溫暖下鄉的方式送給C市轄下偏遠山區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同時還與市老年協會開展合作;開展免費的手工編織技能教學和培訓,進入市委宣傳部大院教領導們編織;與C市其他區縣開展聯合活動。
在地內生的第二個影響是實現認同和人力資源的獲取。評判一個組織是否屬于在地內生,其重要的標準就是其是否是在具體情境中根據具體的需求而產生的。在現實中,有許多組織的產生不是根據內在需求而是通過外力驅使而形成,這就在“基因”上隔離開。H編織隊是社區內部基于共同興趣愛好而形成的,作為趣緣組織,其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本土基因。在最開始,編織隊主要服務于其內部的成員,從需求滿足出發來看,其能夠滿足成員內部的共同愛好的需求。但是,要想獲得長足的發展,組織必須在更大的范圍內實現自己的公共價值,并在更大的程度上滿足更為廣泛的社會需求。從H編織隊的組織策略來看,其主要是采取先社會,后政府的方式來實現自身的服務自主。首先,H編織隊作為興趣愛好型組織,不斷的接納吸收新的成員,為有共同興趣愛好的人提供平臺,滿足社區了部門社區居民自我實現的需求。其次,隨著其志愿隊伍的不斷壯大,H編織隊的手工編織產品增多,編織隊將其編織產品進行義賣,并將其義賣收入用于社區內的志愿活動,如逢年過節將義賣經費用來購買禮品,送給社區內的空巢老人。同時,H編織隊的成員以義工的身份,加入社區志愿者,在社區內做志愿服務,參與地方實踐,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自己的公共價值,滿足地方需求。可以看出,H編織隊是在先滿足了社區需求的基礎之上,再在日常活動中逐步滿足地方治理需求,這種先社區后政府的方式使得H編織隊將組織變為社區自己的組織,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另一方面,在不斷的地方實踐中,H編織隊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由此吸引力更多的成員加入其中,這也使得H編織隊獲得了部分人力資源。“像我們編織隊平時都會配合社區搞活動,進行組織宣傳,大家都知道我們。我們每周星期二都會在社區的會議室組織開展編織活動,有很多居民他們覺得我們這個很有意義,既能夠滿足業余的興趣愛好,同時也能發揮自己余熱,為社會做貢獻,他們自己就會來加入我們。”(訪談資料20190412B)通過在地內生,H編織隊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進來,為組織積累人力資源。
關鍵群體的首要作用是獲取人力資源。H編織隊自成立以來,以隊長、副隊長以及核心骨干為主的關鍵群體在組織管理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社會資本。在中國的鄉土社會中,常常會出現“能人現象”即鄉土精英,他們比普通的公眾擁有更多的知識、經驗等,受到普遍的尊重,能夠進行突出的人員動員,將其移植到基層治理中,這樣的“能人精英”同樣存在。關鍵群體能夠憑借自身的威望和人情法則吸引成員加入。H編織隊的隊長既是編織隊的隊長,同時又是志愿隊的隊長,其擔任隊長時間長,積極熱心,在社區中具有較高的威望,許多成員最初都是在她的號召下加入編織隊和志愿隊。“我加入編織隊是因為王阿姨很熱情,經常喊我們發揮余熱,她能說會道,還積極幫我們解決問題,我們平時生活上有什么問題直接給她說就行了,基本上都能給我們解決。”(訪談資料20190413C)
其次,關鍵群體能夠幫助組織獲得其他相關發展資源。除開對人力資源的吸引,關鍵群體還能依靠自身的一些政治關聯鏈接組織發展所需的其他資源。在某些非盈利組織中的,有政治關聯的組織管理者或是成員會影響組織資源的獲取和自主性,在鄉村治理中,這種具有政治關聯的人常常稱作“政治能人”,體制內的政治能人可以定義為“國家代理人”與“村莊當家人”的雙重角色[26]。在本文中,將與體制內有著較好聯系和良性互動的關鍵群體也稱作政治關聯。H編織隊的副隊長王阿姨就是一個有著政治關聯的關鍵群體。王阿姨身兼數職,首先她擔任社區文化志愿者,這是社區推薦,區文旅委批準的志愿者,作為社區文化志愿者,王阿姨經常和社區分管文化的工作人員以及區文化中心打交道。其次,王阿姨還是社區黨組織分書記,組織黨支部的會議開展,經常社區的工作人員打交道。通過與體制內的人保持長期友好的關系,借助這種政治關聯,H編織隊能夠獲得部分發展資源。如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項目,H編織隊會鏈接社區內的其他組織共同進行服務,獲得部分項目購買資金,同時,在編織隊自身需要進行活動時,可以同社區申請場地、服裝等相關物資資源的支持。
地方民情土壤主要通過在地內生和關鍵群體影響H編織隊的自主性,編織隊在內生實際上是通過在地方具體的實踐中來實現自身的公共價值與社會需求,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服務領域的自主。而服務領域的自主使得編織隊的影響力不斷提高,獲得了許多外部資源,從而使其能夠“走出去”,與不同的組織形成合作,突破地域的限制,獲得自身的服務地域自主。關鍵群體一方面依靠其“能人現象”以及情感互惠,吸引成員加入組織,累積組織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憑借其與體制內的政治關聯,獲得組織發展的支持資源。
2.地方治理網絡下的自主性生成:屬地管理與協同治理
屬地管理使得編織隊獲得了合法性身份和組織發展資源。H編織隊最初是由社區內幾名愛好手工編織的退休人員組成,在2009年成立之初就在街道備案,成功備案后,編織隊就成為較早批納入T街道管理的社會組織。隨后,隨著其不斷壯大,街道對其進行號召引導,逐漸將其納入志愿者服務隊,其成員也不斷增長,于2013年在區民政局備案,至此,H編織隊逐漸擁有官方賦予的合法性身份。合法性身份的獲得使得H編織隊能夠以一個較為正式的身份進行其活動并參與到社區的管理中,開始獲得了其較為初步的自主性和組織發展空間。合法性身份的獲得使得組織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資源,首先,H編織隊在最初備案的時候,獲得了3000元的發展資金,這是H編織隊最初的發展資金。其次,合法性身份也使得H編織隊形成了較為正規的組織結構。街道幫助編織隊形成了有效的組織規章制度,如對編織隊進行組織管理的技術指導,形成了如考勤、財務、日常訓練活動時間、活動安排等規范管理制度和教學方法。
屬地管理下促進了編織隊特殊信任的獲得。屬地管理下的H編織隊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街道社區會將其看作“自己人”,通過體制“吸納”,街道社區一直與H編織隊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在這過程中,街道與組織形成了一定的特殊信任關系。“因為我們是屬于他們(街道)管,平時也都是在社區和居委會的一起,我們和他們的關系非常好,他們也非常信任我們。平時街道要組織什么活動,就直接通知我們就行了,我們搞活動需要一些物資,比如說服裝、道具一些東西,就直接向上申請,一般街道都會批準。”(訪談資料20190413A)可以看出,屬地管理下H編織隊能夠獲得體制內的特殊信任,這種特殊信任也使得H編織隊獲得了組織發展的部分支持資源。一是組織保障資源。H編織隊日常活動在社區,與居委會關系良好,居委會每周星期二下午會預留一間社區內的辦公會議室作為編織隊日常活動開展的場地,并配備桌椅等基本物資,減少了H編織隊的場地費用,日常活動固定物資開銷等,二是提供部分活動物資。H編織隊進行編織義賣活動時,需要購買原材料,一般情況下編織隊會就地取材或者利用組織經費,但當經費不夠時,可以向街道提出申請,街道會在合理范圍內提供部分原材料或是資金。
協同治理模式下促進了認同和人力資源的獲得。協同治理要求充分發揮社會主體的作用,打造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協同共治的局面。在這樣的思路下,地方基層政府通過屬地管理方式將H編織隊納入基層治理體系中。因此H編織隊除開日常的編織活動,同時還參與社區議事、社區服務、社區管理、志愿活動等,在這過程中不斷加深了與社區和居民的交流。“我們會參加志愿活動、打掃社區的清潔、維護社區治安、看望空巢老人,跟社區內的居民都很熟,他們非常相信我們。平時居委會在社區搞活動,我們都去幫忙,給居民進行宣傳,給他們發禮品,和居委會的人也很熟悉。”(訪談筆記20190412A)在協同治理的模式下,H編織隊作為重要的社會參與主體,在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中獲得普遍的認可。一方面,通過合法性身份和日常與居委會的合作等,得到了社區居委會的認同,另一方面,借由居委會的官方治名,在日常社區服務中取得了社區居民的認同,這是其自主性的來源。
五、結論與討論
C市H編織隊的案例反映了地方環境下的社會組織的自主性生成機制,首先,基于共同興趣愛好的小部分群體自發組織,進行興趣愛好活動,此時組織松散、不穩定且具有非正式性,在這個階段,組織具有初步的自主性。其次,隨著組織內關鍵群體的作用,組織開始聚類人力資源,活動不斷不斷擴大、發展,經由身份合法性獲得組織初步發展資源,這個時期組織逐步趨于正式、穩定,并不斷實現在地內生,進行自主擴張。最后,隨著組織內部結構的完善,組織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被納入地方基層治理體系當中,通過社會治理的參與,實現與不同群體的持續性互動,借由這種方式實現反向的在地內生,獲得了普遍的認同和支持,并完成服務領域和服務地域的自主。
隨著社會組織的發展步入“快車道”,對于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的自主性生成機制研究有利于我們全面認識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的內在機理。在中國語境下,對社會組織的研究應當放在其具體實踐的土壤下思考,才能夠窺探其發展全貌。通過C市H編織隊的案例研究表明,深植于地方土壤下的民間趣緣組織的發展深受地方環境的影響,在組織自主性生成過程中,其在地內生是較為重要的因素,在此之下,地方治理網絡也為其自主性獲得提供了一定的空間,自十八大以后,社會力量被納入治理體系,社會力量成為基層治理不能缺少的力量,而擁有較強民眾基礎的地緣性民間組織也逐漸成為基層治理中的重要力量,這要求政府要充分能發揮其組織性,給予合理的制度環境土壤,實現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的良性互動關系。
參考文獻:
[1]俞可平.中國公民社會:概念、分類與制度環境[J].中國社會科學,2006,(1):109- 122,207- 208.
[2]康曉光,韓恒.分類控制: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J].開放時代,2008,(2):30- 41.
[3]劉鵬.從分類控制走向嵌入型監管:地方政府社會組織管理政策創新[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25(5):91- 99.
[4]鄭曉華,于瑞川,劉星宇.政社互動關系視角下的社會組織生存策略研究———以上海市獅子會服務隊和凌云綠主婦為案例的考察[J].中國第三部門研究,2016,12(02):3- 20+160.
[5]唐文玉,馬西恒.去政治的自主性:民辦社會組織的生存策略———以恩派(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為例[J].浙江社會科學,2011(10): 58- 65+89+157.
[6]黃曉星,楊杰.社會服務組織的邊界生產———基于Z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5,30(6):99- 121,244.
[7]管兵.競爭性與反向嵌入性:政府購買服務與社會組織發展[J].公共管理學報,2015,12(3):83- 92,158.
[8]紀鶯鶯.從“雙向嵌入”到“雙向賦權”:以N市社區社會組織為例———兼論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構[J].浙江學刊,2017,(1):49- 56.
[9]黃曉春,嵇欣.非協同治理與策略性應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J].社會學研究,2014,29(6):98- 123,244.
[10]郎曉波.剩余控制權:社會組織自主性的機制考察———以H市多邊合同執行為例[J].中國行政管理,2020(04):117- 124.
[11]馬全中.非政府組織概念再認識[J].河南社會科學,2012,20(10): 36- 39,107.
[12] Salamon L M. The Rise of the Non- Profit Sector [J]. Foreign affair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4,73(4):109.
[13]王晉.第三部門:市場與政府的非零和產物———兼論我國第三部門的現狀及發展趨勢[J].政治學研究,2004,(3):107- 116.
[14]葉士華,孫濤.政府購買服務背景下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影響機制研究———從組織資本視角分析[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20,21(5):89- 99.
[15]黃曉春,嵇欣.非協同治理與策略性應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J].社會學研究,2014,29(6):98- 123,244.
[16]費迪,王詩宗.中國社會組織獨立性與自主性的關系探究:基于浙江的經驗[J].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4,30(1):18- 26.
[17][18]高丙中.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2000(02): 100- 109,207.
[19] Hillman AJ, Withers MC, Collins BJ.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A Review[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9,35(6).
[20]黃曉春,嵇欣.非協同治理與策略性應對———社會組織自主性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J].社會學研究,2014,29(6):98- 123,244.
[21]曾琰.超越“結構性自主”: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的“內在性自主”導向及啟示[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3(6):131- 137.
[22]林磊.在地內生性:社會組織自主性的微觀生產機制———以福建省Q市A社工組織為例[J].中國行政管理,2018,(7):79- 86.
[23]許鹿,李云.社會組織在政治關聯中的自主性生產何以可能?———評《跨部門協同中非營利組織自主性的形成機制》[J].公共管理學報,2013,10(4):12- 14.
[24]方勁,趙翔.內外有別:屬地主義與社會組織的生存空間拓展———基于Z組織發展歷程的案例分析[J].社會工作,2019,(6):76-87,111.
[25]孫柏瑛.當代發達國家地方治理的興起[J].中國行政管理,2003,(4):47- 53.
[26]羅家德,孫瑜,謝朝霞,和珊珊.自組織運作過程中的能人現象[J].中國社會科學,2013,(10):86- 1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