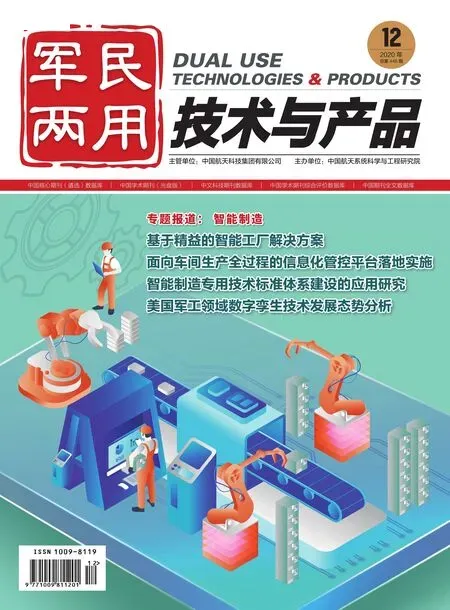日本當前航天政策及其發展動向(下)
福 州 大 學 李瀟瀟
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 王海洋 史 鑫
(接上期)
五、日本航天政策的著力點
日本學者認為,要落實《宇宙基本法》的理念,需要解決3 個方面的課題:其一是配備滿足國家航天戰略所需的裝備;其二是建立基于《宇宙活動法》和《衛星遙感法》的航天產業;其三是必須強化和美國及相關盟國的合作。
(一) 完善航天裝備
日本學者認為,人造衛星、運載火箭等航天裝備是實施國家航天戰略所必需的工具,然而日本在各類航天裝備方面已經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10]。就各類衛星而言,美國、歐洲、俄國及中國目前的在軌衛星種類比較齊全,而日本的在軌衛星相對而言尚不成體系,還不足以實現該國《宇宙基本法》和《國防安全戰略》所設定的目標。為此,日本需要盡快配備滿足其戰略需求的航天裝備,給自衛隊配備包括偵察衛星、早期預警衛星、定位衛星、氣象衛星、海域感知衛星、彈道導彈預警衛星、情報收集衛星、通信衛星、空間態勢感知衛星等在內的一系列外空資產,并形成有效的外空系統(見圖2)[22],包括:海域感知(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MDA)、空間態勢感知(Space Situation Awareness,SSA)和國家地理空間情報(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NGA)系統等。
(二)發展航天產業
日本強調在航天立法框架下發展航天產業(見圖3)。在《宇宙基本法》《宇宙活動法》《衛星遙感法》的框架下,日本政府提出了旨在振興其航天產業并放松管制的航天產業發展愿景:要求簡化民間利用國有設施的手續并設立新的航天發射中心,簡化高壓氣體、燃料的管理辦法,鼓勵企業參與航天發射,從而建立更加堅實的航天產業基礎。同時,出臺航天產業振興政策,鼓勵各地建立航天研發基地,努力降低火箭及衛星成本以提高國際競爭力,推動海域感知衛星等小型衛星的批量生產及海外發射合作[10,22]。
(三)強化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的航天合作

圖2 日本航天政策擬構建的航天裝備體系

圖3 日本航天立法框架與產業愿景的關系
日本沿襲一貫緊跟美國的政策,在航天領域尤其是國防安全相關的航天領域,強調從所謂“國際合作的積極和平主義”立場出發,以美日同盟為主軸擴大和深化與各國的合作關系。通過“日美國防安全協議委員會”,美日重審《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并達成一致[10]。“美日航天相關領域全面對話會議”確認了“根據共同面對的國防安保問題,需要加強日本的航天能力,并提升安全相關外空資產的抗打擊能力”;此外,還提出了遙感及其數據政策,GPS 和“準天頂星”定位系統協同建設,以及完善空間態勢感知和海域感知能力等方面的事項[23]。未來隨著技術進步、危機性質的變化,日本還將進一步深化與美國及其他盟國的合作關系,在亞洲和澳洲地區開始參與國際活動[24,25]。
六、日本航天政策施行中的問題
近年來,日本陸續出臺的航天政策所描繪出的“藍圖”不可謂不宏大。然而,由于日本政府部門的低效,政黨之間的爭執與輪替,以及財政經費的捉襟見肘等一系列問題,一些政策出現反復,制度運行過程中“問題”頻發,相關計劃無法有效施行[1,26—28]。在經費預算方面,各省廳經費籌措效率較低,“國防安全”、“產業振興”和“科學技術”的預算也無法做到均衡分配。在政策重點方面,有日本學者認為,該國航天政策對國防安全領域的關注仍屬“不足”,外空系統在國防安全領域的有效利用還比較“遲緩”。在管理機制方面,各省廳間由于條塊分割,情報不能共享,無法有效統籌“國防安全”、“產業振興”和“科學技術”三方面的任務。此外,日本從事航天產業的企業和人員數量存在萎縮的趨勢,外空開發利用的進度遠低于預期。
七、未來日本航天政策的動向
(一)依托航天技術提高作戰能力
日方對未來航天技術在軍事偵察、預警領域的應用做了比較系統的規劃:不僅要強化對周邊國家軍事設施等目標的監測能力,還要建立對自衛隊海外活動地區周邊國家的動態監測體系,并建立配套的信息傳輸系統,以便及時向任務區域自衛隊傳輸觀測情報[10]。此外,日本還以“朝鮮導彈威脅”為借口,要求提升早期預警及攔截周邊國家彈道導彈的能力,要求研發先進的早期預警探測裝置,并在衛星平臺上搭載這些探測裝置。利用美日同盟關系,一方面,建立來自美國早期預警衛星情報的分析及評價體系,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提高數據分析效率;另一方面,積極參與美國下一代早期預警衛星研發工作,掌握更先進的軍事航天技術[25]。
JAXA 為日本航空自衛隊提供空間態勢感知系統等方面的技術培訓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不僅如此,日本還依據其2018 年的《防衛計劃大綱》設立了20 人組成的“宇宙作戰隊”,預計在2022 年該部隊的人數將增至100 人,2023 年還將在山口縣建立自衛隊的深空探測雷達(Deep Space Radar)[23]。當前,這支“宇宙作戰隊”的任務設定是遂行空間態勢感知任務,監視針對日方衛星的干擾和物理摧毀活動。雖然,其任務設定表面上沒有提及主動攻擊的內容;但日方學者認為,依據《國際法》,在其衛星遭受“攻擊”的情況下,采取反制措施和報復行動理所當然。此外,日本這支“宇宙作戰隊”的設立也是其積極配合美國太空軍建設的重要舉措;預計其未來與美國太空軍開展聯合訓練甚至執行聯合作戰任務也屬大概率事件[25]。
(二)升級裝備強化外空基礎設施建設
未來日本將升級其情報收集衛星的性能,發射20 顆以上的小型高分辨率觀測衛星,對其周邊區域實現每小時一次以上的高頻度觀測,并加大在軌設備的備用品儲備。同時,依托美日同盟,在各自衛星平臺上相互搭載探測裝置,并約定在彼此衛星遭到攻擊的情況下共同防御,從而增強其外空系統的能力和安全性[23]。此外,日本還試圖將民用衛星用于國防,從而增加自衛隊衛星的數量;還考慮與盟國乃至團體、企業簽訂太空監視數據的采購、共享協議。日方學者為其未來(21 世紀20 年代)外空裝備謀劃了一系列發展目標,部分內容如表6所示。
日方強調外空基礎設施的體系化,對其空間態勢感知系統、海域感知系統及區域定位系統等空間基礎設施的建設給予高度重視,并謀求未來對提升相關系統的性能[29]。具體而言,要求空間態勢感知系統具備對太空殘骸的監測能力,并賦予在軌衛星應對撞擊的變軌能力;通過深化與美國的合作,加強對太空碎片和彈道導彈的飛行情況等實施監控[10];同時,提升對海上交通線、專屬經濟區等海域航行船只的監控和追蹤能力,確保政府能持續掌控專屬經濟區的情況。

表6 未來日本的主要外空技術裝備發展目標
在全球定位領域,未來日方謀求建立七星組網的“準天頂衛星”定位系統,實現相對獨立的區域衛星定位功能,確保在沒有美國GPS系統支持的情況下,也能實現獨立定位和授時。同時,通過推廣日本的區域衛星定位系統、出口配套的定位設備,提升其國際地位并在國際定位市場中分得一杯羹[30]。此外,作為其第三版《宇宙基本計劃》中與盟國合作的重要內容,計劃在2023 年發射的“準天頂衛星”上將搭載美國探測裝置。
(三)培育高適應性的運載發射能力
日方考慮到財政吃緊的現實,一方面,將研發小型衛星和提高小型衛星性能作為未來的方向;另一方面,試圖通過模塊化、通用化的設計來壓低新一代運載火箭的研發成本。例如,在其大型H3 火箭研發工作中,要充分共享小型固體火箭埃普西隆(EPSILON)的現有技術,實現助推火箭發動機等部分子系統的共用[31]。同時,日方認為過去其運載火箭研發與發射需求存在脫節現象,要求未來借助軍民兩用技術并著眼國防安全,在運載火箭研發規劃中充分協調運載能力,重點填補大型運載火箭與小型運載火箭之間的能力空白,從而滿足未來的發射任務需要,如圖4 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日方非常重視小型固體火箭在未來航天發射中的作用,認為對其國防安全具有重要意義;要求在發展現有高適應性小型固體運載火箭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自主固體運載火箭技術,將發射準備時間縮短到數天以內[10]。其目的一是滿足高密度發射小型偵察衛星的需求,以便其在軌衛星遭到損毀時可以及時補充;二是看重該小型固體火箭具備快速改裝為高性能彈道導彈的潛力。

圖4 未來日本運載能力的建設目標
同時,日方還認識到新型發射場建設的重要意義,要求籌劃制定發射場建設戰略。一方面,重視商業化發射需求,要求在充分考慮前瞻性、可擴展性及安全性的前提下,建設面向亞洲的開放型航天運載中心,包括由企業主導的商業化發射場[23];另一方面,重視滿足國防目的的發射需求,強調以國家安全為導向建設發射場[22]。此外,日方還謀求新型發射場的高適應性,要求未來發射場能夠適應多類型航天器的發射,包括各類衛星、科研飛行器、無人機及飛船、空中發射系統、可重復使用火箭、太空旅游火箭及太空港等。
八、 結 論
將國家戰略、航天戰略融入法治是日本貫徹其航天政策的重要特征。目前,日本在航天領域的立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以《宇宙基本法》為先導的航天法系初步成形。日本通過立法為航天產業的發展提供依據和支撐,使得政府、企業及科研機構可以依托航天法律體系有序開展行動。盡管日本的“和平憲法”對軍事航天活動存在限制,但日本政府通過對相關條款的曲折解釋“狡猾”地繞開了障礙,使該國的航天活動實質上拓展到了包括國防安全在內的更為廣泛的領域。日本的航天政策強調航天活動對國防安全的重要意義,注重外空與海域的聯動機制,注重信息與情報的收集分析,強調航天裝備的體系化建設。不過,日本航天政策施行過程中的問題也很突出,主要是受到多黨制政體、政府機構的條塊分割,以及自身有限的國力等各種因素的掣肘,其各項政策在施行過程中會出現遲滯,資源投入方面也不時出現短缺。此外,日本航天政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緊跟美國,在政策方面強調與美協調,在研發領域強調與美國協同,在資源方面強調與美國共享。其有利之處在于,能夠獲得有利的發展環境,比較容易獲取各類資源,節約研發成本;不利之處在于,在行動上受到美國限制,在技術上形成對美國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