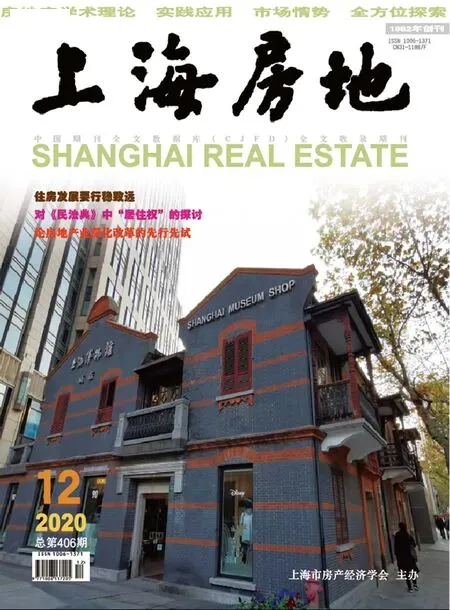房地產(chǎn)泡沫財富效應的實證研究
文/付艷秋 張煒
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為我國房地產(chǎn)行業(yè)的快速發(fā)展提供了機遇,房地產(chǎn)開發(fā)規(guī)模不斷增加,房地產(chǎn)價格也不斷上漲,以致產(chǎn)生房地產(chǎn)泡沫。房地產(chǎn)行業(yè)的發(fā)展也帶動了相關(guān)行業(yè)的發(fā)展,為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為推動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支柱產(chǎn)業(yè)。房地產(chǎn)價格的快速增長對購房者財富與消費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房產(chǎn)的增值引致購房者財富的增加,在樂觀預期的影響下,部分消費者加大消費支出,帶動消費水平的提高,帶來正向財富效應;另一方面,購房時背負的巨額抵押貸款,也給部分居民帶來了沉重的生活壓力,在“房奴效應”的作用下,消費者自動選擇降低當期消費水平,帶來負向財富效應。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但消費率卻較低,并有下降的趨勢。2005-2015年居民消費水平由5671元上升到18929元,最終消費率雖有波動,但均在50%左右,2016年有所上升,為55.1%,但遠遠低于發(fā)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居民消費率同樣較低,2005年居民消費率為38.5%,2015年為37.1%,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和擴大內(nèi)需的基調(diào)中,探討房地產(chǎn)泡沫對消費的影響尤為重要。
一、相關(guān)文獻研究評述
(一)國外文獻評述
1957年,最早的相關(guān)研究提到,未預期的資產(chǎn)價格上升,將影響家庭的財富水平。在發(fā)達國家普遍經(jīng)歷了一場股票大幅增長后,有學者發(fā)現(xiàn)資產(chǎn)的增漲有效地刺激了居民消費,這成為股票財富效應的經(jīng)驗證據(jù)。2007年,有學者研究英國住房價格對居民財富與消費意愿的影響時,發(fā)現(xiàn)二者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便將這種效應解釋為“財富效應”。2009年,有研究首次引入居民預期因素,發(fā)現(xiàn)房地產(chǎn)價格波動影響居民財富消費的主要傳導媒介為預期。2015年,有學者從流動性約束和預防性儲蓄角度來分析房價對財富效應的影響機制,發(fā)現(xiàn)財富效應具有地區(qū)差異性,傳導機制和影響結(jié)果也存在差異性。

(二)國內(nèi)文獻綜述
一些學者認為房地產(chǎn)價格的上漲帶來正向財富效應。周建軍和鞠方(2009)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房地產(chǎn)市場存在顯著的正向財富效應。陳偉和陳淮(2013),采用1998-2011年8月的月度數(shù)據(jù)對我國房地產(chǎn)市場的財富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發(fā)現(xiàn)從長期來看,我國房地產(chǎn)市場存在正的財富效應,房價上升1%,居民的消費支出增加0.966%。
一些學者認為房地產(chǎn)價格上漲存在負向的財富效應。陳彥斌和邱哲圣(2011)通過分析房地產(chǎn)價格上漲對居民儲蓄、福利與財富的影響,發(fā)現(xiàn)房價的上漲使得年輕家庭減少消費以提高儲蓄,整體福利水平不斷下降。況偉大(2011)從計量角度考察了房地產(chǎn)價格增漲對居民財富的影響,認為房價的增漲對居民財富產(chǎn)生擠出效應。顏色和朱國忠(2013)研究認為,房價上漲的財富效應會被房價上漲導致的“房奴效應”所抵消,而暫時性房價快速上漲的“房奴效應”在當前中國可能更加占有主導地位。傅東平(2017)與劉顏和周建軍(2019)認為,房價上漲具有財富效應和擠出效應雙重影響,但總效應表現(xiàn)為對消費的擠出,房價上漲抑制了消費。

(三)對現(xiàn)有文獻的評述和本文的創(chuàng)新
基于不同切入點、研究方法,國內(nèi)外對房地產(chǎn)財富效應的研究已經(jīng)獲得豐碩成果。以往研究缺乏對國內(nèi)外經(jīng)典進行梳理,理論基礎不足。本文研究對國外正向財富效應和負向財富效應經(jīng)典理論進行梳理,為實證分析提供了依據(jù)。以往文獻基于全國視角和區(qū)域視角進行研究,本文以地區(qū)視角進行研究。
二、房地產(chǎn)泡沫對行業(yè)收入差距影響的理論分析
房地產(chǎn)泡沫財富效應是指,當房地產(chǎn)泡沫不斷膨脹時,房地產(chǎn)價格不斷上漲,有房者家庭手中持有的房產(chǎn)價值上升,使得家庭財產(chǎn)性收入增加,對消費產(chǎn)生影響。按照房地產(chǎn)泡沫對消費的不同影響,可以將其劃分為正向財富效應和負向財富效應。房價上漲,導致居民消費水平提升,稱為正向財富效應;相反,房地產(chǎn)價格的上漲造成居民消費的減少,稱為負向財富效應,也稱為擠出效應。
(一)房地產(chǎn)泡沫正向財富效應理論
1.絕對收入理論。凱恩斯首次提出以收入為基礎的消費假說理論,認為居民收入的增長可以帶動消費的增加。其中收入包括絕對收入與相對收入,絕對收入往往指持久性的收入,相對收入指一次性收入或者短期收入。凱恩斯在后續(xù)研究中指出,收入增加可以帶動居民消費,從而帶動整體經(jīng)濟的發(fā)展。
2.行為金融學相關(guān)理論。行為金融學從人性與經(jīng)濟參與者心理和經(jīng)濟行為入手,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資產(chǎn)收入增長所帶來的財富效應。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學說有預期理論、過度自信與從眾心理。
預期理論認為,在樂觀預期下,消費者認為資產(chǎn)未來會帶來更大收益,從而增加當期消費,帶來資產(chǎn)財富效應。過度自信理論認為,消費者在投資的過程中往往會對自己的判斷與決策能力作出超過自身實際的估計。由于以往有快速增長資產(chǎn)的經(jīng)驗,消費者會將未來的資產(chǎn)收益與曾經(jīng)的資產(chǎn)收益相掛鉤,作出過度自信的行為決策,并在此行為決策下保持以往的消費結(jié)構(gòu)與消費水平,從而帶來財富效應。從眾心理,即購房“羊群效應”,指房地產(chǎn)價格被哄抬而上,進一步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注入資金,形成快速增長的棘輪效應,此時房地產(chǎn)投資者看到房價增長,認為自身財富快速累積,便增加當期消費,產(chǎn)生財富效應。
(二)房地產(chǎn)泡沫負向財富效應理論
1.持久收入理論。費里德曼提出持久收入理論,認為消費行為更大程度上受到長期持久性收入的影響,當期收入的一次性或短暫性增長不能帶動消費。只有長期收入的增長才能帶來消費的增加。依據(jù)持久收入理論思想,房地產(chǎn)價格的增加屬于短期收入的增長,不能作為持久收入,不具有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因此,無論房地產(chǎn)價格如何上漲,購房者都會主動減少當期或長期消費,使得房地產(chǎn)對消費產(chǎn)生擠出效應,從而產(chǎn)生房地產(chǎn)負向財富效應。
2.生命周期理論。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消費者的收入與消費支出是整個生命周期的行為。短期收入與長期收入對短期消費與長期消費都具有一定影響,長期影響所占比重較大。消費者是理性的,他們在長期范圍內(nèi)計劃自身的投資、儲蓄與消費,以實現(xiàn)整個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購房者在房地產(chǎn)增值后不會盲目地進行大量短期消費,而會將長期財富與長期收入綜合進行考量。大量的收入被用于每階段的按揭還款,壓縮購房者可支配收入的同時,也會減少其長期消費,最后帶來負向財富效應。
3.心理賬戶理論。投資者通常將自己的意愿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偏保守的避窮部分,另一方面是激進冒險的致富部分。在房地產(chǎn)投資的過程中,購房者往往不具備購房資金,購房準備不足,但是會在從眾心理的推動下作出不理性的超越自身承受范圍的投資決策。在購房之后的時間里,購房者開始進行心理會計,衡量房地產(chǎn)價格增值帶來的收益與沉重房貸帶來的損失。心理賬戶行為金融學理論認為,與收益帶來的快樂相比,同樣程度的損失給投資者帶來的痛苦更大。后期購房者還款數(shù)量遞增,給購房者帶來的壓力與痛苦也遞增。因此,在購房者整個生命周期中,由于還款壓力的邊際遞增,購房者會產(chǎn)生“房奴效應”,降低長期消費水平,力圖盡快減緩購房按揭貸款的壓力。
三、房地產(chǎn)泡沫財富效應實證分析
(一)數(shù)據(jù)來源及模型設置
被解釋變量:居民消費水平(con)。居民消費水平包括居民在物質(zhì)和勞務上的消費,全面地反映居民生存、發(fā)展、享受所及程度。計算公式為:居民消費水平(元/人)=報告期生產(chǎn)總值中的居民消費總額/報告期年平均人口。數(shù)據(jù)整理自國家統(tǒng)計局提供的數(shù)據(jù)。為減少數(shù)據(jù)異方差的影響,對該變量采用取對數(shù)形式。
解釋變量:房地產(chǎn)泡沫系數(shù)(pop)、居民收入水平(inc)和房地產(chǎn)泡沫預期(prep)。
對于房地產(chǎn)泡沫系數(shù)(pop),本文選取房價收入比作為衡量房地產(chǎn)泡沫的最終指標。采用的公式為:房價收入比=商品住宅平均單套價格/城鎮(zhèn)家庭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商品住宅平均銷售價格×商品住宅平均單套銷售面積)/(城鎮(zhèn)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zhèn)家庭戶均人口數(shù))。數(shù)據(jù)整理自《中國房地產(chǎn)統(tǒng)計年鑒2004-2015》、中國資訊行數(shù)據(jù)、中經(jīng)網(wǎng)、房天下、《中國區(qū)域統(tǒng)計年鑒2007-2015》和《中國經(jīng)濟景氣月報》提供的數(shù)據(jù)。
居民收入水平(inc),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居民相對收入為指標:居民相對收入=地區(qū)居民可支配收入/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對于居民可支配收入難以得到直接數(shù)據(jù)的地區(qū),參考高連水的計算方法:yt=puyu+pcyc。其中,yt為地區(qū)居民可支配收入,pu、pc分別代表城市人口占比、農(nóng)村人口占比,yu、yc分別代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農(nóng)村居民純收入。數(shù)據(jù)整理自中經(jīng)網(wǎng)數(shù)據(jù)庫提供的數(shù)據(jù)。為減少數(shù)據(jù)異方差的影響,對該變量采用取對數(shù)形式。

對于泡沫預期(prep),由于居民對房價的估計會影響到消費,選取上一期房地產(chǎn)泡沫值作為居民對房價的預期,故房地產(chǎn)泡沫預期對消費的影響也稱為房地產(chǎn)間接財富效應。數(shù)據(jù)來源同房地產(chǎn)泡沫系數(shù)。
各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結(jié)果如表1所示。

表1 樣本描述性統(tǒng)計
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構(gòu)建如下理論模型考察房地產(chǎn)泡沫的波動對消費的影響:lncon=β1+β2pop+β3 lninc+β4 prep+ε。其中,ε表示隨機誤差。
(二)實證分析
1.單位根檢驗。為了避免偽回歸問題,首先對樣本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相同根情況下的LLC檢驗與不同根情況下的Fisher-PP檢驗和Fisher-ADF檢驗作為判斷數(shù)據(jù)平穩(wěn)性的依據(jù)。檢驗結(jié)果如表2所示。lncon、pop、lninc、prep均不能同時拒絕原假設,原序列不平穩(wěn)。對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lncon、pop、lninc、prep四個變量對應p值均同時小于1%,通過顯著性檢驗。所以,變量為一階單整序列。

表2 各變量單位根檢驗結(jié)果
2.協(xié)整檢驗。本文根據(jù)7個面板數(shù)據(jù)協(xié)整關(guān)系Pedroni檢驗指標和Kao檢驗方法對變量的一階差分數(shù)據(jù)進行面板協(xié)整檢驗,檢驗結(jié)果如表3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Pedroni檢驗的7個統(tǒng)計量中有4個檢驗結(jié)果,Kao檢驗所得的ADF檢驗結(jié)果表明應拒絕原假設。由于本文只選取了2007-2016年30省的數(shù)據(jù),屬于小樣本數(shù)據(jù),因而Panel-ADF和Group-ADF統(tǒng)計量的檢驗結(jié)果更加有效,整體上可以拒絕不存在協(xié)整關(guān)系的原假設,上述四個變量之間存在著協(xié)整關(guān)系,即人均消費水平、房地產(chǎn)泡沫、人均收入和房地產(chǎn)泡沫預期之間存在長期而穩(wěn)定的均衡關(guān)系。

表3 協(xié)整檢驗
3.模型估計。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根據(jù)常數(shù)項和系數(shù)向量是否為常數(shù),分為二者為常數(shù)的混合回歸模型、系數(shù)項為常數(shù)的變截距模型和非常數(shù)的變系數(shù)模型。通常用F統(tǒng)計量來判斷面板數(shù)據(jù)究竟屬于哪種模型。分別對數(shù)據(jù)進行回歸分析,得到變系數(shù)模型的殘差平方和S1=0.63、變截距模型的殘差平方和S2=1.1518、混合模型回歸的殘差平方和S3=3.07。最終得到F1=2.9163,F(xiàn)2=10.082。因此,拒絕變截距和混合模型,接受變系數(shù)模型。其回歸分析結(jié)果如表4所示。

表4 變系數(shù)模型分析結(jié)果
從回歸分析結(jié)果可以發(fā)現(xiàn),全國各地區(qū)的房地產(chǎn)泡沫財富效應系數(shù)存在差異,但整體顯著性較低,天津、江蘇和山東存在顯著正向財富效應。收入對消費的影響系數(shù)全部顯著為正。北京、遼寧、福建、海南四地區(qū),預期對消費的影響顯著,其中遼寧、海南顯著為負。
四、結(jié)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jié)論
從上述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可知:(1)天津、江蘇和山東具有存在顯著正向財富效應;(2)北京、福建存在顯著正向間接財富效應,遼寧和海南存在顯著負向間接財富效應;(3)就我國而言,收入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
(二)政策建議
1.加大對房地產(chǎn)市場的調(diào)控力度,發(fā)揮正向財富效應。我國房地產(chǎn)市場快速發(fā)展,房地產(chǎn)泡沫不斷膨脹。我國房地產(chǎn)市場發(fā)展時間短,市場機制不健全,為此,應該加強對房地產(chǎn)市場的調(diào)控,促進財富效應的發(fā)揮。保障房地產(chǎn)市場健康運行,為消費營造良好環(huán)境。加強對房地產(chǎn)價格的監(jiān)測,防止房地產(chǎn)價格驟升或急降;加強對房地產(chǎn)市場的監(jiān)管,嚴厲打擊投機性需求;健全住房信貸體系,減少居民流動性約束。對信貸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滿足居民購買首套住房的剛性需求;對現(xiàn)有信貸進行整頓改革,提升其金融服務效率,合規(guī)及時地發(fā)放住房貸款;對住房公積金制度進行改革完善,提升其公平性和有效性,使職工更好地發(fā)揮其財富效應。

2.增加居民收入,豐富消費市場。居民收入水平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增加居民收入有利于擴大內(nèi)需,進而促進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和可持續(xù)發(fā)展。消費市場的擴大,增加了居民消費的可選擇范圍,也有利于促進居民消費。因此,在當今多數(shù)地區(qū)房地產(chǎn)市場財富效應不顯著的情況下,增加居民收入、擴充消費市場是必要的。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可提升其消費能力。應擴大就業(yè)市場,增加就業(yè)崗位,支持居民自主擇業(yè)、靈活就業(yè),減少失業(yè)人數(shù)。建立健全勞動力相關(guān)法規(guī),保障勞動力市場的規(guī)范,保障企業(yè)和勞動者的合法權(quán)益。發(fā)展夜市經(jīng)濟,豐富消費市場商品內(nèi)容與形式,向居民提供多種消費選擇;提供高等級產(chǎn)品,刺激高收入群體的潛在消費需求;延長地鐵公交運營時間、商圈營業(yè)時間等,為開展夜市經(jīng)濟提供便利。
3.完善基礎設施,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完善的基礎設施,是居民生活質(zhì)量得以提高的出發(fā)點。政府應加大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投入,切實提高地區(qū)公共服務水平。教育醫(yī)療保障是當今居民關(guān)注的焦點,政府應著重對其加以發(fā)展和完善。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整體教育水平。在不同區(qū)域內(nèi)設立優(yōu)秀小學的分校,將優(yōu)秀師資力量合理平均分配。重視周邊地區(qū)和非經(jīng)濟中心區(qū)域的教育,加大對基礎教育的資金投入,實現(xiàn)教育的均等化和分散化。加大財政支出、政府民生性財政支出,增加對醫(yī)療保障體系的投入,減輕房價上漲對消費的擠出,緩解預算約束效應和替代效應,弱化負向財富效應,減輕居民的收入負擔,提升消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