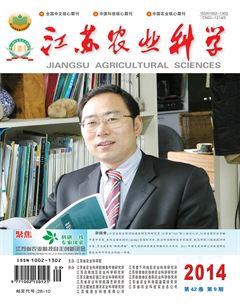響應面法優化胰蛋白酶酶解核桃蛋白的工藝
摘要:以液壓冷榨油后的核桃餅粕為原料,綜合單因素試驗分析,并利用響應面分析方法獲得胰蛋白酶酶解核桃蛋白的優化條件:酶解溫度37 ℃、底物質量濃度31 g/L、反應時間125 min、加酶量[E] ∶[S]=3.2 ∶100,各因素對核桃蛋白酶解的影響順序為酶解時間>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通過驗證試驗表明,利用優化的酶解條件,核桃蛋白利用指數可達47.25%,效果較好。
關鍵詞:胰蛋白酶;酶解條件;蛋白利用指數;工藝優化
中圖分類號: TS201.1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1002-1302(2014)09-0239-04
收稿日期:2013-10-11
基金項目:貴州省農業攻關(編號:黔科合NZ[2013]3016號)。
作者簡介:柳蔭(1987—),女,滿族,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食品生物技術研究。E-mail:liuyin0130@163.com。
通信作者:周鴻翔(1975—),男,副教授,主要從事油脂加工和食品生物技術研究工作。E-mail:zhou-hx@163.com。核桃別稱羌桃、胡桃,隸屬胡桃科胡桃屬。核桃蛋白含有人體所必需的8種氨基酸,且含量接近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規定的標準[1-2],是一種氨基酸齊全的植物蛋白資源。目前,國內外對核桃的研究偏重于對核桃油的提取與精煉,而對核桃蛋白質的開發利用研究很少。生物活性肽是指能夠調節生物機體生命活動或某些生理活性的一類肽的總稱[3-4]。某些低肽不僅能提供人體生長、發育所需的營養物質,而且還能調節人體機能[5-8]。經酶解后的蛋白質主要以低肽的形式存在并被吸收。采用現代酶解技術對核桃蛋白進行酶解,不僅可改變其物理化學性質和功能特性,還能產生營養豐富、供人體生長發育所需要的物質。因此,對核桃蛋白的開發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試驗在前期篩選出胰蛋白酶為酶解核桃蛋白最佳用酶的基礎上,利用胰蛋白酶酶解核桃餅粕,對其酶解條件進一步優化,為核桃功能多肽開發的利用提供理論依據。
1材料與方法
1.1材料
試驗原料為實驗室液壓冷榨油后的核桃餅粕;胰蛋白酶,由北京索來寶公司生產;K2SO4、CuSO4、H2SO4、HCl、NaOH、H3BO3及混合指示劑等均為國產分析純。
1.2儀器與設備
FW-100高速萬能粉碎機,天津市泰斯特儀器有限公司生產;集熱式恒溫加熱磁力攪拌器,鄭州長城科工貿有限公司生產;FA-1004型電子分析天平,上海良平儀器儀表有限公司生產;消化爐、凱氏定氮儀,上海洪紀儀器設備有限公司生產。
1.3試驗方法
1.3.1核桃粗蛋白的制備冷榨后的核桃餅粕加入沸程為60~90 ℃的石油醚,在50 ℃、料液比1 g ∶3 mL、浸提2次的條件下浸泡去除殘油;脫脂后,將蛋白粉置于通風櫥中風干72 h,粉碎,過100目篩,即得核桃粗蛋白。
1.3.2氮含量的測定參照GB 5009.5—2010《食品中蛋白質的測定》,采用凱式定氮法測定可溶性氮含量和核桃蛋白的總氮含量。
1.3.3核桃蛋白的蛋白利用指數計算蛋白利用指數=可溶性氮含量/核桃蛋白總氮含量×100%。
1.4酶解條件的確定
1.4.1底物質量濃度加酶量為[E] ∶[S]=3 ∶100、溫度為37 ℃,在底物質量濃度分別為10、30、50、70、90 g/L條件下水解1 h,以蛋白利用指數為指標,分析底物質量濃度對核桃蛋白酶解的影響。
1.4.2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為30 g/L、溫度為37 ℃,在加酶量[E] ∶[S]分別為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 的條件下水解1 h,以蛋白利用指數為指標,分析加酶量對核桃蛋白酶解的影響。
1.4.3酶解時間底物質量濃度為30 g/L、加酶量[E] ∶[S]=3 ∶100,在37 ℃分別水解30、60、90、120、150、180 min,以蛋白利用指數為指標,分析酶解時間對核桃蛋白酶解的影響。
1.4.4酶解條件的優化基于單因素試驗數據,根據Central composite試驗設計原理,選擇對蛋白利用指數有影響的3個因素即底物質量濃度、加酶量和酶解時間,進行3因素3水平的響應面分析試驗,酶解溫度固定在37 ℃,經過Design-Expert 優化胰蛋白酶酶解核桃蛋白的條件。響應面分析與水平編碼表見表1。
2結果與分析
2.1核桃餅粕和去除殘油后的核桃粗蛋白的基本成分
由表2可見,核桃粗蛋白與核桃餅粕相比,粗蛋白含量明顯上升,粗脂肪含量顯著降低;除粗纖維含量有所下降外,其他成分含量均有所增加,且差異不大。表2核桃餅粕和核桃粗蛋白基本成分
原料基本成分的含量(%)粗蛋白粗脂肪水分灰分還原糖淀粉粗纖維核桃餅粕47.8325.647.045.990.997.015.21核桃粗蛋白59.587.349.266.541.3711.93.83
2.2各因素對胰蛋白酶酶解核桃蛋白的影響
2.2.1底物質量濃度由圖1可知,底物質量濃度低于 30 g/L 時,蛋白利用指數隨著底物質量濃度的增大而升高,之后蛋白利用指數上升趨勢趨于平緩甚至有下降趨勢。這可能是因為低質量濃度時,溶液的流動性較好,酶與底物接觸比較充分;而在高質量濃度時,溶液的流動性較差,酶與底物接觸不夠充分,限制了酶解反應的進行。綜合考慮,選擇胰蛋白酶酶解核桃蛋白的最佳底物質量濃度為30 g/L。
2.2.2加酶量由圖2可知,隨著加酶量的增加,蛋白利用指數增加,在加酶量為[E] ∶[S]=3 ∶100達到最高,隨后基本穩定。這是因為加酶量過大時,蛋白質分子可能已被酶所飽和,過多的酶量并沒有提高蛋白利用指數,反而使其下降。選擇適宜的加酶量[E] ∶[S]=3 ∶100。endprint
2.2.3酶解時間由圖3可知,酶解反應開始后,蛋白利用指數隨酶解時間的延長而升高,胰蛋白酶酶解到達120 min后,反應趨于平緩,變化幅度很小。這可能是由于隨著反應的進行,酶的濃度逐漸降低,活性降低,酶的活性部位已被核桃蛋白分子所飽和,反應趨于平衡。適宜的酶解時間為120 min。
2.3響應面優化酶解工藝
2.3.1二次方程數學模型的建立及最佳化分析綜合單因素數據,基于Box-Behnken中心組合設計原理[9-10],以蛋白利用指數為評價指標,采用Design Expert 7.1 軟件設計響應面試驗方案(表3),建立數學回歸模型,以反映不同因素間的交互影響,最佳化分析酶解工藝參數。
2.3.2響應面結果分析為了檢驗回歸方程的有效性,進一
步確定各單因素對蛋白利用指數的影響程度,對回歸模型進行了方差分析(表4)。以蛋白利用指數為響應值的函數二次回歸方程為:R=-342.475 50+38.675 75A+73.878 00B+3.417 01C-2.780 00AB-0.0111 25AC+0.002 5BC-4.558 25A2-10.323 00B2-0.0136 46C2。由表4可見,一次項中A、B、C偏回歸系數均極顯著,說明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酶解時間對蛋白利用指數均具有顯著性影響;交互項中AB達顯著水平,二次項中A2、B2、C2偏回歸系數達極顯著水平;失擬項P>0.05,差異不顯著,說明殘差均由隨機誤差引起。該模型R2=0.977 6,說明響應值的變化有97.76%來源于底物質量濃度、加酶量、酶解時間,影響蛋白利用指數的因素作用大小為酶解時間>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
由圖4可見,核桃蛋白利用率曲線出現先升高到平緩再略下降的狀態;提高底物質量濃度與加酶量均能提高核桃蛋白利用指數,當底物質量濃度和加酶量分別增大到一定程度時,蛋白利用率趨于飽和,響應曲面變平緩;隨后,若再增大底物質量濃度和加酶量,提取率會略有下降。因此,最佳取值點應取蛋白利用率不再顯著增高的坐標點處。
由圖5可見,底物質量濃度在[2,3.1]范圍內、時間在[100,120]范圍內時,兩者的增效作用明顯,蛋白利用指數隨著底物質量濃度和時間的增加而升高,超過這個范圍之后趨于平緩,再增加蛋白利用指數下降。
2.4驗證試驗
為證實模型預測值與實測值之間的擬合程度,在優化的理論值下進行驗證試驗。由表5可見,試驗得到的蛋白利用指數為47.25%,與預測值接近,預測值與試驗值之間具有良好的擬合性,表明該模型具有有效性。這說明回歸方程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各因素對蛋白利用指數的影響。
3小結
本試驗研究了底物質量濃度、加酶量、酶解時間對蛋白利用的影響,各因素對胰蛋白酶酶解核桃蛋白的影響順序為酶解時間>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
響應面優化設計法是一種常用的優化試驗條件的數學統計方法[11-14]。經檢驗,證明該模型切實可行,能較好地預測蛋白利用指數。確定核桃蛋白的蛋白利用指數最佳酶解條件為反應時間125 min、底物質量濃度31 g/L、加酶量[E] ∶[S]=3.2 ∶100、酶解溫度37 ℃,蛋白利用指數可達47.25%。
參考文獻:
[1]張慶祝,丁曉雯,陳宗道,等. 核桃蛋白質研究進展[J]. 糧食與脂,2003,16(5):21-23.
[2]寇文國,高紅慶. 核桃產品的開發利用[J]. 中國油脂,2000,25(6):112-113.
[3]裴凌鵬,吳穎. 多肽研究進展[J].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25(3):56-60.
[4]吳建中,趙謀明,寧正祥. 食品中的生物活性多肽[J]. 食品與發酵工業,2002,28(11):46-50.
[5]Clareand D A,Swaisgood H E. Bioaclive milk peptides,aprospectus[J]. J Dairy Sci,2000,28(11):1187-1195.
[6]勵建榮,封平. 功能肽的研究進展[J]. 食品科學,2004,25(11):415-419.
[7]Yasuyaki T,Yoshikawa M. Introduction of enterostatin(VPDPR)and a related sequence into soybean proglycinin AlaBlb suhunit by site directed mutagenesis[J]. Biotechnol Bioehem,2000,64(12):2731-2733.
[8]蘇秀蘭. 生物活性肽的研究進展[J]. 內蒙古醫學院學報,2006,28(5):471-474.
[9]Boxgep,Hunter W G. Statistics for experiments: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data analysis and model building[M].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1978.
[10]王世磊. Design-Expert軟件在響應面優化法中的應用[D]. 鄭州:鄭州大學,2009.
[11]唐明霞,陳惠,袁春新,等. 通豆6號大豆響應面法微波燙漂工藝的優化[J]. 江蘇農業學報,2013,29(4):870-875.
[12]朱興一,陳秀,謝捷,等. 基于響應面法的閃式提取香菇多糖工藝優化[J]. 江蘇農業科學,2012,40(5):243-245.
[13]袁志發,周靜芋. 試驗設計與分析[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60-370.
[14]謝捷,于波,朱興一,等. 響應面法優化深層培養中國被毛孢蟲草多糖閃式提取工藝[J]. 江蘇農業科學,2013,41(8):284-286.周方方,吳正鈞,陳臣,等. 腸膜明串珠菌Leuco4發酵稀奶油的條件優化[J]. 江蘇農業科學,2014,42(9):243-245.endprint
2.2.3酶解時間由圖3可知,酶解反應開始后,蛋白利用指數隨酶解時間的延長而升高,胰蛋白酶酶解到達120 min后,反應趨于平緩,變化幅度很小。這可能是由于隨著反應的進行,酶的濃度逐漸降低,活性降低,酶的活性部位已被核桃蛋白分子所飽和,反應趨于平衡。適宜的酶解時間為120 min。
2.3響應面優化酶解工藝
2.3.1二次方程數學模型的建立及最佳化分析綜合單因素數據,基于Box-Behnken中心組合設計原理[9-10],以蛋白利用指數為評價指標,采用Design Expert 7.1 軟件設計響應面試驗方案(表3),建立數學回歸模型,以反映不同因素間的交互影響,最佳化分析酶解工藝參數。
2.3.2響應面結果分析為了檢驗回歸方程的有效性,進一
步確定各單因素對蛋白利用指數的影響程度,對回歸模型進行了方差分析(表4)。以蛋白利用指數為響應值的函數二次回歸方程為:R=-342.475 50+38.675 75A+73.878 00B+3.417 01C-2.780 00AB-0.0111 25AC+0.002 5BC-4.558 25A2-10.323 00B2-0.0136 46C2。由表4可見,一次項中A、B、C偏回歸系數均極顯著,說明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酶解時間對蛋白利用指數均具有顯著性影響;交互項中AB達顯著水平,二次項中A2、B2、C2偏回歸系數達極顯著水平;失擬項P>0.05,差異不顯著,說明殘差均由隨機誤差引起。該模型R2=0.977 6,說明響應值的變化有97.76%來源于底物質量濃度、加酶量、酶解時間,影響蛋白利用指數的因素作用大小為酶解時間>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
由圖4可見,核桃蛋白利用率曲線出現先升高到平緩再略下降的狀態;提高底物質量濃度與加酶量均能提高核桃蛋白利用指數,當底物質量濃度和加酶量分別增大到一定程度時,蛋白利用率趨于飽和,響應曲面變平緩;隨后,若再增大底物質量濃度和加酶量,提取率會略有下降。因此,最佳取值點應取蛋白利用率不再顯著增高的坐標點處。
由圖5可見,底物質量濃度在[2,3.1]范圍內、時間在[100,120]范圍內時,兩者的增效作用明顯,蛋白利用指數隨著底物質量濃度和時間的增加而升高,超過這個范圍之后趨于平緩,再增加蛋白利用指數下降。
2.4驗證試驗
為證實模型預測值與實測值之間的擬合程度,在優化的理論值下進行驗證試驗。由表5可見,試驗得到的蛋白利用指數為47.25%,與預測值接近,預測值與試驗值之間具有良好的擬合性,表明該模型具有有效性。這說明回歸方程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各因素對蛋白利用指數的影響。
3小結
本試驗研究了底物質量濃度、加酶量、酶解時間對蛋白利用的影響,各因素對胰蛋白酶酶解核桃蛋白的影響順序為酶解時間>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
響應面優化設計法是一種常用的優化試驗條件的數學統計方法[11-14]。經檢驗,證明該模型切實可行,能較好地預測蛋白利用指數。確定核桃蛋白的蛋白利用指數最佳酶解條件為反應時間125 min、底物質量濃度31 g/L、加酶量[E] ∶[S]=3.2 ∶100、酶解溫度37 ℃,蛋白利用指數可達47.25%。
參考文獻:
[1]張慶祝,丁曉雯,陳宗道,等. 核桃蛋白質研究進展[J]. 糧食與脂,2003,16(5):21-23.
[2]寇文國,高紅慶. 核桃產品的開發利用[J]. 中國油脂,2000,25(6):112-113.
[3]裴凌鵬,吳穎. 多肽研究進展[J].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25(3):56-60.
[4]吳建中,趙謀明,寧正祥. 食品中的生物活性多肽[J]. 食品與發酵工業,2002,28(11):46-50.
[5]Clareand D A,Swaisgood H E. Bioaclive milk peptides,aprospectus[J]. J Dairy Sci,2000,28(11):1187-1195.
[6]勵建榮,封平. 功能肽的研究進展[J]. 食品科學,2004,25(11):415-419.
[7]Yasuyaki T,Yoshikawa M. Introduction of enterostatin(VPDPR)and a related sequence into soybean proglycinin AlaBlb suhunit by site directed mutagenesis[J]. Biotechnol Bioehem,2000,64(12):2731-2733.
[8]蘇秀蘭. 生物活性肽的研究進展[J]. 內蒙古醫學院學報,2006,28(5):471-474.
[9]Boxgep,Hunter W G. Statistics for experiments: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data analysis and model building[M].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1978.
[10]王世磊. Design-Expert軟件在響應面優化法中的應用[D]. 鄭州:鄭州大學,2009.
[11]唐明霞,陳惠,袁春新,等. 通豆6號大豆響應面法微波燙漂工藝的優化[J]. 江蘇農業學報,2013,29(4):870-875.
[12]朱興一,陳秀,謝捷,等. 基于響應面法的閃式提取香菇多糖工藝優化[J]. 江蘇農業科學,2012,40(5):243-245.
[13]袁志發,周靜芋. 試驗設計與分析[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60-370.
[14]謝捷,于波,朱興一,等. 響應面法優化深層培養中國被毛孢蟲草多糖閃式提取工藝[J]. 江蘇農業科學,2013,41(8):284-286.周方方,吳正鈞,陳臣,等. 腸膜明串珠菌Leuco4發酵稀奶油的條件優化[J]. 江蘇農業科學,2014,42(9):243-245.endprint
2.2.3酶解時間由圖3可知,酶解反應開始后,蛋白利用指數隨酶解時間的延長而升高,胰蛋白酶酶解到達120 min后,反應趨于平緩,變化幅度很小。這可能是由于隨著反應的進行,酶的濃度逐漸降低,活性降低,酶的活性部位已被核桃蛋白分子所飽和,反應趨于平衡。適宜的酶解時間為120 min。
2.3響應面優化酶解工藝
2.3.1二次方程數學模型的建立及最佳化分析綜合單因素數據,基于Box-Behnken中心組合設計原理[9-10],以蛋白利用指數為評價指標,采用Design Expert 7.1 軟件設計響應面試驗方案(表3),建立數學回歸模型,以反映不同因素間的交互影響,最佳化分析酶解工藝參數。
2.3.2響應面結果分析為了檢驗回歸方程的有效性,進一
步確定各單因素對蛋白利用指數的影響程度,對回歸模型進行了方差分析(表4)。以蛋白利用指數為響應值的函數二次回歸方程為:R=-342.475 50+38.675 75A+73.878 00B+3.417 01C-2.780 00AB-0.0111 25AC+0.002 5BC-4.558 25A2-10.323 00B2-0.0136 46C2。由表4可見,一次項中A、B、C偏回歸系數均極顯著,說明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酶解時間對蛋白利用指數均具有顯著性影響;交互項中AB達顯著水平,二次項中A2、B2、C2偏回歸系數達極顯著水平;失擬項P>0.05,差異不顯著,說明殘差均由隨機誤差引起。該模型R2=0.977 6,說明響應值的變化有97.76%來源于底物質量濃度、加酶量、酶解時間,影響蛋白利用指數的因素作用大小為酶解時間>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
由圖4可見,核桃蛋白利用率曲線出現先升高到平緩再略下降的狀態;提高底物質量濃度與加酶量均能提高核桃蛋白利用指數,當底物質量濃度和加酶量分別增大到一定程度時,蛋白利用率趨于飽和,響應曲面變平緩;隨后,若再增大底物質量濃度和加酶量,提取率會略有下降。因此,最佳取值點應取蛋白利用率不再顯著增高的坐標點處。
由圖5可見,底物質量濃度在[2,3.1]范圍內、時間在[100,120]范圍內時,兩者的增效作用明顯,蛋白利用指數隨著底物質量濃度和時間的增加而升高,超過這個范圍之后趨于平緩,再增加蛋白利用指數下降。
2.4驗證試驗
為證實模型預測值與實測值之間的擬合程度,在優化的理論值下進行驗證試驗。由表5可見,試驗得到的蛋白利用指數為47.25%,與預測值接近,預測值與試驗值之間具有良好的擬合性,表明該模型具有有效性。這說明回歸方程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各因素對蛋白利用指數的影響。
3小結
本試驗研究了底物質量濃度、加酶量、酶解時間對蛋白利用的影響,各因素對胰蛋白酶酶解核桃蛋白的影響順序為酶解時間>加酶量>底物質量濃度。
響應面優化設計法是一種常用的優化試驗條件的數學統計方法[11-14]。經檢驗,證明該模型切實可行,能較好地預測蛋白利用指數。確定核桃蛋白的蛋白利用指數最佳酶解條件為反應時間125 min、底物質量濃度31 g/L、加酶量[E] ∶[S]=3.2 ∶100、酶解溫度37 ℃,蛋白利用指數可達47.25%。
參考文獻:
[1]張慶祝,丁曉雯,陳宗道,等. 核桃蛋白質研究進展[J]. 糧食與脂,2003,16(5):21-23.
[2]寇文國,高紅慶. 核桃產品的開發利用[J]. 中國油脂,2000,25(6):112-113.
[3]裴凌鵬,吳穎. 多肽研究進展[J].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25(3):56-60.
[4]吳建中,趙謀明,寧正祥. 食品中的生物活性多肽[J]. 食品與發酵工業,2002,28(11):46-50.
[5]Clareand D A,Swaisgood H E. Bioaclive milk peptides,aprospectus[J]. J Dairy Sci,2000,28(11):1187-1195.
[6]勵建榮,封平. 功能肽的研究進展[J]. 食品科學,2004,25(11):415-419.
[7]Yasuyaki T,Yoshikawa M. Introduction of enterostatin(VPDPR)and a related sequence into soybean proglycinin AlaBlb suhunit by site directed mutagenesis[J]. Biotechnol Bioehem,2000,64(12):2731-2733.
[8]蘇秀蘭. 生物活性肽的研究進展[J]. 內蒙古醫學院學報,2006,28(5):471-474.
[9]Boxgep,Hunter W G. Statistics for experiments: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data analysis and model building[M].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1978.
[10]王世磊. Design-Expert軟件在響應面優化法中的應用[D]. 鄭州:鄭州大學,2009.
[11]唐明霞,陳惠,袁春新,等. 通豆6號大豆響應面法微波燙漂工藝的優化[J]. 江蘇農業學報,2013,29(4):870-875.
[12]朱興一,陳秀,謝捷,等. 基于響應面法的閃式提取香菇多糖工藝優化[J]. 江蘇農業科學,2012,40(5):243-245.
[13]袁志發,周靜芋. 試驗設計與分析[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60-370.
[14]謝捷,于波,朱興一,等. 響應面法優化深層培養中國被毛孢蟲草多糖閃式提取工藝[J]. 江蘇農業科學,2013,41(8):284-286.周方方,吳正鈞,陳臣,等. 腸膜明串珠菌Leuco4發酵稀奶油的條件優化[J]. 江蘇農業科學,2014,42(9):243-24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