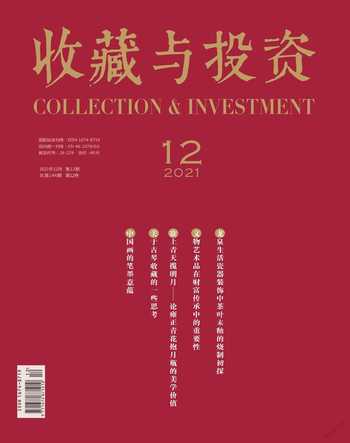博物館策展實踐中數字三維技術的應用
摘要:數字三維技術為策展工作帶來了諸多新的變革,依靠三維數字技術,策展人不僅可以在線上進行直觀的展覽設計,還可以在具體的展覽實踐中引入豐富的數字媒體手段來闡釋展覽主題。更重要的是,藏品資料的數字化使藏品資源的公共化成為可能,全球范圍內的策展人,甚至普通的公眾,都可以利用豐富的文物數字資源建設自己的線上虛擬展館,這在以往的策展工作中是不可想象的。
關鍵詞:數字三維技術;博物館策展;數字博物館
數字技術是指借助一定的設備將聲像圖文等各種信息轉化為二進制數字“0”和“1”后,進行運算、加工、存儲、傳送、傳播、還原的技術[1]。三維數字技術即是利用相關軟件,將所采集的數字資料以三維的方式呈現。目前,三維數字技術在文化遺產的記錄、保護以及重建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同時,隨著“數字博物館”與“智慧博物館”的提出,三維數字技術在博物館中的應用也日益普遍,這一技術的成熟也為現實的策展工作帶來了更多新的變革。
一、展覽的線上規劃
在傳統的策展工作中,展覽的規劃始于展覽主題設計書和展覽結構書的編寫。編寫結束后,文本需要轉化為圖紙。展品、說明文字和輔助展品的位置、相互之間的關系要詳細地標示在主題及展品的平面設計圖中。壁面與展柜、展柜與展品之間的關系則要通過展品的壁面設計圖來標示。圖紙是指導展覽策劃工作開展的根本材料[2]。傳統的策展方式煩瑣復雜,修改不便。更重要的是,平面圖并不直觀,缺乏實踐經驗的策展人很可能無法通過平面圖及時察覺展覽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策展是一個多方合作的過程,在館方、設計方及施工方溝通的過程中,因為平面信息的非直觀性,難免產生溝通不暢和信息誤傳等問題。
為了防止上述情況發生,在一些展覽的設計過程中,會按一定的比例縮小制作展覽的實物模型,然而,這種做法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高昂的金錢與時間成本,這是目前大部分展覽設計者所難以負擔的。
三維數字技術恰好可以用經濟的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新加坡研發的Cybermuseum平臺(圖一),一方面建立了整合全球各大博物館資源的3D互動虛擬博物館平臺,另一方面作為線上策展工具,策展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在線上進行展覽和展品的相關規劃,對展品進行自由組合、布局,改變空間形態、氛圍,并對不同的策展方案進行比較和取舍,以尋求最佳的策展效果,從而為現實中策展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據,降低失誤的成本[3]。在國內,中央美術學院將虛擬策展實驗教學系統(圖二)引入教學和策展工作中,線上策展人可以自由地選擇場地、展具和藝術品,進行燈光的調節和展線的規劃,這一系統不僅可以對實際展覽項目進行設計和評估調整,還可以作為培養學生策展實踐能力的教學工具,為展覽策劃相關專業的青年學生提供“練手”的機會。
二、豐富策展形式
三維數字技術的引入使得博物館實物展覽的形式更加多樣,策展人可以采用多重數字手段來豐富展覽內容。
傳統的博物館展品是固定的,展示的僅是展品的某個特定角度。借助三維數字技術,觀眾便可以在觸摸屏上與文物模型進行互動,實現移動、翻轉、縮放等功能,觀看展品的各個細節,甚至可以將展品進行虛擬拆解、組合,更加深入地了解展品的內部構造。
VR技術,即虛擬現實技術,它可以利用計算機生成模擬環境,將VR技術與三維建模技術相結合,將真實或虛擬的場景引入有限的展覽空間之內,使展覽空間大大擴展。首都博物館曾經利用三維虛擬現實技術將婦好墓1∶1復原,觀眾戴上相應的設備,便能獲得沉浸式的體驗。故宮博物院在上海陸家嘴中心舉辦的“發現·養心殿—數字故宮體驗展”是一場沒有實物的展覽,其中所有展示的文物都是基于數字資料的三維復原。以往的觀點認為,博物館展覽必須依賴實物展品,然而這場沒有實物的展覽卻打破了這種刻板印象,為展覽策劃帶來了新的思路。
數字建模技術與3D打印技術的結合也為博物館展覽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首先,針對可移動展品的3D打印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文物保護與利用之間的矛盾,還可以讓觀眾近距離觀察、觸摸高仿真的復制品,獲得強烈的參與感。隨著技術的發展,不可移動文物的打印也成為可能,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數字文物保護團隊將整個云岡石窟第12窟進行了1∶1的3D打印,實現了對于大體量不可移動文物的復制,復制的“第12窟”如今已在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正式展出,不可移動文物通過這樣的方式,成了博物館展覽的新對象。
博物館不僅是保存物質文化遺產的場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保存和延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責任,非遺的物質載體是容易留存的,而其工藝、過程、技術則難以記錄。但是通過動作捕捉技術,可以抓取技藝傳承人的三維動態數據,全面、細致地記錄民間工藝、技術、表演的整個流程,并在展覽中直觀地傳達給觀眾。這也給博物館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了有效的路徑。
三、虛擬策展與公眾策展

隨著三維數字技術在博物館領域的拓展,數字博物館的概念進入大眾的視野。數字博物館是指把各類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娛樂、展示、教育等功能以數字化方式進行陳列的博物館[4]。《數字博物館研究》一書按照數字博物館與實體博物館的關系將數字博物館分成了兩類,一類是現有的實體博物館的數字化,是實體博物館在功能與時空上的延伸;另一類則完全構建在數字虛擬空間中,不以實體博物館為依托[5]。第一種類型的數字博物館是大眾相對較為熟悉的,自從2000年盧浮宮官網提供了3D虛擬參觀項目之后,線上虛擬博物館的建設便在全球各大博物館內如火如荼地展開。谷歌開發的“Arts & Culture”應用進一步打破了不同博物館之間的界限,利用類似谷歌街景的方式,帶用戶參觀世界各個博物館,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愛好者足不出戶,便可以通過便攜設備在網絡上近距離地觀賞全球各個博物館的經典館藏。
無實體依托的虛擬博物館則算得上是一種新生事物。目前富有代表性的實例集中在國外。2008年,歐洲虛擬博物館“A European”開始免費向用戶開放。其中的“藏品”來自歐洲各個文化中心,而現實中并不存在這樣的博物館。加拿大虛擬博物館整合了全國2 500多個博物館的資源,全國的博物館獲批準后,均可制作、上傳虛擬展覽,這些展覽既可以基于實體展品,也可以是純數字藝術創作。目前,國內也開始了非實物虛擬博物館建設的相關探索,如臺灣中山大學余光中數位文學館[6]、張之洞數字博物館[7]等。但是這類所謂的“線上展館”往往只是文字與圖像資料的整合,并不存在虛擬的博物館空間形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博物館的空間敘事能力。

現在,具備虛擬空間的線上虛擬博物館正在出現,谷歌“Arts&Culture”項目曾利用三維數字技術和AR技術打造了一座維米爾虛擬博物館(圖三),對分散在荷蘭、倫敦、巴黎、紐約、悉尼等地的維米爾作品進行數據采集,再集中在同一個虛擬展館之內呈現,打破了空間的限制,實現了館際,甚至是國際之間的藏品資源共享。
策展一向被認為是職業策展人和相關領域研究者的專職,然而在虛擬博物館內,策展人的“壟斷”地位也開始動搖。克拉克藝術中心是美國最重要的藝術類博物館之一,它推出了一款名為“邀您策展”的應用軟件[8],公眾可以發揮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在線上創造自己的3D虛擬展廳,可利用的素材涵蓋了克拉克中心的大部分館藏。策展變成了一種全民都可以參與其中的創作活動,使線上的“公共策展”成為可能。
四、結語
三維數字技術的發展使策展人可選取的素材不再局限于一館一地,全世界各地的藏品都可以被利用起來,被組織成虛擬博物館,以闡釋展覽主題,表達特定思想。在新技術的參與下,展覽的內容和形式將會得到極大的豐富,公眾也將參與到虛擬策展的工作中來,勢必會為未來的博物館帶來新的生機。
作者簡介
侯雅涵,1997年4月生,女,漢族,山西陽泉人,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研究生。
參考文獻
[1]張麗.數字化時代中國博物館教育發展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5.
[2]嚴建強.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鄭奕.博物館教育活動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173.
[4]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信息中心.數字博物館研究與實踐2009[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147.
[5]鄭霞.博物館學認知與傳播文叢:數字博物館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6]蔡勁松.大學博物館的當代轉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276.
[7]許穎.數字展陳、知識共享:張之洞數字博物館的新探索[J].文化發展論叢,2019(1):267-273.
[8]王婷.博物館教育項目的策劃與實施[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