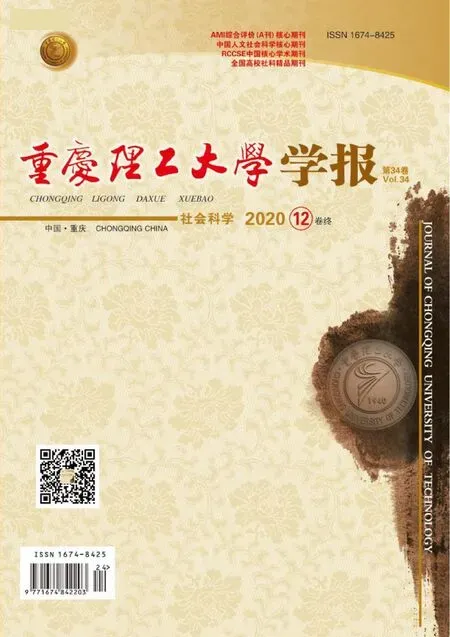笛卡爾《論靈魂的激情》中的論證結構分析與圖解
李憲博
(華東師范大學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一、引言
《論靈魂的激情》是笛卡爾作為哲學家的晚期著作之一。就笛卡爾本人的作品而言,《論靈魂的激情》也是轉折的關鍵節點。在此之前,笛卡爾一直主張“身心的自然聯結原則”,即心靈與身體自然地相聯結,并同時論述身心區分與身心互動,而本書則轉向“身心的習慣聯結原則”,即心靈與身體可以通過習慣相聯結,著重論述身心的統一與互動。這種轉變導向對激情的管控,對相關問題的思考使得笛卡爾從形而上學原則轉向道德哲學[1]。從這一角度看,《論靈魂的激情》奠定了現代主體的條件,即人一方面可以認識自己,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自己。盡管后期對這一觀點仍有相應的哲學探討、哲學爭辯,如休謨作為一個懷疑論者對其予以質疑,但是這并沒有完全脫離笛卡爾所鋪墊的路線。
對于這樣一本具有重要轉折作用的著作,學者的探討主要從激情、哲學概念闡釋、與現代科學(如醫學、心理學)的關系3個方面展開。第一個方面,就激情本身而言,李琍探討了心靈是否有可能主動掌控激情、笛卡爾賦予了激情怎樣的作用等問題,將笛卡爾的思想闡釋為心靈對激情的掌控并非直接、主動,激情的作用是保護身體[2]。施璇從《論靈魂的激情》文本出發,對笛卡爾關于激情功能的觀點給出了不同于標準解讀的解釋,即激情的功能并非是知識性的,感覺的功能才是知識性的[3]。關于激情與活動的關系,劉璐和施璇均有論述。劉璐從文本中發現行動和激情是同一個東西,處于一個相互關聯中的行動和激情必須同時存在,并將二者視為“同一個完整的因果過程”[4]。施璇則認為笛卡爾是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來談論激情與活動的,即將激情與活動當作“靈魂的激情”與“靈魂的活動”來談論思想或心靈的樣態,將激情與活動當作“靈魂的激情”與“身體的活動”來談論激情發生過程中的身心統一[5]。她還談到了激情的分類問題,認為對激情分類法的選擇往往意味著對某套整體性激情理論的選擇,笛卡爾對于激情的分類有自然的、人為的兩套運作方式[6]。第二個方面,一些學者基于《論靈魂的激情》闡釋了相關的哲學概念。賈江鴻從笛卡爾對激情的定義,即“相連于靈魂自身的直覺”(第25條)出發,探討了“我思”的兩種內涵,即阿然奎認為的純粹知性、絕對確定的知覺判斷和米歇爾·亨利認為的“意識對自身的直接把握”[7]。同時,他還對笛卡爾“靈魂”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梳理,認為笛卡爾的靈魂是一種思維的自我,這一概念給予人們從“思維屬性”的角度闡釋靈魂的空間[8]。第三個方面,一些學者根據《論靈魂的激情》這本書討論了與現代科學相關的議題。如李琍認為笛卡爾的激情理論是現代心理學的源頭[2],Joy Albuquerque等學者認為《論靈魂的激情》說明了病理心理學的多重誘因本質,揭示了性情(temperament)與生活經驗的復雜交互[9],Francisco López-Munoz等人認為笛卡爾的理論對整個17世紀、18世紀的精神病理學的研究方式產生了很大影響,為19世紀情緒癥狀學在情緒障礙診斷標準中的運用奠定了基礎[10],等等。從上述研究現狀中可以發現,目前,學者主要將關注點放到文本內容及其引發的問題方面,并未跳出從內容反思文本本身所蘊含的語言特征、邏輯特征等,即仍然集中于基于作品的“語言”工作而忽略了反思文本標記的“元語言”工作,而這些文獻卻或隱性或顯性地反映了“元語言”工作的必要性。李婧宇強調了邏輯分析的重要性,認為對于笛卡爾思想的解讀需要足夠的耐心和清楚的邏輯思路,否則很容易就會產生理解上前后不一致和邏輯混亂之處[11]。李琍通過邏輯學中的定義理論發現“激情”的定義也服從屬加種差的模式[2]。本文從非形式邏輯的角度出發,著重分析文本的論證結構,對笛卡爾的論證過程予以展示,以期幫助學者分析該著作的推理過程。不過,這里只涉及論證結構的分析與圖解,并不對其好壞做出評估,學者可以從前提的可靠性、前提與結論的相關性等方面進行相應評價。
二、論證結構的分析與圖解
在具體分析《論靈魂的激情》中的論證結構之前,首先簡要介紹論證結構分析的相關理論基礎。論證結構分析主要關心組成論證的陳述如何組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宣稱支持某個或某些主張[12],只有將復雜論證拆解成簡單論證之后才能判定其結構特征[13],從而達到有說服力的評估這一目的。為了清晰展示論證類型、可視化前提與結論間的復雜支撐關系,學者經常對論證結構進行圖解。一般認為,比爾茲利(Beardsley)[14]首先提出了論證的圖解方法,區分了基本、線性、收斂、發散的論證結構[15]。之后,托馬斯(S.N.Thomas)[16]在此基礎上引入組合論證,以示多條前提聯合支撐結論的論證結構。斯克里文(Michael Scriven)[17]和戈維爾(Trudy Govier)[18]不僅考慮了正面立論,還引入了否定支持(negative support),即論證者不情愿地承認對其結論的反對的圖解方式。斯克里文的完善還體現在省略論證的圖解方法上,用字母表示那些未陳述出來的假定(unstated assumption)。上述圖解方法稱為標準方案(Standard Approach),后來圖爾敏(Stephen E.Toulmin)提出了一套不同的圖解方法,以主張(claim)、資料(data)、擔保(warrant)、支援(backing)、模態限定詞(qualifier)、反駁(rebuttal)為論證要素進行結構分析,稱為圖爾敏模型(the Toulmin Model)[19]。弗里曼認為標準方案旨在分析論證文本,是作為結果的論證(arguments as products);而圖爾敏模型是對話交流中的論證,即作為程序的論證(arguments as process/procedure)。弗里曼將二者予以整合,提出了整合的宏觀結構論證方案[12]。因為本文研究的對象是早已在17世紀便已成型的哲學著作,更應從作為結果的論證角度予以考察,故將標準方案選為分析工具。
近年對于論證的分析與圖解有進一步研究。2004年,武宏志對論證圖解的產生與發展、論證圖解的類型、標準化論證的策略以及論證圖解和計算機技術的結合做出了綜述性介紹[15];2012年,徐劼較為全面地分析了比爾茲利圖、圖爾敏模型、威格摩爾圖的圖解方法,亦介紹了當代基于互聯網的論證圖解技術[20]。2016年,晉榮東分析了權衡論證的結構,明確了反面理由在論證中的地位以及正面理由、反面理由與結論的聯系方式,改善了戈維爾對權衡論證的圖解方法[21]。同年,金立和汪曼就如何區分組合結構和收斂結構展開進一步討論,細化了組合與收斂論證的方式,從“前提是否可以單獨推出結論”“貢獻均衡度”以及“當一個前提為假,其他前提是否能推出結論”這3個維度共同出發提出了新的判別方案[22]。王建芳介紹了弗里曼論證模型的基本架構、優勢與劣勢[23],并將其與圖爾敏模型比較,著重分析了二者的差異[24]。2018年,徐劼進一步分析了基于論題的信息系統的圖解方法和弗里曼圖解方式[25],他在2019年還介紹了信息化背景下論證圖解的新近網站和軟件[26]。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文獻中涉及的比爾茲利圖及托馬斯、戈維爾、弗里曼提出的改進模型分析笛卡爾的《論靈魂的激情》中條目為命題的論證結構,這里條目應為可以判斷真假的陳述句。為了使論證結構較為清晰簡潔,本文不考慮跨條目的論證,只考慮條目為結論、條目內文本為支撐條目的論據的內容。整個論證分析過程采用標準化論證過程,首先刪除與論證不相干、重復的冗余信息,然后將可能省略的前提補充出來,接著替換一些較為含糊或間接的陳述,最后排列組合有直接連接關系的陳述[20]。圖解過程主要分為以下3步:第一,通讀論證文本,理解所述內容;第二,劃分論證文本、標記論證要素;第三,圖解支持關系,展示論證結構。文本標記過程采用弗里曼在ArgumentStructure:RepresentationandTheory中使用的標注方法[12]。
三、笛卡爾《論靈魂的激情》中的線性結構、收斂結構與組合結構
《論靈魂的激情》中包括含基本論證結構(線性結構、發散結構、收斂結構、組合結構)的論證,由于發散結構(divergent structure)需得到多條結論,而本文分析時以條目中的命題為結論,不存在多條結論的情況,所以這里主要分析著作中的線性結構、收斂結構與組合結構。
線性結構(serial structure)包含這樣一個陳述,它既是一個結論又是一個更進一步的結論的理由[27]。將陳述排列為鏈,每個陳述或有一個直接前驅理由,或有一個直接后繼結論,或既有一個直接前驅理由又有一個直接后繼結論,這反映了理由鏈的序列支撐關系。
在《論靈魂的激情》中,第14條的論證具有明顯的線性結構,如例1所示:
例1第14條:① 〈動物精氣的差異也可以使它們的運動有所不同〉。
② 〈使得動物精氣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進人肌肉中的其他原因,就是這些精氣激蕩得實際上并不均勻,而且它們的部分也是各不相同的〉。因為,③ 〈當其中的某些部分要比別的部分更加粗大并且更加活躍的時候,它們就能以直線的方式而在腦腔和大腦的小孔中走的更遠〉。同樣,④ 〈它們能到達的肌肉也就與那些比它們弱小的部分可到達的肌肉有所不同了〉。
該論證具有線性結構。由陳述③“精氣的某些部分更大且更加活躍便能走得更遠”,可得陳述④“活躍精氣能到達的肌肉與弱小部分不同”,進而證明陳述②“動物精氣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進人肌肉”,得到結論①“動物精氣的差異也可以使它們的運動有所不同”。該論證結構如圖1所示:
第13條的論證也具有線性結構,不過在論證的過程中,有一個理由是以例子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故該論證為具有線性結構的例證。
例2第13條:這種外在物體的活動可以使動物精氣以不同的方式進入肌肉中。
在這里,只舉一個例子。① 〈如果某個人迅速地把手舉到我們的眼前,好像要碰到我們的眼睛一樣,盡管我們知道對方是我們的朋友,他只是在逗著玩,他會非常小心不會給我們施加任何的傷害,但是我們還是很難阻止自己把眼睛閉上〉。這個例子指出,② 〈在并沒有靈魂介入的情況下,眼睛也可以違反我們的意志而自動地閉合上〉,要知道,意志本來是我們靈魂唯一的或至少是基本的行動,但是,這一次卻是由于我們的③〈身體機器的結構,才使得這個移向我們的眼睛的運動在我們的大腦中激起了另一個運動,它引導動物精氣進人相應的肌肉中,從而使我們的眼皮低垂了下來〉。
該論證是一個線性結構。通過例子①可知沒有靈魂參與的情況下眼睛可以自動閉合,即陳述②。以陳述②為例證,采用不完全歸納法可知外在的物體活動引起使得肌肉可以運動(第11條說明肌肉的運動由動物精氣的流動產生),結論(陳述③)得證。該論證結構如圖2所示:
在收斂結構(convergent structure)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前提意在單獨支持結論,獨立為結論提供證據。該結構中每一前提自身就能為結論提供理由,無需參考其他前提[12]。這反映了前提對結論相互獨立的支撐關系。著作中第50條就是包含收斂結構的論證。
例3第50條:并不存在這樣的靈魂,他如此的虛弱以至于通過恰當引導也不能獲得對激情的絕對控制力量。
① 〈無論是小腺體的運動,還是動物精氣或大腦的運動,盡管它們給靈魂呈現了某些事物,它們很自然地與那些在靈魂中激起某些激情的運動相連,然而通過習慣的養成,它們也可以與這些運動相分離,而與另一些非常不同的運動相連〉,甚至這種習慣還可以通過唯一的一次行動而無需長時間的使用就能形成。……既然② 〈人們能通過一些技巧來改變那些缺乏理性的動物們的大腦運動〉,那么顯然,③ 〈人們在自己身上的情況就會更加樂觀〉,④ 〈那些靈魂最為虛弱的人,只要他們運用足夠的技巧來訓練和控制自己的激情,也可以獲得對于他們所有的激情的絕對控制權〉。
該論證是一個收斂結構。笛卡爾從改變大腦運動和改變小腺體、精氣或大腦與激情運動的相連方式兩條路徑論證了所有靈魂通過引導都能絕對控制激情這一結論。其論證結構如圖3所示:
圖3展示了該收斂論證的過程。一方面,根據陳述①,如果不改變小腺體、動物精氣或大腦的運動,可以通過習慣的養成甚至唯一的一次行動便能改變靈魂中激起某些激情運動的連接,這樣便可以獲得對激情的絕對控制力量,結論陳述④得證。另一方面,根據陳述②,人們能通過一些技巧來改變那些缺乏理性的動物們的大腦運動,可以推出人們也能通過一些技巧來改變人類的大腦運動(陳述③),結論陳述④亦能得證。
組合結構(linked structure)指兩個或更多理由以一種聯合或組合的方式支持一個結論,單個理由不能對結論提供支持[27]。組合結構中的前提必須聯合起作用,各前提之間類似于合取關系,去除一個前提可能對論證產生較大影響,這反映了前提聯合對結論的支撐作用。
在《論靈魂的激情》中,第30條和第77條都具有包含組合結構的論證,且通過理由對其中某一前提做出了進一步支持。這兩個論證如例4、例5所示。
例4第30條:靈魂是與身體的所有部分都相聯在一起的。
但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所有的這些東西,就需要我們認識到①〈靈魂是與整個身體都相聯在一起的〉,并且我們完全不能說靈魂是存在于身體的某個部分而不是別的部分中,因為②〈身體就是一個整體,并且以某種方式是不可分的〉,要知道,身體所謂的器官就是如此地相互關聯在一起的,以至于③〈當其中的一部分被取走后,整個身體就不完善了〉……但是,④〈當人們拆除身體的組合的時候,靈魂也就與身體完全分離了〉。
該論證具有組合結構。首先,根據陳述③“身體的一部分被取走后,身體就不完善了”可以得到身體是一個整體(陳述②)。而拆除身體組合時靈魂便會分離(陳述④)可以保證身體與靈魂相聯,根據陳述②和陳述④可得靈魂與作為整體的身體相聯,即結論①。該論證結構如圖4所示:
下例的論證結構和例4類似,也用一個前提對組合結構中的一條理由予以支持。
例5第77條:① 〈那些最愚蠢、最機靈的人都不是最易于陷入驚奇的人〉。
此外,盡管只有②〈那些生性遲鈍和愚蠢的人才根本不會讓自己會對什么事情有所驚奇〉,但是③ 〈這并不意味著那些最機靈的人就總是會最容易使自己陷于驚奇〉,基本上來說,而是那些④ 〈盡管自身具有很好的日常識見,卻又對自己的能力認識不足的人,他們才往往容易使自己感到驚奇〉。
該論證擁有組合結構。理由②說明愚蠢的人不會有所驚奇,可以證明結論①中“那些最愚蠢的人不是最易陷入驚奇的人”。理由④認為自身具有很好日常識見而且對自己的能力認識不足才容易使自己感到驚奇,能夠支撐理由②“不是最機靈的人最容易使自己陷于驚奇”,進而證明結論①中“那些最機靈的人不是最易陷入驚奇的人”。結論①是“那些最愚蠢的人不是最易陷入驚奇的人”與“那些最機靈的人不是最易陷入驚奇的人”的合取命題,兩個子命題都被證成,結論①得證。論證結構如圖5所示:
第2條是一個較為復雜論證結構,其間同時包含了組合結構和收斂結構,通過這種復合論證,笛卡爾論述了為了認識激情區分身體和靈魂的必要性。
例6第2條:為了認識靈魂的激情,就必須要對靈魂的功能和身體的功能進行區分。
① 〈每一個主體對我們的靈魂采取行動要比對身體采取行動更為直接〉(② 〈靈魂是與身體相聯的〉)。并且,由此,我們應該想到③ 〈在靈魂中的激情一般地就是身體上的行動〉。于是,為了④ 〈達到關于激情的認識,沒有比檢驗靈魂和身體的差異更合適的道路了〉,⑤ 〈通過區分靈魂和身體,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每一種功能都分別對應于它們身上〉。
該論證的論點是“為了認識靈魂的激情,必須要區分靈魂的功能和身體的功能”。陳述①、②、③主要說明了身體與靈魂、激情與行動間的關系,可以圖示如下:
從圖6可以看出陳述①、②、③的作用:陳述②表明身體與靈魂相關,陳述③說明靈魂與身體共同指向同一事物,即激情(行動)。陳述②和陳述③共同作用便搭建了靈魂、身體、激情的互動框架,給出了“通過區分靈魂和身體,可以把我們的每一種功能都分別對應于它們身上”(即陳述⑤)的前提。陳述⑤說明區分靈魂和身體可以對應相應功能,于是能更好地認識激情,所以它是結論的正面理由之一。陳述①說明對靈魂采取行動更直接,說明區分身體與靈魂之后,從靈魂作為切入點更易認識激情,也是結論的正面理由。不過它和陳述⑤關聯不大,即二者可以獨立地作為結論的支撐,為收斂結構。因此,整個論證是由組合結構與收斂結構組成的復合論證結構,其結構關系如圖7所示:
根據圖7可以重新梳理論證過程:由于身體和靈魂相聯(陳述②),并且在靈魂中的激情一般地就是身體上的行動(陳述③),我們便可通過區分靈魂和身體把激情的功能對應到靈魂上(陳述⑤),這樣便可達到關于激情的認識(結論④)。另外,由于對靈魂采取行動更直接(陳述①),將身體從靈魂中區分以后便能更直接地認識靈魂的激情(結論④)。
綜上可以發現,《論靈魂的激情》中的基本論證結構較為多樣,其中以組合論證為主,說明證據鏈之間也具有較強的關聯。對于一些關鍵的組合論據,他還進一步給出了新的論據去加以證明,這也增強了其論證的說服力。
四、笛卡爾《論靈魂的激情》中的權衡論證與省略論證
在《論靈魂的激情》中,一些論證對于可能反駁其觀點的論據也予以考慮,構成權衡論證。權衡論證(pro and con arguments)是一種同時包含正面的、支持結論的理由(pros)與反面的、反對結論的理由(cons)的論證,其結論的證成(至少在論證者看來)源于正面理由的邏輯力量經過權衡勝過了反面理由[21]。權衡論證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包含了推論內核(illative core),還對論辯性外層(dialectical tier)有一定接近。
第84條是一個簡單的權衡論證,笛卡爾同時提及正反理由,不過并未對反面理由予以進一步說明,只是通過自身的判斷力認為正面理由更勝一籌。
例7第84條:恨并沒有和愛同樣多的種類。
此外,盡管① 〈恨和愛是直接相對的〉,但是② 〈我們卻不能像區分愛那樣區分出同樣多的恨的種類〉,因為③〈我們在自己想要有意識地與之保持距離的不良事物中并不能區分出像我們在想要親近的美好的事物中能區分出一樣多的種類〉。
可以看出,反面理由①說明愛和恨直接相對,理應推出愛和恨具有同樣多的種類,即結論②的反面。正面理由③認為我們對不良事物會刻意保持距離,而對美好事物會想要接近,二者性質的差異導致了種類的差異,證明了結論②。笛卡爾認為正面理由勝過反面理由,故證成結論②。
圖8顯示出該論證具有權衡論證中最簡單的論證結構,論證僅有一條正面理由和一條反面理由構成。第一條就更復雜一些,是具有組合結構的權衡論證,如例8所示。
例8第1條:對于一個主體來說,作為激情的東西往往在別人看來就是行動。
我們要談論的所有發生的或重新顯現出來的東西,就是①〈在一個主體看來在他身上發生的,而被哲學家們一般地稱作激情的東西〉,以及②〈在一個使之發生的人看來的所謂的行動〉。由此,盡管③〈施動者和被動者通常非常不同〉,但④〈行動和激情則總是一個東西,是依據兩個不同的相關主體給出的兩個不同的名稱〉。
(1) 維修集約范式要素定量化指標體系的建立。為了將城市軌道交通車輛維修集約范式轉移與資源配置、成本控制等目標相結合,建立一套定量化指標體系來合理評價維修集約范式,將成為后續深入研究的關鍵點。
該論證整體而言是由4個陳述組成的權衡論證。論點是“激情就是行動”,理由包括正面理由①、正面理由②和反面理由③。笛卡爾同時承認正面理由和反面理由的存在,但通過權衡正反理由認為反面理由③“施動者和被動者通常非常不同”不會勝過①、②兩條正面理由,由此,結論“行動和激情總是一個東西”得以證成。兩條正面理由對結論的支撐具有明顯的組合結構,因為僅僅通過“在一個主體看來在他身上發生的激情”或“在一個使之發生的人看來的所謂的行動”并不能推導出激情就是行動。兩條正面理由同時作用,便可知同一事物從主體的角度而言為“激情”,從客體的角度而言是“行動”。因此,激情與行動是同一事物不同維度的描述,結論證成。該論證的整體結構如圖9所示:
本文圖解權衡論證時沿用的依舊是戈維爾的傳統圖解方式,因為《論靈魂的激情》中所有正面理由都強于反面理由,否則各條結論不能成立。所以,這里不需要添加一個構件強調正面理由能夠“推倒”反面理由來展示權衡結果。
《論靈魂的激情》中還包含省略論證。省略的前提(Missing premises)指表面上沒有出現但實際被使用過的前提,如人們的常識、共識等[20]。該著作中許多論證包含未陳述出來的假定是因為在其他條目或在笛卡爾的其他著作如《論人》《第一哲學沉思集》中已有論述。
第4條的兩個論證均包含省略論證,如例9所示。這里采用斯克里文的圖解方法,即用字母表示省略的論據。
例9第4條:肢體的熱量和運動源自于身體,思想則出自靈魂。
同樣,由于①〈我們從不會認為身體可以以任何方式進行思考〉,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我們中②〈所有種類的思維都屬于靈魂〉,并且由于我們從不曾懷疑③〈有一些毫無生氣的物體能夠以我們所擁有的各種各樣的甚至更多的方式來運動,也能有各種各樣甚至更多形式的熱量〉(對火的體驗能讓我們看到這一點,也只有火具有比我們的任何一個肢體都多的熱量和運動),我們應該相信,由于④〈我們身上所有的熱和所有的運動從不取決于思維〉,于是就⑤〈只能歸屬于身體〉。
這一條包含“肢體的熱量和運動源自于身體”和“思想則出自靈魂”兩個論證。兩個論證均省略了前提,即笛卡爾身心二元論的主要思路:a〈思想、肢體的熱量和運動要么出自身體,要么出自靈魂〉。后一論證還省略了由①推出的結論,即b〈思維不屬于身體〉。這樣便可得出如圖10所示的兩個論證的結構。
第197條是一個同時包含線性結構、組合結構、省略論證、權衡論證的復雜論證,證明了與憤慨和驚奇、高興等情感同時出現的情形。
例10第197條:憤慨通常與驚奇相伴,而且也能與高興共存。
①〈驚奇通常會伴隨著憤慨而出現〉。因為②〈我們習慣于認為所有的事情將會以我們判斷應該如何的方式來發生,也就是說以我們認為是好的方式來達成〉,因此③〈當一件事情的發生出乎我們的意料時,我們就會感到驚奇〉。④〈憤慨與高興也是能共存的〉,盡管⑤〈它通常更多地會和悲傷相連在一起〉。因為⑥〈當那種我們對之感到憤慨的罪惡并不能傷害我們〉,并且⑦〈我們認為我們自己并不會去做類似的事情時〉,⑧〈我們就會感到高興〉,這可能就是有時候發笑會和這種激情相伴隨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條包含“驚奇通常會伴隨著憤慨而出現”和“憤慨與高興也能共存”兩個論證。第一個論證是一個線性結構的省略論證,省略的陳述是a〈事物不以好的方式發生會出乎我們的意料〉。第二個論證是一個包含組合結構的權衡論證。兩個論證的結構如圖11所示:
根據圖11展示的論證結構,第一個論證結構如下:首先根據理由②,人們認為所有的事情將會以好的方式發生。如果事件不以好的方式發生,便會讓我們感到出乎意料(省略理由a)。進而,出乎我們的意料會使我們感到驚奇(理由③),得到結論陳述①“憤慨會伴隨驚奇”。第二個論證結構如下:理由⑥“憤慨的罪惡并不能傷害我們”和陳述⑦“我們認為自己不會去做類似的事情”同時成立時,我們會感到高興(陳述⑧),所以憤慨與高興共存(結論陳述④)。反面理由⑤認為憤慨通常與悲傷聯系在一起,對“憤慨與高興共存”產生反面效果。作者權衡正反理由,認為正面理由勝過反面理由,故結論陳述④得證。
至此,本文分析了《論靈魂的激情》中的主要論證結構,并對其進行圖解。這里僅將論證結構展示出來,并不對其好壞加以說明,即不對這些論證進行評估。可以發現,在真實的語料中,論證往往結合、嵌套了各種不同的論證結構,較為復雜,這也是學術話語與日常生活中論證的精彩之處。
五、總結與展望
對笛卡爾《論靈魂的激情》中主要出現的條目內論證類型的總結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以發現,該著作使用的論證結構較為豐富,僅在條目內3種基本論證結構均有出現,省略論證與權衡論證也在一半以上的論證中有所涉及。對于組合結構,笛卡爾一般也會對主要的論據予以進一步說明,如用“當其中的一部分被取走后,整個身體就不完善了”進一步說明“身體是一個整體”這條理由,因此從論證結構的圖解中可以進一步判斷前提間的重要程度差異。

表1 《論靈魂的激情》中出現的主要條目內論證類型
本文最主要的意義是便于今后進一步對《論靈魂的激情》的論證評估,評估可以基于約翰遜和布萊爾提出的RSA模型考慮論證的前提是否是可接受的、前提是否為結論提供相關且充足的支持[28],亦可以從謬誤進路的角度考慮這些論證是否存在致命缺陷(a fatal flaw)或表面上的弱點(a prima facie weak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