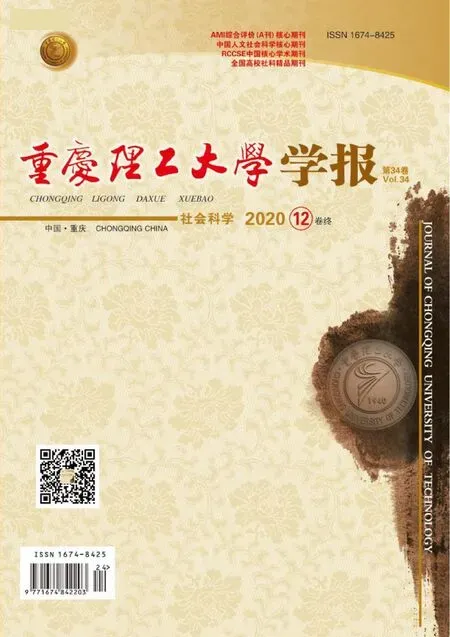從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看中國鄉(xiāng)村振興的走向
王 平
(甘肅政法大學(xué) 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院,甘肅 蘭州 730070)
馬克思為研究城市化問題的先驅(qū)之一[1],他從歷史角度對城市問題做了系統(tǒng)考察,尤其是“城鄉(xiāng)分割、城鄉(xiāng)對立”的分析方法,是我們認(rèn)識城鄉(xiāng)關(guān)系,認(rèn)識我國當(dāng)前鄉(xiāng)村振興問題的重要理論源泉。
一、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
馬克思基于唯物史觀,從城市發(fā)展歷史考察,對人類社會城市化的必然性、城鎮(zhèn)功能、空間演化、城鄉(xiāng)關(guān)系、城鎮(zhèn)發(fā)展的終極目的等方面進(jìn)行了歷史辯證分析,奠定了馬克思關(guān)于城市理論的基礎(chǔ)。這對認(rèn)識當(dāng)代中國鄉(xiāng)村振興與新型城鎮(zhèn)化及其二者的辯證關(guān)系,仍然具有指導(dǎo)意義。
(一)城鎮(zhèn)化的必然性
馬克思從唯物史觀角度考察,認(rèn)為鄉(xiāng)村向城市轉(zhuǎn)化將是現(xiàn)代歷史的必然。在《經(jīng)濟(jì)學(xué)手稿》中,馬克思指出:“現(xiàn)代的歷史是鄉(xiāng)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樣,是城市鄉(xiāng)村化。”[2]馬克思所說的古代城市鄉(xiāng)村化,指的是在封建社會這樣的低級社會形態(tài)中在城市中心劃分土地進(jìn)行“分封制”治理,將城市變成了鄉(xiāng)村。但是他認(rèn)為,在現(xiàn)代社會中,鄉(xiāng)村將會城鎮(zhèn)化,這是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矛盾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勢。這與他關(guān)于城鄉(xiāng)對立、矛盾發(fā)展的理論分析是一體的,他認(rèn)為未來的社會(共產(chǎn)主義社會)在生產(chǎn)力發(fā)展基礎(chǔ)上必然消除城鄉(xiāng)對立、形成城鄉(xiāng)一體,鄉(xiāng)村生活將向城市生活方式不斷發(fā)展。馬克思、恩格斯通過歷史的考察,發(fā)現(xiàn)城市是比國家出現(xiàn)更早的一種形態(tài),產(chǎn)生的根本動因是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帶來的社會分工的出現(xiàn)及其商品交換的頻繁。正如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指出的那樣:“工業(yè)的迅速發(fā)展產(chǎn)生了對人手的需要;工資提高了,工人成群結(jié)隊地從農(nóng)業(yè)地區(qū)涌入城市。”[3]可見,馬克思主義者認(rèn)為,由于生產(chǎn)力是不斷向前發(fā)展的,生產(chǎn)力發(fā)展基礎(chǔ)上的工業(yè)發(fā)展產(chǎn)生了對工人的需求,同時工業(yè)勞動者工資高于農(nóng)業(yè)勞動者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動和集中。人口向城鎮(zhèn)的集中就成了生產(chǎn)力發(fā)展和社會分工的必然結(jié)果,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程度[4]。
(二)城鎮(zhèn)的功能
城市之所以會產(chǎn)生和存在,是因為城市具有某些方面的特定功能。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認(rèn)為,城市的功能隨著歷史演變在不斷變化和完善。城市功能變化和擴(kuò)充的基本軌跡是:防御外敵—政治功能—文化和生產(chǎn)功能—經(jīng)濟(jì)功能[5]。馬克思和恩格斯認(rèn)為早期城市的形成主要是為了防御外敵入侵而進(jìn)行的集中,但隨著社會分工的細(xì)化,階層矛盾及利益沖突導(dǎo)致對城市管理要求提高,需要更多的行政機(jī)構(gòu)加強(qiáng)管理,這就逐漸變成了城市的政治功能;隨著統(tǒng)治階層生活質(zhì)量的不斷提升,他們需要更多的物質(zhì)及精神生活,便產(chǎn)生了城市的生產(chǎn)功能及文化功能;在近代資本主義生產(chǎn)力進(jìn)一步發(fā)展和推動下,城市的經(jīng)濟(jì)功能便成了一項主要功能,特別是隨著市場經(jīng)濟(jì)發(fā)展,經(jīng)濟(jì)功能逐漸占據(jù)主導(dǎo)位置。事實上,在現(xiàn)代社會中,城市的功能是集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功能為一體的,城鎮(zhèn)往往是一個地區(qū)或區(qū)域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中心。列寧將其概括為:“城市是經(jīng)濟(jì)、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6]可見,隨著生產(chǎn)力發(fā)展,城市功能日益多樣化,在城市的諸多功能中,經(jīng)濟(jì)功能是核心、主導(dǎo)功能,由于經(jīng)濟(jì)功能的主導(dǎo),城市是地區(qū)或區(qū)域的科技、貿(mào)易與金融的中心,極大地便利了人們的生活,“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7]。我們發(fā)展現(xiàn)代城市,要以城市的經(jīng)濟(jì)功能為主導(dǎo),同時要配合實現(xiàn)文化、社會管理功能,成為居民生產(chǎn)、消費、文化享受的中心。
(三)城鄉(xiāng)關(guān)系分析的邏輯
馬克思主義者運用“城鄉(xiāng)分離、城鄉(xiāng)對立”的邏輯分析未來城鄉(xiāng)關(guān)系及其變化趨勢。認(rèn)為在人類生產(chǎn)力落后的古代社會,是沒有明顯的城鄉(xiāng)差別的,是渾然一體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chǎn)力的解放和發(fā)展,城鄉(xiāng)的分離和對立產(chǎn)生了。機(jī)器大工業(yè)生產(chǎn)帶來農(nóng)業(yè)在社會經(jīng)濟(jì)中地位的下降,良好的要素向城市集中,城市與鄉(xiāng)村產(chǎn)生了對立。“把一部分人變?yōu)槭芫窒薜某鞘袆游铮蚜硪徊糠秩俗優(yōu)槭芫窒薜泥l(xiāng)村動物”,“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chǎn)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xiāng)村里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從事城市工業(yè)者和鄉(xiāng)村農(nóng)業(yè)者成了“兩個不同階級”[8]。正因為如此,他指出在未來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要把消除城鄉(xiāng)矛盾和城鄉(xiāng)對立作為既定目標(biāo),其基本途徑是通過對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的改造實現(xiàn)城鄉(xiāng)融合。馬克思和恩格斯認(rèn)為,消滅城鄉(xiāng)對立需要物質(zhì)條件為基礎(chǔ),“將城市和農(nóng)村生活方式的優(yōu)點結(jié)合起來”,“通過城鄉(xiāng)的融合,使全體社會成員才能得到全面發(fā)展”[9]。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城鎮(zhèn)化以資本主義城鄉(xiāng)分離、城鄉(xiāng)對立為分析的基本邏輯,不但指出了城市產(chǎn)生的原因、趨勢、目標(biāo),而且指出了城市化的基本途徑。認(rèn)為城市化是必然趨勢,但由于資本主義城市存在矛盾與對立,未來城市化的走向?qū)⑹窍龑αⅰ崿F(xiàn)城鄉(xiāng)融合,實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的最終目的是“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這跟我國新型城鎮(zhèn)化的原則、目標(biāo)取向是一致的,也說明我國現(xiàn)階段推進(jìn)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shè)是遵循城鎮(zhèn)發(fā)展規(guī)律、遵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一次偉大實踐。
(四)唯物史觀下的空間說
馬克思唯物史觀將空間分為兩種:地理空間和社會空間。地理空間是人類從事生產(chǎn)活動和彼此交往的主要場所,是人類生產(chǎn)這種社會實踐對自然實體進(jìn)行改造形成的;社會空間是由包括經(jīng)濟(jì)、文化、政治及生產(chǎn)生活等在內(nèi)的各種人類關(guān)系構(gòu)成的,更強(qiáng)調(diào)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空間組織。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繼承這一唯物史觀的基礎(chǔ)上,認(rèn)為空間不但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并非是空洞和靜止的,“空間并非是純粹的客觀存在形式,而是社會的產(chǎn)物”[10]。唯物史觀的空間說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城市理論的必然延伸,與城市產(chǎn)生的歷史必然規(guī)律、城市前進(jìn)和發(fā)展方向相一致,體現(xiàn)了城市這種“空間”的歷史意義和社會功能,體現(xiàn)出城市不但具有經(jīng)濟(jì)功能而且具有社會功能,不但注重生產(chǎn)力而且注重生產(chǎn)關(guān)系,是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集合。在建設(shè)新型城鎮(zhèn)化過程中,要注意城鎮(zhèn)功能的多元整合,要將產(chǎn)業(yè)集聚與人的發(fā)展、社會發(fā)展結(jié)合起來,避免城鄉(xiāng)“二元對立”,避免單純追求GDP增加的“唯經(jīng)濟(jì)論”觀念,避免僅注重空間結(jié)構(gòu)的“被動式城鎮(zhèn)化”所產(chǎn)生的社會風(fēng)險積聚[8],應(yīng)該將城鎮(zhèn)這種空間看成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協(xié)調(diào)的多元空間集合。
(五)城市發(fā)展的終極目的
馬克思主義者以唯物史觀的方法分析了城市化問題,并從歷史角度對城市發(fā)展進(jìn)行了考察,演繹出了城市發(fā)展的終極目的。首先,城市化是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chǎn)物,城市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出現(xiàn)的物。我國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也印證了這一點。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我國城鎮(zhèn)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推進(jìn)。即便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但不管是否可以取得城鎮(zhèn)戶口,農(nóng)民(農(nóng)民工)向城市的轉(zhuǎn)移還是成了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這是城市高收入和高就業(yè)機(jī)會決定的。其次,城市發(fā)展過程中雖然有不利于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因素,但這些問題同樣需要在發(fā)展中解決。縱觀資本主義城市發(fā)展過程中遇到的環(huán)境污染、城鄉(xiāng)對立等各種矛盾和問題,均只能靠發(fā)展的辦法去解決。要辯證地看到這些矛盾和問題既是城市化發(fā)展的阻礙,但同時又是城市化成熟、進(jìn)步發(fā)展的推動力。例如,環(huán)境污染問題可以通過加強(qiáng)治理、改進(jìn)城鎮(zhèn)化過程中的矛盾、推動生態(tài)農(nóng)業(yè)等城鄉(xiāng)互動加以解決。城鄉(xiāng)矛盾需要通過改造農(nóng)業(yè)和農(nóng)民,將城市和農(nóng)村的優(yōu)點相結(jié)合起來[9],逐步實現(xiàn)城鄉(xiāng)融合,消除城鄉(xiāng)的矛盾和對立。最后,隨著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城鎮(zhèn)成了區(qū)域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及社會關(guān)系的中心,提供城鎮(zhèn)公共物品是城市和諧發(fā)展的必要條件,公共物品的提供也為人的全面發(fā)展提供了保障。城市的發(fā)展是永不停息的,馬克思主義者認(rèn)為其發(fā)展的最終目的是“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這是城市發(fā)展的終極目的。我國城鎮(zhèn)化建設(shè)也一定要為人的發(fā)展服務(wù),為人們提供發(fā)展的條件,支持人的全面發(fā)展,將“人本思想”不斷落到實處,并最終實現(xiàn)人的自由。
二、馬克思理論視角下鄉(xiāng)村振興與新型城鎮(zhèn)化的有機(jī)統(tǒng)一
城市化是推動人類向現(xiàn)代社會形態(tài)變遷的歷史環(huán)節(jié),農(nóng)村的社會變革是城市化的內(nèi)在組成部分[11]。我國近年來提出的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與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相得益彰,也與中國現(xiàn)階段發(fā)展理念相統(tǒng)一。
(一)鄉(xiāng)村振興與新型城鎮(zhèn)化是為了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
馬克思主義者認(rèn)為一切生產(chǎn)的實質(zhì)都是人的自由和解放,是推進(jìn)“人”這一主體的全面自由發(fā)展,因為“全人類的首要生產(chǎn)力就是工人,勞動者”[12],人是生產(chǎn)的核心,生產(chǎn)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馬克思主義者堅信,在人類社會的最高階段——共產(chǎn)主義社會,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必將實現(xiàn)。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不但是城鎮(zhèn)化的理論要求,而且是城鎮(zhèn)化的終極目標(biāo)。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應(yīng)當(dāng)從兩個層次著手。首先,要將“人”這種生產(chǎn)發(fā)展中最具能動性的要素調(diào)動起來,實現(xiàn)人自身的生產(chǎn)能力的提升。沒有人自身的生產(chǎn)能力的發(fā)展,就不可能實現(xiàn)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fā)展歷程中,城鎮(zhèn)優(yōu)先的戰(zhàn)略已經(jīng)對我國發(fā)展起點低、資源短缺情形下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積極作用,使得一部分人已經(jīng)先富了起來。農(nóng)村雖然也取得了巨大進(jìn)步,但與城鎮(zhèn)相比,差距卻越來越大,以致于城鄉(xiāng)差距是我國最大的不平衡問題。如此發(fā)展下去,不但不能實現(xiàn)全體公民的全面自由發(fā)展,而且城鄉(xiāng)失衡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制約我國經(jīng)濟(jì)持續(xù)發(fā)展。
新型城鎮(zhèn)化與鄉(xiāng)村振興均強(qiáng)調(diào)“產(chǎn)業(yè)支撐”的重要性,強(qiáng)調(diào)優(yōu)化配置資源,體現(xiàn)了進(jìn)一步提升生產(chǎn)能力的意圖。應(yīng)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作為判斷一切工作是否有利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是一個結(jié)果,更是一個歷史過程,是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wù)。我國新型城鎮(zhèn)化提出的“城鄉(xiāng)一體、產(chǎn)業(yè)融合”思想與“鄉(xiāng)村振興”中的“生活富裕、產(chǎn)業(yè)興旺”等方針有機(jī)地融合在了一起,都順應(yīng)了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對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需要。
(二)鄉(xiāng)村振興與新型城鎮(zhèn)化是為了實現(xiàn)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再統(tǒng)一
生產(chǎn)力表征了人類作用于自然的活動狀態(tài),是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生產(chǎn)關(guān)系是人們改造自然過程中結(jié)成的相互關(guān)系。馬克思認(rèn)為,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guān)系,生產(chǎn)關(guān)系反作用于生產(chǎn)力。當(dāng)生產(chǎn)關(guān)系能夠適應(yīng)特定階段生產(chǎn)力發(fā)展需要時,對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能夠起到正向推動作用,當(dāng)生產(chǎn)關(guān)系不適應(yīng)特定階段生產(chǎn)力發(fā)展需要時,對生產(chǎn)力發(fā)展起到反向阻礙作用[13]。根據(jù)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論精神,城鎮(zhèn)化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當(dāng)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促使城鎮(zhèn)產(chǎn)生后,相對于原來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城鎮(zhèn)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是一種全新的關(guān)系,這種生產(chǎn)關(guān)系應(yīng)當(dāng)能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發(fā)展需要。從整個社會來看,農(nóng)村進(jìn)步過程中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同樣需要調(diào)整。在小規(guī)模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階段,農(nóng)民之間的合作交往非常簡單,生產(chǎn)關(guān)系也相對單一。但隨著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的提高,農(nóng)業(yè)集約化、規(guī)模化的合作社等模式已經(jīng)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了人們的視野,導(dǎo)致他們之間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也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鄉(xiāng)村振興從某種程度來說是調(diào)整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步調(diào),使二者更加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進(jìn)一步看,城鄉(xiāng)之間的關(guān)系也應(yīng)隨著生產(chǎn)力的改變而調(diào)整適應(yīng)。因此,新型城鎮(zhèn)化與鄉(xiāng)村振興目的一致,都是為了讓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更加適應(yīng)、協(xié)調(diào)。
在我國城鄉(xiāng)發(fā)展實踐中,部分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生產(chǎn)力已經(jīng)發(fā)展但生產(chǎn)關(guān)系未能完全隨著生產(chǎn)力發(fā)展而進(jìn)步的情況,表現(xiàn)為居民應(yīng)當(dāng)被確立的生產(chǎn)、交換、分配、消費未能完全適應(yīng)現(xiàn)階段要求,存在著生產(chǎn)組織和配置效率問題、產(chǎn)品相對過剩問題、交換渠道和成本問題、交換價值非等價問題、城鄉(xiāng)交流阻隔問題、城鄉(xiāng)居民二元身份問題等某些方面的脫節(jié)問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供需不平衡等一系列社會經(jīng)濟(jì)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xiàn),表明了我國城鄉(xiāng)生產(chǎn)力已得到極大發(fā)展但生產(chǎn)關(guān)系尚不能完全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發(fā)展要求,協(xié)調(diào)二者的關(guān)系非常緊迫。
(三)鄉(xiāng)村振興與新型城鎮(zhèn)化是為了達(dá)到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統(tǒng)一
城鎮(zhèn)化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同時城鎮(zhèn)化又通過要素積聚效應(yīng)和分工及專業(yè)化帶來的規(guī)模經(jīng)濟(jì)效應(yīng)、資源整合帶來的創(chuàng)新效應(yīng)等反作用于經(jīng)濟(jì),從而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1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中國實行的是“城鄉(xiāng)分離”的戶籍制度,這種戶籍制度不但分割了戶口,而且分割了許多附著在戶口上的隱形資源分配。這是特定歷史時期的選擇,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和積極因素,但從長期看,這不利于社會公平,不利于社會持續(xù)發(fā)展,不利于工業(yè)品在農(nóng)村的消費,需要對短期與長期利益做出調(diào)整。
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后,黨和國家開始重視“三農(nóng)”問題,這是黨的十六大報告中“統(tǒng)籌城鄉(xiāng)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方略的體現(xiàn)。國家也有意引導(dǎo)“工業(yè)反哺農(nóng)業(yè)”,尤其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旨在發(fā)揮農(nóng)村主體作用的基礎(chǔ)上,讓“城市反哺農(nóng)村”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從短期看,城市對農(nóng)村的支援降低了城市資本的積累;但從長期看,農(nóng)村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為城市工業(yè)和服務(wù)業(yè)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市場,發(fā)揮了農(nóng)村這個“縱深”的作用。早在1984年6月,鄧小平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nóng)村這一穩(wěn)定的基礎(chǔ)是不行的”[15],“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農(nóng)村和城市,就是這樣相互影響、相互促進(jìn)”[15]。鄉(xiāng)村振興與新型城鎮(zhèn)化的同時推進(jìn)是對我國長期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的糾偏,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關(guān)系的再調(diào)整。
(四)鄉(xiāng)村振興與新型城鎮(zhèn)化是消費、積累與擴(kuò)大再生產(chǎn)的辯證統(tǒng)一
整個社會是由眾多消費者個體和一系列生產(chǎn)者主體構(gòu)成的,消費者的收益主要滿足個體及家庭成員消費和再生產(chǎn)。馬克思主義者認(rèn)為,消費與積累是辯證統(tǒng)一的,積累與消費既存在一致的一面,但又是一對矛盾。在同一面上,積累與消費相互促進(jìn),積累越多,可用于擴(kuò)大再生產(chǎn)的資源就越多,越有利于物質(zhì)資料的生產(chǎn),進(jìn)一步提高國民收入、促進(jìn)消費。在對立面上,積累與消費是一對矛盾,消費越多,當(dāng)前可積累的就少,反之亦然。經(jīng)濟(jì)主體獲得的收益是滿足其自身消費、積累及擴(kuò)大再生產(chǎn)的來源,總體來說,“生產(chǎn)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chǎn)”[16]。在消費、積累及擴(kuò)大再生產(chǎn)過程中,消費者或經(jīng)濟(jì)主體收益多少決定了整個生產(chǎn)、再生產(chǎn)及消費與積累能否順暢進(jìn)行。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黨的十六大之前,國家雖然也有重視和推進(jìn)農(nóng)村發(fā)展的意愿,但總體看是“鄉(xiāng)村支援城鎮(zhèn)”的模式。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國工業(yè)是從“一窮二白”的基礎(chǔ)上起步的,發(fā)展工業(yè)所需要的資本非常短缺,于是依靠工農(nóng)產(chǎn)品“剪刀差”擴(kuò)大城市資本積累及其擴(kuò)大再生產(chǎn)。但隨著資本積累越來越龐大,生產(chǎn)能力也空前提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jī)后的經(jīng)濟(jì)刺激計劃,將許多工業(yè)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過剩推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消費與積累的矛盾變得異常嚴(yán)重,于是,振興鄉(xiāng)村也就是振興鄉(xiāng)村的消費,是為了更好地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guān)系,將消費率調(diào)整到符合特定社會階段需要的水平。新型城鎮(zhèn)化與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同時推進(jìn),將會調(diào)整城市工業(yè)品與農(nóng)村消費能力關(guān)系,同時要考慮農(nóng)民進(jìn)城后的利益分配是否足以支持新市民具有可持續(xù)的收益獲取能力與資本的再生產(chǎn)能力[17],從而解決整個社會積累與消費的關(guān)系等現(xiàn)實問題。
三、中國共產(chǎn)黨人實施鄉(xiāng)村振興的邏輯
(一)為人民謀幸福的執(zhí)政理念
“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思想是我黨長期實踐中總結(jié)出來的基本執(zhí)政理念和工作方法,是馬克思主義“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觀念的延伸。以習(xí)近平同志為核心的新一代黨中央,總結(jié)中國共產(chǎn)黨治國理政的基本經(jīng)驗,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總結(jié)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提出“堅持以人為本,重民生,辦實事,解決人民群眾最關(guān)心、最直接、最現(xiàn)實的利益問題,滿足人民群眾最基本、最緊迫的需求”[18],體現(xiàn)出了習(xí)近平總書記的人民情懷觀。習(xí)近平總書記經(jīng)常告誡我黨要“不忘初心”,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應(yīng)有擔(dān)當(dāng)。社會發(fā)展了,經(jīng)濟(jì)進(jìn)步了,城鎮(zhèn)更美了,而鄉(xiāng)村被遺棄、遺忘了,跟城鎮(zhèn)相比變得更落后了,這該怎么辦?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新的歷史時期表現(xiàn)出了新的歷史擔(dān)當(dāng)——“群眾利益無小事,柴米油鹽等問題對群眾來說就是大事。”[18]他們緊緊牽掛著群眾的冷暖,牽掛著9億農(nóng)民的發(fā)展問題,鄉(xiāng)村振興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執(zhí)政理念的生動體現(xiàn)。
(二)穩(wěn)固執(zhí)政基礎(chǔ)的現(xiàn)實需求
中國共產(chǎn)黨帶領(lǐng)全國人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xiàn)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氣,在每一個關(guān)鍵時刻都能做出重大而正確的選擇。從赤貧到富裕再到小康,中國人民見證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帶來的巨變。這成了人民群眾熱愛黨、擁護(hù)黨的現(xiàn)實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奮斗的目標(biāo)”,這是新時期中國共產(chǎn)黨人喊出的最接地氣的聲音,也呼應(yīng)了人民的心聲。從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基本理論看,人的欲望是無窮的,而恰恰是這個無窮的欲望激發(fā)了人們奮斗的動力,催生了人們對更高生活品質(zhì)的追求。對于全體中國人來說,追求富裕幸福的新生活是每個人的權(quán)利。當(dāng)城鄉(xiāng)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農(nóng)民的失落和不平衡就會加劇,從而產(chǎn)生對未來的迷茫,對社會發(fā)展不公的失望,進(jìn)而產(chǎn)生對社會發(fā)展道路的懷疑。這種狀況的產(chǎn)生,顯然不利于國家的穩(wěn)定,不利于我們黨長期形成的執(zhí)政基礎(chǔ)的進(jìn)一步穩(wěn)固。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到:“政治統(tǒng)治者只有在它執(zhí)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維持下去。”[19]中國共產(chǎn)黨清楚地認(rèn)識到了這一點,將“群眾利益無小事”貫穿到執(zhí)政過程中,通過鄉(xiāng)村振興實現(xiàn)全體中國人的發(fā)展,進(jìn)一步夯實我黨的執(zhí)政基礎(chǔ),堅實全中國人民對黨的認(rèn)同和支持,更加鞏固了我黨的執(zhí)政地位。
(三)中國發(fā)展階段的時代選擇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jìn)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可見,經(jīng)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fā)展,中國生產(chǎn)力已經(jīng)得到了極大釋放,社會生產(chǎn)已經(jīng)由全面落后向部分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性落后轉(zhuǎn)化。在這個階段,改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已經(jīng)非常迫切,長期的不平衡將會導(dǎo)致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受到影響。在我國諸多的不平衡中,城鄉(xiāng)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鄉(xiāng)村振興是現(xiàn)階段解決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平衡的重要舉措。從國內(nèi)的現(xiàn)實看,在工業(yè)領(lǐng)域,一方面鋼鐵、玻璃、水泥、電解鋁等一些低端產(chǎn)品產(chǎn)能嚴(yán)重過剩;但另一方面,隨著生活品質(zhì)的提高,對于高科技、高品質(zhì)產(chǎn)品的需求急劇增加,國內(nèi)市場尚不能滿足這一部分需求。于是,出現(xiàn)了排隊買國外知名手機(jī)等現(xiàn)象。在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群眾對高品質(zhì)有機(jī)農(nóng)產(chǎn)品、鄉(xiāng)村生活體驗服務(wù)等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需求非常多,而鄉(xiāng)村的供給和服務(wù)承載能力卻非常有限。現(xiàn)階段實施鄉(xiāng)村振興,可通過城鄉(xiāng)對接,消耗部分過剩產(chǎn)品,開拓高品質(zhì)新產(chǎn)品、新服務(wù),同時將優(yōu)質(zhì)的鄉(xiāng)村資源開發(fā)出來促進(jìn)鄉(xiāng)村發(fā)展,最終實現(xiàn)城鄉(xiāng)均衡發(fā)展。
四、未來中國鄉(xiāng)村振興的走向
(一)城鄉(xiāng)壁壘消除,走向一體化
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告訴我們,城市是歷史的產(chǎn)物,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發(fā)展隨著時代進(jìn)步、生產(chǎn)力發(fā)展而不斷演化(如圖1)。在生產(chǎn)力落后的古代社會,人們之間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比較簡單,城鄉(xiāng)之間是無差別的,是渾然一體的。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分工和產(chǎn)業(yè)的集聚使得城鎮(zhèn)產(chǎn)生,一些鄉(xiāng)村逐漸變成了城市,這就是城鎮(zhèn)化過程。在未來共產(chǎn)主義社會,隨著生產(chǎn)力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城鄉(xiāng)之間的生產(chǎn)力均會得到極大的釋放,城鄉(xiāng)之間的差別將會最終消失。
對中國而言,鄉(xiāng)村振興的目的是在保護(hù)鄉(xiāng)村文化、鄉(xiāng)村文明的基礎(chǔ)上提高農(nóng)村的社會生產(chǎn)力,改善農(nóng)村基礎(chǔ)設(shè)施,改善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生活條件。黨中央、國務(wù)院作出這一重大戰(zhàn)略抉擇的前提是:我國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較長時期的城鎮(zhèn)化過程,城鎮(zhèn)化水平已經(jīng)得到了較大提升。據(jù)統(tǒng)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中國城鎮(zhèn)化率為10.64%;改革開放初的1978年,中國城鎮(zhèn)化率為17.92%,近30年只增長了7個百分點;而2018年,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已經(jīng)達(dá)到了59.58%,接近了60%,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6倍(見圖2)。在城鎮(zhèn)已經(jīng)得到快速發(fā)展的情況下,我國農(nóng)村發(fā)展依然滯后。但相信隨著鄉(xiāng)村振興的開展,城鄉(xiāng)差距擴(kuò)大的局面將逐步得到遏制。伴隨著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向鄉(xiāng)村輻射,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的體制機(jī)制進(jìn)一步建立健全[20],城鄉(xiāng)聯(lián)通將進(jìn)一步加快,城鄉(xiāng)壁壘最終會消失,從而實現(xiàn)城鄉(xiāng)一體化。
(二)鄉(xiāng)村城鎮(zhèn)化,城鎮(zhèn)差異化
馬克思認(rèn)為,城市最初是在鄉(xiāng)村的基礎(chǔ)上,隨著生產(chǎn)力發(fā)展導(dǎo)致的社會分工的出現(xiàn),伴隨著產(chǎn)業(yè)、人口的區(qū)域集聚形成的。也就是說,城市的前身大都是鄉(xiāng)村,城市是在鄉(xiāng)村發(fā)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我國的城市形成過程雖然局部具有國家推動的因素,但總體來說仍然離不開城市發(fā)展的規(guī)律,同樣是在生產(chǎn)力發(fā)展基礎(chǔ)上的產(chǎn)業(yè)和人口聚集。如深圳和長三角、珠三角等區(qū)域,隨著城鎮(zhèn)化加快,一些漁村等變成了遼闊的大都市,這就是鄉(xiāng)村變城鎮(zhèn)的過程。因此,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歷史趨勢就是更多的農(nóng)村、農(nóng)民變成了城市、市民。另一方面,鄉(xiāng)村振興的根本是“產(chǎn)業(yè)興旺”。要發(fā)展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必須以產(chǎn)業(yè)發(fā)展為載體,當(dāng)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力得到了發(fā)展,新型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職業(yè)農(nóng)民、鄉(xiāng)村旅游等在鄉(xiāng)村將成為熟悉的名詞。鄉(xiāng)村的公共服務(wù)能力也會隨著鄉(xiāng)村振興而增強(qiáng),馬克思認(rèn)為“隨著社會發(fā)展,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會顯著地增加,并隨著新社會的發(fā)展而不斷增長”[19]。這樣,鄉(xiāng)村跟城鎮(zhèn)之間的鴻溝將會式微,鄉(xiāng)村事實上已經(jīng)具有了城鎮(zhèn)的特征和屬性。
對于城市而言,隨著城鎮(zhèn)數(shù)量的增大,城鎮(zhèn)的功能和定位將會趨于多元。有的城市可能聚合了完整的工業(yè)產(chǎn)業(yè)鏈,有的城市可能是以現(xiàn)代服務(wù)業(yè)、金融業(yè)為主體,有的可能是物流、商業(yè)的集散地。甚至有些城市可能是由原來的農(nóng)村因具有秀美的山川、濃郁的文化而發(fā)展來的旅游休閑圣地。這些城鎮(zhèn)因具有不同的特征、承載不同的功能而變得差異化。
(三)交流多元化,互動雙向化
城鄉(xiāng)壁壘的消除、城鄉(xiāng)交通的便捷將促進(jìn)城鄉(xiāng)間的交流。這種交流是全方位、立體式進(jìn)行的。既有生產(chǎn)方式的交流,也有生活方式的交流;既有物質(zhì)的交流,也有文化的交流;既有商業(yè)上的交流,也有感情元素的交流。這些社會關(guān)系的變化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jié)果,代表具有落后生產(chǎn)力的鄉(xiāng)村經(jīng)過振興后與代表先進(jìn)生產(chǎn)力的城鎮(zhèn)間的差異會越來越小。這種先進(jìn)的生產(chǎn)力改變了傳統(tǒng)城鄉(xiāng)的交流方式,擴(kuò)大了交流的廣度和深度。
從城鄉(xiāng)互動看,隨著鄉(xiāng)村的發(fā)展,單向式的鄉(xiāng)村向城鎮(zhèn)學(xué)習(xí)、看齊的交流路徑也將會逐步改變?yōu)槌青l(xiāng)互動雙向的交流方式。城鎮(zhèn)有優(yōu)于鄉(xiāng)村之處,鄉(xiāng)村也有比城鎮(zhèn)先進(jìn)的地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將成為常態(tài)。鄉(xiāng)村不再是那個模仿、追趕者,而可能成為被學(xué)習(xí)、被追隨、被羨慕的地域。在人口流動方面,將表現(xiàn)為人口從城鎮(zhèn)流入鄉(xiāng)村和鄉(xiāng)村流入城鎮(zhèn)的雙向互動。馬克思也認(rèn)為,當(dāng)城市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城市人口將會向農(nóng)村開始流動。
(四)差異最小化,文明趨同化
目前,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最大的差異是城鄉(xiāng)居民享受不到同等的公共服務(wù)。但隨著鄉(xiāng)村振興的實施,城鄉(xiāng)公共服務(wù)差異將越來越小。馬克思將勞動者的勞動產(chǎn)品區(qū)分為兩部分,即滿足個人一般消費的部分和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的部分。滿足個人消費的部分是由勞動者及其家屬用來個人消費的部分,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的部分是超出個人消費的那部分,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而不問這種剩余產(chǎn)品怎樣分配”[21]。在《哥達(dá)綱領(lǐng)批判》中,馬克思認(rèn)為,執(zhí)行公共服務(wù)的物質(zhì)來源是剩余勞動,剩余勞動的增加增大了提供公共服務(wù)的物質(zhì)可能,公共物品是集體勞動所得的成果。馬克思認(rèn)為公共產(chǎn)品的范疇包括基礎(chǔ)設(shè)施、保險基金及濟(jì)貧資金等。可見,提供公共服務(wù)和公共產(chǎn)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能,與是農(nóng)村居民還是城鎮(zhèn)居民身份無關(guān)。隨著鄉(xiāng)村振興的推動,鄉(xiāng)村社會公共服務(wù)水平會不斷提升,與城鎮(zhèn)公共管理制度進(jìn)行對接融合發(fā)展[22],與城鎮(zhèn)的差異會越來越小。
此外,我國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提出“鄉(xiāng)風(fēng)文明、生態(tài)宜居”的方針,隨著鄉(xiāng)村物質(zhì)和精神文明的不斷提高,城鎮(zhèn)代表先進(jìn)、鄉(xiāng)村代表落后及城鎮(zhèn)是文明的象征、鄉(xiāng)村是愚昧不發(fā)達(dá)的狀況也將從本質(zhì)上得到改變,城鄉(xiāng)間的文明程度將會趨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