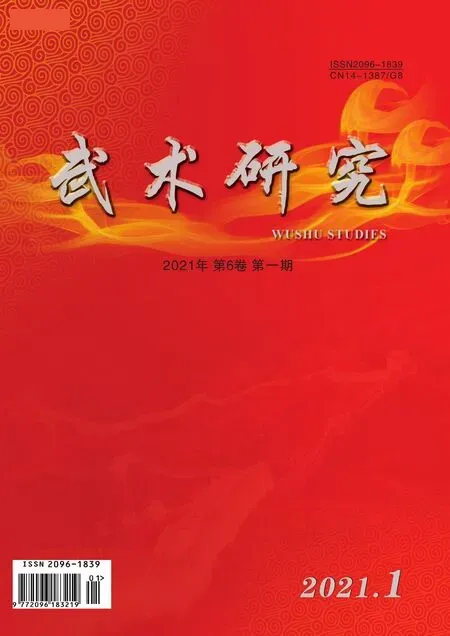大學生參與高校體育俱樂部情況研究
蘇文陽 林昊融
1.大連理工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遼寧 盤錦 114221;
2.北京師范大學體育與運動學院,北京 100875
2019年9月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體育強國建設綱要》指出:大力推動全民健身與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以及大中小學運動隊及俱樂部建設。[1]大學生群體在全民健身中具有特殊地位,高校體育參與度在全民健身活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領導和帶動作用。[2]高校體育俱樂部的存在與發展可反映出大學生的體育意識,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對不同性別大學生參與體育俱樂部主要動機、大學生參與體育俱樂部經歷與運動參與方式關系、大學生參與運動時間及體育場館需求進行調查研究,揭示高校體育俱樂部對大學生體育參與情況的影響為大學生體育參與性別差異、參與形式、高校體育場館使用建議的研究提供參考。
1 研究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結合的抽樣方法,根據我國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六大區域抽取北京師范大學261人;大連理工大學372人;新疆醫科大學172人;山東師范大學120人;中南大學341人;貴州大學125人及其他各高校593人,以高校體育俱樂部對大學生體育參與情況為研究對象,在校學生共計1984人作為調查對象。
1.2 研究方法
1.2.1 問卷調查法
為獲取最新實證數據,本研究問卷發放采用電子問卷將問卷發布在專業在線問卷調查平臺“問卷星”獲得填寫鏈接,收集上述高校大學生參加體育俱樂部情況以及體育參與情況進行調查。共計發放和回收“大學生參與體育俱樂部情況調查”問卷2000份,有效問卷1984份,其中男生990份,女生994份,有效率99.2%。調查初期,擬發放大學生問卷共200份,其中男女問卷各100 份。通過對問卷進行內在信度分析,問卷量表題目可得科隆巴赫系數α=0.750,α系數介于0.7-0.8之間。通過對問卷進行效度分析,得出KMO值=0.642,大于0.6,因而說明數據研究數據信效度在可接受范圍。
1.2.2 統計分析法
在對問卷數據進行整理和錄入的基礎上, 采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 for Windows 17.0進行數據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大學生參與體育俱樂部主要動機分析
如表1所示,“體驗體育運動樂趣”“提高個人組織管理能力”和“健美自身體魄”占大學生參與體育俱樂部主要動機的前三位,其中“體驗體育運動樂趣”占比最高,可見對大學生體育運動興趣的培養是今后高校體育俱樂部發展的關鍵。此外,約23%的同學認為“完成學校(院)要求”及“其他(不明確)”是自身參與體育俱樂部的主要動機。高校體育俱樂部應以“培養學生在體育運動中的運動樂趣”作為俱樂部今后發展和大學生體育參與的重點思考問題。

表1 大學生參與體育俱樂部主要動機

表2 男女不同大學生對參與體育俱樂部主要動機分析
如表2所示,男女不同大學生對參與體育俱樂部主要動機存在一定差異性,“體驗體育運動樂趣”在男女不同大學生中均排名首位,除首要動機“體驗運動樂趣”之外,男大學生認為“提高個人組織、管理能力”為次要動機,而女大學生認為“完成學校(院)要求”為次要動機。可能是由于我國長時間的父系繼嗣家庭制度也許使得大多數男性自幼就具有主動嘗試組織和管理事物的思想,故部分男大學生喜好通過參與俱樂部的形式提高個人組織、管理能力。相對于男性,女大學生更易受到性別因素影響而導致對體育參與情況降低,并且更易遵從學校(院)被動參與,從而非主動參與體育俱樂部。
2.2 大學生體育俱樂部經歷與運動參與方式分析

表3 大學生參與體育俱樂部經歷與運動參與方式
在所調查的1984名大學生中,大學期間參加過體育俱樂部的學生占56.60%,占半數以上。表明現高校體育俱樂部學生參與度良好,但仍有較大可提升空間。大學生俱樂部是大學生活躍思想、展現自我、培養綜合能力的重要平臺。要充分發揮高校體育俱樂部的重要作用,就要提升參與水平,在體育俱樂部參與中,不僅僅要付出時間和行動,還要付出認知和情感。
如表3所示,在大學期間具有參加體育俱樂部經歷的同學運動參與方式中“與同學一起”占比超過六成,其次是以“個人”方式參與運動約占18%,“自由組合”約占17%;在大學期間無參加體育俱樂部經歷的同學運動參與方式中“與同學一起”不足五成,以“個人”方式參與運動約占近三成。
2.3 大學生對體育類社團項目需求分析
在所調查的1984名大學生中,籃球項目占比首位,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學生選擇籃球項目,成為大學生最需求的社團項目;其次為羽毛球和游泳,均超過12%。就不同性別大學生而言,女大學生更偏愛羽毛球和游泳,近五分之一女大學生選擇最需求羽毛球項目。從相關調查中可知,武術在調查對象中項目需求占比較小,僅為3.23%。此外,電子競技超越了2017年度排名第一的足球,成為全球體育行業人士一致看好的最具創收潛力的體育項目,[3]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之下,電子競技項目今后的發展應受到體育界和教育界的廣泛關注。
2.4 大學生參與運動時間和體育場館需求分析

表4 大學生運動參與時間
如表4所示,通常情況下,大學生運動時間最集中于晚上(18時后)時段,下午(14-18時)次之,早上(8時前)、上午(8-11時)和中午(11-14時)較少,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當代大學生入睡時間較晚,且入睡時間有持續移后的傾向,隨著年級的增加睡眠延遲盛行率也越高,[4]為保證一定的睡眠時間,大學生早起人群較少,故晨練人群較少。上午(8-11時)和中午(11-14時)普遍為上課和午休時間,故運動人群同樣較少。
高校體育場館首先應保證在正常教學秩序前提下,多整合符合本校學生需求的集體性項目場館資源以保證大學生體育參與度,例如,籃球場、羽毛球場;并竭力滿足本校學生需求的項目以培養提高大學生運動樂趣,如游泳館、健身房。并且要根據學生運動參與時間,確定運動高峰期,非高峰期可適當節約體育場館資源,如上午和中午時間段可適時適量關閉或半關閉體育場館。
3 討論及建議
3.1 正視并消解大學生性別差異帶來的不平等體育參與情況
建議高校應廣泛采用性別敏感體育參與模式。注重不同性別大學生的共性和差異,考慮男女大學生體育參與的認識和實踐,規避因性別觀念引起的不平等體育參與情況,在體育參與中注融入敏感教育,促使男女大學生在體育參與中成為共性和差異相統一的參與者。加強性別平等宣傳,定期交流研討及存檔備案,并及時給予回饋,不斷完善大學生體育參與性別平等體系,促進高校大學生在體育參與中獲得性別平等的訴求。在大學生體育參與中,先積極促使小部分男女大學生成為共性和差異相統一的體育參與者,之后以點帶面,以面帶全,小部分影響大部分,大部分帶動乃至更多大學生成為共性和差異相統一的體育參與者。
3.2 建議大學生體育參與應以集體形式主動參與為主
集體行動是社會行為的先行者,[5]鼓勵大學生積極參與體育俱樂部、具有體育俱樂部經歷,并且更多的以集體形式參與運動,在體育參與時間和強度等條件一致的情況下,以集體形式參與體育運動對大學生綜合能力有更積極顯著的影響。同時,為了完成學校(院)要求而進行的體育參與往往是非自主性的,故認識和培養的社會行為能力就會相對降低,但以集體形式參與的項目都有一個重要共性:以參與、合作后再競爭的方式進行。這促進了個體間的溝通交流,增進了相互之間的默契行為,且這種行為往往是多維度的,這也是大學生社會性的一種體現,以集體形式主動參與的大學生通過這樣的方式接受到了社會性行為的歷練,獲得了參與社會交際和競爭的機會,因而會形成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
3.3 規劃高校體育場館使用方案保證學生體育參與度
院校學生群體具有特殊性,如師范類院校女生偏多,工科類院校則男生居多,充分及時調研學生對于俱樂部項目需求,了解學生需要,并根據院校自身情況而合理設定項目。明確本校學生運動參與高峰期時間段,保證運動高峰期時間段體育場館開放程度和使用率,高峰期建議多開放學生需求的集體性項目場館,保證大多數大學生的體育參與,同時在非高峰期開放受學生需求項目,通過滿足學生需求,以培養提高大學生運動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