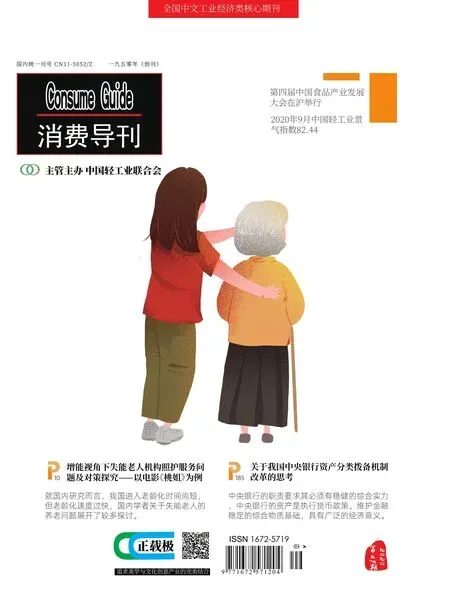增能視角下失能老人機構照護服務問題及對策探究
——以電影《桃姐》為例
李翊銘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
一、研究背景
人口老齡化是當今焦點問題,我國自2005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中國人口展望(2018)》中指出2017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統計結果為1.6億(占總人口數的11.4%),到2033年預計會占比21.0%,[1]而到二十一世紀中葉,我國老年人口甚至會占全球老年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2]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的同時,失能化也日益嚴峻,失能老人數量與速度在不斷增加。“截至2010年末,我國失能老人達到3300萬人,占老年人口的19%”,[3]2018年底已達4400萬人,[4]學者據老齡辦數據預測我國失能老人在2030年將增加至6168萬。[5]且失能老人的養護具有其特殊性,尤其是中重度失能老人,需要專業的生活照料和醫療護理。[6]而在機構養老中,失能老人的照護服務卻存在著諸多問題。電影《桃姐》講述了一個無家庭無子女、因中風帶來失能的老人桃姐在養老機構中安度晚年生活的故事,而養老院中其他失能老人以及與桃姐一樣無家庭的失能老人,她們在該機構中的老年生活質量必然受到極大影響。因此,以電影《桃姐》為例,圍繞電影中的養老院對失能老人的機構養老照護服務展開問題分析及對策探討。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基礎
在國外方面,國外養老機構的服務于管理相對來說比較完善,且十分重視養老機構提供的照護服務。就具體服務而言,西方發達國家的機構照護服務提供主要是以失能老人的照護需求為考慮的。美國半數以上的養老機構能夠提供臨終關懷,醫療服務,足部治療,口腔護理與緊急救助等失能老人急需要的老年服務。多數研究強調失能老人有著更高的醫療護理需求,需要養老機構專業的醫療康復服務以恢復和維持身體功能,同時,有學者強調失能老人也有很強的精神慰藉需求,對于養老機構心理疏導等服務的需求程度同樣很高。[7]國外研究同樣表明養老機構照護服務存在缺乏明確的護理服務標準、精神慰藉服務缺乏對個體異質性的考慮以及機構服務人員短缺等問題。[8][9][10]
就國內研究而言,我國進入老齡化時間尚短,但老齡化速度過快,國內學者關于失能老人的養老問題展開了較多探討,其中有關機構養老模式中的失能老人相關研究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展開。首先是關于失能老人需求的研究。失能老人具有非常高的照護服務需求,普遍自尊心強,自卑和無價值感強,需要日常生活料理、生理療護康復、精神慰藉、社會交往及臨終關懷等。[11][12]其次是關于失能老人機構養老困境研究,總體上呈現機構養老服務與老年需求不適應的矛盾,具體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在機構的服務項目方面,所提供的照護服務不全面,內容較單一,多集中在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上。市場上大多數養老機構尚不具備完整的“養護醫送”相結合的養老服務,[13]如在對北京市養老機構的研究中發現有七成無法提供妥善的醫療服務。[14]此外,失能老人存在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但多數入住老人精神文化單一且專業的心理疏導工作缺失;[15][16]在機構的服務人員方面,養老機構內專業的老年護工缺乏,且護理人員的年齡與性別結構不合理,專業度缺乏,機構的管理人員能力也有所欠缺;[17][18]在機構的服務設施方面,養老機構內存在著機構床位數不足的問題;[19]在機構服務的收費方面,養老機構提供服務時的成本費用遠遠超過保險可提供的補償費用;[20]其三是關于失能老人機構養老照護問題的對策研究,學者們多從以下幾個角度展開。第一是從政府責任的角度,政府應當明確不同類型養老院的定位,解決養老機構資金問題,加大政府投入等;[21]第二是從養老機構發展模式的角度,強調推進“醫養結合”型養老模式,實現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間的多方式結合、優勢互補,[22][23]同時,通過推進“醫養結合”進一步提升養老機構的服務質量;[24]第三是以構建失能老人長期照護體系為核心發展機構養老,與其他模式相比,機構養老模式在提供專業性養老服務方面存在優勢。[25]應當研究發展老年護理保險等相關配套措施和政策,以及通過吸納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協調社會機構各個部門等方式發展養老機構的照護服務。[22][26]
增能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學者Solomon提出,強調的是個人對自身及自身所處環境的控制力,通過外部干預增強個體的能力及對權力的認知,以削弱無權感。[27]在我國本土社會工作中與優勢視角相結合,強調通過增能幫助服務對象增加權力感。需要激發弱勢群體潛能,提高其社會參與能力,擴展利用外部資源幫助其解決問題。[28]具體的增能路徑包個人層次的自我效能感提升,人際層次的社會支持網絡的搭建,以及環境層次的改變阻礙能動性發揮的制度規則。基于此路徑,通過內外力的推動模式實現弱勢群體的增能。[29]綜上,以《桃姐》為例,基于增能視角圍繞失能老人機構照護服務展開探究。
三、養老機構中失能老人的需求
失能老人具有高齡、患有高風險疾病的特點,基于電影《桃姐》,對養老院中失能老人的需求進行總結,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照料、醫療護理、精神慰藉及資金保障四個方面。
(一)日常生活照料需求
個體衰老的過程包括生物與社會方面,與生物方面衰老密切相關的即是失能老年人數量的不斷增多,需要更多的生活照料服務。進入老年期后,身體機能不斷下降,人體各組織器官不斷老化,同時,各類高風險老年疾病極易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及自理能力出現斷崖式下跌。影片中桃姐也是由于罹患中風這一高風險疾病而出現自理能力的下降,右手無力無法完成一些日常活動,無法再擔任從前的社會角色“家傭”,且需要在養老院中由專人照顧。在養老院中,上廁所這一基本日常生活活動也需要艱難完成。在二次中風后,幾乎完全喪失行動能力,需要被繃帶捆在輪椅上出行。養老院中的其他老人一樣,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日常生活照料服務。
(二)醫療護理需求
醫療護理需求對失能老人來說是重要的需求,首先,因中風、高血壓等老年疾病導致的失能需要進行必要的康復復健,其次,失能老人極易再次罹患高風險疾病造成身體機能的再度損傷,必要的醫療護理服務可以基本維持失能老人身體的正常運轉以及緩解生理上的痛苦。影片中桃姐在中風后右手無力需要進行康復復健,同時,還經歷了二次中風不得已再次住進醫院,這一現象不僅表明與自理老人相比,失能老人在醫療護理方面有更高的需求,同時向養老院的醫療護理服務提出了要求。桃姐有雇主家庭的支持得以在醫院與養老院中往返并及時治療,養老院中其他不具備如此條件的失能老人在出現意外或是罹患突發性疾病時極易威脅到生命。同時,若日常復健缺失也不利于病情穩定與老年生活質量的維持。
(三)精神慰藉需求
由于年老所帶來的角色中斷、角色轉變等會使得老年人產生精神上的空虛感、寂寞感以及孤獨感,對于失能老人來說,由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帶來了自卑感和無價值感,對精神慰藉的需求程度更高。影片《桃姐》中有諸多老人自住進養老院始便沒有子女探望,社會上的志愿者來探望老人在臨走時還會帶走月餅,更凸顯了養老院中老人尤其是失能老人的落寞與孤獨。桃姐同樣屬于養老院中失能老人,但是其得到雇主家庭極大的精神支持和撫慰,而其他失能老人自身行動不便、遭受身體疾病折磨,更渴望得到來自朋友、家人以及社會的精神撫慰。因此,失能老人的老年生活質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其精神訴求是否被滿足,以及其獲得的精神支持、精神養老的內容。
(四)資金保障需求
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貧困問題也在不斷凸顯,失能老人作為弱勢群體更易被剝奪,同時,機構中養老的失能老人需要醫療護理等治療費用。影片中老人院的開支與桃姐的退休金形成巨大反差,若桃姐沒有雇主家庭經濟支持,其在養老院中很難負擔起各項服務費用,養老院中同樣有因無法擔負尿毒癥治療費用而離去的人,作為失能老人,日常照料及醫療護理是必要需求,若因經濟負擔未能滿足便極易影響其老年生活質量。因此,在機構中養老的失能老人對資金保障有著更高的需求,尤其是無家庭或被家庭所遺棄的失能老人,若缺乏有效的資金保障、不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那么其他類型的需求滿足程度同樣會受到影響。
四、失能老人機構照護服務問題
影片中桃姐居住的是一家私營養老院,該養老院中居住有許多和桃姐一樣的失能老人,但其所提供的機構照護服務存在著各種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服務設施與環境簡陋
中國養老機構尤其是絕大部分的民辦養老機構都以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服務為主。據2010年“失能老年人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在城鄉178個養老機構中,有醫療室的政府辦機構占52.1%,民辦機構為56%,近一半的機構沒有專門的醫療室以及康復理療室。[21]在電影中,首先,服務設施方面,硬件設施配備缺乏,未設有專業的醫療室及康復理療室,更不具備康復護理器材,不能滿足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人的醫療護理服務的需求,同時,設施的布局缺乏規劃,整個養老院內空間狹窄擁擠,也并未進行功能區的劃分,院內失能老人無論是居住、吃飯或是出行都存在著不便;其次在養老院的環境方面,第一,環境衛生條件較差,例如影片中的吃飯場景中失能老人吃飯時缺乏照料和看護,甚至出現吃飯時拿錯假牙的情況。第二,居住環境較差,居住空間用木板隔開,即使是失能老人也需要群居,不僅隔音不好影響睡眠,公用的廁所和洗澡間不見陽光且通風不暢,嚴重影響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人的生活質量。
(二)服務類型單一
首先,養老院只能滿足失能老人基本的日常生活照料需求,而未能提供更多的醫療護理服務以及精神慰藉類服務。其次,未能針對不同類型的老人進行劃分以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類型,而是統一管理,失能老人亟需的醫療護理服務未能有效提供。桃姐在初入養老院時也因目睹院內老人尤其是失能老人的生活狀態而對機構養老生活產生抵觸抗拒的心理。養老院內不乏有坐在輪椅上每天孤獨的望著窗外的老人,以及未能得到很好的醫療護理而突然離世的老人等等,其中,影片中的堅叔的不正常行為也是在通過畸形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需求,轉移自己精神上的空虛和孤獨,自理老人尚且如此渴望滿足精神需求,更不用說遭受失能痛苦的失能老人。因此,該養老院的服務類型單一也影響著院內失能老人需求的滿足。
(三)服務方式缺乏規范化、人性化
一方面,服務方式缺乏規范化。養老機構中失能老人數量的增加帶來了照護服務需求的上升,同時,養老照護服務更需要較強的專業性,因此需要對不同程度失能老人的照護標準進行分類細化,然而影片中的養老院卻缺乏系統性、針對性及可操作性的照護標準體系。在系統性層面,失能老人的服務需求涉及醫療、飲食、環境、生理心理等各個層面,都有相應的標準,而在該養老院中顯然缺失標準規范;在針對性層面,不同程度的失能老人相應的服務標準的制定也是不同的,在該養老院中未將自理老人與失能老人劃分開來,更未能對失能老人的類型進行劃分并確立相應的服務標準。另一方面,服務方式缺乏人性化。首先,影片中養老院呈現的是機械化的服務方式。例如在吃飯場景中,失能老人坐在一排等待護工喂食,而護工則采用機械化的動作一一遞勺喂食,不帶任何感情的完成流水作業,甚至隨意訓斥,把失能老人當作物品對待,這更易讓失能老人產生自卑感,影響其自我效能感;其次,社會給予養老院中失能老人的是形式化的慰問關懷服務。社會志愿者及媒體前來慰問老人也已然把老人們當作營銷宣傳的工具。
(四)服務管理缺失
首先是對養老院內護理人員的管理,在護工數量方面,院內護工缺乏往往身兼數職,這同樣影響了服務的質量;在護工專業方面,其在向失能老人提供照護服務時缺乏人性關懷甚至有虐待老人傾向,缺乏專業的培訓,而失能老人更要求專業的照護服務,護工提供服務的專業度缺失更反映養老院管理的缺失。其次,在該養老院的定價方面,該養老院的收費五花八門,例如養老院老板表示陪診費根據不同老人的身份則有不同的收費。在這樣條件和環境下的養老院依舊收費定價不菲且標準雜亂也是其管理缺失的表現。綜上,失能老人原本就是生理功能衰弱的群體,養老機構照護服務的諸多問題更使其在日常生活照料、醫療護理及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未得到很好滿足,從而對養老機構缺乏存在歸屬感、對社會缺乏參與度,進一步削弱了養老機構內失能老人的社會支持網絡,影響其在養老院內的老年生活質量。
五、失能老人機構照護服務問題原因分析
(一)政府監管缺失、制度建設不足
首要原因是政府的重視不足,體現在監督監管缺失、引導規劃缺失及制度建設不完善三個方面。首先在政府監督缺失方面,電影初始因為養老院的服務設施不健全,老板娘找了打手裝扮的老板出來對付羅杰。這一事件直接反映出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無力。政府對養老機構尤其是私營養老機構的監管不足,使私營養老機構呈現單向度的運作方式,服務設施環境、服務內容標準不達標、服務定價不合理的養老機構仍得以持續運轉,進一步影響失能老人的生活質量。在引導規劃缺失方面,政府缺乏對不同類型養老機構的規劃及對其發展的引導,對于受眾包含失能老人的養老機構也缺乏政策性的扶持,如專項補貼、床位補貼等,這使得不同養老機構的職能和定位不明確、發展路徑不清晰,而采用統一的管理方法,養老機構并未針對失能老人進行專門的規劃和管理,其成為邊緣的弱勢群體。
在制度建設不完善方面,首先體現在養老機構照護服務制度的建設和落實缺失,需要對失能老人養老機構照護服務的開展進行管理和規范,包括對機構所提供的照護服務標準與內容的規制,制度的缺失和不健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管理的松懈和重視程度的不足,也使私營養老機構鉆空子運營。其次體現在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未能對失能老人進行全方位的覆蓋保障,和桃姐一樣無家庭無子女卻沒有雇主家庭眷顧的失能老人便會面臨經濟負擔而無法接受必要的服務。
(二)養老機構定位理念偏差
在政府監管及制度缺失的背景下,養老機構尤其是私營養老機構自身的運營理念及定位偏差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監督真空的狀態下,私營養老機構往往營利至上而忽視社會服務的屬性。影片中的養老院資金足夠卻并未用資金來發展養老機構的設施、改善服務環境、擴充服務隊伍,而是坐收盈利,這也是對機構的定位偏差的表現。在這樣的機構定位和運營理念下,老人尤其是失能老人的生活狀態與困境并不會引起機構的關注,不同類型老人的服務需求不是機構提供服務的出發點,因而機構提供的是單一的服務類型與服務內容,護工的服務方式也是機械而缺乏人性化的。同時,這也影響著養老機構對服務資源的有效整合,未能充分調動和運用社會力量,不同的養老機構間呈現競爭關系而不是相互溝通幫助。
(三)社會監督缺位
社會同樣應當在養老機構的運營中扮演監督者的角色,但是在電影養老院中呈現的是社會監督的缺位。形式化的探訪背后原因即是社會監督的缺失。社會各類民間組織或機構應當在探訪養老院的過程中發現并提出問題、及時監督,從而反映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人真實的生活狀態,這是對養老機構服務的監督,而社會組織的訪問和探訪流于形式,監督同樣流于形式,養老機構的服務模式得到默許,更不利于其服務設施環境、服務內容、服務管理等的改善,同時更影響失能老人的生活狀態與生活質量。綜上,私營養老機構在各方監督缺位、制度漏洞的環境下運營,進而形成了阻礙失能老人個體能力發揮的外部環境,而失能老人因生理能力限制,再加上在機構中照護服務問題的持續累積,在內外力共同作用下則將持續處于“無權”的弱勢地位。
六、完善失能老人機構照護服務的對策
基于增能理論視角,從外力推動及內力推動兩個方面提供完善失能老人機構照護服務的對策。在外力推動方面,從政府及養老機構及社會三個層面展開。
(一)政府加強管理、建立健全相關政策
就外力推動中的政府主體而言,首先在管理層面上包括兩點,第一,明確養老機構的職能定位、推動其分類發展。政府應當對不同類型養老機構的發展進行統籌規劃,通過公辦民營或民辦公助的形式,建設具有醫療護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基本照護服務的養老機構,以此保障機構中低收入失能老人的照護服務需求,而對于經濟收入較好、服務需求較高的老年群體,則可以由市場根據其需求提供相應的機構服務;第二,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加強監督管理。政府作為管理社會的權力部門,應當依據法律法規及政策進行服務質量、服務價格等方面的監督,防止出現如影片中私營養老院違規運營的現象。其次,完善養老機構相應的考核評估標準,規范養老服務市場的準入制度,在政府加強監管的同時通過市場競爭機制淘汰養老服務質量低下的養老機構。
在政策層面上,主要包括三點,第一,完善機構照護的服務標準并以政策形式落實。對養老機構服務的提供標準、管理標準等方面予以統一規范,形成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提高其對不同類型失能老人的針對性,更重要的是予以標準法律強制力,以保障標準的強制性;第二,完善對養老機構扶持性的社會政策,失能老人的護理成本更高,需要區別于常規養老機構的扶持性政策。影片中的私營養老機構若是大力發展專業護理型,可能不具備服務條件,需要政府出臺資金、人員培訓及床位補貼等方面的扶持性政策,支持其加強對失能老人的照護服務;第三,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建立長期照護保險。我國現行保障制度無法支持大部分失能老人的醫療護理等費用,借鑒國際經驗,推動建立納入社會保險體系的長期照護保險制度,根據不同類型失能老人及不同地區的差別,推動商業照護險和社會照護險相結合,減輕失能老人的護理費用負擔。
(二)推動養老機構照護服務體系化建設
養老機構自身應當第一,明確機構的職能定位,落實服務標準政策。養老機構尤其是私營養老機構更應當明確自身的職能定位,自覺落實機構照護服務的相關標準,尤其是與失能老人密切相關的日常照料服務、醫療護理服務等,并依據本機構的特殊性進行標準可操作性的調整和補充;第二,吸納社會力量參與到服務建設中,社會力量在機構失能老人的照護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失能老人的機構照護服務可以與社會志愿服務相結合,但需要保證志愿服務的連續性以及社會互動的質量;第三,以失能老人的需求為出發點提供針對性服務。對不同類型的失能老人進行需求評估,提供多元化、多層次的照護服務而非單一性服務;第四,加強對高水平護理人才及社工的培育。加強對機構內護理人員的護理知識、技能的培訓,提升其專業度,確保失能老人的照護服務質量,同時加強社工隊伍建設,由專業社工輔助志愿者團隊,精準識別失能老人的需求,為機構內失能老人制定有針對性的干預和增能計劃。
(三)發揮社會及家庭監督的作用
家人同樣是能夠直接接觸到養老院的監督主體,其與政府的宏觀監督相比更具連續性也更深入,更能及時發現失能老人在養老機構中的困境和問題。而影片中不少失能老人的家屬自將老人送進養老院后便再未進行探視,或因忙于工作,又或是親情淡薄,皆加劇養老機構肆無忌憚的運作。因此,家人應當時常關注老人在養老院的生活狀態,保持對養老機構的日常監督,從而確保養老機構服務質量。另一方面,對于更多和桃姐一樣無家庭無子女的失能老人而言,他們更需要社會中的民間組織發揮監督作用,民間組織有著更豐富的資源和能力,其可以通過第三方視角對養老機構進行全方位的評估,但是電影中形式化的慰問暴露出社會中的民間組織在助老服務中的認知偏差和能力缺陷,將其當作自身宣傳營銷的工具。因此需要民間組織在認知和能力上進行優化,正確認識助老服務的本質,而后再進一步發揮對私營養老機構的社會監督作用。在政府、養老機構、社會及家庭的共同作用下,通過外力推動為失能老人建立起正能量的場域環境,同時要通過內力推動即社會工作者對失能老人的介入實現增能意識的內化,幫助失能老人改變相對弱勢的地位。
(四)加強支持網絡建設,實現失能老人自我增能
首先需要加強失能老人的社會支持網絡建設,包括機構內失能老人與朋輩群體、與家人以及與護理人員的關系建設。在朋輩群體支持方面,結合機構內失能老人的情況進行類型劃分,針對輕度失能的老人推動建立興趣愛好小組,同時探索失能老人間的互助模式,引導建立輕度失能老人與中重度失能老人互助、自理老人與失能老人互助的模式,從而幫助失能老人搭建朋輩群體支持網絡;在家庭支持方面,社工加強與失能老人家庭的聯系,輔助機構內的失能老人通過視頻或電話的方式定期與親屬進行溝通互動,讓失能老人感受到家庭、親人的支持和關懷,使其精神慰藉需求得以滿足。其次,失能老人雖然是弱勢群體,但增能路徑強調的即是從問題視角向優勢視角的轉變,從而激發失能老人的潛能,幫助其提升自我效能感,找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因而在提供照護服務、干預介入的過程中應當通過適當的方式幫助失能老人認識發揮自身的優勢,傾聽是基礎性工作,鼓勵老人傾訴,并與其一起回顧生命歷程中的快樂,找到生命的價值、樹立正確的生死觀念并開始積極的晚年生活。同時注重失能老人間的差異性,從興趣愛好切入幫助失能老人增強自我認同感而減少對自己的負面評價。綜上,基于增能視角,在外力推動模式中從政府、養老機構、家庭及社會層面營造利于失能老人發揮自我效能的場域,同時在內力推動模式中通過社工的干預促進失能老人增能意識的內化,以幫助失能老人改變相對弱勢的地位。
七、小結
基于電影《桃姐》,對失能老人機構照護服務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立足增能視角,改變失能老人的“無權”狀態需要通過外力與內力共同推動,通過個人層面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人際層面社會支持網絡的搭建以及環境層面種種阻礙因素的破除實現失能老人的增權,更滿足其在養老機構內的養老需求,以真正保障養老機構內失能老人的老年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