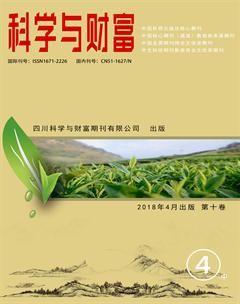鐵路路基維修養護管理技術探討
姜建秋
摘 要: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都在持續發展進步,在這個過程當中,交通運輸起到的作用更為明顯,同時在各個領域當中,交通運輸的需求總量也在不斷提高。在整個交通運輸系統當中,鐵路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設施,在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之中一直被譽為大動脈。但是在長期運行過程當中經常容易出現一些質量問題或者直接造成損壞,所以我們應該做好養護工作個,這樣才能給我國鐵路運輸系統帶來更高的安全性。本文首先針對鐵路路基常見的病害情況進行了分析,之后結合實際情況提出了一些可行的維護對策,希望可以給相關工作的開展提供一些參考。
關鍵詞:鐵路路基;維修養護;方法
在鐵路設施沒有使用的時候會承受一定的靜荷載,但是有列車駛過的時候就會承受動荷載,在這個過程當中,是通過地基將荷載向地面深處進行傳遞的,所以如果其出現不穩定和不牢固的問題將會直接給整個路面的穩定穩定性造成影響,所以相關部門應該對這項工作給予有足夠的重視,提高整個路基結構的抗侵蝕能力,采用有效手段來開展維修工作和養護工作,這樣才能不斷提高整個工程的質量,既可以讓整個使用壽命得到延長,同時還能不斷提高整個工程的穩定性,讓整個工程可以最大限度上發揮出自身的作用來。
1 當前階段鐵路路基維護工作當中出現的問題
1.1 重視程度不足。鐵路工程本身具有著里程長、范圍廣的特點,其鋪設的范圍非常廣泛,河流上、平原上、丘陵山地和高原都有分布,其中設計到的學科是非常廣泛的,不僅僅有力學和地址,還有水文等學科知識的要求,所以這樣看來,自然因素對其造成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在外力影響之下就很容易導致出現病害,如果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將會直接導致整個線路質量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其運營情況。其實很多管理部門并不重視路基養護的相關環節,內部管理工作運行不暢,這也會直接影響到其工作的積極主動性。
1.2 人員配備方面的問題。現階段我國進行的鐵路的維修和養護大多仍然局限在上部建筑上,對于路基的維修和養護不僅程度非常不足,技術水平也不過關,同時從另一方面來看,鐵路維修人員配備不足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現階段工區段管轄范圍還在不斷擴大,如果單純針對鐵路的上部建筑進行維修,恐怕仍然是難以得到要領的,同時也由于人手不足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多的工程的維修工作都流于形式,認真仔細的維修開展起來難度很大。
1.3 建設過程中的質量問題。在進行路基線路的建設過程當中,路基鋪設完畢之后,施工所需要動用的車輛就直接從路基上行駛運輸材料,在這個過程中就會出現很多問題,例如路基填料受到影響、出現了板結問題,在整個線路當中導致了嚴重的翻漿,同時還有很多路基的隱蔽工程的施工過程中會挖掉大量棄土,但是其內部結構空隙是很大的,在運營過程當中出現沉降問題,也會給后續的維護工作帶來很大的難度。這些現象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在建設過程中就缺乏完整的質量意識,經常是治理了先前的問題,但后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給維護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2 鐵路路基的作用
2.1 關于鐵路路基的作用探討。對于整個鐵路來說,鐵路路基屬于基礎的作用,最為直接的就是能夠直接承載軌道和列車的重量,并且在運行過程當中將自身的重量擴散到地基深處當中,和整個鐵路共同構成了一個結構。對于路基來說,最重要的衡量指標就是鐵路系統運行的安全性和穩定性,所以路基能夠保證列車的安全,在整個交通運輸體系當中作用都是很大的。
2.2 路基工程的特點。路基其實是一種建筑在巖土地基之上的巖土結構。巖以及土都是不連續介質,有著一定的破碎性、孔隙性以及多相性,其性質也具有復雜多變性,不僅僅因為線路通過的地形、地質條件不同而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即便是相同一種巖土,因為氣候變化、水位漲落、受力情況等等變化也都會導致其對工程性質產生一定的影響。路基完全暴露在大自然之中,因此其工作環境比較惡劣。在鐵路的延伸,路基通常遇到的是各種地形、地質、水文、氣候以及地震區劃等等條件完全不同的工作環境,所以,在進行路基的設計、施工以及養護工作之時,不能同當地具體的自然條件分開。
3 鐵路路基病害類型及原因
3.1 翻漿冒泥。翻漿冒泥是比較常見和突出的路基病害形式,當鐵路道床和基床某些部分所用土質不符合要求或遭受污染時,一旦降雨形成不利條件,就容易發生翻漿冒泥。翻漿和冒泥是不同作用機制導致的道床基床常見病害,主要是道床臟污和土質基面或風化石質基面被水侵蝕軟化雨后積水無法排除,導致的泥漿擠壓冒出,相對來講,冒泥會導致基床的永久變形,危害也較大,由于翻漿冒泥嚴重導致枕木破壞、鋼軌折斷的事情也偶有發生,因此對行車安全的影響是巨大的。
3.2 路基下沉。當路基的填筑密度、強度均小于要求時,就會出現路基下沉、道碴囊等,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作路基下沉。由于路基下沉而最終使得路基斷面尺寸發生改變,我們稱這種現象叫路基沉陷病害。組成的路基的土必須滿足強度和密度要求,如果密度不夠,或者強度不足,再加上雨水,重載列車通過時產生的振動,就會發生基床、堤體或者基底下沉現象。
3.3 擠出變形。路基擠出變形形式最常見的有路肩隆起、側溝被擠,路肩外擠和邊緣外膨四種。造成擠出變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土體強度不足,列車行駛過程中產生的振動通過道床傳遞給路基,加上一些降水或地下水,久而久之導致處于軟塑狀態的路基土發生外擠變形。
3.4 邊坡沖刷。邊坡沖刷主要發生在多雨地段,按照沖刷后果可以分為:邊坡淘刷和邊坡沖溝。邊坡沖刷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植被護土不良,路塹路堤邊坡上的土質受到雨水水路沖刷,導致邊坡上的泥土遭受侵襲流失,逐漸形成路塹、路堤的邊坡沖溝,嚴重者可能發展成為邊坡沖鋸。邊坡沖刷多發生在新建線路,我段管內設備發生路基邊坡沖刷較少,只在新頂進涵洞、地道橋等對路基有破壞的施工地段,偶有發生。
3.5 陷穴。鐵路運行距離較遠,常常需通過不同的地質帶,進而存在不同程度的黃土陷穴、巖溶洞穴、鹽蝕溶洞和墓穴獸洞等陷穴病害。雖然大秦線在鋪設時已經對此進行了充分的考慮與整治,暫時不存在陷穴的病害,但不排除在施工工程中存在沒有發現的洞穴,特別是近幾年地殼運動造成地震頻發,陷穴這一病害的存在也勢必要提前防御。一旦隱形的空穴造成陷穴沒有及時發現或處理時,就可能會引起基床和道床塌落,引起道床或軌道的懸空,甚至可能導致列車顛覆。
4 鐵路路基維修養護的常用方法
4.1 表層原位壓實法。對于壓實度不足的鐵路路基,采用表層原位壓實法,通過機械或者人工的方式對鐵路路基表層進行振動、夯實、碾壓等密實處理,加固鐵路路基,提高路基的承載能力和地基強度,減少路基的沉降量,提高路基結構和路面表層的承載力,表層原位壓實法可以用于處理鐵路路基的淺層土體。
4.2 強夯法。強夯法也可以成為動力壓實或者固結法,對鐵路路基采用強夯法,主要是使用很重的力氣,反復地擊打路基土層,給路基以巨大的振動和沖擊,提高路基的壓實度,降低壓縮性,從而保障鐵路路基的強度。
4.3 碎石樁法。碎石樁法是通過水沖、沖擊或者振動等方法,在鐵路路基中鉆孔,然后將碎石或者砂石擠壓到路基孔中,從而形成碎石樁,這種方法可以有效提高鐵路路基的密實度和強度。
4.4 釘形雙向水泥土攪拌樁法。釘形雙向水泥土攪拌樁是一種重要的路基維修養護方法,在水泥土攪拌過程中,利用動力系統,外層同心鉆桿和內層同心鉆桿上的旋轉葉片,同時進行旋轉攪拌水泥土,形成水泥土攪拌樁,這種方法主要被用于粉土、粉質黏土、淤泥土和水分較高的黏土等路基土層中。
4.5 混凝土預應力管樁。混凝土預應力管樁是指在路基中添加活性減水劑,施工預應力,離心蒸汽高速養護工藝中采用細長空心的預制樁,將地基荷載傳給具有抗壓性能和抗彎性能的受力桿件,加固鐵路路基邊坡和軟弱地基。
5 結束語
其實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整個交通運輸系統所承擔的壓力越來越大,而鐵路在交通體系當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能夠影響到整個路基穩定性的因素有很多,這其實就需要我們采取有效手段提高整個工程結構的穩定性,并且重視日常的監測工作,將整治和預防這兩項內容結合起來,避免鐵路路基的病害嚴重和擴大,在最大限度上延長其使用壽命,保證整個鐵路路基的穩定性才能給我國鐵路運輸的發展帶來更大的推動力。
參考文獻
[1]胡浩幫.探析鐵路路基的無損檢測與養護維修[J].卷宗,2017(15).
[2]駱武偉.長吉城際鐵路路基養護維修對策與建議[J].中國鐵路,2016(8):30-32.
[3]杜君.鐵道線路養護維修問題與管理措施分析[J].工程技術:引文版,2016(8):00077-00077.
[4]吳仲倫.高速鐵路路基凍脹對軌道不平順的影響分析及動力響應[D].北京交通大學,2015.
[5]賈維慶.風沙地區某鐵路路基綜合防沙減沙體系研究[J].鐵道勘察,2016,42(6):57-59.
[6]尹紫紅,朱波,楊明,等.超重貨物作用下的鐵路軌道路基響應機理研究[J].鐵道標準設計,2017,61(7):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