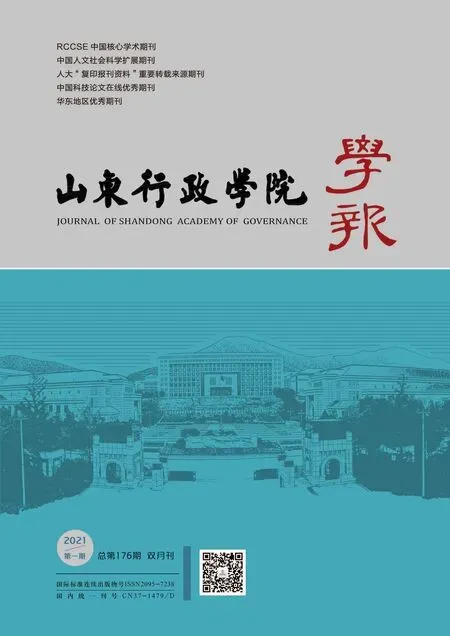西方激進型協商民主的理論前提批判
池忠軍
(中國礦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西方協商民主與中國的協商民主雖然共用一個詞匯,這種同名雖然具有偶然的巧合機緣,但卻表達了不同的意涵。西方協商民主理論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話語,學術指向有不同的派別,但對我國影響較大的是“話語民主”理論途徑的“激進型協商民主”,它所依賴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市民社會”。有些學者已經指出了西方協商民主僭越中國內生的獨特的協商民主的危害性,但還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市民社會理論上,揭示其文化市民社會這一理論前提的謬誤,在理論淵源的深層揭示西方話語民主的意識形態戰略,惟此,方可看清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實質差別。
一、西方協商民主的理論激辯與激進型協商民主理論的興起
西方學者共用“Deliberative Democracy”這一語詞,中文都可以翻譯成“協商民主”。但協商民主只是一個論域,論題的不同協商民主的概念也不同。從論域來看,對“民主的不滿”是西方協商民主共同的問題域;從論題來看,可以厘清三種協商民主的理論路徑:傳統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的辯護解釋論、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建構論、左翼自由主義話語民主的“文化市民社會”建構論。
美國學者畢塞特于1980年首次用“Deliberative Democracy”這一新概念表達美國憲法中內涵的一種民主思想。這與西方民主概念的諸如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共和民主(Republic Democracy)等形成很大差別。“Deliberative”這一概念有兩層詞典含義:對個人理性來說,主要體現審慎的、深思熟慮的;對群體來說,是商談的、討論的、協商的、審議的、評議的等。將兩個層次結合起來的協商民主,就包含民主參與中的個人理性運用于公共理性的建構邏輯。畢賽特為什么用協商民主表達美國憲法精神所內涵的民主理論?用意何在?從社會背景來看,與西方國家的民主浪潮密切相關。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形成了強烈反抗自由民主制度的沖擊波,這是民主制度遭遇激進民主沖擊的集中表現。這股沖擊波的持續引起學者們對西方自由民主制本身的高度關注。就問題的歸因來說,形成兩種相反的判定:一種是,所謂的代議制就是現代“貴族制”“精英制”;另一種是,大眾民主形成了多數暴政。畢塞特的歸因是后者。他認為民主的亂象違背了立憲者們的初衷而致大眾民主的無序。畢賽特使用協商民主概念,是指“議會”中的代表之間的協商,既代表了多數又限制了多數。但問題就出現在代表的個人理性能否生成公共理性?代表被選舉與選舉人聯系的中斷,選舉人的意見被拋棄或被過濾、篩選,代表奉行了私人理性,議會的協商終究還是利益集團的爭斗。因此,畢賽特基于傳統自由主義的協商民主解釋是乏力的,出現了有少數的協商而非民主的困境。
新政治自由主義的代表羅爾斯,繼承和發展了康德的“理性公開運用”的思想,在公共理性維度上闡釋了協商民主思想。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啟蒙時指出:“我回答說:必須永遠要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私下運用自己的理性往往會被限制得很狹隘,雖則不致因此而特別妨礙啟蒙運動的進步。而我所理解的對自己理性的公開運用,則是指任何人作為學者在全部聽眾面前所能做出的那種運用。一個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職崗位或職務上所運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稱之為私下的運用。”(1)[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25-26頁。在這一認知的途徑上,羅爾斯認為,私人理性是不可能生成公共理性的。公共理性是基于正義原則的公共政治推理所獲得;而私人理性是世俗理性,它是基于多元的社團的信仰、價值和生活觀念的理性;世俗理性是非政治的,也不可通過民主程序獲得公共理性,相反,社會主體的相互尊重和平等需要公共理性的維護(2)[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增訂版)》,萬俊人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420-421、416、416頁。。羅爾斯將西方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影響的民主政體的動蕩,在經驗上歸因于私人利益加總即公共利益的功利主義邏輯,試圖以公共政治推理的可靠邏輯獲得公共理性,使民主政治制度獲得正義的規范,因而規范立法、執法、政治論壇、市民論壇,使其整合在公共理性的公共性維度上。羅爾斯認為“協商民主的明確的理念,即是協商本身的理念。”(3)[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增訂版)》,萬俊人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420-421、416、416頁。民主是政治的范疇,協商民主也只能是政治制度的問題,協商的可能性在于三個要素的缺一不可:公共理性的理念、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公民們普遍具備遵從公共理性的理想、知識與愿望(4)[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增訂版)》,萬俊人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420-421、416、416頁。。從羅爾斯基于公共理性維度的協商民主理論來看,將先驗的嚴密的形而上的邏輯推理的公共理性觀念嵌入民主政體是他的方法論。
哈貝馬斯、科恩、曼寧等相互援引將協商民主引向社會建構,推動了文化市民社會建構論的協商民主理論研究途徑。科恩認為,“民主并不專門是一種政治的形式;它是一種社會和制度安排的框架。”(5)[美]喬舒亞·科恩:《民主與自由》,約·埃爾斯特:《協商民主:挑戰與反思》,周艷輝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185頁。“協商民主的觀念來源于民主社團的直觀理想,在這種社團中,其條件和狀態的正當性是通過平等公民之間的公開爭論和推理而實現的。”(6)[美]伯納德·曼寧:《論合法性與政治協商》,陳家剛:《協商民主與政治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47頁。實際上,科恩并不是忽視利益集團操控政治、政黨斗爭的經驗事實,而是從這種經驗事實中推不出協商民主;只能“通過闡釋理想的協商程序而追求一種更實質性的協商民主表述。”(7)[美]伯納德·曼寧:《論合法性與政治協商》,陳家剛:《協商民主與政治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47頁。法國學者曼寧,在對傳統自由主義將法律合法性作為民主的前提批判基礎上,將民主合法性的“全體一致”確立為個人自由、自主的根基,由此確認“作為合法性基礎不是他們業已確定的意志,而是他們決定他們意志的過程。這就是協商的過程。”(8)[美]伯納德·曼寧:《論合法性與政治協商》,陳家剛:《協商民主與政治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41頁。哈貝馬斯吸收了科恩和曼寧的協商民主思想,將文化的社團理論納入到話語民主理論之內,構建介于市場經濟與政府之間的“文化市民社會”作為政治的公共領域,在功能上它既限制政府權力又限制利益集團僭越政治的權力。哈貝馬斯基于文化市民社會理論的對話式協商形成了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主流。這一派別試圖重構“激進型協商民主”的新范式,形成具有世界意義的潮流。
激進型協商民主理論有其生發的關鍵事件和背景,“始于對自由民主規范實踐的批判。作為一種具有潛在影響的改革和政治理想計劃,協商民主延續著‘激進’民主的傳統。不過,它延續的方式是通過強調公共討論、推理和判斷來調和激進的包容性的人民參與觀點”(9)[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協商民主:論理性與政治》,陳家剛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1頁(中文版序言)。。美國學者本哈比指出了協商民主的一個意識形態計劃:在1989年“柏林墻”被推倒,弗朗西斯·福山做出了“意識形態終結”和普世性的自由民主政體是人類社會的最后形式的判斷之后,西方新一波的民主浪潮再次興起的經驗證明此預言是一種謊言,“這些說明,‘自由民主的普世化遠未完成’”(10)[美]塞拉·本哈比:《民主與差異:挑戰政治的邊界》,黃相懷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2、3頁。,而協商民主是解決民主困境的最好選擇。協商民主對西方的民主國家來說是政治公共領域的重建;對處于族群民族政治的非民主國家來說,“尋求的是重新界定政治體制的構成,并且意在創造出新的政治性主權機構”(11)[美]塞拉·本哈比:《民主與差異:挑戰政治的邊界》,黃相懷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2、3頁。。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思潮作為自由民主普世化的意識形態戰略,也在尋求可普世化的協商民主語詞。澳大利亞的德雷澤克指出,話語民主更具普適性,“話語民主思想的一個優勢是它能夠與許多不同類型的協商實踐聯系起來。尤其與中國的地方層級上的協商實踐聯系起來。重要的是,它可以與中國許多地方城市和鄉村正在開展的咨詢會、懇談會和聽證會等協商實踐形式聯系起來”(12)[澳]約翰·S.德雷澤克:《協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與批判的視角》,丁開杰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1(中文版序言)、4頁。。盡管德雷澤克強調話語民主的協商旨在突破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約束或者自由主義的局限,但正如有的西方學者指出,超越西方政體的更寬泛的協商民主,包括科恩、曼寧、哈貝馬斯等都是“左翼自由主義的”(13)[澳]約翰·S.德雷澤克:《協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與批判的視角》,丁開杰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1(中文版序言)、4頁。。話語表面上是中性的,但在什么語境、什么理論途徑的話語卻有本質的差別。左派自由主義協商民主雖占上風,但各說自話,以至于形成“重大的裂隙。所有的人都在談論協商,但是沒有人能夠說出它是什么,或者它怎樣才能在真實的社會狀況下發揮作用”(14)[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協商:多元主義、復雜性與民主》,黃相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1頁。。此判斷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研究的狀況。
二、激進型協商民主的理論前提:文化市民社會
我們不能忽視,近年來左翼自由主義協商民主研究的理論基礎,是從一度流行的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發展出來的事實。市民社會概念的流行,與“發現市民社會”“重建市民社會”等觀點的民主重構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興起,各派別學者也有趕時髦的風潮,概念模糊不清,甚至是“市民社會的定義取決于你內心期望它承擔什么使命”(15)[美]唐·E.艾伯利:《市民社會基礎讀本——美國市民社會討論經典文本》,林猛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7、9頁。。但在發現市民社會和重建市民社會的價值與功能設定上,可以追尋激進型協商民主的“文化市民社會”之理論基礎。
所謂發現市民社會,起因之一來自于蘇聯崩潰和東歐劇變(16)[日]植村邦彥:《何謂“市民社會”——基本概念的變遷史》,趙平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頁。,主要觀點在于:在國家權力強勝的地域仍然存在并具有重建民主的巨大力量的社團。起因之二來自于西方世界解構“福利國家”重建“福利社會”的邏輯。重建市民社會的價值和民主的功用在于:“其一,在個人與市場、國家這些更宏觀的結構之間充當中介,抑制任何一方所可能帶來的不良社會后果;其二,創造更重要的社會資本;其三,培養民主價值與習性。”(17)[美]唐·E.艾伯利:《市民社會基礎讀本——美國市民社會討論經典文本》,林猛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9頁。顯然,這種建構市民社會介于市場與國家之間的所謂“第三域”,即公共領域,它所依賴的是“社會組織”。這一觀念的理論來源,是阿倫特的“公共領域”觀念與哈貝馬斯的“文化市民社會”觀念的整合。阿倫特重建公共領域觀念引導了“參與式民主”浪潮的形成,啟發了哈貝馬斯重建“文化市民社會”的沖動。
阿倫特于20世紀50年代撰寫的《人的境況》一書,從人的“積極生活”視角,以亞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動物”和“人是勞動動物”的兩極,區分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私人領域,是以家庭為單位,家長統治的生產生活的隱私領域,也是通過“勞動”而能夠使肉體存在的自然必然性領域。公共領域這一概念是一種理想類型。作為理想的公共領域,阿倫特用“政治體”這一概念來表達。政治體是人的本質或自由所體現的生入死出、對所有人公開的開放的彼此聯系的共有的空間性和時間性。所謂空間性,是平等的自由的個人間無排斥性的交往和言說的公共領域;所謂時間性,是指這種交往共同體的超歷史性,每一代人都生入死出并創造人的自由生活的過程(18)[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15、24、25-26、21、30、18頁。。私人領域是家長統治,社會領域是社會統治,這兩種都是支配與被支配、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是個人被動生存的境況;而只有在理想的政治體中,個人才是積極的自由的生活境況。這種理想的政治體是否有存在呢?在阿倫特看來,這一問題是個人自由、平等的參與創造積極生活的歷史過程,并非在歷史階段上的事實存在。
阿倫特從“社會”術語的意涵演變與歷史經驗的雙重路徑上揭示了社會統治的邏輯。社會這一概念,在古希臘還沒有與其對應的詞,它產生于古羅馬的拉丁語詞(Socidtas),原初意涵是指“人民之間為了一個特定的目標而結成的聯盟”,這就初顯了“社會”的政治意義(19)[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15、24、25-26、21、30、18頁。。近代的社會是家務管理和家政經濟從“遮蔽的家庭內部浮現出來,進入光天化日之下,不僅模糊了私人與政治之間的古老界限,而且使這兩個詞(社會與政治,作者所加)的意思變的幾乎不可辨認,同時也改變了它們對于個人和公民生活的意義。”(20)[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15、24、25-26、21、30、18頁。這也就是說,政治與社會的等同,社會獲得了政治功能,將原來的家長直接統治“轉化為一種無人統治”,但這種無人統治并不是統治的無人格性,而是經濟的人格化,是統治“扮演著社會整體利益和在沙龍中標榜為文明社會意見的‘無人’”(21)[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15、24、25-26、21、30、18頁。。阿倫特從經驗的歷史邏輯上分析了社會隱蔽人身的統治形式的發展過程:封建主的統治代替家長制,但仍然采取家長制私人塑造人的關系模式,而且把古代家長所不知道的正義、法律運用于社會生活的集體經濟管理。“中世紀城市特有的職業團體:行會、同業會、工友會、甚至發展出最早的商業公司”(22)[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15、24、25-26、21、30、18頁。即是如此。現代社會“在一個相當短的時間內,新興的社會領域把所有近代共同體都變成了勞動者和打工者團體……在它里面,人們為了生命而非別的什么而相互依賴的事實,獲得了公共的重要性,與純粹生存相聯系的活動被允許獻身于公共場合。”(23)[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15、24、25-26、21、30、18頁。阿倫特還指出了這種統治實際上是由一門來自統計學的政治經濟學實現的。本來經濟學是家政的,是私人的,但“‘政治經濟學’本身就是個語詞的矛盾”(24)[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15、24、25-26、21、30、18頁。,它指涉了社會統治使政治的非經濟利益的領域與私人利益的領域的疊加矛盾。把中世紀的只用于私人領域的“共同善”所表達的共有的精神和共有的物質利益轉換為集體的,“在經濟上把眾多家庭組織成一個超級家庭的模式,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其政治組織形式就是所謂的‘國家’。”(25)[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64頁。也就是說,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國家社會化與社會國家化使政治公共領域消失,因此重建公共領域也就成為應然的要求。
阿倫特繼承了海德格爾學派對古希臘學術概念的詞義與現象經驗相對解釋的專長,得出了市民社會政治化、政治民主經濟化、商品化的結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阿倫特在經驗的社會演進分析中具有馬克思的人類學知識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蹤跡。解讀者往往忽視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簡短致謝所言明的,這一成果是在“卡爾·馬克思與政治思想傳統的標題下”所完成的(26)[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64頁。。她未完成的著作《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本來是受資助研究馬克思的極權主義思想的,但她卻得出相反的結論:無論如何,馬克思與極權主義沒有直接的聯系,而馬克思實際上與亞里士多德最近(27)[美]漢娜·阿倫特:《馬克思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孫傳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頁。。阿倫特雖然對馬克思高度褒揚,但她認為馬克思既復活了亞里士多德,但卻將亞里士多德貶低的“勞動”提升到工人階級乃至所有人的解放的境地,忽視了政治即言說、人是政治動物的本質規定性,社會統治依然是馬克思及其后繼者的追尋。這是阿倫特對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及其功能的曲解和誤解。但不可忽視她所建構的理想公共領域思想的影響力。在繼承阿倫特思想遺產的道路上,將現代社會統治的囚籠撐開,重建公共領域,以參與式民主為條件就成為一種致思路徑。美國學者加諾芬指出,《人的境況》問世以來“引起了激烈的政治爭議,它對勞動動物的處理和對社會問題的分析讓它的作者在許多左派那里不受歡迎,但她對行動的解釋卻為其他激進派傳遞了希望和鼓舞人心的消息,包括各種民權運動中和鐵幕背后的激進人士。在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中,《人的境況》被歡呼為參與式民主的教科書”(28)[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頁。。
哈貝馬斯接受了阿倫特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劃分邏輯,既分析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關系的演變,又設置了實現公共性的“市民社會文化化”的議程。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代表作中,哈貝馬斯將兩條線路交織在一起,一條是重釋阿倫特的市民社會僭越公共領域的經驗道路;另一條是從黑格爾、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的經濟利益的辯證法提煉出“公共性辯證法”(29)[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134、12(序言)、29(序言)、29(序言)頁。。前者是經驗的,后者是理論的,兩條線路的整合,在整體的邏輯結構中貫穿了市民社會的物質性與政治公共領域的意識形態的關系,揭示了資產階級“新社團主義的‘國家社會化’和‘社會的國家化’”所造成的“國家私人化”和“政治民主經濟化”的弊端(30)[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134、12(序言)、29(序言)、29(序言)頁。。哈貝馬斯揭示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是合一的、異化的,公共領域就是私人利益公開化的政治空間。但在如何超越市民社會上,轉向了“文化市民社會”的建構。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并沒有文化市民社會的概念,但突出了私人領域的文學沙龍、社團的批判功能。在英語世界興起市民社會研究熱潮中,此著作被熱捧,哈貝馬斯在1990年新英文版的序言中提出了“文化市民社會”概念。文化市民社會“它也倚賴于文化傳統和社會化模式的合拍,倚賴于習慣自由的民眾的政治文化。”(31)[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134、12(序言)、29(序言)、29(序言)頁。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市民社會是祛除私人利益的社團協作,受公共性支配并以公共利益為指向的公共事務參與機制。哈貝馬斯著重指出,此“市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不同于黑格爾和馬克思將“‘Societascivilis’翻譯成德文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詞……它不再包括控制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的經濟領域”(32)[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134、12(序言)、29(序言)、29(序言)頁。。這也就是在市場經濟與政治國家之間構建所謂第三域的文化社團的邏輯。哈貝馬斯指出:“要在有關的書籍中找關于市民社會的清晰定義自然是徒勞的。無論如何,‘市民社會’的核心機制是由非國家和非經濟組織在自愿基礎上組成的。這樣的組織包括教會、文化團體和學會,還包括了獨立的傳媒、運動和娛樂協會、辯論俱樂部、市民論壇和市民協會,此外還包括職業團體、政黨派別、工會和其他組織等。”(33)[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12(序言)頁。這也就是說,哈貝馬斯的致思路徑在于,將阿倫特所說的社會統治的囚籠撐開,形成政府、市場經濟、社團三個領域,社團脫域于經濟,作為獨立于前兩者的第三域,發揮批判的既不受市場經濟統治,也不受政府統治的自由自主的公眾輿論的功能,這也是他的文化的市民社會的涵義。問題在于,文化的市民社會能否在這些社會組織中生成?文化的市民社會與市民社會的文化化,社會組織的文化化、政治化,其實是一回事。社會組織文化化能隔斷私人利益的“臍帶”嗎?
三、文化市民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批判
西方激進型協商民主理論是左翼自由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共有的論題。他們對西方民主問題的揭弊是有價值的,關注社會大眾被排斥的現實而試圖構建協商民主走出這一困境,也有可圈可點之處。但是文化市民社會這一前提、以及建立在這一前提基礎上的社團革命,影響中國的協商民主發展是不容忽視的。哈貝馬斯自己也意識到社團民主面對社會碎片化、民主碎片化的問題,所以他將文化建立在經驗的“生活世界”的原初,調整為從康德出發的“交往理性”基礎上。但康德的交往理性是先驗的,能夠改造市民社會的資本邏輯嗎?青年馬克思曾經受到過赫斯哲學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其原因就在于赫斯以康德的交往理性來重構市民社會,使市民社會成為交往共同體。在西方的學術概念中,共同體是相互依賴、和睦生活的倫理實體,交往共同體將個人自由嵌入到這種倫理體之中,這是赫斯哲學共產主義的理想。馬克思在深入研究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基礎上,既得出了與黑格爾相反的結論,也否定了作為青年黑格爾學派赫斯的哲學共產主義暢想。
在現時代,要看清哈貝馬斯所設計的“文化市民社會”的虛幻,還要回到馬克思和黑格爾。馬克思和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概念不是頭腦中想象出來的。黑格爾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關于商業社會的交換邏輯,以及社會團體之間及其自身都與物質利益相聯系的現實,用德文“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市民社會表達兩層意思,廣義指物質生活關系總和(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狹義指資產階級社會。黑格爾將市民社會的特征概括為,是私人欲望涌流、每個人都視他者為工具的利益戰場。黑格爾一方面確認市民社會與資產階級同命運,但另一方面又認為理性的倫理國家將解決市民社會的問題。這就是黑格爾的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命題邏輯。
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國家本體的精神前提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就是建立在市民社會基礎上的。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從三重邏輯揭示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原理。
第一,“受到迄今為止一切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0、582-583頁。這一揭示,既確立了市民社會源起于部落制為基礎的古老家庭內部的分工,又指出了市民社會與生產力的邏輯關系。市民社會“以簡單的家庭和復雜的家庭,即所謂部落制度作為自己的前提和基礎的……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3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0、582-583頁。
第二,“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市民社會’這一用語是在18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系已經擺脫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真正的市民社會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3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0、582-583頁。馬克思在這一層揭示上說明,資產階級社會是市民社會的完成形式,社會組織的私人利益性完全表現出來,與以前相比,社會組織不再以倫理、神性、共同的善等虛假意識形態所蒙蔽,物質利益性的敞現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經驗的體現;而且一切時代的社會組織都是國家和上層建筑觀念的基礎,只是前資本主義的歷史是被文化所遮蔽的。在這層邏輯上,馬克思區分了古典古代、中世紀、資本主義三個歷史時期市民社會及其性質和特征。馬克思揭示前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之用意,在于揭示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淵源,著力點在于揭示社會組織的物質利益的根基。馬克思在“使用價值”生產被資本主義時代的“交換價值”生產所代替的歷史維度上,深刻揭示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組織與社會權力的邏輯關系。人們的“社會聯系表現在交換價值上”(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51頁。。一方面,每個人必須以交換價值為中介才使毫不相干的各個人聯系在貨幣上,“另一方面,每個個人行使支配別人的活動或支配社會財富的權力,就在于他是交換價值的或貨幣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裝著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系。”(3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51頁。這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組成社會組織,工人也組成社會組織,但是錢袋的社會權力是政治權力的根基,所以資產階級所宣稱的全民國家,只不過是一種抽象邏輯。
第三,馬克思提出了基于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社會歷史解釋途徑。馬克思指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是這樣的:“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4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83-584頁。這一闡釋,既與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區別開來,同時也指明了歷史唯物主義把握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方法論。國家作為市民社會的政治表現形式和中介是馬克思的基本語境。馬克思的語境中所謂國家獨立或外于市民社會的話語,是批判獨立說或分離說的。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已經是一個階級,不再是一個等級了,所以他必須在全國范圍內而不再是在一個地域內組織起來,并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種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擺脫了共同體,國家獲得了和市民社會并列并且在市民社會之外的獨立存在;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4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83-584頁。這段話的前半句,馬克思在言說私人利益被抽象為普遍利益的時候,國家獲得與市民社會并列和外于市民社會的虛假觀念的境況,但這是思維的抽象力所造成的二元論,是虛幻的虛假共同體的形式。但后半句所說卻是實際情形。由此也否定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中立說。那些將馬克思劃入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離、中立說的,只援引前半句,并且擴大化,因而造成嚴重的誤解。
應當說,哈貝馬斯在揭示現代社會的典型癥候是國家社會化與社會國家化,是對馬克思的繼承。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領軍者的哈貝馬斯,與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的思想中有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離說不同。如果存在國家與社會的分離也不需要重構文化市民社會。哈貝馬斯試圖以“文化市民社會”實現物質利益的“脫域”而設置話語共同體的協商民主,以其改造民主議程,也受到西方一些學者的批判。美國學者艾麗絲·馬里恩·揚指出,懸置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這一自由主義的難題,試圖立足于文化的言談方式的理想設計而想抹平社會權力的不平等,但“事實上,只有當我們進一步將他們在文化和社會地位上的差異抹平后,這種設想才能成為現實。”(42)[美]艾麗絲·馬里恩·揚:《交往與他者:超越協商民主》,[美]塞拉·本哈比:《民主與差異:挑戰政治的邊界》,黃相懷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119頁。現代社會的明顯特征是社會權力的應有、所有、實有的問題,應有是倫理的、價值的;所有是法律的;實有源于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建立在經濟權力之上。“由其財產狀況產生的社會權力,每一次都在相應的國家形式中獲得實踐的觀念的表現。”(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2頁。作為市民社會表現形式的社會組織是受“社會權力”所左右的,它受金錢所詛咒,社會組織之間的利益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4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頁。盡管當今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具有多樣性,但“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45)《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1頁。離開階級、離開國家政體、離開生產生活的經濟基礎,僅僅在社會組織的文化化途徑討論民主,此“文化市民社會”作為“天女”般被描繪,依然是“思想創造現實”的唯心主義。不可否認,市民社會的民主政治也包括隱蔽的文化沖突,美國學者桑德爾分析了西方程序共和國的立法和司法深受基督教及其變種文化的制約,為狹隘的不寬容的道德說教打開了大門,但形式民主依然是它的理想設計(46)[美]邁克爾·桑德爾:《民主的不滿:美國在尋找一種公共哲學》,曾紀茂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27頁。。這是一種“否決型”的形式主義政體,由“有否決權的玩家”所操控(47)王紹光:《國家治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04頁。。當然,基于文化市民社會而建構協商民主議程的學者,并不忽視這些批判,他們的立意在于,不是現實中是否可能,而在于構建一種批判理論。
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作為對西方形式主義民主的救治議程,具有積極意義。但忽視馬克思所指出的市民社會的個人的錢袋里裝著他的社會權力的論斷,所設想的個人自由、平等協商的初始條件就是虛擬的;在政治上,重建民主文化社團的追求也是無解的。以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關切中國或解釋社會主義的協商民主也是僭越性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在超越市民社會的道路上形成和發展的。不否定這種協商民主具有借鑒意義,但鑒于以話語民主和民主社團而設置中國協商民主發展的影響來看,應處理好立足本有與批判性借鑒外來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