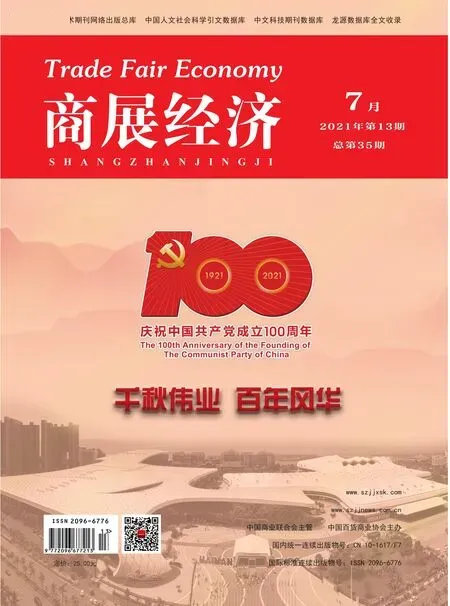金融全球化境遇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①
——基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過程
安徽財經(jīng)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 王程
如何在金融資本主義體系中謀求發(fā)展,走出一條符合自身發(fā)展的“中國道路”,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因此,只有準(zhǔn)確分析中國具體國情,深刻洞悉國際資本主義秩序的形成原因和特點,才能為中國的發(fā)展提供準(zhǔn)確的建議。
1 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展邏輯
資本主義最初萌芽于意大利,但興盛于英國、法國和美國。在其確立后的兩百多年里,人類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資本主義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其核心源于資本的“魔力”。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剩余價值的最大化,不斷地擴張,由此帶來了兩個積累,即資本的積累與貧困的積累,因此,資本主義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資本積累和貧困積累的過程。
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以國際分工的基本建立、世界市場和世界貨幣體系的出現(xiàn)、全球殖民體系的建成為主要標(biāo)志的一個世界性的國際資本主義秩序開始形成。在這個體系中,歐洲列強轉(zhuǎn)型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由于資本的積累和貧困的積累不斷地進行,兩極分化日益加重,生產(chǎn)的不斷擴張和工人生活的日益貧困使資本主義世界爆發(fā)了嚴(yán)重的經(jīng)濟危機。資本達到了邊界,只有通過刺激消費和創(chuàng)造新的經(jīng)濟空間來解決;貧困達到了邊界,則會引發(fā)社會革命和嚴(yán)重的經(jīng)濟危機,最終導(dǎo)致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因此,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從深層次分析,是資本主義強國瓜分世界,贏得更多經(jīng)濟空間的必然結(jié)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人類在遭受慘痛的教訓(xùn)之后不得不重新反思現(xiàn)代性的后果。一方面,經(jīng)過戰(zhàn)火的洗禮,世界各國人民都不愿再重新卷入戰(zhàn)爭;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矛盾仍然沒有克服,資本依然要尋求擴張的空間。因此,在美蘇等大國主導(dǎo)下建立的新的世界秩序就是大國直接相互博弈的結(jié)果。在這個秩序下,資本主義通過新的方式在全球進行擴張。
(1)產(chǎn)業(yè)鏈:建立國際生產(chǎn)線,母國遙控他國,通過產(chǎn)業(yè)鏈進行生產(chǎn)控制,具有科技含量和高額利潤的研發(fā)和銷售在母國進行,利潤率低、缺乏科技含量的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在他國(一般是第三世界國家)完成。由此形成產(chǎn)業(yè)鏈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
(2)金融鏈:主要依靠虛擬經(jīng)濟網(wǎng)絡(luò)。金融權(quán)力使發(fā)展中國家處于被支配的地位。資本具有預(yù)付的性質(zhì),通過金融網(wǎng)絡(luò)把零散的資金集中起來,為產(chǎn)業(yè)鏈提供資金保障。預(yù)期產(chǎn)生了虛擬性,金融鏈?zhǔn)且粋€不平等的社會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大眾處于被支配的地位。這個國際網(wǎng)絡(luò)也是不平等的結(jié)構(gòu),發(fā)達國家通過發(fā)行大量金融衍生品,不但吸納發(fā)展中國家的資金,同時達到了對發(fā)展中國家進行經(jīng)濟控制的目的。
(3)貿(mào)易鏈:資本只有制造流動壁壘,才能促進高額利潤的產(chǎn)生。通過諸如“知識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稅”“勞動力”等要素,通過不平等的貿(mào)易,加強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控制。
(4)文化鏈:以西方文化產(chǎn)業(yè)為主導(dǎo)的文化符號系統(tǒng),占據(jù)國際文化的統(tǒng)治地位,形成國際文化霸權(quán),實施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文化滲透與主宰。
發(fā)達國家通過上述四個鏈條,實現(xiàn)了資本全球化擴張,擴大了資本主義的生存空間,極大地推動了二戰(zhàn)后資本主義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在于,戰(zhàn)爭動搖了殖民者的權(quán)力,眾多民族主義團體在混亂的戰(zhàn)爭中逐漸積聚起自利的影響力,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驅(qū)逐了殖民者,實現(xiàn)了民族獨立。這些新興的國家急切地希望實現(xiàn)經(jīng)濟增長,追求有效的民族國家,他們需要國外的資本和技術(shù)幫助自身實現(xiàn)發(fā)展,因此,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在這種新的國際秩序下形成了互動關(guān)系,相互影響。然而,很多發(fā)展中國家的生產(chǎn)空間逐漸被壓縮,開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jīng)濟放緩,物價上漲,失業(yè)率上升,拉美和非洲地區(qū)出現(xiàn)了社會動蕩。發(fā)達國家同樣爆發(fā)了嚴(yán)重危機,兩次海灣戰(zhàn)爭、“911”恐怖襲擊事件、2008年金融海嘯,給美國主導(dǎo)下的國際資本主義秩序帶了來嚴(yán)峻的挑戰(zhàn)。發(fā)展中國家進一步謀求發(fā)展和地位,美國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國際合作和支持的現(xiàn)實;另一方面加緊軍事準(zhǔn)備,重新調(diào)整軍事戰(zhàn)略,不愿放棄其所謂的領(lǐng)導(dǎo)地位,國際形勢日趨復(fù)雜。這對中國既是契機又是挑戰(zhàn)。
2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邏輯
“一個國家要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它必然都面臨著資源有限和人的需求無限這兩個約束條件,能夠在這樣苛刻條件下發(fā)展就必須采取兩種變革:一是建立一個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經(jīng)濟資源的經(jīng)濟體制;二是有一個具有現(xiàn)代意識,并致力于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政府。而上述的經(jīng)濟體制的基礎(chǔ)就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否存在較為發(fā)達的市場機制和體系,是傳統(tǒng)經(jīng)濟與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一個分水嶺。”鄧小平在會見吉布尼時指出:“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jīng)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jīng)濟為主,也結(jié)合市場經(jīng)濟,但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2]中國進行市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研究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沖破“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jīng)濟”的僵化思維,從計劃經(jīng)濟理論到有計劃商品經(jīng)濟理論(十一屆三中全會至十二屆三中全會);第二個階段:從有計劃商品經(jīng)濟理論到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理論(十二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大);第三個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理論的不斷豐富和發(fā)展創(chuàng)新(十四大到十八大);第四階段: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這四個階段既是實踐發(fā)展的結(jié)果,也是理論跟進的過程。中國在歷史轉(zhuǎn)折的關(guān)鍵時刻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國際環(huán)境。
(1)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時,工業(yè)基礎(chǔ)尤其薄弱 ,即便是在1952年新中國經(jīng)濟恢復(fù)到戰(zhàn)前最好水平時,工業(yè)產(chǎn)值只占工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的20%左右,其中手工生產(chǎn)的輕工業(yè)又占了工業(yè)產(chǎn)值的72%之多,重要的工業(yè)產(chǎn)品不但產(chǎn)量非常低,而且質(zhì)量達不到要求,與主要發(fā)達國家相比差距懸殊。中國的工業(yè)尚未形成規(guī)模和體系。在這樣的情況下直接實行市場經(jīng)濟體制,勢必會受到國外資本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經(jīng)濟是最好的選擇。經(jīng)過30年的努力,到1977年,我國的工業(yè)總產(chǎn)值已經(jīng)占到工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的74.8%,而其中重工業(yè)又占工業(yè)產(chǎn)值的56%。至此,國家工業(yè)體系的構(gòu)建基本實現(xiàn),中國經(jīng)濟起飛所必需的物質(zhì)資源積累也基本完成。新中國擺脫了對國外資本的依附,真正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但是計劃經(jīng)濟發(fā)展到后期,其負面影響越來越嚴(yán)重。經(jīng)濟缺乏活力與創(chuàng)新、效率低下、體制僵化、人才流失等問題嚴(yán)重阻礙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
(2)國際環(huán)境的變化。20世紀(jì)后半葉,各資本主義國家相對穩(wěn)定,國際資本主義秩序處于相對穩(wěn)定時期,尤其是美國、日本、西歐等國家發(fā)展迅猛,在20世紀(jì)70年代末均已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但是,資本主義世界生產(chǎn)空間不足的危機已經(jīng)開始顯露,這些國家擁有大量資金和技術(shù),急需到海外尋求市場,中國是最理想的地方。
3 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秩序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探索
進入新時代之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改革方向。這是權(quán)衡國內(nèi)國際發(fā)展形勢做出的正確判斷,是有步驟有計劃推進改革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我們應(yīng)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正確解讀“市場起決定作用”的內(nèi)涵。
(1)社會主義的性質(zhì)要求我們正確解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 “社會主義是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而來到世間的。”[3]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是其自身無法克服的,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一方面要以改革開放的精神吸收資本主義國家一切有利的經(jīng)驗和成果;另一方面要保持清醒的認識,市場起決定作用應(yīng)在什么層面,什么領(lǐng)域內(nèi)起決定作用?怎樣起決定作用,這些仍是當(dāng)今要認真加以研究的問題。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在當(dāng)今資本主義國家尚且行不通,在中國更會帶來巨大的災(zāi)難。尤其在當(dāng)今國際資本主義秩序下,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通過文化鏈更為隱蔽而有效地滲透進來,更應(yīng)引起高度警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jīng)濟制度下,應(yīng)牢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只有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的矛盾,才能使國民經(jīng)濟均衡發(fā)展。
(2)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秩序體系需要中國更完善的市場經(jīng)濟體制。經(jīng)過40多年的發(fā)展,中國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市場經(jīng)濟體制,但是仍存在許多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在于市場管理體制不完善,存在大量多重管理、過度管理的現(xiàn)象。在信息革命時代,產(chǎn)業(yè)鏈、金融鏈、貿(mào)易鏈、文化鏈通過網(wǎng)絡(luò)形成了更有效的控制,沒有有效的體制,缺乏有效的監(jiān)管,給資本的負面影響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繁榮背后隱藏著巨大的隱患,不但不能促進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反而給我們的改革道路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因此,市場起決定作用的一層含義在于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guān)系,在管理科學(xué)方面,可以大膽借鑒西方的經(jīng)驗。
(3)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需要。21世紀(jì)以來,國際國內(nèi)形勢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市場起決定作用的目的在于進一步激發(fā)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當(dāng)今中國被稱作“世界工廠”,但是我們的產(chǎn)業(yè)大多數(shù)還處于世界產(chǎn)業(yè)鏈的中間環(huán)節(jié),低利潤、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能耗,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迫在眉睫。進一步激發(fā)市場的作用,可以提升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占據(jù)產(chǎn)業(yè)鏈的核心。
世界資本市場作為市場經(jīng)濟的最高形態(tài),使沒有“冷戰(zhàn)”的“冷戰(zhàn)”成為國家間博弈的主要形式[4]。以金融資本為主體的金融體系在新的國際經(jīng)濟秩序生成中占據(jù)核心地位,金融戰(zhàn)爭的威力絲毫不亞于軍事戰(zhàn)爭,無論是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希臘主權(quán)債務(wù)危機[5],再到美國通過一系列財政與貨幣政策干預(yù)人民幣匯率,分割中國實體經(jīng)濟財富[6],阻撓其伙伴國加入“亞投行”等等,可以發(fā)現(xiàn),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體系給人類的發(fā)展帶來了三個方向性的抉擇。一是全球資本金融運行能否實現(xiàn)“非零和博弈”,實現(xiàn)人類共同富裕、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還是會加劇世界經(jīng)濟失衡,導(dǎo)致兩極分化更加嚴(yán)重?二是金融資本主宰的國際格局能否促進人類永久和平,還是會激化地緣政治沖突,制造新的戰(zhàn)爭和災(zāi)難?三是資本主義國家是否愿意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和治理機制[7]?這三個問題的解決并非是資本主義國家自身可以完成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優(yōu)越性能否顯現(xiàn),對于解決這些問題至關(guān)重要[8],它不僅關(guān)涉中國自身的發(fā)展,更關(guān)涉社會主義道路的走向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否最終形成,社會主義制度能否用她巨大的生命活力使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guān)系成為現(xiàn)實,迫切需要我們提交出一份思考人類未來發(fā)展的“中國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