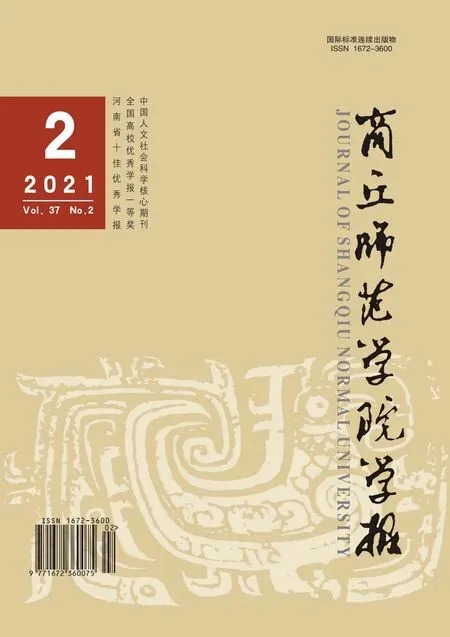唐代愛情詩研究綜述
張翠真
(1.陜西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陜西 西安710119;2.青海大學(xué) 圖書館,青海 西寧810016)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xué)(1)王國維認(rèn)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xué),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xué),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見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自序,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年版。。唐詩作為唐代文學(xué)典范備受歷代學(xué)人關(guān)注。唐代愛情詩是中國古代愛情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當(dāng)時的審美觀、婚姻觀和社會風(fēng)尚。隨著學(xué)術(shù)界對古代愛情詩的關(guān)注,唐代愛情詩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亦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梳理并總結(jié)唐代愛情詩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日后研究重心的確定和研究方向的把控不可或缺。為便于行文論述,本文將唐代愛情詩的研究按綜合研究、個案研究、分類研究依次述評。
一、綜合研究
綜合研究是唐代愛情詩研究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就唐代愛情詩選本而言,現(xiàn)有兩種(2)參見李小梅《唐代情詩精萃》,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鄭在瀛《唐代愛情詩萃》,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另,《唐代情詩精萃》選取唐代愛情詩500余首,占唐代愛情詩總篇目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即李小梅的《唐代情詩精萃》和鄭在瀛的《唐代愛情詩萃》,它們對所選詩歌均有簡要注釋,省去讀者翻檢案卷之苦而對唐代愛情詩有基本體認(rèn)。不足之處是選本僅涉及唐代愛情詩的一隅,不能呈現(xiàn)其全貌,如《唐代愛情詩萃》[1]1僅選出“208首近體愛情詩(其中少量的楊柳枝詞、竹枝詞及短小的樂府民歌,與絕句相似,可以視為近體詩)”。據(jù)筆者檢索《全唐詩》,現(xiàn)存唐代愛情詩有2300首之多,故針對唐代愛情詩的系統(tǒng)研究,尚缺全選本。
研究論文方面,學(xué)者們主要作了興盛原因、思想內(nèi)容、藝術(shù)特征等方向的探索。韓德泰[2]認(rèn)為社會清明、禮法松弛、思想解放是愛情詩在唐朝繁榮的社會基礎(chǔ),杜巧月[3]承襲了這一觀點(diǎn)。張艷玲進(jìn)一步指出,“愛情詩的興盛是中晚唐詩壇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學(xué)現(xiàn)象”[4],并從時代精神、審美趣味、愛情意識等三個方面進(jìn)行成因分析。以上研究論證較為薄弱,但為后續(xù)的深入研究貢獻(xiàn)了可供借鑒的研究路徑。
顏邦逸[5]是較早總結(jié)唐代愛情詩內(nèi)容的學(xué)者,他從歷時角度將其分為初盛唐、中唐、晚唐三個階段,并概述了各階段的愛情詩總體特征、代表詩人和題材內(nèi)容。石志明[6]按題材內(nèi)容將其分為閨怨詩、女性戀歌、戀情詩及反映夫妻摯情的愛情詩四種。蘭翠[7]則根據(jù)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將唐代愛情詩分為女子和士人兩類。以上三種分類模式較具代表性。其中,歷時角度和題材內(nèi)容,是唐詩研究中較常用的分類模式,差異多體現(xiàn)在分類標(biāo)準(zhǔn)的不同帶來的具體內(nèi)容的差別。就具體內(nèi)容而言,顏邦逸的分類方式涵蓋性更強(qiáng),后兩種并不能統(tǒng)攝全部的唐代愛情詩。
李小梅[8]提出唐代愛情詩以含蓄為主要特色。楊景龍稱,“風(fēng)騷傳統(tǒng)、倫理精神、重情傾向和叛逆色彩,以及悲劇調(diào)性”[9]是中國古典愛情詩的鮮明特征。唐代愛情詩自然不能例外。以上研究只是粗略涉及了唐代愛情詩的藝術(shù)特征,楊景龍的研究極具啟發(fā)性,但他的研究視域是整個中國愛情詩,故針對性不強(qiáng)。李小梅的研究結(jié)論固然不錯,但尚未揭示出唐代愛情詩藝術(shù)風(fēng)格的傳承流變。此外,學(xué)者還研究了唐代愛情詩和小說的互動關(guān)系[10][11]。
二、個案研究
唐代愛情詩的個案研究成果豐碩,尤以李商隱、元稹等知名詩人的詩歌作品為著。20世紀(jì)80年代之前,唐代愛情詩研究處于萌芽階段。此期研究成果數(shù)量不多,主要以李商隱、元稹的經(jīng)典愛情詩為研究對象。
蘇雪林《李義山戀愛事跡考》[12]通過李商隱的愛情詩,考證他和女道士、宮嬪之間的戀愛過程。朱偰《李商隱詩新詮》[13]、鈴木虎雄《李義山之無題詩》[14]、高橋和巳《詩人的命運(yùn)》[15]、劉學(xué)鍇《李商隱的無題詩》[16]分析了李商隱的無題詩。惕生[17]和申乃緒[18]分析了元稹悼亡詩的內(nèi)容。俞平伯[19]考辨了《長恨歌》的內(nèi)容和李楊情事。總之,李商隱的無題詩和元稹的悼亡詩是此階段唐代愛情詩研究的重心。
20世紀(jì)80年代迄今,唐代愛情詩研究進(jìn)入發(fā)展期。其中,個案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關(guān)注和成果。根據(jù)被關(guān)注程度,排名前三的詩人分別是:李商隱、元稹、李白。
(一)李商隱愛情詩研究
1.詩歌內(nèi)容研究。鄭訓(xùn)佐[20]指出,李商隱愛情詩蘊(yùn)含深沉的憂患意識;陶光[21]對李商隱與女道士的戀愛史作了考證;鐘來茵在《李商隱玉陽之戀補(bǔ)證》[22]中,對李商隱與女道士的戀愛史作了補(bǔ)證。蔡燕《劉郎已恨蓬山遠(yuǎn),更隔蓬山一萬重——論李商隱愛情詩的“間阻之慨”》[23]指出,“間阻之慨”是李商隱愛情詩中反復(fù)書寫的內(nèi)容,并對“間阻之慨”的成因作了透辟的分析。余金龍[24]考證了《夜雨寄北》的寫作時地和抒情對象。何林天[25]、詹亞園[26]、田谷[27]等學(xué)者還作了李商隱單篇愛情詩內(nèi)容分析。李商隱愛情詩研究是一個重鎮(zhèn),其內(nèi)容研究遠(yuǎn)不止上述篇目,但側(cè)重點(diǎn)多為李商隱戀愛本事的考證和情感內(nèi)涵的挖掘。其詩中隱晦的戀愛本事屬于婚前行為,與妻子無關(guān)。他對妻子的深情,貫注于多篇悼亡詩中。盧燕平[28]稱,李商隱悼亡詩中情感內(nèi)容除了“痛悔”、還表現(xiàn)為“盼來和疑來”;沈文凡《李商隱悼亡詩敘議》[29]認(rèn)為,李商隱的悼亡詩中寄寓著深沉的身世之慨;李聰聰碩士論文《唐朝悼亡詩研究》[30]指出李商隱的悼亡詩“多寫故宅與七夕、羈旅之苦”“多含身世之傷”。要之,雖然悼亡詩有學(xué)人研究,但其成果無論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都不及戀情類愛情詩。
2.審美特征研究。羅錫詩在《論李商隱的愛情詩及其朦朧美》[31]一文中,詳細(xì)論述了李商隱愛情詩的朦朧美及其主要表現(xiàn)形式。方紅[32]認(rèn)為,李商隱的愛情詩有以悲音為美的特征。羅、方二人的概括相當(dāng)準(zhǔn)確,但方紅的論證較單薄。
3.藝術(shù)特色研究。黃渡在《李商隱的愛情詩》[33]中指出,李商隱愛情詩具有“側(cè)重寫無題詩”“抒情為主,著重表現(xiàn)主人公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等特點(diǎn)。王世英[34]稱,李商隱的愛情詩具有巧用典、麗筆寫哀思、善寫心理活動的特點(diǎn)。呂逸新[35]分析了李商隱愛情詩的兩難結(jié)構(gòu)。
4.佛道兩教的影響研究。鐘來茵在《唐朝道教與李商隱的愛情詩》[36]一文中,從詩歌內(nèi)容、寫作手法、審美特征三個方面分析了道教對李商隱愛情詩的影響。也有碩士論文[37][38]探討了道佛兩教對李商隱愛情詩的影響。
5.歷史地位和價值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文艷蓉[39]從愛情題材開拓、情愛心靈世界的探索、愛情題材的詩詞過渡等三方面論述了李商隱愛情詩在古典愛情文學(xué)史上的重要地位。
綜上所述,針對藝術(shù)特色的研究已經(jīng)比較深入,而佛道思想對李商隱愛情詩的影響及其在古代愛情文學(xué)史地位的研究尚有很大的開拓空間。
此外,相關(guān)專著有兩部:鐘來茵《李商隱愛情詩解》(學(xué)林出版社,1997年版)、滕學(xué)欽《李商隱情詩解讀》(中國海洋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相較而言,鐘來茵的著述能在吸收前賢見解基礎(chǔ)上樹立己見,而且注釋翔實、論證嚴(yán)謹(jǐn),堪為研究李商隱愛情詩的必讀書目。但書中部分篇目是否屬于愛情詩,有待學(xué)界進(jìn)一步討論,如第四輯“含有性幽默的游戲之作”中選錄篇目。
(二)元稹愛情詩研究
元稹愛情詩綜合成就不及李商隱,但其悼亡詩成就卓然,深受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注。
1.詩歌內(nèi)容研究。張振謙在《元稹愛情詩〈離思〉的道教文化解讀》[40]中指出,《離思》(其四)的內(nèi)容與道教文化有關(guān),“巫山云雨”的意象源于道教中祈雨儀式。沈文凡[41]等探討了元稹愛情詩中的婚戀觀。王燕[42]、陳英木[43]探討了元稹悼亡詩的內(nèi)容。從論證角度來看,以上論文雖非無可指摘,但貴在視角新穎,給后續(xù)研究思路以啟發(fā)。
2.詩歌藝術(shù)研究。卞良君在《一代風(fēng)流,千古絕調(diào)——談元稹悼亡詩的藝術(shù)成就及其地位》[44]中指出,元稹的悼亡詩具有情真事實、撫存感往、記夢言情等三大特點(diǎn),并認(rèn)為元稹善于通過“對人物典型的生活細(xì)節(jié)的刻畫來寄寓作者對佳偶亡故的哀思”。其后,不少關(guān)于元稹悼亡詩藝術(shù)的文章僅是對卞良君觀點(diǎn)的重新演繹,而無實質(zhì)性突破。蔣寅稱,“元稹悼亡詩最突出的特點(diǎn)是高度典型化的細(xì)節(jié)選擇和概括力極強(qiáng)的抒情力量”[45]。概括十分準(zhǔn)確,是我們了解元稹悼亡詩的鎖鑰。此外,也有碩士論文[46]簡略分析了元稹婚戀詩的敘事特色。
3.悼亡詩比較研究。(1)元稹與潘岳。此類文章寫得較有特色的是宋洋《論潘岳〈悼亡詩〉與元稹〈三遣悲懷〉的異同》[47]。(2)元稹與李商隱。有關(guān)此類文章并無太多創(chuàng)新。
要之,元稹的悼亡詩研究是熱點(diǎn),成果豐富。婚戀詩藝術(shù)研究較為薄弱,比較研究亦有不少學(xué)人涉足,尚缺乏解決根本問題的扛鼎之作。
(三)李白愛情詩研究
1.詩歌內(nèi)容研究。肖文苑[48]簡要總結(jié)李白愛情詩的內(nèi)容。趙曉嵐將[49]將其分為“熱烈的贊歌”“率真的情歌”“無望的悲歌”三類。肖文苑是較早總結(jié)李白愛情詩內(nèi)容的學(xué)者,但可惜未能對其全面總結(jié),如未曾提及李白的贈內(nèi)詩。趙文對李白愛情詩作了詳盡評述,但以詩歌情感基調(diào)予以分類的模式,其精準(zhǔn)性有可商榷之處。王輝斌[50]和伍寶娟[51]總結(jié)了李白贈內(nèi)詩的內(nèi)容,并強(qiáng)調(diào)了其對后世贈內(nèi)詩的影響。查屏球[52]考釋了李白的贈內(nèi)詩《寄遠(yuǎn)十二首》內(nèi)容,并探討了他的家庭生活和唐朝婚俗,此文考證嚴(yán)謹(jǐn),論述精當(dāng),是贈內(nèi)詩研究中的佳作。
2.詩歌藝術(shù)研究。肖文苑《淺談李白的愛情詩》、趙曉嵐《論李白的贈內(nèi)詩》、謝資婭《論李白愛情詩的特征》和袁迪《李白贈內(nèi)詩的藝術(shù)評述》,探討了李白愛情詩的藝術(shù),或各有創(chuàng)見,但缺乏翔實論證。
要之,李白愛情詩的內(nèi)容研究較為成熟,詩歌藝術(shù)研究還有較大空間。他的贈內(nèi)詩深受學(xué)界關(guān)注,也已取得不小突破。
此外,王昌齡、韋應(yīng)物、白居易、李賀、杜甫的愛情詩也有學(xué)者研究。王昌齡的愛情詩研究以宮怨詩為主。陳邦炎[53]分析了王昌齡宮怨詩的內(nèi)容,畢士奎[54]歸納了王昌齡詩中的宮女形象和藝術(shù)特征,并分析了他的創(chuàng)作心理。劉淑麗[55]從詩歌史的角度,強(qiáng)調(diào)了王昌齡宮怨詩的特征和對宮怨題材的獨(dú)特貢獻(xiàn)。韋應(yīng)物的愛情詩成就在悼亡詩。周如月碩士論文《宋前悼亡詩研究》[56]分析了韋應(yīng)物悼亡詩的藝術(shù)特征。謝衛(wèi)平[57]對韋應(yīng)物悼亡詩營造的“時空體系”作了闡釋。蔣寅在《悼亡詩寫作范式的演進(jìn)》[45]中稱,韋應(yīng)物“改變了悼亡詩的寫作范式,使詩歌表現(xiàn)的重心由悼亡主體向悼亡對象轉(zhuǎn)移,從而奠定了韋應(yīng)物在悼亡詩寫作史上的重要地位”。白居易愛情詩研究集中在《長恨歌》。張軍[58]和杭勇[59]認(rèn)為,《長恨歌》中蘊(yùn)含了白居易和湘靈的愛情生命體驗。陳智賢[60]從《長恨歌》為何長恨的角度詳細(xì)考辨《長恨歌》的主題,他認(rèn)為《長恨歌》是愛情主題,但其中包含了對國家興衰的慨嘆。《長恨歌》是白居易代表作之一,自唐至今有無數(shù)學(xué)人從各種角度研究,關(guān)于主題仍然存在分歧,僅舉視其為愛情詩的論文。李賀愛情詩的研究比較分散。張振謙[37]分析了道教文化對李賀愛情詩的影響,強(qiáng)調(diào)李賀對后世女性仙鬼題材有開創(chuàng)之功。狄松[61]分析了李賀愛情詩體現(xiàn)的病態(tài)情感特征。魏娜[62]分析了李賀長安生活經(jīng)驗和宮怨詩、閨怨詩創(chuàng)作之間的關(guān)系。杜甫愛情詩研究以贈內(nèi)詩為主,數(shù)量少且欠創(chuàng)新。魚玄機(jī)、薛濤、李治三人在唐朝女詩人中頗為知名,她們愛情詩創(chuàng)作不少,但研究論文與作品數(shù)量不成正比。韓偓、溫庭筠、權(quán)德輿、王建和張祜等人的愛情詩數(shù)量可觀,但研究很少。
總之,就個體研究而言,李商隱和元稹的愛情詩成果最多,其他詩人的愛情詩學(xué)界亦有涉及,但是無論數(shù)量、質(zhì)量均不能望其項背,特別是唐代女性詩人和王建、張祜等人的愛情詩尚缺乏應(yīng)有的關(guān)注。
三、分類研究
個案研究外,唐代愛情詩分類研究取得了較多成果,尤以宮怨詩、閨怨詩研究為突出。
(一)唐代宮怨詩研究
1.文體辨析和興盛原因研究。梅紅《宮詞和宮怨之辨析》[63]從內(nèi)容、體式、藝術(shù)手法等角度,對宮詞和宮怨詩予以辨析。王娟《宮怨詩范疇辨析》[64]將宮怨詩和宮體詩、閨怨詩、宮詞比較,以明確宮怨詩的概念。孫紅[65]在王娟的基礎(chǔ)上,更詳細(xì)論證了宮怨詩和宮體詩的異同。關(guān)于唐代宮怨詩的繁榮,張浩遜[66]指出,后宮制度、寬松的文化政策、比興傳統(tǒng)是宮怨詩在唐代繁榮的原因。曹金貴[67]認(rèn)為,唐前宮怨詩提供了“可以借鑒的寶貴資料和經(jīng)驗”,是其發(fā)展的重要前提。王娟[68]補(bǔ)充說,唐代詩人干預(yù)社會的精神和士人的懷才不遇也是宮怨詩繁榮的重要因素。
2.詩歌內(nèi)容研究。張垂明[69]總結(jié)了唐代宮怨詩中的五種“怨”情。陳俊偉[70]分析了銅雀臺主題的宮怨詩內(nèi)容。吳雪伶[71][72][73]從詩人性別視角,分別總結(jié)了宮怨詩的內(nèi)容,并強(qiáng)調(diào)了宮怨詩中女性意識的文化價值。梁曉霞[74]論述了宮怨詩在初、盛、中、晚唐的嬗變情況。
3.詩歌藝術(shù)研究。顧愛霞[75]指出,“獨(dú)特的意象結(jié)構(gòu)群”“曲折多致的比興寄托”“細(xì)致入微的心理刻畫”是唐代宮怨詩的主要特征。曹金貴[67]探討了唐代宮怨詩在意象運(yùn)用和意境營造方面的特點(diǎn)。張曉斌[76]則探討了唐代宮怨詩的“含蓄美”的表現(xiàn)形式。
總之,宮怨詩在唐代繁榮一時,興盛原因的研究已相對成熟。而有關(guān)整體內(nèi)容和藝術(shù)風(fēng)格的研究,學(xué)界成果不少,但缺乏體系健全、論證精深的作品。
(二)唐代閨怨詩研究
1.詩歌內(nèi)容研究。曹治邦[77]認(rèn)為,閨怨詩主要是征婦怨、游子妻怨、商人婦怨三種類型。盧佑誠[78]總結(jié)閨怨詩有兩個主題:一是愛情,二是托志帷房。張明非[79]對閨怨詩的界定則有所不同,他將宮怨詩也歸入閨怨詩。李致蓉[80]對征婦類閨怨詩中的怨情作了細(xì)致分析。秦志娟[81]指出了文人閨怨詩中女子等待現(xiàn)象的虛構(gòu)性,并分析了潛藏其后的男性文人心理。
2.詩歌藝術(shù)研究。李紅在《唐代閨怨詩研究》[82]中總結(jié)了唐代閨怨詩的主要創(chuàng)作手法和基本意象。陳葉[83]探討了閨怨詩中代言體的功用。
要之,閨怨詩的界定雖有分歧,但學(xué)界更為接受的是曹志邦的觀點(diǎn),具體內(nèi)容的研究成果較多。詩歌藝術(shù)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著眼于唐代閨怨詩整體發(fā)展流變和藝術(shù)溯源等問題還未全面解決。
研究唐代棄婦詩的文章僅7篇,此類文章中多討論廣義“棄婦”,即指情感上被拋棄的女性而與婚姻存續(xù)與否無關(guān)。有學(xué)者將宮怨詩納入棄婦詩范疇,如王春庭《論棄婦詩》、鄧多軍《唐代棄婦詩研究》、馬言《唐代棄婦詩創(chuàng)作對樂府的接受》等。王春庭[84]、劉育紅[85]對唐代棄婦詩的內(nèi)容作了簡略分析。鄧多軍[86]指出,樂府體、幽怨冷寂的意境是唐代棄婦詩的主要特征。馬言[87]分析了唐代棄婦詩對樂府的接受方式。關(guān)于棄婦的界定,尚永亮[88]認(rèn)為,“已婚”和“離開夫家”是兩個基本條件。這種分法比較有代表性,而棄婦詩的界定在學(xué)界尚未形成定論。目前棄婦詩研究的重鎮(zhèn)仍在《詩經(jīng)》,唐代棄婦詩研究處于初級階段,研究成果少且缺高水平的論文。
唐代悼亡詩的研究論文僅4篇,王芳[89]對唐代悼亡詩內(nèi)容作了簡略分析。馬亞倩[90]總結(jié)了唐代悼亡詩的主要特征。周如月《宋前悼亡詩研究》主要分析了韋應(yīng)物、元稹、李商隱等三人的悼亡詩,對唐代悼亡詩整體性研究著墨較少。李聰聰《唐朝悼亡詩研究》探討了唐朝悼亡詩的藝術(shù)特色和創(chuàng)作局限性。總之,唐代悼亡詩研究以個案為主,整體性研究十分薄弱。此外,唐人創(chuàng)作了大量婚戀詩,與之相關(guān)的整體性研究則完全沒有,學(xué)界對婚戀詩的關(guān)注點(diǎn)大多黏滯于《詩經(jīng)》中。
綜上所述,唐代愛情詩綜合研究論文成果很少,全選本和規(guī)范的分類標(biāo)準(zhǔn)還沒有形成,整體藝術(shù)特色和發(fā)展流變研究問題亟待解決。個案研究中,李商隱、元稹的愛情詩研究比較充分,而韓偓、溫庭筠、權(quán)德輿、王建、張祜等人的愛情詩數(shù)量雖多,但研究相對不足;薛濤、魚玄機(jī)、李治等知名女詩人創(chuàng)作的愛情詩不少,但研究還很薄弱。分類研究中,宮怨詩、閨怨詩研究成果較多,悼亡詩、棄婦詩研究不足,婚戀詩研究最為薄弱;文化研究則更少,唐代愛情詩中反映的婚姻習(xí)俗、社會風(fēng)尚、倫理觀念等尚待開掘。因此,唐代愛情詩研究空間極為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