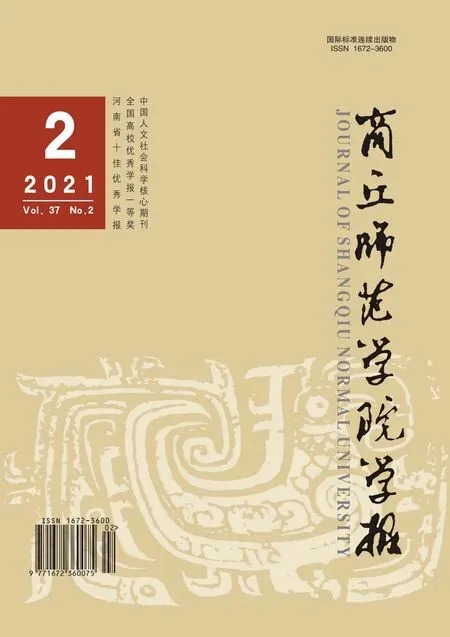宋代官員經商之風盛行的原因
楊忠偉 胡慧蓮
(哈爾濱商業大學 商業經濟研究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8)
在中國古代的歷史長河中,很早就涌現出了許多成功的商人,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就記載了范蠡、白圭等人經商致富的事跡。但是官員參與經商活動,從先秦至漢魏六朝皆極少,自唐漸多,至宋而盛。宋代官員從事經商活動,在各種史書、文集、筆記中記載頗多。他們不但包括大量的中下級官員,也包括一些宰臣高官,他們或者經營酒店邸店,或者進行販賣交易。販賣的對象不但包括鹽、茶、酒、水產、糧食、木材、絲帛等日常生活用品,還包括戰馬等軍備物資、香藥珠寶等海外舶來品,甚至銅錢和人口。經營方式有的倒賣販運,有的自產自銷;有的親自經營,有的委托代理。可以說,宋代官員經商之風的盛行,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歷史現象。對此現象的關注始自全漢升,其后亦有一些研究成果,學界對官員經商的物資種類、經商方式、社會影響等論述得較為充分,觀點也比較一致,但對“原因”的分析,總體上比較薄弱且說法不一(1)見全漢升《中國經濟史研究》,稻香出版社1991年版,第397—405頁;賀達《宋代官僚經商之風摭談》,《河北學刊》1992年第2期;程民生、白連仲《論宋代官員、士人經商——兼談宋代商業觀念的變化》,《中州學刊》1993年第5期;郎國華《宋代官吏營商之風的原因及危害》,《江蘇商論》2003年第1期;郭學信《宋代士大夫貨殖經營之風探源》,《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等。,本文即就此謹陳己見,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宋代官員經商之風盛行的表層原因
宋代結束了五代興替的動亂局面,隨著社會的安定,生產力迅速發展,可供買賣的勞動產品變豐富了;同時因為生產技術的進步,農業勞動力有了剩余,使得一些人轉而從事商業經營;社會財富的增加,增強了民眾的購買力;人口數量的增長,城市規模的擴大,又增強了社會的商品消化能力。此外,經濟中心城市的不斷涌現,都市中居住之“坊”和貿易之“市”分隔傳統的被打破,以市舶司的設置和諸多邊境榷場的開設為標志的對外貿易的發展,乃至交子、會子等流通媒介的出現,都為宋代商業的迅速發展創造了條件。在時代商業大發展的背景之下,宋代官員經商之風盛行,其一般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社會的奢靡風氣
追求財利享樂是人的本性,自古皆然,但宋代更有自己的特色。宋代社會的奢華享樂之風,是由上及下地輻射開來的,官僚階層首倡,商人緊隨其后且更有甚之。趙宋建立之初,那些開國重臣憑借軍功,紛紛聚斂資財,不甘落后地追求奢華的生活。比如石守信,“累任節鎮,專務聚斂,積財巨萬”[1]8811。大將曹彬奉命征討江南,臨行時太祖許諾,待江南平定后,即加封其為“使相”。但后來太祖并未履行諾言,而是賜錢五十萬。曹彬感慨道:“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2]364太祖采取了“釋兵權”的措施之后,開國重臣們雖交出了軍權,但更加追求物質享受,這種示范效應影響到了官員們的價值取向,進而成為帶有普遍性的社會風尚。有一些影響也是來自皇帝的,雖然宋代的皇帝也有主張節儉并屢下“禁奢令”的,但也不乏追求奢靡的皇帝,而且后者的負面影響更大,因為它更契合普通民眾貪圖享受的人性。繼太祖、太宗的艱辛開創之后,真宗在前期尚能勵精圖治,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史稱“咸平之治”,但后期惑于天書符瑞之說,封泰山,祀汾陽,勞民傷財,廣建宮觀苑囿。至仁宗后期,隨著升平日久,社會上的奢靡之風漸盛,司馬光說,士大夫在宴飲賓客時,“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后敢發書。茍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3]141。秦觀也說過,“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余年矣……田疇邸第,莫為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4]120冊46。到宋神宗時,“今一最下士人,亦須月費百千以上”[2]6102。整個社會的奢侈之風,已經非常嚴重。宋徽宗信任童貫、蔡京等佞臣,朝政逐漸荒廢,乃至四處搜求精巧別致的“花石綱”,北宋的奢靡風氣又一次掀起了高潮。隨著金兵的南下,北宋滅亡。偏安江南之后,南宋的歷代皇帝多數不思恢復,茍安于南北對峙的局面,“直把杭州作汴州”,最后在蒙古鐵騎的無情踐踏之下,一切瓦解冰消。
通過上述的縱向梳理可知,宋代上層集團的奢靡風氣幾乎是一以貫之的,朝廷屢下“禁奢令”,正可說明社會奢靡風氣之盛。而官員欲追求物質享受,當然需要財力的支持。若不想在仕宦生涯中冒著太大的觸犯法律風險(比如搜刮或貪污),通過經商來使個人財富迅速增長,就成了官員們的首要之選。
(二)職權的便利條件
官員憑借自己的身份,可以在經商行為中擁有許多優勢,進而實現職權向財利的轉化。這種以權謀私的優勢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在生產及銷售的過程中,打著官家旗號,利用官府的各種資源,包括私役吏卒節省工錢,挪借公款保障資金運轉,利用公家的原材料、生產及運輸工具、經營用地等。如并州知州孫沔,“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1]9690。給事中邊肅,“嘗以公錢貿易規利”[1]9984。虢州知州滕宗諒,“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驢車四十輛,載茶三百余籠出引,逐處不得收稅”[2]3538。京東轉運使和峴,“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1]13014。一些地方官員在出租官田時,因其所收糧谷中有部分可抽取歸己,所以格外賣力,“方起納之時,督責甚于稅賦,逮其既足,不時變糶,坐邀善價”[5]4626。
第二,利用公事往來之機攜帶商品進行經商。許多官員極力謀求去富饒郡任職,趁機商販。或者巧立名目尋求出差機會,以便公開調用船只運輸商品,“多求不急差遣,乘官船往來,商販私物”[5]7122。以至于長江之上,“巨艘西下,舳艫相銜,捆載客貨,安然如山,問之則無非士大夫之舟也”[5]6386。甚至有的商人把商舟附于官船,而官員則借機索要高昂的費用,船隊過征稅渡口時,官員假托各種借口,為商舟申請免稅放行,往往“一舟所獲,幾數千緡”[5]6386。兩宋與遼、西夏、金在局勢緩和時,官方禮節往來較多,這需要出使官。其實,朝廷提供給出使官的待遇并不高,但有些官員極力爭取出使機會,就是想借機與外國做商業交易,為自己謀取經濟利益。
第三,一些官員憑借權勢強買強賣,或者搞商業壟斷,與普通商人進行不平等競爭。如“方臘亂后,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蔡)薿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強取之”[1]11172。高宗朝宰相湯思退“貨縑帛于鄉郡,糶俸米于近州,責其倍償,公私咸擾”[6]3130。南宋時,還有臣僚指出,“今之任于廣者,凡有出產,皆賤價收之,而歸舟滿載。南方地廣民稀,民無蓋藏,所籍土產以為卒歲之備。今為官吏強買,商旅為之憚行”[5]8356。
(三)朝廷的寬松態度
宋代對官員經商是明令禁止的,“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賈事”[1]55。禁令在初期被執行得很嚴格,乃至犯禁有被處以死刑者,如“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錢糴糶,棄市”[1]67。但更多的情況則是雖然名義上反對,在對具體事件的處理上,常常又表現出寬松的態度,這在針對邊將時體現得尤為突出。宋初上承唐末五代藩鎮割據之余緒,邊將多跋扈難治,加之天下未定,正是用將之時,因此對邊將經商常常不太干涉。李漢超守關南齊州時,朝廷給了他極大的地方財政支配權,而且賞賜極為豐厚,但他仍從事經商活動,“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1]8972。因為有朝廷如此厚重的恩遇,加之又涉及不斷增長的個人財富,所以李漢超全力守邊,“畢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靜”。邊將經商者,非李漢超一人,《宋史·賈昌朝傳》即提及其他十余位高級將領。因為邊將靠私營商業,手里的錢多了,賞賜豐厚,所以士兵才愿意出死力;蓄養間諜,才能了解敵方的詳細情況,預知敵方的行動。朝廷出于邊防考慮,對這些邊將的經商行為,都采取一種放任的態度,“聽其貿易,而免其征稅”,二十年間,也確實收到了無外顧之憂的效果。可以看出,只要邊將的經商行為是為了擴大經濟實力,進而更有效地保障邊防安全,朝廷并不強加干涉。即使邊將經商完全是為了滿足私欲,朝廷也能以邊境安全為重,以拉攏安撫為主。后來,對其他官員經商的態度也是如此,哲宗元祐四年,左司諫劉安世在奏章中說:“祖宗之制,唯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茍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2]10429這里的“從官”是指數量很少的達到一定級別的近臣高官,說明祖制只是對高官經商進行限制。而且,何為“殖貨太甚”,并沒有固定的標準,因此在具體處理時彈性較大,只要不惹出麻煩,比如招致社會廣泛非議或被人彈劾舉報、染指官府專賣物資、因違犯其他法律被捎帶出來等情形,一般經商都沒事,官府不會去認真調查追究。朝廷的寬松態度還體現在對官員經商不征商稅,所以他們的交易成本更低,獲取的利潤更大。朝廷如果對官員經商征稅,不但等于降低了官員傳統以來的身份地位,同時相當于承認了官員的經商行為是合法之舉,會導致類似行為的擴大化。因此,雖然對官員經商屢頒禁令,但因對違禁的懲處力度不夠,禁令常常流于形式,在這種相當于默許寬縱的態度之下,官員的經商之風也就愈演愈烈了。
(四)俸賞的不夠開銷
官員的合法收入通常包括俸祿和賞賜兩方面,而以俸祿為主體。相較于唐代而言,宋代官員的俸祿是比較低的,尤其是中下級官員。俸祿低的主要原因,是宋代官員數量巨大。自太祖釋兵權開始,朝廷對官員實行分權制,讓他們互相掣肘,再加上宋代科舉錄取比例及名額遠超唐代,這樣就導致了“冗官”現象極為嚴重。官員數量的增多,勢必會影響他們的俸祿收入。因此,官員僅靠俸祿來安排生活支出,常常會捉襟見肘。關于宋代官員生計困窘的情況,史書上多有記載。“有平羌縣尉鄭宗諤者,受賕枉法抵死,會赦當奪官。帝問輔臣曰:‘尉奉月幾何,豈祿薄不足自養邪?’王欽若對曰:‘奉雖薄,廉士固亦自守。’”[1]5017“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亦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1]8696“(王希呂)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1]11901“(吳奎)沒之日,家無余資,諸子至無屋以居。”[1]10321“吳交如死,無棺斂,(辛)棄疾嘆曰,‘身為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1]12165因為日常開銷常常困窘不堪,故官員多靠經商來貼補家用。王安石說:“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7]8隨著時間的推移,宋代的通貨膨脹也越來越嚴重,薪俸雖漲,物價更漲。紹興三年,高宗說:“自元豐增選人俸至十千二百,當時物價甚賤,今飲食衣帛之價,比宣和間猶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責以廉潔難矣。”[8]180宋代的候補官數量眾多,常常要數年后才有謀得實職的機會,他們“守選、待闕”之時,“衣食不足,貸債以茍朝夕”,赴職之后,為了還債,常常“不恥賈販,與民爭利”[4]18冊107。而且,候補官為了盡早謀得實職,任官者為了早日升遷或謀求肥美官職,還常常需要打通關節,而鉆營攀附所需的錢物,也往往要借助于經商之利。兩宋與遼、西夏、金對峙之時,軍費劇增,議和之后,則須送出大量歲幣及各種賞賜,這對宋代官員俸祿的影響都是較大的,不但多次減俸,而且還常常拖欠或者以實物充抵。這樣,為了保障家庭開銷,官員的經商行為更是不足為怪了。
以上從四個方面剖析了宋代官員經商之風盛行的一般原因,當然,這四個方面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不同階層官員所體現出的側重點也不盡相同,比如,為追求享樂而經商的多是高級官員,迫于生計而經商的多是中下級官員。原因也不僅此四點,比如有的官員出身于經商家庭或者本人此前即有經商的經歷,這樣靠科舉做官之后從事經商活動自然駕輕就熟。
二、宋代官員經商之風盛行的深層原因
上文我們論析的是宋代官員經商的表層原因,更深入一步,其深層原因則是在宏觀時代背景之下,宋代官員們對“財富”“商業”及“商人”的認識較之傳統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輕視拒斥轉變為認同接受。以前是經商不做官,做官不經商,宋代則兩美兼得,做到了官僚身份和商人心態的結合。
從春秋時期開始,中國傳統上是以農業為“本”,以工商業為“末”的。因為,從經濟角度,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生產力低下,統治者讓大量人口從事農業生產,保障基本物質需要是第一位的,而一些本應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轉而進行商品經營,必然削弱了農業勞動力資源。從王權角度,商人與國家搶占自然資源,相當于挖國家墻腳,逃稅也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一些大富商收納了許多流民,他們只服從于商人,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削弱了王權的影響力,危害封建等級秩序,甚至有一定的叛亂威脅,沖擊中央集權。從世風角度,從事農業的民眾是寡欲、安于現狀的,而商業是刺激物欲的,商人致富后,易助享樂之風,且僭亂國家禮法。奔走經營的商人和“安土重遷”的農民相比,少有厚樸之心,易敗壞社會風氣。另外,經商需要智巧,或疏通關節,或囤積居奇,都會影響社會的安定秩序。所以,從先秦到兩漢,統治者都是重農抑商的,體現在社會思想觀念上,就是“重義賤利”。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9]39,認為“言利”在思想境界上就是低層次的。孔子并不是完全地看不起商人,端木賜善經商,是其門徒中首富,但孔子更主張“仁以為己任”“士志于道”,因此“罕言利”,把追求、踐行先王圣道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是迫于衣食去為市井小人之事。孟子也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10]1,認為只有推廣仁愛之心,行王道,施仁政,才能統一天下。商鞅是最早對商人進行抨擊的,他說,“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11]50,其變法的重要舉措就是“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其后的荀子也鮮明指出,“工商眾則國貧”[12]129。這樣,社會普遍認知方面,就突出了商業“智巧逐利”的弊端,而忽視了它“溝通有無”的價值。《史記·平準書》載:“(漢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13]1418。至武帝時期,更增加了對商人“困辱”的力度。“困”是物質層面的,對商人的經營行為設置障礙,如官府對鹽鐵等物資實行官營禁榷,搞資源壟斷。同時還對商人重征商稅。“辱”是精神層面的,比如視經商為犯罪,實行人身制裁,商人的社會地位很低,不能成為官吏,乃至在服飾出行婚娶等方面都有嚴格的限制。這種對商業及商人的輕視態度,從漢及唐,都沒有明顯的變化。
宋代對“經商”的態度發生明顯轉變。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理論層面。宋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儒家傳統地位的動搖,社會對“義”“利”關系的態度,從對立到逐漸開始兼容。北宋李覯首倡其端,肯定“利”的價值。他說:“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14]326“賢圣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14]133其后蘇洵主張:“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義利、利義相為用。”[4]43冊159認為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北宋影響最大的是王安石,其主張“利者義之和,義固所以為利也”[2]5321,“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7]97。把理財上升到了國家大義的地位。王安石變法,關鍵也是財政體制改革,于是時代思想由“諱言財利”向“利義均重,利義相輔”轉變。宋代理學家也未全然否定人欲功利,如程頤即講:“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15]215“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15]249南宋浙東學派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了“義利統一”的價值觀,陳亮高揚求利合理的大旗,結合《易經·乾卦》的卦辭“乾。元亨利貞”,闡發說:“《乾》無利,何以具四德?”[16]1850葉適說:“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耳。”[17]324“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18]658認為“利”是“義”的基礎,主張把“義理”與“功利”結合起來。
宋代義利觀的發展影響到了本末觀的轉變,肯定“利”的價值及“逐利”的必要性,勢必會提高社會對商業及商人地位的認識,兩種思想觀念的發展可以說是并駕齊驅的。李覯雖仍堅持“所謂末者,工商業”的傳統觀念,但反對政府專賣政策,主張發展民間商業。認為,“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管勿賣買,聽其自為”[14]149。歐陽修認為,“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鈦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19]3646。主張商業的地位不應該受到輕視。王安石建議茶葉應由國家專賣變為準許商人自由販運,“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7]366。進入南宋,主張提高商人地位的呼聲更加強烈。陳亮說,“農商一事也”,“商籍農而立,農賴商而行”[20]140,高度評價二者之間的互利共生關系。葉適說,“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17]273。葉適弟子陳耆卿在編修《嘉定赤城志》時,采用紹圣三年時地方官鄭至道所作《諭俗七篇》內容,旗幟鮮明地反對“農本工商末”的傳統觀念,他認為士、農、工、商各有自己的社會功能,“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21]406。隨著這些有識之士對商業發展和商人價值的重視,再輕視商業已不合時代潮流了,理論發展為官員們的經商行為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是現實層面。在宋代國家財政收入中,商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征收網點密布全國,為了保障商稅的收入,必須維持商業經營隊伍的穩定。為此,宋代始終致力于商稅征收的透明度和規范化,太祖時即下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22]401歷任皇帝還不時采取減免商稅的措施。這些措施提升了商人的經商熱情,促進了商業的發展,也使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當然眾多小商人仍處在社會底層,富商大賈的情況則好一些。隨著財力增長帶來的自信,富商們欲在政治上謀求話語權的想法也越加濃重。后來隨著國家財政的困窘,商稅漸增,加之各級征稅官吏位卑而權重,肆意征收,或邀功于上或私入己囊,大商人又加重了有富無貴的生存危機。在這兩種因素的驅動之下,他們極力謀求進入仕途。最正統的方式是通過科舉。宋初是明令禁止商人參加科舉的,后來略有松動。允許“工商雜類”中有“奇才異行”者參加科舉。但商人本人通過科舉登上仕途的較少,更多的則是培養子弟參加科舉,“父商子仕”現象極為普遍。第二種途徑是捐納。宋代政府賣官現象是很普遍的,尤其在軍費吃緊或賑災之時,往往借此來緩解財政問題。范仲淹之子范純粹曾說,“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并免試注官”[1]10281。后來賣官現象在全國各地全面鋪開。到北宋末年,身穿朝廷命服的富商大賈,已是“遍滿天下,一州一縣,無處無之”[5]4518。第三種途徑是攀附賄賂權貴。如“杭州俞緡,東南大姓,賈販小人,未嘗為安禮門客,特以賄交,去歲大禮,(王安禮)遂奏緡為假承務郎”[2]8329,“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閽寺以進,至秘閣修撰,廣南轉運使”[23]183。朱沖、朱勔父子本是蘇州富商,曾因殺人而被判死罪,靠行賄得以免死,然后去了京城,攀附權臣童貫、蔡京,經二人運作提攜,逐漸發跡作了高官。后向徽宗游說東南富有奇石異卉,于是領旨搜求,假公謀私,“往來商販于淮浙間”[24]95。第四種情況是聯姻。宋代皇族宗室女眾多,朝廷有專門機構負責為她們選婿,對娶宗室女者會授予官職,擇婿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男方家庭的財力。于是,“富室多賂宗室求婚,茍求一官,以庇門戶,后相引為親”[25]112。許多商人及其子弟因此登上了仕途。雙方各取所需,收到了以富求貴、以貴求富的雙贏效果。而許多商人步入仕途,也影響了社會普遍對商業及商人態度的變化。
在上述理論層面和現實層面的共同影響之下,官員士人群體的價值觀念逐漸發生了傾斜。“君子憂道不憂貧”的傳統價值觀已被世俗享樂所代替,對人欲功利的肯定和提倡,對官員經商之風盛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官員不再以商人為賤、以經商為恥,并且紛紛付諸行動。北宋時,蔡襄在給皇帝的奏章中說,三十年前,“仕宦之人,粗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為恥”,如今,“紆朱懷玉,專為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茂遷往來,日取富足”,尤其令人憂慮的是,“貪人非獨不知羞恥,而又自號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怪”[26]380。南宋高官張俊,“歲收租六十四萬斛,偶游后圃,見一老兵晝臥,詢知其能貿易,即以百萬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大獲而歸[27]284。歲收租六十余萬斛,所擁有的田產數量驚人,進而行商海外,投資竟達百萬之巨,“官員、地主、商人”就這么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甚至官員在經商求富時,已不再顧念品行名節。比如:石揚休“平生好殖財”,做官后回到家鄉,眾人以為會得賞,但“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1]9931。徐休復的父母早年在青州簡單安葬,他后來請求去主政青州,好為父母隆重改葬,“至青州逾年,但聚財殖貨,終不言葬事”[1]9400。官員逐利經商助長了社會的貪奢之風,而貪奢之風的熾盛,又促使官員更努力地去經商逐利。這種惡性循環,對宋朝國運的逐漸式微,確實應承擔相當大的責任。
三、 結語
通過上述論析可以看出,宋代官員的經商之風盛行,有一般原因(客觀原因),也有根本原因(主觀原因),而后者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兩種層次分析的意義,更能理清脈絡,把握關鍵。宋代官員經商行為的大量涌現,有它的時代必然性。因此,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之上,對其“實質”可以作如下概括——在宋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下,隨著制度約束的寬松及對個體存在意義認識的改變,財富的魅力影響到了官員們的內在心態,進而體現為外在行為。宋代官員從事經商活動,多數情況下是以權謀私,容易涉嫌貪污,其負面影響更大,但兩者絕不是完全等同的關系。有些官員的小規模經商行為并不構成貪污,還有些官員經商的初衷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利。如趙不主政夔州時,屬轄無法交納足夠的“上納銀”,百姓深受其苦。他調撥公款,把本地官家鹽場完成官賣數額的剩余鹽,買了數十萬斤,“易米得三萬余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十五余萬”[1]8758。再如濱州知州王起等人,“以私船回易官鹽以益公用”[5]4806。雖然這種現象很少,但不能完全忽視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