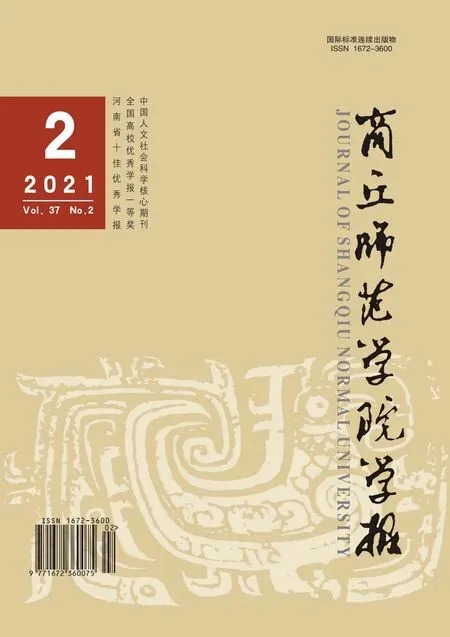《宋氏女科撮要·敘》辨疑及其文獻價值
徐艷芹
(中央民族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北京 100081)
明朝女科醫家宋林皋曾作《宋氏女科撮要》一書,借以總結行醫經驗并傳與后世。在正文前的自敘中,宋林皋詳細描述了家族醫學始祖、祖先遷居四明以及自己撰寫此書的緣由等情況。經查閱相關史料,我們發現其中多處記載與史實不符,宋氏所提及的幾處地名、人物需要進一步考證核實,以便明晰這篇敘文的引用和參考價值。文中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宋氏女科撮要》版本及相關研究
據王英《〈宋氏女科撮要〉版本及學術思想探要》一文可知,此書流傳有五種版本[1]。1975年,中國臺灣的臺聯國風出版社印行了《四明宋氏女科秘書》。其中,明抄本為善本;清抄本體例及內容與明抄本不同;曹炳章抄本內容有缺,但從敘文來看,此版本或由明抄本而來;萬有書局鉛印本與中醫書局鉛印本內容相同;臺聯國風印本,與萬有、中醫書局同文。盡管前幾年王英校注了《宋氏女科撮要》[2]1-2一書,但敘文中仍存在一些記述疑點需要進一步考訂。
關于《宋氏女科撮要》一書的探究,前人多關注醫書的醫學價值、醫術及醫方的功效等內容,如陳雅萍的博士學位論文《產后從虛從實病機探析》,葉賽雅、張翼宙《浙江四大中醫婦科流派調經學術經驗與特色比較》,余凱、錢俊華、莊愛文《浙派婦科芻議》以及宋俏蔚、施燕《〈宋氏女科秘書〉運用風藥特點探析》等。但以上研究成果未多留意敘文中宋林皋所述先祖及遷徙等問題,這也是本文核心關注之處。
二、《宋氏女科撮要·敘》疑點辨析
(一)宋氏先祖居所中的疑點
敘文中“余先世居郢州之相,即今商丘是也”一句提及“商丘”,據《明史·地理三》記載,弘治十五年(1502),商丘縣舊地因為黃河水患之災而城陷,之后便將城址由黃河北面遷到南面。商丘在當時隸屬于歸德府,而歸德府在洪武元年(1368)被降為州,屬于開封府,直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才再次升為府[3]984。由此便可大致得出商丘一地的方位。
關于“相”字,筆者認為可有兩種解釋:一為“相近、鄰近”,二為“廂”字的假借。當作鄰近之義理解時,我們可以推測“郢州”的具體位置。《明史》中無“郢州”的相關記載,卻有“潁州”一地。潁州的南面和北面分別是淮河、潁河,洪武二十四年(1391),河南府一處的黃河河段決口,在陳州與潁河合流,至壽州匯入淮河。在明朝宣德至正德年間,黃河和潁河時通時塞,當時人便將潁河稱為小黃河[3]914。潁州的相近之地為亳州,亳州在明洪武初年被降為縣并隸屬歸德州,與上文的商丘處于同一轄區之內。洪武六年(1373),亳州又改屬潁州。至弘治九年(1496)再次升為州一級的行政單位[3]915。亳州所屬由歸德府轉移到潁州,而后獨立成州,這或是因為黃河決堤造成的區域性動亂。也可能是亳州處于歸德府與潁州交界,潁州又屬應天鳳陽府,統治者必然依據應天府與周邊州府的形勢劃定亳州的歸屬。由此看出,亳州所屬不及潁州穩定,在判定地理方位時大多不及潁州更具代表性。“郢州之相”中的“郢州”便有可能是宋林皋在先輩記述或口述過程中“潁州”的訛誤,這樣便符合與商丘臨近的位置關系。
若“相”為“廂”的假借,意為靠近城的地區,即城郊之地。因此不論是郢州城郊還是潁州城郊皆不是商丘一地。再看宋林皋所提及唐朝名相宋璟,他是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4]3029。先秦時期,“祖乙遷于邢(耿)”[5]130,邢州之地曾作為商朝都城而存在。“邢”“耿”字形雖異,但古音相同。有學者曾對祖乙所遷之都城的地望進行考證,證實“邢”或“耿”大致應在今河北邢臺一帶[6]。由此可推測“郢州”也可能是“邢州”的誤記,此處的“商丘”便不能理解為歸德府的商丘,而是指商朝的都城或某一城。聯系起來理解,即宋林皋的遠祖居于邢州城郊的商朝古城舊地。
但此處若非誤記,關于“郢州”一地,《舊唐書·地理二》記載,武德四年(621)置郢州,貞觀元年(627)廢郢州,十七年(643)復置郢州,治所在京山一地。天寶元年(742)改名為富水郡,乾元元年(758),復名為郢州[4]1548。可知,郢州在今湖北省鐘祥、京山一帶,明朝這一區域屬承天府,而承天府與商丘所在的歸德府相去甚遠,并不是“相”的位置關系。
綜上可知,“郢州”應為“潁州”或“邢州”的訛誤,同時這一錯誤降低了此文獻記載的真實性和史料的精確性。
(二)宋氏家族南遷中的疑點
關于宋氏家族遷徙的情況,宋林皋稱家族中有位先祖名為宋欽,他在南宋建炎初年“由進士,任七子城使”,并跟隨皇室南遷到四明。之后宋氏子孫有的參加科舉入仕,有的則精于醫學之術。敘文中的“學正”為中國古代基層文官,“院判”“院使”均為太醫院官員,這正與宋氏家族成員身處官場和從事醫學兩方面相對應。
上文提及“七子城使”一詞,經查宋朝文獻中并無“七子城”的記載,因此暫把“七”理解為量詞。關于“子城”,《舊五代史·王镕傳》記載,某天夜里,王镕親自率領士兵十余人,從子城的西門翻墻而入[7]730。《太平廣記》卷二八一《袁繼謙》亦記載,袁繼謙任職兗州推官時,東鄰呂君因為自己宅第低矮,便命令兵卒削掉子城下面的土用來培高自己的宅子。而后袁繼謙夢到有一人騎馬從子城東門樓而上,“自稱子城使也”[8]2239。這段材料源自王仁裕《玉堂閑話》,此書中所載大多是唐末和五代時中原、關隴及蜀地等處的舊事,其中部分是撰者親歷或者是當時人轉述而來,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和參考價值。由這兩則材料可推知,“子城”應指附屬于某一內城的甕城,建于城門之外,作防御外敵、守衛主城之用。
再則是“子城使”一詞,袁繼謙所夢之人自稱“子城使”,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牙職”記載,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十月,有大臣上奏,豪民聚集在刺史以上等武官的門館前,希望謀求一官半職,如教練使、衙內指揮使、內知客、子城使或者是押衙回圖軍將等[9]4374。教練使、指揮使、子城使均為武職,內知客為官員府中類似迎來送往的仆役官,押衙回圖則是衙門中負責貿易轉運的文職。宋仁宗時,地方官府中有“子城使、教練使、都教練使”等多種名目的職官,當時就準備修整官制,革除時弊,意欲將這些職官名改作“都史、副史、介史”等[9]4375。又有《宋史·張永德傳》云,張永德同母異父的弟弟劉再思,因張氏之功任職子城使[10]8918。《宋史·閻文應傳》中也提到宋仁宗試圖納陳氏女為后,而陳氏女之父號為陳子城,于是閻文應的兒子閻士良勸說皇帝:“子城使,大臣家奴仆官名也。”[10]13656由以上多則材料可知,北宋確有子城使這一官職,且在地方官員中品級較低,并于徽宗政和年間被提議改置。回看《宋氏女科撮要·敘》,宋林皋將宋欽記作子城使。從職官名來看,“子城使”之名從被提出廢改到完全消失需要經過一定的流程,這項更改舉措由中央傳到地方亦會存在時間的延遲。因此,宋欽在兩宋之交任職子城使也是有可能的。但因低品階官員的事跡很難進入史書,現下我們不能找到關于宋欽的任何史料,所以此處記述仍需存疑。
還有“四明”一處,據《舊唐書·地理三》載,唐玄宗時在越州縣設明州,天寶元年(742)改名為余姚郡,至乾元元年(758)時又改回明州,皆是以當地的四明山為命名之源[4]1590。《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二》亦載,開元二十六年(738),采訪使齊浣上奏在縣一地設置明州,其名也是由境內的四明山而來[11]629。又據《明史·地理五》可知,寧波府在元朝時屬浙東道宣慰司管轄,名為明州府。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二月,因避諱“明”字,改名為寧波府。府內有鄞縣,鄞縣之東有山,西南有四明山[3]1108-1109。據雍正《寧波府志·山川上》載,四明山在寧波府西南方向五十里,是寧波之鎮山,因山上有一塊方形巨石,四面透亮如窗,日月和星宿之光可通達石頭的中心[12]1。明州一名源于四明山,可知此山當時在此地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唐朝明州與明朝寧波府所轄區域大略相同,至明朝寧波府時,四明山仍處于該府南面,清雍正時稱之為鎮山,因此四明山至晚從唐朝開始便在當地頗有名氣,成為寧波府的代稱。聯系上文,宋欽帶領家人選擇“四明”一地為居所,即是定居于寧波府境內。
(三)考證宋璟是否為宋氏女科始祖
在敘文中,宋林皋自稱“宋廣平公二十七代孫”。“廣平公”即為唐玄宗時的名臣宋璟,開元十七年(729),宋璟官至尚書右丞相,晉爵廣平郡公。由“始祖廣平公璟精于醫”一句可知,宋林皋將宋璟追溯為醫學始祖。以往研究中,宋璟多以玄宗朝名相、賢臣的形象被探討,此處名醫與賢臣兩種角色形成鮮明對比,它們是否同時屬于宋璟這一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由此或可發現宋璟社會身份的更多面相。
1.正史、石刻材料中關于宋璟的記載
敘文中提及宋璟“精于醫”,遠觀病人的容色便可看透病情,時人皆稱其為神。那么,宋璟既為賢相,是否又是良醫,這需要進一步的考證。據《舊唐書·宋璟傳》載,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宋璟因年老以至于“積羸成憊,沈錮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便上書辭官退居洛陽就醫養病。開元二十二年(734),玄宗駕臨洛陽并派遣榮王李琬慰問宋璟,之后時常命人為他送去湯藥[4]3035-3036。由《天圣令·醫疾令》唐令第十條可知,唐代五品以上職事官辭官返鄉后,若是患病,官府負責供給醫藥[13]319。由此可知,宋璟被賜藥亦屬常理。以上材料雖提及宋璟晚年身體較差,但并無其學醫、懂醫的明確記載。
又考察《新唐書·宋璟傳》《資治通鑒》和顏真卿所作的《大唐故尚書右丞相贈太尉文貞公宋公神道之碑》以及唐代筆記小說,其中多記載宋璟為名相,偏重敘述其政治才能。今人著述多是對宋璟政治思想與貢獻、文學作品和宋璟碑文的探究。因此,從史料記載和現今研究成果來看,宋璟多被描繪為朝臣良相,并無宋璟“醫”角色的記載。
2.方志材料中關于宋璟后裔遷居四明的記載
由上文可知,史料中并無宋璟本人懂醫的記載,那么宋林皋追溯其為醫學始祖是否與宋璟后裔有關呢?宋氏子孫是否有遷居四明的經歷,是否有人精于醫學呢?
唐代正史傳記中載,宋璟為邢州南和人。據康熙年間所刻《南和縣志》“魏序”:“自漢唐以來為邢州封域之內……自古明賢,指不勝屈,而鐵骨冰心為有唐賢相第一人者,莫過宋文貞公。”[14]2可知宋璟的個人品質深受時人贊頌。又據奉政大夫直隸順德府同知春榖王奐所作敘文載:“余始令浙奉化,簿書暇曾取舊志修輯之,覽其人物諸傳,知有宋文貞公苗裔存焉。宋氏在唐為南和人,朱梁時裔孫徙家奉化,至今號為望族。”[14]1可知,清朝官員王奐曾在奉化任官,在記錄財務出納的閑暇之余修訂舊縣志,發現人物傳中記載宋璟后裔定居于奉化。他們在唐末朱溫變亂時由南和遷入,到清朝已經發展為有威望的家族。
《南和縣志》卷八《藝文志》收錄明代宋佳所作的《崇祀先賢疏》,文中提到自己是浙江寧波府奉化縣人,本為唐朝丞相宋璟的十八世孫。宋璟曾孫宋嗣宗在唐朝末年定居奉化縣。“弘治十七年,直隸順德府南和縣知縣朱銳因彼戶絕無人,□取族弟宋伍來南和縣奉祀。”[14]4又收倫文敘所作《宋文貞公祠記》:“僖昭之季,或避地西蜀,或阻亂奉化,弗返……又移文奉化,求可以紹公后者。俾世承厥祀,得公十八世孫伍,奉公遺像暨牒以至。”[14]19這兩則材料明確了唐末至奉化的人是宋璟曾孫宋嗣宗,國家動蕩使他不能在任職期滿后返回南和,便留居并入籍奉化。至弘治十七年(1504),南和宋氏一脈無后人繼承,奉化的宋伍作為宋璟的第十八世孫便回到南和延續宋氏家族。由此似可看出,這兩處宋氏分支在明朝仍有一定的聯系。
又據乾隆《奉化縣志》卷九《名宦志》載,宋嗣宗在任奉化縣令時,興修水利設施引水灌田,深受百姓愛戴。朱溫篡唐之時,宋嗣宗堅持對國盡忠,依憑優勢組建了水兵和陸兵,抵御叛軍,之后宋氏家族繁衍壯大。當地人為紀念他的政治功績,在浦口建立風墩廟以奉祀他[15]2。反觀唐末奉化一地,正與宋林皋提及的先祖宋欽所遷之四明的位置一致。
但現今未有史料記載宋嗣宗習醫并精于女科,宋欽與宋嗣宗所處年代相隔兩百余年,暫時無法證明兩者之間有親屬關系。因此,宋林皋將宋璟作為醫學始祖一事亦可存疑。
三、《宋氏女科撮要·敘》的文獻價值
由以上論述可知,《宋氏女科撮要》的敘文中有多處記述尚可存疑:其一,宋氏先祖所居之“郢州”一地應為誤記;其二,宋氏先祖宋欽所任“子城使”一職在北宋末年確實存在,但史料中缺乏對宋欽的記載,不可被證實;其三,宋林皋將宋璟追溯為女科始祖,但正史、碑刻等文獻中并無宋璟精通醫學的記載。方志材料中雖提及宋璟曾孫宋嗣宗在唐末移居奉化,但尚無材料指明宋嗣宗懂醫以及他與宋欽是否有親屬關系。
又因中古墓志、明清方志及族譜中多見攀附之事,文字撰寫者會將墓主的祖先追溯為過往的賢哲、名臣等有社會地位的人物,或將其家族遷徙放到某一影響較大的社會動亂時期。葛劍雄在《研究中國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一文中提到,一般的家譜多會借助歷代圣賢、名臣等人來塑造自己的祖先世系。這樣的先賢大多出自北方黃河流域,于是這些家譜撰寫者就為自己的家族構建出一段從黃河遷徙而來的光榮歷史[16]。王朝更替之時社會混亂,民眾忙于謀生或遷徙,所以后世多會將戰亂期作為擬寫先祖、攀附先賢的時間縫隙,趁著戰爭造成的史料損毀和記載缺失的機會進行主觀性的始祖建構,其中也就帶有一定的褒揚情感色彩。
因此,從始祖建構和攀附的視角考察此敘文,我們可推知,宋林皋以宋璟為醫學始祖,其目的或是為了增長家族門面,塑造源遠流長的女科發展史和祖源記憶,試圖使家族為社會所認可。宋璟能夠成為被攀附的對象,多是因為他的個人德行和政治功績,由此可知明人對宋璟仍是褒揚的態度。宋林皋將宋璟定為醫者身份,也可能是將女科醫學與前朝名臣聯系在一起,塑造自身發展的政治合法性。
另外,敘文中提到宋璟夫人余氏專于婦女一科,李志生在《中國古代女性醫護者的被邊緣化》一文中曾把余氏當作士人家族女醫的典型案例[17]。之后在《中國古代婦女史研究入門》“中國古代的婦女醫護”一講中仍沿用余氏一例[18]267-268。由上文分析可知,現今不能確定宋璟精于醫學,因此余氏“竊”其醫術的記述亦不可被證實。又據顏真卿《大唐故尚書右丞相贈太尉文貞公宋公神道之碑》載,宋璟夫人為滄州長史崔藝之女,慈愛而有威嚴,輔佐宋璟且德行無虧[19]20。宋璟作為玄宗朝的名臣,以唐朝著姓博陵崔氏為妻也符合當時士人娶世家女的社會風尚。且此神道碑文為顏真卿所撰寫,后由宋璟之孫宋儼立碑,其中所載當不為虛。因此,宋璟夫人余氏及其女醫身份皆存疑。
再者,宋林皋撰寫此醫書,是源于“臺郡樂清邑三州范君之請”。由此來看,范君或許才是宋氏女科的真正宣傳者,至于其與宋氏家族有何關聯,我們至今無從得知。因此,敘文中的多處文字仍需琢磨,我們在引用時也應謹慎考慮其精確性和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