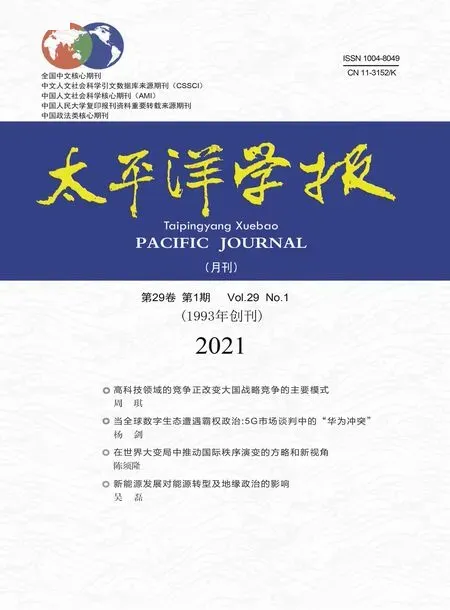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正改變大國戰略競爭的主要模式
周 琪
(1.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100720;2.同濟大學,上海200092)
在2017年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2018年1月發布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中,特朗普政府都把中國稱為“修正主義者”和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者”。①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7,p.2.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更是聲稱,“國家間的戰略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者,現在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擔憂”。②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8,p.1.從此,大國競爭成為美國與中國打交道時的關鍵詞,而且美國稱當今時代為“大國競爭時代”。壓制中國經濟的發展,阻止中國高科技領域研發和生產的快速發展帶來綜合國力的增強,成為美國政府的當務之急。其出現的第一個跡象是,2018年3月22日,當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在為當天下午將要宣布的對華貿易制裁在國會作證時,強調特朗普政府將重點對中國一些高科技產品加征關稅,如新的先進信息技術、自動化機床和機器人,“因為中國打算投入幾千億美元,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如果讓中國如愿以償,將會對美國非常不利”。①“U.S.Trade Representative Robert Lighthizer Testified before 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on Trade Policy and the Recent Steel and Aluminum Tariffs Announcement from the White House,”CSPAN,March 22,2018,https://www.c-span.org/video/?442748-1/us-trade-representative-lighthizer-testifies-steel-aluminumtariffs&start=317.
伴隨著貿易制裁,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發展的打壓逐步升級。雖然特朗普在2020年的大選中落敗,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成為新一任的美國總統,但美國對華政策決策所處的國內外環境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而且在對華政策上兩黨政治家已經形成一些重要共識,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美國必須采取更為強硬和有效的對華戰略來應對中國的競爭”。在拜登政府執政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及外交策略會發生一些調整,如將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戰略威脅”。用拜登的原話來說就是,“美國目前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俄羅斯,因為它破壞了我們的安全和同盟關系”,“最大的競爭對手是中國”。②“Biden Says Russia Key Threat to US,”TASS,October 26,2020,https://tass.com/world/1216217.但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不會完全回到奧巴馬政府時期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路線,他仍將注重“大國競爭”,并在此框架下與美國的國際盟友攜手處理對華關系。
一、高科技領域競爭的含義
“大國競爭時代”這個概念在對高科技發展狀況進行的分析中被越來越多地使用。在美國與中國展開的大國競爭中,日益明顯的事實是,高科技被視為競爭的重點領域。人們普遍認識到,能否在高科技發展中占據領先地位,不僅將決定一國能否在經濟發展中占得先機,而且也將為其帶來更大的國家安全保障。
信息技術革命為大國科技競爭創造了基礎和平臺。大國在科技領域里的競爭主要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過程中展開的,可以說,假若沒有第四次工業革命,就不會有如今日益激烈的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前三次工業革命分別以蒸汽機、電力和數據來識別,而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不同,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信息技術(IT)為核心,與此相應的是,信息技術已成為現代大國財富和競爭優勢的基礎以及地緣政治權力的來源。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物聯網、自動駕駛汽車、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技術、材料科學、能量存儲和量子計算等新技術的應用,“將以積極的方式徹底改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第四次工業革命“是新興大國競爭時代的關鍵因素”。③T.X.Hammes and Diane DiEuliis,“Contemporary Great Power,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 Factors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Thomas F.Lynch III,ed.,Strategic Assessment 2020,Into a New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2020,p.105.
不僅如此,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降低精密制造和先進制造的價格,從而產生了新一代更小巧、更智能、更便宜的武器。④Ibid.,p.xx.甚至有人認為,“或許全球范圍內技術的最大飛躍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日益普及的技術獲取途徑。10年前,分析家預測,到2020年,三分之二的人類將擁有一部智能設備,每部手機的計算能力都具有超過美國宇航局將人類送上月球所需的計算能力”。如今,這些預測在許多方面被證實。第四次工業革命“大大擴展了世界各地人們的聯系、協作和學習能力。更重要的是,這種轉變釋放了人才和創新能力,永久改變了可以在新的全球經濟中競爭的人及其競爭方式。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加速了所有這些趨勢”。⑤Karen Kornbluh,Sam DuPont,and Eli Weiner,“Ideas for Digital Democracy,”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November 2020,p.5,https://www.gmfus.org/digital-innovationand-democracy-initiative.而且,隨著“大國競爭時代”制造業的持續快速變化,出現了一個關鍵問題:哪個國家能最快、最有效地適應這場革命,成為更具競爭力的國家。
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委托撰寫的關于高科技領域里競爭的報告于2020年11月問世,這是包含8篇分報告的系列報告,其中一篇報告的作者寫道:“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來臨時,許多最重要的相互依存關系都與現代技術相關聯。”因此,與這些技術相關的思想、信息、商品、服務和人才流動的互動成為競爭的空間。①Richard Danzig and Lorand Laskai,“Symbiosis and Strife,Where Is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Bound?”JHUAPL,November 2020,p.7,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Danzig-Laskai.pdf.這些報告的十幾位作者都含蓄或明確地預測,中美將在貿易、技術和金融方面競爭優勢地位。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上述系列報告的兩位編者理查德·丹齊格(Richard Danzig)和羅蘭·拉斯凱(Lorand Laskai)敏銳地覺察到:“令人驚訝的是,對中美關系的戰略思考現在普遍沒有像過去十年對美蘇關系的思考那樣,開始進行一場對重大戰爭風險的反思。雖然人們普遍認識到,存在發生戰爭的危險,但戰爭可能由尚無法確定的原因引起,如意外事件、臺灣問題或其他原因”,因而兩國都在密切關注對方的軍事力量建設。然而,他們發現,無論是這些報告的作者還是兩國決策者,都不認為未來幾十年會爆發一場重大的戰爭,其證據是,假若這些人認為這一期間有發生這種戰爭的可能性,他們會提倡封鎖和禁運、大幅增加軍事投資,以及比這一系列討論中所顯示的要嚴厲得多的立場”。②Ibid.,p.8.
在競爭能夠產生效果的范圍內,對戰爭功能的認識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因為“顯然,美國和中國都不想征服和占領對方”。③Ibid.,pp.7,9.在大戰并不迫在眉睫的情況下,非軍事領域里的競爭,如貿易、經濟、金融和科技成為大國競爭的集中領域。如今,在電信、半導體、人工智能、生物科學和太空等高科技領域里的競爭,不僅展現為新的國家競爭模式,而且被利用來作為打敗競爭對手的武器,例如,對高科技產品出口的限制,以及其最極端的形式——科技“脫鉤”。在經歷了40年中美在科技方面的相互依賴之后,美國的口號變成了“分離”“脫鉤”和“脫離”。據此一些人甚至認為,至少在未來的十年里,應當把競爭的重點放在武裝沖突以外的問題上,從當前的演進來看,特別是放在高科技領域里的競爭上。進而言之,在用科技競爭/裝備競賽可以達到目的的情況下,大國之間的戰爭不是當務之急,不必急于為戰爭支付高昂代價。這也正應了美國決策者對“大國競爭時代”的構想。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大國競爭在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的托馬斯·F.林奇(Thomas F.Lynch III)主編的著作《2020年戰略評估,進入大國競爭的新時代》(Strategic Assessment2020,Into a New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中被列為中位的,亦即中等強度的互動關系,離戰爭相差兩個等級。④Thomas F.Lynch III,ed.,Strategic Assessment 2020,Into a New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2020,p.3.詳見下圖:

圖1 大國互動狀態序列
中國在高科技領域里的研發水平和能力與美國相比,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但近十幾年來,競爭一直以有利于中國的效果改變全球力量的平衡,并且即將進入一個被稱為“戲劇性”的新階段。⑤Ibid.,p.xx.中國的追趕速度令美國深感擔憂,特別是在美國的許多戰略家終于承認美國處于相對衰落,并且對美國保持優勢地位的能力信心不足的情況下。一些美國科技專家認定,“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大國競爭的基礎已經改變。對工業資源的控制曾經是地緣政治力量的關鍵所在,如今對信息資源的控制最為重要”。“信息而不是物質資源,現在是地緣政治實力的基礎。就像信息技術(IT)在過去十年中逆轉了以物理為基礎的商業與以信息為基礎的商業的相對價值一樣,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人工智能將顛覆基于物理和信息的大國政策與政治的有效性。”他們認為,“中國目前正大力投資三項關鍵的新信息技術——第五代移動通信網絡(下文簡稱5G)、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作為其信息戰略的一部分,這將極大地提高其對全球信息流的控制力。美國決策者必須認識到新現實并采取行動”。①Richard Andres,“Emerging Crit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in Thomas F.Lynch III,ed.,Strategic Assessment 2020,Into a New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2020,pp.139,140.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感到,美國在全球科技中的主導地位已經受到挑戰。“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在先進技術方面取得全球領導地位。下一屆政府將繼承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在該領域最脆弱的全球地位。在今天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未來30年的技術變化將使過去30年顯得微不足道。下一屆政府還將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長期影響,以及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合法和非法手段迅速侵蝕美國技術優勢而帶來的急劇變化的全球格局。”在競爭中贏得這場斗爭,“不僅會影響美國經濟,還會影響整個世紀。下一屆政府必須制定全面的技術議程,以刺激美國的創新”。②Karen Kornbluh,Sam DuPont,and Eli Weiner,Ideas for Digital Democracy,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November 2020,p.3,https://www.gmfus.org/digital-innovationand-democracy-initiative.
《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犀利地點明,特朗普政府視高科技競爭是一場“新軍備競賽”,并提出應如何估價這場軍備競賽。文章說,“美國政府認為,世界正在加入一場新的軍備競賽。這場軍備競賽涉及的是技術而不是常規武器,但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同樣嚴重的危險。在當今時代,最強大的武器(無核武器)是由網絡控制的,無論哪個國家主導5G,都將在21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獲得經濟、情報和軍事上的優勢”。③David E.Sanger,Julian E.Barnes,Raymond Zhong and Marc Santora,“In 5G Race with China,U.S.Pushes Allies to Fight Huawei,”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6,2019,https://www.nytimes.com/2019/01/26/us/politics/huawei-china-us-5gtechnology.html?_ga=2.209569618.1726742918.1609863825-543320348.1586029176.
2020年2月,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也充滿激情地談到了美國維持科技領先地位的緊迫性。他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全球范圍內的緊張狀態和競爭的新時代。”“毫無疑問,中國的技術推進對美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自19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是創新技術的世界領導者。正是美國的技術實力使我們變得繁榮和安全。我們的生活水平、我們為年輕人和子孫后代不斷擴大的經濟機會,以及我們的國家安全,都取決于我們持續的技術領先地位。”④2020年2月6日,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應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CSIS)邀請,在“中國行動計劃會議”(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上所作的主題演講,參見“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s Keynote Address: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Center for Strategic&International Studies,February 6,2020,https://www.csis.org/analysis/attorney-general-william-barrs-keynote-address-china-initiative-conference.
高科技競爭已經構成了這個時代的特點。雖然美國政府口口聲聲說,從國際關系的角度講,當前的時代是“大國競爭時代”,并把戰略競爭的對象確定為中國和俄羅斯,而不是與美國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相同的西方發達國家,但在日益成為戰略競爭重點的高科技領域,由于俄羅斯的競爭力已經遠遠落后于中國,美國所設想的競爭對象其實就是中國(這在下文關于中美在高科技各領域的競爭的論述中可以明顯看出),因此,在高科技領域的大國競爭就體現為中美之間的競爭。許多西方分析者都在談論中美在各高科技競爭中追求相互主動“脫鉤”,但事實是,美國是先發制人的一方,是美國開啟了大國科技競爭的新時代,并把“脫鉤”作為阻攔中國獲得先進技術和設備的手段,試圖延緩中國高科技的發展,以此維持美國的實力領先地位,而中國則是處于被動應對的一方。中國提出的經濟“雙循環”和科研自主的努力,最初不過是對美國來勢洶洶的制裁手段的應對之策。
當今最引人注目的科技領域是人工智能、電信、半導體、太空及生物科學,在下文所討論的科技領域競爭中,僅舉其中三個相互交織的領域為例,即人工智能、電信和半導體。
二、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①本章中關于中美人工智能發展狀況的對比,部分基于作者半年前的另一篇論文:周琪、付隨鑫:“美國人工智能的發展及政府發展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6期,第28-54頁。
在大國競爭中,人工智能領域不僅是競爭的一部分,而且日益被看作是一個核心部分。②Christine Fox,“An Entwined AI Future:Resistance Is Futile,”JHUAPL,November 2020,pp.vi,11,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Fox-AI.pdf.
一般在提到人工智能時,可以把人工智能通俗地理解為“機器學習、自動推理、機器人、計算機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NLP)的總稱”。③Katharina E.H?ne,Lee Hibbard,Marília Maciel,Katarina An?elkovi,Nata?a Peruica,and Vird?inija Saveska,“Mapp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the Conduct of Diplomacy,”Diplo Foundation,January 2019,pp.6,10-11,https://www.diplomacy.edu/sites/default/files/AI-diplo-report.pdf.人工智能對經濟將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它不僅催生了圖像識別、語音識別和機器翻譯等新興產業,其更廣泛的應用是所謂的“AI+”,即人工智能為醫療、制造、運輸、金融、零售、教育和農業等傳統行業賦能,提高這些行業的智能化水平,推動傳統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向“工業4.0”轉變,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ricewaterhouse Coopers)預測,到2030年,人工智能對全球經濟的累積貢獻可能高達15.7萬億美元,其中6.6萬億美元源自生產率的提升,9.1萬億美元源自消費,今后對美國經濟的累積貢獻將達到3.7萬億美元。④Willie Schoeman,Managing Director at Accenture Technology,“W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Future of Growth,”https://www.accenture.com/za-en/company-news-release-why-artificial-intelligence-future-growth,訪問時間:2021年1月15日。
最近十余年,人工智能在美國得到迅速發展。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研發方面居于全球領先地位。其中,學術機構仍是美國人工智能研發的主力,企業界的作用也在不斷增強。人工智能已在美國商業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催生了眾多新興產業,并提升了傳統行業的智能化水平,從而產生了可觀的經濟效益。美國也在積極把人工智更多地應用于政府部門,特別是軍事領域。
一份對美國、中國、歐洲人工智能發展的比較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在六項指標⑤六項指標是人才、研究、開發、采用、數據和硬件。中,美國處于絕對領先地位,中國位居第二,歐洲居第三。根據對2018年在21個主要人工智能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的作者獲得博士學位情況的調查,其中有44%的人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比在歐盟(估計為21%)和中國(11%)的總和還多。⑥Field Cady and Oren Etzioni,“China May Overtake US in AI Research,”Allen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y 13,2019,https://medium.com/ai2-blog/china-to-overtake-us-in-airesearch-8b6b1fe30595.這在很大程度上為美國提供了人工智能人才的優勢。根據人工智能論文和專利記錄,在雇用人工智能人才最多的20家公司中,2017年有一半設在美國。這10家美國公司合計擁有1 623名人工智能人才。相比之下,歐盟有6家這樣的公司,總共有522名人工智能人才。排名前20位的唯一一家中國公司是華為,擁有73名相關人才。⑦“《2018年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中國經濟學人》雜志官方公眾號,2018年7月,第32頁,https://mp.weixin.qq.com/s/_3UVjYe7g8ws81sH0YDZQQ。
美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根據全球最大的引文數據庫Scopus的檢索結果,2018年美國共發表了16 233篇與人工智能有關的同行評審論文。論文數量的快速增長主要發生在2013年之后,五年內增長了2.7倍。同一時期,中國和歐盟的人工智能論文數量也增長迅速,而且每年發表論文的數量明顯超過美國,兩者2018年的發表數量分別高達24 929篇和20 418篇。⑧Raymond Perrault,et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19,Data,”Stanford 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stitute,pp.14,21,33,https://hai.stanford.edu/sites/g/files/sbiybj10986/f/ai_index_2019_report.pdf,訪問時間:2021年1月15日。
不過,美國人工智能論文的質量一直大幅度領先于其他地區,2018年美國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為2.23次,而中國為1.36次。美國每個作者被引用的次數也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0%。然而,中國與美國在這方面的差距正在縮小。艾倫人工智能研究所2019年對人工智能論文進行的分析發現,在被引用最多的10%的人工智能論文中,美國所占份額從1982年的47%下降到2018年的29%,而中國從1982年的大約為0增長到26.5%。①Field Cady and Oren Etzioni,“China May Overtake US in AI Research,”Allen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y 13,2019,https://medium.com/ai2-blog/china-to-overtake-us-in-airesearch-8b6b1fe30595.
美國人工智能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在迅速增長。2010年至2019年,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工作崗位占總工作崗位的比例從0.26%上升到1.32%。其中,機器學習所占的比例最高,占到總工作崗位的0.51%。②Martijn Rasser,et al.,“The American AI Century:A Blueprint for Action,”CNAS,December 17,2019,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he-american-ai-century-a-blueprint-foraction.信息產業對人工智能人才的需求量最大,其次是高科技服務業和金融保險業。
美國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公司數量及對這些公司的投資也在快速增長。美國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超過5 000家,數量遠超其他國家。排名第二的英國大約有1 000家,中國大約有300多家。③“Govern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adiness Index 2019,Data,”Oxford Insights,Oxford Ins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https://www.oxfordinsights.com/ai-readiness2019,訪問時間:2021年1月15日。在全球排名前100的人工智能初創公司中,77家位于美國。2018年,美國人工智能初創公司共獲得187億美元的私人投資,相當于2013年的7.6倍,大約占全球總量的46%。④Bastiane Huang,“When Will We See the First Wave of AI IPOs?”Towardsdatascience,December 16,2019,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when-will-we-see-the-first-wave-of-ai-ipos-8ab4ddda6657.在人工智能公司的風險資本和私募股權融資方面,美國也居于首位。2017年至2018年,美國的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融資數額約為169億美元。其次是中國,約為135億美元。排第三的是歐盟,約為28億美元。⑤Daniel Castro,Michael McLaughlin and Eline Chivot,“Who Is Winning the AI Race:China,the EU or the United States?”Datainnovation,August 19,2019,https://www.datainnovation.org/2019/08/who-is-winning-the-ai-race-china-the-eu-or-the-unitedstates/.
美國在發展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公司中處于領先地位。美國公司在專利和主導性人工智能收購方面表現強勁,例如,在15個機器學習子類別中,微軟(Microsoft)和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在8個子類別中申請了比其他任何實體公司都更多的專利,包括監督學習和強化學習類。美國公司在20個領域中的12個領域的專利申請處于領先地位,包括農業(迪爾公司)、安全(IBM),以及個人設備、計算機和人機互動(微軟公司)。中國科學院則在深度學習方面申請了最多的專利,西門子公司(德國)在神經網絡方面申請了最多的專利。⑥“WIPO Technology Tren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Raw Data Chapter 4 figures,fig4.7,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March 2018,https://www.wipo.int/tech_trends/en/artificial_intelligence/.
此外,2012年至2016年,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人工智能專利申請為3 677項,居全球之首。Alphabet公司⑦Alphabet是 谷 歌 重 組 后 的“傘 形 公 司”(Umbrella Company)的名稱。Alphabet采取控股公司結構,把旗下搜索、You-Tube和其他網絡子公司與研發投資部門分離開來。Alphabet將取代Google INC成為上市實體公司,所有谷歌的股票都會自動轉換為相同數量的Alphabet股票,并享有同等權利,而新谷歌將成為的全資子公司。有2 185項,微軟有1 952項,均位列全球前五名。1960年至2018年,專利申請人在美國專利數據庫(USPTO)中申請了28 031項高引用率專利,這大大超過了歐盟的2 985項和中國的691項。⑧See“WIPO Technology Tren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Raw Data,”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https://www.wipo.int/tech_trends/en/artificial_intelligence/,訪問時間:2021年1月15日;Daniel Castro,Michael McLaughlin and Eline Chivot,“Who Is Winning the AI Race:China,the EU or the United States?”Datainnovation,August 19,2019,https://www.datainnovation.org/2019/08/who-is-winning-the-ai-race-china-the-eu-or-the-unitedstates/.
目前,美國已經制定了完備的人工智能發展戰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制定人工智能發展戰略時,一直把中國當作首要的比較和防范對象,把與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里的競爭視為爭奪世界領導權的戰略競爭,密切關注中國在發展人工智能方面的動向,竭力防止中國獲得該領域的領先地位。
早在2016年10月至12月,奧巴馬政府就發布了《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規劃》等多份與人工智能發展相關的重要文件。2019年2月,特朗普總統簽署了題為《保持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on Maintai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啟動了“美國人工智能倡議”。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正式發布了《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2019年更新》(The National A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2019 Update),對2016年奧巴馬政府末期的戰略進行了更新,從而形成了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研發戰略。特朗普政府為美國人工智能發展設立了目標和原則,成立了指導和實施機構,注入了大量資金,并積極推動數據開放、標準制定、人才培養、政府與企業合作,以及風險管控。值得回味的是,當初在中國國內不那么為人知曉的2017年國務院印發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卻在國外,尤其是美國的眾多政策分析報告中被反復提及,并且成為刺激美國制定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的重要因素。
除美國外,其他國家也都紛紛制定了本國的國家人工智能發展戰略,以應對人工智能對國際關系帶來的沖擊。許多國家的政府都發布了本國人工智能發展戰略報告,旨在引導本國的國家戰略。由于認識到人工智能領域“早期移動用戶能夠獲得顯著競爭優勢”,這些國家都渴望成為首批開發人工智能的國家。自2017年以來,有關國家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的報告不斷涌現,出現了一場在“人工智能領域充當全球領先者的競爭”。
各國的戰略報告有一個共同的突出特點,即強調本國必須在人工智能方面保持競爭力,或朝著在人工智能領域發揮主導作用的方向邁進。在這些報告中,受到最多關注并被反復提及的是中國以及中國政府于2017年發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這些報告認為,“中國的戰略在這方面設定了三個非常雄心勃勃但也是非常具體的目標”,到2030年,中國要在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方面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在發展人工智能方面的意識與國際上許多主要國家基本同步。在2017年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發布兩個月之后,普京也公開宣布俄羅斯追求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他斷言:“成為這一領域的領袖將統治世界”。①Tom Simonite,“For Superpower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els New Global Arms Race,”Wired,August 8,2017,https://www.wired.com/story/for-superpowers-artificial-intelligence-fuelsnew-global-arms-race/.
在人工智能方面,美國最擔心的競爭對手是中國。美國國會研究局2019年的報告明白無誤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人工智能市場的潛在國際競爭對手正在給美國制造壓力,迫使其在軍事人工智能的創新應用方面展開競爭……迄今為止,中國是美國在國際人工智能市場上最雄心勃勃的競爭對手。”②“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Updated January 30,2019,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p.19,https://fas.org/sgp/crs/natsec/R45178.pdf.在美國看來,全球只有中國有能力在不久的將來與美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相抗衡。“在人工智能時代,就技術發展或國家實力而言,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追趕美國或中國,而美國和中國都無法獨占這一領域或脅迫對方。”③Ryan Hass and Zach Balin,“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rookings,January 10,2019,p.5,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us-china-relations-in-the-a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根據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一份得到廣泛引用的研究報告,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為全球經濟帶來的15.7萬億美元的財富中,美國和中國將占70%。目前,在全球涉及人工智能的公司中,約有一半在美國運營,三分之一在中國運營。
然而,隨著在特朗普政府時期中美關系的整體惡化,美國越來越多地轉向使用傳統工具來保護人工智能。2018年8月通過的《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要求美國商務部考慮控制“新興的”和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基礎”技術。①Michael Brown and Pavneet Singh,“China's Technology Transfer Strategy:How Chinese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Technology Enable a Strategic Competitor to Access the Crown Jewels of U.S.Innovation,”Silicon Valley:Defense Innovation Unit Experimental,2018,https://admin.govexec.com/media/diux_chinatechnologytransferstudy_jan_2018_(1).pdf.50 USC§4817.美國商務部隨后發布了一份征求公眾反饋的通知,人工智能就位列清單之中,②關于這個清單的詳細情況,可參閱池志培:“美國對華科技遏制戰略的實施與制約”,《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6期,第34頁。隨后,基于人工智能的地理空間分析應用首次受到控制。③Department of Commerce,“Review of Controls for Certain Emerging Technologies,”15 C.F.R.744,Federal Register,Vol.83,No.223,November 19,2018,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8/11/19/2018-25221/review-of-controls-for-certain-emerging-technologies.
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中,芯片是關鍵。人工智能需要高效的專門芯片,并為高級機器學習算法進行優化。預計到2025年,這些“人工智能芯片”將占價值4 500億美元半導體芯片市場的20%。④MacroPolo,“Big Picture:AI Chips,”https://macropolo.org/digital-projects/supply-chain/ai-chips,訪問時間:2020年12月27日。目前,在中國使用的半導體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由國內生產。⑤Josh Horwitz,and Sijia Jiang,“China Chip Industry Insiders Voice Caution on Catch-up Efforts,”Reuters,June 13,2019,https://news.yahoo.com/analysis-china-chip-industry-insiders-1217443 12.html.美國主要半導體公司從中國市場獲得的利潤高得不成比例,而且其中大部分利潤都用于維持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優勢的研發。為了阻止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的追趕,美國正竭盡全力阻止世界各地的公司使用含有美國技術的設備和軟件為華為生產或設計芯片。
對于美國的做法能否奏效,普林斯頓大學組織撰寫的系列報告中關于中美人工智能競爭部分的作者克里斯汀·福克斯(Christine Fox),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和控制人工智能傳播的難度源于其通用技術的特點。人工智能不是一種可以控制的“物品”,它是由基于數學的算法組成的,這些算法最終將普遍應用于人類的所有事務。人工智能正變得與20世紀的電力、數字計算,甚至算術一樣普及。因此,人工智能的基礎不可能也不應當受政府行為的控制。他贊同政府控制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某些特定應用程序和數據集,但他斷定,試圖切斷與中國研發活動的聯系不會推動美國前進,也不會顯著延緩中國的進步,而只會拖美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后腿。⑥Christine Fox,“An Entwined AI Future:Resistance Is Futile,”JHUAPL,November 2020,pp.vi,11,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Fox-AI.pdf.歸納起來,他列出的原因為:
第一,盡管中國不太可能在半導體制造領域迅速追趕,但中國正在取得進展。在內存芯片或閃存芯片等更基本的芯片技術方面,中國已經具備了競爭能力,美國竭力阻礙芯片龍頭企業向中國供貨,將激勵中國投入更多的資金,并專注于發展本土有能力的芯片產業。但如果給予中國獲得美國芯片的可靠和互利的渠道,可以降低中國發展本國研發能力的動機,從長遠來看可以保護美國的市場和供應鏈。
第二,全球開發人工智能應用生態系統不可能排除中國,“脫鉤”最終將損害美國公民的利益和福祉。
第三,退出與中國的交流與合作,實際上意味著退出與世界主要國家的交易,包括美國的貿易和安全伙伴。美國不僅可能會失去很大一部分市場,還會退出關于人工智能技術在社會中發揮適當作用的討論。
第四,不與國際標準制定組織經常交流,不與其他國家合作,美國將無法對全球應用規范產生影響。特別是,中國已經制定了成為“標準發布國”的明確目標,并協調政府、行業和學術界開展標準工作,還經常在國際組織舉辦會議期間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伙伴組建投票團。⑦作者的這些觀點散見在該報告的以下各頁:Christine Fox,“An Entwined AI Future:Resistance Is Futile,”JHUAPL,November 2020,pp.6,8,9,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Fox-AI.pdf.
總而言之,中國的優勢是龐大而強勁的市場、人才和熟練的培訓項目,這些優勢將不可避免地使中國成為強大的人工智能競爭對手。美國必須對自身市場的穩固性、人才和培訓項目進行相應的投資。“讓美國更強大比讓中國更弱更有效,試圖通過‘脫鉤’使中國更弱,只會削弱美國”,因為“脫鉤”會將美國與世界上許多繼續與中國做生意的國家隔離開來,同時切斷美國獲得人工智能人才和創新的主要來源。①Christine Fox,“An Entwined AI Future:Resistance Is Futile,”JHUAPL,November 2020,p.vi,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Fox-AI.pdf.
三、電信行業的競爭
在電信行業,5G成為觸動國家科技競爭“神經”的第一個重要領域。愈演愈烈的競爭主要發生在中美之間。
中美原本在電信行業里有著互聯互通的長久歷史。根據保羅·特里奧羅(Paul Triolo)②保羅·特里奧羅領導歐亞集團的地理技術業務,重點關注全球技術政策、網絡安全、互聯網治理、信息與通信技術(ICT)監管問題及5G部署等新興領域。他在美國政府中擔任高級職務超過25年,主要關注中國作為科學技術和網絡大國的崛起,其關于全球技術問題以及中美貿易和技術競爭的觀點,經常被媒體所引用。的看法,中國參與全球電信業的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90年以前。在這一時期,中國電信業嚴重依賴國外電信設備,從最初僅限于使用西門子、日本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和阿爾卡特的設備,到后來擴大到包括朗訊、愛立信和北電的設備。底層的傳輸網絡也對國外設備有同樣的依賴。
第二階段為1990—2005年。其間,華為在1993年開發了C&C08交換機,并迅速獲得了市場份額。到2000年,中國企業③主要是華為、中興通訊、大唐和巨龍,它們當時被并稱為“巨大中華”。已經成為朗訊、北電、西門子和阿爾卡特等公司在大型存儲程序控制交換機方面的競爭對手,同時在傳輸設備、光纖電纜和其他固定線路通信設備方面也能夠與外國公司展開競爭。中國聯通和移動通信相繼成立,并主導了中國的電信業。1997年,華為推出了第一款無線產品和全球移動通信基礎設施系統,并開始大舉進軍國外市場。
隨著中國公司在光纖電纜系統基礎設施和數據中心等其他關鍵領域的發展,中國固話網絡中的所有西方設備幾乎全部被國產設備所取代。盡管中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排除在3G標準流程之外,但是華為積極參與4G標準制定,并申請了近四分之一的4G專利。
第三階段為2005—2015年。在這十年中,中國公司擴大了其在移動通信標準方面的影響力,華為和中興通訊成長為全球競爭對手。同時,在中國國內市場上,移動電信網絡開始了快速、強勁的增長,并在中國新的移動通信領域里開始全面占據主導地位。
第四階段從2015年至今。中國公司在移動電信基礎設施和消費產品領域已經占據主導地位,從而降低了美國技術帶來的供應鏈風險。在近十年內,華為和中興通訊從在全球電信市場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力,發展到占據全球移動基礎設施的40%~45%。2013年,美國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曝光以來,中美之間的政治和技術沖突不斷加劇,中國為此開始發展“安全且可控”的技術供應鏈。這一時期,中國5G部署整體戰略趨于完備,引起美國的警覺,促使兩國的電信產業進一步疏遠。直到2018年底,美國政府才意識到5G時代正在到來,而美國缺乏能夠挑戰華為在5G領域主導地位的公司。④對四個階段的劃分見Paul Triolo,“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US-China Context:Evolving toward Near-Complete Bifurcation,”JHUAPL,November 2020,pp.1-3,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Triolo-Telecomms.pdf。
在2018年7月舉行的“五眼”國家情報部門的秘密會議上,參會國就遏制華為的戰略達成了一項協議。在接下來的兩年,美國國務院和國務卿邁克爾·蓬佩奧不斷把華為描繪成一個“不受信任的企業,違反了美國的制裁令,并竊取競爭對手的知識產權”。為了進一步遏制華為5G業務的開展,美國在2019年初以存在“銀行欺詐”和“違反制裁令”為由,對華為提起刑事訴訟。4月底,美國又以影響“情報合作”為由要求英國拒用華為5G設備。美國負責網絡空間、國際通信和信息政策的副助理國務卿羅伯特·斯特雷耶(Robert Strayer)警告說,華為“不是一家值得信賴的供應商”,在5G網絡中使用華為的任何技術都存在“風險”,并稱如果英國同意采用華為5G技術,可能將影響該國與美國的情報合作。①“專家解讀:涉5G安全的‘布拉格提案’劍指何方”,中國新聞網,2019年5月16日,https://www.chinanews.com/cj/2019/05-16/8838548.shtml。最終在2019年5月,在由美國主持召開的“布拉格5G安全會議”上起草的“布拉格提案”,提出了將供應商原產國的政治和法律結構作為對使用該供應商而進行的風險評估的依據。在整個2019年,歐洲各國政府和歐盟委員會都在討論如何改善5G供應鏈的安全,以滿足美國的要求,同時保留其國內運營商的靈活性,但政府和商界在此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
以英國而論,英國政府與華為公司有著長期的合作關系,2010年英國政府、英國電信公司就與華為共同成立了網絡安全評估中心,以檢測華為在英國部署設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根據英國政府與華為達成的協議,華為的設備被允許納入英國的4G網絡。2020年1月下旬,基于網絡安全評估中心的評估,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決定允許華為進入英國的5G網絡,但附帶條件是運營商在無線接入網(RAN)中使用華為設備的比例不得超過35%。
然而,在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對華為采取進一步的制裁措施之后,局勢發生了變化。英方在進行內部評估后認為,一方面,美國加強對華為的技術與設備出口管制迫使華為不得不調整其供應鏈,開始自主研發部分產品;另一方面,英國政府與華為共同建立的網絡安全評估中心本身已受到美國的制裁,使其不能履行原設定職能。基于此,英國政府最終認定,華為已無法滿足英國對5G網絡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②該信息來自2020年7月22日,本人及同事與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Barbara Woodward)等多名外交官的會談。美國的壓力迫使英國最終做出決定,在2027年之前從本國網絡拆除華為的所有設備。事實上,國外分析認為,在英國政府進行關于中國和華為的重大辯論期間,2020年新冠疫情流行引起英國國內對中國的反感,而到6月,英國國內對中國政府香港政策的不滿又加劇了這種情緒,這些也是英國政府作出此決定原因。③UK Government,“Huawei to Be Removed from UK 5G Networks by 2027,”press release from Department for Digital,Culture,Media&Sport;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July 14,2020,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huawei-to-be-removed-fromuk-5g-networks-by-2027.
大約在同一時間,歐盟委員會發布了緩解5G網絡安全風險的原則,其中包括一套歐洲成員國有權自行實施政策的自愿準則。2020年上半年,歐洲的辯論仍在繼續。由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領導的德國政府面臨來自聯邦議院越來越大的壓力,考慮對華為施加更嚴格的限制,而商業團體和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等主要運營商則反對采取更嚴格的措施。但是到2020年8月,像英國一樣,歐洲各國政府越來越意識到,美國針對華為供應鏈采取的行動,令人有理由擔心華為是否有能力繼續履行現有的和新的合同。④Jack Stubbs and Kate Holton,“UK Tells Telcos to Stockpile Huawei Gear in Face of U.S.Sanctions:Letter,”Reuters,June 19,2020,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britain-huawei/uk-tellstelcos-to-stockpile-huawei-gear-in-face-of-u-s-sanctions-letteridUSKBN23Q33R.
當中國開始制定和實施5G戰略時,美國竭力阻止具有領先優勢的中國電信供應商進入美國市場。2018年1月,華為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達成協議,通過該公司在美國銷售手機。幾天后,這家公司在國會和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巨大壓力下,取消了該協議。美國國會進而在2019年“國防授權法”(NDAA)第889條中加入了一項條款,禁止聯邦機構和接受聯邦政府資助的第三方購買華為或中興產品。2019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宣布把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及其位于26個國家的68家非美國關聯公司列入“實體清單”。①當一個企業被列入實體清單后,任何其他企業(包括中國企業)需要與其進行涉及《出口管制條例》所管轄物品的交易時,必須向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申請許可。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共發布三個系列的“實體清單”:實體清單(Entity List)、未確認清單(Unverified List)和軍事最終用戶清單(Military End-User List)。美國國防部也于2020年7月發布了詳細規則,要求向美國政府出售商品和服務的承包商必須證明未使用華為或中興產品。大約在同一時期,美國政府開始嚴格審查中國電信供應商的活動,并利用美國的“長臂管轄”制度限制它們獲得美國技術的機會。美國使用實體清單等工具來對付幾乎所有的中國科技領軍企業,包括中興通訊、華為、中國三星電子,以及在2019年10月已被列入實體清單的8家中國領先的人工智能和計算機視覺公司。②Paul Triolo,“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US-China Context:Evolving toward Near-Complete Bifurcation,”JHUAPL,November 2020,p.5,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Triolo-Telecomms.pdf.
到2020年5月上旬,當中國計劃于2021年初加速獨立網絡建設時,美國針對華為旗下海思半導體有限公司新的出口管制限制給中國的5G部署計劃帶來了嚴重障礙。最初,特朗普總統在2020年2月發布一條推文表示,他不想采取措施削弱美國公司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能力,但隨著新冠疫情在3—4月加速蔓延,特朗普因疫情的出現可能令其在大選中失利而遷怒于中國。4月,特朗普批準了一項針對海思及其關聯公司的規則,要求為指定公司生產半導體的第三方制造商必須申請政府許可,這意味著美國將在境外擴大針對華為的出口管制,從而削弱了臺積電(TSMC)為華為生產尖端半導體的能力。這一舉動被認為是中美科技和電信業關系的轉折點。③Ibid.,p.9.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采取更廣泛的行動,從美國基礎設施中移除中國設備。到2020年3月,美國商務部和其他政府機構一直在權衡行業意見,并考慮如何更好地執行2019年底發布的一項新規則,以實施特朗普總統2019年關于信息和通信技術(ICT)供應鏈安全的行政命令。新規則最初的目的是政府禁止在美國農村無線網絡升級中使用中國電信設備。但是,該規則可以適用更廣泛的領域,使美國政府能夠迫使本國供應商從其供應鏈中淘汰幾乎所有中國零部件。④Ibid.,pp.11-12.
接下來,新冠疫情的暴發打亂了美國原定于2020年初舉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這些會議預計將主要議題放在如何充實美國的5G整體戰略。5月初,美國國務院5G負責人基思·克拉希(Keith Krach)提出了一項新計劃,要求美國電信運營商向美國政府提供5G用戶服務,以確保政府的網絡通信以及使館之間傳遞的敏感數據不通過任何不能被信任的供應商,特別是中國的主要供應商華為和中興。這一計劃最初被稱為“清潔網絡”計劃,其目的也是為了向歐洲政府施加更大壓力,要求其禁止中國供應商推出5G網絡。
2020年8月,美國國務院將“清潔”概念擴展到運營商、應用程序、應用程序商店、云服務和光纖電纜系統。8月3日,美國國務院網站公布了一份所謂“5G清潔網絡”(5G Clean Networks)名單,宣稱目前全球已有27家運營商在5G網絡建設中放棄采用華為和中興設備,從而構建了“5G清潔網絡”,確保了“最高的安全標準”。⑤Roslyn Layton,“State Department's 5G Clean Network Club Gains Members Quickly,”Forbes,September 4,2020,https://www.forbes.com/sites/roslynlayton/2020/09/04/state-departments-5gclean-network-club-gains-members-quickly/?sh=7ed6eeb57536.當月,特朗普總統發布了兩項新的行政命令,禁止中國社交媒體應用TikTok⑥TikTok系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短視頻社交平臺。和微信在美國運營。8月下旬,美國商務部發布了第二份與中國軍方有聯系的中國公司名單,其中包括中國聯通,這使得中國三大手機通信運營商都被列入該名單(其他兩家是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到2020年底,美國對中美運營商層面的行業分離幾乎全部完成。⑦Paul Triolo,“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US-China Context:Evolving toward Near-Complete Bifurcation,”JHUAPL,November 2020,p.16,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Triolo-Telecomms.pdf.
除了向美國技術公司和第三方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停止向華為及其主要子公司供應設備外,美國還采取措施在運營商服務和光纜著陸站方面進一步分離電信行業。
2020年4月,美國根據一項行政命令設立了一個由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和國防部組成的跨部門團隊——電信小組(Team Telecom),該小組以國家安全為重點,跟蹤和批準外國電信運營商在美國境內運營的許可證申請,包括那些由外國公司提交的申請及連接美國和其他國家海底光纜的申請,其主要目標是中國。此后,“電信小組”正式更名為“外國參與美國電信服務部門評估委員會”。8月,國務卿蓬佩奧宣布了新的清潔運營商倡議,基本上認可了早些時候向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提出的撤銷中國運營商運營許可證的建議。
在此之前,連接美國和香港約13 000千米的太平洋光纜網絡項目已于2019年底接近完工。谷歌和臉譜(Facebook)是其主要支持者。然而,在2020年6月,美國電信團隊建議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拒絕頒發該電纜香港部分的許可證,反對香港作為著陸地點,并反對一家中國寬帶提供商——太平洋光數據通信公司的子公司鵬博士電信傳媒集團,作為寬帶合作伙伴。
所有起源于美國的跨洋電纜項目都要經過美國政府的嚴格審批,因此,美國若進一步中斷電纜的許可審批過程或對其造成不確定性,對于信息通信技術行業和互聯網的未來都具有深遠影響。海底電纜系統需要大量投資,通常涉及國際投資者和運營商財團,其交貨期較長,需要明確的經濟監管審批過程。由于目前對帶寬的需求已經超過了現有電纜的承載能力,美國若試圖限制在中國著陸的電纜監管方式,將對未來的電纜系統規劃造成極大破壞。①Paul Triolo,“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n US-China Context:Evolving toward Near-Complete Bifurcation,”JHUAPL,November 2020,p.16,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Triolo-Telecomms.pdf.
盡管美國在制定短期、中期和長期的5G戰略方面進展緩慢,但在少數領域,尤其是在對華問題上,已達成重大共識,即擴大美國政府在標準制定中的作用,其目的是“反擊”中國和中國公司在國際電信聯盟(ITU)和第三代移動通信伙伴項目(3GPP)標準制定過程中對美國的不利影響。美國政策的重點將是最終建立一個符合“適當的”和“負責任的”標準的新程序,這個程序可能把“敵對”國家或相關公司排除在外。②Ibid.,p.17.由于中美整體技術沖突愈演愈烈以及兩國電信行業的分離,這預示著未來在互聯網領域里可能有更廣泛的爭斗,也使得人們所擔心的中美在科技領域里的“脫鉤”有成為現實的可能。
不僅如此,電信網絡中的問題只是兩國之間更廣泛“脫鉤”可能性的一個子集,這種“脫鉤”正在向金融服務、跨境支付和數據系統等領域擴展。
美國之所以煞費苦心地打壓華為,是因為沒有一家美國公司能像華為那樣擁有廣泛的技術覆蓋范圍。華為在提出下一代互聯網架構、開發人工智能堆棧并對其開源、在新的區塊鏈項目上開展合作,以及參與從增強現實和虛擬現實到自動駕駛汽車、智慧城市和智能工廠等關鍵消費和工業應用領域,都是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歐洲電信供應商在移動基礎設施方面仍然具有很高的能力,但遠不及華為的技術或影響力。③Ibid.,p.20.
2020年2月6日,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行動計劃會議”(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上,道出了美國政府為何非要將華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動機:“5G技術處于正在形成的技術和工業世界的中心。本質上,通信網絡不再僅僅用于通信。它們正在演變為下一代互聯網、工業互聯網,以及依賴于該基礎架構的下一代工業系統的中樞神經系統。”“中國已在5G領域占據領先地位,占領了全球基礎設施市場40%的份額。而且,有史以來第一次,美國沒有引領下一個技術時代。”巴爾接著說,據估計到2025年,由5G推動的工業互聯網將創造23萬億美元的經濟機遇,如果中國引領5G技術,它將能夠主導這一機遇。中國在5G基礎設施方面的成功也轉化為與5G相關的一系列新技術的優勢,與工業互聯網交織在一起的人工智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目前,華為已成為除北美以外各大洲的領先供應商,而美國沒有設備供應商。此外,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如果工業互聯網變得依賴于中國技術,美國今天擁有的經濟制裁手段將黯然失色。巴爾認為,未來的五年將是確定5G的全球市場份額和應用程序主導地位的時期,在這個時間窗口內,美國及其盟國必須迅速采取行動,向華為發起強勁競爭,以獲得盡可能大的市場份額。①“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s Keynote Address: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Center for Strategic&International Studies,February 6,2020,https://www.csis.org/analysis/attorney-generalwilliam-barrs-keynote-address-china-initiative-conference.
總而言之,如今,中美之間電信業原有的連通性和依賴性問題,已經轉變為關于整個網絡空間下一代架構和治理系統的全球競爭,美國在全球的科技主導地位也已讓位于更加復雜、激烈的競爭。在特朗普政府期間,美國針對中美網絡關系的政策日益顯示為基本上是從競爭、安全和人權立場出發,而且日益傾向于與中國直接對抗,完全不顧現有的國際貿易規則,而且看不到軟化立場的前景,這會帶來消除技術堆棧、供應鏈和市場“脫鉤”的效應。從上文所給出的現實情況來看,分離和“脫鉤”正在悄然全面展開。最令人擔憂的是,鑒于美國國內政治的現狀,這些政策一旦啟動,就很難逆轉。即使在美國專家中,也有很多人擔心,兩國的創新體系和數十年建立起來的全球價值鏈將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在今后的五年里,幾乎完全的分離可能導致兩種各自獨立且相互競爭的國家標準,造成互操作性困難及全球化價值鏈的斷裂,以及隨之而來的成本提高、創新速度放緩和兼容性下降等問題。一旦如此,兩大電信系統之間的鴻溝會越來越大,并在許多技術領域產生廣泛的連鎖反應。
四、半導體產業的競爭
半導體是電信、人工智能計算和許多其他高科技產品的核心部件,許多高科技產品的研發都依賴于半導體產品等級的提高和穩定供應。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半導體產業經歷了從一蹶不振到復蘇的過程,原因之一是美國工業界通過與臺灣公司的聯合,對半導體價值鏈進行了改造。②半導體價值鏈可以看作由三大部分工作組成(不包括市場營銷和分銷):(1)設計:將設計理念執行為代碼(通常為gDsii文件。gDsii是一個數據庫文件格式,用于集成電路版圖的數據轉換,并成為事實上的工業標準),該代碼可作為在制造階段集成電路(IC)的藍圖。(2)制造:在設計規范的指導下,使用光刻技術將電路刻印到物理材料上(通常以一種硅為主要材料),然后用化學物質處理物理材料。重復以下三個主要過程50次以上:沉積(將材料沉積到晶圓上)、光刻和蝕刻(從處理過的晶圓上去除不需要的材料)。在制造階段生產出來的是裸露的、未封裝的,因而是沒有保護的集成電路模具。(3)組裝和測試(A&T):其一,對芯片進行封裝以保護它,并使其能夠連接到其他電子組件和設備,其二,測試IC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從而生成最終的IC芯片。在大約十年的時間里,美國集成設備制造商(IDMs)將半導體生產的大部分部門整合在一起,基本上拆分成專注于半導體價值鏈中較小部分的企業,其中主要的企業是專注于制造的“純生產型”代工廠,以及專注于芯片設計的無工廠設計公司。整個行業被重組為一個全球價值鏈,從而鞏固了美國在電子設計自動化(下文簡稱EDA)③EDA是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的縮寫。該技術是以計算機為工具,設計者在相關軟件平臺上,融合應用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信息處理及智能化技術的最新成果,進行電子產品的自動設計,完成對電子產品從電路設計、性能分析到集成電路(IC)版圖或印制電路板(PCB)版圖的整個自動處理過程。電子設計自動化技術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電路設計的效率和可操作性。工具方面近乎壟斷的地位。不僅美國在無晶圓廠設計中占據主導地位,而且美國半導體資本設備制造商的競爭地位也同時得以提高。
盡管臺灣代工廠的興起降低了美國在全球制造能力中所占的份額(如今甚至在尖端制造能力方面也是如此),外國代工廠的興起仍然使美國受益,因為美國的無晶圓廠設計公司和資本設備制造可以獲得可靠的供應商和消費者。同樣,國外無晶圓廠設計公司的興起促進了美國EDA供應商的市場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半導體行業中的專門設計公司和專門制造公司(純晶圓代工廠)隨之興起。專門設計公司有兩種類型:設計和銷售本企業芯片的無晶圓廠設計公司,以及為其他公司承擔部分或全部設計過程的設計服務公司。
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三種變化造就了以軟件為基礎的EDA產業。第一,橫跨所有重要設計功能的開發軟件工具在技術上迅速發展,因而可以有一套EDA工具覆蓋整個設計流程。第二,多重任務、功能強大的工作站的出現,讓只使用軟件的EDA公司獲得競爭優勢。第三,EDA工具的標準化使其工具在商業市場中獲得了更廣泛的認可。①Alberto Sangiovanni-Vencentelli,“The Tides of EDA,”IEEE Design & Test of Computers,Vol.20,Issue 6,Nov.-Dec.2003,pp.61-65.
20世紀90年代,刺激EDA行業的第四個發展是為無晶圓廠設計公司生產芯片的純代工工廠(如臺灣積體電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積電)的成熟。鑄造廠和無晶圓廠設計公司都不會像IBM這樣的大公司過去所做的那樣,花錢開發內部EDA工具,而是依賴于EDA供應商的設計工具。于是,EDA公司開始與供應商密切合作。
集成電路(IC)②IC系integrated circuit的縮寫,意為“集成電路”,一般用于半導體元件產品的統稱。設計的創新步伐進展神速,并產生了一系列芯片產品。為了跟上進展步伐,兩家最大的供應商楷登電子公司(Cadence)和美國新思科技公司(Synopsys)每年通常將其收入的30%以上用于研發。③Jackson E.Ader,Sterling Auty,Matthew Parron,and Sahil Sharma,“Assuming Coverage of EDA,”research report,J.P.Morgan,September 11,2019,轉引自Douglas B.Fuller,“Cutting off Our Nose to Spite Our Face:US Policy toward Huawei and China in Key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puts,Capital Equipment,and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Tools,”JHUAPL,November 2020,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Fuller-Semiconductors.pdf.也由于此,EDA行業尚未發展出一個占主導地位的設計平臺,而是出現了三大供應商的寡頭壟斷,它們是美國新思科技公司、楷登電子公司和門拓(Mentor)④自2021年1月起,門拓更名為Siemens EDA,即西門子EDA。。據行內人士稱,三巨頭在技術上各有千秋:美國新思科技公司擁有最好的編譯器,楷登電子公司有最好的布局工具,門拓有最好的驗證工具。也有專家認為同時使用所有三家供應商的工具是最好的方法。
三巨頭一直占據著三分之二的EDA市場,并已統治這個領域長達30年。由于這三家公司都位于美國,⑤德國西門子在2017年收購了Mentor。它們的EDA技術大多數源自美國,因而EDA工具嚴格處于美國“實體清單”的出口控制之下。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EDA的發展不僅受到與三大EDA供應商創造的產品匹配困難的限制,而且由于三巨頭與領先代工廠的密切聯系,它們能夠在制造方面跟上變化,使其軟件設計能緊跟最新工藝技術,從而領先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潛在競爭對手。新的中國競爭對手只有在新流程開發出來之后才能進入,而且其準入范圍不會像三巨頭那么大。此外,許多中國的軟件工程師都為三巨頭工作,在中國的1 500多名工程師中,僅有300名左右為本國公司工作。而僅僅美國新思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就有超過5 000名這樣的工程師。⑥Randall Stewart,“Why Chinese EDA Tools Lag Behind,”Technode,November 13,2019,https://technode.com/2019/11/13/silicon-why-chinese-eda-tools-lag-behind/.
如今,美國公司在集成電路資本設備領域的全球營收占比為52%,而日本為27%,歐洲為17%。在較窄的相關晶圓廠設備類別中,五大公司中有三家是美國公司,即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科林研發(Lam Research)和科磊半導體(KLA),這五家公司占2018年總營收的71%。其中,應用材料是最大的公司,占全球營收的18%。然而展望未來,荷蘭的阿斯麥公司(ASML)有可能成為最大的光刻公司,因為它壟斷了高端光刻(即極紫外光刻,EUV lithography),并在光刻領域占據主導地位。⑦Jerome Ramel and David O’Connor,“Entering the EUV Era:Winners and Losers,”research report,BNP Paribas,April 8,2020,轉引自Douglas B.Fuller,“Cutting off Our Nose to Spite Our Face:US Policy toward Huawei and China in Key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puts,Capital Equipment,and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Tools,”JHUAPL,November 2020,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Fuller-Semiconductors.pdf.2001年在阿斯麥公司收購美國最后一家光刻設備生產商硅谷集團光刻系統公司(SVGL)后,美國退出了光刻市場。當時,硅谷集團光刻系統公司在極紫外光刻研發方面領先于阿斯麥公司。
今天,最著名的美國公司在多個類別的集成電路資本設備方面擁有龐大的市場份額。截至2018年,美國公司壟斷了四個產品領域的生產:光學掩模制造光刻(非集成電路光刻)、斜邊去除(干式)、柵堆疊工具和超高劑量摻雜設備。在蝕刻、計量和檢查等其他領域,美國公司在某些高端產品中保持壟斷地位。①Douglas B.Fuller,“Cutting off Our Nose to Spite Our Face:US Policy toward Huawei and China in Key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puts,Capital Equipment,and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Tools,”JHUAPL,November 2020,p.9,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Fuller-Semiconductors.pdf.
為了完成集成電路上的電路層,需要反復進行光刻并完成其他工藝。檢測和過程控制設備在制造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每種生產過程都需要不同類型的設備。如今,每一種類型的設備在全球都由一家供應商主導(占超過50%的市場份額)。
中國在全球制造能力中的份額從2000年的不到1%增長到2018年的12%,其中大部分仍然是外資所有。2019年,中國半導體資本設備支出達到180億美元,占全球資本設備總支出的20%。中國的資源主要集中在制造,其次是設計,對設備部門的投資獲得的政策支持相對較少。目前,中國生產商能夠為晶圓廠生產“非關鍵”設備,已經能夠銷售更多的集成電路制造以外的設備,包括太陽能電池板、集成電路及平板顯示器等。據估計,2018年中國國內生產商的資金投入僅占中國半導體設備總支出的5%~10%。②Ibid.,p.14.
根據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近期發布的一篇報告《對華貿易限制如何結束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領導地位》的統計,美國半導體產品占全球市場份額的45%~50%。2018年,其銷售額達2 260億美元,分別是韓國、日本、歐洲企業銷售額的2倍、5倍和6倍,是中國企業的15倍。美國半導體產品銷售額的80%依賴出口。③Antonio Varas and Raj Varadaraja,How Restrictions to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s,Boston Consulting Group,March 2020,p.8,https://image-src.bcg.com/Images/BCG-How-Restricting-Trade-with-China-Could-End-USSemiconductor-Mar-2020_tcm9-240526.pdf.
自2009年以來,韓國和中國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份額分別上升了12個百分點和3個百分點。同一時期,美國在其國內市場也面臨著來自歐洲和日本企業的競爭壓力。2018年,中國企業(不包括外國在華企業)在全球半導體生產和銷售方面僅占約4%的份額,但中國1 600余家無晶圓廠的半導體設計企業合計占全球市場的份額,從2010年的5%上升至如今的13%。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的測算,中國的市場需求占全球半導體產業總需求的23%,而中國國內企業只能滿足中國全部終端產品需求的14%。美國半導體專家分析認為,到2025年,中國可將國產半導體的自給率提升至25%~40%,但尚達不到70%的預期目標。不過,中國在5G商用、區塊鏈和加密貨幣、人工智能、存儲設備,以及量子計算等領域取得的重要進展,已經引起美國的高度關注。④Ibid.,p.6.
半導體是電信、人工智能計算和其他許多高科技產品的核心部件,而且美國EDA和資本設備公司在為全球半導體產業提供技術密集型投入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鑒于美國在EDA技術方面的壓倒性優勢和集成電路制造設備領域的市場主導地位,美國將這一價值鏈作為“武器”、將半導體置于打擊華為政策的前沿和中心也就不足為奇了。
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導致中美關系進一步惡化,這為美國對華鷹派提供了進一步采取針對華為行動的機會,特別是對華為供應鏈中最大的軟肋,即芯片供應下手。2020年1月,在時任政策規劃官員厄爾·科姆斯托克(Earl Comstock)的領導下,美國商務部官員推出了幾項旨在切斷美國對華為技術供應的新規定。2020年4月,當美國在海外擴大針對華為的出口管制時,為了避免斷供的后果,華為開始從臺積電那里囤積零部件和其他半導體。然而,由于華為的5G基站以及企業、云和人工智能產品的核心芯片都依賴臺積電制造,臺積電不能滿足其全部芯片需求,致使華為面臨迫在眉睫的供貨短缺局面。對于華為來說,唯一的解決方案是重新設計其生產的所有產品。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到2020年6月,臺積電表示將遵守美國法律,停止與華為在半導體新產品生產方面的合作。
2020年5月,華為已將其部分半導體生產轉移到一家國內代工企業中芯國際半導體制造有限公司(SMIC)。但是,中芯國際缺乏生產低于10納米級別的先進商業設計的能力和設備,而且可能無法在短期內達到供貨目標。據報道,這是因為2019年美國政府向荷蘭政府施壓,要求其取消中芯國際從全球唯一的供應商荷蘭阿斯麥公司購買尖端超紫外光刻機的許可,致使中芯國際在支付定金兩年之后,仍然沒有得到交貨。①這一信息在2020年8月25日筆者與同事對中芯國際進行考察時被證實。如果得不到這套設備,中芯國際和華為海思在生產先進半導體方面至多只能停留在14納米至10納米的水平,而據說臺積電已經在研發3~5納米的芯片。其結果最終將使華為無法與其國外競爭對手愛立信、諾基亞等進行競爭。
2019年5月,美國政府將華為及其附屬公司列入“實體清單”,試圖切斷華為與美國半導體技術的聯系。2020年5月15日,美國政府加大對華為的制裁力度,限制華為進入美國在半導體價值鏈中具有特殊優勢的兩個領域:用于芯片生產的資本設備,以及用于芯片設計的EDA。美國政府于2020年8月17日頒布的新法規進一步加強了對華為的制約,明確禁止未經許可與華為建立供應鏈。②Douglas B.Fuller,“Cutting off Our Nose to Spite Our Face:US Policy toward Huawei and China in Key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puts,Capital Equipment,and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Tools,”JHUAPL,November 2020,pp.26,34,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Fuller-Semiconductors.pdf.
制造芯片所需的資本設備是集成電路價值鏈中技術最密集的部分之一,也是美國政府限制中國能力的重點。中國領先代工廠中芯國際(BIS)由于受到美國的長臂管轄,沒有美國許可無法向華為供貨。而讓事情變得更為復雜的是,2020年12月18日,美國商務部將中芯國際也列入與中國軍方有密切聯系的“實體清單”,這使得華為在短期內獲得高端芯片的機會更加渺茫。
然而,根據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上述報告的評估,美國將價值鏈武器化的企圖很可能會以失敗告終。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得益于對研發的巨額投資。在過去十年里,美國半導體行業共投入研發資金3 120億美元,僅2018年就達390億美元,是當年其他所有經濟體總投入的近兩倍。而美國之所以能維持巨額投資,主要由于其在此行業中的巨大營收。美國半導體產業能夠居于全球領先地位,主要依靠良性創新循環。
正因為如此,美國對華為芯片供應的封鎖必然會產生“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效果。自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以來,美國排名前25位的半導體公司收入中位數增長率,已從2018年7月中美雙方加征首輪關稅之前四個季度的10%,下跌至2018年末的1%。2019年5月,在美國將華為等中國企業和機構列入“實體清單”后的三個季度內,美國頂級半導體公司的收入中位數普遍下降4%~9%。多數美國企業認為中美“貿易戰”是造成其營收下滑的重要原因。美國從中國制造商那里可獲得約490億美元的年收入,占其總收入的22%。③Antonio Varas and Raj Varadaraja,How Restrictions to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s,Boston Consulting Group,March 2020,p.13,https://image-src.bcg.com/Images/BCG-How-Restricting-Trade-with-China-Could-End-USSemiconductor-Mar-2020_tcm9-240526.pdf.若美國持續加強對華技術和產品的單邊貿易限制,可能使美國企業在華市場份額大幅度下降,甚至導致其維持半導體產業發展的良性創新循環不復存在。未來美國對華技術和產品出口的限制,在最壞的情況下可能演變成科技“脫鉤”。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的報告認為,對半導體企業施加廣泛的單方面出口限制,將對美國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可能危及美國長期以來在全球半導體領域的領導地位。①Antonio Varas and Raj Varadaraja,How Restrictions to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s,Boston Consulting Group,March 2020,p.4.
報告預測,這些出口管制措施的實施,有可能開啟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美國發起的對華為的圍剿可能引發相應的回應,中國政府可能為保持華為獲得芯片的能力而提供大量補貼,使華為能夠提高制造服務的價格,從而讓臺積電和三星感到將一些生產線去美國化是值得的。此外,嚴格執行“實體清單”出口管制會刺激美國公司將部分生產轉移到海外,以規避出口管制,而為華為供貨的法律責任所帶來的風險不一定能抵消在海外設廠所受到的壓力。最后,其他排在美國和日本之后最大的半導體資本設備生產國,很可能會被誘導為去美國化提供一些政策支持,以重新獲得芯片競爭優勢。由于這些原因,先進晶圓廠設備的去美國化可能會相對較快地發生。②Ibid.,pp.13-15.
普林斯頓大學關于中美在半導體領域競爭的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在半導體方面的‘脫鉤’很可能在短期內實現”,但由于以下幾個原因,這個戰略是錯誤的。首先,其商業成本將完全由美國承擔,尤其是考慮到美國在EDA領域處于近乎壟斷的地位;其次,外交成本將非常高,而且不僅針對中國政府,還關系到眾多中國企業的業務;最后,美國將在中期甚至更早的時間內削弱其在EDA基礎設施方面的力量,而且“脫鉤”將鼓勵其他國家(不僅是中國)考慮替代方案。③Douglas B.Fuller,“Cutting off Our Nose to Spite Our Face:US Policy toward Huawei and China in Key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puts,Capital Equipment,and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Tools,”JHUAPL,November 2020,p.18,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Fuller-Semiconductors.pdf.
毋庸置疑的是,在芯片制造基礎設施設計以及用于制造和測試的硬件工具方面的“脫鉤”,可能威脅到中國最大的電信公司華為的生存。④Kathrin Hille,“US‘Surgical’Attack on Huawei Will Reshape Tech Supply Chain,”Financial Times,May 18,2020.業內專家認為,中國在設計和建模軟件的發展上落后美國五到十年,要超越這一領先地位將是極其困難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對中國進行技術、產品和設備封鎖可能有利于維持美國目前在創新商業化方面所具有的領先優勢。如果美國同時加快創新步伐,復合效應可能會導致總體能力的差距,而中國將很難超越這一差距。
然而,華盛頓大學副教授羅伯·卡爾森(Rob Carlson)及其合作者里克·韋伯林(Rik Wehbring)認為,從長遠來看,美國為使技術與中國“脫鉤”而采取的任何步驟都只會在短期內減緩中國根據自己的戰略發展科技的速度。美國不太可能在未來主導所有科技領域,就像它不能在當今的所有創新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一樣。對中國人才的投資和創新將不可避免地產生世界領先的科技。因此,“我們重申,無論是否實施‘脫鉤’政策,美國維持其戰略領先地位的主要長期戰略必須是提高其本國的發明和創新能力”。⑤Rob Carlson and Rik Wehbring,“Two Worlds Two Bioeconomies,the Impacts of Decoupling US-China Trad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JHUAPL,November 2020,p.20,https://www.jhuapl.edu/Content/documents/Carlson_Wehbring-Biotech.pdf.關于這一點,世界銀行前行長兼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話表達得最為明確:“如果一攬子禁令和壁壘取代了風險評估,我們都會變得更糟。美國對中國創新議程的最佳反應是增強我們自身的能力,并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創意、企業家和風險投資。我們只有勇于面對自己的缺點,而不是責怪他人,才能取得成功。”⑥James Politi,“Fears Rise that US-China Economic‘Decoupling’Is Irreversible,”Financial Times,January 21,2020.
鑒于芯片和芯片設備供應在中國半導體業、電信業和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未來拜登新政府是否會把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的芯片封鎖政策繼續下去,是中國需要密切關注的動向。
五、結 論
與當前大國戰略競爭模式不同的大國競爭的典型案例是冷戰年代的美蘇戰略競爭。當年被稱為“冷戰”的美蘇競爭的典型特征是,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政治對壘、相互脫離的市場和經濟體系、全球范圍的軍事和安全對抗,以及完全排斥合作的零和游戲。冷戰時期,美蘇之間也存在科技競爭,在冷戰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通過1949年組建的“巴黎統籌委員會”來糾集西方盟國對蘇東集團進行科技封鎖,70年代初經過短暫的緩和,到80年代美蘇在軍事科技領域的競爭又在里根所發起的“星球大戰”中達到頂點。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當前形式的大國高科技競爭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出現后才初露端倪,而中美兩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正在改變以往大國戰略競爭的模式。
第一,高科技競爭首次并日益成為當代大國競爭首要的、決定成敗的關鍵領域,其戰略意義更為顯著。美國與中國科技競爭的強度隨著美國對科技競爭在“大國競爭時代”意義上認識的逐步清晰而不斷升級。這場中美之間方興未艾的科技競爭起始于2018年3月開始的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那時美國已經有意識地針對《中國制造2025》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加征關稅;發展于隨著中國5G部署戰略的推進,美國在2018年7月與“五眼”國家就遏制華為的戰略達成協議,并于2019年初以“銀行欺詐”和“違反制裁令”為由,對華為提起刑事訴訟;而其高潮發生于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發期間,隨著中美關系的急劇惡化,美國對華鷹派獲得了進一步采取針對華為行動的機會。2020年5月,美國將華為及其附屬公司列入“實體清單”,并于5月15日和8月17日兩次加大對華為的制裁力度,限制華為獲得無線通信網絡的核心部件——芯片。美國的科技“脫鉤”措施并不限于針對華為,還包括要求美國公司從中國遷回美國,嚴格審查并限制與中國的科技交流。①由于篇幅限制,這部分就不在此展開了。
第二,高科技領域的競爭之所以是關鍵性的,是因為高科技的發展水平可以直接影響其他領域競爭的結果,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優勢可以轉化為市場競爭和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因此競爭雙方在貿易和經濟領域里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產業技術水平的競爭。此外,在軍事技術水平日益接近的情況下,中美雙方都沒有把握在軍事上徹底擊垮對方,而高科技在軍事上的應用所造成的軍事水平差距,是軍事威懾產生實際功效的關鍵。
第三,高科技競爭的跨空間性改變了大國競爭的地理模式,大幅度削弱了地理空間爭奪,甚至搶占了戰略要地的重要性。高科技的發展,特別是其中新材料科技的發展,使當代工業生產對原材料的依賴日益減弱,從而使軍事占領原材料產地的行動日益變得得不償失。而高科技帶來的遠程兵力投放能力和遠程軍事打擊能力的空前提高,亦使地域爭奪變得不再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冷戰年代蘇美在第三世界的地理爭奪模式在當代便失去了意義。
第四,高科技競爭改變了國家投資的主要方向。顯而易見,在傳統的冷戰年代的大國競爭中,競爭各方都在國防領域耗資巨大。例如,僅僅核軍備競賽一項,根據俄羅斯原子能部戰略穩定研究所的統計,蘇聯核武庫中的戰略和戰術核彈頭總數在1986年達到峰值,為45 000枚,美國在1984年達到峰值,為23 600枚。蘇聯的常規力量在數量和重武器配備上也超過美國,俄羅斯專家認為,冷戰年代蘇聯70%的產業部門與軍工有直接和間接聯系。②俄羅斯原子能部戰略穩定研究所編:《核裁軍,反擴散與國家安全》,莫斯科,2001年,第63頁。(原文為俄文)而在當代中美高科技競爭中,科研經費和國防預算的投入對比呈現出另一番景象。例如在2019年,中國的科技研發總投入為22 143.6萬元人民幣,約合3 300億美元;而國防預算約為11 899萬元人民幣,約合1 774.9億美元。③關于中國的兩個數據分別來自“2019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2020年8月27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8/t20200827_1786198.html,以及“兩會開幕:中國軍費增速下降,但仍高于GDP增幅”,BBC中文網,2019年3月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7451881。從美國方面來看,2018年美國對科技研發的支出為5 800億美元(其中聯邦政府和企業研發資金的支出占總數的91.6%),從2009年至2018年10年間增長了約1 800億美元;而相比之下,美國的國防開支在2008年增加到超過6 500億美元之后,到2018年仍僅為約6 800億美元,在2008年至2018年期間一直在7 000億美元上下徘徊。①Se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U.S.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ing and Performance:Fact Sheet,”FAS,January 24,2020,https://fas.org/sgp/crs/misc/R44307.pd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U.S.R&D Expenditures,by Source of Funds and Performing Sector:1953–2018,”January 8,2020,https://ncses.nsf.gov/pubs/nsf20307#&;The World Bank,“Military Expenditure(current USD)-United States,”December 16,2020,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CD?locations=US.顯然,即使美國的科技研發經費尚未超過國防開支,前者的增加速度也要大大快于后者。
第五,當前高科技領域的大國競爭,不僅集中于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關鍵產業之核心技術領域,而且正著手通過切斷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方式來進行。競爭優勢方往往可以在短期內利用對劣勢方的“卡脖子”戰術,獲取一時的戰略約束功效。值得關注的是,這些關鍵的高科技競爭點,將會不斷地被挑選或凸顯出來,而以此方式進行的戰略博弈,將很可能成為今后較長時期大國戰略競爭的主要特征。因此,未雨綢繆,不斷預先辨別出、把控住這些關鍵科技領域,乃至產業鏈、供應鏈的關鍵環節,將是中國頂層戰略規劃與設計面臨的迫切與長遠的任務。
可以看到,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對與中國的科技“脫鉤”在逐步升級;另一方面,美國大多數對科技“脫鉤”政策的評估者都站在美國的立場上,批評美國的現行政策。盡管這些批評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某些審查和限制是必要的,但他們都認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得太遠了。例如,霍普金斯大學系列報告第一篇的標題就是:“三思而后行:評估某些中美技術聯系”;另一份報告的標題是:“跟自己過不去:美國在半導體工業關鍵投入、資本設備和電子設計自動化工具方面針對華為和中國的政策”;還有一份報告則直接采用了這樣的標題:“交織在一起的人工智能未來,抵抗是徒勞的”。
科技“脫鉤”不僅不符合科技發展方向和發展規律,而且從戰略角度講,“脫鉤論”也存在其固有盲點。眾所周知,冷戰期間,蘇聯曾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和意識形態競爭對手,美國對向蘇聯出口技術實行廣泛而嚴格的控制。然而,蘇聯從未成為美國的主要市場或全球供應商競爭對手,因而美國在盟國的配合下,對蘇聯進行技術封鎖相對容易。同樣,日本在許多行業中是美國強大的競爭者和重要供應商,但對于大多數西方公司而言,日本從來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市場(部分原因是日本經常排斥外國公司),而且美國可以利用日本對美國安全保護傘的依賴來迫使其在半導體、汽車出口及匯率方面做重要讓步。但是,由于蘇聯和日本都沒有在經濟上與西方深度融合,美國和其他國家同它們打交道時可以有更大的政策回旋余地。然而,如果美國對中國采取相同的做法,如上文所說,它將付出更大的代價,而且可能很難得到盟國的合作。
如今,原本是在科技領域里的競爭,正在被美國演化為一場爭奪世界領導權的戰略競爭。大國競爭已成為美國外交和安全戰略的指導理念,這導致每天都有人用“冷戰”來描述中美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并頻繁用“軍備競賽”來類比雙方在包括人工智能和5G在內的先進技術的競爭。國際上許多人擔憂,如果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固化為持久的全球沖突格局,可能會引發去全球化,最終導致兩個平行的秩序,一個由美國主導,另一個由中國主導。如果中美沖突繼續加劇并加速國際體系的兩極分化,全球多邊主義的基礎可能將不復存在。基于此,今后最引人關注的動向是,在拜登執政之后,美國在科技方面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會沿著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繼續走下去,還是會有所調整?無論情況如何,鑒于美國目前與中國科技“脫鉤”的勢頭,我們都必須意識到,美國對中國在科技領域里的圍堵從長遠來看不會停手,而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未來可能會比預想的要更加艱難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