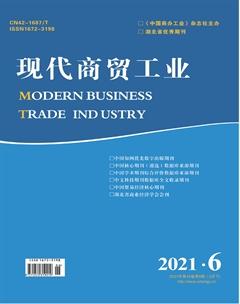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協同發展研究
蔣恩東
摘 要:城鄉關系既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鄉村振興戰略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猶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從經濟倫理和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兩大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是一次發展理念的根本轉變,體現了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倫理觀的扭轉,也是在城鄉發展不平衡達到一定程度之后迫在眉睫的制度變遷,其協同發展應當從經濟倫理實現和制度變遷動力兩方面來看。經濟倫理和制度變遷的實現中最核心的要義則是內心信念的轉變。
關鍵詞: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經濟倫理;制度變遷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06.003
城鄉關系既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的發展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城鄉發展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同時各自也面臨不同的發展困境,這既有歷史因素的沉積,亦有現實因素的影響。如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難題,實現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業已成為我國當今社會的重要課題。基于此,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先后被提出。
學者普遍認為,兩者并非對立關系,而應該相互推進。陳麗莎(2018)認為,兩大戰略都是為了積極利用農村勞動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而解決好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卓瑪草(2019)認為,“解新型城鎮化困境之‘圍需要鄉村振興支持,助鄉村振興戰略之‘力需要新型城鎮化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天然擁有著協同發展的屬性要求。在更深層次上來看,兩大戰略的提出是一次對城鄉關系認知的徹底性改變,也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變革。
1 理論基礎
1.1 經濟倫理
經濟倫理概念由馬克斯·韋伯于20世紀初提出,但主要服務于他對宗教社會學的研究。發軔于美國的當代西方經濟倫理學理論來源廣泛,雖受韋伯的啟發,但同韋伯的經濟倫理概念不能完全等同。經濟倫理學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論體系,甚至是在基本的經濟倫理概念上仍存爭議。在當代我國,經濟倫理蘊含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最為關鍵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理念,同時也包括以新發展理念為核心的經濟發展倫理等重要內涵。“市場經濟運作不能沒有道德基礎,社會秩序本身也不是沒有倫理維度。”經濟倫理主要回答的是經濟發展、制度、行為、政策和目標等經濟領域諸多方面的道德合理性問題,體現相應的價值訴求和道德規范,以價值判斷為準繩,評價、規范和約束經濟主體行為。作為一種倫理價值規范和柔性約束力量,任何一種倫理規范的遵循和倫理目標的實現都離不開相關主體的價值信念。
1.2 制度變遷
20世紀70年代以前,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問題時,往往把制度排除在外。以諾斯(North)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則把制度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進行考察,認為制度變遷是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制度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受資源稀缺性的影響,制度的供給是有限的。諾斯(North)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包括正式制度規則和非正式制度規則。制度變遷指“制度創立、變更以及隨著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變遷是一個從收益最大化出發而根據時空變化進行不斷調整規則的漸進性過程,也就是諾斯所說的“規則是從自利派生出來的”,但制度變遷同時存在“路徑依賴”的問題,即制度的自我強化,或者說,當制度進入某一路徑時,無論結果怎樣,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依靠,甚至處于“鎖定”的桎梏之中。
2 經濟倫理和制度變遷視角下的協同困境
“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和農情決定鄉村振興戰略的必要性,城市化的不斷加快和城市建設各種問題的客觀存在也迫切需求新型城鎮化建設。從根源上看,城鄉發展困境的出現一方面出于制度上城鄉二元體制的固化難以化解,另一方面則由于對城鄉的價值判斷存在偏差和對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的貫徹不徹底。傳統的城鄉發展理念的價值判斷偏向城市。城鄉區別最突出的體現就在于要素生產效率的不同,這又同生產要素的配置密切相關。城市擁有著數倍于農村的人均資本,特別是人力資本,天然在要素爭奪、生產效率以及人均收入上占有優勢。城鄉二元結構在一定時期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迫切追求城市經濟和工業發展的既定經濟倫理思想指引下,伴隨而來的城鄉二元體制又在制度上強化了這種天然差別,帶有強制行政性的資源配置政策割裂了城鄉融合發展的同時,不但使資源稟賦不占優勢的農村地區進一步衰落,又造成了城市建設盲目擴張的種種問題,使傳統模式城市擴張的邊際收益急劇下降,也讓農村流入城市的資源利用效率大打折扣。
經濟倫理和制度安排之間割舍不斷。一定的經濟倫理觀念會引致相應的制度安排,同時,制度安排也蘊含著內在的經濟倫理。但是,經濟倫理具有一定的粘滯性,制度變遷會有“路徑依賴”的問題。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出于對城鄉價值判斷偏差的反思,也是一次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和體制的制度變遷過程,因此其協同發展難免受困于此。
2.1 經濟倫理方面
在較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城市優于農村、工業優于農業既是一個客觀現實,也形成了固定的舊有觀念。對行政主體而言,長期追求城市化率、城區建成面積、工業產值等指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的增長,卻忽視了農村、農業帶有的價值屬性,只是把農村作為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地以支撐了城市的高速成長;對市場主體而言,由于城市具有空間積聚、基礎設施完善、人口密集等優勢,特別是要素稟賦的集中,經濟活動多發于城市而少發于鄉村,鄉村備受投資的冷落;對個人選擇而言,城市不僅僅擁有基礎設施完善、教育和醫療條件優越、社會保障充分、收入水平較高等客觀優勢,根深蒂固的城市現代文明優于農村傳統文化的觀念也引導著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這個過程的過快推進造成了鄉村空心化和鄉村文化快速衰敗,熟人社會的淳樸與誠信喪失殆盡,現代契約精神又未能構建,城鄉面臨了更高的經濟倫理風險。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的擴張不斷侵蝕著鄉村土地,加上對城鄉土地性質不同而帶來的價值巨大落差,使得經濟各主體都試圖將鄉村用地轉變為城市用地,造成了大量失地農民。這些農民被迫離開土地,背井離鄉,漂泊于城市之中而難以融入城市生活。與此同時,城市用地擴張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又造成了土地資源的空置于浪費。
城鄉融合發展、城鄉二元結構的破除以及兩大戰略的協同發展受困于由來已久的“重城市、輕鄉村,重工業、輕農業,重現代、輕傳統”的經濟倫理思維,過程中需要不斷調整的各項經濟規則和經濟行為面臨著倫理道德上的風險和考量。特別是對關鍵要素土地的認識上,當前土地的利用功能日趨多元,不僅僅是作為生產要素一種功能,其價值內涵也逐漸拓展到社會和生態等多方面,對土地的物質價值需求也轉化為對土地多元價值需求,價值選擇已經成為土地開發利用的核心內容。
2.2 制度變遷方面
城鄉二元體制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路徑依賴問題不容忽視。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中,城鄉融合和協調發展政策經歷了多次演變。農村方面有農村改革、城鄉統籌發展、鄉村振興戰略逐步演進,城市方面有小城鎮、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建設步步升級,其核心要義就是通過制度安排扭轉城鄉二元結構固化的局面,實現城鄉融合以及高質量發展。
在城鄉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安排上,土地產權逐步有重視歸屬轉向重視利用,比如家庭聯產承包制到農地宅基地“三權”分置;土地配置從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比如鼓勵農地經營權合理流轉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土地利用從規模控制轉向利用控制,比如嚴格控制城市用地規模到劃定生態紅線和城市低效率用地再開發。這種制度的變遷源自于土地價值內涵的變化和城鄉用地矛盾的凸顯。在構成城鄉二元體制的另一個重要制度戶籍制度上,我國逐步對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政策進行了完善,也開始逐步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的區分,但城鄉身份區別依舊存在,顯示出城鄉二元戶口結構的路徑依賴,阻礙著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協同發展。
總體來看,我國城鄉各項政策的安排主要由政府主導的供給型制度變遷為主、具有長時期漸近性特征。對于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而言,由于歷史因素和客觀顯示的多重因素,舊有的城鎮擴張模式難以短時期改變,農村的經濟發展潛力短期內難以被激活,導致了城鎮化建設問題無法全面解決和農村經濟文化建設依舊滯后,由于現有城市擴張的收益依舊高于尚未被挖掘潛力的農村地區,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痕跡明顯,兩大戰略的協同發展受到政策梗阻和結構鎖定。
3 結論與展望
無論是從經濟倫理角度來講,還是從制度變遷角度來講,最核心的要義是內心信念的轉變。鄉村振興戰略和新型城鎮化建設互為補充,體現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倫理訴求,也是一個基于現實困境和人民訴求的制度變遷過程,其協同發展應當從經濟倫理實現和制度變遷動力兩方面來看。
其一,切實轉變傳統的城鄉價值判斷偏差,在城鄉融合和協調發展的理念指引下,根據當地實際而因地制宜地制定具體建設發展規劃,防范城鎮化過程中與農村建設發展爭地問題。
其二,通過制度創新推進鄉村基礎設施、教育衛生條件的完善,同時引導城市過剩的發展要素回流農村,特別是人力資本,同時警惕資本盲目下鄉,體現城鄉之間不同的價值擔當。
其三,樹立城鄉互動的觀念意識,統籌城鄉發展,整合城鄉資源,同過倫理引導和制度安排糾正城鄉二元的舊有思維,利用市場配置實現要素的優化配置和城鄉生產生活資源的合理布局,實現城鄉資源租值的充分挖掘。
參考文獻
[1]卓瑪草.新時代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融合發展的理論依據與實現路徑[J].經濟學家,2019,(01):104112.
[2]陳麗莎.論新型城鎮化戰略對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帶動作用[J].云南社會科學,2018,(06):97102.
[3]蘇華,陳偉華,陳文俊,等.要素生產率和要素配置作用下的中國城鄉收入差距[J].經濟地理,2012,32(04):4449.
[4]龔天平,王澤芝.制度安排與經濟倫理[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53(05):1625.
[5]葉超,高洋.新中國70年鄉村發展與城鎮化的政策演變及其態勢[J].經濟地理,2019,39(10):139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