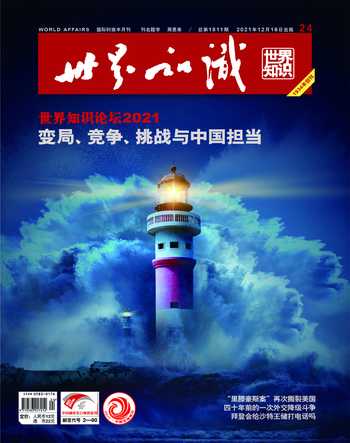大國戰(zhàn)略競爭和國際軍控的衰落
李彬(清華大學(xué)國際關(guān)系學(xué)系教授):
關(guān)于2021年的軍控形勢和未來的走向,我想談四點(diǎn)。
第一,美國黨派政治對全球軍備控制有很大的破壞作用。民主、共和兩黨關(guān)于軍控的政策偏好有個一般性的規(guī)律:冷戰(zhàn)之后,共和黨傾向于反對以條約為基礎(chǔ)的軍備控制,不斷退出雙、多邊軍控條約;民主黨則傾向于推進(jìn)和維護(hù)軍控條約。但在美國,退出軍控條約比推進(jìn)軍控條約要容易得多,兩黨對軍備控制的嚴(yán)重分歧致使美國的軍備控制政策經(jīng)常出現(xiàn)搖擺,而搖擺的結(jié)果就是美政策越來越保守。美國的軍控政策變得保守,其他國家卻很難勸阻美國,導(dǎo)致國際軍控倒退。
特朗普執(zhí)政時期,美國退出了一系列軍控條約,如《開放天空條約》《中導(dǎo)條約》《聯(lián)合全面行動計劃》(即伊朗核協(xié)議);美國當(dāng)時勉強(qiáng)沒有退出《全面禁止核試驗(yàn)條約》《新削減戰(zhàn)略武器條約》等。拜登上臺后,其團(tuán)隊(duì)有意推進(jìn)一些軍控議程,但也力不從心。美國對《新削減戰(zhàn)略武器條約》做了續(xù)約,但繼續(xù)推進(jìn)戰(zhàn)略核裁軍缺乏力度;在伊朗核協(xié)議問題上,美國和伊朗仍在博弈,前途未卜;美國政府2021年5月宣布,將不會重返《開放天空條約》。總的來說,拜登政府在軍控領(lǐng)域能做的事情有限。

2021年4月21日,伊朗總統(tǒng)魯哈尼出席內(nèi)閣會議時宣布伊朗核問題談判取得進(jìn)展。
拜登團(tuán)隊(duì)曾有一個思路,就是宣布美國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懾止和反擊核進(jìn)攻。對此持反對立場的不僅有共和黨人,也包括一些民主黨人士,拜登政府內(nèi)部也有反對聲音。奧巴馬在執(zhí)政期間也曾考慮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當(dāng)時美國內(nèi)一些人發(fā)動盟國反對奧巴馬政府的想法。日本一直明確反對美國的這項(xiàng)動議,一些歐洲國家現(xiàn)也開始加入反對陣營。可以預(yù)計,拜登政府宣布這項(xiàng)新政策仍有很大難度。
第二,中小國家主導(dǎo)的軍備控制仍在繼續(xù)發(fā)展。這包括《武器貿(mào)易條約》、全面禁止反步兵地雷的《渥太華公約》等。中國在1995年前對中小國家主導(dǎo)的軍備控制議程予以全力支持,現(xiàn)在仍大力支持。比如2020年中國加入了《武器貿(mào)易條約》。中國沒有參加《渥太華公約》,但參加了部分限制反步兵地雷的《過分殺傷常規(guī)武器公約地雷議定書》。對于中小國家主導(dǎo)、五個核大國都不支持的《禁止核武器條約》,中國的立場較特殊,曾對相關(guān)議案投出棄權(quán)票。在中小國家主導(dǎo)的軍備控制方面,中國在尋求共同點(diǎn),不可能全部支持。
第三,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的危險上升。美國將大國戰(zhàn)略競爭置于軍備控制之上。根據(jù)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關(guān)系(AUKUS)協(xié)議,美英將向澳轉(zhuǎn)讓核潛艇建造技術(shù)。美國完全可以利用一些防擴(kuò)散措施對該協(xié)議做“包裝”,但它沒有這樣做,而是極力渲染對抗氣氛,直截了當(dāng)?shù)匦技夹g(shù)轉(zhuǎn)讓。在軍控領(lǐng)域,美國還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破壞當(dāng)前務(wù)實(shí)的軍控磋商氣氛。比如美國在海基和空基中程彈道導(dǎo)彈方面有優(yōu)勢,中國在陸基中程導(dǎo)彈方面實(shí)力不俗。美國每次提到中導(dǎo)問題,都直指陸基中導(dǎo),對海基和空基中導(dǎo)選擇性“失明”,實(shí)際上海基和空基中導(dǎo)對地區(qū)和全球戰(zhàn)略穩(wěn)定性的破壞作用更為明顯。對于這些問題,美國不去尋求務(wù)實(shí)的解決途徑,而是一味向中方施壓,要求中國參與談判。
危機(jī)管控本應(yīng)有兩個思路:第一,減少危機(jī)的發(fā)生;第二,一旦危機(jī)產(chǎn)生了,管控其升級。這兩方面都很重要。美國目前的邏輯是:發(fā)生危機(jī)是正常的——畢竟大國競爭是其全球戰(zhàn)略新內(nèi)核。但如若危機(jī)真的發(fā)生了,其他國家必須配合美國管控其風(fēng)險,不能讓沖突升級到不符合美國利益的程度。這一邏輯相當(dāng)危險,令人擔(dān)憂。另外,隨著近年來中國國防實(shí)力的增長,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關(guān)于中國軍事能力的報告,還將出核態(tài)勢評估報告;一些智庫和媒體也極力渲染“中國威脅論”,這個現(xiàn)象今后幾年將會愈演愈烈。
第四,高新技術(shù)在軍事上的應(yīng)用帶來諸多不確定性。人工智能在軍事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可能使非授權(quán)的軍事對抗升級,也就是說,某些時候人工智能可能替代軍事主官做出行動升級的決定,而決策者未必能夠察覺。人們?nèi)粢乐谷斯ぶ悄軒淼姆鞘跈?quán)軍事對抗升級,只能有意識地犧牲一些軍事作戰(zhàn)效率。網(wǎng)絡(luò)攻擊也是個重要問題。過去,我們作戰(zhàn)采用動能攻擊的方式。雙方可以等待時機(jī)后發(fā)制人,如果雙方都觀望,就有可能把危機(jī)拖過去。但網(wǎng)絡(luò)攻擊不是這樣,作戰(zhàn)雙方不知道自己的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是否被對方擊破了,搶先發(fā)動進(jìn)攻的壓力更大,軍事對抗也就更容易升級。
高新技術(shù)還會產(chǎn)生一個后果,即自我實(shí)現(xiàn)的軍備競賽預(yù)言。軍備競賽的各方都瞄著對方的未來,一方幾十年后要發(fā)展什么軍備,另一方現(xiàn)在就要做準(zhǔn)備。結(jié)果是,物質(zhì)上是否有軍備競賽的基礎(chǔ)不重要,思想上有軍備競賽的基礎(chǔ)就夠了。高新技術(shù)為這種類型的軍備競賽提供了場所。例如,一些專家認(rèn)為在人工智能軍備競賽中將是贏者通吃。一旦大家有了這樣的認(rèn)知,競賽就可能發(fā)生,而且還會相當(dāng)激烈。
另外,國際社會在地區(qū)防核擴(kuò)散問題上的合作面臨困境,朝核問題一時還看不到出路,伊朗核問題重新惡化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總體而言,國際軍備控制日漸衰落,軍控體系面臨嚴(yán)峻挑戰(zhàn),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升級的風(fēng)險日益增加,我們需要做好自己的事,積極探索減緩風(fēng)險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