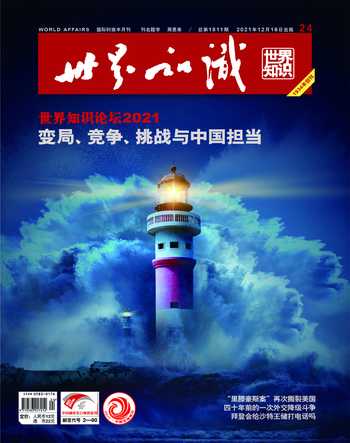歐洲:大變局推動大轉型
2021年歐洲和歐盟的關鍵詞是“恢復”和“自主”:從新冠疫災中力推經濟復蘇,在大國地緣政治競爭中爭取自主。為了應對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歐洲選擇了經濟轉型和外交轉型,這兩個轉型將對歐洲以及歐洲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產生重大的影響。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核潛艇風波對法美和歐美關系的沖擊,以及“后默克爾時代”中德和中歐關系的走向等也值得關注。
推動經濟復蘇是歐洲國家第一要務。近年歐洲遭遇不少危機和挑戰。從經濟方面來看,新冠疫情導致的危機是繼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后,歐洲在十多年來遭遇的第三大也是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對歐洲各國經濟均產生了巨大沖擊。2020年歐盟27國整體國內生產總值下降6.3%,歐元區下降6.8%。2021年隨著社交限制措施逐步取消以及疫苗廣泛接種,加上歐洲本地區及全球各方面需求復蘇,歐洲國家經濟在第二、第三季度強勁反彈,尤其是第三季度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環比增長2.1%,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增長2.2%。但歐盟國內生產總值在2021年底前能否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尚不確定。疫情反彈、供應鏈問題、通脹飆升、能源價格高企等問題很可能會拖累第四季度歐洲經濟增長水平。
歐盟力推在疫后復蘇中實現綠色轉型和數字化轉型。2020年歐盟委員會宣布歐盟將2030年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由原有的40%提升至55%,“綠色新政”變成2019年底走馬上任的新一屆歐盟委員會的“頭號工程”。歐洲各國的交通運輸、建筑業等正成為生態轉型的重點行業。在加速推進綠色轉型的同時,2021年3月歐盟委員會提出了未來十年數字化轉型的目標。主要涉及數字技能、企業數字化轉型、數字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數字化四大方面。如果說2020年歐盟各國做出的最重要決定是就高達7500億歐元的“經濟復蘇基金”達成一致,那么2021年歐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將該基金中的大量資金投向生態轉型和數字革命,如歐盟撥給西班牙等國復蘇基金的40%將被用于應對氣候變化和在2050年前實現經濟全面脫碳的目標。

2021年11月3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勃艮第大區著名葡萄酒之鄉伯恩接待了卸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
世界變局推動歐洲對其國際角色再定位。歐盟不甘心僅扮演貿易和經濟行為體,成為一支地緣政治力量的愿望與日俱增。歐盟所說的地緣政治力量實際上是指在國際舞臺上可以自主發揮作用的力量,如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所言“能在國際上像其他大國一樣說話做事”。
歐洲所希望的“自主”很大程度上并非主動而為,而是形勢所迫。歐洲國家曾對奧巴馬提出的“重返亞洲”半信半疑,但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發生后北約又很快將“集體防衛”作為其首要任務,這意味著美國仍然保持著對歐洲的安全承諾。直到特朗普上臺,歐洲才開始認真思考美國若離開歐洲怎么辦。當2021年初拜登入主白宮并高呼“美國回來了”時,不少歐洲人如釋重負。但后來發生的兩件事再次激活了歐洲自主意識:一是美國不顧歐洲的意見執意從阿富汗倉促撤軍,二是美國與英國和澳大利亞組建新安全同盟。
歐洲人已經習慣了美國把戰略重心放在歐洲,然而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印太”日益成為美國的戰略優先地區,對于歐洲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很難接受的變化。雖然美國對修補美法關系非常上心,但從2021年9月22日馬克龍和拜登在核潛艇風波后首次通話時所講的內容來看,法國在經歷此事件后愈加堅信歐美關系與誰擔任美國總統關系不大,美國戰略重心轉移已成事實,歐洲必須增強自身防務能力,努力實現“戰略自主”。
2021年歐盟與中國的關系變化反映了其復雜特性。中歐關系近年來已經發生了嬗變,造成這一變化的既有歐洲中國觀的調整,也有來自美國的影響。當然首先需要指出,中歐經濟合作面仍然保持。2020年中國與歐盟貿易額達6495億美元,中國首次取代美國躍居歐盟第一大貨物貿易伙伴。2021年1~9月,中歐貿易額達5993.4億美元,增長30.4%。歐盟也是中國重要的外資來源地和直接投資目的地。同時,中國領導人與歐洲國家領導人以及歐盟高層通過電話和視頻保持了密切交流。但中歐保持經貿合作的同時,歐洲在與中國的交往中越來越強調競爭。2021年4月19日,歐盟外長理事會發布《歐盟印太合作戰略報告》,明顯體現了歐洲國家希望擴大自身在該地區影響以制衡中國的意圖;7月12日歐盟通過的“全球互聯互通戰略”則被一位文件起草者描述為雖只字未提中國,但中國卻無處不在。9月在歐洲議會做年度“盟情咨文”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宣布將歐洲的聯通戰略定名為“全球門戶”(global gateway)戰略。
在維持和擴大合作的同時,如何管控好分歧,已成為中歐雙方目前面臨的緊迫問題。這一點將因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離任而變得更加突出。2021年是德國大選年,也是默克爾總理告別政壇之年。默克爾連任四屆德國總理,執政16年間為中德和中歐關系的務實合作作出重大貢獻。“后默克爾時代”的德國和歐洲走向以及中德、中歐關系發展值得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