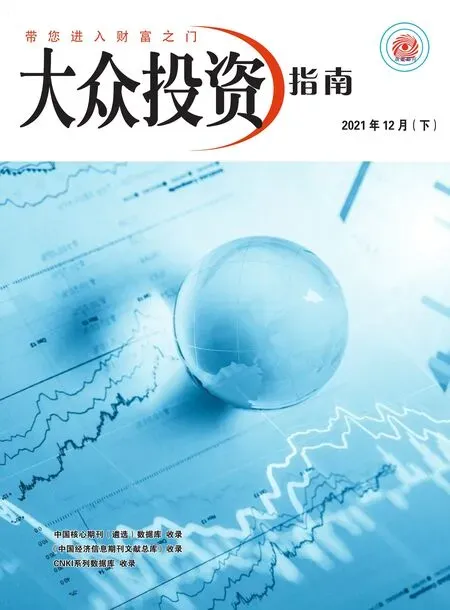異質(zhì)性環(huán)境規(guī)制、財政分權(quán)與綠色創(chuàng)新
鄺金平
(湖南科技大學(xué)商學(xué)院,湖南 湘潭 411201)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chuàng)新、協(xié)調(diào)、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fā)展理念,十九大將“綠色發(fā)展”與堅持“創(chuàng)新驅(qū)動”的作為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重要指引。綠色創(chuàng)新兼具“創(chuàng)新”和“綠色”兩種特性,既體現(xiàn)了綠色發(fā)展、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本理念,又符合經(jīng)濟(jì)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時代要求,是解決經(jīng)濟(jì)增長與資源環(huán)境沖突的重要手段。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不僅是治理污染外部性問題的重要手段,也是激勵企業(yè)綠色創(chuàng)新的源驅(qū)動力[1]。但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能否有效執(zhí)行與分權(quán)制度有關(guān)[2]。因此,有必要從財政分權(quán)視角考察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目前關(guān)于財政分權(quán)與環(huán)境規(guī)制及其相互結(jié)合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涉及尚少,財政分權(quán)制度作為了央地政府基本的制度配置,與地方政府的環(huán)境規(guī)制作為相輔相成。財政分權(quán)與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如何影響城市綠色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三者之間存在怎樣的影響機(jī)制?關(guān)于上述問題的回答,對于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以及綠色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一、研究假設(shè)
(一)環(huán)境規(guī)制影響綠色創(chuàng)新的直接效應(yīng)
根據(jù)“成本效應(yīng)”和“波特假設(shè)”理論,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呈“U型”。而“綠色需求引導(dǎo)”和“公眾輿論監(jiān)督”的存在,也使得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呈“U型”。
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通過政府或行政部門的直接命令與控制對社會主體施加影響,一方面,“成本效應(yīng)”認(rèn)為在高強(qiáng)度的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約束下,企業(yè)需要進(jìn)行生產(chǎn)技術(shù)革新和生產(chǎn)流程的調(diào)整,這無疑增加企業(yè)的管理成本和運(yùn)營成本,并且成本的增加又會進(jìn)一步擠占企業(yè)的研發(fā)資金,從而抑制企業(yè)的綠色創(chuàng)新活動。另一方面,“波特假說”認(rèn)為企業(yè)為了規(guī)避高昂的規(guī)制成本,會通過綠色工藝創(chuàng)新提升企業(yè)的污染治理能力,并且技術(shù)創(chuàng)新帶來的收益會抵消環(huán)境規(guī)制帶來的環(huán)境成本增厚企業(yè)利潤,促進(jìn)企業(yè)的綠色創(chuàng)新活動。
假設(shè)1a: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與綠色創(chuàng)新之間存在“U型”非線性關(guān)系。
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是公眾環(huán)保意識的集中體現(xiàn),一方面,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通過政府、學(xué)校、和環(huán)保NGO等組織或團(tuán)體對社會公眾進(jìn)行環(huán)保教育,培育環(huán)保意識,引導(dǎo)公眾開展綠色消費,這會影響企業(yè)的供給結(jié)構(gòu),促使企業(yè)進(jìn)行綠色工藝創(chuàng)新,改良生產(chǎn)流程,推動產(chǎn)品向綠色產(chǎn)品轉(zhuǎn)型。另一方面,當(dāng)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為帶來較大的輿論壓力時,會增加企業(yè)的輿論公關(guān)成本。同時,輿論迫使企業(yè)減少排污行為,企業(yè)的生產(chǎn)成本相應(yīng)增加,從而擠占企業(yè)的研發(fā)支出,不利于企業(yè)綠色創(chuàng)新活動的開展。
假設(shè)1b: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與綠色創(chuàng)新之間存在“U型”非線性關(guān)系。
(二)財政分權(quán)對環(huán)境規(guī)制與綠色創(chuàng)新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
財政分權(quán)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必然通過影響特定環(huán)境下的行為主體才能真正發(fā)揮效用[3]。一方面,在財政分權(quán)兩種激勵機(jī)制下,地方政府推動轄區(qū)綠色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動力將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環(huán)境規(guī)制作為政府進(jìn)行轄區(qū)環(huán)境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城市環(huán)境保護(hù)意識與污染治理能力的體現(xiàn)。在財政分權(quán)背景下環(huán)境規(guī)制規(guī)制效率得到改善[4]。另一方面,由于生態(tài)績效作為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指標(biāo)之一,財政分權(quán)下地方政府獲得更多和財權(quán)和事權(quán)[5],因此在投資時地方政府會考慮環(huán)境狀況以及民眾訴求,制定與本地的現(xiàn)狀相適應(yīng)的政策制度,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將具備更強(qiáng)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從而提升正式、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實施效率,有助于城市綠色創(chuàng)新的實現(xiàn)。
假設(shè)2a:財政分權(quán)在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中有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
假設(shè)2b:財政分權(quán)在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中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
二、研究設(shè)計
(一)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選取的樣本為2005-2018年中國285個城市的面板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均來自《中國城市統(tǒng)計年鑒》《中國統(tǒng)計年鑒》以及部分地方統(tǒng)計局,在實證中除綠色創(chuàng)新數(shù)據(jù)外對所有變量取對數(shù)處理。
(二)變量定義
綠色創(chuàng)新:本文運(yùn)用SBM模型測算城市綠色創(chuàng)新水平。將地方科技從業(yè)人員數(shù)以及地方財政支出中科技投入作為綠色創(chuàng)新投入變量。用專利申請數(shù)作為綠色創(chuàng)新的期望產(chǎn)出指標(biāo)。將工業(yè)廢水排放量,工業(yè)煙(粉)塵排放量以及工業(yè)二氧化硫排放量作為綠色創(chuàng)新的非期望產(chǎn)出,具體數(shù)值運(yùn)用MAX—DEA軟件測算。
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用熵權(quán)法對工業(yè)固體廢物利用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以及污水集中處理率三個指標(biāo)進(jìn)行綜合測度。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用熵權(quán)法對工資水平、人口密度以及教育水平三個指標(biāo)進(jìn)行綜合測度,其中工資水平用城鎮(zhèn)職工平均工資水平表示,教育水平用每萬人在校大學(xué)生數(shù)表示。財政分權(quán):為全面考察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quán)程度,財政支出分權(quán)水平:用地區(qū)人均一般公共預(yù)算財政支出與當(dāng)年全國人均總預(yù)算財政支出之比衡量。
在控制變量中,外商投資:選取各地區(qū)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與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之比表示,并用歷年的美元年平均匯率將其折算為人民幣。政府干預(yù):用地方政府公共預(yù)算支出與地方生產(chǎn)總值之比衡量。地區(qū)交通水平:用人均實有道路面積數(shù)衡量。地區(q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用第二產(chǎn)業(yè)占比除以第三產(chǎn)業(yè)占比衡量。
(三)估計方法
為考察正式、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本文構(gòu)建如下模型:

在式(1)中,gii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綠色創(chuàng)新水平,l.giit為滯后一期的綠色創(chuàng)新水平。X為解釋變量,分別表示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X2分別表示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的二次項。Control為各控制變量,λi為個體固定效應(yīng)、μt為時間固定效應(yīng),εit為隨機(jī)擾動項。α、β0~β6表示待估參數(shù)。
為進(jìn)一步考察財政分權(quán)對正式、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和綠色創(chuàng)新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構(gòu)建如下模型:

在式(2)中,lnfediit表示財政分權(quán)水平、Xlnfediit分別表示正式、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與財政分權(quán)水平的交互項,用于考察財政分權(quán)的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γ1、γ2表示待估參數(shù)。其余變量參考式(1)。
三、實證分析
(一)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直接影響
表1給出了系統(tǒng)GMM模型下,綠色創(chuàng)新滯后項以及正式、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回歸結(jié)果。

表1 正式、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影響綠色創(chuàng)新的實證檢驗
各模型中綠色創(chuàng)新滯后一期的估計系數(shù)在1%的水平下均顯著為正,表明我國綠色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存在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具有顯著的正向積累效應(yīng)。模型(1)中,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的二次項系數(shù)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整體上呈先抑制后促進(jìn)的“U型”關(guān)系。模型(2)中,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二次項系數(shù)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整體上呈現(xiàn)出先抑制后促進(jìn)的“U型”動態(tài)變化過程,實證結(jié)果驗證了假設(shè)1a。從控制變量來看,交通水平和外商投資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為正。政府干預(yù)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顯著為負(fù)。
(二)財政分權(quán)對環(huán)境規(guī)制與綠色創(chuàng)新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表2 為運(yùn)用系統(tǒng)GMM模型考察財政分權(quán)對正式、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與綠色創(chuàng)新調(diào)節(jié)作用的影響。
在表2中,財政分權(quán)的回歸系數(shù)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財政分權(quán)有助于綠色創(chuàng)新活動的開展,在模型(3)中,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與財政分權(quán)的交互項系數(shù)為0.0129,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財政分權(quán)在環(huán)境規(guī)制與綠色創(chuàng)新之間產(chǎn)生了正向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財政分權(quán)下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具有更強(qiáng)調(diào)動性和針對性,增加了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的靈活性,有助于綠色創(chuàng)新活動的開展。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與財政分權(quán)的交互項為0.0297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財政分權(quán)在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與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中存在顯著的正向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財政分權(quán)提高了普通社會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主體的政治積極性得到提高,有助于監(jiān)督和約束地方政府的投資偏好行為,進(jìn)而促進(jìn)政府參與城市綠色創(chuàng)新活動的效果,支持了假設(shè)2a、2b。

表2 財政分權(quán)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的實證檢驗
四、結(jié)論與建議
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得出以下結(jié)論:一是整體上正式、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與綠色創(chuàng)新存在“U”型非線性關(guān)系。二是財政分權(quán)在正式、非正式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創(chuàng)新的影響中均存在正向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因此,政府需要優(yōu)化分權(quán)體制,明確地方政府在環(huán)境規(guī)制中的事權(quán)與職責(zé)。健全地方環(huán)保責(zé)任機(jī)制,按照責(zé)權(quán)對等原則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在環(huán)境規(guī)制中的權(quán)責(zé)利益,引導(dǎo)規(guī)范地方政府良性競爭;規(guī)范地方激勵機(jī)制,避免地方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扭曲。深化地方政府官員的晉升考核機(jī)制改革;制定差異化的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體系。無論在監(jiān)管還是執(zhí)行的過程中,應(yīng)有的放矢,目標(biāo)明確。針對不同財政分權(quán)水平、區(qū)域發(fā)展水平以及行政等級等因素實施差異化的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