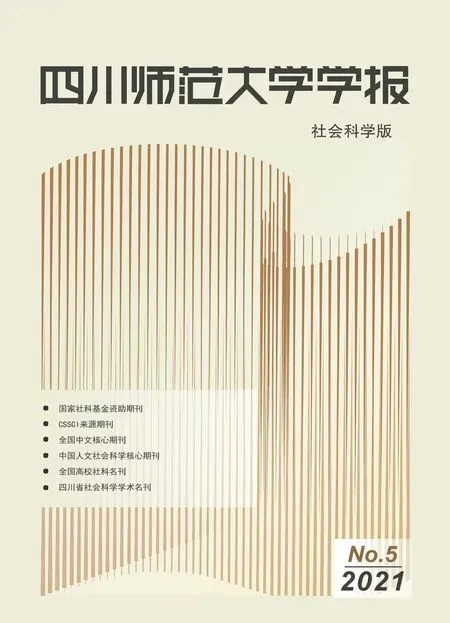西方政治馬克思主義話語框架的解釋性反思
——以“過渡—危機”之爭的論證為例
亓光 魏凌云
近年來,政治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不斷攀升,特別是在“資本主義起源”的論爭中表現(xiàn)突出,成為“多布—斯維奇之辯”(1)莫里斯·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與保羅·斯維奇(Paul M. Sweezy)在資本主義第一推動力問題上針鋒相對。多布提出應該將封建制度視為生產(chǎn)關系,而生產(chǎn)關系改變的主要動力應該是工業(yè)資本家。這一論斷遭到斯維奇的批判,他認為多布的觀點不能在制度內(nèi)部得到解釋,將封建制度視為服務于生產(chǎn)的保守制度更為合理,在此,長途貿(mào)易被斯維奇判定為導致封建社會解體的根本因素。的主要延續(xù)與重要深化,已經(jīng)形成了系統(tǒng)完整的學術譜系(2)政治馬克思主義(Political Marxism)是產(chǎn)生于20世紀70年代,由布倫納、伍德引領的西方左翼思潮,主張構(gòu)建以超經(jīng)濟關系為核心的資本主義起源解釋框架,主要探討歷史上非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發(fā)展方式。其創(chuàng)建人是羅伯特·布倫納與艾倫·伍德。艾倫·伍德是加拿大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國內(nèi)也譯作埃倫·M·伍德、埃倫·伍德、艾倫·梅克辛斯·伍德、埃倫·米克辛斯·伍德等。。在政治馬克思主義內(nèi)部,布倫納與伍德主張以社會財產(chǎn)關系解釋資本主義起源、從過度競爭角度挖掘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這引發(fā)了西方左翼學者激烈的辯論,激發(fā)了曠日持久的“過渡—危機”之爭(3)所謂“過渡之爭”,主要指政治馬克思主義主張以“社會財產(chǎn)關系”解釋資本主義的農(nóng)業(yè)起源,認為“市場迫切性”是生產(chǎn)關系改變的主要動力。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主張?zhí)岢鲑|(zhì)疑,如應該從經(jīng)濟(市場、貿(mào)易、技術)角度還是從政治(階級關系)角度探索資本主義起源、起源地點發(fā)生在工業(yè)領域還是在農(nóng)業(yè)領域、發(fā)源地點在英國還是法國,等等。所謂“危機之爭”,主要指針對本世紀初經(jīng)濟長期停滯的現(xiàn)象,政治馬克思主義提出經(jīng)濟危機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產(chǎn)能過剩,這與當時將此類危機歸類為“金融危機”的主流觀點產(chǎn)生爭論,如以壟斷作為經(jīng)濟停滯原因的“壟斷資本主義說”、以和諧勞資關系建構(gòu)為核心的“社會積累結(jié)構(gòu)瓦解說”與調(diào)節(jié)學派的“福特制危機說”。,至今熱度不減。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政治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域進一步拓展到了社會財產(chǎn)關系理論、過度競爭理論、新帝國主義理論、階級理論、民主理論、國家理論等方面,并在與大衛(wèi)·哈維、E.P.湯普森、尼克斯·普蘭查斯、鮑勃·杰索普、拉克勞與墨菲等西方學者的理論爭論中越發(fā)顯學化,由此也引起了國內(nèi)學界廣泛關注。在紛繁復雜的“保護性論證”和“隱喻式闡釋”中,政治馬克思主義關于“過渡—危機”之爭的學理性反思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以此為核心對象而構(gòu)建起來的“政治性分析”的概念框架則是當代西方“整體性馬克思主義”反思的基礎性分析路徑之一。因此,為了有效厘清政治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框架,進而把握“過渡—危機”之爭的分析架構(gòu),就有必要探討其“理論預設—論證邏輯—范式歸屬”的研究理路。
一 “簡單適用的重建”:跨接經(jīng)典與現(xiàn)代的理論預設
人們普遍認為,理論預設或福柯所認為的“共識”又或蒂利希(Paul Tillich)所強調(diào)的“終極原則”,主要是指提出者認為不證自明、理所當然的公理命題。正如有的學者所言:“聰明的人在敘述或解釋任何問題時,總有一個邏輯起點成為他的盲點,那就是不必論證和思索的終極依據(jù)。”(4)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頁。簡言之,理論預設是歷史分析中的主要背景與依據(jù)。政治馬克思主義在介入“多布—斯維奇之辯”伊始,就十分重視理論預設的指認。然而,隨著知識的豐富性與思想的復雜性不斷滋長,這個背景和依據(jù)在時間的流逝中漸漸隱沒。正因為如此,我們有必要首先揭示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預設,厘清其理論體系的根基。
眾所周知,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學術界關于馬克思主義是否具有整體性的分歧愈發(fā)凸顯,很多學者都認為存在“青年”與“老年”兩個馬克思,似乎為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的割裂性找到了現(xiàn)代解釋經(jīng)典的理由。在這里,“過渡—危機”之爭中呈現(xiàn)出諸多政治性議題,都似乎出現(xiàn)了轉(zhuǎn)變性路徑的“曙光”。對此,政治馬克思主義一經(jīng)問世,就旗幟鮮明地主張馬克思的整個思想具有結(jié)構(gòu)的完整性,而支撐這一結(jié)構(gòu)完整性的基礎就是對“過渡—危機”之爭的“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上堅持“簡單適用”原則,即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中分別提出的“分工論”與“生產(chǎn)方式論”過渡解釋模式,被西方學者判斷為兩種不同理論的決裂。在布倫納看來,雖然早期馬克思具有濃厚的斯密式思維,但“馬克思似乎在某些重要方面遠遠超越了斯密。……正是憑借對階級和財產(chǎn)權概念的發(fā)展”(5)〔美〕羅伯特·布倫納《馬克思社會發(fā)展理論新解》,張秀琴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頁。,而“生產(chǎn)方式論”就是沿著這一理論思維的進一步豐富。政治馬克思主義正是在政治經(jīng)濟學分析框架內(nèi),以核心概念為依據(jù),將唯物史觀的基本判斷及其在人與社會、階級與革命、理論與實踐、財產(chǎn)與人性、勞動與異化等議題上的基本結(jié)論直接運用到分析理路中,體現(xiàn)出其所秉持的新歷史主義原則以及將社會發(fā)展作為核心概念的選擇。由此,在簡單適用中就生成了聯(lián)結(jié)經(jīng)典與現(xiàn)代的理論預設。
一方面,在“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的批判性解構(gòu)基礎上,政治馬克思主義揭示了“社會財產(chǎn)關系”概念詮釋起源問題,并形成了“基礎—上層建筑”的理論預設。在這一理論預設的形成中,唯意志主義傾向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在政治馬克思主義之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譜系內(nèi)普遍認為,馬克思去世之后,無論是“蘇俄”的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還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如阿爾都塞等)均對“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理論模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夸大與自我解讀。伍德認為,正是這一過程,使得該理論模型被曲解了,讓原本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化的命題陷入了二元論的困境,進而帶來了割裂理論與現(xiàn)實、歷史與偶然、資本主義政治與經(jīng)濟關系的錯誤認識,導致了對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泛化理解。與此同時,在政治馬克思主義者那里,在對生產(chǎn)方式的界定方面,既存解釋的缺陷也比較明顯。伍德就明確指出,“生產(chǎn)方式不只是一種技術方式”,而是凝結(jié)全部社會關系而形成的權力關系(6)〔加〕艾倫·梅克森斯·伍德主編《民主反對資本主義——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呂薇洲、劉海霞、邢文增譯,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頁。。事實上,西方學界的多次爭論均內(nèi)置于這一理論框架之內(nèi)。在這里,為擺脫術語的語義約束,真正揭示“生產(chǎn)關系”中的“技術”因素的本質(zhì)意義,布倫納提出并構(gòu)建了“社會財產(chǎn)關系”概念,其主要指直接生產(chǎn)者之間的關系、剝削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剝削者與直接生產(chǎn)者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為個體和家庭獲取生產(chǎn)資料以及從事既定的社會生產(chǎn)提供了可能性和具體形式。在政治馬克思主義那里,這是分析社會形態(tài)問題的首要理論預設。布倫納指出,這種對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史觀的“簡單適用”具有經(jīng)典語義的現(xiàn)代話語價值,而這一概念的合理性在于階級關系貫穿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并包含了同階級之間的水平關系與不同階級之間的垂直關系。作為政治馬克思主義首要理論預設的核心概念,“新概念”一經(jīng)提出就引發(fā)了極大爭議(7)蓋·鮑耶斯(Guy Bois)批評政治馬克思主義不僅忽視了歷史唯物主義最有效的概念(生產(chǎn)方式),而且放棄了現(xiàn)實的經(jīng)濟領域。。為此,伍德等人進一步指出政治馬克思主義提出的社會財產(chǎn)關系概念所進行的“簡單適用”至少具有兩個層次:一是采納并堅持“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的關系模型,二是在馬克思整體性思想上理解這一關系模型,并就此構(gòu)建一種標簽化的批判方式。在此基礎上,通過在歷史特殊性與歷史過程中尋找邏輯之間的辯證法,根據(jù)時代與社會條件的變化,就可以“去除馬克思之后人們在‘基礎—上層建筑’隱喻中添加的雜質(zhì)”(8)姜霽青《拯救被曲解的“基礎—上層建筑”隱喻——埃倫·伍德對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理論的批判與重構(gòu)》,《云南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第38頁。。不過,以“社會財產(chǎn)關系”替代“生產(chǎn)關系”,并將其作為資本主義起源闡釋的主要依據(jù),至少存在四個方面的長期性質(zhì)疑難題:(1)從“階級關系”分析資本主義起源,將“生產(chǎn)力”置于次要位置,明顯忽視生產(chǎn)力因素;(2)“生產(chǎn)關系”概念內(nèi)涵的界定問題在“社會財產(chǎn)關系”這里難以充分回應,因為政治馬克思主義對“生產(chǎn)關系”概念的詮釋否定了技術因素而使其成為純粹的階級關系概念,這種認識的合理性存在較大爭議;(3)從“結(jié)構(gòu)性”角度看,“財產(chǎn)關系決定‘再生產(chǎn)規(guī)則的說法’,又非常接近于制度學派關于制度決定‘游戲規(guī)則’的思想”(9)魯克儉、鄭吉偉《布倫納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評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6年第2期,第26頁。;(4)從“原始積累”角度質(zhì)疑“社會財產(chǎn)關系”尚不足以對馬克思所論述的資本的原始積累諸要素在資本主義初始發(fā)展階段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充分說明。
另一方面,在全面反思商業(yè)起源說、人口起源說等資本主義普遍化觀念的基礎上,政治馬克思主義通過“資本主義特殊性”、“階級關系存續(xù)性”與“農(nóng)民地位的關鍵性”三個預設命題,構(gòu)建了“市場迫切性”作為資本主義起源之合理性因素的理論預設。首先,在資本主義特殊性問題上,政治馬克思主義強調(diào)其遵循了馬克思“證明資本主義是一種歷史存在,是有其產(chǎn)生亦有其終結(jié)的歷史性存在物”(10)王南湜《中西現(xiàn)代性的再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古典哲學比較與匯通的前提性考察》,《哲學動態(tài)》2018年第10期,第9頁。的原則方法。在這里,與經(jīng)濟主義的解釋路徑相比,政治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評價是較為客觀公允的。其次,在階級關系存續(xù)性問題上,政治馬克思主義對“階級關系”的分析引發(fā)了較大的爭議。布倫納將“階級關系”視為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紅線,進而將論證的重點放在農(nóng)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關系(社會財產(chǎn)關系)如何推動資本主義要素的產(chǎn)生方面。他繼而將其看作一種內(nèi)部要素(本質(zhì)性的),并對其推動社會變革給予了全面肯定。不過,圍繞資本主義是萌芽于封建主義母體還是縫隙的問題上,政治馬克思主義自身出現(xiàn)了內(nèi)部分歧。有論者指出從階級關系(內(nèi)部競爭)維度能夠為不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落后提供合理性依據(jù),但同時夸大了競爭的作用,偏離了馬克思經(jīng)典作家所指認的競爭是“使資本主義內(nèi)在規(guī)律外在化”的基本判斷;這一特征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排斥生產(chǎn)力決定論,無疑就是在否定一種“理想主義的理論神話”時卻勾勒了另外一個“理論神話”。之所以會出現(xiàn)上述問題與分析,關鍵就在于政治馬克思主義者在對待經(jīng)典作家所提出的生產(chǎn)力概念時,建構(gòu)了一個“理論斗爭的標靶”,試圖將生產(chǎn)力概念作為一個純粹性、物理性、自發(fā)性的范疇,進而加以批判以避免陷入歷史決定論的話語陷阱。為此,他們只能通過借喻方式揭示生產(chǎn)力決定論是動態(tài)的而非機械的,那么這里產(chǎn)生的分歧實際上并不會影響其總體性的理論預設,只能是一種理論體系的內(nèi)在豐富。最后,在農(nóng)民地位關鍵性的問題上,政治馬克思主義主要聚焦于西歐英國、法國兩大國家的農(nóng)業(yè)結(jié)構(gòu)問題,力圖在對西歐國家的資本主義產(chǎn)生的關鍵因素判斷中突出農(nóng)民地位,即指出是農(nóng)民因失去生產(chǎn)資料而與雇主最早生成強制性的市場迫切性造成了資本主義的早期萌芽,進而得出資本主義最先發(fā)生于農(nóng)業(yè)領域的基本結(jié)論。不過,該假定忽視了富裕農(nóng)民經(jīng)濟和農(nóng)村階級分化等狀況,難以充分評價生產(chǎn)中的農(nóng)民作用,這也就為其理論預設的完整性留下較大的漏洞,特別是為了張揚歷史特殊性而突顯主體能動性的做法,消解了普遍規(guī)律的存在,使之理論預設的構(gòu)建陷入經(jīng)驗主義的泥潭,這導致了其在系統(tǒng)論證國家等更為復雜的問題時,出現(xiàn)了還原成因分析的單向度性。
通過上述兩點,不難看出,政治馬克思主義在建構(gòu)它的理論大廈時,首先尋求的是“適用”經(jīng)典作家的基本判斷,并根據(jù)其所意圖解決和指認的社會現(xiàn)象與問題進行“簡單化”的適用性解釋,不過這種“簡單適用”并不是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爾派時的觀念適用的簡單化確認,而是希望在直面人類社會的當下問題特別是解構(gòu)性、風險性、后現(xiàn)代性的歷史趨向的理論困境時,能夠在經(jīng)典作家與時代議題之間找到一個簡單適用的重建性模型。
二 “本質(zhì)—結(jié)構(gòu)—方法”論證邏輯:“整體性”的內(nèi)在風險
在對“過渡—危機”之爭進行論證的過程中,政治馬克思主義試圖將實證分析與語境分析結(jié)合在一起,由此構(gòu)建資本主義批判的“語言—歷史”的論證邏輯。然而,在切入“過渡—危機”之爭時,這一重塑論證邏輯的策略與嘗試逐漸暴露出了其在論證邏輯上的內(nèi)在風險,這主要體現(xiàn)在“本質(zhì)—結(jié)構(gòu)—方法”這一整體性論證邏輯的自身缺陷上。
在20世紀中葉前,無論是針對資本主義起源問題還是關于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問題,主要存在兩條典型的解釋路徑:一是“規(guī)范性論證”路徑,其專注于編織復雜交織的概念網(wǎng),環(huán)環(huán)相扣地從理論的必然性中闡發(fā)相關論題;二是“經(jīng)驗性論證”路徑,其致力于對歷史具體事件進行具體探析,以此種實證分析推理“歷史”—“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必然性。這二者雖然并不存在態(tài)度性或意見性的對立,但卻在方法論層面上出現(xiàn)了論證邏輯的分歧,進而帶來了“理論與現(xiàn)實”、“規(guī)范與經(jīng)驗”、“政治哲學與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割裂性后果。為了彌合這一論證邏輯上的對立狀態(tài),當代加拿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麥克弗森(C.B. Macpherson)提出將政治理論與歷史語境相結(jié)合的新路徑,并得到了政治馬克思主義的高度贊同與響應支持(11)〔加〕艾倫·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公民到領主》,曹帥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頁。。在這里,政治馬克思主義者運用語境主義方法,凸顯了歷史特殊性,繼而從實證分析路徑提出并探究了資本主義作為社會形態(tài)的階段性、作為歷史事件的偶然性以及作為市場邏輯的強制性等三個典型特性。通過“整體性論證”,政治馬克思主義認為其超越了既存論證邏輯的局限性,并得出了資本主義并不具有普遍性、歷史唯物主義只能適用于對資本主義的解釋的基本結(jié)論。他們認為,經(jīng)典作家關于“過渡—危機”的論述已無法解決人類社會的時代挑戰(zhàn),難以解釋當代資本主義如何邁向過渡以及如何跨越“資本主義危機”的問題,因而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重建戰(zhàn)略。客觀而言,這一認識的形成是在“簡單適用”的理論預設下,是其理論體系內(nèi)的“整體性”與“歷史性”的內(nèi)在矛盾所造成的“本質(zhì)—結(jié)構(gòu)—方法”這一論證邏輯的必然結(jié)果。因此,這應是反思西方政治馬克思主義話語的解釋性框架的關鍵所在,需要從問題根源(本質(zhì)邏輯反思)、理論自洽(論證結(jié)構(gòu)反思)與方法論生成(方法運用反思)等三個維度加以具體批判。
第一,針對“過渡—危機”之爭的根源性問題,政治馬克思主義存在本質(zhì)邏輯反思科學性不足的風險。在“過渡之爭”問題上,政治馬克思主義從“市場依賴性”首次出現(xiàn)的地點、集權化統(tǒng)治方式保障物質(zhì)基礎、經(jīng)濟權力與超經(jīng)濟權力的平衡與佃農(nóng)推動市場形成等四個方面論證了英國的農(nóng)業(yè)資本主義起源,得到較為清楚且科學的結(jié)論。然而,當其轉(zhuǎn)向法國革命時,西方思想界關于“革命性質(zhì)與合法性”歷史爭論中的悖論再次出現(xiàn)。政治馬克思主義認為應該清楚區(qū)分“法國革命是資產(chǎn)階級的,不是資本主義的”的觀點,這就背離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歷史語境解析,而將法國工業(yè)資本主義的提出置于“資產(chǎn)階級—資本主義”的概念混淆之中,由此滑向了自由主義思潮(12)George Comninel,“Revolution in History: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ontext,” in The Social Question and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Marx and the Legacy of 1848, eds. Douglas Moggach and Paul Leduc Browne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0),72.。之所以出現(xiàn)此種問題,主要原因在于:(1)關于資本主義起源于農(nóng)業(yè)的論斷,究竟是依據(jù)歷史事實而得出的普遍結(jié)論,還是僅僅從農(nóng)業(yè)視角對資本主義起源現(xiàn)象所做的描述,政治馬克思主義并未明確區(qū)分和清楚論證;(2)政治馬克思主義將農(nóng)業(yè)資本主義的發(fā)生歸因于大規(guī)模的無產(chǎn)階級化,進而將“農(nóng)政轉(zhuǎn)型與無產(chǎn)階級化的同一性及其與商業(yè)資本主義的聯(lián)系”(13)葉敬忠、吳存玉《馬克思主義視角的農(nóng)政問題與農(nóng)政變遷》,《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2期,第15頁。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3)政治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起源于封建主義的縫隙,完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的“孕育說”,進而在“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之關系的討論上必然出現(xiàn)主次倒置的問題;(4)政治馬克思主義將革命看作是偶然事件,因而無法準確把握歷史決定論與人的能動性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在“危機之爭”的闡釋上,以布倫納為代表,政治馬克思主義者往往將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歸結(jié)為過度競爭導致的利潤率下降,而以利潤率下降屬于資本主義的階段性特征還是趨勢性特征來作為資本主義本質(zhì)的新解釋路徑,這本身就具有極大爭議。具體而言,僅從利潤率下降的表現(xiàn)來看,國際競爭加劇即便與利潤率下降有關,但也只能解釋利潤率在邊際上的下降(14)趙亮亮《布倫納利潤下降式危機說及其批評》,《金融評論》2013年第1期,第118頁。,絕非資本主義本質(zhì)性的表達。而過度競爭說也忽視了知識資本與技術革新對社會生產(chǎn)的影響,直接弱化了其作為價值理論關鍵概念的基礎性知識,加之局限于競爭層面而忽視對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雇傭勞動的研究——也就無法進一步揭示“過度競爭”的根源性因素(15)劉元琪《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蕭條性長波產(chǎn)生的根源——西方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近期有關爭論綜述》,《國外理論動態(tài)》2003年第6期,第9-13頁。。
第二,政治馬克思主義建構(gòu)了以“階級—國家”為核心的論證結(jié)構(gòu),但卻難以達到充分的理論自洽性。一方面,政治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階級與階級關系范疇,強調(diào)階級關系在人類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關系的分析時卻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具體而言,政治馬克思主義普遍指出,農(nóng)民階級在資本主義革命理論中占據(jù)關鍵地位。布倫納通過英法農(nóng)民階級的對比,論證了農(nóng)民起義對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重要性,卻夸大了法國農(nóng)民的階級地位,低估了英國農(nóng)民的獨立地位。還原式的階級關系分析與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精確性并不相同,復雜性的簡單還原與階級關系的“理論—現(xiàn)實”的歷史本質(zhì)研究之間存在很大的距離。因而,政治馬克思主義從農(nóng)民革命中的資本主義因素確認中得出農(nóng)業(yè)資本主義起源的判斷,這本身就不自洽。理論的不自洽造成了抽象的理論論證及其建構(gòu)上的“理論圓融性”,但這種圓融性是無法接受現(xiàn)實問題的挑戰(zhàn)的。比如,布倫納的過度競爭說提出利潤率下降而形成低利潤也是一種均衡,卻從基礎上混淆了個別行業(yè)利潤率下降與整個行業(yè)利潤率下降的差異性。特別是從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角度看,如果總需求不足且儲蓄大于投資,那么就不會形成過度競爭。近年來,在新帝國主義的理論爭論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內(nèi)部提出了諸多論斷,而圍繞權力邏輯與資本積累在資本全球擴張時代的內(nèi)在矛盾問題,伍德與哈維進行了深入的爭論,特別是在“政治—經(jīng)濟”關系范疇框架下的資本積累與帝國擴張問題上,產(chǎn)生了較為嚴重的分歧。伍德認為世界體系仍然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組成單位,但是從當前全球化的發(fā)展趨勢來看,國際組織與跨國公司在一定時期內(nèi)仍然發(fā)揮不可取代的作用。新帝國主義爭論隨之帶來如何看待全球化時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這也基本上代表了政治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認識,然而在國家的多元性和帝國主義關系的持續(xù)存在、經(jīng)濟斗爭轉(zhuǎn)化為階級斗爭的具體路徑等問題上,其“新解釋”在正—反分析的論證過程中,依然遮蔽了現(xiàn)代國家本質(zhì)的核心要義,而從政治現(xiàn)象與政治過程加以論證的理論結(jié)構(gòu)也已暴露出了無法自洽的弊端。
第三,政治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全面倒向了唯心主義,無法有效實現(xiàn)對其主訴論題的客觀性、經(jīng)驗性的反思需要。在政治馬克思主義者那里,他們的歷史研究中的確運用了大量經(jīng)驗材料,對英國、法國、荷蘭等國的資本主義歷史進行考察,由于研究的歷史視野較為長期,因此如何把握經(jīng)驗分析與歷史分析之間的距離問題成為論證科學性的關鍵。政治馬克思主義在經(jīng)驗論證時出現(xiàn)了三個問題:一是史實性研究中大量運用二手資料,以所謂的方法論框架代替史實性基礎,而史料與個案卻難以支撐上述框架;二是“以對象限定方法”,因其主要研究對象和視角是歐洲國家,而不是對國家的整體歷史與總體類型進行考察,所以出現(xiàn)了“確定性思維”的通病,即將特殊的“歷史政治”作為普遍的“理論政治”;三是學理性歸納優(yōu)先于歷史的具體,以至于政治馬克思主義越成熟,其預設性判定就越發(fā)抽象,而其學理性闡釋的歷史缺失也就越發(fā)明顯。與此同時,政治馬克思主義在科學抽象與具體歷史之間還試圖引入“經(jīng)歷”方法論,伍德一方面確實突破了湯普森將“經(jīng)歷”等同于“社會存在”的局限性,使之能夠更加科學地闡述“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16)馮旺舟《艾倫·梅克森斯·伍德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5頁。;另一方面,由于“經(jīng)歷”概念自身的本質(zhì)存疑性,就不能不面對“抽象”與“具體”的選擇困境,而抽象性闡釋如何能夠進入“具體”論題,這至今仍是政治馬克思主義在方法論上的難題。也正因為如此,政治馬克思主義在其方法論指引下,得出“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只適合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觀點也就是必然了。
三 “范式—本質(zhì)”的共性批判: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范式歸屬
眾所周知,研究范式是集結(jié)概念預設、分析工具、邏輯論證、研究方法的網(wǎng)絡框架,更是判斷問題解謎路徑的基本依據(jù)。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流派之一,政治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學術共同體,關鍵在于它在研究中形成了典型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從其研究范式的歸屬就能夠進一步發(fā)現(xiàn)其選擇問題的標準,當此種范式被視為理所當然時,這些被選擇的問題可以被認為是有解的問題。客觀而言,政治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起源與經(jīng)濟危機的研究范式并非獨創(chuàng),而是西方政治哲學與分析哲學的運用典范。因此,從共性角度分析,通過“范式—本質(zhì)”對比政治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路徑,不僅能夠發(fā)現(xiàn)該學派所具有的本質(zhì)缺陷,而且有助于推動厘清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共性”問題。
首先,政治馬克思主義在概念框架的構(gòu)建上呈現(xiàn)唯意志主義范式歸屬的特點。從馬克思主義整體性角度來看,伍德將政治與經(jīng)濟分離視為資本主義的特殊樣態(tài),主張從超經(jīng)濟因素的整體上來研究和把握資本主義,本質(zhì)上是“從反對經(jīng)濟決定論走向了片面強調(diào)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另一種決定論”(17)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整體性視角下世界主要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黨政研究》2015年第6期,第39頁。。最為明顯的是,政治馬克思主義將“生產(chǎn)關系”重新概念化為“社會財產(chǎn)關系”,主張“社會財產(chǎn)關系”超越“生產(chǎn)力”在社會歷史發(fā)展中占據(jù)主導地位。對此,有論者就指出,政治馬克思主義通過賦予“生產(chǎn)關系”概念主動性與豐富內(nèi)涵,使其擁有更多的獨立生存空間,脫離開對生產(chǎn)力的嚴重依附關系,呈現(xiàn)出歷史發(fā)展復雜性與個體化并存的豐富論證,有利于“打破人們頭腦中生產(chǎn)力單向度直線發(fā)展的慣性思維”(18)王麗麗《馬克思“社會形態(tài)”概念邏輯演進蘊含的思維特征——兼論西方學者關于馬克思社會形態(tài)理論的爭論》,《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317頁。。不難發(fā)現(xiàn),政治馬克思主義在凝練核心概念時,始終在歷史唯物主義與唯意志論之間搖擺不定,既想在理論層面強調(diào)歷史過程的線性必然性,又試圖在現(xiàn)實層面凸顯階級力量的主動性與偶然性。可見,政治馬克思主義背叛了歷史唯物主義,在研究范式上皈依了唯意志主義。
其次,政治馬克思主義在話語邏輯的推演中展現(xiàn)分析哲學范式歸屬的特點。眾所周知,在整個20世紀的語言學轉(zhuǎn)向中,幾乎所有的理論流派在話語分析的邏輯上都直接受到了分析哲學的影響,政治馬克思主義也并不例外。在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自我建構(gòu)中,布倫納就作為“九月小組”加入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繼承了語言分析、邏輯分析的方法,在政治學、經(jīng)濟學、歷史學、哲學等領域開展對“過渡—危機”之爭核心議題的研究。因此,挖掘政治馬克思主義論證邏輯中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源成為當前研究熱點。有論者從理論繼承性角度,提出政治馬克思主義社會內(nèi)在增殖動力論與分析馬克思主義將生產(chǎn)力、競爭作為社會發(fā)展動力具有內(nèi)在一致性;或從概念發(fā)展角度,認為伍德對湯普森“經(jīng)歷”概念的發(fā)展說明了其對分析馬克思主義的繼承關系。還有論者認為政治馬克思主義“一方面被一些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論者劃歸為科學主義、特別是分析主義馬克思主義行列,另一方面又與后者保持著適當?shù)木嚯x與差異”(19)張秀琴《當代美國“經(jīng)濟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fā)展觀——以布倫納的“社會財產(chǎn)關系論”為例》,《江海學刊》2012年第4期,第33頁。,而這一趨勢正是戰(zhàn)后美國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問題,如何看待這一變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最后,政治馬克思主義對關鍵概念的分析引發(fā)了結(jié)構(gòu)主義范式歸屬的爭論。在提出并論證關鍵概念的過程中,政治馬克思主義全面批判了阿爾都塞的結(jié)構(gòu)主義論,認為“這是在理論和歷史之間建立僵化的二元論,是一種悖論,最終將結(jié)構(gòu)決定論排除在歷史之外”(20)馮旺舟、俞麗君《評析艾倫·梅克森斯·伍德對阿爾都塞結(jié)構(gòu)決定論歷史觀的批判》,《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36頁。。然而當資本主義起源的闡釋轉(zhuǎn)向階級關系的分析理路時,政治馬克思主義卻陷入了新的結(jié)構(gòu)主義,即“介于結(jié)構(gòu)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的方案”(21)張秀琴《當代美國“經(jīng)濟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fā)展觀——以布倫納的“社會財產(chǎn)關系論”為例》,《江海學刊》2012年第4期,第33頁。。在階級結(jié)構(gòu)、財產(chǎn)關系、階級斗爭等關鍵概念的具體闡釋時,政治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新結(jié)構(gòu)決定論”始終旨在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的復雜性與特殊性的闡釋,在具體的偶然性事件中難以確認一般的規(guī)律性認知,這直接產(chǎn)生了必然性與偶然性的二元對立。正是在這里,政治馬克思主義就必然會進一步消解歷史唯物主義。尤為典型的是,政治馬克思主義對阿爾都塞式結(jié)構(gòu)主義的批判,一針見血地指出結(jié)構(gòu)主義陷入將經(jīng)濟以外因素無限拔高的極端主義傾向,但是這種批判一旦從對象的批判轉(zhuǎn)為批判的對象時——如對農(nóng)民的評價——分析框架的結(jié)構(gòu)性是清楚可見的,如布倫納分析“租金上漲源于封建關系,領主依靠封建權力剝奪農(nóng)民”(22)M.M. Postan and John Hatcher, “Popul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Feudal Society,” in 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eds. T.H. Aston, and C.H.E. Philp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75.。在這里,根本的缺陷在于人們并不能由社會的“結(jié)構(gòu)”中找到通向自然經(jīng)濟轉(zhuǎn)變的基礎模式,必須扎根于物質(zhì),布倫納卻在歷史追溯中形成了結(jié)構(gòu)分析而非階級分析的基本判斷,因而徹底改變了階級分析方法等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適用性。
四 政治馬克思主義話語解釋框架的新探索:初步反思的基本路向
從整體上看,政治馬克思主義始終深陷于“整體性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之中,其既有試圖揭示西方馬克思主義話語解釋框架的割裂性的主觀訴求,卻又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受限于分析哲學路徑下“準確性”追索而造成的碎片化的現(xiàn)實傾向。也正是在這里,政治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其相對獨特的話語解釋框架。布倫納、伍德等人在回歸經(jīng)典文本特別是通過“階級關系”來解讀《資本論》的基礎上直面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現(xiàn)實問題,提出一系列著名論說。而《資本論》的政治解讀、經(jīng)濟危機的根源分析、布倫納辯論、全球化與新帝國主義之辯以及“階級斗爭”與新社會主義之辯等五個方面,是全面把握其話語解釋框架的主要路向。
其一,政治馬克思主義在超越作為“科學”的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中探究《資本論》的政治性解讀。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持續(xù)展開與社會抵制運動的不斷發(fā)生的現(xiàn)實共同推動了《資本論》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研究的緊迫性,問題的關鍵是在《資本論》的解讀中深刻揭示階級關系與歷史規(guī)律的內(nèi)在關聯(lián)性。政治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財產(chǎn)關系”就是建基于達爾多(Pierre Dardot)、雷諾(Emannual Renault)、赫策爾(Ludovic Hetzel)的研究成果,對《資本論》政治性解讀的一次有益嘗試。在這里,科米奈爾提出:“如果你想了解前資本主義社會,你就必須理解階級關系是如何作為權力(power)而發(fā)揮作用的。”(23)張福公《“政治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fā)展與理論“重建”——訪喬治·科米奈爾教授》,《國外理論動態(tài)》2019年第2期,第7頁。正是在分析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矛盾的基礎上,政治馬克思主義試圖回應當代新自由主義將資本主義普遍化的傾向,并力圖從學理上證明《資本論》在當前階級斗爭中的現(xiàn)實價值。
其二,政治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利潤率下降的分析中闡發(fā)了危機根源問題,明顯與勞動價值論偏離。布倫納基本遵循了馬克思從內(nèi)部(市場價值形成)研究經(jīng)濟規(guī)律的路徑選擇,但是在“競爭”問題上產(chǎn)生分歧:在馬克思看來,“競爭”是外在性因素,而布倫納認為是主動性因素。二人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關鍵在于對危機根源的歸納不同:馬克思通過勞動價值論分析,認為資本的剝削本質(zhì)導致了危機持續(xù)存在;而在布倫納這里,資本的特性被概括為盲目積累與過度競爭。可見,過度競爭理論明顯地偏離了勞動價值論旨歸。除此之外,值得關注的是,馬克思與布倫納由于時代局限性都是根據(jù)實體經(jīng)濟的發(fā)展情況得出利潤率下降的結(jié)論,而當代技術與知識在資本主義生產(chǎn)中的地位與作用愈加明顯,因而在今后資本主義危機分析中,有必要加強金融業(yè)與第三產(chǎn)業(yè)的研究。
其三,政治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起源的爭論中基本厘定了歷史唯物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內(nèi)在關系的價值意義。眾所周知,研究起源問題的難點并不在于歷史實證性,關鍵在于蘊含其中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尤其是生產(chǎn)力決定論與階級能動性之間的獨特張力。由于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與《資本論》中提出兩種過渡理論,前者傾向于生產(chǎn)力,而后者傾向于生產(chǎn)關系。理論分野究竟是因為早期馬克思尚未擺脫斯密式思維,還是根本性的斷裂式轉(zhuǎn)向,在西方學術界引起理論爭鋒,其根本原因在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與階級斗爭理論的關系難題。值得肯定的是,政治馬克思主義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斯密主義、新馬爾薩斯主義的生產(chǎn)力決定論掩蓋了階級斗爭的獨特價值,違背了馬克思生產(chǎn)力決定論與階級能動性之間具有張力的思想,有助于進一步推動和深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但是在其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卻滑向另一個極端——階級決定論。
其四,在批判新帝國主義的過程中,借由資本積累于權力邏輯的理論交鋒,政治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內(nèi)在運行機制進行了深刻反思。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的縱深發(fā)展,帝國主義研究近幾年熱度不減,其中,伍德與哈維將視野聚焦到資本邏輯與領土邏輯在資本主義內(nèi)在機制中的地位問題,引起國內(nèi)外學者的關注,如何理解“民族國家在全球體系的形成與運行”成為亟需解決的重大現(xiàn)實課題。在這里,二人的主要分歧在于資本主義內(nèi)在機制是否包含政治權力。哈維認為,資本邏輯將“政治”從“經(jīng)濟”中剝離,資本積累必須依靠政治權力的無限擴張,因而全球化必須依靠國際組織;但伍德認為,資本主義經(jīng)濟實質(zhì)是政治權力的內(nèi)部分化,也就是政治與經(jīng)濟的雙重邏輯,而國際組織無法執(zhí)行“全球國家”職能,能夠承擔這一職能的只有民族國家。在此,伍德與哈維的爭論將政治與經(jīng)濟的關系問題重新帶到人們面前,啟示人們關注全球資本與國際秩序的調(diào)整。
其五,政治馬克思主義在批判新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義時凸顯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現(xiàn)實價值。當代資本主義的突出特征就是技術與知識在社會生產(chǎn)領域占據(jù)關鍵地位,隨著工人階級整體教育程度的提高,階級的劃分極具不確定性,新中間階層的成分更加復雜化。對此,后馬克思主義者提出“新的真正社會主義”(NTS)理論,主張無產(chǎn)階級與社會革命的關系具有偶然性,其不確定性表明只有依靠代理人才能實現(xiàn)自身解放。對此,伍德認為資本主義新特征在社會領域凸顯,有必要重新審視界定階級分析的標準,以“結(jié)構(gòu)性過程”替代“結(jié)構(gòu)性定義”,以階級意識作為評判階級性質(zhì)的標準。政治馬克思主義無疑在這場爭論中捍衛(wèi)了階級斗爭在社會發(fā)展中的地位,但是,以“階級意識”作為評判標準的做法是否科學需要進一步研究,而如何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界定無產(chǎn)階級、如何認識階級斗爭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聯(lián)性、如何發(fā)動新社會運動,也是亟待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
五 結(jié)論
總之,西方政治馬克思主義話語框架顯露出這一學術流派的理論抱負絕不局限于學術思潮,其內(nèi)在要求與終極理想必然是在社會群體中掀起一場思想劇變。從話語框架本身來看,政治馬克思主義自介入“過渡—危機”之爭起,就開始鋪墊民主理論的出場,資本主義本質(zhì)理論與民主理論共同為政治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傳播打開了空間。依據(jù)社會財產(chǎn)關系理論,政治馬克思主義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本質(zhì)歸納為“市場迫切性”,意在表明純粹的市場經(jīng)濟并非資本主義的本質(zhì),只有當市場經(jīng)濟成為一種強制性的權力關系時,才具有資本主義屬性,這為理解市場經(jīng)濟與資本主義關系提供了一種新思路。那么,資本主義“政治”與“經(jīng)濟”形式分離也就不言自明了。正基于此,政治馬克思主義將民主理論的發(fā)展置于階級關系理論框架之下,將這一過程視為“純粹‘經(jīng)濟’權力代替了政治特權的制度”(24)〔加〕艾倫·梅克森斯·伍德主編《民主反對資本主義——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第200頁。,這的確為理解當代西方民主運行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會思潮的傳播往往是特定學術思潮社會化、概念化、標簽化、世俗化的結(jié)果。從譜系學角度看,政治馬克思主義是植根于新左派思潮并逐漸成為其新的理論內(nèi)核的。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新左派思潮曾圍繞“市場經(jīng)濟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和“實質(zhì)民主的內(nèi)涵”等議題與新自由主義進行了廣泛爭論,這一爭論發(fā)生時正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建立之際并由此奠定其作為當代我國重要社會思潮的地位。站在歷史的高度,新左派思潮的理論依據(jù)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關系理論,強調(diào)西方民主的局限是政治的有限民主,主張實現(xiàn)包括經(jīng)濟、文化領域的全面民主。在這里,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框架已然成為新左派思潮的重要理論支撐,助推了新左派思潮的持續(xù)傳播。正因為如此,面對新左派思潮的高度活躍,對其進行積極有效的思想引領就必須著眼于它的理論基底和思想變型進行嚴肅的學理性批判,這也正是對政治馬克思主義話語框架進行解釋性反思的真正價值與長久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