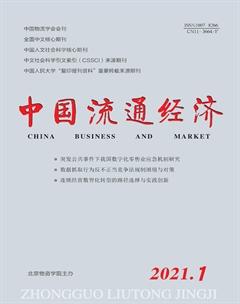社交電商的法律問題與監管優化
梁棟
摘要:隨著傳統電商遭遇發展瓶頸,作為電子商務經濟模式的一種衍生形態,社交電商在近年來獲得了較快發展。按照經營模式,社交電商可以分為四類,分別是拼購型社交電商、會員分銷型社交電商、內容分享型社交電商和社區團購型社交電商。社交電商平臺在具備私法屬性而同平臺內其他主體處于平等法律關系地位的同時,還需要配合監管部門對平臺內活動的其他主體承擔更多的監督管理責任。在快速發展過程中,社交電商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突出的包括經營模式隱傳銷化、虛假廣告泛濫、售后服務機制不健全和用戶個人信息保護不到位。面對此種情況,應從平臺內外兩條路徑進行監管優化。在平臺內部,提高商家入駐平臺門檻,完善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雙向監督機制,構建對社交活動參與者的信用評價體系,督促社交電商平臺履行個人信息保護義務;在平臺外部,出臺具備更高效力的社交電商經營規范,完善社交電商市場主體登記的相關規定,適度提高對社交電商違法經營行為的罰款額度,加強監管部門與社交電商平臺之間的監管協作。
關鍵詞:社交電商;法律問題;監管優化;制度完善
中圖分類號:F724.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266(2021)01-0105-08
電子商務自20世紀90年代誕生以來不斷發展,在諸多細分領域衍生出多種形態,如跨境電商、鄉村電商、社交電商等。其中,社交電商近年來獲得較快發展,由國家商務部、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布的《電子商務“十三五”發展規劃》明確提出鼓勵社交網絡發揮優勢,支持其開展電商業務。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遭受沖擊最為劇烈的是實體經濟領域[ 1 ]。在這種經濟背景下,線上經濟卻發展得更加迅速,社交電商甚至迎來了野蠻發展階段。
一、社交電商及其類型化
(一)社交電商及其特點
社交電商將網絡媒介和電商業務鏈接與融合起來,通過人際互動和優質內容來收獲流量、從事商品交易和提供服務。其核心機制可以概括為:以社交激發消費需求和助力營銷推廣,以信任提升購買效率和促使消費轉化。這一模式最初萌芽于2009年到2011年之間,以微商為代表,之后經歷了2012年到2018年之間的模式探索期,2019年進入成熟發展階段[ 2 ]。2019年,中國社交電商市場已經擁有5億用戶和近5 000萬從業者[ 3 ]。2020年,預計社交電商市場銷售規模將首次達到3萬億元,占整個在線零售交易市場的近三分之一[ 4 ]。
相較于傳統電商,社交電商具有顯著的特點及優勢。首先,就消費需求產生和購買模式來看,傳統電商模式下一般是用戶先產生需求,然后再進行購買,這個過程中消費者往往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對商品貨源信息進行對比甄別;而在社交電商模式下,用戶最初往往并無硬性消費需求,電商經營者借助社交網絡和人際傳播刺激用戶產生購買興趣,進而升級為消費行為。其次,就面向的用戶群體和消費黏性來看,傳統電商面向的消費群體更廣,用戶面對單向且陌生的信息很難產生信任,消費黏性較低;社交電商則更多通過熟人社群之間的口碑進行傳播,用戶對于來自熟人社群的意見傳達更容易產生信任,消費黏性較高。最后,站在平臺內商家的經營成本角度看,傳統電商平臺入駐門檻較高,平臺內的競價排名及主頁展示位等營銷推廣方式需要商家繳納高額費用;而社交電商的入駐門檻較低,商家依賴社群口碑傳播,在收獲較好營銷效果的同時無需繳納過高的廣告宣傳費用。總的來看,社交電商相較于傳統電商在拓寬用戶社交關系、提高消費轉化效率、創新營銷傳播推廣方式、提高社會整體效益等方面均實現了價值創新[ 5 ]。
(二)社交電商的經營模式類型
在演化發展中,社交電商市場逐漸形成四大板塊,出現了拼購、分銷、內容分享、社區團購四種類型:拼購型以拼多多、蘇寧拼購等為代表;會員分銷型以云集、貝店等為代表;內容分享型以小紅書、抖音電商等為代表,網絡關鍵意見領袖(KOL)帶貨直播是該類電商模式的一種典型展現;社區團購型以興盛優選、美家優享等為代表。
拼購型社交電商主要借助于價格優勢獲取流量,面向中小城市的價格敏感用戶,流通商品以生活用品為主。其典型特征是擁有強大的渠道分發能力,平臺首先聚集兩人及以上的用戶并鼓勵其分享互動組團,并在組團成功后享受更大優惠。平臺只需在最初引流過程中投入較多成本,此后更多依賴用戶主動分享拼團購物鏈接,實現傳播次數和訂單數的雙重裂變增長,這種類游戲的傳播方式極大地降低了平臺的獲客成本[ 6 ]。
會員分銷型社交電商的特點在于去中心化、整合供應鏈和挖掘用戶價值,平臺首先對采購、倉儲、物流、售后客服、信息技術(IT)系統等電商要素進行整合,為平臺內小b店主提供中后臺支持,小b店主則負責利用社交工具進行前端的用戶引流和關系維護,增進同用戶之間的社交信任[ 2 ]。
內容分享型社交電商是指平臺內商家以消費者為中心創作內容,通過社交網絡進行傳播以觸發消費者興趣并力爭轉化為購買行為的電商模式,網紅(KOL)帶貨直播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商家一方面通過知識產權(IP)打造和來源于生活體驗的優質創意內容,聚集具有共同興趣愛好和需求痛點的消費群體,激發彼此間的互動和對相關生活方式的認同感;另一方面邀請明星、網紅、KOL等達人駐場,發揮其粉絲效應,提高用戶黏性和購買轉化效率。
社區團購型社交電商具有立足社區、貼近用戶的特點,商品以生鮮為主,依靠社區實現運營。平臺招募和雇傭團長并為其提供供應鏈支持,團長負責基于鄰里關系的客戶運營、產品推薦和售后服務,部分社區團購平臺也會自主布局線下門店進行運營,用戶在線上下單后可在社區內自提商品或者由團長送貨上門。
二、社交電商相關法律關系
互聯網平臺是網絡空間的基本支撐點,平臺在加速信息流通、激活社會閑置資源的同時,也起到了助推生產方式變革和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 7 ]。互聯網平臺具有多種類型,其中電商平臺是指通過提供線上營業場所和交易撮合、信息發布等服務以促成交易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實踐中還存在平臺直接向消費者售賣商品和提供服務的情況,此時平臺也扮演著“平臺內經營者”的角色。
作為交易活動的參與方,社交電商平臺具有私法屬性,同交易活動的其他參與主體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交易主體之間的糾紛更多地通過合同予以解決。此時,電商業態的合同關系包括“三個基本合同關系+三種輔助性合同關系”。前者涵蓋平臺與平臺內經營者之間的服務合同、平臺與用戶之間的服務合同、平臺內經營者與用戶之間的買賣或服務合同;后者則包括平臺與支付機構、征信機構以及平臺內經營者與物流企業締結的合同[ 8 ]。
同時,由于電商活動中發生的各種爭議和權利沖突大多與平臺相關,作為網絡服務的提供者,平臺需要對發生于平臺內的交易活動承擔更多的監督管理責任。特別是面對海量化的線上交易,僅依靠監管部門的力量實施監管根本不可能實現,更多地需要依賴平臺解決。平臺一方面需要配合監管部門管理平臺內的交易內容和信息,另一方面也需要直接對平臺內發生的交易活動實施監管。
三、社交電商模式下的法律問題
在社交電商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背后也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新生事物的發展總是機遇與挑戰并存,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面對社交電商業態下出現的問題,我們不應刻意忽視和回避,而應在準確剖析和認識問題現狀及成因的基礎上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經營模式隱傳銷化
從初期萌芽到成長成熟,外界對社交電商的經營模式一直存在傳銷的質疑,實踐中出現了多起社交電商因涉嫌傳銷而遭到處罰的案例。2016年9月,湖北省咸寧市工商局對廣州云在指尖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做出處罰決定[ 9 ];2017年5月,浙江省工商部門對“云集”做出處罰決定①;2018年7月,“達人店”被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予以行政處罰[ 10 ];2019年3月,“花生日記”被廣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予以行政處罰②。
在“云集微店”案中,經營者入駐平臺之前需要交納365元的服務年費才能成為“店主”。“店主”可以繼續邀請他人入駐,邀請人數達160名可晉升為“導師”,團隊人數達1 000名可成為“合伙人”。團隊發展一名“店主”,“導師”和其上線“合伙人”便可從其交納的服務費中抽取提成。在“花生日記”案中,平臺規定,普通會員僅有優惠券獲取資格,超級會員和運營商才可以發展新會員并獲取傭金,普通會員在交納99元升級費后可成為超級會員。運營商由平臺建立的分公司管理,通過發展大量下級超級會員來計提傭金收入;超級會員可不受限制地邀請其他人加入超級會員并成為其下級。這一過程不斷重復,在運營商與超級會員、超級會員與超級會員之間不斷形成新的上下級關系,最終形成以平臺為統領、以運營商為塔尖、超級會員不斷縱深發展的金字塔型結構。上述社交電商平臺經營模式與《禁止傳銷條例》中關于“拉人頭”“入會費”和“團隊計酬”的行為模式特征十分類似③,存在傳銷嫌疑。
(二)虛假廣告泛濫
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虛假廣告始終是令消費者頭疼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對虛假廣告的內涵和廣告發布者的責任有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更是規定了虛假廣告罪。但即便如此,社交電商領域的虛假廣告問題仍然十分突出。
虛假廣告的本質是商家在經營活動中以廣告的形式傳達不符合實際狀況的虛假信息從而引發消費者誤解,其中可能是商品或服務的品質與功能虛假,也可能是價格虛假,還可能是相關資質的證明材料虛假。作為一種不正當的競爭手段,虛假廣告背后隱含的是平臺內經營者對商品銷量的極度渴望,這種行為對市場的公平性和真實性造成破壞,容易給消費者帶來困惑,打擊消費者信任感,不利于整個社交電商行業和市場的發展。如在時下火熱的網紅(KOL)帶貨直播領域,由于平臺在內容審核和監管機制上的不健全,夸大、虛假宣傳問題非常突出。中國消費者協會2020年3月發布的《直播電商購物消費者滿意度在線調查報告》顯示,“夸大其詞”和“虛假宣傳”是消費者吐槽最多的問題,在消費者對直播購物全流程不同環節的評價中,宣傳環節的滿意度排名最低[ 11 ]。
(三)售后服務機制不健全
售后維權困難同樣是社交電商領域的突出問題。網經社2020年3月發布的《2019年度中國社交電商消費投訴數據與典型案例報告》顯示,多數社交平臺在售后服務領域收到較多的消費者投訴。如有消費者在云集平臺購買了心率手環和藍牙耳機,在收到貨物后按照平臺規定申請開具發票,但在超出平臺承諾的3個工作日期限后,平臺仍顯示“待開票”狀態;又有消費者在斑馬會員平臺購買價值399元商品,使用過程中發現商品質量同宣傳嚴重不符,反饋后商家聲稱須付80元費用才能更換新品;也有消費者在萌推平臺購買商品,超出最晚發貨時間仍未發貨,后商家虛假發貨,消費者與商家協商無果。此外,還存在霸王條款、保證金不退還、退款困難等問題[ 12 ]。
由于電子商務采用線上交易的形式,消費者只能從商家描述及圖片和短視頻展示中了解商品信息,無法如同線下交易一般進行商品甄別和挑選,因此在交易過程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特別是在社交電商領域,法律和監管機制尚不完善,再加上利用粉絲效應和熟人之間的信任進行商品售賣,經營者違法經營和消費者沖動消費的概率較傳統電子商務更甚,而且部分社交電商平臺不通過第三方支付收款,而是直接借助微信、支付寶,這就使得侵權違法行為更容易發生,后續維權更加困難,打擊了消費者本就脆弱的信任感。
(四)用戶個人信息保護不到位
個人信息已經成為數字經濟時代一項重要的資源,無論是在個人、企業還是國家層面均受到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簡稱《民法典》)明確界定了個人信息的概念和范圍,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形式記錄,能夠單獨或者同其他信息相結合而識別出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等④,其中具有較強私密性的信息屬于隱私范疇,被稱為“私密信息”⑤。社交電商的本質是發揮個人影響力并利用人際關系網絡催動購買行為的產生和拉動更多人參與,核心是以較低的成本獲取較大的流量,同時不斷裂變形成新的流量入口,在這個過程中便產生了個人信息的交換與流動。以社交電商中經常出現的砍價鏈接為例,一般來說,當用戶打開分享到微信聊天框或者朋友圈中的商品鏈接時,往往會彈出“授權登錄”對話框,需要用戶輸入手機號碼等個人信息或者通過社交賬號注冊登陸才能完成砍價,此時社交電商平臺便完成了對用戶個人信息的采集。用戶在進入社交電商平臺之后的購物環節,同樣會產生大量的個人信息流動,如用戶需要填寫住址供物流快遞配送。對于上述環節的個人信息采集,用戶最初或許并不在意,但如果平臺監管不嚴,就可能出現用戶個人信息泄露的情況。目前社交電商平臺中個人信息被泄露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種:第一,平臺在采集個人信息后將信息非法出售;第二,平臺內部員工利用職務之便盜賣個人信息;第三,網絡黑客通過“撞庫”⑥獲取平臺存儲的用戶個人信息;第四,不法分子直接利用平臺進行個人信息相關交易。近年來,社交電商平臺用戶信息泄露和用戶因為信息泄露遭遇電信詐騙的事件頻繁發生。2017年,小紅書平臺內的用戶購物信息遭到泄露,多名用戶遭遇電信詐騙后受騙;2019年,貝貝網被投訴和通報未經用戶同意收集個人信息,后平臺收集的個人信息遭大量泄露;同年,云集平臺用戶信息被泄露,部分消費者受騙。
4.督促社交電商平臺履行個人信息保護義務
近年來國家層面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規范日益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即將出臺。就平臺層面來說,《電子商務法》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條雖然就電商平臺的個人信息保護義務做出了規定,但在具體實踐落地時仍然失之籠統。本文將社交電商平臺直接參與的個人信息流通概括為事前、事中、事后三大環節,平臺在每個環節具有不同的義務。
所謂事前環節,即在平臺對個人信息進行采集和利用之前。此時平臺應履行規則制定和明示告知的義務,現實中平臺多采用制定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的方式履行這兩項義務。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平臺規則更多體現平臺方意志,可能存在平臺過多削減用戶權利和增加用戶義務的情況,需要平臺在制定規則過程中更多聽取用戶意見,同時采取多種明顯形式展示和提醒用戶以確保其對平臺采集與利用其個人信息知情權的實現。
所謂事中環節,即平臺采集和利用個人信息的過程本身。此時平臺應履行最少必要和正當利用的義務,當前電商平臺對個人信息的采集過程呈現出多樣、過量和任意的特點,極易對信息主體造成損害,平臺對個人信息的采集應遵循最少必要的原則,對與平臺開展經營活動無關的信息不予采集;在合法采集后的信息利用環節,應限制在事先名示告知的明確和特定使用范圍內,不得超出。
所謂的事后環節,是指信息存儲過程。平臺應建立嚴格的內部人事管理和信息管理機制,利用、改善和提高防火墻等信息技術,防止內鬼和黑客的信息竊取行為,一旦出現信息泄露,必須及時向監管部門報告,通告信息主體并對其履行損害賠償義務。特別是對社交電商平臺內部人員直接利用平臺進行個人信息交易的行為,社交電商平臺應履行審查監管義務,建立關鍵詞過濾機制和其他技術手段進行主動審查,也可借助“通知—刪除”規則動員多方主體的力量進行審查。
(二)外部監管路徑的優化與完善
1.出臺具備更高效力的社交電商法規
優化對社交電商的監管需要完善相應的法律規范。隨著電商行業的不斷發展,電子商務已經從單一的綜合電商衍生出跨境電商、社交電商、生鮮電商等多種新形態。《電子商務法》中部分規定過于籠統,缺乏足夠的針對性。特別針對社交電商領域,商務部2018年7月發布《社交電商經營規范(征求意見稿)》,從社交電商活動的參與主體、基本原則和要求、電子支付、快遞物流以及消費者權益保障幾個方面對社交電商領域的市場經營活動做出了具體規定。但截至2020年8月,正式規范仍未出臺。與社交電商2018年和2019年分別達到255.8%和110.%的行業規模年增速相比[ 14 ],規范的制定和出臺遠遠滯后于社交電商行業的發展。而且,即使在經營規范正式出臺后,由于其屬于行業標準性質,更多依賴于行業成員的自覺遵守而沒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在未來具體的落地實踐中效果仍可能有限。因此,監管部門一方面應加快推進《社交電商經營規范》正式出臺,另一方面也應研究制定更高效力層級和能夠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社交電商行業法律規范,以便利和強化對社交電商經營活動的監管。
2.完善社交電商市場主體登記的相關規定
無論是對社交電商的經營主體抑或是整個社交電商市場來說,市場主體登記制度均具有重要意義。依法辦理市場主體登記有助于確認經營者主體資格、捍衛其市場聲譽和切實保障其享受國家相關政策優惠[ 15 ]。同時,通過市場主體登記管理,能夠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必要信息,保證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落實,間接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優化社交電商市場結構,維護社交電商市場秩序。關于社交電商市場主體登記的相關規定見于《網絡交易管理辦法》《電子商務法》和《市場監管總局關于做好電子商務經營者登記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登記意見》)等法律和規范性文件中。《網絡交易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經營者在開展線上商品交易及服務時應辦理工商登記。《電子商務法》第十條列舉了三種無需辦理登記的具體情形⑧。《登記意見》對前述規定進一步細化,允許申請注冊為個體工商戶的電商經營者將網絡經營場所登記為其經營場所。在具體實踐中,相關規定的細節還需進一步明確。就申請注冊登記的方式來說,考慮到社交電商經營活動的特點,監管部門應開設渠道允許申請人在線提交申請并在線受理和審查,對符合注冊登記條件的,應為其頒發電子營業執照并進行線上公示和電子檔案備份,申請人可以同時申領紙質版營業執照。
3.適度提高對社交電商違法經營行為的罰款額度
作為行政處罰的一種,罰款對違法行為的行政相對人起到了較好的警示、懲戒和防止其再犯的作用。對電子商務領域的違法行為,《電子商務法》同樣規定了相應的行政處罰手段。《電子商務法》第七十四至八十八條對電商平臺經營者和平臺內經營者的違法行為分別設置了最高200萬元和50萬元的罰款處罰額度,但問題是,無論是對社交電商平臺經營者抑或是對平臺內經營者來說,罰款最高額度均顯得過低。特別是對社交電商平臺經營者來說,以拼多多和云集為例,2019年兩平臺全年分別實現營收301.4億元[ 16 ]和116.72億元[ 17 ]。相較于此,200萬的最高處罰額度無法對平臺起到足夠的打擊和震懾作用,而過低的違法成本很可能引發再犯風險,產生更大的社會危害,因此,加大對社交電商經營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和提高罰款額度就很有必要。但是,如果毫無限制地加大處罰力度和提高罰款額度,可能又會打擊社交電商經營者活動的積極性,阻礙社交電商行業的長遠發展,同樣具有社會危害性。因此,可以采用比例罰款制度,以比例的形式對罰款金額予以規定,如規定對社交電商平臺和平臺內經營者的最高罰款限額為上年度營收的20%。比例罰款制度的優勢在于賦予監管部門更多的執法靈活性,監管部門可以根據社交電商經營者的具體經營情況合理確定罰款數額,既可避免因罰款額度過低不能對社交電商經營者起到有效的震懾作用,也可避免因罰款額度過高阻礙和限制社交電商行業的發展。
4.加強同社交電商平臺之間的監管協作
由于社交電商領域的交易活動具有模式多樣、交易頻繁、體量龐大的特點,同時具有傳統電商活動交易跨地域性的特點,單純依靠監管部門的力量可能導致管轄的分散和監管效率的低下,因此改革傳統的監管思路,推進線上監管和加強同社交電商平臺的監管協作就很有必要。第一,平臺總部及服務器所在地監管部門在平臺交易中心設置機構并派駐人員處理違法案件,監管部門在接到對違法行為的舉報投訴后直接調用平臺內的商家和商品服務信息進行判斷與處理,其他地區的監管部門在接到舉報投訴后也可直接向平臺所在地的監管部門發出執法監管的協作請求,并由社交電商平臺協助實施;[ 18 ]第二,監管部門指導社交電商平臺建立違法交易審查系統和線上快速維權機制,當平臺收到侵權投訴或者發現可能存在侵權糾紛時,先由審查系統對侵權與否做出初步判斷,然后再聯系監管部門、調解機構和司法機關進行處理,為防止惡意投訴,可以要求侵權行為的投訴人提供一定的擔保,對簡單案件可直接以平臺審查系統的判斷結果作為處理依據;第三,監管部門同社交電商平臺采取專項行動,通過綜合判斷侵權行為的高發領域有針對性地確定重點監管對象,合作制定專門預防方案以應對突發情況的發生,避免執法遲延,并及時公布侵權違法行為的處理結果。
注釋:
①參見浙江省杭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濱江)市場監督管理局杭高新(濱)市監罰處字[2017]2101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②參見廣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穗工商處字[2019]13號行政處罰決定書。
③《禁止傳銷條例》第七條規定:“下列行為,屬于傳銷行為:(一)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對發展的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包括物質獎勵和其他經濟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費用或者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費用,取得加入或者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④《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條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等。個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適用有關隱私權的規定;沒有規定的,適用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
⑤《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條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刺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
⑥“撞庫”是黑客通過收集互聯網已泄露的用戶和密碼信息,生成對應的字典表,嘗試批量登陸其他網站后,得到一系列可以登陸的用戶。很多用戶在不同網站使用的是相同的賬號密碼,黑客通過獲取用戶在A網站的賬戶嘗試登錄B網站。
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電子商務平臺知識產權民事案件的指導意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因情況緊急,電子商務平臺經營者不立即恢復商品鏈接、通知人不立即撤回通知或者停止發送通知等行為將會使其合法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平臺內經營者可以依據前款所述法律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采取保全措施。”
⑧《電子商務法》第十條:“電子商務經營者應當依法辦理市場主體登記。但是,個人銷售自產農副產品、家庭手工業產品,個人利用自己的技能從事依法無須取得許可的便民勞務活動和零星小額交易活動,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不需要進行登記的除外。”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2020年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初步核算結果[EB/OL].(2020-04-28)[2020-09-10].http://www. 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602.html.
[2]億歐智庫.2019中國社交電商生態解讀研究報告[R/OL].(2019-05-15)[2020-10-18].https://www.iyiou.com/intelli? gence/report629.html.
[3]中國互聯網協會微商工作組,創奇社交電商研究中心.2019中國社交電商行業發展報告[R/OL].(2019-07-11).[2020- 10- 10].https://www.isc.org.cn/editor/attached/fi le/20190711/20190711170456_25286.pdf.
[4]中商產業研究院.2018—2023年互聯網+社交網絡市場前景研究報告[R].2018.
[5]億邦動力.2019中國社交電商白皮書[R/OL].(2019-09-26)[2020-10-20].http://www.199it.com/archives/950433.html.
[6]王玲.中國社交電商行業發展現狀分析[J].互聯網經濟,2019(Z2):80-89.
[7]周漢華.論互聯網法[J].網絡信息法學研究,2017(1):3-30,385.
[8]楊立新.網絡交易法律關系構造[J].中國社會科學,2016(2):114-137,206-207.
[9]舒仁慶.云在指尖公司網絡傳銷案被罰150萬元[EB/OL].(2017-09-23)[2020-09-17].www.100ec.cn/detail--64169 93.html.
[10]馬炎.浙江公布傳銷典型案例“達人店”涉傳銷被罰400萬[EB/OL].(2018-08-09)[2020-09-18].http://zjnews.chi? na.com.cn/yuanchuan/2018-08-09/143531.html.
[11]中國消費者協會.直播電商購物消費者滿意度在線調查報告[R/OL].(2020-04-02)[2020-09-17].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99987.
[12]電子商務研究中心.2019年度中國社交電商消費投訴數據與典型案例報告[R/OL].(2020-07-05)[2020-09-19]. https://t.cj.sina.com.cn/articles/view/6132378868/16d84ac f401900tujp?from=tech.
[13]朱晶晶.浙江杭州跨境電商大數據平臺累計完成近15 000家企業信用評級[N].杭州日報,2018-06-21(A17).
[14]艾瑞咨詢.中國社交電商行業研究(2019年)[R/OL].(2020-07-11)[2020-09-18].http://report.iresearch.cn/re? port_pdf.aspx?id=3402.
[15]蔡立東.電子商務經營者依法辦理市場主體登記的長遠意義[N].光明日報,2019-03-23(11).
[16]王言.拼多多2019年營收超300億,交易額破萬億[EB/ OL].(2020-03-11)[2020-09-18].https://tfcaijing.com/ar? ticle/page/4d636f4a5065717564552f37644453317a666b36 55513d3d.
[17]云集發布2019年財報:全年GMV增至352億元凈盈利440萬元[EB/OL].(2020-03-24)[2020-09-19].https:// tech.sina.com.cn/roll/2020- 03- 24/doc- iimxxsth1487267. shtml.
[18]李娜,余翔.互聯網電子商務知識產權協同執法機制建構初探[J].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66-70.
責任編輯:方程
The Legal Issues and Regulatory Optimization about the Social E-commerce
LIANG Dong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With the traditional e-commerce encountered development bottlenecks,as a derivative form of e-commerce economic model,social e-commerce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e-commerce can be broadly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namely,buy-to-share social e-commerce,member distribution-based social e-commerce,content-sharing social e-commerce and community group-purchased social e-commerce. While the social e-commerce platform has the attributes of private law and is in an equal leg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subjects in the platform,it also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assume mor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to other subjects of the activities within the platform.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development,social e-commerce is also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including business model hidden marketing,the proliferation of false advertising,the not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mechanism,and the not-in-position protection of us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face of these problems,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two regulatory path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latform:inside the platform,we should raise the threshold for businesses to enter the platform,perfect the two- way supervision mechanism between operators and consumers,construct a credit evaluation system for participants in social activities,and urge the social e-commerce platform to fulfill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personal information;and outside the platform,we should formulate more effective regulations,increase the amount of punishment,and strengthen regulatory collaboration between regulators and social e-commerce platforms.
Key words:social e-commerce;legal issues;regulatory optimization;system impr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