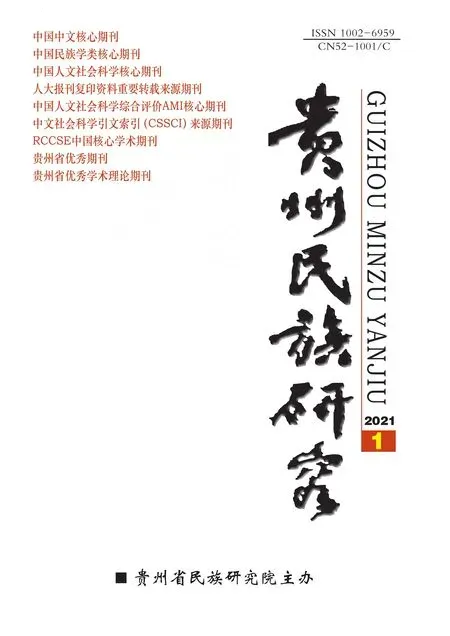生態式發展理念下傳統古鎮建設
——以昆明官渡古鎮為例
梁苑慧
(云南大學 歷史與檔案學院,云南·昆明 650031)
官渡古鎮位于昆明城市腹地的螺峰村與尚義村區域,地處滇池北岸、寶象河下游,它不僅有展示早期人類生活蹤跡的“貝丘”文化,也有唐宋以來的古渡口,還擁有眾多民居與宗教的建筑遺存。2016年12月,云南省人民政府發布了《昆明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2014—2020)》 (以下簡稱《規劃》),在《規劃》中將官渡古鎮劃定為歷史地段。然而在城市發展中,它又面臨著一種困境。2019年5月,中央發布《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 提出了“重塑新型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的具體要求。當今,城市與鄉村要協同融合發展,就涉及到像昆明官渡古鎮這類在不同歷史文化上各種民族文化共同開發的地區,應該如何與城市協同發展?我們今天提出城鄉融合,顯然得考慮它的歷史、自然背景和文化生態變遷過程。遺憾的是,能夠從歷史和文化生態過程這兩個視角去規劃生態式發展的研究項目和成果相對偏少,不足以支撐時代發展要求。縱觀此前對官渡古鎮的研究,其歷史分期是值得商榷的,它的文化生態變遷軌跡也需要隨之調整。為了正本清源,筆者認為對不同時期的各種誤判、誤解加以解釋、說明、匡正和補救,才能為今天官渡古鎮的下一步開發、利用奠定堅實的歷史文化基礎與滿足資料儲備的需要,才能為傳統古鎮生態式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路徑選擇。于此,我們將就官渡古鎮的歷史積淀或獨特的文化生態過程,展開嘗試性的分析討論。
一、狩獵采集時代
地質學家認為,6500萬年時地球進入了新生代,新生代所產生的海洋陸地結構得到了大致定型,到更新世時,地球的地質地貌結構已經與當代所見到的大體相似。換句話說,今天所見的官渡古鎮地區的地質地貌結構,其生態背景的源頭確定在自然環境原生形態的這一歷史時期。
與當代的滇池相比,新生代后期的遠古滇池要大得多、深得多。在其后的3000多萬年的一系列地質變遷中,古滇池才最終定型為與當代相似的面貌,即形成了典型的高原外流型淡水湖泊,并發育了高原濕地生態系統。根據黃展岳和趙學謙1958 年1月在滇池東岸,即官渡古鎮區域的考古調查結果顯示,“滇池東岸是一片平壩,古文化遺址很多,這些遺址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即普遍存在著大量的螺螄殼堆積層和一種為數眾多的手制泥質紅陶器,螺螄殼成白色,一般長7~8厘米,在他們的遺址中堆積如小山,當地群眾往往稱之為螺螄山、螺髻山或螺螄堆。官渡、石子河遺址的堆積長達里許,高出地面2~3米,地面下深也在2~3米以下,螺殼層堆積中一般夾雜少量灰土,或純屬螺殼堆積,其中包含著大量的陶片和少數的石器骨器等。每個螺殼尾部都有一個敲通的小洞,顯然這是被食用過的痕跡。”[1](P173)據此描述,新石器時代在這兒定居的遠古人類是以螺螄為主要食物來源。采食后,將其外殼定點拋棄堆放,天長日久,這些有規律被拋棄的螺殼,就形成了大量的堆砌物。對于這樣的情況,考古學家稱之為“貝丘”文化,或者是“貝冢”文化。當代官渡古鎮所處的區位恰好就是“貝冢”文化的密集分布帶,但形成密集分布的原因絕對不是今人描述的“生活在水邊的先民將螺螄取肉后,螺螄殼就地扔除后散落岸邊”,也不是“由于鎮邊的寶象河水常年泛濫,自東北向西南沖刷入湖,而滇池常年刮南風,湖浪由西南向東北奔涌,河水與湖水形成上沖下頂之勢,螺殼等水生動物遺骸遂匯聚于此,與泥沙堆疊而成大小不等的貝丘。”[2](P10)因為它忽略了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方國瑜先生在《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中對滇池水域情況的考證:“從元初開始,特別是大德五年(1305年) ‘開中慶路昆陽海口’亦決滇池水,自后屢經興工挖低海口河,滇池水面縮小,四周露出良田,故官渡原為渡船處。”[3](P1117)據方氏所言,在宋末元初之際,今天官渡古鎮的所處位置,實際上還處于一個大部分為水域,僅有少量島嶼初露水面的濱水地帶。
在湖水環繞的官渡島嶼要采集螺螄,或是采食水生動植物必須要在湖灘地區才能完成。遠古時代的氐羌民族具有極高的智慧,他們根據經驗積累和教訓的規避,將吃剩下的螺螄殼有規律地集中堆放,以免干擾活著的軟體動物的正常生存,其目的是為活著的其他軟體動物騰出生存空間和環境,從而使得人和水生動物的協同共生關系能夠獲得可持續的延伸。一些作者把它想象成是一個純粹自然行為造成的堆積,違反了時間進程的基本規則。官渡古鎮周邊貝丘的存在與發掘,讓我們今天看到了“貝丘”文化遺址的某些標志性文化事實。更何況在考古發掘中還發現螺螄殼尾部都敲有小洞,將小洞與活蝸牛解剖的研究相對接,被敲小洞的位置恰好是蝸牛韌帶和蝸牛殼粘連的位置,如果不敲這樣的小洞,蝸牛肉很難從殼中取出。我們在這里至少可以得出3個結論:一是當時的遠古居民是生食軟體動物的;二是他們在經驗上已經掌握解剖蝸牛身體結構的技術;三是他們的解剖方式已經獲得了文化的認同,而得以代代相傳。所以即便是新石器時代的遠古人類,他們其實也擁有經驗積累和知識、技術,只不過此前沒有被發現和證實而已。此外,明英宗天順六年(1462年),“欽差鎮守太監羅公珪大為興復(妙湛寺)”[4]并增建金剛塔。建造金剛塔后,“由于地下水下降,金剛塔的基座逐漸下沉,加上新修的路面抬高,致使金剛塔的底部略低于路面1.6米。”[5](P318-319)2001年4月,為了改變金剛塔繼續沉降的狀況,2002年7月將金剛塔整體頂升2.6米。這恰恰是1948年云南文物訓練班在官渡進行發掘實習的實證:“發現在螺螄殼堆積層下,發現了質地堅韌,黏稠的黑膏泥層,以至于洛陽鏟都無法探穿。”[1](P173)這些由1000多萬年的湖相沉積而形成的泥炭層,透水、透氣性能極差,在這樣的土層上進行建設工作,其承重能力十分有限。當代的地面建筑如果建得過高,過重都會存在傾斜坍塌的風險,從而造成難以預料的損失。
就這一考慮,在從事地表資源利用的今天,需要采取規避的原則。當下的城市發展對此考慮不足,對官渡古鎮區域在遠古時代的歷史積淀和遠古文化生態,以及狩獵采集時代的文化生態過程缺乏了解。這對于古鎮保護和開發、利用乃至建設,顯然是需要及時加以匡正和補助。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具體到官渡古鎮今天的建設而言,一方面,必須對這些貝丘文化的遺址加以保護,劃定保護區。讓今天的人們可以一睹遠古時代的文化生態風貌,知道遠古人類也有聰明才智,既有教育意義,對旅游開發也有厚重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在規劃利用土地資源,展開地面建筑的建設、利用時,對其存在的隱患、地段,也必須慎重考慮,規避它的薄弱環節,以免觸動了它的脆弱區,給以后的建設造成危害。這兩個方面都兼顧了,當代的生態式建設才算落到了實處。
二、早期原始農業時代
官渡所處地區的原始農業發端于何時,終結于何時,由于相關的史料記載和考古發掘所獲資料較為零散、殘缺,以至于時至今日學界還無法做出定論和達成共識。筆者考慮到《史記》 《漢書》 《后漢書》和《華陽國志》都提及滇池莊蹻入滇的故事。“變服,從其俗,以長之”[6](P2291)證明春秋戰國時期在滇池周邊地帶,已經有了小型政權,標志著他們已經進入了原始農業時代。原始農業在這一地區終結于何時?以樊綽的《蠻書》記載為依據,此時出現了統一云南地區的地方政權南詔,要建立這樣政權,沒有固定農耕文化的支撐,是絕對辦不到的。因而有理由認定這一地區原始耕作終結的下限應該在隋唐之際。
對官渡地區的原始農業文化生態而言,《史記》 除了提及當地小邦林立以外,還明確提及“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6](P2291)。魋結,是古氐羌族群為適應于水域生活環境的產物。只有將頭發扎成魋結,無論是撿田螺,捕魚蝦,或者從事水生植物的培育,都會非常方便。魋結之俗是文化適應環境的產物,憑借水生作物產品,支撐一個龐大政權是不夠的。因為這些產品不耐儲存,難以運輸,也不容易平均分享,而這正是當地“靡莫之屬以什數”小國林立的經濟基礎原因之所在。《史記》上又記載,秦朝統一全國后,曾經大力開辟五尺道,希望達到通滇的目的,這也證明了包括官渡在內的滇池地區,已經有了較大的財富積累和糧食儲備,有必要納入郡縣管理。值得一提的是,來自中原地區的早期農業文化與技術,在當地得到了高效的吸收消化和創新利用。創新利用的絕好例證,就是以晉寧石寨山為代表,擁有“滇王之印”印章的古滇國考古發掘。莊蹻此前把漢族地區種粟的文化與技術帶到滇池地區,當地的古氐羌民族掌握了山地種粟技術。因而,石寨山能夠發展為當地的大邦,為其后漢武帝開辟西南夷,降服滇國,設置益州奠定了基礎。
對上述史實的綜合考量,有3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在當時的滇池周邊地區并存著兩套農業文化,一套是在水域環境中實行的水域狩獵采集文化,另一套則是在山區實行以粟為代表的原始種植農業;其二是滇池地區已經成功地接受了來自中央的文化和農耕技術的影響,農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其三是原始農業對不同的生態背景環境的后續影響(刀耕火種) 有其特點又有區別,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個問題學界早有關注,且研究極為深入,尹紹亭先生和裴盛基先生的相關研究可做代表,在此無需贅言。對于官渡所處的濱水小島地區而言,也有它的原始農業,主要依靠種植兩棲性的水生作物。這樣的濱水區域不能用犁耕作,也不需要除草,只要將頭年的殘株拔掉,再根據水的深淺,把塊根和種子踩入淤泥中,就可以完成播種。但播種的區段必須長期觀察,選擇雜草不容易生長的區域。我們假設,這個區段就是狩獵采集文化時期丟棄的“貝丘”,因為“貝丘”下面是厚厚的螺殼層和泥炭層,只要人類有意識地播種,將種子踩入螺螄殼間的夾縫中,種子就能順利地生長成為農作物。要深入展開這方面的考古研究,目前困難很大,但在官渡地區的水域環境中曾經存在過水生型原始農業的事實卻不容置疑。其后歷史進程就進入了南北朝時期,當地的氐羌民族乘勢而起,進一步發展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的原始農業。文獻中稱為“爨”,其傳世至今的爨龍顏碑和爨寶子碑的碑文就是有力的例證。這時的氐羌民族政權結構規模已經很大了,原始農業發展也進入了鼎盛時代。爨蠻各部選擇到山區去發展刀耕火種的旱地農業,將政權建造在位于山區的曲靖陸良也是基于無法控制水域的水位、水流以及水產作物有限等原因。
總的說來,這一階段對于今天的古鎮保護而言,喜憂參半。所喜之處在于,本階段原始農業對生態的干擾非常有限,只需按照前一階段的保護措施,作出應對就夠了。所憂之處在于水域原始農業不僅歷史文獻留下的記載極為匱乏,而且尋找考古遺存也極為艱難。另外,要傳承這一時段的文化生態,恢復這一時段的文化生態原貌,弘揚其文化,實現去粗取精,建立相應合適的文物陳列機構難度和挑戰極大。好在滇池周邊濕地生產系統的物種構成,古今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當時種植過的植物即便野化了,在滇池周邊還可能找到活態的物種植株,他們到底種過哪些植物,通過生物學方面的鑒定和分析還是可以得而知之。在這一基礎之上,要建構盡可能符合屬于原始農業面貌的陳列設施,而以上的分析和探討,在這一方面恰好可以提供有力的參考數據。
三、繁榮的原始農業時代
官渡古鎮所在的滇池地區,其繁榮時代于何時開始經營,又終結于何時同樣沒有定論。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出現了唐、宋兩個強大的中央集權行政機構。唐代依然是以粟、麥等作物為主,到了宋代以后,精耕細作的稻田文化得以定型。由于滇池地區乃至整個云南全境,在當時社會背景和技術條件下,難以做到大規模的旱地開辟。不過,相繼興起的南詔、大理地方政權,標志著其進入高度繁榮的原始農業時代,因而這一歷史時期的上限應發端于隋代史萬歲接管滇池一帶,下限應延續到元代賽典赤治理滇池之際為止。
在原始農業的種植當中,在山區發展空間最大的是粟、麥類作物,山區原始農業發展受到地理環境和種植技術的節制,很難實現連片種植,平壩、盆地就發展成為云南地區的糧食生產重地,因而,巍山、下關一線成為了云南新的政治和經濟中心。而滇池地區,由于地理位置優越,成為了這兩個政權的東都和行宮所在地。唐永泰元年(765年),閣羅鳳命其長子鳳迦異于昆川(州) 置拓東城,“王都羊苴咩城(大理城),別都鄯闡府”[9](P6267)。官渡古鎮在其中扮演了獨特的文化生態角色,使得官渡古鎮的原始農業另有一番景象表達:一方面傳統的水域原始狩獵采集農業得到了較大程度的復興,不僅營造出美好的濱水景觀也滿足了王公貴族的娛樂享受;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從官渡古鎮通向滇池西側的水上航路也有較快的發展,作為娛樂場所的配套設施,出現了官渡古鎮最早的大型碼頭“蝸洞”。鄯闡府對南詔而言,有著重要的軍事政治地位作用,官宦們從大理到別都鄯闡府,除了陸路之外,還須從西山碧雞關的高峣村乘船走水路到東岸的“蝸洞”。當時滇池水位較高,為了方便從碧雞關至“蝸洞”,經石虎關進入拓東城,考慮到船舶安全和官宦們方便,在現在官渡古鎮境內的高地上修了一個供皇家專用的渡口。
雖然目前無法考證出渡口的具體位置,但在古鎮區域范圍內還是留下了至今可以實地考察的唐文化遺址,成為了當代旅游的標志性人文景觀。查閱這一時期文獻記載,對古鎮的文化生態描述并不充分和詳實,但有很多信息只要做進一步的探究就會發現具有不少歷史價值的蛛絲馬跡。舉例來說:“蝸洞”名稱的來源,就是因為在官渡古鎮地區有大量遠古時代留下的蝸牛殼堆積,成為容易識別的地理標志而得名。內地唐宋交接之際,云南地區也由大理段氏重新統一,并建立了大理政權。宋元豐三年(1080年),“段思平封開國元勛高方泰為岳侯,封地于鄯闡(今昆明),子孫世襲。至高智時,在‘蝸洞’筑城郭,置府第,建法定禪寺,倡興佛教。”[8](P4)官渡古鎮地區的人文景觀得到進一步的弘揚和光大。忽必烈接管云南后,此前作為東都的拓東城及其周邊的官渡一帶也作為東部重鎮而得以延續和發展。這一時期保留在地面的重要建筑,傳承至今的妙湛寺碑文提供了相應的記載。元統三年(1335年),普祥撰書的《創建妙湛寺碑》載:“滇城之翼隅二十里有郭曰蝸洞……乃古拓東演習高侯之苗裔生世攸乂之所也。”[9]
綜上所述,本時段官渡古鎮一帶的文化生態特色在于作為皇家的行宮所在地而存在,其經濟雖遜色于繁榮的大理,宗教性和玩賞性的景色卻反超過它。與此同時,滇池的水位由于當時的經濟活動并沒有直接涉及到海口開鑿問題,導致官渡地區直到元代初年都還處于煙波浩淼的水域環境,延續了早期水域農業文化。這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示,在涉及到唐宋兩代的文物古籍保護和當代利用時,我們不建議將農田等農耕元素配置在寺院的周邊,而應該盡可能恢復仿生的園林置景和植物配置,才有助于當代的旅游者更好地領悟唐宋時代官渡地區的文化生態原貌。而且,對于滇池水位下降才出現的河道、農田、渡口也應當作出重新考量和探討。之前有不少學者用元代以后的文化生態景觀去猜度唐宋時代的官渡古鎮的文化生態景觀,這顯然是個失誤。比如元代以后官渡的位置以及渡船的形式,特別是寶象河的出現,都理解為唐宋時代的史實,這樣的理解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在唐代,這些部分都還處在滇池的水下,不為人們所見。當時的渡口,在蝸洞的地理位置要比在后代官渡古鎮的位置要高得多,渡口的形式也是用劃船或帆船來靠岸,而不是像后世那樣拉纖過河,如果不注意這樣的時代差異,憑借后世的景觀去復原唐宋時代的歷史景觀,去構建相應的旅游目的地,我們的觀賞對象肯定會違反歷史的真相,誤導人們的認識,這些是當前旅游開發和城鄉協同融合發展值得高度警惕的地方。
四、固定農耕時期
官渡地區正式進入固定農耕時期要比內地晚得多,其間的關鍵原因在于,在云南這樣的高原山區,僅靠人力營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難度很大。元代初年,在云南正式設立行省后,文化生態背景情況大不一樣。由于元朝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匯集了眾多的民族和社會力量,賽典赤組織了大量人力、物力實施拓寬、拓深滇池海口的行動。工程完成后,水位隨之急劇下降,大面積的湖底由此變成了陸地,大規模的稻作農耕在滇池周邊形成。這一深刻的歷史文化變遷,使官渡地區的農耕經濟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另外,就筆者的淺見,這一時期應該起源于13世紀中后期,結束于20世紀初。
至元十二年(1275年),“(鄯闡府) 改善州,領縣二曰昆明、官渡”[10(P13)],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 “復改州為中慶路,治昆明,尋并官渡入焉”[10](P13)。官渡古鎮先后載入史冊既表明它成為了行政區域,也表明它從皇家的私人禁地變成了民間公地。而此時的官渡也迎來了文化生態環境發生巨大轉變的時機。時任云南平章政事的賽典赤因“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廢棄,正途雍底”[11]而對滇池進行了大規模的治理。據《元史》記載:“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之間,環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眾源所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其水,得壤地萬余傾,皆為良田。”[12](P1458)這次疏浚工程,使滇池水位急劇下降,周邊區域從“滄海”變成了“桑田”。水位的下降,我們還可以推測出,此時官渡的渡口不止一個,畢竟它要滿足王室貴族的登陸需要,還要成為民間公眾與貨物的集散地。
此外,普祥撰書的《創建妙湛寺碑》 (官渡古鎮) 載:“滇城之翼隅二十里有郭曰蝸洞,西北瞰碧雞金馬,煙波秀麗,云水杳靄;東南瞻瑯藏寶江,環注諸滇,林壑岈洼,田疇豐穰,宅民素樸。尤篤于浮圖氏,樂乎漁樵,藝植茂林修竹之趣。鄉士大夫游賞,纜船于渡頭,吟嘯自若,陶陶而忘返,命之曰官渡。故有停舟之賦,乃古拓東演習高侯之苗裔生世攸乂之所也。”我們對碑文的解讀可以作出合乎科學的解釋:其一,當時的官渡地區周邊依然還是水域,雖然建了“攸乂之所”,但是它依然處在被水環繞的濕地生態環境中。元代的官渡位于高水位滇池的岸邊,盡管名稱沒有變,但今天官渡的區域范圍位置有所下移。其二,生活在官渡地區的人們過上了固定農耕的定居生活,否則不會有田疇豐穰、樂乎漁樵、藝植茂林修竹田園風光和閑適生活。其三,鄉士大夫纜船于渡頭,吟嘯自若的場景反映出滇池經過治理后,寶象河露出湖面并與官渡古鎮關系密切。用今天的民間田野調查可以再現纜船于渡頭的場景,在河的兩岸用粗壯的纜繩聯結起來,在來往船只的船舷上加一個鐵環,用鐵環扣住纜繩,拉動纜繩船就可以在河與湖間往返自如。
明天順至成化元年(1465年) 所建的《妙湛寺增建佛殿記》載有:“滇池之東約三百余步有古剎曰‘妙湛’,乃前朝所造而頹圮已久。”如果按照當代的計步來看,300余步大約有150米左右。這說明,經過不間斷對滇池出海口的疏通,官渡地區水位逐步下降,陸地范圍也在增加。正德《云南志》卷二記載:“滇池為云南巨浸……弘治十四年,巡撫右副都御使陳金、鎮守太監劉泉、總兵官黔國公沐崑委軍、民、夫、卒數萬,浚其泄處……于是池水頓落數丈,得池旁腆田數千頃,夷、漢利之。”[13](P7)土地大量出現,人口逐年增加,手工業的發展及各類貿易往來,還修建了孔廟,設立社學,其經濟文化面貌煥然一新。而且明代的云南:“屯田之制,所以甚利最善,而視內地相倍蓰也。又內地各衛,俱二分操守,八分屯種,云南三分操守,七分屯種。”[13](P10)官渡河尾屯作為官渡地區的屯田中心,不僅使官渡地區成為了重要的軍事重鎮,也使官渡地區走上了真正農耕種植的興旺之路。清代,官渡地區的發展依然是聚焦于對滇池海口河的疏通治理,相關也記載較多。從康熙到道光年間,滇池經過數次疏浚,雍正九年(1731年) 把海口河中的牛舌灘、牛舌洲和老埂挖掉,使湖水大量得以外泄[14]。
道光十六年(1836年) 在海口河上筑屢豐閘,用以調節滇池水位[15]。此時,位于滇池岸邊的古鎮官渡離滇池越來越遠,但因各個時期的人文景觀匯聚于此,它成了明清無數詩人詠唱的對象。無論是張仕廉在《官渡漁燈》中體驗的“朝泛昆池艇”[16](P201),還是楊慎在《官渡妙湛寺》 看到“香臺夜景澄”[16](P200),都被熊郢瑄描繪進“太華平臨野氣新”[16](P78)和“水天一色好風光”[16](P199)的優美畫卷中,還勾起人們“桑田幾度滄州改,莫向漁翁話舊愁”[17](P78)的回憶。1910年,滇越鐵路通車,在官渡古鎮內的西莊設置車站,官渡古鎮成為昆明南部東連鄉村集鎮小板橋,南通呈貢的重要門戶和交通要沖。
這一階段對于今天的城鄉融合發展而言,有其不可忽視的特點。一方面,隨著精耕細作的完成和相關配套水利設施的完善,其稻田農作生產逐步與內地趨同,且保有高原湖泊的特色;另一方面,此階段留下的人文景觀遺址以及相應的文獻記載都極為豐富多樣,對于具體的人文生態變遷過程可以做出精準可靠的說明。但也提出了新的挑戰:首先,滇池湖面的降低是一個持續變遷的過程,因而官渡古鎮地區的成陸存在著先后次序的區別。實施文化遺跡保護利用時,要嚴格依照海拔的高低順序分別對待,盡可能用現代手段呈現不同時期的文化生態原貌。其次,由于在這一時段內的不同時期,傳入了各不相同的外來文化,多元文化復合并存的格局在這些遺址和相關建筑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開發利用的時候,都要進行觀照和盡可能地復原其原貌,發掘其不同特點,使之能為當代人所共享,也更能體現歷史名城的魅力。
有鑒于以上兩個方面的文化生態變遷軌跡,現當代的建筑和設施的配置要高度審慎,既不能破壞歷史的遺跡,也不應當忽視這一時期文化積淀的后遺影響。如大面積的稻田開辟后,要配置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這樣的水利工程分布面和涉及面都很廣,在外行人看來很難發現這些遺跡在當代的存在,還誤以為是荒地,而將其毀壞。這對于建設歷史名城的昆明肯定會造成諸多遺憾。同樣的,不同時期的商業經營和手工業門類會因為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遷,也會在商行遺址和手工業作坊中留下明顯的歷史記憶,這在當代經濟環境中容易被忽略。這些重要的文化生態變遷內容,一旦在當代建設中被摧毀,將導致不可修復的遺憾。
五、結論與討論
官渡古鎮雖說只是滇池邊極其有限的地理區位,但從4次漫長的歷史時期文化生態變遷歷程而言,它卻是一個難得的歷史積淀和文化生態變遷的微縮景觀,足以集中表現滇池周邊地區的文化生態變遷,為今天提供豐厚的歷史積淀和文化生態變遷特證。誠如上文所言,從遠古狩獵采集時代到原始農耕時代再到固定農耕時代,這里的文化生態沉淀應有盡有,無所不包,來自國外的生態文化影響和遺跡存留也多樣并存。就這意義上說,官渡古鎮是一個文化交流溝通,協同發展,協同變遷的縮版。要將這兒打造成為能夠系統反映滇池環境歷史過程的旅游目的地顯然是一個理想的選擇,也可以成為古為今用的樣板。但與此同時,值得警惕的地方也很多。這是因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們認識古典文獻和認識考古遺物的水平也得到提升,此前的工作盡管存在這樣的或那樣的缺陷和不足,但隨著學科水平研究的提升,此前的誤判都可以得到改正,此前的遺漏都可以得到補救。當下的古為今用,城鄉融合發展就不能按習慣辦事或者套用其他地方的開發模式去一刀切地執行。而是要對這一地區的歷史積淀和文化生態變遷先作出精準的研究和復原,再經過統一規劃,才付諸實踐,絕不可草率行事。否則的話,不可再現的歷史遺跡和遺物就會毀于一旦,也無法體現昆明的歷史積淀和文化生態變遷軌跡。只要我們把官渡古鎮再利用工作做得好,它就有可能成為全國可資仿效的樣板,從而具備推廣、創新、利用的新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