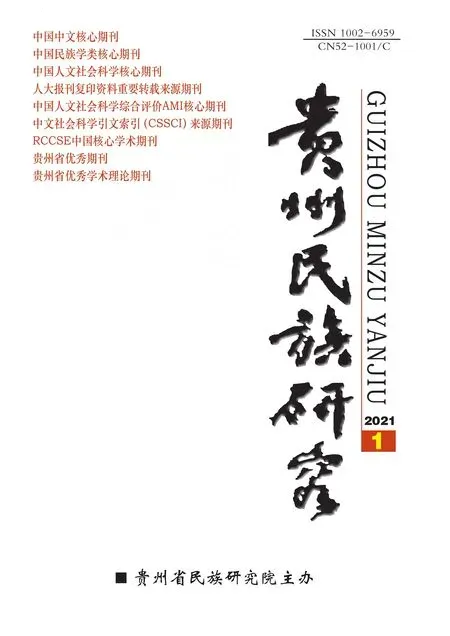試論清末水族作家遷徙文學的書寫特征
——以潘文秀的《譜牒記事》為例
潘光繁
(貴州省民族研究院,貴州·貴陽 550004)
水族主要聚居在珠江水系的龍江、都柳江上游的貴州省三都水族自治縣和荔波、榕江、獨山、丹寨、從江、都勻等縣市。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水族人口數為41.1847萬人。水族是中國的一個古老民族,其起源和遷徙,歷史上雖然沒有文獻記載,但水族卻有自己獨立的語言和文字。水族之有文學,應始于水族活動之初。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水族使用本民族語言創作了大量的口頭文學,并以口耳相傳的形式,為后代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民族文學遺產。水族雖然有一種名為“水書”的古老文字,但這種文字僅有400多個單字,而且其功能也僅限用于送神驅鬼、擇吉避邪、祈福禳災等祭祀活動,不具備人際交流、記載事物等方面的功能。水族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均以漢字作為記事和交際工具”[1](P1)。故水族口頭文學只能在本民族內部流傳,其他民族無法領略和欣賞到其外在的語言色彩和內在表達的深層含義。唐史載東謝地方“俗無文字,刻木為契”,以“刻木為契”來記事,就水族地區而言,直到清代這種方式依然存在。在水族地區,刻有漢字的墓碑,以清康熙年間為古,這種跡象說明清代中期漢文化教育才開始出現于水族集中居住的區域。
在水族鄉村,始終存在著文學的因素,正是那些血液中流動著水族文化元素的民間文人,將水族文學的精義一代代地傳承下來。清代雍正年間,朝廷實行改土歸流,農耕文化得到推進,水族地區經濟取得相應的發展,由此義學和私塾逐步興起,漢文化教育推動了水族書面文學的出現。水族書面文學,顧名思義指的是水族作家用漢語來描物敘事的書面文學作品。水族書面文學由飽受中華傳統知識和家國情懷熏陶的水族文人創作。他們創造出來的文學范例,影響當時的水族社會,激勵水族后人,為水族融入中華多民族文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水族書面文學的出現,時間大概在1855年前后,以潘文秀的詩作《一兩五有序》為標志。1889年,潘文秀在結合水族地區關于潘氏源流及分布傳說的口頭資料的基礎之上,完成了《譜牒記事》的創作。《譜牒記事》又名《潘氏宗譜》或《潘氏本源》。
宗法式家族實質上是一種血緣組織,用文字把這種血緣組織關系記錄下來,就是所謂的譜牒。在中國,譜牒歷史悠久,它承擔著記述氏族世系的功能,并作為一種書籍的形式而存在,明清編修族譜的風氣依然盛行。在譜牒的發展過程中,作為譜牒形式之一的“家譜”,亦叫單姓族譜,其不單單只是記載家族的歷史名人事跡,還把家族內非名人的所有族眾都一一地貫串起來,并注明他們之間存在的血緣關系。譜牒為“實錄”,即非“虛構”,記事應如實反映。而潘文秀的《譜牒記事》 在敘事上,形式不僅類似于傳統章回小說,而且內容上還具備情節、環境、人物等描寫內容,和傳統小說敘事均無兩樣。清末以來,虛構是小說本質特征的觀念成為一種共識,俠人則說:“小說者,一種之文學也。文學之性,宜于凌虛,不宜于征實。”虛構作為小說的一種本質屬性,在通讀的《譜牒記事》文本時,可以看出潘文秀創作的《譜牒記事》在水族遷徙歷史傳說的基礎之上,進行了虛構和演繹,并增加了許多令人神往的奇聞軼事,使文本的傳奇色彩與可讀性都得到了顯著的增強。此外,《譜牒記事》與清末小說在文本敘述、情節安排、環境描寫、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辭海》“小說”條云:“一種敘事性的文學樣式。以人物形象的刻畫為中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具體環境的描寫,廣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會生活。”《譜牒記事》 完全就是歷史小說的寫法和表述模式,潘文秀在尊重水族口傳歷史原貌的基礎上,對必旺、高彥等人物和他們所經歷的事件,在情節上進行適當的虛構和補充,使《譜牒記事》具有濃厚的文學性和審美性。在表現技巧和文字修飾方面,作家也花費了大量的心血,使《譜牒記事》適合大眾閱讀,流傳久遠。這些均是歷史小說的明顯特點。
譜牒的目的是真實反映、再現宗族傳承脈絡,為后世展現真實的家族歷史,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在潘文秀的虛構和演繹下, 《譜牒記事》成了水族遷徙人物和遷徙事件的演義小說,由此衍生出了它的重要文學意義。因此,作為由詩文到小說的過渡性作品,《譜牒記事》雖名為族譜,實則是水族小說的濫觴之作。作為最具水族遷徙書寫特征的《譜牒記事》,其蘊藏的精神特征,在水族文學史上具有非凡的意義。
一、蘊含著濃烈的家國情懷意識
“潘文秀,字松亭(約1837—1904年),貴州省荔波縣三洞鄉梅山村(梅山村,原屬荔波縣,1957 年三都水族自治縣成立,劃歸三都水族自治縣) 人,清末秀才。潘文秀于清同治五年(1867年) 在家鄉創辦梅山學館,潘文秀終身執教,著有《松亭詩稿》,但已散佚。”[2](P226)潘文秀一生致力于水族地區的教育事業,他以教書育人為己任,并把在水族地區實施漢文化教育當成是啟發水族民眾和促進水族社會融入封建主流社會的一個重要途徑。在接受漢文化知識和長期的教育實踐過程中,潘文秀自覺地擔當起水族教育家的職責。漢文化在水族地區得到推廣,使得擁有漢文化知識的水族人逐漸增多。在封建社會,居住于窮鄉僻壤的少數民族往往受到諸多歧視,清朝后期,隨著漢文化教育在水族地區的逐步深入,為了避免本民族在參加科舉考試時遭受民族歧視,水族文人敏銳地意識到整理族譜是水族融入現實社會的一種需要,加上出于對本民族歷史淵源的一種文化探索,生活在貴州南部邊遠山區的水族文人回應了這個問題。于是水族遷徙歷史得到書寫,用以表達水族與周邊其他民族乃至國家的關系。為此水族諸多文人作出了艱辛的建構和探索。水族書寫在文學創作上,這一時期以潘文秀創作的水族小說《譜牒記事》最具代表性。
在《譜牒記事》第一回,作者開門見山對水族先民必官、必旺、必宦三兄弟略作介紹之后,便這樣敘述道:“只因金兀術五路進兵,朝遣派三昆玉帶兵去助韓世忠元帥守兩狼關。”[3](P173)如此便將水族先民置放到韓世忠率軍反抗金兀術入侵南宋的戰場之上,體現了濃厚的家國情懷。家是人成長開始的地方,國是人愿景的源泉。簡而言之,家就是最小國,國即是千家萬戶的有機組合。生活在現實社會中,每個人的生命和體驗都與家國有著密不可分的諸多聯系。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核心內涵之一的家國情懷,其本質上是主體對共同體從內到外的認同,并促使其朝良性方向不斷發展的一種愿望、思想及理念。家國情懷內涵囊括家國同構和仁愛之情,從古至今,都是行孝盡忠、鄉土觀念、民族精神、愛國主義的高度融合,以致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直以來都是中華民族亙古不變的人文理想。作為水族小說濫觴之作的《譜牒記事》,其以水族先民遷徙故事為題材,是一篇帶有濃厚歷史演義傳奇色彩的英雄傳奇小說,作家以中國傳統章回體的形式,在鎮守兩狼關、激戰黃天蕩、征服汝南等戰役中,將水族先民必官、必旺、必宦的忠義之心,在文字中淋漓盡致地顯現出來。以韓世忠抗擊金兵入侵的廣闊歷史為背景,水族先民在抗擊外侮上,與抗戰派同舟共濟、生死與共的衛國書寫,表達了清末水族文人對家國命運和民族命運的關注與思考,將水族族群的命運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命運史,將水族族群的抗爭植入華夏民族的抗爭長流,將水族族群的榮辱植入中華民族的榮辱觀念,作家的目的是為了體現水族歷史和家國的緊密相連,在榮辱與共的歷史長河中,書寫水族先民參與著名歷史事件,不僅是尋求外界對水族歷史的認可,也是對水族傳統文化的一種超越,更是激發水族民眾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精神力量。
在《譜牒記事》的文本敘事中,當金兀術五路進犯南宋時,潘文秀以邊遠山區水族文人的視角回顧歷史,他建構和贊揚了水族先民必官、必旺、必宦等人用生命護衛國家政權存續和領土完整的愛國情懷。“必旺殷勤忠友,元帥以鳳鼓與之。巡夜有功,元帥都督夫人梁氏以其義女吳氏配之。及與元帥征服汝南有功,保奏必旺公晉升,特授知州之職。至攻黃天蕩,吳氏侍候梁夫人在桅竿頂上鼓樓,看職有功,因此夫人請元帥保奏吳氏七品孺人。”[3](P173)通過抵御金兀術進犯、黃天蕩水戰、征伐汝南等一系列戰爭的描寫,水族先民的忠義得到了彰顯。盡管戰爭場面在作家的筆下,常常是一筆帶過,但戰爭的激烈和殘酷,透過文字,仍然能夠讓讀者感受到歷史事件的艱險和悲壯。風平浪靜式的語言表述下,娓娓道來的是波濤洶涌的靜水深流,水族先民必官、必旺、必宦三兄弟在抵御外侮戰爭中,敢于拋頭顱、灑熱血的家國情懷在作家的筆下,隔著歲月的塵埃,依然能夠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地呈現于讀者的腦海之中。
面對外敵入侵,水族先民的表現不是被動地防守,而是主動、積極地參與民族的抗擊,在《譜牒記事》中,潘文秀用了“三昆玉帶兵去助韓世忠元帥鎮守兩狼關”等語言表述,以示水族先民為抗擊外侮,敢于出戰的勇毅情懷。且作家在創作時有意識地把歷史事件和文學建構緊密地加以聯系起來,形成一個意蘊獨特的水族先民參與抗擊外侮的戰爭場面,使得原本隔著歷史歲月的歷史事件和地處貴州南部邊遠地區的水族人民,在文學的建構中,融入匯集之后,變得相互交織起來。作家想要表達的是生活在貴州南部邊遠水族地區的民眾,在重要歷史事件上,是有力量助力國家抵御外侮的族群,從而建構出水族先民為捍衛國土完整而義無反顧地奔赴戰場的情景。
家國情懷是中華民族能夠綿延不絕、繼往開來的、極為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中華民族最素樸、最深層、最持久的一種情感。千百年來,家國情懷更是華夏民族個人的立德之源和立功之本。在歷史發展的長流中,家國情懷在民族受辱和國家危亡時刻常常表現出強勁的生命力。把水族先民植入保家衛國的戰爭中,充分表現出水族作家潘文秀對水族先民在抵御外侮上的重視,體現出他的民族情懷和家國責任感。戰爭結束,功成名就,作家隨即將水族先民必官、必旺、必宦三兄弟的志向置放在他們的對答之中:“必旺公曰:‘值此天下大亂,朝廷聽奸害忠,不可仕也。我兄弟共尋一山明水秀,躬耕為樂得以自由罷。’必官,必宦二公同曰:‘士各有志,勿庸拘乎一轍,二哥歸田以祀先人,乃是盡孝之意。我二人出仕,以祀人主亦為盡忠之情。’”[3](P173)必旺直接放棄知州之職,為實現“躬耕為樂得以自由”開始了帶領水族先民“尋一山明水秀之地”的漫長遷徙之旅。
二、流淌著強烈的民族團結情愫
水族的遷徙之路,在《譜牒記事》敘事文本中,是充滿執著和艱辛的一個漫長過程,這一過程中,在水族先民的身上,作家的筆下流淌著一股強烈的民族團結情愫。戰爭結束,志向明確之后,作家在《譜牒記事》中這樣寫道:“於是昆玉議曰:吾兄弟俱有山高水遠之志,恐異日子孫無憑可記,難認弟兄,遂伐椿木芽一株作船,三枝于紅水河之間,共分手足,兄從紅水而上去做土司,弟從清水而下去任漢官。我祖仲氏必旺公入營以來,不言官爵,故撤營之際,丟官不做,懸掛鼓冠遂與吳太泛舟從中河向黔南,往尋一知水仁山以自樂。”[3](P173)自此之后,在先民必旺的帶領下,水族民眾開始了他們執著前行又漫長艱辛的遷徙歷程。
從前面所述,可以看出潘文秀把水族參與歷史抗戰事件不斷融入到中華民族中的這一過程進行了開門見山式的表述。在潘文秀本人看來,《譜牒記事》不只是文學文本的建構,更是水族民眾千百年來永不褪色的理想和信念。在水族遷徙的過程中,潘文秀認為水族理應和其他民族和諧相處,并共同走向社會歷史發展的征程。他的這一思想,在小說文本中,借助必旺、高彥等人,得以一一實現。因此,在《譜牒記事》中,作家特別注重對水族先民必旺的刻畫,他既機智勇敢、又能功成身退,作為小說中的兩大主人公之一,在必旺的身上流淌著強烈的民族團結情愫。在他那里,我們可以看到水族族群堅持與人為善的性格得以集中體現。在遙遠、漫長、艱辛的遷徙路上,無論是在“山明水秀,層巒疊嶂,煙鎖波瀾,瀠洄不堵”的南丹州,還是在“山中虎踞龍蟠帝王居,地勝南丹百十倍”的東土十二洲,抑或是在“西山呈爽氣,西壁聳文峰”的西十二濂和“地方山勢奇聳,水流曲回”的集賢村,必旺都親自率眾筑屋、播谷、種瓜,他率領族群與人為善,自給自足,不與周邊發生紛爭。雖然在“四面青山如筆畫,一坪沃壤盡桑麻。水涌波濤,山出荔枝”之地時,和廖德產生過土地紛爭,但必旺也沒有采取蠻橫粗暴的方式,而是有理有據地跟廖德進行商議談判,最后讓廖德心服口服、主動地停止紛爭。必旺不僅是水族民眾的生活模范,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又是水族民眾的精神偶像和情感歸宿;“爾等唯耕讀為本,勤儉是務,為人總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此八個字乃我格言,你們子孫須記在心。”[3](P179)必旺臨終囑托后人的這一遺言,更是遷徙途中水族民眾都一致堅持遵循的處世法則。
必旺逝后,必旺之子高彥成為《譜牒記事》中的主要人物,相比其父,作家對高彥的人物性格刻畫,顯得更加豐滿。在處理周邊民族諸多紛爭上,以高彥為代表的水族先民一如既往地繼承了必旺那種強烈的民族團結情愫,并將之發揚光大,達到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效果。
“妙厘人與七葉妙爭田地十余年打仗不停,聞我高彥公時在營盤帶有強勇,特備禮物聘請彥公去打七葉妙,奪回失地。彥公再三辭金不受,勸他回去和息。他實不肯跪哭求之,公不已,帶家勇起程。”[3](P181)高彥首次處理民族內部紛爭是在妙厘和七葉妙為爭田搶地混戰十余年之時,受妙厘人之邀,高彥答應幫助妙厘人奪回其失地,在參與奪回失地的過程中,高彥運用自己的智慧,數次捉到七葉頭人,但他都沒有加害,而是以酒肉送食,然后釋放,最終讓七葉妙心悅誠服地把侵占妙厘的土地退還對方,消除了妙厘人和七葉妙多年爭斗不休的混戰局面。“次年東妙厘與西妙厘同爭中妙絕業田地,仗打十余年,不得清楚。東妙厘人聞我公高彥打平七葉,故備禮聘請我彥公,公亦承領。”[3](P184)在東妙厘人和西妙厘人同爭中妙絕業田地中,戰事一觸即發之際,高彥私底下就交代自己的部將不要濫殺無辜,為避免雙方出現更多的傷亡,高彥又使人勸人多勢眾的西妙厘,說:“你雙方所爭田地,乃是絕業之地,又不是你們的本己地,勸你二比均分和息了事,免得兵勇死傷。你們家眷大小依人分得地豈不甚好。”[3](P185)西妙厘,不聽勸阻,戰事無法避免之后,高彥并不大開殺戒、濫殺無辜,而是運用自己的實力、智慧、勇武,贏得了戰事雙方的尊重,讓雙方平分了彼此所爭的田地,調停了東妙厘和西妙厘之爭。最后,高彥“將于西妙得貨物概退還原,東妙謝金亦辭不受,東西妙厘共感公之恩德。”[3](P185)
此外,在處理此彼妙就土地的紛爭問題上,高彥也力勸雙方和平商議,反對武力戰爭,最終“眾誠曰:‘倘日后再爭此田地者,天誅地滅,絕種斷根。’”[3](P188)作家在水族遷徙過程中致力于書寫民族交流,他筆下呈現的是從“戰爭”到“和平”的過程,突出地表現出水族先民在遷徙過程中強烈的民族團結情愫。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潘文秀倡導水族與周邊民族和諧相處的主張,不僅是對封建王朝把水族地區視為“化外”的不滿,更是體現出作家對水族民眾既能跟其他民族和諧相處又敢于反抗外來侵略的自信與自尊。
潘文秀通過《譜牒記事》,向我們敘述了水族在遷徙過程中與周邊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和交融,以必旺、高彥為代表的水族先民在不斷調停其他民族內部紛爭的一系列過程得到一一呈現。這不僅是作家為了告訴人們水族不是想象中的蠻荒和落后,還要表達的是水族在遷徙過程中感應著歷史和社會的進步。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為清末邊遠地區的水族文人,潘文秀已然把民族與民族之間和諧相處當作是促進民族地區發展、體現國家民族認同,并將這一進程通過文學,動態地表現出來。借助潘文秀的《譜牒記事》,我們可以深層次地探討他在創作過程中所帶有的那種強烈的民族團結情愫,以及建構出水族在遷徙路上與周邊兄弟民族在交往中出現縱橫交錯,共同發展的密切關系。
三、 體現出勇武的民族性格特征
在漫長的遷徙過程中,曲折的經歷不僅增強了他們外在的體質,更是磨礪了他們內在的意志;水族民眾不僅形成了開拓進取、勇于奮斗的民族精神,更是形成了勇武豪放,坦率重義的民族性格。水族族群的民族性格在《譜牒記事》中,潘文秀刻畫得尤為明顯,從必官、必旺、必宦三昆玉帶兵去助韓世忠元帥守兩狼關,到高彥出兵幫助妙厘人收復失地、調解東西妙厘之爭、平息此彼妙互爭田地的一系列事件中,戰爭場面此起彼伏、斗智斗勇場合輪番出現。作為水族遷徙先民的代表性人物必旺、高彥、岜扈等人,他們往往能身先士卒,表現出水族族群的智慧、堅韌、擔當,散發著勇武的民族性格特征。這種性格刻畫成就了《譜牒記事》人物的活靈活現,其中尤以高彥勇殺猛貅最為震撼。“勇殺猛貅”在《譜牒記事》中,是一段極為精彩的文學表達,作家入木三分的語言表達,淋漓盡致地刻畫出高彥藝高膽大、勇武機智、敢于為民除害的性格特征。
“妙厘客議道有大猛獸常吃牲口,逢人一口便吞去,在他山那一方做不得活路了,甚是害怕,不知何物。高彥公曰:‘聞古人云,貔貅猛惡,莫非此獸?地方何不殺之?’客曰:‘身大如房,頭大如倉,誰人敢近?’高彥公曰:‘不如請我以除民患。’第二日,妙厘集數百人來請我公去殺此獸。引到那山,我彥公身披鎧甲,腰扎牛劍,手拿金葫蘆,中有火鋼花染毒。貔貅一來,撞樹樹倒,踐石石崩。我公舉劍向獸猛砍。獸皮厚硬不能砍進。砍了半日,獸猛地撲公,公以金葫蘆一揮,火鋼花射著獸右眼,獸一吼聲倒樹崩石而去。土人請公回館款待安宿。次日土人有一二千來迎我公,去再打猛獸。公帶金锏一雙重一百二十斤,向獸飛打如故。獸眼已著火毒,不見分明了,我公與獸打了半日,鋼锏打斷獸的一腿,獸又再逃。土人喜歡又迎公回館倍加款待。安宿一夜,第三早土人又二三千人,來求公再打。我公問土人:‘你地方有更重的軍器否?’土人曰:‘前世遺有一把斧頭重三百斤。’公曰:‘還可!’眾人將斧磨利。此斧乃金鋼口,檀木柄。我公持斧到那山,猛獸雖傷,一跳起來,樹倒石崩,我公仍用锏飛打,日至將午力漸衰。獸猛地撲公,我公執斧正立,猛獸見斧檀桿便倒威蹲伏股栗,我公將斧飛打獸頭,一劈腦漿迸裂,獸大吼一聲,倒從山頭而下,與木石并滾,落到轟硐口斃死。四方土人天天來看往來不絕,個個割肉嘗其猛獸肉。地方土人湊成千金以謝我公,我公辭曰:‘此乃除孽,敢救生靈,吾乃取之是禍也。’辭金不受,回轉岜榮。”[3](P183-184)
借妙厘客之言,極言貔貅性情兇猛:“常吃牲口,逢人一口便吞去。”體型之巨:“身大如房,頭大如倉。”力氣之大:“撞樹樹倒,踐石石崩。”高彥自告奮勇,愿意為民除患。然后描寫高彥先后用利劍、金锏、重斧與猛貅決斗,連斗三日,方擊斃猛獸。極力描寫貔貅的兇猛,目的是為了更加襯托出高彥的無畏。
作家呈現出不斷變化的勇武場面,也是為了凸顯水族先民在遷徙路上的執著前行。作家選擇高彥在具有象征意義的“勇斗猛貅”中奏起勝利之歌,是為強調水族先民的英雄氣概,以及他們的敢于擔當和使命意識。
此外,在遷徙路上,在必旺、高彥的帶領下,水族族群身上“匯集著廣大群眾的機智勇敢,閃爍著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1](P234)。無論是抗擊外侮、參與戰爭,還是商議談判、決斗猛獸,以必旺、高彥為代表的水族先民,在知己知彼中,往往有理有據,并能渾身是膽、沖鋒陷陣,勇往直前,凸顯出水族先民剛毅勇武的民族性格。
四、具有豐富的人道主義精神
所謂的人道主義精神,它的特質具有相對的崇高性和超現實性。精神層面的東西,往往超越現實而存在,所以精神多指愿望中的東西,在常規的現實生活中,精神常常是空間存在的一種人為愿望。因此人道主義精神,往往更著重地體現以人為本,并以人類社會基于自身功能帶來的良知為基礎,在此意識的支配下,形成一種以高度文明和人類和諧發展的一種普世價值取向。
中國封建時代,性別歧視色彩濃厚,女性常常被社會所“物化”。絕大多數女性,在其一生中,很少有思想上的自由。由于長期受到封建思想的荼毒,婦女的生存空間極為狹窄、精神狀態極為壓抑,以“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和“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為主要內容的“三從四德”,在封建時代,是常常用來約束婦女的行為準則。長期受“三從四德”的制約和影響,許多年輕寡婦以守寡為榮。而在潘文秀的《譜牒記事》中,作家卻能獨樹一幟,突破封建主流社會對女性的壓制,描述在地處邊遠的水族山區,婦女在夫死之后順利改嫁,還能贏得子女及眾人尊重的事例。“吳太曰:‘我一去,我家內治無主,喊我媳來一一交代與她清楚我才放心下堂。’喊媳婦韋氏交代明白,遂教岜扈去拉茅寨報接親之期。韋氏奶曰:‘要一男媒,要一女媒,要十名人伕。’去人轉來到家說知其情。太曰:‘女媒現有,男媒請誰?’高彥公曰:‘煩廖德公一往。’德公曰:‘我去,我去。’高彥公曰:‘要轎子去。’德公曰:‘要這轎子何為?’高彥公曰:‘吳氏腳細走不得路。’德公看見旗傘、鑼鼓,問曰:‘要這些做什么?’高彥公曰:‘這旗,恐路上有風,遮之;這傘,恐路上有雨,蓋之;這鼓,恐路上撞鬼,打之。’德公曰:‘諾,諾。’眾勇笑曰:‘德公真長者也。’人伕轎馬百余,路上到了拉茅,韋奶點數謂曰:‘連我轎子,才滿十數,何以拾完東西?’岜扈人說:‘怪為弟不明白,多喊幾個人伕來,若抬不完丟一些寄于此處,二回再抬。’於是,讓廖德公騎馬趕先,韋氏拖懶搭坐我吳太的綠鷹撒網轎。人伕轎馬,旗鑼執事,吹簫鼓樂,山鳴谷應,簇涌如云離硐溪。燭搖紅彩,儀金鳳香,噴青煙、舞玉龍。二人堂前先拜天地祖宗,重拜母親。”[3](P180)
作家以較大的篇幅,對吳太改嫁一事,進行了詳細的敘述,字里行間呈現出沉靜自若的語言風格。人道主義充盈其間,“為女性如何獲得自由和解放這種宏大命題留下思考的空間”[4](P40)。可以這樣說,身處封建社會,又能跳出封建時代的觀念局限,在對待封建婦女人生的問題上,作家的思想傾向和創作態度,洋溢出濃烈的人道主義精神。
經過漫長的歷史歲月,人類最終從動物界分化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和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有道德觀念和廉恥之心而動物沒有。孟子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禮記》亦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數千年來,人類逐步從蒙昧、野蠻走向了禮儀、文明。進化到文明階段的民族,往往都具備著鮮明的倫理道德觀念,有倫理、知禮儀是一切民族脫離蒙昧野蠻,走向文明的重要標志。《譜牒記事》敘述了有人以猴為妻的事例。“一日,我高彥公思母吳太,乃備禮帶家勇同往妙厘探母。路過四方井,坳上見一猴子手提尿片,彥公問勇曰:‘此猴何故?’勇曰:‘聞楊柳人有姓王者,其妻死,以猴婆為妻,接養孩兒,即此猴也。’彥公曰:‘吾不忍人墮於禽獸,射死此猴,吾愿以家女代之。’家勇聞公言此,即張弓搭箭射之,猴倒地死。是晚,公宿楊柳,王姓抱兒查訪誰射殺猴死。公曰:‘吾令家勇將猴獸射死。’王姓哭曰:‘誰撫養此兒長大?’公曰:‘猴死不能復生,若你無妻撫子,我有一外甥女嫁與你做妻,豈不甚好。’王姓喜歡,即殺雞而黍以謝恩。”[3](P181)不忍人倫墮獸何,高彥消除了人以猴為妻的落后習俗,讓人懂禮儀、有尊嚴地活下去。正如《譜牒記事》詩云:一弓射罷無猴氣,楊柳於今獸俗泥。高彥踐行“止利害,化仁義”,做到“排難、解紛、和爭、息訟”,勤耕苦讀,仰崇仁義。
此外,無論是妙厘人與七葉妙戰事、還是東西妙厘之爭,抑或是此彼妙之戰,在諸多爭奪田地的對抗中,水族先民高彥都信奉:“將在謀而不在勇,兵貴精而不貴多。”且通常采取商議談判的方式來解決戰爭中的諸多問題。在不可避免的戰場上,他也總是想方設法,從力求雙方人員傷亡最小的角度出發,盡量避免殺人,從而在爭奪資源的殘酷戰事中,閃現出人道主義的光芒。“在某種意義上,文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以給我們提供一種類似于自然美的東西”[5](P150)。如上所述,《譜牒記事》做到了這一點。作為水族文學歷史上小說的濫觴之作,《譜牒記事》的遷徙書寫蘊藏著豐富的人道主義精神,清末水族文人建構水族先民處理民族矛盾采取的人道主義精神,對當今世界范圍內,小到民族矛盾,大到國家紛爭,仍然具有現實的指導和參考意義。
五、結語
“士人們需要更加豐富的思想資源的補給來拓寬精神向度。”[6](P58)作為封建末代文人,潘文秀對水族的遷徙書寫,源于他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水族人,通過長時間對水族地區歷史文化,和當時水族社會現狀的考察研究,使得潘文秀對水族的遷徙書寫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在創作上,他能站在歷史的高度來追溯水族的往日歷史。他以文學作品的方式向世人呈現出水族在遷徙過程中的果敢姿態。“民族,作為客觀存在,是民族自然體、民族社會體和民族人種體的多維統一。”[7](P103)潘文秀以激動振奮的心境,書寫水族遷徙的內在精神。水族匯入歷史的動態過程,通過作家的《譜牒記事》,得以生動描繪。就民族文學創作而言,“少數民族作家大多采用可靠敘述的形式,以展現民族身份,表現本民族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顯現出來的民族風俗、風物人情、民族心理等方面的變化,從而在可靠的敘事中寄寓對本民族生活現狀以及未來發展的深層思考”[8](P67)。基于此,在《譜牒記事》創作中,潘文秀亦將水族地區的民族風俗、風物人情、民族心理等方面盡情地融入其中,形成了一幅幅生動的水族遷徙的歷史動態畫卷。
整理族譜的目的是想得到封建王朝主流社會的認可,作為清末水族地區文人,無可否認的是,潘文秀創作的《譜牒記事》,其直接目的應該是希望水族士子在參加科考中免遭歧視。同時潘文秀又是一個具有民族情感和家國情懷的水族作家,他摯愛黔南大山深處的水族山鄉,長期在梅山學館從事私塾教育,使得他心中聚集著強烈的民族使命感。清末時期,作為水族地區文化教育的先行者,潘文秀通過教育實踐和文學建構,為推動水族地區社會文明和進步而不遺余力。文學不僅對個人品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對于民族精神的建構,在價值觀上更是無可替代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學起著引導和奠基的作用。為此,清末水族秀才潘文秀以梅山學館為陣地,在教書育人的同時,從事文學創作,創作出水族小說的濫觴之作《譜牒記事》。在尋根情感中,是潘文秀對本民族歷史來源的一種文化探索,其目的是用來提升水族民眾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更深層次的是不斷地在水族山鄉建構起民眾的家國情懷,這種家國情懷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