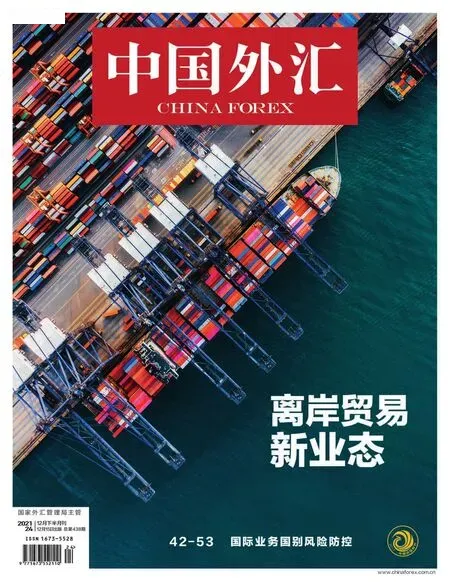新興經濟體經濟修復困局與加息預期
文/鄧宇 編輯/張美思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新興經濟體經濟受到嚴重沖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2020年全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速為-7.3%,而俄羅斯、土耳其、南非等國的GDP增速已下滑至歷史低位,至今仍處于艱難復蘇階段(見圖1)。未來一段時間,在疫情影響持續、經濟內生動力不足、主權債務違約風險增加和通脹形勢嚴峻等因素的制約下,新興經濟體復蘇前景充滿不確定性。此外,隨著美聯儲開啟貨幣政策正常化,新興經濟體大概率將繼續當前的大規模加息操作,但此舉可能會對其經濟修復造成進一步的負面影響。

圖1 部分新興經濟體實際增長率預測(單位:%)
疫情影響持續與內生動力不足削弱了新興經濟體的復蘇基礎
2020年,由于新興經濟體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具有明顯弱勢,遭遇的經濟挑戰也相對更大。2021年,除中國、印度等部分國家外,新興經濟體疫苗接種進度普遍較慢,疫苗供應嚴重短缺。綜合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發達國家的疫苗接種率普遍達到了70%以上,部分國家超過80%;而新興經濟體國家在2021年的整體疫苗接種率很難達到20%。因此,未來一段時間,疫情的負面影響仍將持續,限制新興市場的復蘇步伐。
從更長期看,目前市場和機構對于部分新興經濟體疫情后經濟復蘇的前景仍有一定的擔憂。主要的擔憂在于,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內部經濟結構并不穩定,缺乏內生性增長動能,疊加國際貿易規則競爭、大國政策溢出等風險,未來的復蘇進程會受到更多層面的制約。客觀上,一些具備資源能源儲備優勢的新興經濟體如巴西、智利等國,在2021年借助于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良好預期獲得了一定的貿易順差。以巴西為例。由于巴西經濟對外依存度較高,外貿以資源能源出口為主要驅動,在糧食、原油和鐵礦砂等國際大宗商品需求上漲推高商品出口價格的背景下,2021年上半年其外貿順差同比增幅達68%,創下近三十年歷史最好水平。但對于巴西、俄羅斯、土耳其等內生性增長動能缺乏的國家而言,其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對能源資源的需求,經濟具有明顯的脆弱性,復蘇基礎并不牢固。
IMF在2021年10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1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率為6.4%;到2024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中國)的總產出預計仍將比疫情前的預測值低5.5%。從當前的態勢看,發達經濟體的復蘇節奏要明顯快于新興經濟體,而新興經濟體內部的復蘇分化也在加劇,內生性增長動能不足的經濟體增長前景更不明朗。
新興經濟體財政政策的施展空間有限
當前,除了少數幾個新興經濟體國家外,低收入和內部發展不平衡的新興經濟體國家普遍面臨債務水平高企的困境。不斷上升的財政赤字和債務率,使這些國家未來財政政策的施展空間變得極為有限。
自疫情暴發以來,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收支狀況出現惡化,經常賬戶差額失衡有所加劇。從直接投資凈額看,近十年來,新興經濟體直接投資凈額始終在 [-300,-400] 億美元區間。IMF的數據顯示,新興經濟體外債總額從2008年的4716億美元增至2020年的11143億美元,增幅高達136%;2020年外債總額占GDP的比重則超過30%。而新興經濟體的外債償付額則從2010年的1萬億美元升至2020年的3.9萬億美元,更是增加了四倍。這表明,新興經濟體外債負擔較重,大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收支處于不平衡狀態。此外,2021年4月IMF發布的《財政監測報告》的數據顯示,2020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平均總體赤字占GDP的比率達到9.8%,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則為5.5%。根據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的統計數據,2020年,新興經濟體外債總額溫和增長5.1%,較2009—2013年平均增速低了7.1個百分點;而同期新興經濟體的債務率、負債率和償債率則分別上升了19.9、2.2和6.1個百分點。同時,此輪通脹率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帶來的影響有極大差異,二者的政策工具和面對的風險因子并不一致,將導致政策協調更加困難。在債務問題愈發突出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國家面臨財政刺激政策空間有限的局面。
此外,目前新興經濟體非金融部門和居民的債務規模呈緩慢上升態勢,其風險也在逐步顯現(見圖2)。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經濟復蘇不及預期將使得企業和居民的信貸資產風險大幅增加,很可能對銀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構成新的挑戰;另一方面,財政發力不足將使得居民消費需求難以形成支撐,會降低投資信心和預期,導致經濟復蘇的節奏變得更加緩慢。在未來財政刺激政策空間有限,且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外債和前期的財政刺激政策臨近到期或已經到期的情況下,如何應對接下來的疫苗接種、經濟復蘇和非金融部門/居民的經濟救助等,將是擺在新興經濟體政府部門的頭等大事。

圖2 新興經濟體政府、非金融部門和居民杠桿率(單位:%)
新興經濟體通脹壓力加大與未來加息預期
過去一年多來,歐美等發達經濟體普遍采取了無限量化寬松政策,大量持續“放水”推動全球資產價格暴漲,引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階段性快速上漲,導致通脹率高企。在供給短缺和產能修復較慢等多重因素的驅動下,新興經濟體的通脹水平更攀升到了新的高度。2021年以來,俄羅斯、土耳其、巴西、智利等新興經濟體的通脹率已處于歷史高位。數據顯示,俄羅斯、土耳其、巴西三國的通脹率分別從2020年6月的3.2%、12.62%、2.13%升至2021年6月的6.5%、17.53%、8.35%,同比漲幅分別超過103%、39%和292%,通脹風險累積過高(見圖3)。

圖3 主要新興經濟體國家CPI同比走勢(單位:%)
當前,新興經濟體面臨的通脹風險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極端天氣及疫情等導致大宗商品供需不平衡,助推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價格普遍上漲;二是由于大規模的量化寬松政策拉高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量“放水”進入到金融市場,導致期貨價格和市場預期走高,加之國際金融市場大宗商品投機炒作加劇了不合理的價格上漲,新興經濟體承受著大國外溢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三是前期全球產業鏈供應短缺,部分國家采取加征關稅、出口技術管制和重要大宗商品、原材料出口限制等措施,使得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重啟面臨核心技術和關鍵領域“短缺”問題。
居高不下的通脹壓制了新興經濟體國家民眾的消費需求,造成企業生產成本大幅抬升,對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復蘇造成嚴重打壓。為抵御嚴峻的通脹壓力,2021年3月以來,已有巴西、俄羅斯、土耳其、墨西哥、智利等新興經濟體國家先于美國進行了加息操作,其中部分國家甚至已多次加息。展望未來,預計在美聯儲、英國央行等主要國家央行釋放提前加息預期的背景下,新興經濟體國家大規模加息的勢頭還會延續。新興經濟體被迫加息將不可避免地帶來負面效應: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經濟復蘇需要較低的國內信貸利率水平支撐,以支持企業和居民通過積極信貸減緩財務壓力,多輪加息則會抬升資金借貸成本;另一方面,多輪加息還會加大其國際資本外流壓力,特別是在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的背景下,美元指數反彈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上揚會進一步加劇新興經濟體的資本外流及貨幣貶值,使其經濟修復雪上加霜。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