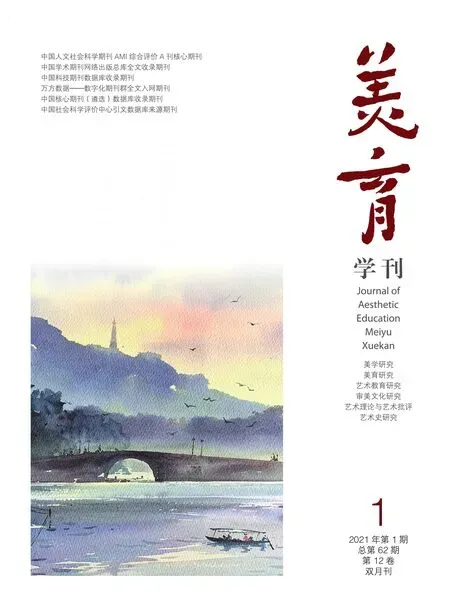中華教育改進社美育組會議述略
胡知凡
(上海師范大學 教育學院,上海 200234)
中華教育改進社是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著名的教育學術團體之一。1921年12月23日由新教育共進社、《新教育》雜志社和實際教育調查社合并改組而成。總事務所設于北京。推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黃炎培、汪精衛、熊希齡、張伯苓、李湘辰、袁希濤九人為董事,張謇、梁啟超、孟祿、杜威、嚴修、李石岑等為名譽董事,陶行知為總干事。
中華教育改進社以“調查教育實況,研究教育學術,力謀教育進行”[1]為宗旨。下設32個專門委員會(1)1922年7月第一屆年會議決組建各專門委員會,年底組建了24個委員會。1924年7月第三屆年會,擴大為33個委員會。1925年8月第四屆年會將“體育委員會”和“教育衛生委員會”合并為“體育與衛生委員會”,委員會總數成為32個。,集中了教育界和眾多學科專家,分別研究各級、各類、各學科的教育問題。1922年12月23日,通過選舉還成立了美育委員會,其中主任為蔡元培,副主任為陳衡恪,書記為武紹程,委員有13人。(2)據《新教育》1924年第9卷第3期刊登分組會議議決案致函委員的名單來看,美育委員有:蔡元培、周玲蓀、李毅士、劉質平、俞寄凡、阮叔平、李文華、雷家駿、彭沛民、劉海粟、張道藩等。此外,還有副主任陳衡恪、書記武紹程等。
按照《中華教育改進社簡章》規定“每年開全體大會一次,于暑假期舉行”。從1922年至1925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先后在濟南、北京、南京、太原召開過四次年會,后因北伐戰爭而中止。每年的大會,除全體會議之外,還有分組會議。美育組分組會議主要討論有關美感教育方面的議案。每年當年會的會期與地點決定后,即由總事務所印就提議案格紙,向各方面的會員、教育機關征集議案。然后,將征集到的議案付印成冊。開會時,將裝訂成冊的議案送到各組。以下將四屆會議中有關美育組會議的議案情況作一介紹,從中我們可以了解民國初期在倡導美感教育時所思考的各種問題,以及美育組的這些參會藝術教育家和學者們為美感教育所作出的努力。
一、第一屆年會美育組會議
1922年7月3日至8日,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年會在山東濟南召開。7月4日美育組分組會出席的代表有: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鄭錦(北京美術學校校長)、武紹程(北京美術學校教員)、高鴻縉(武昌教育廳科員)、陳衡恪(北京教育部編纂員)、張鼎(北京高等師范)、劉海粟(上海美術學校校長)、錢稻孫(北京教育部視學)、吳新吾(北京美術學校)。旁聽者有:李景綱(直隸保定第二師范教員)、周愛周(濟南第一師范教員)、劉坤山(濟南模范小學教員)、雷家駿(南京第四師范學校及附屬小學教員)。主席為蔡元培,副主席為鄭錦,書記為武紹程。(圖1)

圖1 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屆年會美育組
會議審查議案四件:
1.請政府增設國立美術展覽會(劉海粟提);
2.欲求美育普及宜設美術院(鄭錦提);
3.普通美育以造成普通國民具有美的賞鑒與制造之興味為目的(武紹程提);
4.擬于退回賠款中撥出一部分經費實施美育案(梁啟超、鄭錦、劉海粟提)。
在討論武紹程的議案時,陳衡恪認為:“美學原系哲學中之一部分。教育中講美育,只好講藝術之美,就算夠了。”錢稻孫則認為:“若講藝術之美,我國中小學校刻下亦難講及。試觀德國人不獨學生都曉美觀,就是普通社會中人,冠履服裝整齊,到處多有照鏡,人人有各自審美之機會。回觀我國,無論普通人與學生無審美知識,就是學生用器如教科書,登載廣告之類,辦學人亦多不知有礙美育,美術又何從說起。”蔡元培也認為:“此時講美育,本系困難,但美育在教育中又極重要。”為此,會議將劉海粟、鄭錦、武紹程所提的三件提案,合并為一件通過,以學校美育為第一條,美術院為第二條,美術展覽會為第三條。蔡元培并提議由陳衡恪和錢稻孫二人來修改該提案。梁啟超、鄭錦、劉海粟的第四件提案,經全體代表討論也獲得認同。最終全體議決通過了兩件議案。
(一)普及美育獎進美術建議案
該議案對為什么要普及學校美育,為什么要設立美術院和美術展覽會作了說明。議案認為:
今日中國青年之道德日趨于卑下,志趨日流于齷齪之境者,蓋無高尚純潔之美育為之涵養,為之引導故也。夫所謂美者,又非絢爛奢華之謂,無形之中,使有悠然自得之樂,而人生事業,由此發達,此其所以普通宜注重美育之理由也。[2]
提案還認為:
普及美育造就專門人才,不僅囿于學校教育,而學校之外,尤宜設立美術院,以為群才之領袖,美術之淵藪,增造文化,發揚國光,不可缺此宏達之規畫。……美術院中,更宜設永久之陳列館,搜集海內之美術品,任國民縱觀。古時為帝王之私有者,今則公諸民眾,歸美術院管理。省會地方,亦宜設置,不拘其數及大小,相機經營而擴充之,以資參考。而美術院中,延攬海內美術家,使之鑒定古今名跡,并隨時制作或傳摹美術品,以增長其學力,而古跡得以流傳(唐宋帝室除收集真跡外,多摹寫副本)。且使長于論著者,從事編纂論說或講演,以傳播美術之智識,又收集近人作品,開定期、臨時或巡回之展覽會,品第其甲乙,以資獎勵。如此使國民知美術之可貴,美術思想知識因以增進,而美術人才因以興起。古來美術之淵源,系統或以不墜,否則因循坐廢于盲昧之中,而國民美育之精神,不能啟迪,美術其有望乎!此美術院不能不設之理由也。[2]
為此,該議案建議:
第一普通教育宜注重美育
(1)修身禮儀,宜注重美的陶冶。
(2)教科應多取養成美感之教材。
(3)教科書宜注意美的體裁。
(4)校舍教具及教室設備應雅潔整齊,以引起美感。
(5)宜時時有美育上之訓話及展覽會等事。
(6)師范及中等學校,宜授簡略之美術史及美學大意。
第二造就專門人才
(1)擴充美術專門學校。
(A)美術學校于圖畫外,宜加雕塑、鑄造等科。
(B)國內增設美術學校。
(2)工業學校增加圖案、圖畫科。
第三設美術院
(1)延攬美術家以任鑒定、制作、編纂之事。
(2)設永久陳列館羅列古今美術品。
(3)收集近人作品,開定期、臨時,及巡回展覽會。[2]
(二)擬于退回賠款中撥出一部分經費實施美育案
該議案理由是:
我國現在教育學者知美育之重要亟提倡之,惜鮮研究及實施機關,空言亦有何效?茲述啟超(即梁啟超——引者注)對于美育實施計劃,并擬于退回庚子賠款內為最低度之要求,撥出建設費二百五十萬元,每年常年費一百四十四萬元充實施經費,即請公決。[2]
為此,該提案建議:
(1)先就中央建設國立美術館一所,搜集國內外古今美術作陳列之,開辦費二百萬元,每年經常費總額二十四萬元。
(2)就國內相當地點設立國立美術專門學校若干所,開辦費總額七十五萬元。每年經常費總額六十萬元。
(3)擇優獎勵私立美術學校,給予補助經常費總額五十萬元。
(4)每年派研究有素之美術學者二十名赴歐美日本考察,經常費總額限十萬元。
(5)每年派國內美術學校畢業學生十名赴歐洲各國美術學校留學,經常費總額五萬元。
總計建設費二百七十五萬元,每年常年費一百四十四萬元。(3)原文中“建設費”和“每年常年費”計算有誤。此項計劃以施行十年為限,第十一年以后另定之。[2]
二、第二屆年會美育組會議
1923年8月22日至24日,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二次年會在北京清華學校召開,美育組分組會出席的代表有:李榮培(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教員)、鄭錦(北京美術專門學校校長)、馬寶恒(天津直隸教育廳視學)、汪亞塵(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授)、黃公覺(北京師范大學編輯)、張鼎(北京師范大學教員)、劉海粟(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校長)、董永森(武昌共進中學事務主任)、楊白民(上海城東女學校長)、彭紹夔(湖北省教育會干事)。主席為李榮培,書記為汪亞塵。(圖2)

圖2 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二屆年會美育組
會議審查議案三件,最終通過以下兩件:
(一)小學及初級中學各種藝術科應與其他學科同樣重視(鄭錦提)
該議案理由是:
(1)藝術科在普通教育之教育的價值,不亞于傳授知識之學科。因陶冶美感,鍛煉筋肉,訓練觀察,具體的發展思想養成勤勞的習慣,非賴藝術科之力不為功。而欲收藝術科之完全利益,不得不視其與其他學科同樣重要。
(2)我國向來的教育,乃理智的教育,干枯無趣的教育,即因不注意藝術科之故。今欲使教育顧及情的方面,美的方面,與實行,則于小學及初級中學重視藝術科,實為至要。
(3)查歐美各先進國,或以工藝發達稱,或以美術見長聞,其故即因于中小學重視藝術科。我國工藝美術不見發達進步,實因學校對于藝術科向不注意之故,今欲救斯弊,惟有重視藝術科之一法。
(4)救濟現在沉悶的,墮落的社會最重要之方法,即陶冶一般人之美術化的人生,而樹此基礎,即于小學及初級中學重視藝術科。[3]
為此,該議案建議:
(1)藝術科鐘點應比從前酌量增多。
(2)藝術科之設施應比從前完備。
(3)教法應引起學生對于藝術科之重視。
(4)教材形式方面與實質方面并重。
(5)對于藝術科教員之待遇應于對于其他學科教育之待遇同。
(6)藝術科教育應聘請藝術科專家充任。[3]
(二)各省高級中學起首至少有美術工藝科或學校兩處續年增設案(鄭錦提)
該議案認為:
教育當適合個性之要求。在初級中學畢業之生徒當具選擇職業之觀念,倘其興趣在從事美術,而強使其學理、工、農,等科,則為戕賊其天性,大背教育原理。此高級中學應有美術科或校或美術工藝科或校之設一也。學術愈分,則文明愈進。曩日中學僅有文實兩科之分,迄今則細分為農、工、商、教育等科。美術一科自應加入,以示學術之進步。此高級中學應有美術科或校或美術工藝科或校之設二也。教育須從低級至高級,組成一種有系統之組織。如大學有理科,高級中學便須有理科,以為其準備。大學有文科,高級中學便有文科之設。今既有美術之高等教育矣,而無美術之中等教育以樹其基,其可乎哉?此高級中校應有美術科或校或美術工藝科或校之設三也。美術學校應注意關于區域的制造業及手工業之應用,須以本地工業為美術學校功課之中心。換言之,美術學校須按地分配。此各省高級中學應有美術科或校或美術工藝科或校之設四也。美感之天性,乃人人所具有,非少數人所特有,故美術教育須注意多數人之需要。倘將美術視為少數人或專門家之事,則為貴族式之美術,而非美術平民化矣。今欲使美術平民化,使一般人有研究之機會,則不得不擴充之于中等教育。此高級中學應有美術科或校或美術工藝科或校之設五也。社會、家庭、建筑、制造、服飾、娛樂、消遣,各方面無不應用美術;少數美術專門家之力必不足恃,必須造就多數美術人才,始能應付一般的要求。此高級中校應有工藝科或校或美術工藝科或校之設六也。高級中學當設美術科或校之理由綦多,茲所述者特其犖犖大者耳。[3]
為此,該議案建議:
當先于各省高級中校設之。為設施利便起見,初時可設兩校,續年增設一二校。如此,則美術教育可望進步,而社會文化可望發達矣。[3]
(三)各省應專設美術品陳列館(黃公覺提,汪懋祖、張鼎附議)
此為一件保留議案,該議案的理由是:
(1)美術品是代表文化的品物,宜有一機關保存之,不應使其散失。
(2)美術品乃一般人所欲鑒賞者,宜有一公共場所將其陳列,以供眾覽。
(3)美感乃德育之基礎,欲陶冶社會一般人之道德,當將美術品陳列于一定場所,供一般人參觀,藉以引起高尚之心思,優美之情感。
(4)我國社會一般人,對于美術,向不注意,實緣當局不思提倡之方之故。提倡之方,宜搜集美術家之作品陳列之,使一般人稱美。故設美術品陳列館,實為提倡美術之最大助力。[3]
為此,該議案建議:
(1)由各省教育廳籌辦,館須獨立,地點須在省會適宜之處,館之建筑,須合美的原則。
(2)陳列之品物:
(A)古人美術作品。
(B)今人美術作品,內中分學校美術成績品,社會美術家美術作品。
(C)各種美術標本。[3]
該議案雖然“主文已通過,因時間不足,未能議及辦法,故議決作保留案”[3]。
三、第三屆年會美育組會議
1924年7月3日至9日,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三次會議在南京東南大學召開。7月4日至8日美育組會議出席的代表有:劉海粟(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校長)、雷家駿(南京第四師范學校及附小教員)、周玲蓀(東南大學附屬中學教員)、李毅士(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務長)、李文華(工作單位不詳)、劉質平(私立上海藝術師范大學教員)、阮叔平(江蘇省立藝術專科音樂系主任)、俞寄凡(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授)、李榮培(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教員)、汪亞塵(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授)。主席為劉海粟,書記為雷家駿。會議審查提案九件,最終通過以下六件:
(一)高級中學必設藝術科(李文華提)
該議案的理由是:
歐洲文藝復興以前,足以維系其社會者神的宗教也;文藝復興以后,足以維系其社會者人的宗教也。人的宗教,不啻藝術品之愛也。我國社會舊為孔氏倫理生活所維系,今則受西洋藝術生活之影響(西洋教育自盧梭而后趨重于藝術自由生活),對于理論之說有懷疑,對于宗教又無信仰,其足以維系者,只有真理之倡耳。真理為究觀的,究觀之乎,愈窘而懷疑愈深,社會愈不足以維系;然則,所欲持以維系社會者,將何待乎?或言以藝術代宗教;謂以藝術代宗教,不啻謂藝術維系社會人心。藝術之足以維系社會人心,中外學者多倡之,無待贅述,今高中課程中獨不標明藝術科而略去之。高中,社會之中堅教育也,是烏乎可?況所謂職業者,師范科亦列為職業一項:師范科之為職業,將助社會之工商、農業而生產歟;抑別,有所職歟!蓋足以直接謀社會之利者,皆得為職業,藝術之足以維系社會,大利于社會也,職業之重要者也。以職業為目的,可不設藝術科歟?竊以為高級中學必設藝術科。[4]
(二)中小學校圖畫科教學廢止臨摹(孫壎提)
該議案理由是:
圖畫一科,在我國覺進步遲緩,歐美則進步較速,其最大原因,多由我國教授圖畫,偏重臨摹,歐美注重自然對象也。例如國畫,其初作者,雖由想象構成,尚不失個性理想的表現,乃他人效而法之,無論臨摹合法與否,已成劃地自限;況犧牲自己的主張,個人的個性真性的修養,理知的探究,尤為不合藝術本性,不明澈藝術原理。今國中藝術界,多能徹底明了此意,已覺前此之非,則當對于中小學校圖畫一科,廢止臨摹,而注重自然對象;蓋從自然對象研究教授結果,覺優點有六:發展個性,其優點一;涵養真的心靈,其優點二;去其依賴,培植起能力自動,其優點三;發覺新的理知,其優點四;得到直覺表現的快感,其優點五;以自然美為根基,則應用變化不窮,其優點六;今因此案覺為重要,特臨時提出。[4]
為此,該議案建議:
(1)用文字發表臨摹繪畫之流弊。
(2)凡會員遇相當時機指導臨畫教員修正教法。
(3)由改進社通函全國教育機關促其注意。
(4)本屆審查成績遇取材臨畫者加以糾正。[4]
(三)組織中華藝術協進社(劉海粟提)
本議案由主席劉海粟提議。汪亞塵、周玲蓀、李毅士、李榮培、雷家駿附議。推舉籌備委員二十人(李毅士、周蓮塘、李榮培、周玲蓀、沈溪橋、唐堯臣、張孟虛、莫運選、雷家駿、李文華、汪亞塵、劉海粟、陳啟民、錢際榮、魏啟宇、黃代國、郝繩祖、雷紹春、周襄南等),雷家駿起草大綱。
中華藝術協進社的宗旨是“聯絡全國藝術團體、藝術家、藝術教育家及從事藝術事業之同志協謀藝術及藝術教育之改進與發展”。
(四)擬請于英國退還賠款(4)1922年12月,英政府宣言:“中國應付未到期之庚款,即將退還中國,作為有益于兩國教育文化事業之用。”自此以后,英國即將中國逐期所付庚款、專款存儲,準備退還。嗣值英國國會改選,內閣變更,因以擱置。迨1925年6月始由其國會正式通過“中國賠款案”。當時英政府以茲款用途及其管理,有先事研究之必要,特成立咨詢委員會;選派調查團來華調查,由威林頓子爵(The Viscount Willingdon)任團長,胡適、丁文江、王景春三博士,及安特孫女士(Dame Adelaide Anderson)、蘇德赫教授(Prof. W. E. Sothill)任團員,于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至6月份分赴京滬平津等處,實地調查,征詢輿論。該調查團之報告書,即為此后中英兩國換文之根據。1930年9月,兩國正式換文,我國政府同意將退還庚款盡數參照咨詢委員會調查團之意見,作為基金借充整理及建筑中國鐵路暨其他生產事業之用,而以其息金用于教育文化事業。詳見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庚款與辦教育經過”,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1575頁。中劃撥一百六十分之一建造美術館(劉海粟、汪亞塵提)
該議案的理由是:
以億萬神明遺胄生聚之區,廣袤達四千余萬里,徒有河山錦繡而無美術館所,寧非大憾乎!在昔美術品深藏于大內之中,珍絕之作,非無可稽,但收集限于一域,觀賞不及平民,龜玉櫝毀,無稗于世;然猶有所萃聚也。今則幾經變革,零落流散,舉數千年發明文藝之品,全付諸無何有之境;非獨無以慰吾民愛美之真,亦且無以發揚國光,上慰先哲也。
邇者,英國有退還庚子賠款,發展我華文化事業之議。友邦之惠我誠深,但所謂文化事業者,乃包含精神與物質而言。茍徒于科術加以助益,而對于足以補救宇宙理智之枯澀,安慰人類生活之興趣者,反無提倡之方,則所謂文化者不過窮功利究物觀之人事耳,不足言文化之全色量也。且我國美術待發揚也,東西美術待溝通也,于此時而謀設美術館所,一部分購備英國美術品,一部分裒集我國舊有美術,合力圖之,可事半而功倍。[4]
為此,該議案建議:
(1)由本社組織統一臨時討論會;討論對于要求英國退還庚子賠款提作購置英國美術品,及我國美術品之各項問題。
(2)討論結果,以本社名義向吾國方面之委員會代表,要求其正式提出此條于退款用途中,將來與英國委員會代表磋商。
(3)由本組推舉代表一人,以備向英國委員會赴華代表要求。
(4)由本組同人分途在各報宣傳此項理由。[4]
(五)各省設立省立美術館(王濟遠、李毅士提)
該議案理由是:
今各省既對于知的方面,而有通俗教育館,體的方面而有公共體育場,考古方面亦間有古物保存所之設,獨于足以培養民情豐富生活之趣之美術館者,付諸闕如。是其所設施率偏于肉體與理智之一方,而無精神上情感之教。夫所謂教育者,乃完全人們之生活,今偏于肉體與理智,生存則有余,生活則未也,能謂社會教育之完全乎。原美術館之設,其效率足以使社會一般受美的熏陶一也;因美的享樂,足以豐富其生活一也;因美的鑒賞,足以引起研究美術者之靈感又一也。他如國有美術之陳列,足以引起一般愛國之念,是又稗于公民教育也;因美術的發揚,而能增進我國之光,是更益于國家之前途也。此外古物保存之有資于歷史考證,工用美術之有關于實業振興,雖其用不顯,亦皆美術館之為功也。今省且無美術館之設,寧非缺陷乎!竊以為省之設美術館,為現時社會教育中急切之務,諸君子其亦以為然耶?[4]
為此,該議案建議:
如經費不充裕,則在原有通俗教育館,擴充美術部。所陳列者以本省范圍以內之美術為主體,其他各地美術為附屬。或在省有學校中附設美術院,公開觀覽。其陳列品以學校美術品為主體,其他為附屬。
如經費充裕,則于省會處特設美術館,并舉行各項美術定期或不定期的展覽。[4]
(六)建議教育行政機關添設藝術學科指導員案(雷家駿提)
議決:交改進社備函致教育部咨各省仿照其他學科指導員成例辦理。
(七)組織中小學校藝術科教學研究會(雷家駿提)
此為一件撤銷議案。議案由原提議人自請撤銷,將來再提出于中華藝術協進社討論辦法。
(八)編輯統一中國美術史案(周蓮塘提)
此為一件保留議案。討論時,多數贊成,故將此案保留。
(九)中小學校藝術科教學應取消編時編班制改為課外自由作業案(莫運選提)
此為一件否決議案。該議案理由是:
現在各初中及小學招收學生每班常自四十人至六十人以上。對于藝術各科,教學時間,大都每科每周中,只有一小時,縱有二小時者亦甚少。既一時聚多數人于一室,在一短時間內,教者學者要來創作一種藝術,當是件難事;況中間還須經過材料之預備,方法之指示,錯誤之改正,及學者創造之程序。任此項教職者,想都同感困難。又許多學校,對于藝術各科,全無相當設備,教者雖有良好計劃,亦將無從著手。[4]
為此,該議案建議:
(1)圖畫、手工、音樂,均須有特別設備的作業室,及教學上相當的設備。
(2)各室須在課外間時,有稍寬裕時間開放。
(3)先須制定一表格,規定學生每周來室作業一次或二次,(多者聽)在表格上作一記號,以防止其自由缺業。
(4)考查成績與課程預定,宜先有計劃,如國畫一學期須作多少畫,手工作多少物件,音樂須唱多少歌,及學多少樂理,可規定經過一學期幾分之幾時間,作完預定課程者,即為本期每科工課完畢。多作者聽,或預作下期功課。
(5)教者須與學者共作,不可任意將作業室啟閉;并且察知學者好尚,予以指導或糾正。
(6)此法如在行道爾頓制(5)道爾頓制(Dalton plan),美國教育家帕克赫斯特20世紀初創行的一種個別化教學形式。其原則主要有兩條:一是自由,即學生在身心方面都能自己計劃自己的事情,自己克制自己的活動,以此培養學生自我教育的能力;二是合作,即打破班級界限,強調團體活動中的合作和交互作用,以使學生在民主合作的氛圍中得到發展。由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馬薩諸塞州道爾頓中學所創行﹐因此得名。之學校,當較此或有更良辦法;但在任何學校都可推行,除教室外,其他都不發生困難。[4]
該議案在組內討論時,雷家駿認為此提案“時機未成熟,各地因經濟人才的關系實行困難;且流弊甚多”,為此“本案無成立之必要”。周玲蓀、李榮培附議,全體會員無異議。最終該提案被否決。
年會召開期間,中華教育改進社還與東南大學教育科、中華職業教育社、江蘇平民教育促進會、中國科學社共同舉辦了全國教育展覽會。陳列室分六區二十余組,分別在東南大學體育館和南京舊貢院展出。美育組分師范教育、中學教育、職業教育組。另外,還有國畫組,分別在東南大學體育館展出。作品包括鉛筆畫、水彩畫、油畫、國畫以及木工、紙工、刺繡等。美育組的主任為劉海粟、周玲蓀,干事為周適、龔心正、周繼善。國畫組的主任為呂鳳子,干事為何龍、孫毓驊、聞鈞天、王霞宙、周貞禾。與此同時,還成立了鑒別委員會。美育組的鑒別委員有:劉海粟、周玲蓀、汪亞塵、華堪、許瑞書、張季信、徐康民、馮澄如。國畫組的鑒別委員有:呂鳳子、蕭庢泉。
1924年9月,《新教育》第9卷1、2合期為南京年會論文專刊,其中美育組刊登了劉海粟《藝術與生命表白》、李毅士《藝術與社會化》、汪亞塵《藝術與社會》三篇論文。
四、第四屆年會美育組會議
1925年8月17日至20日,中華教育改進社第四次會議在山西太原山西大學召開。美育組會議出席的代表有:劉海粟(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校長)、李榮培(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教員)、王濟遠(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授)、金夢疇(浙江第一師范教員)、滕固(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員)、張華(工作單位不詳)、宗孔(工作單位不詳)、張悌(工作單位不詳)。主席為劉海粟、李榮培,書記為王濟遠。會議審查議案五件,最終通過以下四件:
(一)舉辦全國美術展覽會(劉海粟提)
該議案理由是:
各國有國家美術展覽會,有團體或個人之美術展覽會。政府獎勵于前,國民奮起于后。以故審美教育之宣化,疾如風電,豈徒以空言而能致今日之效哉?反觀我國,寂然罕有聞焉。間有一二團體或私人羅列作品舉行展覽會,作品既不多,而為效亦僅局促于一隅,滋可憾焉。近者國人漸感藝術之尊貴,而莫有晉接之機會,則全國美術展覽會之舉辦,實為當務之急也。尤有進者,國人雖知藝術之尊貴,而其尊貴所在,猶屬茫然。制作者不自策勵,故步自封;鑒賞者認識力弱,看朱成碧。此審美教育上大障礙,是以救藥此種弊病者,厥有待于展覽會。則全國展覽會之舉辦,誠不容或緩矣。[5]
為此,該議案建議:
(1)征集、陳列、審查,俱組織委員會。
(2)由中華教育改進社呈請政府撥給經費。
(3)定期展覽在北京、上海二處舉行。不定期展覽,在各大埠舉行之。
(4)出品范圍國畫、洋畫、雕刻三部。
(5)展覽會出品人按其作品之等列分別給獎。[5]
代表們一致同意組織籌辦全國美術展覽會委員會,并推舉李榮培、金夢疇、熊連城、王濟遠、蔡元培、李祖鴻、汪亞塵、張華、宗孔、張悌、任恒德、王悅之、滕固、俞寄凡、錢稻孫、王敬章、劉海粟等十七人為委員會委員。
8月20日下午,在山西大學舉行了第一次談話會(籌備會),到會者有劉海粟、滕固等八人,公推劉海粟為主席。討論結果:第一,全國美術展覽會組織大綱起草員公推劉海粟、滕固、王濟遠、李榮培、熊連城擔任。第二,由本組正式具函本社報告情形請董事部速籌經費。第三,全國美術展覽會預定明年在武昌舉行,如有機會,運往各省輪流陳列。
(二)籌設國民美術館(劉海粟提)
該議案理由是:
近年來國內文藝界之先驅者,盛唱新文藝。國人對于藝術之制作力與鑒賞力,雖漸次提高,而無由接近世界藝術巨制之機緣,因此不能療治其心靈之饑渴,誠為憾事。夫欲搜集世界藝術巨制,縱有財力,縱有時間,而此貴重之世界的無雙品又寧堪以財力時間為代價,咄嗟立致耶?矧財力時間今猶難言,則國民美術館終無實現期矣。近年德國印行之世界名畫,自文藝復興以還,各國美術館貯藏名跡搜羅無遺,而形式一如原本,茲擬募款購置,建館陳列。益以中國古今名作,蔚為巨觀。茲事易舉,期以必成。[5]
為此,該議案建議:
(1)由中華教育改進社募集金額四萬,組織委員會辦理之。
(2)以一萬元購德國所印文藝復興以還各國美術館名跡。
(3)以一萬元購置中國美術名作。
(4)以二萬元建筑館舍。
(5)地點在上海,因上海既無古代建筑可觀瞻,又為商工競爭之地,最非藝術的,須以為冥眩之藥。[5]
(三)組織中華古美術品調查委員會(李榮培提)
議案通過并議決:請原議案人起草中華古美術品調查意見書,由本組函請各省圖書、博物館、古物陳列所、美術學校以及其他美術機關,就各所在地組織古美術品調查委員會,隨時隨地,調查報告本組,匯印成書,以為中國美術史之草創。[5]
(四)請山西省政府保護大同云岡石佛寺案(張華、張悌、任恒德、宗孔四人提)
該議案理由是:
大同云岡之石佛,不但為中國美術史上之偉跡,抑亦世界之偉跡,國人向未注意及此。而東西人士,斤斤考據,不憚煩苦,良有以也。是寺實為天然之美術館,而居民不察,不加保存,以致剝蝕零落,時加涂塑,浸失原有精神,殊非尊重國寶之意。故請本地長官,嚴加保護,藉久流傳。
議案通過并議決:由本組具公函請本地長官嚴加保護。[5]
(五)藝術教育宗旨應趨重平民主義(龍文提)
此為一件保留議案。
五、美育組會員為美感教育所作出的努力
有關中華教育改進社美育組的會議議案,舒新城在1929年編寫的《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中曾有過研究和總結,他認為,“十一年(即1922年)集合全國教育界人士于一爐的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都有美育組,每次均有提案若干。雖然該會每次都只在集合若干教育者為蜂哄的討論不注意于實際的設施,但十一年以后,美感教育思想發展的情形,卻可于其提案之言論中見之”。他還認為:“自十一年至十四年的四年間,教育改進社年會關于美育之提案二十件,通過者十六,其思想的傾向可別為三大類:第一類為普及:即于普通教育中盡量推行美感教育,于一般社會上設置美術館及開美術展覽會等;……第二類為應用:即使美術應用于實際生活及各種工藝上,……第三類為存古:即設立機關保存中國固有之藝術品。”[6]195舒新城對中華教育改進社美育組會議議案的歸納和總結是準確的,但是他說當時教育者“蜂哄的討論”,“不注意于實際的設施”,這或許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
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之時,中國正處在北洋勢力分裂為直、皖、奉三系,三系矛盾日益激化,軍閥混戰時期;再加之后來的北伐戰爭,因此政治時局不穩,經費缺乏是使許多議案無法實際設施的主因。但是,美育組在蔡元培的關心下畢竟集合了如劉海粟、鄭錦、滕固、汪亞塵、俞寄凡、王濟遠、王悅之、李毅士、陳衡恪、雷家駿、劉質平等國內藝術教育界一批著名藝術家和學者,甚至還有像錢稻孫(6)錢稻孫(1887—1966),浙江吳興人。翻譯家、作家、教育工作者。在語言、文學、音樂、戲劇、美術、醫學等方面有精深的造詣,精通日語、意大利語、德語、法語。曾譯《神曲》《萬葉集精選》等。、高鴻縉(7)高鴻縉(1892—1963),字笏之,湖北沔陽人。著名古文字學家、教育家、書法家。畢業于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英語部。1923年春奉派美國舊金山任中國代表團代表,出席第一屆世界教育會議。后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教育。1947年赴臺灣省立師范學院講學,1961年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大學。、黃公覺(8)黃公覺,廣西桂林人,我國著名法學家、翻譯家。1924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政治碩士學位,1931年回國,獲法學博士和政治碩士學位。曾任廣西大學政治系主任,著有《嘉木氏之美育論》《中國制憲史》《比較憲法》,譯著《飛龍演繹》《性教育》等。等這些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們“未嘗因政局之紛擾而離散”“同具教育救國之信心”[7]為普及美育提高國民的藝術素養而努力。現將美育組會員為普及美感教育所作出的努力歸納如下:
(一)參與中小學音樂、圖畫課程綱要的制訂
1923年6月4日頒布的《小學音樂課程綱要》《初級中學音樂課程綱要》《小學形象藝術課程綱要》《初級中學圖畫課程綱要》,是由全國教育聯合會組織“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聘請劉質平、劉海粟、俞寄凡、何元、宗亮寰制訂的。其中劉質平、劉海粟和俞寄凡都是中華教育改進社美育組的成員。這些綱要具有許多開創性之處:
其一,首次將“欣賞”一項,作為中小學圖畫學科的學習內容列在了課程綱要之中,并指出:“欣賞一項,向來大家不甚注意。但在普通教育的美育上很為重要。我國社會欣賞美術的程度很低,學校中應該特別注意。所以學校宜設法多備些美術品,使兒童時常欣賞。”[8]194音樂學科強調“涵養美的情感與融和樂群的精神”[8]17。
其二,首次將圖畫學科的教學內容和方法作了規定。中學階段教學內容和方法有:理論、觀察、實習三個方面。其中理論,主要教授有關色彩、透視、素描等方面的基本理論。觀察,要求學生觀察自然物和人造物的色彩、紋樣、形狀等,甚至還要求學生參觀美術展覽會、工藝展覽會,來研究現代美術作品。實習,主要讓學生進行一些美術技能方面的訓練。
其三,首次將西方美術教育中有關透視、人物畫、色彩、素描、圖案畫知識以及構圖與美的法則等理論,系統地寫入中小學圖畫課程綱要之中,奠定了中小學美術學科的理論知識體系。
其四,首次制訂了針對中小學生畢業時,音樂、圖畫學科應達到最低限度的標準。
總之,1923年頒布的中小學音樂、圖畫學科課程綱要對我國中小學音樂、美術教育發展,所起的影響和促進作用不容低估,在中國近現代中小學藝術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9]
(二)高中開設了音樂和圖畫科
1923年由鄭錦提議的“各省高級中學起首至少有美術工藝科或學校兩處續年增設案”,以及1924年由李文華提議的“高級中學必設藝術科”議案,終于在1932年得到落實。這年,教育部頒發了《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和《高級中學圖畫課程標準》,標志著自清末癸卯學制規定中小學開設音樂和圖畫科后,我國高中也開始有音樂和圖畫科了。高中音樂科的培養目標強調“增加鑒賞音樂之程度”,“涵養諧和、優美、剛強、沉著之情感,并發揚仁愛、和平、勇武、壯烈等之民族精神”。[8]33高中美術科的培養目標主要強調“繼續培養美的德性與興趣”,“培養表現思想感情之創作能力,以促進新生活之實現”。[8]214
(三)參與教科書的編寫
1924年7月至1930年12月,劉海粟應商務印書館的邀請編寫出版6冊《新學制圖畫教科書》。劉海粟在此套教科書的“述意”中指出:“迄今國內一般中學校每周所授兩小時之圖畫科,也總不外是拿些花鳥、山水的舊稿子,或所謂圖畫范本,使學生臨摹一下;或有剽竊些俗臭的西洋畫片,間接為學生臨摹者,即自許為推陳出新的了。不僅使學生干燥無味,且大背藝術教育之本旨,抑亦大背教育目的。年來天下樂道圖畫應當寫生,不追窮其所自標的,只知隨波逐流,掇拾一二,且欲從而實施于學校課程,亦復何益于事。”為此,他認為:“初中圖畫科的教學主旨是:1.增進鑒賞知識,使能領略一切的美,并涵養精神上的安慰愉快,以表現高尚人格。2.練習制作技藝,使能發表美的本能。3.養成一種藝術,而為生活之助。”[10]
1933年7月至1934年4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濟遠編寫的6冊《復興初中圖畫教科書》。王濟遠在該書的“編輯大意”中指出:本書主要“使學生了解藝術與人生之關系。對于東方繪畫之特殊優點一再闡發,表揚中華民族固有之文化,并采用歐西繪畫之技術與原理,合乎世界潮流,貫通時代思想。”并認為:“本書啟迪學生審美本能,注意藝術之應用,養成學生健全之思想與技能。”[11]
1934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濟遠編寫的3冊《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圖畫》。王濟遠在該書“編輯大意”介紹:“本書取材,務切實際,以期美化人生,使學者了解藝術與國民及其與工業之關系。”此外書中還有“各欣賞圖,尤為中西畫哲杰作,用作鑒賞,使學者得認知繪畫之極致”。[12]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中圖畫課程標準沒有頒布之前,在南京東南大學附屬中學教書的周玲蓀于1924年2月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水彩風景畫》。他在“編繪大意”指出:“新學制高級中學,概取分科選課制度,俾得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庶學者可得事半功倍之效。而圖畫一門,亦為高中普通科選修課之一。”[13]從中可見,當時某些地區的普通高中課程里圖畫已作為選修課的了。
(四)舉辦展覽會
1925年5月26日,中華教育改進社美育組及江蘇省教育會美術研究會在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三洋涇橋(今延安東路江西中路之間)安樂宮舉辦“中國現代名畫家近作展覽會”,展出十天。陳列吳昌碩、王一亭、曾農髯、劉海粟、許醉侯、吳臧庵、王陶民、錢瘦鐵、吳杏芬、楊雪玖、胡偉平等十余人書畫三百件。[14]629
1922年和1925年,劉海粟提議舉辦全國美術展覽會的議案,經過多年努力,于1929年4月10日在上海南市國貨路新普育堂隆重開幕。據《上海美術志》介紹:
當時中外來賓千余人,于軍樂聲中魚貫入場,由熊式輝夫人揭幕,教育部次長馬敘倫致開幕詞,總干事孟壽椿報告籌備經過。新普育堂為上海有數之大建筑,曾作國貨展覽會場,分東西兩樓各有三層。下層為美術印刷局,并分設書畫商店、飲食店,東樓二層為西畫部、美術工藝部、建筑攝影部,三層為參考品陳列部。西樓二、三層均為中國畫。中樓為雕塑部。各室布置均別出心裁。計陳列國畫1300余件,西洋畫600余件,參考品展覽部則陳列我國各時代各家平生精品。至28日起,參考展覽部又作專題美術展出,第一日展出石濤精品,第二日展出八大山人精品;第三日展出唐宋元明各家精品;同時陳列古銅器珍品。展覽會出版《美展》三日刊,由徐志摩、陳小蝶、楊清磬、李祖韓編輯。材料豐富,每期八頁,除文字外又銅版畫三十余幅,刊出均為展品中之精美者。共出十期。會場又有專場國樂演奏,更有劇場演出,請尚小云、小翠花、俞振飛、楊寶忠、吳老圃等串演《梅龍鎮》等名劇。藝術氣氛濃郁,展至30日閉幕。展出以來,本市和各省市機關團體、學校學生、工商各界人士以及歐美日等國外賓、記者絡繹不絕參觀,共近十萬人,盛極一時。[14]644
另據1929年4月11日的《申報》報道,全國美術展覽會第二日,蔡元培、何香凝、陳樹人等也來參觀。[15]
六、結語
據舒新城的研究,自民國初年蔡元培提出美感教育之后,雖然“蔡元培十余年來常有提倡的美育的文章發表,但在五四以前,社會上竟少反應”。[6]1981922年之后,由李石岑主編的《教育雜志》“以提倡美育為唯一的職志”[6]195,于是美育才蔚成一種思潮。中華教育改進社是把改進和發展整個教育事業作為自己的宗旨,“對中國教育之改進,功績甚大”[16],可以這么說,中華教育改進社美育組為20世紀20年代美感教育思潮的傳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