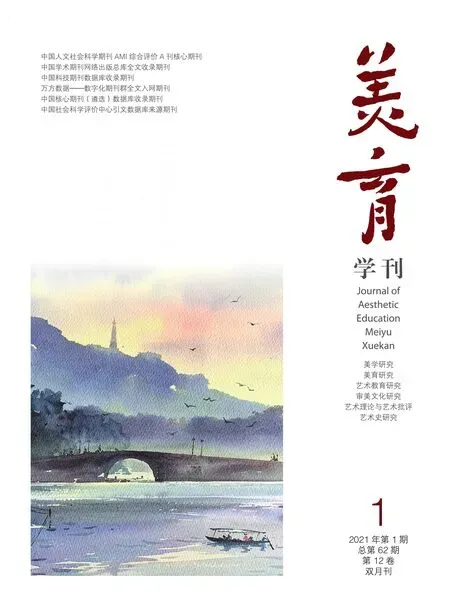巫鴻美術(shù)史研究的空間性內(nèi)涵
王同森,李慶本
(杭州師范大學(xué) 藝術(shù)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傳統(tǒng)美術(shù)史視閾下的“武梁祠”研究
長(zhǎng)期以來美術(shù)史研究主要以時(shí)間、歷史為線索探索藝術(shù)發(fā)展過程中形式和風(fēng)格的變化,“圖像”和“形式”也是傳統(tǒng)美術(shù)史研究中的兩個(gè)核心概念。早在16世紀(jì),意大利批評(píng)家瓦薩里將藝術(shù)的發(fā)展視為進(jìn)步的、線性的演進(jìn)過程,雕塑、繪畫、建筑這些藝術(shù)門類都會(huì)經(jīng)歷出生、成長(zhǎng)、衰老和死亡四個(gè)階段。瑞士學(xué)者沃爾夫林通過比較文藝復(fù)興鼎盛時(shí)期和17世紀(jì)的藝術(shù)得出了著名的五對(duì)反題概念:線描的和圖繪的,平面的和縱深的,封閉的和開放的,多樣統(tǒng)一和整體統(tǒng)一,清晰性和模糊性。他從觀看的歷史來分析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藝術(shù)和巴洛克藝術(shù)的不同視覺特點(diǎn)。在沃爾夫林看來由于風(fēng)格具有不斷變化發(fā)展的內(nèi)在傾向,這五對(duì)概念也適用于視覺藝術(shù)的所有媒介。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xué)研究”將圖像學(xué)的方法分為“前圖像志描述”“圖像志分析”“圖像學(xué)解釋”三個(gè)層次,重點(diǎn)研究了圖像題材、象征含義與文化意義。
在《武梁祠》中巫鴻花了大篇幅對(duì)過往的“武梁祠研究”做了梳理,巫鴻發(fā)現(xiàn),“以往對(duì)漢畫的分析往往多在高低兩個(gè)層次上進(jìn)行。低層研究專注于對(duì)單獨(dú)畫像的形式、內(nèi)容分析,而高層研究則宏觀漢畫的發(fā)展以及與社會(huì)、宗教、意識(shí)形態(tài)的一般性關(guān)系”[1]。這里所指的“低層研究”與“高層研究”實(shí)際上因循了傳統(tǒng)美術(shù)史對(duì)“形式”和“圖像”的關(guān)注。
在武梁祠內(nèi)的石刻畫像拓片被帶入歐洲后,西方的藝術(shù)家站在藝術(shù)史的角度對(duì)武梁祠石刻畫像展開了研究。最為典型和最能代表早期西方對(duì)中國藝術(shù)形式理解的要屬“形式分析”的美術(shù)史研究方法。威廉姆·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在《大英博物館圖錄》(DescriptiveandHistoricalCatalogueofaCollectionofJapaneseandChinesePaintingsintheBritishMuseum)中將中國藝術(shù)風(fēng)格概括為:“(一)書法式的描繪,重輪廓線和筆觸而不重對(duì)形體的科學(xué)觀察。(二)等距透視。雖然少數(shù)中國畫和佛教繪畫表現(xiàn)了平行線向焦點(diǎn)的聚合因而顯示出對(duì)線性透視系統(tǒng)的幼稚理解,這些作品中焦點(diǎn)的位置總是錯(cuò)誤的、對(duì)距離的處理也反映出畫者缺乏明智的觀察力。”[2]柏克豪夫(Ludwing Bachhofer)在總結(jié)中國繪畫發(fā)展規(guī)律時(shí)將繪畫發(fā)展的規(guī)律概括為二維空間繪畫向三維空間繪畫的演進(jìn)。其基本邏輯仍舊是從進(jìn)化論的視角來總結(jié)中國古代繪畫形式的內(nèi)在發(fā)展規(guī)律。在形式分析的美術(shù)史研究下,“空間”被視為一種藝術(shù)技法附屬于繪畫的視覺形式。而形式分析是在西方架上繪畫研究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這種形式分析暴露出的某種西方中心主義傾向顯然是無法正確解釋和揭示中國古代繪畫藝術(shù)的豐富內(nèi)涵的。
索珀(Alexander Soper)在武梁祠石刻畫像研究中將漢代藝術(shù)區(qū)分為王都和外省兩種風(fēng)格,認(rèn)為“武氏祠浮雕代表了一種特殊的藝術(shù)風(fēng)格”[3]64。時(shí)學(xué)顏(Hsio-yen Shin)同樣注意到外部地緣空間對(duì)藝術(shù)風(fēng)格形成產(chǎn)生的影響,她以形式分析為準(zhǔn)則考察了不同地域的漢畫像石,認(rèn)為不同地區(qū)之間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在相互借鑒影響的情況下,逐漸掌握了如何在二維空間上進(jìn)行圖像表現(xiàn)的方法。“對(duì)她來說,通過對(duì)風(fēng)格的形式分析,學(xué)者可以把包括武氏祠在內(nèi)的所有時(shí)間、所有地區(qū)的畫像組群排列在一條空間意識(shí)不斷覺悟及圖像化的鏈條中。”[3]66索珀與時(shí)學(xué)顏雖然顯示出了對(duì)地緣空間的關(guān)注,但是武梁祠石刻畫像的藝術(shù)形式被置于“時(shí)間”向度加以考察,不同地緣環(huán)境下的視覺表現(xiàn)形式仍然被視為是線性的、發(fā)展的、進(jìn)化的。而中國古代繪畫藝術(shù)這種空間表現(xiàn)的獨(dú)特性則被忽略掉,被簡(jiǎn)單歸納到西方美術(shù)史研究的傳統(tǒng)之下。
除了對(duì)武氏祠石刻畫像形式特質(zhì)的關(guān)注,學(xué)者們對(duì)畫像的內(nèi)容及其社會(huì)性和思想性也展開了研究。這就是巫鴻所謂的“高層研究”。在對(duì)圖像的分析中“歷史特殊論”成為主流的研究方向,“持這種觀點(diǎn)的人認(rèn)為漢代墓葬和祠堂畫像中的母題和畫面表現(xiàn)的一定是某些特定歷史人物和事件、與墓主的生活、思想或背景密切關(guān)聯(lián)”[3]69。如眾多學(xué)者將“水陸攻戰(zhàn)圖”“出行圖”中的主人公視為墓主人生前的經(jīng)歷。而勞弗(Berthold Laufer)則認(rèn)為武氏祠內(nèi)的石刻畫像大量重復(fù)了先前社會(huì)中廣為流傳的圖像主題,圖像的內(nèi)容并非專指墓主人的生前經(jīng)歷。在其后的數(shù)年間不斷出土的漢代石刻畫像也證實(shí)了勞弗的觀點(diǎn)。另一些學(xué)者則以象征主義的解釋方法對(duì)武梁祠內(nèi)的石刻畫像進(jìn)行了新的解釋。持這種觀點(diǎn)的學(xué)者認(rèn)為石刻畫像的真正含義在于其內(nèi)涵的潛在意見,因而漢代畫像背后的生死觀、文化觀則成為了研究者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他們更注重對(duì)漢代歷史文化環(huán)境的考察。巫鴻舉了多理斯夸松(Doris Croissant)在1963年以德文寫成的博士論文的論證,多理斯·夸松認(rèn)為漢代祠堂和墓葬裝飾不僅象征著死者在另一世界的宮室,也象征著一種英雄崇拜。無論是“歷史特殊論”還是“象征主義”的研究方法,無疑都是用西方美術(shù)史研究方法來審視中國古代石刻畫像。藝術(shù)外部的社會(huì)、文化、政治空間受到關(guān)注,但畫像藝術(shù)形式本身以及藝術(shù)與藝術(shù)外部空間的特殊關(guān)系被忽略掉,歷史活動(dòng)、社會(huì)藝術(shù)文化觀念被簡(jiǎn)單壓縮為抽象的概念。
對(duì)武氏祠石刻畫像的研究從簡(jiǎn)單的通過榜題對(duì)圖像進(jìn)行闡釋,不斷發(fā)展為經(jīng)由圖像向整個(gè)漢代祠堂墓葬裝飾藝術(shù)風(fēng)格和漢代文化環(huán)境的“延伸”。“對(duì)漢畫像藝術(shù)的研究基本上從一元發(fā)展到多元,人們逐漸認(rèn)識(shí)到漢畫像藝術(shù)的分布地域是多元的,發(fā)展也是多元的。”[4]但在傳統(tǒng)美術(shù)史視域下,對(duì)武梁祠石刻畫像的研究主要在“低層”或“高層”進(jìn)行,圖像的視覺表現(xiàn)形式被置于“空間意識(shí)”不斷覺醒的線性鏈條,而“圖像學(xué)”的分析方法將武梁祠內(nèi)的圖像視為漢代藝術(shù)文化觀念的直接反映。這種研究范式脫胎于西方傳統(tǒng)美術(shù)史研究,并將西方藝術(shù)傳統(tǒng)作為先例來衡量中國古代藝術(shù),這種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美術(shù)史研究方法忽視了中國古代藝術(shù)的獨(dú)特性。
二、武梁祠的建筑空間與圖像程序
武梁祠石刻畫像的豐富性和復(fù)雜性顯示出中國古代繪畫有著獨(dú)特的藝術(shù)追求,西方傳統(tǒng)美術(shù)史研究的方法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武梁祠石刻畫像的藝術(shù)價(jià)值。為了更為準(zhǔn)確地把握武梁祠石刻畫像的藝術(shù)內(nèi)涵,巫鴻在實(shí)際研究中采取了“中層研究”(1)“中層研究”的方法與社會(huì)學(xué)研究所關(guān)注的“中層結(jié)構(gòu)”有著關(guān)聯(lián)性,“中層結(jié)構(gòu)”的理論源于20世紀(jì)下半葉的美國社會(huì)學(xué)研究,社會(huì)學(xué)家彼得·伯杰在《權(quán)力下放:中層結(jié)構(gòu)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Empower People: The Role Of Mediating Structures in Public Policy)中認(rèn)為“中層結(jié)構(gòu)”是介乎個(gè)人生活(微觀構(gòu)成)和社會(huì)(宏觀構(gòu)成)之間具有的共同性結(jié)構(gòu)。的方法。“中層研究”即“專注于代表性的墓葬、享堂或塋域,細(xì)致分析題材的選擇、題材之間的聯(lián)系,以及裝飾部位的意義”[1]。與注重單獨(dú)畫像形式內(nèi)容的“低層研究”和宏觀把握漢畫發(fā)展與宗教、意識(shí)形態(tài)的“高層研究”不同,“中層研究”不僅能夠把握特定題材在墓葬空間的特殊意義,而且也能夠揭示畫像與墓主人思想、漢代藝術(shù)風(fēng)格等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系,“中層研究”打通了實(shí)存的武氏祠石刻畫像與漢代社會(huì)文化的聯(lián)系,而在提出這個(gè)研究方法時(shí)巫鴻主要考慮的是漢代畫像石的組合及結(jié)構(gòu)因素。
與過去專注于單個(gè)武梁祠圖像研究的方法不同,巫鴻在著手分析武梁祠石刻畫像之前首先對(duì)武梁祠的建筑空間結(jié)構(gòu)以及圖像風(fēng)格進(jìn)行了考古發(fā)掘式的清理。費(fèi)慰梅在《漢武梁祠建筑原形考》(TheOfferingShrinesof“WuLiangTz’u”)中指出:“當(dāng)這些石刻被當(dāng)作散落的石板或拓片來研究時(shí),它們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和位置意義就失去了。對(duì)石刻畫像原有位置的把握能夠解除目前研究題材方面遇到的障礙。”[5]費(fèi)慰梅試圖重新建構(gòu)起武梁祠的建筑空間,并將整套圖像置于武梁祠最初的建筑空間中進(jìn)行考察。巫鴻認(rèn)同費(fèi)慰梅對(duì)“畫像原有位置”的關(guān)注,并認(rèn)為武梁祠原有的建筑空間結(jié)構(gòu)是整套畫像實(shí)存的物質(zhì)載體,只有將整套畫像放置在武梁祠完整的空間單元中才能真正理解圖像的意義。如此一來對(duì)武梁祠建筑空間結(jié)構(gòu)的“重構(gòu)”是研究武梁祠畫像的重要一環(huán)和先決條件。通過對(duì)武梁祠保存的實(shí)存材料和圖像配置的細(xì)致分辨,在復(fù)原后的武梁祠空間結(jié)構(gòu)內(nèi)部,巫鴻發(fā)現(xiàn)了祠堂內(nèi)整套畫像的程序結(jié)構(gòu)。屋頂對(duì)應(yīng)上天征兆;山墻對(duì)應(yīng)西王母和東王公的神仙世界;墻壁對(duì)應(yīng)三皇五帝、貞婦孝子、忠臣義士的人間歷史。巫鴻并沒有直接將西方美術(shù)史作為衡量武梁祠石刻畫像的先例,而是致力于重構(gòu)武氏祠石刻畫像的“歷史原境”(historical context)。這樣的原境首先顯示為武梁祠特定的“建筑空間”和“圖像程序”,對(duì)武梁祠原初建筑空間結(jié)構(gòu)的復(fù)原也是在重構(gòu)武梁祠石刻畫像的具體存在空間,進(jìn)而在“歷史原境”中考察整套圖像的內(nèi)容指向。
藝術(shù)史研究中的重構(gòu)不僅包含建筑的,也包含禮儀的和宗教的各種層面的內(nèi)容。中層研究不僅關(guān)注武梁祠原初的建筑空間,而且非常注重武梁祠石刻畫像圖像程序的內(nèi)在邏輯以及背后的禮儀、宗教等外部因素。巫鴻在《武梁祠》中具體考察了漢代山東嘉祥縣的宗教禮儀和社會(huì)文化觀念,通過將武梁祠整套圖像內(nèi)容放置在漢代社會(huì)的思想模式中,巫鴻發(fā)現(xiàn),“武梁祠祥瑞圖像及相關(guān)榜題揭示出一種流行于漢代,將某些特定自然現(xiàn)象解釋成上天意愿的思想模式。這種思想方式與漢代建立在天命論基礎(chǔ)上的政治體系息息相關(guān)”[3]103。巫鴻又進(jìn)一步對(duì)祥瑞圖像進(jìn)行分析,發(fā)現(xiàn)武梁祠內(nèi)的祥瑞圖像與武梁碑銘存在著相互對(duì)應(yīng)的聯(lián)系,武梁祠祥瑞圖像的選擇體現(xiàn)著這位退隱的韓詩學(xué)派儒生對(duì)歷史社會(huì)的認(rèn)識(shí)以及對(duì)政治的看法。通過對(duì)漢代歷史觀的梳理和武梁祠墻壁上整套圖像程序的分析,巫鴻認(rèn)為武梁祠畫像與漢代流行的歷史觀又存有極強(qiáng)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墻壁上的古帝王像與《史記》中的《本紀(jì)》相呼應(yīng),烈女、刺客與《列傳》有著同樣的內(nèi)在原則,而被認(rèn)為是象征武梁本人的“處士車”則被認(rèn)為與《史記》中的“太史公曰”有著對(duì)應(yīng)聯(lián)系。總之,“同樣的尋求和描述歷史模式的愿望激發(fā)了武梁祠畫像石的創(chuàng)作,司馬遷的歷史等級(jí)結(jié)構(gòu)為其設(shè)計(jì)者提供了藍(lán)本”[3]171。
巫鴻通過中層研究的方法重構(gòu)起武梁祠建筑空間,并在具體的“歷史原境”中發(fā)現(xiàn)了武梁祠石刻畫像的圖像程序及石刻畫像與漢代藝術(shù)文化觀念等外部因素的關(guān)系。與注重線性時(shí)間內(nèi)藝術(shù)形式發(fā)展的形式分析不同,巫鴻更加注重武梁祠石刻畫像在特定空間單元中的表現(xiàn)及圖像程序隱含的漢代藝術(shù)文化觀念,也避免了將具體歷史活動(dòng)簡(jiǎn)單概括為抽象概念。
三、武氏祠石刻畫像的空間與再現(xiàn)
20世紀(jì)90年代興起的以社會(huì)學(xué)為主導(dǎo)的美術(shù)史研究方興未艾,但巫鴻始終非常看重傳統(tǒng)美術(shù)史研究中“形式分析”的研究方法,他對(duì)“以‘視覺文化’替代‘美術(shù)史’的趨向持有更為審慎的保留態(tài)度”。[6]巫鴻的美術(shù)史研究始終緊扣實(shí)存圖像的“歷史物質(zhì)性”(historical materiality),即“即藝術(shù)品原來的面貌和構(gòu)成及其體質(zhì)和視覺的屬性”。[7]在對(duì)“實(shí)物”(actual objects)關(guān)注的基礎(chǔ)上,巫鴻重新發(fā)掘了傳統(tǒng)美術(shù)史研究中“形式分析”和“圖像學(xué)”包含的“空間”問題,并將“空間”視為解讀武氏祠石刻畫像的新途徑。
武梁祠內(nèi)的石刻畫像拓片被帶到歐洲后,引起了眾多西方美術(shù)史家的關(guān)注。由于武氏祠石刻畫像主要以正、側(cè)形象為主,西方美術(shù)史家以二維空間繪畫到三維空間繪畫的演進(jìn)為準(zhǔn)則認(rèn)為中國古代這個(gè)時(shí)期的繪畫尚未擁有對(duì)“空間”表現(xiàn)的自覺。但通過研究考證,巫鴻發(fā)現(xiàn)武梁祠內(nèi)的繪畫并非是不懂得如何正確把握“空間”透視繪畫技法的使用,“漢畫的目的并不在于重構(gòu)人類真實(shí)視覺經(jīng)驗(yàn)中的三維空間,而在于通過圖像傳達(dá)畫者希望傳達(dá)的特定信息”。[8]索珀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武梁祠內(nèi)的一些石刻畫像已經(jīng)顯露出了一些創(chuàng)新性和更為進(jìn)步的風(fēng)格。在“荊軻刺秦王”的圖像中,三個(gè)人物互相疊壓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了空間層次。但索珀認(rèn)為武梁祠的畫像“幾乎完美的平面再現(xiàn),缺乏背景,對(duì)半側(cè)面表現(xiàn)方法一無所知”[3]64。索珀仍然是站在“進(jìn)化論”的角度來審視武梁祠石刻畫像,并將石刻畫像內(nèi)出現(xiàn)的這種創(chuàng)新性風(fēng)格歸結(jié)于不同的地域分布和藝術(shù)文化傳統(tǒng)觀念。巫鴻則通過對(duì)武梁祠屋頂上石刻畫像的考察,發(fā)現(xiàn)屋頂上所刻的祥瑞圖像都是剪影般出現(xiàn)在空白的背景上。眾多的祥瑞圖像以二維的空間表現(xiàn)排成幾個(gè)平行的長(zhǎng)列,設(shè)計(jì)者避免了疊壓和覆蓋這種能夠形成圖像縱深的做法,而是力求清晰明了地刻畫出所表現(xiàn)的祥瑞圖像輪廓。“這種概念式的表現(xiàn)可能是將征兆視覺化以便作為圖像‘索引’之用的最佳方式,‘自然主義’的表現(xiàn)方式反而會(huì)削弱這些圖像幫助人們判斷征兆的作用。”[3]102同樣,通過觀察分析武梁祠中的九幅孝子圖也可以發(fā)現(xiàn),在這些雕刻中“人物形象的形似讓于道德教化的目的”[9]353。由此可以見出武梁祠祥瑞石刻畫像表現(xiàn)的是抽象的類型,關(guān)注是圖像的功能,而這種剪影式的視覺感知及再現(xiàn)手段能夠最大程度上將圖像功能清晰、完整地展示出來。顯然設(shè)計(jì)者并非是出于對(duì)“空間”運(yùn)用的不成熟,“他所關(guān)心的并不是空間的統(tǒng)一性”。[9]28武梁祠石刻畫像的“視覺空間”并沒有被納入“空間意識(shí)”不斷覺醒的形式主義進(jìn)化論中,這種空間表現(xiàn)模式的淵源、目的性和修正邏輯顯示出漢代畫像藝術(shù)有著與西方藝術(shù)傳統(tǒng)不同的藝術(shù)趣味追求,而視覺空間的切入為理解和揭示武梁祠石刻畫像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視角。
武氏祠后壁及左壁的第一層裝飾帶上包含了七幅基于《列女傳》描述而創(chuàng)作的繪畫,每幅畫面都表現(xiàn)了一個(gè)女子貞潔的故事。在武梁祠內(nèi)的“列女”系列故事中,“梁高行”的事跡被刻在前面的位置。“梁高行”并非畫像中女子的真實(shí)姓名,而只是代指品行極高的梁國女子。梁王聞得梁高行的美貌便派人前去聘迎,但是梁高行不愿意因利益放棄信義,她為了表現(xiàn)自己堅(jiān)守貞潔的信念于是就用刀割掉了自己的鼻子。通過對(duì)梁高行圖像內(nèi)容的分析,巫鴻認(rèn)為武氏祠的設(shè)計(jì)者是有意將這個(gè)故事置于列女系列故事的首位,因?yàn)槿寮医?jīng)典的首章通常被認(rèn)為具有特殊的意義,作為韓詩學(xué)派一員的武梁本人對(duì)武梁祠畫像的設(shè)計(jì)也體現(xiàn)了這樣一種選擇,希望宣達(dá)梁高行“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10]。如果說在《武梁祠》的研究中巫鴻對(duì)“梁高行”的解讀主要關(guān)注的是武氏祠石刻畫像與武梁祠設(shè)計(jì)者本人選擇間的關(guān)系,那么巫鴻在后來的研究中又進(jìn)一步分析了“梁高行”圖像所展示的“女性空間”。“梁高行”畫像并沒有代表具體位置的宮室建筑,圖畫與其他“列女圖”相比更為簡(jiǎn)潔。但巫鴻認(rèn)為“通過隱去具體的房屋形象,畫面中的女性空間脫離了對(duì)外在建筑的依賴而轉(zhuǎn)化為構(gòu)圖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在更深的層次上控制著對(duì)人物關(guān)系的視覺表現(xiàn)”[11]。
潘諾夫斯基指出,“當(dāng)藝術(shù)家投身研究一件或一系列作品時(shí),他必須把他所認(rèn)為的這些作品的內(nèi)在含義,與他可能盡量掌握、并認(rèn)為與這些作品具有歷史關(guān)系的其他所有文化資料的內(nèi)在含義加以對(duì)照”[12]。巫鴻則認(rèn)為武氏祠石刻畫像顯示出的社會(huì)、宗教、政治文化觀念是在空間結(jié)構(gòu)層面與圖像發(fā)生關(guān)系的。巫鴻對(duì)武氏祠石刻畫像的分析沒有直接將宏大的漢代藝術(shù)文化、宗教背景引入,而是著眼于武氏祠石刻畫像的空間與再現(xiàn),并將圖像建構(gòu)起來的結(jié)構(gòu)性聯(lián)系視為“空間”的重要內(nèi)涵,通過對(duì)具體石刻畫像的空間分析來研究圖像所傳達(dá)出的內(nèi)在含義。
結(jié) 語
巫鴻美術(shù)史研究的“空間轉(zhuǎn)向”是在傳統(tǒng)美術(shù)史研究方法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空間”問題在傳統(tǒng)美術(shù)史研究中已經(jīng)受到關(guān)注,如“圖像空間”和“視覺空間”就是沿著“圖像”與“形式”的研究方法發(fā)展出來的。但“空間”的內(nèi)涵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美術(shù)史研究中的地緣空間或視覺感知及再現(xiàn)手段,不同空間表現(xiàn)方式后隱含的藝術(shù)趣味和目的不斷受到關(guān)注。空間指涉的不僅是“作為藝術(shù)‘內(nèi)部因素’的圖像內(nèi)容和形式”[9]8,還包括作為藝術(shù)外部因素的“藝術(shù)品產(chǎn)生和展示的條件和環(huán)境”[9]11。“空間”呈現(xiàn)出“多維指涉”的特性。而巫鴻對(duì)“空間”方法的運(yùn)用恰恰是在藝術(shù)形式分析的基礎(chǔ)上,向藝術(shù)的外部因素不斷擴(kuò)展,尋求藝術(shù)內(nèi)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連接點(diǎn)。在武梁祠石刻畫像研究中巫鴻所使用的“中層研究”方法,注重多組畫像在武梁祠建筑空間單元內(nèi)部建構(gòu)起來的結(jié)構(gòu)性聯(lián)系,而這樣的結(jié)構(gòu)性聯(lián)系又與漢代畫像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以及文化觀念有著對(duì)應(yīng)聯(lián)系。“中層研究”溝通了實(shí)存的武氏祠石刻畫像與漢代宗教、政治、藝術(shù)等宏大觀念,初步發(fā)掘了“空間”在美術(shù)史個(gè)案研究中的活力點(diǎn)。對(duì)圖像空間表現(xiàn)模式及其背后藝術(shù)目的和趣味的關(guān)注也避免了將西方美術(shù)史傳統(tǒng)作為衡量中國古代藝術(shù)的準(zhǔn)則。在《武梁祠》后,巫鴻的美術(shù)史研究越發(fā)顯示出了對(duì)“空間”問題關(guān)注的自覺性,“空間”作為美術(shù)史研究的方法在巫鴻的美術(shù)研究實(shí)踐中也越發(fā)明晰。
- 美育學(xué)刊的其它文章
- 伊夫-阿蘭·博瓦的結(jié)構(gòu)主義藝術(shù)批評(píng)和《作為模型的繪畫》
- 王光祈創(chuàng)造國樂思想與傳統(tǒng)禮樂的現(xiàn)代音樂轉(zhuǎn)進(jìn)
- 民族男高音歌唱藝術(shù)的審美認(rèn)同與技術(shù)訓(xùn)練方法探究
- 同題異趣:從牡丹題材傳統(tǒng)美術(shù)作品看審美趣味的文化分層
- 師范生美育的雙重目標(biāo)及其改革路徑
- 《關(guān)于全面加強(qiáng)和改進(jìn)新時(shí)代學(xué)校美育工作的意見》:一部新時(shí)代學(xué)校美育改革發(fā)展的綱領(lǐng)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