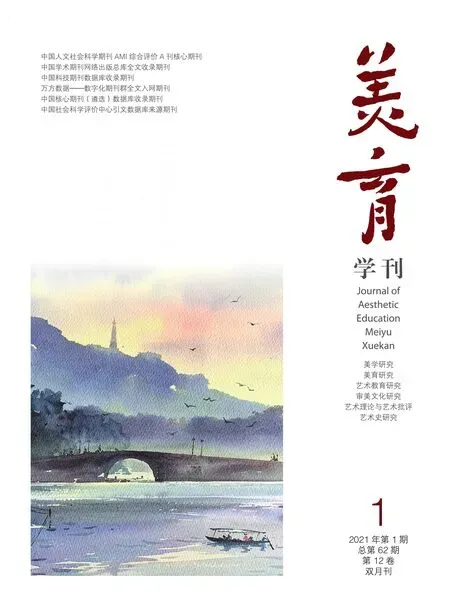經亨頤與“寒之友”社研究初探
周錦嫦
(何香凝美術館,廣東 深圳 518053)
一、詩畫唱和與“寒之友”結社
1927年,是中國歷史上腥風血雨、寒氣蕭殺的一年。蔣介石發動了屠殺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分子的“四·一二”政變,“被屠殺者達數千人”,“六天后,在4月18日,國民黨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1]此事件成為國民黨的重要分水嶺,早期跟隨孫中山革命的一些元老,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感到不滿,他們紛紛轉向文藝,以遠離政治權力中心。中央執行委員經亨頤(1877—1938)在按捺多年之后,終于提起畫筆,在紙上揮毫潑墨,繪竹、松、梅、菊、水仙等耐寒高潔植物,以表達胸中塊壘。當時的經亨頤,已年屆五十。經亨頤在日本留學時加入同盟會,早年活躍于教育界,因教育理念不為當局所容投身政界,試圖從政治方面著手教育改革。1924年后,具有老同盟會員資格的經亨頤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國民黨一大,1926年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經亨頤雖位居中央執委,實際并不得志,他的提案不被當局取納,政治上無所作為,常處于一種“無所事事”的狀態。與當局始終不相投的經亨頤,遂成為政變中“轉向”文藝的一員。如姜丹書所言,自1926年以來,與其說是經氏的政治生涯,不如說是其藝術生涯:
如此閑情逸致,亦無幾時,于是南游粵嶠,北作燕客,奔走國事,浮沉政途,故不得志。既復優游漢皋,終乃還來京畿,雖為中央委員,而仍只空懸名義,無所事事。……溯自民十五年后,與其謂先生政治生涯,毋寧謂為藝術生涯,蓋其于政治,始終氣味不相投,而于藝術,則所樹立者高焉。[2]
經亨頤的同僚好友陳樹人(1884—1948),也在此次政變中深受打擊。1927年,陳樹人辭去廣東省政府委員及省民政廳廳長等職,將大量精力投入文藝事業。1928年至1929年間,陳樹人相繼出版《陳樹人畫集(第一輯)》《陳樹人畫集(第二輯)》《陳樹人畫集(第三輯)》,以及詩集《寒綠吟草》。時任中央婦女部部長的何香凝(1878—1972),一如其激烈個性,1928年底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聲明,辭去國民黨內一切職務,并移居上海。何香凝1908年入日本女子美術學校撰科日本畫科學習,同時入名師田中賴璋門下學習獅虎動物畫,是20世紀初期為中國畫變革吹入新風的重要畫家。辛亥革命前后,何香凝常以獅、虎猛獸動物畫激勵革命將士,是其標志性的個人圖式。
經亨頤、陳樹人、何香凝三人不僅政治立場一致,在繪畫、書法、金石、詩詞方面各有獨到造詣。面對當局的統治,詩畫唱和成為他們表達內心、不同流合污的方式與手段。1927年前后,對大庾嶺盛放之梅的吟詠,已見唱和之端倪。1927年,經亨頤作《梅(元旦過大庾嶺抵漢皋)》:“嶺上寒梅倒影多,不知殘折幾經過。抽毫寫出冰堅意,不在花間在斷柯。”[3]3何香凝1926年秋作《詠梅(一九二六年秋北伐經大庾嶺見梅花盛開有感而作)》:“南國有高枝,先開嶺上梅。臨風高挺立,不畏雪霜催。”(1)雙清詩畫集編輯委員會編印:《雙清詩畫集》,香港:香港時代有限公司,1982年。此詩為何香凝詩篇第六首。又于1927年作《重游大庾嶺(北伐途中一九二七年)》:“十月重觀嶺上梅,黃花笑雪傲霜開。梅蘭菊竹同時會,羨卻庾山獨占魁。”[4]
大庾嶺,又稱梅嶺,為中國五嶺之一。地處今江西大余縣與廣東南雄市交界,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南北交通要塞。大庾嶺之梅,以“天下梅信之先”而聞名。在戎馬倥傯、揮師北上的情境下,兩人不約而同地引發詩興,抒發了對不畏寒冬、傲雪開放的梅花的贊美。恰好說明兩人對“梅”這種傳統象征物共同的文化理解和價值取向。
經亨頤、何香凝對于庾嶺之梅的吟詠與贊美,由于各自處于不同時空中,彼此并未互通。而到了1928年初,經、何、陳三人合繪一件作品,則是有意識地相互唱和。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議在南京召開。對全會背離孫中山三大政策,經亨頤、陳樹人、何香凝等人十分不滿。會議期間,他們一同前往正在建設中的紫金山總理陵園。掃墓歸來,三人感傷于時局與人事變遷,抑郁難平,于是合繪了一幅《歲寒三友圖》(圖1)。其中經亨頤畫竹、何香凝畫梅、陳樹人畫松。全幅以水墨寫成,不求形似、盡寫胸中意氣。于右任為之題:“紫金山上中山墓,掃墓來時歲已寒。萬物昭蘇雷啟蟄,畫圖留作后人看。松奇梅古竹瀟灑,經酒陳詩廖哭聲。潤色江山一枝筆,無聊來寫此時情。”(2)該作收藏于何香凝美術館,又名《松·竹·梅》。詩中“經酒”指經亨頤,“陳詩”指陳樹人,“廖哭聲”指何香凝。“松奇梅古竹瀟灑、經酒陳詩廖哭聲”一句,將經、何、陳比作歲寒三友,三人的立場與處境可見一斑。實際上,他們自身也以耐寒不屈、堅貞高潔的松、竹、梅自擬自勵。經亨頤愛松入骨,室名長松山房。其有詩曰:“為木當作松,松寒不改容。我愛太白句,居亦曰長松。”[3]21或許是受了經亨頤的影響,何香凝也逐漸以梅自況。她作于1929年的題畫詩:“先開早具沖天志,后放猶存傲雪心。獨走天涯尋畫本,不知人世幾升沉。”(3)何香凝在1951年繪制的《梅菊》一圖上重題了這首詩,該作目前收藏于何香凝美術館。儼然將梅花當作自己的化身。

圖1 經亨頤、何香凝、陳樹人合作《松·竹·梅》,水墨紙本,137×34厘米,1928年,何香凝美術館藏
此后,歲寒三友在經、陳、何同仁的詩畫創作中日漸頻繁。尤其是經亨頤,他是書畫社團“寒之友”社的最主要倡導者。“寒之友”一詞,最早出現在其與陳樹人1928年合作的《竹菊圖》題詩中的一句,“此間俱是寒之友,不道尋常傾蓋歡”。[3]71929年初,經亨頤又作《山茶水仙》,小標題為“創寒之友社”,可見是1929年初為紀念“寒之友”社成立所作。關于社團成立的時間,在經亨頤等當事人的資料中并未見有明確記錄。借助當時的報刊資料,有刊載于1928年12月17日《申報》“昨午,書畫家二十余人正式討論組織寒之友社事”的報道。[5]這是目前所見資料中有確切時間的最早一次記錄。可見,“寒之友”社的成立當不晚于1928年12月16日。經亨頤為之刻“寒之友集社”印以作紀念,邊款為“十七年除夕頤淵為寒之友刻”(圖2)。聯系當時的社會環境,“寒之友”社中的“寒”字,帶有強烈的映射色彩,暗喻其時政治黑暗,有如寒冬。而“寒之友”,顯然就在這種“寒”的環境下,不屈服于當局的同仁。

圖2 “寒之友集社”印章及邊款
二、經亨頤的文人畫傾向與圖式
經亨頤是“寒之友”社的創辦者、組織者,從其畫學師承、入畫經歷、作畫題材、筆墨圖式,以及在畫面中所寄托的人格精神等方面看來,皆與傳統文人畫之間有著相當程度的契合。經亨頤的風格取向,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團的整體藝術氛圍。經亨頤雖自詡50歲學畫畫,但與畫界淵源甚深。早在1903留學東京時,就與后來著名的文人畫家、理論家陳師曾(1876—1923)(4)陳師曾(1876—1923),又名衡恪,號朽道人、槐堂,江西義寧人(今江西省修水縣),清末民國初年著名畫家、書法家、繪畫理論家和藝術教育家。同窗并切磋論藝。陳師曾是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在20世紀西學東漸的大潮中,在康有為、陳獨秀、徐悲鴻等一片美術革命的呼聲中,陳師曾力排眾議,舉起文人畫的大旗。他的畫學觀點,主要體現于《文人畫之價值》一文。在該文中,陳師曾對文人畫進行了歷史性總結,提出文人畫的藝術本質所在,充分肯定文人畫的人文與靈性特征。文章立論清晰、旁征博引,既追溯了中國文人畫之歷史發展源流,又通過比較西方繪畫之特征,引入現代藝術流派之趨勢,闡明“文人畫”并非保守陳舊而具有現代性。陳師曾對文人畫價值的肯定,成為當時美術革命聲中的一股清流,對國人審視傳統文化、提升民族自尊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陳師曾多元的價值參照體系與世界文化眼光與他留日八年的教育經歷不無關系。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全面接受西方現代文明洗禮,也較中國更早向現代學術體制轉型。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日本人對于本國文化的態度,經過了一段復雜的歷程。作為東方繪畫代表的文人畫,其命運也隨之而幾經浮沉。日本文人畫源自中國,隨著17世紀儒學教育在日本的興盛流行了幾個世紀。明治時代(1868—1912)仍為收藏家和美術家所珍重。[6]自1882年費諾羅薩(1852—1908)(5)恩內斯特·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出生于美國馬薩諸塞州,畢業于哈佛大學,東京帝國大學美術教授,曾擔任日本文部省和內務省美術專員、帝室博物館美術部主任等職。在龍池會發表演講《美術真說》對文人畫進行大肆抨擊以來,在后續的30年間,文人畫在日本跌入歷史低谷。隨著大正時期的到來,一部分畫家、批評家逐漸對當時的藝術風氣感到不滿而進行反思,他們重新發現了文人畫的魅力。又由于大量高質量的文人畫從中國流入日本,啟發了一批學者對文人畫的研究興趣。京都大學教授內藤湖南(1866—1934)(6)內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今日本秋田縣人,是日本近代中國學的重要學者,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在他的美術史講座中引用了大量新發現的文人畫作為圖例。東京帝國大學美術史教授瀧精一(1873—1945)(7)瀧精一(1873—1945),日本知名畫家瀧和亭之子,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國華》雜志主編。1922年發表了《文人畫概論》。而在今天最為人所熟知的,是由東京美術學校教授大村西崖(1867—1927)(8)大村西崖(1867—1927),日本靜岡縣人,東京美術學校教授,著有《東洋美術史》十五卷。1921年1月形成的重要論文《文人畫之復興》,這篇文章被陳師曾翻譯為中文并與他的《文人畫之價值》一同發表。陳師曾對大村西崖《文人畫之復興》一文的共鳴、翻譯、推廣,一個側面反映了這股文人畫潮流已經成為中日兩國共享的思想資源,以文人畫為代表的東方繪畫,已經超越了繪畫本身成為民族文化的代表。在20世紀20年代以來國粹主義思潮盛行的中國,國畫重新被發現為傳統文化的經典,國畫家的本體文化立場進一步堅定,其中不乏以研究國畫、發揚國光為宗旨的個人和團體。經亨頤是與陳師曾、魯迅同期的留日學生,作為肩負起救亡求存、民族自強重任的一代知識分子,對此不能不有所觸動。經亨頤的畫學觀點與創作手法深受陳師曾影響。根據經亨頤的回憶,二人在弘文學院就讀時曾同寓冰川館一年多,讀書之暇,師曾繪畫,頤淵則刻石助歡。[3]441之后一同升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就讀。歸國后,雖南北異處,仍時常書畫往還。經亨頤評師曾“金石書畫一以貫之”“作畫勤而不茍”因而“尤佩其品格”。[3]441經亨頤學畫,即以陳師曾之竹入手。陳師曾于1923年患病早逝。經亨頤悲痛不已,1936年,初度花甲之年的經亨頤為紀念亡友,搜集坊間及故友手中的師曾遺畫,集成《陳師曾遺畫集》一冊以行世,并親自作序。
經亨頤的文人畫觀,在他1932年作的一篇題為《從國畫說到教育——對前浙江第一師范在京校友講演》中有明確的表述:
我所愛的是“文人畫”,從表面上看,也許不為流俗所愛好;然而,除畫的本身以外,卻另有其更重要的意義在。很簡單的幾筆淡畫,有詩的,金石的風韻,同時表現。……畫以外另有詩的金石的而且有國粹特性的文人畫,有崇高的人格上的修養,艱苦卓絕的精神,特殊的民族性內容。丹青畫可以中西合璧,文人畫萬不能中西合璧。[7]
經亨頤是近代著名的民主主義教育家,深諳西方現代文明思想,但如同其他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對中國舊學亦了如指掌。[8]在他的繪畫作品中,經亨頤偏愛具有傳統象征意義的“寒之友”“歲寒三友”題材,這類題材自宋代以來就成為文人畫圖式的重要組成部分。經亨頤的作品真跡流傳較少,大部分只能通過文獻圖錄來進行分析。根據《經亨頤詩文書畫精選》中收錄的經亨頤個人及合作畫40余件看來,其中竹、松、水仙位列前三,所作均為十幅以上。緊跟其后是梅、菊,兩者數量相當,蘭、芭蕉、石頭、楓、桃偶有所作,但為數不多,或為點綴。由此可見歲寒花木題材占據絕對優勢。經亨頤的松圖,一般為獨幅,用筆灑脫、粗枝大葉、濃淡暈染、滿紙淋漓,著力表達蒼松的偉岸氣魄。如《蒼松圖軸》《山間松色仰高風》《蒼色參天圖軸》等。其畫竹,一改畫松之粗放筆法,初期取法陳師曾,大部分為直節朗逸、細枝疏葉之作。其寫水仙,以白描手法勾勒花、葉,群而不亂、輕盈挺拔,于秀美中透出堅韌之氣。經亨頤大量繪寫耐寒植物,結合其人生際遇,實則表達環境險惡,懷才不遇、不同流合污。如同蘇軾、文與可、倪云林等古代文人那樣,他實際是把書畫或者藝術作為完善或表達自己人格的一種途徑和工具。鄭曼青對經亨頤書畫的評價,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其借物述懷、畫以傳人的文人畫隱喻特點:“頤公五十始畫竹、畫松,寫其品性而已”,“頤公茍以直道行于當世,涇濁當分,何清可待,各其未能,即以直道表現于書畫之間,特立獨行,亦足以垂不朽矣。”(9)鄭曼青:《〈經亨頤金石詩書畫合集·書畫篇〉序》,珂羅版線裝本,1936年。
在《何謂國畫》一文中,經亨頤論述了文字、書法對繪畫的重要性:“如其要確定國畫的意義,據我想非從文字講起不可。我們中國的文字特別困難,原來(是)教育上一個不好解決的問題。上古文字永諸金石,由金石而書,由書而畫,所謂書畫一體,骨干還在金石。”[9]此觀點與陳師曾《文人畫之價值》中書畫關系的看法一致:“且畫法與書法相通,能書者大抵能畫,故古今書畫兼長者,多畫中筆法與書無以異也。可見文人畫不但意趣高尚,而且寓書法于畫法,使畫中更覺不簡單。”[10]經氏學畫之前對金石書法有較深的研究,他畢生致力于《爨寶子碑》,逐漸發展出獨樹一幟的爨體書風。《爨寶子碑》為出土于云南曲靖的東晉碑刻,是由隸書過渡到楷書的典型。在目前所見經氏的題畫詩或書法作品中,均以爨體面目出現。1929年下半年,經亨頤在白馬湖畔集中精力完成《爨寶子碑古詩集聯》。對于書法修養較高的畫家而言,以書入畫是自然而然之事,他曾戲言其畫不算畫,算寫字:“丹青派精細的作品,我沒有學,如其這種畫就算代表國畫,那末像我亂涂幾筆蘭竹可以不算畫,算寫字罷。”[9]在他作于1934年的一首詩中,明確闡發了金石書法與繪畫的關系:“金石畫之骨,淡墨色之源。古今陶冶甚,率爾發毫端。”[3]117時人謝玉岑這樣評價經亨頤的作品:“經子淵先生水墨竹石,俱有金石氣,字法二爨,絕不矜飾,寐叟后一人。”[11]不僅書與畫,經亨頤還主張書、畫、詩、印之間要各自相通:
昔人能書、能畫、能詩,曰“三絕”,蓋謂各造其極也。書自為書,畫自為畫,詩自為詩,絕亦何足尚。竊思藝術不在“絕”,而在通。不限書、畫、詩“三絕”,應加金石而為“四通”。畫通于詩而金石實為其骨干,四者關系莫殆不然。(10)經亨頤:《〈爨寶子碑古詩集聯〉序》,鉛印線裝袖珍本,1930年。
詩、書、畫、印四通,對很多從事中國畫的畫家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大部分畫家能畫未必能書,能書者未必能作詩,治印亦如是。在經亨頤的作品中,詩、書、畫、印,均能不借助他人。經亨頤全面的藝術修養,是他站在陳師曾同一陣線,實踐、延續文人畫命脈的基礎,也是其五十歲步入藝壇,仍能迅速融入圈子的關鍵所在。
三、經亨頤、“寒之友”社與海上畫壇
“寒之友”社的活動據點主要在經濟文化發達、交通便利的上海。一方面由于經亨頤出身江浙,在江浙一帶人脈關系較深。另一方面,是兼容并包、開放多元的海上文化環境,為“寒之友”社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合適的土壤。據《申報》的報道,1928年12月16日,經亨頤、陳樹人、王一亭、徐朗西、謝公展、劉海粟、李祖韓、李秋君、鄭曼青、王個簃、錢瘦鐵、王陶民、張善孖、俞劍華、馬公愚、熏哲香、賀天健、鄭午昌、方介堪、馬孟容、王季眉、張寒杉、汪英賓等二十多位畫家在上海三馬路會賓樓正式召開“寒之友”社第一次組織大會。[5]所到場者當天即簽名入社,并通過了章程及第一屆展覽會細則,大會決定于1929年1月9日在寧波同鄉會舉行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并設立了展覽會的分工、辦事人和聯絡地點,其中李祖韓、謝公展、馬孟容、汪英賓、經亨頤、陳樹人、劉海粟、徐朗西、王濟遠為責任干事,李祖韓擔任事務主任兼會計,王一亭、謝公展擔任征集主任兼陳列編輯,馬孟容、鄭午昌、方介堪擔任文書主任兼陳列,汪英賓、徐朗西擔任宣傳主任兼新聞,劉海粟、經亨頤、陳樹人擔任交際主任兼編輯,王濟遠擔任陳列主任兼編輯。會上經亨頤發表了社團宣言:
金石有堅忍之質、松柏無凋謝之容。書畫之友,寒云乎哉。取義曰寒,初無消沉之感。寓滬同人,發起斯社,有所惕勵。社會自然之進取,何得謂世道陵夷、自鳴高蹈,惟欲圖安慰,非具有寒的精神,萬難解除一切。金石書畫可作游戲,不可依為生活,亦矯情之談。以此為游戲固可,以此為生活無不可,若孳孳于此而為所奴隸則大不可。寒之友之作品,更愿使社會之寒之友,不費巨資,均得享受,以引其美感。薄酬所入,如有超于生活者,應公之于社。集眾力以興辦藝術事業,此則同人等所致宣言者也。[12]
1929年1月9日,“寒之友”第一次展覽會在上海寧波同鄉會開幕。展覽共征得作品四百多件,首日展出三百多件,其余作品陸續更換展出,參展書畫家多達八十余人[13],甚至還有來自日本的參展者。如此大規模的展覽,在當時也是不多見的。展覽作品以書法篆刻為多,精品如經亨頤的水仙朱竹,陳樹人的村景,何香凝的雪景,黃賓虹的山水,王一亭的達摩,于右任的書法,鄭曼青的芭蕉,李氏兄妹的工筆,劉海粟、王濟遠、汪英賓、楊淸磬、錢瘦鐵的山水等。其中參展的女畫家也不少,有何香凝、張紅薇、李秋君、張默君、趙含英等人。其洋洋大觀,可謂各家各派書畫精品之大集會。參觀者評價其:“名作相投、滿壁琳瑯、低徊俯仰其間,如入寶山、美不勝收。”[14]謝玉岑專作《寒之友集會讀畫絕句》連載于《申報》,記述會中展出精品及各家特色。(11)謝玉岑:《寒之友集會讀畫絕句》(上、中、下),連載于《申報》,1929年1月14-16日。展覽得到了滬上媒體的關注和報道。《上海畫報》給予了專頁報道。(12)“寒之友畫展會專頁”,載《上海畫報》第431期,1929年1月9日,第2頁。《申報》進行了連續多天的展覽預告、展覽開幕報道。從展覽的整體情況來看,可以說圓滿成功,以至于他們產生了當年7月舉行第二回展覽會的設想,但不知何故,第二回展覽會并未在當年舉行。
如此大規模的展覽,如果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運轉核心,是不可能達到的。而在“寒之友”社的多位發起人當中,經亨頤無疑是最為關鍵的人物。在入社的名家社友中,大部分與經亨頤有著不錯的私交。此處略舉兩例。“藝術叛徒”劉海粟(1896—1994)是經亨頤的多年好友,在“寒之友”成立之初就積極參與。劉海粟輩分雖不及黃賓虹、王一亭,但在上海是十分有影響力的新一代青年教育家、畫家。1912年,劉海粟在上海開辦我國第一所私立美術學校上海圖畫美術院。劉海粟辦學大膽,堅持采用裸體模特兒教學,敢于與保守舊勢力叫板。又多次前往日本、歐美考察教育,不斷改革校務、與時俱進。這與曾經活躍于教育一線的經亨頤多少產生共鳴。1922年,劉海粟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舉行了一次個人畫展。經、劉相識約在此時。1928年底,劉海粟即將出國之際,經亨頤為其組織餞行會,其間合作了一件由經亨頤畫竹、劉海粟畫八哥、俞劍華畫石、謝公展畫菊的作品,經亨頤題詩“夕照荒園人跡少,偶來覓食好婆娑。西風催緊秋江去,無限離情問八哥”[3]7,表達了對劉海粟離滬出國的不舍。后經亨頤又組織海上畫友在海廬設宴為劉海粟餞行,甚至有資料顯示,就是在那次宴會上首倡成立“寒之友”社。“寒之友”之取名,亦與劉海粟對經亨頤的建議不無關系。據賀天健引劉海粟的回憶:“據劉君海粟言,經君亨頤原欲發起一書畫會,征意于劉君。劉君極贊其成,苦無相當名稱,適經君佩有玉印一方,上鐫寒之友三字。劉君認為其義甚高,即請以為該社名。”[12]劉海粟還與陳樹人、何香凝等非江浙籍社友保持了良好關系。在1929年教育部第一屆全國美展中,出品了一張由經亨頤、陳樹人、劉海粟三人合繪的作品。其中有經亨頤的題跋:“何處幽巖得地寬,移來佳種玉團團,此間俱是寒之友,不道尋常傾盡歡。十七年十二月樹人畫友初晤海粟于其寓,相見甚得,曼青補蘭合成此幀。”[15]這件作品不僅是陳樹人、劉海粟首次見面的見證,也是目前所見“寒之友”一詞首次在經亨頤詩文中出現。劉海粟歐游期間,特意造訪了同在法國的何香凝。盡管人在異鄉,仍然不改雅集合作的舊習,兩人合繪了《歲寒三友圖》《梅菊》《瑞士勃郎崖風景》(13)何香凝、劉海粟合作的《歲寒三友圖》《梅菊》收藏于上海劉海粟美術館,《瑞士勃郎崖風景》僅見圖錄和文獻資料,未見實物。等作。劉海粟在藝術界人脈關系不淺,教育界泰斗蔡元培是強有力的支持者。劉海粟本人則中西畫皆通,劉海粟的加入,使得“寒之友”社在上海年輕一輩的畫家中也能產生影響,甚至引起西畫家的側目。
黃賓虹(1865—1955)是另一位與經亨頤有著密切交往的“寒之友”社的名家成員。作為公認的20世紀國畫大師,在1928年“寒之友”社成立之時,黃賓虹已經是63歲的畫壇宿耆,也是“寒之友”社年齡最大、資格最老的成員。1932年,黃賓虹應經亨頤邀請,前往白馬湖一帶寫生,并與張大千、張書旂等社友雅集于長松山房。黃賓虹作畫贈經亨頤并題:“梁棟森郁盤,蛟龍任飛舉。長松勢擎天,蘇物作霖雨。”[16]“寒之友”社第二次展覽會,又名“古畫寒花展覽會”,就主要得力于黃賓虹。黃賓虹被委托為展覽征集人,區別于前一次展覽的大而全,此次展覽是一次專題展,其限定主題為“寒花”。“寒花”即耐寒的花,主要為梅、菊等冬天開放的花,意趣方面也更接近社團宗旨。展覽時間為1932年6月22日夏至當天,意為以寒花銷夏。作品數量共三十余件,展覽地址為康悌路光裕坊八號的“寒之友”社。該展覽不作宣傳,因此在當時的報紙中罕有報道。目前流傳下來的僅有《申報》刊登的一張經亨頤、黃賓虹等人的合照(圖3)和幾行報道文字。與1929年首次展覽的熙熙攘攘相比區別甚大。由此也反映出“寒之友”社在藝術趣味、水平方面逐漸走向成熟。其他的海上名家如王一亭(1867—1938)(14)王一亭(1867—1938),號白龍山人、梅花館主、海云樓主等,法名覺器。祖籍浙江吳興,生于上海周浦。清末民國時期海上著名書畫家、實業家、杰出慈善家、社會活動家與宗教界名士。,其在海上畫壇馳騁多年,又是知名的大慈善家和買辦,可謂風云人物。王一亭是“寒之友”社最早一批會員,無論是“寒之友”社第一次展覽會還是后來何香凝主辦的救濟國難書畫展覽會,王一亭都在繁忙的公務之余,給予大力支持。又如李祖韓(1893—1964)(15)李祖韓(1893—1964),字左庵,齋名怡如廬,浙江鎮海人。工畫山水。著名女畫家李秋君為其胞妹。、李秋君(1899—1973)(16)李秋君(1899—1973),名祖云,字秋君,以字行,浙江鎮海人,初隨長兄習書作畫,后得張大千指點。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兄妹,作為上海本土畫家,多次借其寓所為“寒之友”社開會、雅集之用,極盡地主之誼,又承擔了“寒之友”社第一屆展覽的多項實操工作。可以說,“寒之友”社能在海上畫壇迅速確立并產生回響,與海上畫家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經亨頤在上海書畫圈子的號召力與影響力。

圖3 “寒之友”社第二次展覽會部分與會者合影經亨頤(左一)、黃賓虹(左二)、張善孖(左三)、王一亭(左五)
第一次展覽會成功舉辦后,“寒之友”社也于上海一舉成名,成為海上畫壇眾多社團的其中一員。這次華麗亮相的另一層意義在于,使得原本屬于左派內部的詩畫唱和活動,從一種小范圍的筆墨聚會向外擴展,直接面向社會大眾,并獲得了專業身份。這對有著政治背景的經亨頤、陳樹人、何香凝來說意義尤為重大,就在展覽會舉辦的當年,他們聯袂參與了多項藝術活動,包括1929年4月的教育部第一屆全國美展、1929年7月的藝苑繪畫研究所名家捐助書畫展覽會、1929年7月的中日畫家聯歡繪畫展覽會,及1929年底的新華藝術大學籌款書畫會等,可見其投身藝術活動前所未有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四、“經陳合作”與“歲寒三友圖”再作
“寒之友”社一方面活躍于喧鬧繁華的大都市上海;另一方面,又多次“隱入”遠離塵囂、世外桃源般的白馬湖。1922年,經亨頤在其家鄉上虞白馬湖畔創辦春暉中學并任校長。白馬湖山明水秀、環境幽美,又延請夏丏尊、朱自清、豐子愷、劉質平等一批名師,使之增添了濃厚的人文氣息。白馬湖逐漸成為經亨頤退隱政治江湖、寄情書畫的一方精神家園。1929年秋,經亨頤在白馬湖畔的長松山房落成,之后多次邀請書畫好友前來雅集。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白馬湖的雅集,書畫合作是其中的重要環節。從經亨頤目前的書畫作品和詩文看來,他的合作者非常多,合作模式也多種多樣。而在眾多合作者和模式當中,“經陳合作”與“歲寒三友圖”合作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兩項。
“經陳合作”指的是經亨頤與陳樹人之間的書畫合作,不同于何香凝、柳亞子這類左派的個性激烈、外向奔放,經、陳態度溫和,步調更為一致。目前所見兩人最早的合作,產生于1929年4月的白馬湖雅集。參與此次雅集者有經亨頤、陳樹人、居若文、何香凝、方介堪、伯滌等人。時逢江南暮春、鶯飛草長,一路上名勝古跡不斷,眾人陶醉于湖山勝景、憑吊懷古、撫往昔今,一時詩興、畫興勃發。陳樹人為此畫了不少寫生圖,如《山溪新綠》《蘭亭》《柯巖》《黃杜鵑》《紹興東湖》。經亨頤則為之題《宅址喬松》《白馬湖新綠》《蘭穹福仙寺》《東湖》《蘭亭》《鑒湖》等多首詩。之后的1930年、1931年間,兩人迎來了合作的高峰。1930年夏,經亨頤、陳樹人一同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擴大會議,兩人同居一樓,因命樓名為“寒之友樓”。9月,擴大會議移師太原,陳樹人、經亨頤同往,其間合作了《菊桂圖》《水仙梅花》等作品。相傳太原晉祠內有周朝所植之側生柏樹,陳樹人前往寫生,經亨頤為之作題畫詩《宋柳》《唐槐》《周柏》。1931年,經、陳同寓天津,其間合作了《赤松白梅》《雨竹凌霄》《雨竹紅葉》《石海棠》《竹菊》《雞冠紡織圖》《紫藤蜂鳥》《月中丹桂》等作品。該年6月,二人又一同南下廣州,同寓東山區松崗之“松蟀樓”,相繼合作了《竹雀圖》《竹石榴圖》《柏樹萱草圖》《蘭桂圖》《竹水仙圖》《松菊圖》等作。據《頤淵詩集》,1930年、1931年間,經亨頤、陳樹人二人合作的題畫詩就有十七題二十首,是所有合作者之中數量最多的。“經陳合作”的作品,多取材于竹、梅、水仙、松柏、蘭等歲寒三友或四君子,以表達堅貞不屈、相互砥礪。手法上,多為清逸冷峻的文人畫手筆。二人的合作方式也比較自由,有經陳合繪、陳畫經題或兩人合繪合題。作于1930年的《寒梅水仙》(圖4),是一件經陳合繪、合題之作。(17)該作曾刊登于《京報圖畫周刊》,1931年1月15日。從畫面看來,先由經亨頤起筆畫水仙,用筆細膩、線條優美,枝葉條分縷析,毫不馬虎,著力傳達出水仙輕盈挺秀,冰清玉潔之氣。水仙是經亨頤的經典圖式,如同徐悲鴻形容得那樣,經子淵“最清勁作品,尤在水仙,輕盈挺拔,若聞微香,所謂傳神,庶乎近之”[17]。水仙上方,是由陳樹人補作的梅,寒梅從水仙叢中橫斜伸入畫面,梅干清勁有力,短枝發其上,梅花點點,有含苞待放者,又有盛放全開者。在構圖上,豎生的梅花與塊面的水仙,互相補給,很好地平衡了畫面。作品為立軸,右上方留白處分別是兩人的題跋。經亨頤題詩曰:“難得山間水一涯,盈盈寒意釀奇葩。天教珍重好顏色,歷盡冰霜始著花。”[3]32樹人和詩:“為抱堅貞清白性,不辭凌雪犯霜開。春和景淑知終有,且讓群芳取次來。”[18]“經陳合作”在當時兩人合開的書畫潤例中也見一斑。1931年初,兩人合開之書畫潤例在《申報》中刊出:“一、經陳合作寫意花卉每方尺十元;二、陳單作花鳥山水加倍;三、經單作書畫一律折半。”[19]由此可見,經陳合作已經成為流行樣式,并在當時的書畫市場中擁有一席之地。

圖4 經亨頤、陳樹人合作《寒梅水仙》,尺寸、藏處不詳
《歲寒三友圖》是由經亨頤、陳樹人、何香凝三人合繪、于右任題詩的作品。如上文所述,首次作于1928年初,是他們詩畫唱和的先聲。八年后三人又同作,恰好構成“寒之友”社詩畫合作的頭尾兩端。1936年11月,日本實施大陸政策之重要一步的綏遠戰役爆發,中國各地發起了大規模的援綏救國運動。為抗日援綏,何香凝決定在南京舉行“救傷救國書畫展覽會”。展覽在“寒之友”社、南京婦女界的協助下,征集到了蔡孑民、于右任、陳樹人、經亨頤、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李協和、柳亞子、高劍父、馮玉祥等多件名家作品。展覽從1936年11月20日開幕到11月28日閉幕。參觀者多達萬人,所有作品均售賣一空。(18)《青島時報》1936年12月2日、《民國日報》1936年11月29日的報道為“參觀者十萬人”,《青島時報》1936年11月29日報道為“參觀者萬人”。筆者認為在為期不足十日之內有十萬參觀者之數有夸張之嫌,此處從參觀者萬人之說。由何、經、陳合繪,于右任題詩的二十多幅《歲寒三友圖》,成為此次展覽義賣會上的最大亮點。此系列作品大部分已經散佚,如今流傳下來的有藏于何香凝美術館(圖5)、廣東省博物館(圖6)及私人收藏各一件。另有收錄于展覽照片集中的圖錄兩件。從這五件作品的畫面看來,每件作品均由三人合繪,三人分別畫松、竹、梅中的一種,時或互換,并不固定。在創作手法上,均為逸筆草草、折枝局部的寫意之作。構圖方面,松、竹、梅自由組合、相互掩映,畫面無一雷同。裝裱形式上,立軸和橫幅皆有。每件作品均由于右任題詩并跋,詩為1928年1月在南京題于首幅《歲寒三友圖》之詩。根據“十七年一月作于南京廿五年又同作”的跋語看來,此系列作品為八年之后的再次合作,并形成了這樣一個巧合,同樣的題材、同樣的創作者,創作地點同在南京。

圖5 經亨頤、何香凝、陳樹人合作《松·竹·梅》,設色紙本,143×47.4厘米,1936年,何香凝美術館藏

圖6 經亨頤、何香凝、陳樹人合作《歲寒三友圖》,水墨紙本,113.6×40.2厘米,1936年,廣東省博物館藏
《歲寒三友圖》于20世紀50年代曾有過一段回響。1958年,于右任在臺灣偶然獲得一幅當年合作的《歲寒三友圖》,勾起了對親友的無限思念,并提筆補上當年題詩缺漏的一個“時”字。憶及經亨頤、陳樹人均已去世,感慨萬千的于右任賦詩《懷念大陸及舊友》:“三十余年補一字,完成題畫歲寒詩。于今回念寒三友,泉下經陳知不知?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師友記同游。中山陵樹年年老,掃墓于郎已白頭。”[20]該詩發表在1958年11月12日的《人民日報》上。當年的合作者之一,尚在人世的何香凝見到老友的這兩首泣血之作,便步于右任詩原韻,和出一首《遙念臺灣》。首句引用于右任1934年題何香凝、王一亭合作《青山瀑布》(19)于右任《青山瀑布》跋:“能為青山助,不是界青山,出山有何意,聲留大地間。”該作現藏于何香凝美術館。詩一句開篇:“青山能助亦能界,二十余年憶此詩。歲寒松柏河山柱,零落臺灣知未知?錦繡河山無限好,碧云寺畔樂同游。驅除美寇同仇愾,何事哀傷嘆白頭?遙望臺灣感慨憂,追懷往事念同游。數十年來如一日,國運繁榮度白頭。”[21]對于經歷了長期戰亂的何香凝來說,新中國的成立、和平年代來之不易。何香凝在詩中對好友表示思念外,還向好友描述了新中國山河一片繁榮的氣象,表達了希望兩岸攜手共同對抗美帝國主義,爭取統一的愿望。于右任在政治立場上雖不能歸為與何、經、陳、柳同一陣營,但他是他們詩畫合作每一個階段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于、何的這段酬唱,將人們的思緒引向了并不遙遠的30年代。但人與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恐怕是當時眾人都難以料及的。
五、結語
書畫結社中國古已有之,身處于接續傳統與現代歷史大變革的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們大多有較好的傳統文化涵養,為其詩畫唱和及結社活動打下了基礎。政治混亂、派系相爭的黑暗局面,使得其中抑郁不得志者,悲極思退,轉而通過詩畫來表達內心和立場。無論是前期經、陳、何“詩畫唱和”,還是之后的“寒之友”結社,核心參與者經亨頤的學養、身份、經歷、創作圖式,均體現了起源于中國的“文人畫”傳統,又極大地影響了社團的主體風格取向。他們創作了大量的“歲寒三友”詩畫作品,其中經亨頤的松、何香凝的梅、陳樹人的竹,將物象人格化、人格象征化,是該社的經典圖式。因經亨頤的人脈關系以及當時上海寬松的文化環境,“寒之友”社成功舉辦了規模盛大的展覽、雅集活動,在海上畫壇取得了一席之地。黃賓虹、劉海粟、王一亭、謝公展、李祖韓等名家的加入,使“寒之友”社的藝術水平與社會影響力俱增,讓原本小范圍的詩畫唱和轉而面向社會大眾,并獲得了專業身份。“經陳合作”以及經、何、陳合繪《歲寒三友圖》的創作模式,是該社的兩種突出創作特點,也是了解該社不可忽略的切入點。本文希望通過以上論述,使得“寒之友”社與創辦者經亨頤之間關系逐步明晰,從而為對“寒之友”社的整體研究有所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