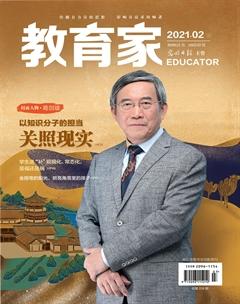在藏地森林學校,探索創變未來的力量
王夢茜


墨爾多山腳下的中路藏寨,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這處古老的嘉絨藏族村寨,處于河谷邊的山地上,傳統的嘉絨藏房與古碉樓靜謐地散落在山林梯田間。走到山路盡頭處,踏上一個小坡,能看到一所名為“登龍云合”的森林學校。這是一幢由傳統嘉絨藏房改建而成的建筑,白墻紅窗,樓頂屋檐上懸掛著的五彩經幡隨風飄蕩。
“這里的生活簡單而真實。每天早上被小松鼠砸核桃的聲音叫醒,一出門看到小牛成群結隊來森林學校吃零食(廚余),猴子下山到玉米地里找吃的,喜鵲、啄木鳥、紅嘴藍鵲不時出現在視野里。動物和人共享著大山里的一切,你會覺得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平等和尊重自然的心便會不由自主地生發。”森林學校校長沈書琴說道。
在自然中尋找“平衡”的答案
沈書琴在杭州出生長大,大學在成都讀建筑設計專業,后赴芬蘭學習環境藝術專業。留學期間,她游歷多國,曾踏足五大洲、22個國家。在旅程中,她發現城市里的人都非常相像。“不管在赫爾辛基、巴塞羅那還是在圣克魯斯,人們有差不多的人生軌跡、相似的思考方式,每天用差不多的商品,有著相似的焦慮。城市里的生活似乎就是不停地消費、不停地消耗資源與產生垃圾,這就是我們大多數人活著的方式嗎?”對于這一問題,她覺得在一些仍保持著傳統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地方,或許能找到答案。
于是,沈書琴走入曠野中的傳統部落,如非洲的斯威士蘭、芬蘭的拉普蘭,看到不同文化中的人對自然的不同認知。畢業回國后,她來到四川藏區,發現這里面臨與全球其他少數民族部落相同的困境——社區經濟發展與在地自然環境、傳統文化保護傳承間存在矛盾,亟須構建一種新的和諧。“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源于現代社會對經濟單一發展的迷信,這首先是個認知問題。要構建新的和諧,根本的解決辦法就是教育。我們這一代人需要重新去思考自然的位置以及人在地球上的位置,認識到人是地球共同體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人的決定會影響地球的未來。我們要把自然重新放到一個基礎性位置,經濟的基礎,教育的基礎,所有行業的基礎,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2015年,沈書琴因緣際會通過一場水磨志愿者的項目加入登龍云合團隊,并投身于森林學校的建設,探索一種社區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的和諧模式。四處游歷的她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的土壤,并隨著森林學校一起,在中路藏寨慢慢生長。
區別于城市中的自然教育機構,森林學校本身就位于自然保護區社區,為人們親近自然、修復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場域。一棟名為“自然”的校舍、一棟名為“自在”的宿舍與名為“自我”的工作坊區域構成學校校區。此外,森林學校還有自己的菜園、牛圈、生態旱廁。來到這里的學習者,在每日自給自足的生活實踐與真實情境的問題解決中,學習書本上無法獲得的知識與能力。他們可以在這里體驗零廢棄的生活方式,去山里采蘑菇,創作一幅大地藝術作品,就地取材做一頓美食;可以在村民家做客,記錄口述歷史,學習在地文化智慧;或是與村民一起自制工具、篩土、修屋頂,在勞動的過程中感受嘉絨藏房中蘊含的因地制宜、生態環保的理念。
真實的自然及自然中的生活方式,需要來自城市的學習者做出改變。“剛開始,他們會覺得大自然的夜晚好黑、校門口竟然還有牛屎,學校里四處攀爬的壁虎和蜘蛛也令他們感到害怕。這也是由于一直以來他們離自然很遠。后來,他們慢慢習慣了,知道蜘蛛不會傷害人,在自然中有牛糞也很正常。這個克服心理障礙的過程,就是走進自然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他們必須走到自然中去真正地體驗,而不是在認知上熱愛自然,實際卻沒有辦法與自然共處。”
沈書琴介紹,森林學校的教育內容,可以劃分為四個學院,分別代表四個主題,其中喜馬拉雅生態學院以生態類項目為主線,希望學習者通過古老的智慧和現代的科學去了解自然,學習自然的內在秩序,從中得到靈感、激發創造力,建立以生態為基礎的世界觀,培養世界共同體意識。在保護地研修中,他們的足跡到過墨爾多山自然保護區、被譽為橫斷山脈之心的格聶山以及橫斷山脈最高峰貢嘎雪山,在真實的自然環境中進行地質學、動植物學等相關課題的學習。志愿者陸佳瑤是牛津大學地球科學系的在讀學生,于她而言,在森林學校中所得到的自然體驗是極為重要的一課。“一抬頭便是漫天的星星,同時被大鵬鳥巨翅般的山脈環繞。我對行星與山脈有著完全的信任和尊敬,這是一種臣服。”
如何與家鄉的土地再度相連
森林學校的學生,不僅有從城市中千里迢迢而來的孩子,還有許多丹巴縣的學生。2019年,274名丹巴高中學生、37名中路鄉小學學生,成為森林學校生態教育入校園的首批受益學生。其中一節課,沈書琴與團隊成員們將在種子博物館項目中制作的標本與搜集的種子帶到丹巴高中的課堂上,為學生們上了一堂“種子的奧秘”。許多種子,孩子們或許看到過,卻并不了解。“我們會說到這個地方屬于橫斷山脈,是生物多樣性的全球熱點地區之一,這里還有很多稀有的動植物,孩子們就會覺得非常新鮮,同時也很自豪,發現原來自己的家鄉這么厲害。”沈書琴介紹道。
中路鄉有200多名學齡兒童,許多去了外地讀書,每年放寒暑假才回家鄉。森林學校邀請這些在外求學的丹巴學生,回到家鄉參與鄉土文化課程。在成都讀初中的劉光佳在森林學校的活動中,第一次參加了敬山儀式。“雖然是當地人,但我從來沒有刻意了解過周圍的神山,當我看到一棵棵高大的白樺樹和隨風飄揚的經幡時,我的內心被震撼了,這里是我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啊,這里是多么的美好……”劉光佳說。
沈書琴告訴記者,當地的孩子,其實也沒有太多時間與自然共處。他們對于腳下的這片土地,同樣缺乏深入了解的機會。山村留不住年輕人,也鮮少有人意識到當地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我們希望能在保護區社區的年輕一代心底,種下熱愛與保護大自然的種子。希望更多當地人能通過森林學校與家鄉的土地再度相連,成為家園的守護者。”沈書琴表示這是森林學校在地生態教育的重要目標。
在地性是森林學校的特性。許多生態實踐項目,從前期調研到項目的設計與實施,都與當地村民的期望與需求緊密相連。沈書琴介紹道:“項目中有一部分學習內容就是在地問題的看到與在地智慧的學習。在地性就是全球性,在地問題經過深度挖掘與提煉往往就是全球共通的問題,折射出發展中的困境。”
例如,丹巴臘月村的水磨修復項目。在當地人的記憶里,磨坊不僅是糧食加工的場所,也是人們情感和價值傳遞的紐帶。水磨的落寞預示著民族文化所面臨的斷層危機。通過修復已廢棄多年的水磨,當地年輕人認識到水磨所承載的文化價值與民族傳統智慧,并自發組織了村文化保護志愿者組織。
又如,中路鄉的古道修復項目。對于當地人來說,古道也不僅僅是腳下的基礎交通,更是連接著情感、宗教和文化的紐帶。但如今,古道因年久失修而變得泥濘,部分路段甚至堆滿了生活垃圾。參與項目的學生們通過“激活”一條古道,激活了當地發展生態旅游的價值與活力,同時也讓當地人看見、認可、尊重自己的傳統文化。
當看到許多外來的志愿者為幫助村莊而努力時,當地的年輕人會受到影響與啟發——覺得自己或許也可以為這個村子做一些事情。27歲的達瓦初曾一度盼望離開村莊,如今她選擇留了下來,成為森林學校的運營團隊成員。“曾經達瓦初很害羞,現在她能像主人一樣,非常流利和自豪地向他人介紹自己的家鄉。”沈書琴表示,希望通過森林學校培養一批這樣的當地年輕人,未來他們將成為建設家鄉的中堅力量。“當地人如何在家鄉找到發展的機會,并能夠有意識地去保護這片土地,找到一個發展與保護間的平衡,這是非常重要的。而希望就在年輕一代。”
探索自我,篤信改變世界的夢想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沈書琴作為大學生志愿者參與了重建當地小學的項目。這個項目讓她看到“原來,我的行動可以為他人帶來改變”。在芬蘭留學時,沈書琴經常和不同專業背景的同學一起,就一個議題以藝術作品的方式作出回應,在這個過程中向真實的世界學習。而他們的作品,也對真實的世界產生了作用。沈書琴第一次參與的工作坊在芬蘭圖爾庫。圖爾庫擁有芬蘭唯一一個中世紀留下來的廣場。在“高效”的網格化規劃思路的影響下,政府規劃建設了一條橫穿古老廣場的車行道,將廣場一分為二,并計劃進一步拓寬這條路。針對這一快速發展與當地環境間的矛盾,沈書琴做了一個“很小”的作品:一天深夜,她用手在路中間鉆了一個洞,在洞里放入了植物種子;她的一位同學則將中世紀的篝火搬到了路面上。后來,這一作品被當地報紙報道,引發了全城人的討論和思考。政府最終改變了原來的規劃,將橫穿廣場的車行道改為地下通道。
學生時代的經歷,給予了沈書琴開闊的視野與篤定的信心。“在一個真實的項目中,你會碰到真實的人,你會提出你的想法,你會被否定,也會被支持,但你還是會努力地付出行動,去實現你的想法,然后你會看到你的行動給世界帶來的改變。”沈書琴認為,這種基于真實社會的學習對于學生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把過去自己體驗過的、讓我有所改變的、我認可的東西,帶給更多的人。”反映在森林學校的教育方法上,即強調“在解決真實問題中學習”,運用跨學科項目制學習的方式,讓學生通過自主學習,解決真實、復雜的問題,最終完成一項工程或作品,獲得與項目相關的重要知識和技能。
當被問及創變未來的人需要具備哪些特質時,沈書琴向記者介紹了森林學校的教育板塊。除了以培養地球共同體意識為主題的喜馬拉雅生態學院,還有三個重要板塊——生命成長學院,強調從自然中獲得內在成長與自我認知的智慧和力量;青年公益學院,培養年輕人的同理心,做到“心中有他人”;貝果商學院,培養具有環境社會責任的未來創變者。“自然是一切的基礎。創變者應有生態意識,能夠認識自我,了解自己進入社會后能做什么,將學習、工作、生活與生態相結合,做一些積極利他的行動。”
沈書琴這樣定義森林學校——一座踐行本土創新教育,培養跨學科深度學習的能力,啟發學生遇見未知的自己并篤信改變世界夢想的未來學校。從2015年參與森林學校的創建至今,她已經在這里守候了將近六個年頭,見證著城里孩子與當地年輕人的成長。“我想他們一定不會忘記遼闊的大山、溫暖的陽光、伙伴們的面龐、親手制作的東西、付出的勞動……小小的種子已經種在了他們心里,等待著發芽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