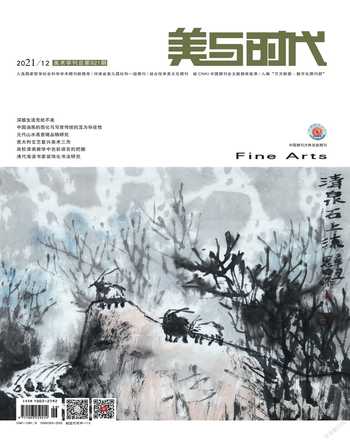繪畫中的“蒙太奇思維”探析
劉爽
摘 要:藝術世界是人類想象的集合,繪畫作品的呈現形式多種多樣,不僅有恢弘壯闊、場面宏大的歷史畫,也有諸多如中國卷軸畫般需要用“游歷”的觀看方式欣賞的繪畫作品。畫家用不同的手法把原本一目了然的畫面情節、主題隱藏或隱喻在畫面中,等待觀眾的解讀。而面對畫幅限制的問題,藝術家巧妙地使用蒙太奇手法把大千世界用幾幅畫展現出來。基于此,挖掘“蒙太奇思維”在繪畫作品中更優秀的表現力。
關鍵詞:“蒙太奇思維”;繪畫;時間;空間
“蒙太奇”一詞源于法語,是音譯的外來語,原為建筑學術語,意為構成、裝配,在電影發明之后又在法語中引申為“剪輯”。之后蒙太奇又引申為一種影像專業術語,區別于電影誕生最初一鏡到底的拍攝方式。蘇聯導演庫里肖夫曾做過一個實驗,將同一張無表情的特寫鏡頭與三組不同鏡頭剪輯在一起,這三個鏡頭分別為一個湯碗、一個女孩、一具遺體。觀眾在觀看三組鏡頭的時候,會用人類思維的邏輯性,自動在“開始”和“結束”之間做連線。根據庫里肖夫效應,蒙太奇一詞被用來定義并解釋這種前后連接的關系。“蒙太奇思維”早已經存在于古今中外的繪畫作品中。例如,中國的卷軸畫,或是西方的立體主義、表現主義等,把不同時空的東西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全新的時間和空間,這種組合結構正是蒙太奇手法的一種。
一、繪畫作品中的敘事蒙太奇
敘事蒙太奇主要是將鏡頭按照時間順序或邏輯順序組合在一起,每個鏡頭都含有事態性的內容,讓觀眾把注意力集中在劇情上,使觀眾在能讀懂劇情的前提下對時間和空間進行重組。在敘事蒙太奇中,有一種顛倒蒙太奇,它將故事發展的時間順序打亂重組,將現在、過去、回憶,和幻覺的時空有機地交織在一起。早在中國古代,繪畫就已經開始作為敘事的工具,當時的畫家為解決畫幅對信息量的限制想出了很多方法。西方的繪畫從中世紀時期開始就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畫面的空間和透視關系隨畫家的需要而更改,出現一種把繪畫進行剪切、拼貼的手法,這種手法與電影技術發明后使用的蒙太奇手法如出一轍。
在制作工藝不發達的古代,繪畫作品是靜止的,只能記敘事件發生的特定時間和空間內的信息。不同于舞臺戲劇與文學作品,繪畫只能表現瞬間事件的特性使一幅畫具備的信息量相比于電影、小說而言恐怕僅有一個杯底那么多。蒙太奇手法的介入把繪畫原本的單一視點改為多視點,增加了繪畫作品的信息量。無論是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壁畫,或是中國古代人物故事畫,都出現過同一人物在不同時空、不同情節下的單幅繪畫作品。這就是“蒙太奇思維”在繪畫作品中的運用。在梅姆林的作品《圣母的歡樂》中,盤曲的小路上多次出現耶穌的形象,跟隨著畫面中隱藏的單線任務式路線,完整地講述了耶穌一路上發生的故事。敘事視角可以簡單分為兩種,即全知視角和限知視角。全知視角類似于“上帝視角”,可以知曉故事的全部情節;限知視角是指個體只具有單一的視點。運用蒙太奇手法繪制的《圣母的歡樂》就是一種全知視角,觀眾在觀看該作品時可以像拖動電影的進度條一樣自由調節故事進度,對畫面主觀構建多個視點。使用了蒙太奇手法的繪畫作品解決了傳統繪畫中時間和空間的矛盾問題,這種創新可以理解為一種人為的、非合理性的戲劇沖突。
在中國,蒙太奇手法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出現,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代帛畫《轪侯妻帛畫》,畫中人物漫長的人生經歷很難完整地在尺寸有限的經幡上訴說明白,運用蒙太奇手法則可以最大限度地突破畫幅的限制,把不同時空的故事拼在一起。南唐畫家顧閎中利用長卷式構圖創作的《韓熙載夜宴圖》中,將五個場景用屏風分割,將不同時間和不同空間的人物安排在一幅長卷中。這種采用段落式空間的敘事方式頗具“蒙太奇思維”。
在我國的文化瑰寶敦煌壁畫中有一幅本生故事畫把蒙太奇手法運用得更具形式美感。北魏時期,敦煌254窟南壁描繪的《薩埵那太子本生圖》在構圖上用蒙太奇手法把不同視點交織在一起。乍一看,畫面中的人物故事繁雜,不容易看出這幅畫的精妙之處,仔細看就會發現,這幅畫是將不同時間和空間內發生的十個情節交織在一起。現藏于428窟的《舍身飼虎圖》的畫面布局沒有特定的規律,情節安排自下而上再到中心。北周時期,在第257窟東壁門南描繪的《鹿王本生圖》用的是普通的構圖方式,故事在獨立的場景中發生,將各個故事用山巧妙分屏,這種分段的方式與《韓熙載夜宴圖》有異曲同工之妙。《鹿王本生圖》的情節順序呈橫向發展,與《圣母的歡樂》的故事情節表現手法一樣,都是橫向線性發生,類似現在的橫幅連環畫。這兩幅繪畫作品雖然都運用了蒙太奇手法,但《鹿王本生畫》更具沖突效果,構圖上也更具形式美感。但時代最終選擇了“再現型”的繪畫理念,使用固定的透視法作為常規的繪畫方式。從歷史上看,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古典美學家們將模仿現實事物的精準度視為藝術的進步,刻畫出能夠以假亂真的畫面成為畫家的目標,西方繪畫逐漸由平面走向立體,符合傳統透視的繪畫方式開始長時間占據繪畫領域。
二、具有詩意境界的表現蒙太奇
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技術的進步使攝影設備的造價愈發低廉,雖不至于一文不值,但也成為普通人用一個月的薪水即可消費得起的新奇物件,一閃即逝的時光成了隨手可得的“廉價物品”。繪畫作品中用敘事蒙太奇制造的戲劇性沖突元素隨著圖像的泛濫與后現代主義的發展逐漸被畫家拋棄。
表現蒙太奇不同于敘事蒙太奇,它致力于在觀眾思想中不斷產生割裂效果,使觀眾在理性上失去平衡。表現蒙太奇中有一個分類為抒情蒙太奇,也可說是詩意蒙太奇,它可以連接兩組看似毫無關系但卻具有隱喻或暗示意味的鏡頭。不少藝術家將詩意判定為藝術的最高境界,具有詩意的藝術作品往往看似一目了然,但卻雋永深刻。如果說敘事蒙太奇手法將時間用因果關系連接起來,那詩意則具有無因果的關聯性。詩意蒙太奇作品使用的是日常熟知或可見的元素,但拼湊在一起,無論是在色彩上還是在構圖上都具有一種神秘的特質,讓人不能一眼看懂畫中的主題或內容。但是,通過畫面中的元素能夠領略到別具一格的詩意,就像“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或是在影片中,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突然將畫面轉到了水面或者竹林,這些看似無意義的空鏡頭為觀眾留下了無盡的思考空間,再或是日本雋永的俳句,“海暗了,鷗鳥的叫聲微白”。這種轉變看似沒有原因,但在實際上各元素之間存在著關聯性。詩意的畫面或許能讓觀眾形成一種理性或非理性的概念,并逐漸成為一種流淌著的思維。詩意的概念是模糊的,但一定是富有意境的。
基里科采用“形而上”繪畫手法的繪畫作品是運用表現蒙太奇手法體現詩意的典范,他的作品將不和諧的建筑和具象靜物進行組合,仿佛是把現實世界和夢境這兩個不同的維度融合在一起,借由繪畫的形式傳達對哲思的探索。基里科在文學上受到尼采和叔本華的影響,叔本華思想中對自在之物的思考繼承于康德,因此,基里科將意志認定為不可遏制的、盲目的沖動,在理性背后是非理性的思想在運作。
基里科作品中常見的廣場、雕塑是非常具象的,物與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這種把無關的元素拼接在一起的手法,使藝術家通過藝術作品進行表達時不再受現實世界時空的限制,甚至也已不再是某種特定的情感的抒發,而是對于事物真實存在的形式的深層揭示,用分離的手法來表現尋常事物背后的非理性思維。如塔可夫斯基的詩意性電影一樣,基里科的作品沒有一條線性的、完整的故事,而是采用碎片化、非線性的敘事方式。這種敘事方式是塔可夫斯基強調的“詩的邏輯”。基里科繪畫作品中昏黃的顏色與刻意拉長的影子讓那些希臘式的雕像顯得格外有質感。在這一點上,基里科的作品打破了萊辛在《拉奧孔》中開篇寫的“畫是空間的藝術,詩是時間的藝術”,與米切爾在《布萊克的合成藝術:一個插圖詩的研究》中對形象與文本的研究相符,基里科的繪畫作品中不僅有空間觀念,而且暗含了時間的存在。詩和繪畫并不是二元對立的,萊辛認為,詩和畫都是在模仿自然,但是媒介的不同導致了藝術表現上的不同,他或多或少把詩奉為更高級的藝術形式。格林伯格在支持“形式主義”的時候以威廉·布萊克的作品為例,反對萊辛“詩如畫”的觀點。他認為,“圖畫”不只是對一個文本的模仿,而是有自己的象征維度。”從西方的藝術發展史來看,繪畫作品中的敘事蒙太奇在美術的發展中逐漸退化。故事性逐漸從繪畫作品中消失,從馬奈的“為藝術而藝術”開始,繪畫作品中的形式、語言逐漸從敘事功能中獨立出來,作為繪畫作品受人欣賞的主要部分。新萊比錫畫派中堅人物尼奧·勞赫的繪畫作品把如夢境一樣的場景展現在畫布上,把各種場景編組在一起,將夢幻與現實進行模糊化處理,把那些在現實生活中對于社會、制度的情感通過繪畫抒發出來。模糊化的處理方式也傳達了當下人們的迷惘與思考。社會發展至此,畫家在二維平面上的“仿真”技術再高超,恐怕也無法超越相機。在繪畫語言發展趨于多元化的今天,飽含藝術形式的知識都是一座座值得挖掘的思維寶庫,“蒙太奇思維”的應用和研究或許將為當代繪畫內容和形式的創新注入新鮮的血液。
參考文獻:
[1]愛森斯坦.蒙太奇論[M].富瀾,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9.
[2]馬爾丹.電影語言[M].何震滏,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
[3]鄧燭非.電影蒙太奇概論[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
[4]德勒茲.時間:影像[M].謝強,蔡若明,馬月,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
[5]萊辛.拉奧孔[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作者單位:
中央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