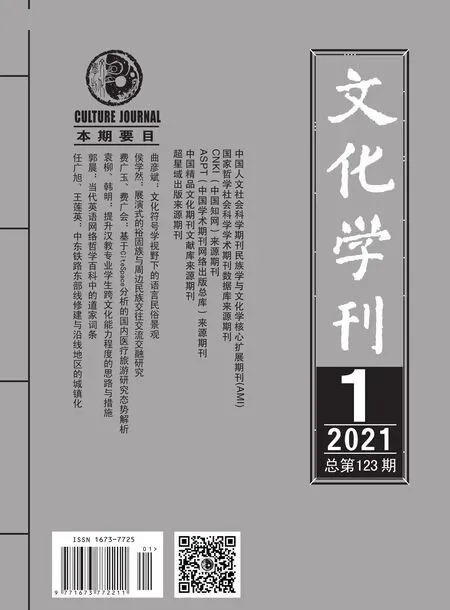亞里士多德幸福理論的分層解讀
辛 苗
一、亞里士多德幸福理論的歷史淵源
很多學(xué)者都聚焦于亞里士多德對幸福理論的闡釋,但是真正在西方率先論及幸福理論的還不是亞里士多德,之所以古今中外的學(xué)者們都熱衷于研究和探索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論,主要是因為他提出的幸福理論比較具有權(quán)威性、典型性和代表性。事實(shí)上,在亞里士多德之前就有很多古希臘的先哲們對幸福理論作了深入的思考、探索和論述。基于對古代先賢們有關(guān)論述的分析和反思,亞里士多德在批判繼承前人論述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自己的幸福理論。換言之,前人的研究為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論提供了理論支撐,成為其存在的歷史依據(jù)和歷史淵源。
古希臘先賢們對幸福理論的思考始于對幸福含義的探索。從感性的角度來說,他們對于幸福的含義的理解和闡述也具有很多感性思考、判斷和分析。在此意義上講,他們起初所探索的包含了他們基于一些基本生活經(jīng)驗的感性標(biāo)準(zhǔn),進(jìn)而對自身以及他者切身生活經(jīng)驗作感性思考。
辯證唯物主義認(rèn)識論告訴我們,人類對事物的認(rèn)識總會從感性向理性過渡和轉(zhuǎn)化,古希臘先賢對人類幸福的認(rèn)識也不例外。因此,從理性的角度來說,他們對衡量幸福的標(biāo)準(zhǔn)也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初步凸顯出他們理性的思考、判斷和分析。不過,由于當(dāng)時的研究條件和技術(shù)手段等的限制,要找到一個客觀而又理性的標(biāo)準(zhǔn)也并不容易,除非他們能夠通過某種特別的研究手段真正了解衡量人類幸福的理性標(biāo)準(zhǔn)。正因如此,這些判斷和衡量人類幸福的理性標(biāo)準(zhǔn)被深深地隱藏于人類的意識深處而不容易被挖掘出來。結(jié)果,這些理性的判斷和衡量標(biāo)準(zhǔn)常常被人類在不知不覺中用其主觀而又感性的直覺來替代了。從本質(zhì)上說,這也正是享樂主義幸福觀的錯誤之處。
在古希臘學(xué)術(shù)研究的歷史上,從蘇格拉底到斯多亞學(xué)派的先哲們已經(jīng)開始認(rèn)識到了這種存在于人類潛意識中的理性標(biāo)準(zhǔn),并一致認(rèn)為這種理性就是人類善良的本性。首先,蘇格拉底認(rèn)為:“一切的存在都是在追求其完美性,以‘善’為目標(biāo)是其存在的根本理由。追求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標(biāo)志,是人獲得真正幸福的保證。”[1]28可以說,善良作為一種德性知識是人們理解幸福和獲得幸福的前提。在善良的基礎(chǔ)之上,蘇格拉底提出且奠定了幸福理論的理論基礎(chǔ)并確立了其理論雛形。其次,時隔一段時間,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又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發(fā)展和完善了這一理論雛形,并為其精心設(shè)計完成了最初的理論構(gòu)架。再者,亞里士多德在其倫理學(xué)著作中,為其幸福理論找到了更為基礎(chǔ)的理論框架:以善良為基礎(chǔ)的至善[2]18。在他看來,人類所從事的每種技藝與研究以及所參與的每種實(shí)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良為目的。善良是在參與這些活動的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應(yīng)追求的目的。因此,人要獲得最大的幸福就應(yīng)該先擁有至高的善良。古希臘時期先哲們有關(guān)幸福觀的論述,為亞里士多德確立其幸福理論打下了堅實(shí)的基礎(chǔ)。正是在吸收前人關(guān)于幸福理論的思想精華的基礎(chǔ)上,亞里士多德經(jīng)過反復(fù)對比、分析和反思,發(fā)展和完善了他們的理論,最終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
二、亞里士多德幸福理念的概念范疇
古希臘時期先哲們在幸福觀方面的論述,為亞里士多德幸福理論的確立打下了堅實(shí)的基礎(chǔ)。值得一提的是,亞里士多德明確界定了幸福理論的概念范疇。事實(shí)上,先賢們思考和探索幸福理論的歷史軌跡,已表明亞里士多德所發(fā)展的幸福理論是有明顯的概念區(qū)分的。這個概念范疇包含他在《尼可馬倫理學(xué)》中主張的至善的幸福、美德的幸福、節(jié)欲的幸福、適度的幸福和沉思的幸福。不過,幾乎上述每一個范疇都從不同視角將人類的善良這一根本的特征貫串他的整個理論體系中。由此可見,善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jīng)成為亞里士多德幸福理論的核心理念,因為它是人類一切快樂、滿足、愉悅、友誼、愛情和婚姻等情感體驗和社會交往的源泉。在上述四大理論范疇中,四者之間相互聯(lián)系、相互補(bǔ)充、相互完善;當(dāng)然,有時也相互沖突。
三、亞里士多德幸福理論的內(nèi)涵
(一)幸福是至善
早在古希臘先哲蘇格拉底生活的年代,蘇格拉底就率先在西方倫理思想史上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了善良這一基本概念。他明確提出了人生的最大目標(biāo)就是盡可能地實(shí)現(xiàn)人們的善良。不僅如此,他還從各個不同角度系統(tǒng)地論述和探究人的善良,這為其最終確立幸福理論體系打下基礎(chǔ)。
此后,亞里士多德又進(jìn)一步豐富和完善了蘇格拉底基于善良的幸福理論,并把它當(dāng)作其研究的理論起點(diǎn)。具體說來,亞里士多德所倡導(dǎo)的善良具體指向善良的兩個方面:具體的善良和最終的善良。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前者指的是體現(xiàn)在不同的情形,如榮譽(yù)、快樂和美德等之中的具體目的[2]18;從因果關(guān)系來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可見,作為人生目的的善良,既可能體現(xiàn)在某些具體情形的具體善良之中,又可能體現(xiàn)在具體情形之外的最終善良或者最高的善良之中[3]5。
(二)幸福是美德
除了對關(guān)于善良進(jìn)行過思考之外,亞里士多德也開始思考關(guān)于美德的幸福。具體來說,他把人類的幸福生活具體劃分為兩個方面,即沉思的幸福生活和有美德的幸福生活。前者闡發(fā)的是人類幸福生活的本義,后者闡發(fā)的則是其引申義。由此推斷,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幸福之人應(yīng)該是既過著沉思的幸福生活又過著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的人,因為這兩種意義上的幸福生活將人類的善良和美德都有機(jī)地融合在其幸福理論之中。
在亞里士多德以及其他許多哲學(xué)家看來,人的美德往往是相對于其理性的靈魂和良好的欲求而言的,因為“美德和其他技術(shù)一樣,是用了才有,不是有了才用”[4]。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美德是人在其特有的幸福生活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優(yōu)點(diǎn)和促使其實(shí)現(xiàn)上述幸福生活所需要的品質(zhì)。換言之,美德也就是使人類日趨向善和臻于完善,同時也是實(shí)現(xiàn)其幸福生活的美好品質(zhì)。簡而言之,亞里士多德所闡釋的幸福本身也就是人類善良和美德品質(zhì)的延續(xù)和發(fā)展。
(三)幸福是節(jié)欲
基于幸福獲得的歷史過程,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以下論斷以進(jìn)一步豐富和完善其幸福理論。首先,他認(rèn)為人類的幸福是人類在某種學(xué)習(xí)過程中、養(yǎng)成某種習(xí)慣以及在長期的學(xué)習(xí)和模仿過程中自然而然獲得的[5]116。其次,他認(rèn)為人類獲取幸福的關(guān)鍵在于凈化自己的靈魂,即節(jié)制心中的欲望和樹立高尚的美德,使自己在追求靈魂的純潔中獲得自身基于善良的幸福。在他看來,這種幸福的獲得“需要完全的善和一生的時間”[1]26。再次,他始終相信需要獲取幸福的人類始終堅持樹立和發(fā)揚(yáng)自己的美德,規(guī)范和約束自己的言行,養(yǎng)成良好的習(xí)慣,最大限度地傳遞和匯聚自身的善良。
(四)幸福是適度
在闡述基于善良、美德、節(jié)制的幸福的同時,亞里士多德也強(qiáng)調(diào)適度。在他看來,人類在追求基于上述特質(zhì)的幸福的時候,也不能過于極端,應(yīng)該把握適度的原則,在各種看似矛盾對立的特質(zhì)之間學(xué)會取舍、取得平衡。這是因為,從人的本性上說,人是不會滿足沉思的生活和有美德的生活的;相反,人類還“需要健康的身體和他者的照料”[1]310,除了內(nèi)在的善良,人類的幸福還應(yīng)基于外在的善良。不過,亞里士多德指出在處理內(nèi)在善良和外在善良的同時應(yīng)該本著適度原則。
(五)幸福是沉思
為了確立幸福理論,亞里士多德根據(jù)人類對幸福的不同理解把人的生活進(jìn)行了以下分類:享樂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的生活。他的研究和觀察顯示:多數(shù)人想過享樂的生活,因為他們想要實(shí)現(xiàn)各自目的不同的奴性生活[3]52;有些人想要過政治生活,因為他們特別在意自己的名聲并把榮譽(yù)誤認(rèn)為是幸福,然后就讓自己終生都在艱辛的政治生活的奴役之下生活。在這三種生活中,亞里士多德最主張沉思的生活,因為他認(rèn)為基于沉思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貴的生活,也是最大的幸福。
四、亞里士多德幸福理論對我國當(dāng)代生活的重要意義
首先,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理念有助于激發(fā)個人的進(jìn)取精神,他認(rèn)為幸福是靠后天的努力而得到的,不是人生來就有的,要實(shí)現(xiàn)長久的幸福只有靠自己后天的學(xué)習(xí)、實(shí)踐才能不斷提升自己的幸福感。這種理論啟示我們要想獲得長久的幸福,必須要不斷地學(xué)習(xí)和參加社會實(shí)踐,更要不斷地提升自己的德性修養(yǎng),這樣我們在實(shí)現(xiàn)自己的人生目標(biāo)的過程中才能獲得幸福感。反之,如果一個人不注重后天學(xué)習(xí)和德性的培養(yǎng),就會喪失人生的奮斗目標(biāo),目光短淺,胸?zé)o大志。在學(xué)習(xí)和工作中也會消極懈怠,不思進(jìn)取,最終會感到毫無幸福感可言。
其次,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理念有助于個人的精神層面的提升,他認(rèn)為人的幸福不只是物質(zhì)上的滿足就獲得幸福感,也不是獲得各種名利、權(quán)利就能幸福,而在于靈魂都能按照理性開展各種積極的現(xiàn)實(shí)活動,即使在物質(zhì)比較匱乏的時候,只要精神層面的追求存在,在努力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的過程中,人的精神層面的滿足才是真正的幸福。新時代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美好愿望,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為獲得幸福感才是人生追求的目標(biāo)。現(xiàn)今社會很多人認(rèn)為追求金錢、權(quán)利、地位才能獲得幸福感,所以“拜金主義”“利己主義”“官本位”等不良風(fēng)氣和思想才會存在。因此,學(xué)習(xí)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論對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都有重要的意義。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相對而言,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論有著較長的理論淵源、有著較寬的概念范疇以及較深刻的理論內(nèi)涵,因為他的幸福理論已全面涵蓋了至善的幸福、美德的幸福、節(jié)欲的幸福、適度的幸福和沉思的幸福。可以說,他的幸福理論至今對人們都有非常深遠(yuǎn)的意義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