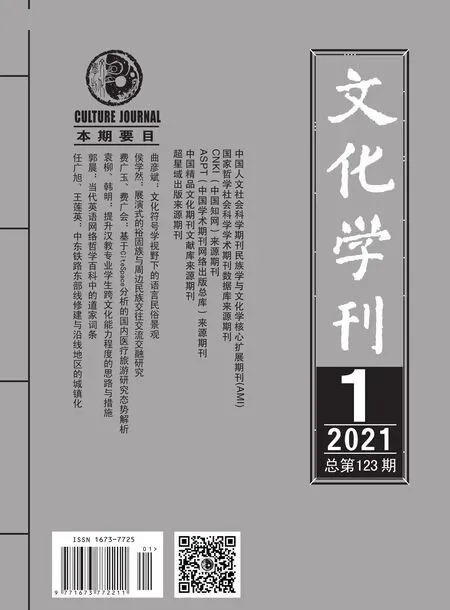得意與愧悔:“貳臣”吳偉業的尷尬處境
——以吳偉業散文為例分析
齊睿聰
吳偉業,生于萬歷三十七年(1609),卒于康熙十一年(1672),字駿公,號梅村,江南太倉人。吳偉業為明崇禎四年(1631)進士。順治十年(1653)被強征入京,授予秘書院侍講,國子監祭酒,參與《順治大訓》《內政輯要》等書的纂修。順治十三年(1656)以丁憂為由逃離官場,再未出仕。吳偉業在明清易代之際變節,身仕二朝,故屬“貳臣”之列。欲仕明而明亡,不愿仕清而不得不仕清。作為前朝臣子,無法融入新朝,更不能實現政治理想,吳偉業作為“貳臣”,面臨極為尷尬的處境。
一、吳偉業散文評價
吳偉業詩詞流傳甚廣,而散文為人所忽視。《四庫全書總目》高度贊揚吳偉業詩歌而貶低其散文的價值,呈現截然不同的褒貶態度。書評吳偉業散文,引用黃宗羲的評價:“惟古文每參以偭偶,即異齊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黃宗羲嘗稱《梅村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于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為倒卻文章家架子,其糾彈頗當。蓋詞人之作散文,猶道學之作韻語,雖強為學步,本質終存也。然少陵詩冠千古,而無韻之文率不可讀。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也。”[1]黃宗羲不滿吳偉業散文的文人筆法,認為自己遵守嚴格的章法、用透徹的論述而作之文,才可為后世學者確立寫文章的體式和標準,言辭辛辣犀利,卻有失公允,否定了吳偉業散文的所有成就。
作為有著錚錚鐵骨遺民的黃宗羲,對吳偉業的諷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貳臣”的身份。針對時人對吳偉業文章的攻擊批判,陳瑚贊其“憶瑚煩躁發時,先生以制舉義冠南宮,反天下程文腐爛之弊,而振之以東西兩漢、唐、宋八家之學,一時號稱得人”[2]1490,贊揚了其制舉之文。尤侗稱他“先生文章仿佛班史,然猶謙讓未遑,嘗謂予曰:‘若文則吾豈敢,于詩或庶幾焉’”[2]1494。尤侗推崇吳偉業散文,也非常欣賞他謙遜的品格。歸莊則評價吳偉業“博極群書,才備眾體。柳子厚謂:‘詩、古文二者,燕公、曲江所不能兼。’而先生兩擅其長,韶夏之音,山龍之采,蛟蟠鳳躍之狀,震耀耳目,不可測識”[3]。作為吳偉業的朋友,這些評價略顯溢美,卻提醒人們注意被忽視的吳文。
清朝官方對吳偉業散文作品多消極評價,導致其散文價值未被充分挖掘。吳偉業散文稍遜于其他文體的作品,但也是分析他人生經歷的各階段心態的重要環節。
二、前半生:承蒙圣恩,春風得意
在明代,吳偉業持有傳統的儒家道德觀念。崇禎四年(1631)參加會試,奪得會元,應殿試,中一甲第二名,少年高第,獲得了崇禎皇帝的賞識和優待。兩榜聯捷和賜假歸娶的榮耀使他春風得意,風光無兩。在這個階段,吳偉業光明正大、名正言順地在仕途上內圣外王,謀求修齊治平。
吳偉業出生于一個家道中落的清貧塾師之家,從小與書本為伴,生活難以為繼,境況困窘。“嘗吾父之有聲場屋,屢試不收,而祖母湯淑人已老,家貧無以為養,吾母為余言之而泣。”[2]1016可見,吳偉業企望通過科舉實現政治抱負,也希望改善家庭窘迫的現狀。受崇禎帝的賞識拔擢使得他一生都頗為感激,這也正是他入清為官后產生糾結痛苦心理的重要原因。
吳偉業早期散文以科舉制藝的創作為主,大量時文創作體現了他在政治上的進取之心,如早期的八股文稿《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4]。此類制藝類文章立足于經史,追本溯源,分析透徹精辟。由于其“年壯志得”而“特厭苦俗儒之所為”,體現在文章中,即為“騁其無涯之詞”,將自己的見解在文章中肆意表達抒發。在《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中,吳偉業針對“用人之法”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同時抒發了自己希望進入仕途的遠大志向。
吳偉業年少時兩榜聯捷且高中榜眼,從為生計發愁、為科舉考試閉門苦讀的吳中學子變成參與國家大事、立朝聽政的官員。崇禎九年(1636),吳偉業典試湖廣,創作了《湖廣鄉試程錄》,該文集是其政論文的典型。吳偉業初入仕途,經觀察和了解時局,犀利地覺察到了“今者內寇外虜”的國家危機,并為解決問題提出切中要害的辦法。在《第三問》中,吳偉業歷數農民起義和明軍討賊過程,提出三點軍中之弊。吳偉業直截了當、清晰明暢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其言切中時弊,體現了他深厚的憂患意識和對解決人民問題的強烈緊迫感。
三、后半生:進退失據,落魄愧悔
在國破家亡、生死劫難的易代之際,吳偉業背棄儒家經典的教導、辜負前朝君主深恩而變節,且仕于為中原漢族文化所鄙棄的異族政權。變節之舉是對吳偉業平生人格和人生信念的侮辱與毀滅,因此,他茍且偷生的后半生在進退失據的落魄與大節已虧的愧悔中度過。
明亡前,吳偉業多創作應試時文和參政、議政的文章;明亡后,吳偉業遠離政治中心,轉而更多創作與友人交游中的應酬贈文。吳偉業與友人共歷江山易主,且共懷故國之思,文章情感激蕩、郁憤。特別是他為故友所作序文、墓志銘等散文,因情感深厚而真切動人。
如吳偉業在明亡仕清前創作的《彭燕又偶存草序》,其大量詩文“累牘連章,盈囊溢幾”,經歷戰亂后“卷帙磨滅,十不傳一”,甚至“蕩為云煙,散為灰燼”[2]670-671。“偶存”言詩,實言人事,他借此感嘆江山易主后的故交零落。吳偉業揭露了戰亂的生活對文化的摧殘和毀滅,字里行間毫不掩飾地傾瀉著哀傷、悲憤之情,體現了對故國的魂牽夢縈和對滿清統治破壞和平生活的極度不滿。
順治十年(1653)九月,吳偉業懷著愧疚和恥辱的心情入京,這與在明代通過科舉入朝為官的心境大為不同。接近京城時,他在《將至京師寄當事諸老·其四》中寫下“記送鐵崖詩句好,白衣宣至白衣還”這樣無奈反抗的詩句。這種矛盾的心情在《與子暻書》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改革后吾閉門不通人物,然虛名在人,每東南有一獄,長慮收者在門,及詩禍史禍,惴惴莫保。十年,危疑稍定,謂可養親終身,不意薦剡牽連,逼迫萬狀,老親懼禍,流涕催裝。同事者有借吾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2]1132
茍且偷生、大節已虧的吳偉業仕清及以后的應酬、應制文,多有言不由衷、用典過繁、諛詞太重之弊。文章套路較為固定,情感不夠真切動人,語言不夠質樸細膩,文學價值不高。同明代創作的感情真摯強烈的文章相比,此時吳偉業的應制、應酬之作更顯無聊、虛假。這一階段吳偉業文章的創作水平完全不及前期創作,這恰是吳偉業茍活于異族政權統治下,自幼秉持忠君不貳信念崩塌的反映。
在此時期,吳偉業多創作華麗富贍而缺乏真實情感與深刻內涵的阿諛奉承之作。如吳偉業創作于順治十二年(1655)御試之時的《擬上親征朝鮮大捷,國王率其臣民歸降,群臣賀表(崇德二)》,盛贊皇太極“允文允武,乃圣乃神”。他在順治十六年(1659)所作的《江海膚功詩序》贊梁化鳳“庸江寧一捷,再造南土”[2]732,他在康熙四年(1665)創作的《梁宮保壯猷記》“今日江湖生齒,煙火晏然,誰之賜也?公之德豈不大哉!”[2]638亦充溢著華麗的贊美。諛奉表功的語言降低了吳偉業文章的水平,種種偏離本心且質量不高的應酬之作,更體現出這是源于自身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做出的最為“安全”的選擇。
仕清三年后,故國之思與失節之恥使吳偉業的余生在惴惴不安和無盡的愧悔中度過。變節仕清的行為有悖于儒家傳統,更為人所鄙棄。吳偉業對自己的內心進行了無情的剖析和拷問,他身仕兩朝,對明不忠,也未被清朝接納,于是臨終之際只能無奈選擇以僧裝入殮,并鐫以“詩人吳梅村之墓”,體現出不能忘懷故國亦不能忘記失節恥辱事實的萬般無奈。他在《與子暻書》中自述“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2]1133,充分概括了自己作為“貳臣”的亡國之痛、易主之悲、失節之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