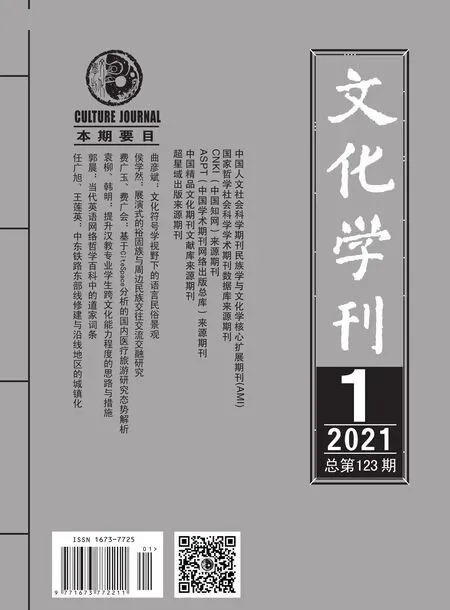羅馬帝國與中世紀西歐的自治城市比較研究
楊婉嘉 王振霞
自治城市是羅馬帝國與中世紀西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相對獨立的政治共同體,且都是政治體制不完善的產(chǎn)物。但二者處于不同的歷史文明階段,歷史背景不同,因此二者的自治城市也有許多不同之處。通過在起源、本質(zhì)及其影響上的比較,可以進一步厘清羅馬帝國自治城市與中世紀西歐自治城市的差異。
一、自治城市的起源
自治城市是統(tǒng)治體制不完善的產(chǎn)物。羅馬帝國和中世紀西歐都屬于君主專制體制,羅馬帝國是在武力征服中形成的從城邦體制發(fā)展而來的軍事與行政的結(jié)合體,所以早期帝國不具備一個完善、有效的管理體系。早期帝國的官僚體制僅僅是輔助機構(gòu)和監(jiān)督機構(gòu),地方的自治城市才是早期羅馬帝國維持統(tǒng)治的重要手段,因此羅馬政府極少干預(yù)城市事務(wù)。如果說它也有所干預(yù)的話,那只是協(xié)助城市對自己的事務(wù)推行更為有效的管理而已。[1]“它幾乎只專管收稅(大多由城市經(jīng)手),經(jīng)營皇莊和國家的田莊,以及管一部分司法事務(wù),其余就不過問了。”[2]同樣,封建制度的脆弱與不完善也是中世紀西歐城市自治的一個重要原因。日耳曼人在西羅馬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國家,這些國家形成了中世紀的西歐各國。日耳曼人沒有公共權(quán)力的概念,因此沒有形成權(quán)力組織對國家進行有效的控制。隨著封建制度的不斷發(fā)展,王權(quán)日漸衰微,而封建主的私權(quán)卻日漸強大。封建主在自己的領(lǐng)地中享有,如征稅權(quán)、土地占有權(quán)、征兵權(quán)、土地占有權(quán)、司法審判權(quán)、戶口管理權(quán)、壟斷權(quán)等各種權(quán)力。恩格斯這樣論述當時國王的地位:“在每一個中世紀國家里,國王是整個封建等級制度的最上級,是附庸不能撇開不要的最高首腦,而同時他們又不斷反叛這個最高首腦。”[3]西歐城市之所以有自治權(quán),是因為城市興起于封建主的領(lǐng)地內(nèi),同世俗和教會封建主相對立,因此城市必須爭得且保持同樣的獨立地位才能存在和發(fā)展。隨著君主集權(quán)和官僚體制的完善,羅馬帝國和中世紀西歐的城市喪失自治權(quán)。
此外,羅馬帝國和西歐的自治城市有著不同的社會條件。在古代,政治和軍事力量決定著城市的統(tǒng)治階層和民主利益。羅馬帝國的自治城市與軍事有關(guān),它們大多數(shù)是通過征服而形成的,這些城市的自由民一開始就是強者、征服者[4]。 因此,當羅馬帝國征服地中海世界以后,帝國行政制度的基礎(chǔ)依然是自治城市。中世紀西歐的自治城市則不然,他們絕大多數(shù)是經(jīng)濟發(fā)展和武裝斗爭的結(jié)果。馬克堯先生的觀點是,生產(chǎn)的發(fā)展是中世紀西歐城市興起的基礎(chǔ),但中世紀西歐城市興起的原因卻是多種多樣,比如因手工業(yè)發(fā)展、商業(yè)發(fā)展或是軍事原因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如果說西方城市的政治制度與傳統(tǒng)誕生于羅馬帝國,那么它的經(jīng)濟屬性與商業(yè)屬性則是產(chǎn)生于中世紀的西歐。掌握貨幣使城市具有了經(jīng)濟實力,他們用金錢贖買的方式向封建主購得自治權(quán),貨幣是市民階級巨大的政治平衡器。[5]450
二、城市自治的內(nèi)涵
在羅馬帝國和中世紀西歐,自治城市有一定的獨立性,是管理當?shù)厥聞?wù)和當?shù)毓駲?quán)益的地方自治單位。在羅馬帝國,自治市的管理機關(guān)一般由公民大會、市政官員和市議會組成。公民大會有立法、選舉市政官員的權(quán)力。市政官員由司法官、財務(wù)官、營造官等組成,他們需要具備一定的財產(chǎn)資格才能當選。司法官負責當?shù)厮痉ā⑿姓芾硪约柏敭a(chǎn)調(diào)查;營造官負責公共工程、市場管理和治安事宜;財務(wù)官是當?shù)氐呢斦賳T,多數(shù)市政官員卸任后進入市議會。中世紀西歐城市從封建主那里獲得不同程度的立法、司法、行政管理上的自治權(quán),城市成為了持久的自治共同體。
自治城市社會生活的主體都是自由民。羅馬時期的自由民是除奴隸以外所有居民的統(tǒng)稱。與奴隸不同,自由民擁有獨立的人格,他們不從屬于任何人,其他人也不能對他們進行支配。自由民的根本特征就是享有公民權(quán)與財產(chǎn)權(quán),他們擁有自己的財產(chǎn)、家庭和奴隸,按自己的意愿支配生活,可以享有選舉權(quán)、被選舉權(quán)、婚姻權(quán)、財產(chǎn)權(quán)、訴訟權(quán)等。羅馬時期的自由民分為貴族和平民上下兩層。上層自由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也屬于他們,他們享有大量的財產(chǎn),而且有許多經(jīng)濟政治特權(quán)。而羅馬的下層自由民有少量生產(chǎn)資料,享有人身自由,但沒有政治經(jīng)濟特權(quán),不能參與國家管理大事,且常會受到上層自由民的剝削,向上層自由民繳納賦稅,因此羅馬上下層自由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中世紀西歐的自由城市居民與農(nóng)奴相比享有普遍的人身自由。他們不需要繳納賦稅,“城市基本上是自由的庇護所”[6]。城市居民都可以自由結(jié)婚,可以不受領(lǐng)主的管制自由支配財產(chǎn),可以轉(zhuǎn)讓、抵押、租出或是典當土地,也可以交換、讓渡、饋贈或是遺傳他的動產(chǎn)或是不動產(chǎn),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錢來促進商業(yè)活動。在這種自由的基礎(chǔ)上,一些商人們也締結(jié)契約,成為封建體制之外的自治團體。
此外,羅馬帝國與中世紀西歐城市自治的本質(zhì)不同。羅馬帝國的自治城市源起于古希臘的城邦制度。古希臘時期的城邦自治,具有高度的主權(quán)自由,且公民可以直接參與城邦管理。亞里士多德說,“城邦的一般含義就是為了要維持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shù)的一個公民集團”。[7]后來羅馬帝國統(tǒng)一了地中海世界,保留了其城市自治的傳統(tǒng)。類似城邦時代,市政官員是無薪俸的,因為為城市出力的民政官或是宗教官都把它當作是一種榮耀或是一種負擔,但無論是榮耀或是負擔,城市都不會支付給這些長官們薪俸,也就是說城邦時代的市政官員是沒有報酬的。因此羅馬帝國的城市不再是一個政治機構(gòu)和主權(quán)系統(tǒng),而成了一種行政管理的方式。
自治城市成為了中世紀西歐國家的“體制外權(quán)力中心”,但城市的自治在本質(zhì)上屬于封建特權(quán)。中世紀西歐是以采邑制為經(jīng)濟基礎(chǔ)的社會關(guān)系,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是以土地分封為紐帶所建立起來的人身依附關(guān)系。“在中世紀,權(quán)利,自由和社會存在的每一種形式都表現(xiàn)為一種脫離常規(guī)例外的特權(quán)”[8]。中世紀西歐國家的國王會為封建主頒布特許狀,在法律層面上承認城市的自治權(quán)利,因此城市的自治權(quán)是以與封建主簽署的特許狀為根據(jù)的。特許狀承認了城市內(nèi)市民的身份自由,保障城市市民的人身安全,城市市民的土地所有權(quán)與使用權(quán),免除城市居民的封建賦稅,承認市民享有特定的經(jīng)濟特權(quán),明確城市享有一定的政治管理權(quán),獨立的司法審判權(quán)。中世紀西歐為封建主頒布特許狀,是以契約的方式進入某種以法律形式規(guī)定的身份協(xié)議之中。西歐城市頒布特許狀,不僅使中世紀的西歐誕生了許多新興城市,也使中世紀的西歐走向了法制化的道路,促進了中世紀西歐城市的發(fā)展與封建社會的進步。
三、自治城市的影響
作為法律、政治、思想、文化和本地區(qū)的經(jīng)濟中心,自治城市是羅馬帝國和中世紀西歐各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有利于政局的穩(wěn)定。自治城市是羅馬帝國管理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是各個地方的政治中心。人們在這里討論國家事務(wù)及城邦事務(wù),召開公民大會,進行司法審判。在城邦時代,城市與其周圍農(nóng)村同屬一體,同樣羅馬帝國的自治城市與屬于它的周圍農(nóng)村在政治上屬于一個整體。農(nóng)村居民與城市居民擁有同等的公民權(quán)、政治權(quán)力與社會權(quán)力。隨著公民權(quán)的擴展和行省地位的提高,城市貴族也躋身羅馬元老和騎士階層之中,從而得以參與羅馬國家的政治生活,有利于帝國政局的穩(wěn)定。
在中世紀西歐,城市產(chǎn)生于封建主的領(lǐng)地和堡壘、封建莊園、教會領(lǐng)地和修道院的包圍之中。城市是在束縛人身自由的封建體系包圍下的一個自由、自治的世界[9]。也就是說,城市與它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是分離的。這一分離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中世紀的城市因此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和自由。為了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城市反對封建割據(jù),支持王權(quán),因此與王權(quán)結(jié)盟,對此恩格斯評價說,“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tài)中,王權(quán)是進步的因素,這是十分清楚的。王權(quán)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代表著正在形成的民族而與分裂或叛亂的各附庸國的狀態(tài)對抗。”[5]453同時市民階級參與政治,也促進了議會制度的出現(xiàn)。以上都促進了西歐國家的集權(quán)與穩(wěn)定。
其次,有利于經(jīng)濟的發(fā)展。城市是羅馬帝國的經(jīng)濟中心,自治城市促進了羅馬帝國的經(jīng)濟,特別是行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不過,以土地財產(chǎn)和農(nóng)業(yè)為基礎(chǔ)的自然經(jīng)濟是古羅馬最重要的經(jīng)濟特征,很大一部分城市居民是土地所有者,他們的生活或者依靠耕種他們在城外擁有的土地,或者依靠這些土地的收益,“集中于城市而以周圍土地為領(lǐng)土,為直接消費而從事勞動的小農(nóng)業(yè);作為妻女家庭副業(yè)的那種工業(yè)(紡和織),或僅在個別生產(chǎn)部門才得到獨立發(fā)展的工業(yè)等”[10]476。羅馬帝國城市與屬于它的周圍農(nóng)村在經(jīng)濟上屬于一個整體,且古典時期由于羅馬帝國城市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基礎(chǔ),使它比中世紀城市對農(nóng)村具有更大的依賴性。[11]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一旦奴隸制經(jīng)濟衰退,城市也就開始衰落。
中世紀的西歐封建社會是農(nóng)本經(jīng)濟,城市發(fā)展是從鄉(xiāng)村發(fā)展開始的,并在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對立中獲得了進一步發(fā)展[10]480。城市的發(fā)展帶來商品經(jīng)濟的繁榮,從而引發(fā)了農(nóng)村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變化,瓦解了封建制度自給自足的經(jīng)濟基礎(chǔ),成為西歐封建制度迅速解體的根源,也促進了商業(yè)資本文明的發(fā)展。“凡是在貨幣關(guān)系排擠了人身關(guān)系和貨幣貢賦排擠了實物貢賦的地方,封建關(guān)系就讓位于資產(chǎn)階級關(guān)系。”[5]450城市的發(fā)展為王權(quán)提供了資金支持,也改變了階級關(guān)系的構(gòu)成,產(chǎn)生了資產(chǎn)階級的前身——平民階層。
最后,有利于文化的繁榮。城市是羅馬帝國的文化中心,人們在這里參加各種公共節(jié)日和宗教節(jié)日,也在這里觀看戲劇和決斗表演。羅馬城市按照統(tǒng)一的體制與市政規(guī)劃建設(shè)起來,擁有一致的文化風格及公共設(shè)施。而隨著城市的普遍繁榮與公民權(quán)的不斷發(fā)展,對羅馬古典文化傳統(tǒng)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因為古典文化首先是城市的文化、公民社會的文化,只有奠基于這種更大范圍的公民權(quán)與自治市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古典文化的廣延才不致于使其傳統(tǒng)遭到削弱,反而有所加強。”[12]
中世紀西歐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在當時的西歐,人們只知道一種意識形態(tài),那就是宗教和神學,教會極力宣揚蒙昧主義、禁欲主義和來世主義。自治城市則明顯地區(qū)別于封建體制和教會所建立的社會秩序,文化教育不為教士所壟斷,隨著城市的發(fā)展,漸漸產(chǎn)生了市民所需要的世俗文化,世俗教育。
雖然羅馬帝國與中世紀西歐各國的城市在自治起源和內(nèi)涵上各有異同,但他們都對當時的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