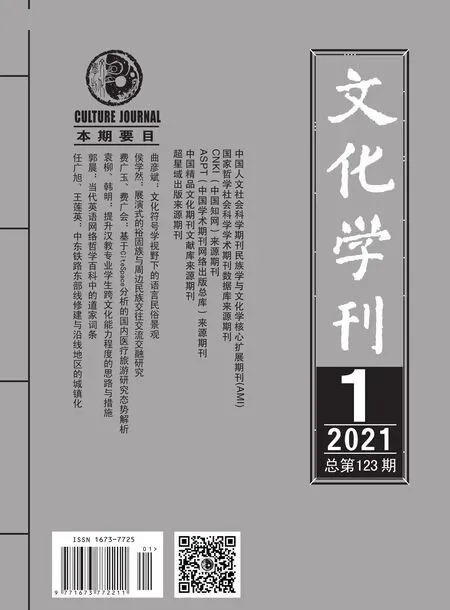關羽形象在朝鮮的接受及神化過程
趙婉彤
中國民間自古就有將德行兼備的英雄封神的習慣,關羽作為本土英雄,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對漢室的“忠義”,對劉備的“情義”,對曹操的“仁義”,對黃忠的“俠義”早已深入人心。他為大義犧牲小我的精神符合東方的審美,所以人們將關羽的形象“武將文雅化,英雄神異化”,稱其為“忠義貫古今、神勇震乾坤”的民族武圣,使關羽這一歷史人物的形象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封神。
一、關羽中國本土形象的神化
關羽中國本土形象的神化主要體現在民間和統治階級兩個層面。民間層面的神化主要體現在民間傳說、戲劇、文學作品的塑造上。一是民間傳說中對“美鬢”和“紅臉”的神化。《三國志平話》中將關羽的胡子稱為“虬髯”,“虬”呈彎曲狀,象征“龍的幼子”。傳說中關羽有一根又細又長的胡須,是“黑龍”北海龍王的化身,龍王將自己的神力全部轉給關羽,因此后世用“美髯公”指代關羽。《紅臉關公》中稱“關云長”是云間掉落的一滴血水長成,解釋了關羽的臉譜是象征著忠勇俠義“紅臉”的原因。除了形象方面細致入微的刻畫,在《磨刀雨與曬龍衣》中,關羽以曬龍衣要挾海龍王借磨刀雨為人間解決大旱的傳說,又使關羽被塑造成了福澤一方的保護神。二是戲劇上對關羽的神化。《花關索傳》中,桃園三結義后為了卻心中掛念,關羽、張飛分頭殺死對方老小,與其子花關索構成了一個由劍神、水神與小童組成的完整神話象征體系[1]。三是文學作品上對關羽的神化。《東城關公廟記》《嘉興縣志》《壽春庵新建漢壽亭侯關王祠記》《常州新建關帝廟記》《五雜俎》《南澳鎮城漢壽亭侯祠記》等都重點描繪了關羽顯圣護國保民的形象,將其塑造成“戰神”。此外,晉商隨身攜帶關羽的畫像,將其視作“財神”;小孩子淘氣夜間不睡覺的話,關羽還以“厲鬼”形象出現[2]。可以說,關羽的民間形象是多元有趣的,具有神話志怪的特點。
關羽形象統治階級層面的神化主要體現在宗教和修建關帝廟上。儒教認為關羽夜讀《春秋》符合儒家教義;道教將《關云長大破蚩尤》中的關羽列入祭祀行列中;佛教也為了立足于荊州,賦予玉泉寺“鬼助土木之功”的神話,鋪墊了“關羽顯圣”的故事。宗教本身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以教化民眾忠于君王,維系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為目的。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大興土木建筑關帝廟宇,這些廟宇不僅氣勢宏偉、富麗堂皇,而且都使用了皇家專屬的帝王黃色,體現了關羽在皇家帝王這些身份至高無上的人物心里的地位和榮耀,朝鮮順安門外的關帝廟、中國地安門外的關帝廟皆是如此裝點[3]。百姓捐資捐物修建關廟,祈求關帝顯圣保佑,足見中國本土對關羽的喜愛與崇拜是發自內心的,關羽在中國本土的神化已經達到巔峰。
二、關羽的神化形象傳入朝鮮
為進一步鞏固與藩屬國朝鮮的關系,明朝開始有意借“壬辰倭亂”向朝鮮傳播關羽崇拜的思想,以形成共同的意識形態。朝鮮認為,關羽雖然忠勇,但敗走麥城,身死人手,并無豐功偉業存世,并不想大興土木工程,勞民傷財地修建異國英雄的廟宇。明神宗于萬歷六年(1578)將關羽封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比朝鮮國王的地位還要高出一等,這一行為更是激發朝鮮極其不滿的抵觸情緒。只不過迫于與明朝的外交關系不得已而為之,平定戰事后修建的關帝廟也受到了朝鮮人民的冷落,可見接受新文化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直到朝鮮宣祖時期,朝鮮遭遇倭寇入侵,連年的戰事使得政局不穩,急需樹立一個英勇無敵的形象,激發民眾同仇敵愾的情緒,共同抗擊侵略者。關羽忠勇,又護國有功,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一方面,將戰爭的勝利歸功于關羽的保佑,希望借修建關帝廟犒勞關羽的顯靈之功,繼續保佑朝鮮的“運祚之綿遠”;另一方面,為改變朝鮮重文輕武的風氣,重塑朝鮮國家形象,恢復朝鮮士林的文化自信[4]。統治階級規范全國各地的關帝祭祀活動,“捍災御寇護國保民”體現了朝鮮政治方面的訴求,因此歷代的統治者都親至關帝廟祭拜。這從出使中國的朝鮮使臣那里也可見一斑。朝鮮學者李安訥《關王廟》中的“百戰英靈凜九原”和“陰兵助順神功著”,把將軍關羽與戰神關帝聯系在一起,完成了朝鮮關羽由人到神的神化轉變[5]。
朝鮮接納關羽的形象后,關羽的形象發生了極大改變。俄國學者李福清在《關羽肖像初探》中指出:“韓國人畫的關帝像都韓國化了,韓化的程度比蒙藏還多,與中國關帝像相較之下,韓化的關帝像畫法不同,把人物擴大化了,服飾也不同。特別是1800年左右,全羅北道南原絹本唐彩畫持青龍刀的關帝,完全不像中國關帝像。姿勢、臉、眼睛、服飾都不像,只有青龍刀及帽上的絨纓與中國圖相同。”[6]遭受“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后,朝鮮盛行“慕明惡清”力求“反清復明”的思想[7]。如果說納貢給朝鮮經濟上帶來的負擔尚能接受,那么背叛明朝投降清朝則是奇恥大辱。朝鮮文人階層愿像關羽忠于漢室一樣,忠于明朝,以表示對明朝的“再造藩邦”之恩。像關羽忠于劉備一樣,恪守君臣之禮,忠于儒家君為臣綱的正統觀念。
朝鮮使臣俞彥述的《燕京雜識》更是表現出對清朝將關帝像放在佛像中祭拜,甚至將關羽像放在“雜處于腥穢之中”的強烈不滿,一方面體現了朝鮮對滿清異族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說明朝鮮對關羽的神化已經達到頂峰,關羽的形象已經上升至朝鮮的自尊心。大韓帝國時期正式停止關帝廟祭祀,神化關羽的全盛時代結束了,但是民間祭祀活動沒有停止,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朝鮮半島的信仰文化。與中國將關羽的形象融入三教之中不同的是,朝鮮形成了只崇拜關羽的“關圣教”,至今仍把關羽作為忠義和財神的象征加以崇拜[8]。關羽能夠得到朝鮮官方和民間的雙重喜愛,與其英勇無畏、忠肝義膽的特征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能夠在朝鮮獲得如此廣泛的喜愛,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是難能可貴的。
三、關羽形象在朝鮮的神化
朝鮮對關羽的崇拜不僅體現在政治層面,還逐漸滲透到了文學領域,分為對關羽的“顯性崇拜”和“隱形崇拜”[9]。
“顯性崇拜”主要體現在《壬辰錄》《祀典典故》《敕建顯靈關王廟》的關公顯圣,以及《壬辰錄》《天倪錄·送使臣宰定廟基》《天倪錄·見夢士人除妖賊》的三次托夢中。關公顯圣的傳說對鼓舞朝鮮士兵為國家的安定浴血奮戰,以及在民眾間形成同仇敵愾抵抗倭寇的情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次托夢,第一次預示大難將至,第二次告知避寇之道,第三次向李如松舉薦水軍將領李舜臣[10],緊扣“壬辰倭亂”爆發、宣祖還宮、丁酉再亂爆發三個關鍵時間點。既塑造出關羽先知先覺的神通廣大,又表現出關羽心系百姓的赤子之心。
“隱性崇拜”主要體現在將關羽的精神特質投射到朝鮮本民族英雄身上。例如,將《三國志·關羽傳》中“刮骨療毒”的故事移植到李舜臣身上,將“溫酒斬華雄”的故事投射到金應瑞斬殺倭將的片段中,暗示李舜臣和金應瑞就是朝鮮的“關羽”,以此凸顯朝鮮民族英雄英勇無畏、大義凜然的形象。關羽經過朝鮮歷代文人的虛構想象逐漸本土化,被視作朝鮮國家與國民的保護神。后期隨著民族意識的增強,關羽的神化對統治者的地位產生了沖擊,《壬辰錄》中關羽和朝鮮國王對話時不再自稱“我乃上古關云將也”,而是有意將關羽描述成只能依靠神宗才能將倭寇驅逐出境的武將形象,使其恪守朝鮮的君臣禮法。即便地位有所下降,關羽的形象仍在朝鮮維持著極高的熱度。不僅影響了朝鮮英雄類小說、野談類小說、夢游錄小說等,直到今天韓國的小說、漫畫中還會出現關羽的形象,對韓國作品審美價值和社會功能的實現、推動文學事業的進一步繁榮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結語
中國本土對關羽的熾熱崇拜是不難理解的,朝鮮對“關羽”這一異國形象的態度經歷了從抵觸到接受再到神化,最終有意貶低的復雜過程。對于當時的朝鮮,能出使中國直接感知中國文化的人還是少數的,大多數人要通過閱讀或者其他方式接受外來文化,通過閱讀記錄使臣出使中國的文獻和文學作品,想象并塑造著朝鮮人心目中關羽的形象。所以,關羽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歷史審判,原話語經過中間媒體的解構和合成,成為文化的變異體,文化的變異體已經不再是文化的原話語。有新文化文本的產生不是為了重復原話語,完全是為了本土文化的需要[11]。因此,朝鮮在特定的審美經驗上,對關羽形象的價值和屬性進行主動選擇、接納或拋棄,把握其形象背后蘊含著的民族情感和思想寄托,并順應時代大環境的發展趨勢,融入朝鮮本土化的特征,在文學領域進行再塑造,將對關羽的崇拜深深根植在朝鮮的政治文化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