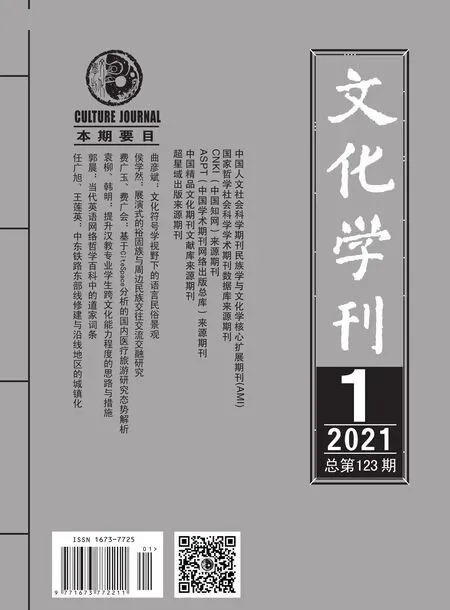從堪輿論《儒林外史》的科舉觀
任文珠
一、《儒林外史》中的堪輿與科舉
(一)堪輿的內(nèi)涵及發(fā)展
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1]堪輿也稱為天地之學(xué),亦指仰觀天象,俯察地理,后世專稱看風(fēng)水的人為堪輿家。“風(fēng)水”一詞首次出現(xiàn)在晉人郭璞《葬書》:“葬者乘生氣也。……氣乘風(fēng)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fēng)水。”[2]可見,迷信風(fēng)水的人們?cè)谡嘏c墓地的選址時(shí)會(huì)綜合考察附近的山水景觀以及地勢(shì)地貌,以求達(dá)到理想的建筑效果。在原始社會(huì),為了生存,人們大多選擇“近水向陽”的地方生活,追求更加合適的生存環(huán)境。進(jìn)入封建社會(huì)以后,堪輿不斷發(fā)展,人們開始注意選福址、擇良日等,明、清兩代更是堪輿學(xué)說的泛濫時(shí)期。
(二)《儒林外史》中堪輿與科舉之關(guān)聯(lián)
《儒林外史》這部士人小說寄寓了作者的理想,一方面揭露和批判沉迷科舉的士人,一方面肯定和贊揚(yáng)堅(jiān)持自我的士人。這部寫實(shí)主義的小說為何多次出現(xiàn)堪輿現(xiàn)象呢?首先,明清兩代堪輿盛行,上到帝王下到平民百姓,都熱衷于堪輿。美國文藝學(xué)家艾布拉姆斯曾提出文學(xué)四要素,童慶炳先生認(rèn)為其中的“世界”就是我們所指的社會(huì)生活,社會(huì)生活是一切種類的文學(xué)藝術(shù)的源泉[3]。文學(xué)來源于生活且反映生活,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雖然是一部關(guān)于士人的專書,其中必定會(huì)有堪輿現(xiàn)象的相關(guān)描寫來反映社會(huì)生活。其次,吳敬梓在書中多次描寫堪輿現(xiàn)象一定程度上也是為刻畫人物形象服務(wù),使其不脫離社會(huì)生活。作者通過描寫世人對(duì)堪輿的態(tài)度,反映出他們不同的堪輿觀和科舉觀,使人物形象更豐滿,具有更強(qiáng)的藝術(shù)感染力。再次,吳敬梓描寫堪輿現(xiàn)象在某種程度上是為小說的主旨服務(wù)的,是為了體現(xiàn)和傳達(dá)自己對(duì)堪輿和科舉的態(tài)度與觀點(diǎn)。作者通過夸張的藝術(shù)形式生動(dòng)地刻畫出因追求科舉而沉迷堪輿的世人形象,嘲諷了沉迷堪輿的世人,批判了當(dāng)時(shí)的科舉制度,表現(xiàn)出自己對(duì)堪輿和科舉仍持有的理性且清醒的認(rèn)識(shí)。
二、《儒林外史》中的堪輿現(xiàn)象研究
(一)惑于風(fēng)水的科舉士人
《儒林外史》第四回,范進(jìn)在母親去世后說:“今年山向不利,只好來秋舉行,但費(fèi)用尚在不敷。”[4]80-81范進(jìn)作為科舉士人,飽覽詩書,居然信奉風(fēng)水,因“山向(1)舊時(shí)看風(fēng)水的所定的墳塋方位,據(jù)說山向的吉兇與年月日有關(guān)。《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劉猛進(jìn)墓志》中的“即以其年建子之月三日丙寅穸乎南海郡西北朝亭東一里半,墳向艮宮,厥名甲寅之墓”一句,即山向之說。不利”而推遲了母親的安葬期,實(shí)際上違反了古代所提倡的“入土為安”的孝道,實(shí)為可悲。《儒林外史》第六回,嚴(yán)貢生在弟弟去世時(shí)說:“祖塋葬不得要另尋地。等我回來斟酌。”[4]114嚴(yán)貢生作為無惡不作的“優(yōu)貢”(2)清制,每三年各省學(xué)政于府、州、縣在學(xué)生員中選拔文行俱優(yōu)者,與督撫會(huì)考核定數(shù)名,貢入京師國子監(jiān),稱為優(yōu)貢生。《清史稿·選舉志一》載:“貢生凡六,曰:歲貢、恩貢、拔貢、優(yōu)貢、副貢、例貢。”,在幫弟弟料理后事時(shí)對(duì)祖塋的選擇卻十分慎重,可見品性惡劣之人同樣十分迷信風(fēng)水。
(二)迷信風(fēng)水的其他人士
《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記載:“余敷把土接在手里……嚼了半日……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主人慌了道:‘這地可葬得?’余殷道:‘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窮了!’”[4]762-764作者把余敷、余殷驗(yàn)土相墳時(shí)裝腔作勢(shì)的可憎的嘴臉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他們二人實(shí)為無師之學(xué),卻可以靠幫人看風(fēng)水來謀生計(jì),可見當(dāng)時(shí)世人對(duì)科舉、財(cái)富的熱衷及對(duì)風(fēng)水迷信的沉迷。《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寫道:“余大先生道:‘正是。敝邑最重這一件事。人家因?qū)さ仄D難,每每耽誤著先人,不能就葬。小弟卻不曾究心于此道。’”[4]748作者通過于大先生之口,揭露了世人普遍沉迷風(fēng)水的社會(huì)現(xiàn)象:他們渴望通過風(fēng)水求得仕途、獲得財(cái)富等,甚至為此摒棄古人所推崇的孝道。
(三)以風(fēng)水謀生的陰陽先生
《儒林外史》第四回:“次日,請(qǐng)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該請(qǐng)僧人追薦。”[4]74范進(jìn)中舉后,母親突然離世,范進(jìn)請(qǐng)來陰陽徐先生為母親寫七單(3)七,指喪事“作七”之七,七單是請(qǐng)陰陽先生推算列出死者生歿時(shí)辰與七七沖煞時(shí)辰的單子。。陰陽徐先生以幫人看風(fēng)水謀生,在《儒林外史》中多次出現(xiàn)。《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虞博士帶了羅盤,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過了墳,那鄭家謝了他十二兩銀子。”[4]611-613虞博士本為科舉士人,但因多次落第,在祁太公的建議下做了一段時(shí)間的陰陽先生,以謀生計(jì)。《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的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xué),我們還是請(qǐng)張?jiān)品迳套h為是’。”[4]765陰陽先生張?jiān)品逯饕谛≌f第四十五回中集中出現(xiàn),余氏兄弟料理父親后事時(shí)請(qǐng)張?jiān)品鍨槠淇达L(fēng)水。
(四)理性對(duì)待風(fēng)水的真儒
遲衡山在《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中提出:“只要地下干暖,無風(fēng)無蟻,得安先人,足矣!”[4]748他還說:“士君子惑于龍穴、沙水之說,自心里要想發(fā)達(dá),不知已墮于大逆不道!”[4]748遲衡山雖然在作品中有著積極的入仕態(tài)度,支持通過科舉改變命運(yùn),但他依然遵守孝道,不盲目迷信風(fēng)水,是小說中的真儒之一。《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杜少卿道:‘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4]751可見,杜少卿極其重視孝道,能夠理性對(duì)待堪輿,支持用相應(yīng)的法律來規(guī)范世人,是作者筆下為數(shù)不多的真儒形象中較為理想的一個(gè)。
三、從《儒林外史》中的堪輿現(xiàn)象論吳敬梓的科舉觀
(一)從作品人物的堪輿觀論作者的科舉觀
吳敬梓在小說作品中刻畫了范進(jìn)、嚴(yán)貢生、余氏兄弟等眾多迷信風(fēng)水的世人形象,并對(duì)他們的迷信行為進(jìn)行放大、嘲諷和批判。多年來,學(xué)者看到更多的是瘋狂追求科舉的士人的扭曲性格,看到了科舉制度的弊端,但深究這些人如此熱衷科舉、迷信風(fēng)水背后的原因,可以發(fā)現(xiàn),世人能夠做官的機(jī)會(huì)很少,較為公平的科舉便是他們最有希望的一種途徑。科舉制度作為朝廷選拔官員的制度,相對(duì)于世襲制有著一定的進(jìn)步性,萬千寒士便希望通過科舉考試來改變自己的命運(yùn)。作者所刻畫的范進(jìn)、周進(jìn)等人,作為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上萬千寒士的代表,也正是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改變了自己的命運(yùn),實(shí)現(xiàn)了自己的價(jià)值。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說中也刻畫了一些真儒形象,他們并不熱衷于風(fēng)水,對(duì)堪輿保持著清醒、理性的認(rèn)識(shí)。例如,作品中出現(xiàn)的遲衡山更注重儒家所提倡的孝道,并不一味追求所謂的名利。且遲衡山閑話時(shí)說起:“少卿兄,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jīng)事,方不愧我輩所學(xué)。”[4]574可見,其對(duì)科舉并不反感,反而認(rèn)為品行好、有才學(xué)的人為官可以貢獻(xiàn)社會(huì),有所益處。因此,作者對(duì)于科舉制其實(shí)并不是一味反對(duì),而是客觀地看到了科舉制度的價(jià)值與弊端,看到了科舉對(duì)當(dāng)時(shí)世人的影響。
(二)從吳敬梓的堪輿觀論其科舉觀
吳敬梓在書中借遲衡山之口讀詩嘲諷道:“氣散風(fēng)沖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尚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4]748可見作者并不相信風(fēng)水迷信,對(duì)風(fēng)水持有科學(xué)、理性的態(tài)度,吳敬梓的堪輿觀也從側(cè)面說明其具有正確的科舉觀。《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雖然不全是吳敬梓,但卻投射了他的身影,作者企圖借杜少卿來表達(dá)自己的情感[5]。杜少卿不僅對(duì)風(fēng)水有著清醒、理智的認(rèn)識(shí),對(duì)科舉制度也有著自己的看法,他并不熱衷科舉取仕,甚至裝病辭去朝廷對(duì)其征辟。但杜少卿反對(duì)八股取士可能更多是因其對(duì)自由的向往與追求,并不是厭惡科舉制度本身。吳敬梓對(duì)魏晉六朝的社會(huì)風(fēng)尚十分神往,對(duì)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作品非常喜愛,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保留著明顯的魏晉六朝風(fēng)尚的影響[6]。熱衷于魏晉風(fēng)流的杜少卿向往自由,斷然不會(huì)被科舉所束縛。因此,作者并不是借杜少卿這一人物形象去批判科舉制度本身,而是批判那些被科舉束縛而性格扭曲的世人。
四、結(jié)語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畫了對(duì)堪輿持有不同態(tài)度的人物形象,通過小說中的堪輿現(xiàn)象研究,可以看出作者對(duì)堪輿和科舉有著理智而清醒的認(rèn)識(shí)。吳敬梓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科舉制度為萬千寒士打開一扇門,也令多數(shù)士人迷失自我、人格扭曲,甚至沉迷于堪輿等封建迷信之中。可見,科舉制度在清代社會(huì)是一把雙刃劍,當(dāng)代社會(huì)亦是如此,人們應(yīng)該理智地看待各種考試和選拔,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同時(shí)堅(jiān)守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