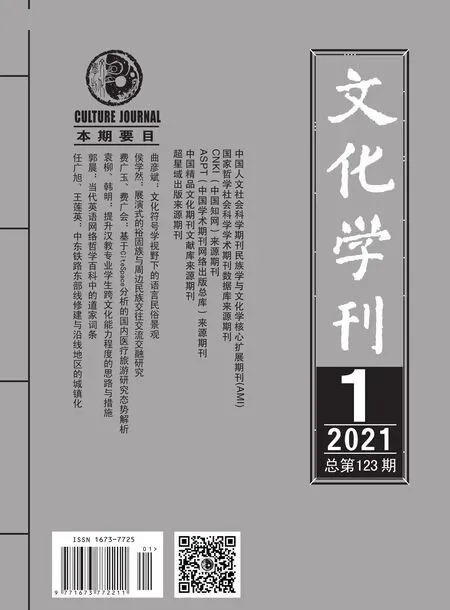英漢詩歌“杜鵑”意象對比研究
——以《致杜鵑》和《宣城見杜鵑花》為例
徐山燕
“意象”首次出自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載有“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shù),謀篇之大端”[1],但這里的“意象”并未涉及詩歌,真正研究詩歌中的“意象”起于明代王廷相對其進(jìn)行的系統(tǒng)論述,而后作為清代文學(xué)家評詩論美的重要標(biāo)尺。詩歌中的意象是物象和心象的融合,也就是說,客觀物體需要與詩人的心性、情感、審美、智慧融為一體。韓經(jīng)太指出中國詩學(xué)就其基本特質(zhì)而言是一種意象詩學(xué)[2]。對中西方文學(xué)而言,詩歌都是文學(xué)高造詣的集中體現(xiàn),其語言簡潔凝練、“言有盡而意無窮”,“意象”的作用功不可沒。
《致杜鵑》和《宣城見杜鵑花》兩首詩中都使用了“杜鵑”意象,那么,同一意象,在中西方詩人使用中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藝術(shù)效果呢?《致杜鵑》作者威廉·華茲華斯,是英國文學(xué)史上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開創(chuàng)了英國詩歌浪漫主義新時代,被譽為“桂冠詩人”。他的詩歌文筆樸素清新,使人感受到一種未經(jīng)雕琢的自然之美。《宣城見杜鵑花》作者李白,是繼屈原之后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其詩歌特點既豪邁奔放又清新飄逸,想象豐富,意境奇妙,語言輕快。對比研究英漢中具有典型性的浪漫主義詩人的詩歌,有助于讀者更好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英漢詩歌的差異。
一、英漢詩歌中“杜鵑”意象對比研究
杜鵑作為一種意象深受詩人喜愛。“杜鵑”意象在英漢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相同之處在于杜鵑都被用來表達(dá)報春之喜和纏綿悱惻的愛情,這時“杜鵑”意象便渲染了一種美好的意境。如杜甫的《洗兵馬》、李白的《贈從弟冽》、蘇軾的《山村絕句》,都將杜鵑看作一種喜鳥。再如一首古老的詩歌《杜鵑之歌》,詩中描寫到“歌唱吧,杜鵑,乘現(xiàn)在,唱吧,杜鵑。歌唱吧,杜鵑,唱吧,乘現(xiàn)在,杜鵑……種子茁壯成長,草地綠得新鮮。樹枝正抽芽長葉,歌唱吧,杜鵑!母牛跟著牛犢叫哞哞,母羊跟著羊羔叫咩咩”[3]。通過這首詩的具象描述,讀者似乎能夠身臨其境,感受春回大地帶來的生機(jī)與活力,地上綠意盎然,牛羊成群,天上有杜鵑助興高歌。此外,杜鵑還用來表達(dá)愛情之意。如李商隱《錦瑟》“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4]248,詩人將對情人的思念之情通過杜鵑表達(dá)出來。在英詩中,杜鵑愛情的寓意體現(xiàn)在杜鵑那似乎永不停歇的叫聲之中,如英國詩人勃朗寧夫人在《請再說一遍吧》中寫道“說‘我愛你’即使那樣一遍遍重復(fù)/你會把它看成一支‘布谷鳥’的歌曲”。
同是杜鵑鳥,英漢詩人對此有著不同的解讀和理解,使得“杜鵑”這個意象變得豐富、飽滿。在中國,相傳杜鵑是蜀帝杜宇死后冤魂的化身,死后日夜啼叫。正由于此,“杜鵑啼血”便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中悲苦的代名詞。“杜鵑”意象具有思鄉(xiāng)離別愁緒,如唐代無名氏《雜詩》中“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4]347一句。然而,由于不同的認(rèn)知體驗,西方人賦予了杜鵑一些獨特的寓意。其一,杜鵑代表著理想和希望。如威廉·華茲華斯的《致杜鵑》。其二,杜鵑象征“孤獨”。由于杜鵑是一種候鳥,經(jīng)常不筑巢,所以,常用來意指無家可歸的人。其三,由于杜鵑的寄生現(xiàn)象,再加上cuckoo與cuckold從詞源上來說是同義詞,所以就有了愛情中“不忠貞”的意味。“杜鵑”意象的韻味如此之多,在一首詩中究竟取何種寓意,還需要根據(jù)語境與詩歌具體分析。
二、兩首詩歌中“杜鵑”意象的相似性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人稟七情,應(yīng)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5]這句話是說,人類有七情六欲,所以會由感物而感悟,這其中之物就包括自然之物。鐘嶸在《詩品·序》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5]詩人面對諸物有感,繼而成詩。《致杜鵑》和《宣城見杜鵑花》都是通過“杜鵑”這個意象觸動詩人的情感神經(jīng),引起詩人情感上的波動,或是歡喜或是悲傷,都將詩人所思所想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在華茲華斯眼里,杜鵑是魅力和純真的化身,它勾起了詩人歡樂的童年回憶。在《致杜鵑》中,詩人“躺”在草地上,“傾聽”杜鵑歌唱,聲音忽遠(yuǎn)忽近,如同在跟他捉迷藏,這是一件多么開心的事啊,讀者可以從字里行間感受到詩人當(dāng)時的心態(tài)是多么放松。在詩人眼里,杜鵑絕不是一只普通渺小的鳥類,而是一種讓他魂牽夢繞的眷戀。正如他在詩中描寫的那樣,詩人熱烈地歡迎杜鵑,認(rèn)為杜鵑的叫聲如同歌聲般優(yōu)美,讓人著迷。詩人孩童時期就經(jīng)常追尋她,認(rèn)為是杜鵑讓這個世界變成了仙島。從詩人對杜鵑的直抒胸臆,我們可以感受到杜鵑帶給他的快樂和希望。
《宣城見杜鵑花》這首詩是由感“杜鵑”而起興的。葉嘉瑩指出:“‘賦、比、興’乃《詩經(jīng)》和中國古代詩歌借物象與事象傳達(dá)感動并引起讀者感動的三種表達(dá)方式,是心物之間互動關(guān)系的反映。”[5]興是由物及心,看到杜鵑花,詩人想到了杜鵑、杜鵑的悲啼,進(jìn)而想到自己的家鄉(xiāng)。詩的前兩句“蜀國曾聞子規(guī)鳥,宣城還見杜鵑花”本應(yīng)是先寫杜鵑花再寫杜鵑鳥,詩人蓄意如此安排,先虛后實,真實再現(xiàn)了觸動鄉(xiāng)思的過程,也說明了思鄉(xiāng)之情并非一時之感,而是積蓄已久。詩的第三、四句“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描寫杜鵑那經(jīng)久不息的啼叫,每叫一聲,詩人都如肝腸寸斷般痛苦,一聲又一聲,這叫詩人如何經(jīng)受得住,“陽春三月”本是美好的節(jié)令,詩人卻無心欣賞。此時,詩人年邁體虛,正值流放,他沒有實現(xiàn)自己的鴻鵠之志,種種苦悶無人能說,詩人的苦痛似乎無窮無盡。
三、兩首詩歌中“杜鵑”意象的相異性
(一)構(gòu)造的意境不同
意境的構(gòu)造具有主觀性。意象是意境的基礎(chǔ),意境依附于意象的本體而存在[6]。意境的構(gòu)造首先是基于詩人對于意象的感知、選擇。其次是將“象”與“象外之象”,以及詩人自我的格局結(jié)合而成。
《致杜鵑》中以“杜鵑”為主要意象,結(jié)合“草地”“山丘”“藍(lán)天”“平原”等背景,讓人覺得細(xì)膩且真實可感,營造了一種唯美的意境。詩人在詩中提到,小時候就經(jīng)常找尋杜鵑,找了天上,找了樹上,還是找不見。盡管如此,詩人對杜鵑的愛絲毫未減。在詩人眼里,杜鵑就是希望,就是愛。《宣城見杜鵑花》中則不然:在詩中,既聽不到鳥的叫聲,也看不到花的絢爛,僅僅由“曾聞子規(guī)鳥”“還見杜鵑花”一帶而過。這個地方體現(xiàn)了中國詩意境創(chuàng)造的常用手法,即虛實結(jié)合,以強(qiáng)化意境。“實”在杜鵑花,“虛”在杜鵑。詩人此時所寫杜鵑并非是眼前之杜鵑,而是心中之杜鵑,是由杜鵑花想到的杜鵑,是詩人內(nèi)心的一份眷念,這樣就使詩之意境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營造了一種悲傷、憂郁又遼闊的意境。
(二)情感表達(dá)不同
若要讀者完全感知詩人所表之情,需要讀者與詩人產(chǎn)生完全的共鳴,但這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高標(biāo)準(zhǔn)的要求需要讀者與詩人達(dá)到相同的層次、心態(tài)、格局,如此才會產(chǎn)生相同的共鳴,否則讀者很難理解詩人所要抒發(fā)的感情,特別是中國詩歌。
在威廉·華茲華斯的《致杜鵑》中,詩人要表達(dá)的感情非常明顯,他的喜悅溢于言表,熱烈而奔放,如詩人在詩中直接寫“聽到你唱我就高興”“聽著你在唱,我的心回到黃金般的時光”“你呀卻是希望、卻是愛”等等,讀者可以比較容易地感知到詩人要表達(dá)的歡樂以及對杜鵑的喜愛,因為這種感情的傳遞是直接的。但在《宣城見杜鵑花》中,詩人想要表達(dá)的感情就不是那么容易被讀者感知到,它不如英詩那么直接。在這首詩中,李白并沒有直接表達(dá)他內(nèi)心的悲傷,只是稍微提及了“杜鵑”這個意象,這就需要讀者有先前對“杜鵑”意象認(rèn)知的積累,了解詩人當(dāng)時背景,如此才可以感受到詩人要傳達(dá)的是思鄉(xiāng)之情、老年孤苦之情、壯志未酬之情。
(三)傳情方式不同
前面分析了兩位詩人抒發(fā)的不同情感,但是,他們是如何抒發(fā)的呢?若要知道詩人是如何抒發(fā)情感,可以借鑒前人思想,從不同的視角探索。司空圖強(qiáng)調(diào)“詩家之景”,又強(qiáng)調(diào)“目擊可圖”,這表明了他詩情畫意一體生成的詩學(xué)觀念[2]。每一首詩都是一幅畫,那么便可以嘗試從繪畫的角度去解讀這兩首詩的詩中之畫。
在《致杜鵑》中,詩人通過具體的物象,如地上樹林、草地、山丘和鮮花,天上杜鵑歌唱,陽光將天地相連接,花紅草綠,動靜結(jié)合,如同一幅豐盈的西方油畫。我們可以將英詩這種通過“務(wù)實”、細(xì)致的意象刻畫來表達(dá)感情的方式類比為西方油畫。油畫的特點在于強(qiáng)調(diào)色彩和光線,追求真實,為了達(dá)到逼真的藝術(shù)效果,油畫畫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要求光線、構(gòu)圖、透視、影射與現(xiàn)實情況分毫不差。與《致杜鵑》相比,《宣城見杜鵑花》這首詩所呈現(xiàn)的畫面則不是那么豐盈,山、鳥、花三者成畫,其余的任由讀者想象。中國詩這種通過“虛實”意象相結(jié)合的方式來含蓄表達(dá)情感的方式可以類比為中國畫。中國畫重在寫意,追求“以形寫神”,且大都是通過極簡線條勾勒,這與西方油畫的審美情趣完全相反。中西方繪畫創(chuàng)作方式不同,中西方詩歌中情感的傳達(dá)方式也不同,想要更好地了解中西方詩歌文化的不同,可以從繪畫這個視角來尋找答案。
四、英漢詩歌中“杜鵑”意象異同成因
(一)中西方對待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認(rèn)知異同
中西方人皆對大自然有情,但情有所不同。在西方,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是物我兩分。受地理環(huán)境影響,西方國家以商業(yè)和畜牧業(yè)為主,他們需要與大自然進(jìn)行搏斗,如此才能生存,所以他們對自然抱有敬畏之心。西方著名哲學(xué)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強(qiáng)調(diào)自然是神或理念的化身,人無法把握。所以,從本質(zhì)上來說,他們的內(nèi)心與自然是有距離的。體現(xiàn)在詩歌表達(dá)中就是景物中不承載強(qiáng)烈的主觀色彩和文化意義,華茲華斯對杜鵑的描寫就是從杜鵑本身出發(fā),而不帶有強(qiáng)烈的主觀色彩抒發(fā)他情。
以李白為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詩人,崇尚的卻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萬物與人的關(guān)系應(yīng)是異質(zhì)同構(gòu)、交互感應(yīng)的。《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其追求的便是順應(yīng)自然變化,“萬物與我為一”的終極大化。唯有在與自然的情感交流中,人才可能獲得生命的終極體驗。在中國詩歌中,詩人追求情景交融,將情寓于景中,并賦于景以內(nèi)涵,然后再通過景表達(dá)出來。如杜鵑之鳴具有悲傷、愛情、抑郁或思鄉(xiāng)之意皆是人們賦予它的文化內(nèi)涵,詩人將人文色彩融入大自然之中,從而達(dá)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中西方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異同點
詩歌是感情的真實流露,不論是西方詩歌外顯性、具象、真實的描寫,還是中國詩歌內(nèi)斂性、含蓄、抽象的表達(dá),都遵循了這個原則。他們都強(qiáng)調(diào)詩歌中想象的重要性,浪漫主義詩人更是如此。
中國詩歌審美意象的緣起一般都是以特定的情思為出發(fā)點,然后在現(xiàn)實里尋找各種各樣的和人的既成心理相適應(yīng)的對應(yīng)物,使之承載主體的情思[8],這在《宣城見杜鵑花》這首詩中就有體現(xiàn)。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樣,詩人的思鄉(xiāng)之情并不是源于瞬間,而美國意象派詩人龐德給意象下的定義是“一剎那間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一個理性和情感的復(fù)合體”[9]。中國詩歌重在抒情,意在筆先,先有意,后尋找能寄情的同構(gòu)之物;而西方詩歌重在情感的一時激發(fā),強(qiáng)調(diào)由于物的刺激而使詩人有感,這是兩個不同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起點。東西方審美意象緣起的不同,導(dǎo)致東西方審美標(biāo)準(zhǔn)也不同。中國詩歌呈現(xiàn)的意境悠遠(yuǎn)而深長,但不易被讀者理解;西方詩歌的意境具象豐富、流露于表象,易于被讀者理解。
五、結(jié)語
通過對《致杜鵑》和《宣城見杜鵑花》的比較,可以看出意象的重要性。意象給予詩歌靈魂,沒有意象性,就沒有作品的藝術(shù)性和審美價值,如此強(qiáng)調(diào)意象一點都不為過。意象源于物象但又超越物象,從物象轉(zhuǎn)化為意象需要一個過程,那就是人的主觀情思構(gòu)架,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英漢詩人面對同樣的杜鵑卻有著不同的情感。本文在概括英漢詩歌中“杜鵑”意向總體差異的基礎(chǔ)上,細(xì)致分析了“杜鵑”意象體現(xiàn)在英漢兩首詩歌中的異同點以及產(chǎn)生這種差異的原因,以期幫助讀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意象,感知英漢詩歌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