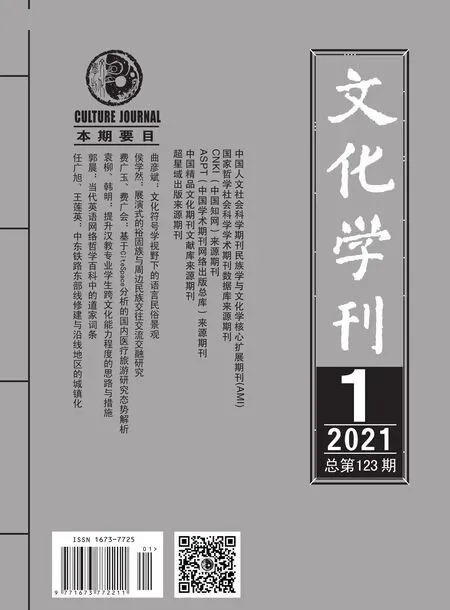贖刑之“贖”如今何“解”
孫佳偉
關于贖刑一詞,最早見于《尚書·舜典》:“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說文解字》有云:“贖,貿也。”“贖,質也,以財拔罪也。”有關贖刑的起源,因為沒有相關的史料支撐,所以至今仍無定論,有人認為堯、舜、禹時期便有了贖刑,也有觀點認為贖刑起源于夏,但至少可以明確的是,最晚在西周時期贖刑便已經存在。贖刑制度從出現到鼎盛,直至消亡于清朝,其在中國歷史上走過了數千個春秋,尋其足跡,覓其因果,與今對照,發掘其中的可借鑒部分,可對當今法律制度的改進發展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以何贖之
(一)錢之贖
《尚書·呂刑》就贖刑的具體內容作出以下規定:“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1]鍰即當時銅的貨幣單位,一鍰系六兩。自此,開啟了以錢贖刑的序幕。
以錢贖刑在其后的朝代都有所沿用,且各朝代對以錢贖刑的適用對象、贖刑標的、交納標準均有具體規定。直至清末修律,廢除了贖刑制度。
對于以錢贖刑中的“錢”,需作廣義的理解,并不單指銅。明代贖刑的財物便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清代允許犯人納谷或米等實物,折算標準是每谷一石,折米五斗,每米一石,折銀五錢。康熙年間,捐贖則以米、谷、駱駝等實物為主。
(二)役之贖
秦朝豐富了贖刑標的,規定贖刑除用金錢外,還可以用勞役。《秦律十八種》記載:“有罪以貲贖及有責于公,以其令日問之,其弗能入及賞,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錢,公食者日居六錢。”[2]即是說,無力交納贖金,可以用勞役贖罪。
唐代創設了“官役折庸”制度,《通考·一百七十一》中記載了唐玄宗天寶六年(747)時的敕令:“其贖銅,如情愿納錢,每斤一百二十分。若欠負官物,應征正贓及贖物,無財以備,官役折庸。其物雖多,限三年。”[2]即規定了以官役折換刑罰。
明代贖刑制度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在贖刑方式上以罰役為主。罰役有屯田、種樹、運糧、運灰、運磚、運炭、煎鹽炒鐵以及其他勞役[3]。同時,對于不同的罪名,明朝在贖刑罰役的時間上還作出了規定:“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滿日疏放。”《大明律》還專附“納贖諸例圖”,例圖明確周詳。
勞役贖刑,在清朝被沿用且適用范圍也愈加廣泛。
(三)功之贖
康熙十六年(1677)有“出征之處殺人贖例”的規定,其大意為武職殺人既要追銀贖罪,還要軍前效力贖罪。此后,軍前效力贖罪不僅包括武職人員,還包括大量文職官犯。
通過效力贖罪,在當時確實使一些官員以“戴罪”去“贖罪”,也確實贖了罪,如修筑塔蘭奇水渠終將“石田”變“樂土”的蘇齡阿。
二、因何立之
(一)起之緣
最初定贖刑究竟為何,由于無史料的支撐,已不得而知,張兆凱先生曾言西周《呂刑》規定的贖罪是贖刑萌芽狀態[1]。事實上,西周以前的社會活動中就已經出現贖刑適用之實例,如《尚書·虞典》就記載過舜“金作贖刑”的實例。
秦代以役贖刑的出現,使得應受刑者通過無償勞動而減輕刑罰,這種做法其實不僅減輕了受刑者的勞役負擔,而且為國家財政節省了開支。《明史·刑法志》中載:“國家得時籍其入,以佐緩急。而實邊、足儲、振茺,宮府頒給諸大費,往往取給于贓贖二者。”[2]
清朝官員效力贖罪的出現也有著其獨特的歷史背景。清初在經兵燹戰亂之后,各地城池急需修整,但是官府并沒有足夠的經費,認工贖罪條例應運而生[4]。
(二)興之因
有學者評《呂刑》中的五罰之贖時說道:“周律之繁極矣,五刑之屬至三千,若一按律盡而刑之,何非投機觸罟者?天下無完膚。是穆王哀之,五刑之疑各以贖論。”[1]漢朝首創“女徒顧山”(一種贖刑)對婦女進行了特殊保護。由此可見,贖刑最開始適用的目的在于憐恤、在于恤刑。這種慎刑思想,是贖刑可以在歷史上存在許久的原因之一。
清朝的效力贖罪則彰顯了對官員的改造作用。清雍正帝指出:“獲罪之人賜之以自新之路令其圖功贖罪。”[4]清乾隆帝也指出官員效力贖罪意為原諒過去的過失,在其他領域重新錄用,給其改過自新的機會。
(三)滅之故
有學者認為,贖刑自始便展示出極強的封建特性,是為維護封建等級身份、維護特權階級利益所服務的。如朱熹認為:“古人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撲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5]統治者對于贖刑的規定大多看似適用廣泛,官民均可適用,但由于贖金高昂,窮苦百姓無力支付,其依舊是富者得贖。
清朝末年,平等、自由的觀念逐步興起,反對特權也就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維護特權的贖刑制度勢必遭到抵制。贖刑在此背景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三、以何“解”之
贖刑因其落后性停下了腳步,留在了中國歷史的長河中,這是符合發展需要的。但是,對其全盤否定也不合理。在現今社會,反觀一些制度的設定,讓人們以一個新的視角重新認識贖刑,感受贖刑帶來的現代價值,即對贖刑作以“新解”。
(一)取其精華
贖刑最開始適用的目的在于憐恤、在于恤刑。各朝代的刑法幾乎都把憐恤觀念當作適用贖刑的重要指導思想。現今,輕刑化思想所蘊含的寬和、人道化的精神與贖刑的思想可謂一脈相承。
以錢贖刑貫串贖刑制度的始終,是重要的贖刑方式。現今,刑事和解制度中被告人對受害人予以賠償,得到受害人諒解,進而作為對被告人量刑考量的依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實施細則》中第25條規定:“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的,綜合考量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以及認罪、悔罪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6]
現今的刑事和解制度中的部分內容似乎對古代勞役贖刑給予了擴大解釋,不再是簡單地做工服勞役,而是著眼于解決現今的實際問題,基于所犯之罪,有針對性地完成作業,如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過實踐探索在全國率先提出“綠色司法”,主要內容為:“涉林刑事案件發生以后,積極促成被告人與受害人之間刑事和解,并簽訂‘補種復綠’協議,且由法院進行司法確認,作出補植管護令,按規定責令被告人對其破壞的森林資源及時進行原地或者異地補種及管護,福建省法院在五年時間里,共審理了適用‘補種復綠’的毀林案件516件;共作出‘管護令’‘補植令’等五百余份;責令涉林刑事被告人及時管護、補種林木面積達四千多萬平方米。解決了以前刑事被告人重新回歸社會難、被毀山林復綠難、受害人權利得不到救濟的難題,實現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3]
(二)去其糟粕
贖刑,歸根結底所體現的是特權思想,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即“特權階級享有最終解釋權”,似乎與受害者無關,受害者反而被排除在外,犯罪者符合贖刑標準的均可適用,無論受害者贊同與否。古代贖刑解決的是犯罪者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與受害者之間的關系,因為以錢作贖,錢的去向即收歸國家所有。
現代的刑事和解制度規定了將賠償直接給予受害者。刑事和解制度的目之所及,即是受害者,因為犯罪行為對受害者的傷害最為直接、最為嚴重,理應受到合理的對待,讓受害者決定是否接受與犯罪者的和解并作為量刑的考量因素,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對于受害者而言,身體與精神所受到的傷害不言而喻,刑事和解制度中受害人得到相應的補償也可解決其迫切的需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對于讓受害人收取賠償這一規定的首功不在我們,因為清律在有關過失殺傷收贖中便規定了過失殺傷準其收贖,但贖銀并非上交政府而是由被害人之家收領,作為營葬醫藥的費用。可見,古代贖刑確實有其可供借鑒之處。
(三)贖刑現代價值的研究成果
近年來,部分學者對贖刑的現代價值有著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研究,并且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成果也愈見其多。
張兆凱先生對贖刑沒有采取一種全面否定的態度,其在《贖刑的廢除與理性回歸》一文中提出了贖刑的現代價值,認為在契約社會平等觀念的指導下,沒有了特權階層,如果贖刑仍行用于當今,贖刑和易科罰金刑應當具有同等的適用理念[1]。
在世界刑法向著輕刑化方向邁步的潮流中,我國也在逐步探索解決之道,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現及適用便與之緊密相連。
徐欣欣在《論中國古代贖刑制度及啟示》一文中對刑事和解制度與贖刑制度進行了對比研究,其認為贖刑的興衰對現今刑事和解制度的構造有所啟示:必須要認清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目的是彌補受害人所受到的傷害,也是為了解決當事人訴爭的法律問題,進而使罪犯真正悔罪,以便促使其更好地重返社會[2]。
四、結語
贖刑制度固然以其落后性、特權性勢必被淘汰,但是其根植于我國土地之上,經歷了兩千余年的發展變化,適應當時歷史階段的需要,做出了它的貢獻。贖刑制度也許沒有被人們完全忘卻,但自它滅亡開始可能就被疏遠了,對其研究、探索并不多見。法治的發展需要符合國情,刑事和解制度需要完善,借鑒外國的先進經驗固然可取,但從挖掘類似贖刑這些漸被疏遠的本土法律資源入手,進而批判繼承、改造完善,相信更易被接受,因為有一脈相承的文化理念作為根基,這也許是一條合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