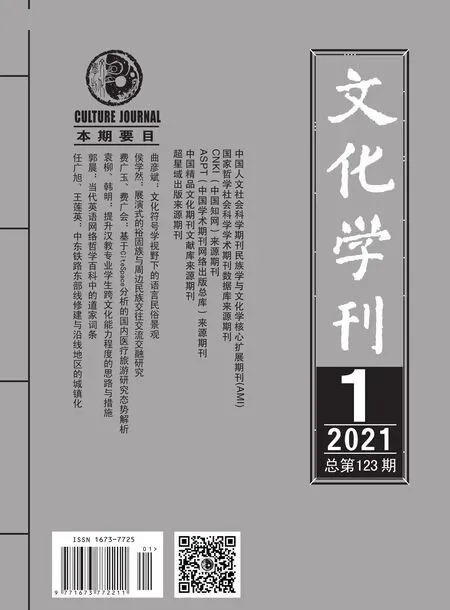淺析《史記·龜策列傳》重視龜卜的緣由
李妮娜
《史記·龜策列傳》是《史記》中記載龜策的一篇列傳。“龜策”即卜筮,《禮記·曲禮上》云“龜為卜,策為筮”[1]。一般情況下,“卜”為用龜甲占卜,“筮”為用蓍草占卜。在西漢初年,“龜策”受到統治者的推崇。武帝時,“數年之間,太卜大集”[2]3224。武帝擊匈奴,攘大宛,收百越時,“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于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2]3224。翻開《史記·龜策列傳》,可以發現其中記載龜卜之處遠遠多于蓍占,基本可以稱之為“龜卜列傳”了。那么《史記·龜策列傳》為什么會這么側重描寫龜卜呢?本文將通過分析龜卜的傳統、西漢初年對龜和龜卜傳達天命的神圣認識,對比當時其他占卜方法,從史學史的視角出發,結合作者和當時的寫作背景,探討《史記·龜策列傳》側重描寫龜卜的原因。
一、龜卜的傳統與神圣性
龜類為爬行變溫動物,主要生活在熱帶及溫帶地區。溫帶地區的龜類在冬季寒冷時要冬眠,熱帶地區的龜類在夏季干旱、炎熱時要夏眠,休眠期間不進食。龜類多雜食,耐饑力強,壽命可長達數十年至上百年。其中,半水棲龜類通常生活在河流、湖泊岸邊的低地和沼澤中。新石器時代到早期文明起源時期,黃河流域的氣候溫暖濕潤。西周時期經過一個短暫的寒冷期后,至春秋時氣候逐漸回暖。秦漢之際,溫暖的氣候和發達的水系為半水棲龜類的生長繁殖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采集狩獵時代和農業不發達的史前時代,大量龜類很有可能作為食物為古人捕獲食用。有學者依據浙江河姆渡遺址中發現的龜類骨骼,認為龜作為一種食物來源而成為先民的崇拜對象[3]。既然龜類在當時是可以食用的常見動物,那么作為獵物,先民必定仔細觀察過龜類的外形特征、生活習性以及生存環境。再結合史前時期流行的“萬物有靈”思想,將龜的形象進行抽象并賦予其神奇的意義便成為可能。
在商代的占卜中,使用龜甲代替牛肩胛骨,可能有著實用與神圣的雙重含義。一方面龜甲的產量比牛肩胛骨的產量高,另一方面很可能也是因為龜被人賦予了特殊的神圣意義。有學者認為,古人將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與龜的形態相結合,龜代表著宇宙:龜足立于西北、西南、東北、東南四個方位,與“十”字形的東、南、西、北四個基本方位結合,是為“八柱”,撐起圓形的天,龜背甲就代表天[4]。
龜卜自商代起盛行,至西漢初,依然流行于世。查閱《史記·龜策列傳》的記載可以發現,西漢初流傳著龜的種種神異。針對龜殼上的花紋,時人認為這些花紋與天象地理相應,所謂“八名龜”中有七種以天象或地理命名[2]3226。在龜的生存習性方面,古人認為龜是一種長壽的動物,應四時變化甚至可以不食休眠[2]3231,且將龜不進食的原因歸結為龜“行氣導引”的結果[2]3228,于是,養龜被認為“有益于助衰養老”[2]3225。至于龜的生存環境,也充滿著神秘氣息:龜常伴蓮葉、蓍草等靈物而生,在江南無毒蝎猛獸,野火、斧斤不及的森林中,擇蓮花所居[2]3226。龜在外觀、習性、生存環境方面的神奇,都暗示著龜是與天相通、與天相感的靈物,它的出現自然被視為是天降祥瑞,人們認為龜作為天的使者,可向天子傳達天命,代表天子受命于天。龜被古人視為“邦福重寶”,就連一國強盛的原因也歸于龜之力[2]3227。在古人眼中,龜可以知利害、察禍福,言而當,戰而勝,以此來安社稷,強國家[2]3231。普通人得名龜,可得財富[2]3226,甚者得到神龜,可為人君[2]3227,但也有人因為殺名龜而“身死,家不利”[2]3228。《史記》將“身死,家不利”的案例原因歸為“人民與君王者異道”,普通百姓得名龜不能殺而用之,天子圣王卻可以用它來占卜,且可以“十言十當”[2]3228,這與普通人得名龜后得財富和為人君的說法是矛盾的。這種矛盾出現的可能原因是:在統治穩定時,統治者利用當時龜與“天”相通的認識,為統治帶來合法性,由此對龜卜的使用進行壟斷;在政局不穩、改朝換代時,龜的壟斷性削弱,為新君的上位提供“天人感應”的合理性,也為普通老百姓謀得的利益提供了一些合理的依據。這種矛盾也顯示出龜的種種人為的神圣傳說,其根本出發點是為現實形勢服務。正因為以龜為寶、以龜為卜,時人爭相得之,龜的數量由此減少。隨著本來已是寶物的龜數量減少、使用減少,人們必然更加珍視龜,有利于龜及龜卜被渲染上更加神秘而又神圣的“天命”色彩。
二、龜卜與其他占卜方法
西漢初年,國家在長時間戰亂后重獲統一。經過幾代的休養生息,民生得以恢復。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統一思想領域以服務于“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占卜的興盛并非偶然。秦漢時方術流行,神秘信仰乃普遍的社會心理。當時的人們將“天”視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主宰,“天”具有了神格化的意義。“天命”是“天”做出的至高無上、不可置疑的決定,決定人間的吉兇禍福。人必須順應“天命”,否則就會招來禍患。而天子為人君,當然也是因為“天命”所歸。在當時,占卜被認為是知曉天命的一個有效途徑。
卜筮是一種溝通天人、預決吉兇禍福的占卜方法。卜筮起源甚古,商周時期頗為興盛,至春秋戰國時期日漸衰落但仍不絕于世。《史記·龜策列傳》載古代圣王皆以卜筮決疑[2]3223-3226。卜筮自上古時期起就受到重視,經過多代依舊保留了下來。所以,卜筮在西漢時期的興盛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和社會心理基礎。
《尚書·洪范》記載了卜筮交相用的情況[5],以龜為工具的卜和與蓍草為工具的筮并用,故并稱“卜筮”。蓍草也是一種神靈之物,班固《白虎通》載孔子云“蓍之為言耆也。老人歷年多,更事久,事能盡知也”。之所以叫蓍草,是因其壽長而事事盡知,故稱“耆”[4]。蓍草所生之處無虎狼毒蟲[2]3225,生滿百莖的蓍草,下面有神龜居住,上面有青云覆蓋[2]3226。蓍草也可以與天感應,天下太平時蓍草可生百莖[2]3226。蓍草是靈性之物,常與神龜共生,與龜卜同用,占卜也相當靈驗[2]3227。《史記·龜策列傳》中龜卜的記載明顯多于筮占,原因有三。其一,蓍草雖然也是靈物,也可以感天,但不是天的使者,并沒有被賦予傳達天命的功能,在代表天意方面比龜對天的代表性遜色很多。其二,與龜在傳統崇拜和占卜中的重要地位有關。從商代起,龜卜一直有著較高的地位。而龜作為動物,在遠古時期可以作為直接的食物解決生存問題,相比于植物崇拜,動物崇拜的地位更為重要,更具有現實意義[3]。可以說,龜崇拜的傳統根基深厚,延續日久,影響亦深遠。其三,“物以稀為貴”心理的影響。龜數量較少、價格昂貴,出現即為祥瑞的征兆;而蓍草常見,數量多,方便易得,并非難得一見的祥瑞。如此一來,龜的神圣性比蓍草更強,在卜筮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
除了卜筮,星占、日占、夢占、雞卜也是當時使用的一些占卜方法。關于星占,《史記·龜策列傳》中載宋元王問衛平所夢為何物時,“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兇,介蟲先見”[2]3229。可以看出,星占的體系較為復雜,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和易經八卦。另外,天象只能顯現國家大事,一般小事則不能顯現。故星占占卜的是國家的軍機大事,歷來為官方壟斷,民間幾乎無人知曉[4]。而龜卜大事小事都能占卜,操作較為簡易,流傳甚廣,民間也有運用,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操作,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易于被人們接受。
日占則是結合陰陽五行學說和方位來占卜時間吉兇。《史記·日者列傳》集解云:“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2]3215裴骃認為“占候卜筮”通稱日者,可以說這是廣義上的日占,狹義上的日占指“占候”。日占與龜卜相比,日占主占時,而龜卜主占事,占卜的理論不同,占卜對象各有側重,日占不能傳達天命。夢占與雞卜前者是解夢,后者是利用雞進行占卜,其神圣性遠遜于龜卜,只能占卜小事,不能占卜大事,更不能傳達天命,在《史記》中的記載也相當有限。
三、《史記·龜策列傳》的背景
《史記·龜策列傳》的作者背景和寫作背景,在一定程度主導著其價值觀。《史記·龜策列傳》的作者是何人歷來都有爭論。《史記》在流傳過程中遺失部分內容,故《漢書·藝文志》載“太史公百三十篇”,班固注“十篇有錄無書”,但未指明其缺補之處[6]。褚少孫增補史記,增補之處皆有“褚先生云”,經后人考證,多有疑云。《太史公自序》中載“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兇,略窺其要,作《龜策列傳》”[2]3225-3226。另《史記·龜策列傳》索隱云“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正義云“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日者、龜策列傳”[2]3223。所以,目前多認為《史記·龜策列傳》亡佚,為褚少孫增補。也有學者認為《史記·日者列傳》內容實為《史記·龜策列傳》部分軼文,而現《史記·龜策列傳》部分為司馬遷所記,部分為褚少孫所補[7]。
可以肯定的是,司馬遷所著《史記》中確有《龜策列傳》一篇,無論作者是司馬遷還是褚少孫,他們作史都不可避免帶有當時官方的烙印。司馬遷作《史記》本為私人修史,但司馬遷官太史令,執掌史職,接觸的人物以皇帝和各級官員為主,其所聞所見必然以官方的見聞為主。《史記》所用各種資料多為官方藏書,也正因為司馬遷能夠自由閱讀官方藏書,《史記》才有成書的條件。《史記·龜策列傳》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余年……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2]3225-3226褚少孫本人不僅是郎官,而且增補《史記·龜策列傳》的內容也是求訪了當時的掌管卜事“太卜官”和掌管禮樂制度的“掌故”,至于“文學長老習事者”,則是當時有文化知識且深諳卜筮之術的人,這樣的人絕非普通的平民百姓,應該是當時有身份地位的人物。
包括司馬遷、褚少孫以及這些太卜、掌故、長老在內的人物,都與上層統治階級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或許位于統治階層的底端,但是他們所能接觸的資料和信息都是官方的內容,浸染著官方的價值取向。在他們的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官方的意識形態。在那個“天”信仰根深蒂固的時代,在“天人感應”“天命至上”的官方意識形態之下,統治者利用具有深厚文化積淀和社會影響力的、并帶有強烈神圣色彩的龜崇拜和龜卜,宣揚王朝大一統乃“天命所歸”,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找到了其統治的合理性,而且擴大了統治基礎,使其統治有了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色彩。因此,《史記·龜策列傳》重龜卜,恰恰從一個側面透視出當時統治階級通過“天命”觀的宣傳來鞏固統治。
四、結語
龜崇拜擁有悠久的社會文化歷史,在誕生之初及歷史的發展演變的過程中,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利用“龜”的祥瑞為自己的利益尋求合理性,賦予其神圣性,根本的作用是為現實服務。在西漢時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龜”和“龜卜”被當時的統治階級所重視,統治者借助“龜卜”宣揚天子天命所歸的統治合法性。在他們的改造宣傳下,“龜卜”作為新的“君權神授”工具而重獲新生。從作者的身份背景和產生背景可以看出,《史記·龜策列傳》不可避免地映射出當時官方的天命觀念,正因為如此,“龜卜”才得以在《史記·龜策列傳》中占據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