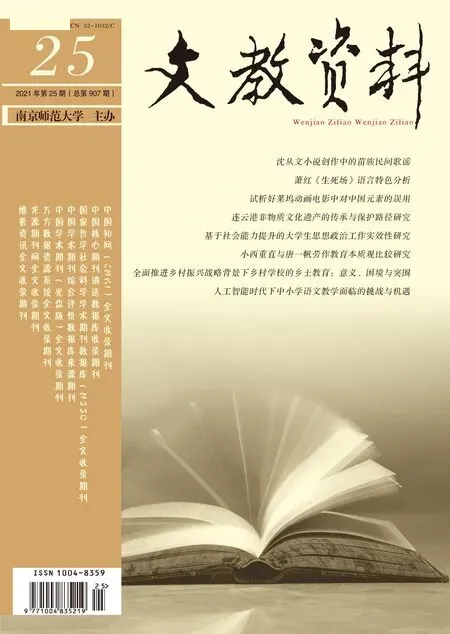沈從文小說創作中的苗族民間歌謠
弓皓然 趙洪奕 雷 霖
(懷化學院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南 懷化 418000)
沈從文在小說創作中常常會利用苗族民間歌謠作為敘事的輔助,賦予作品張力,歌謠作為作者建構湘西世界的文化符號之一,具有結構與內容上的雙重意義。以往學術界對沈從文作品中歌謠的研究,往往著重于對文本的探討,如歌謠對小說人物性格的彰顯,對情節的影響,歌謠本身的修辭藝術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了作品的文化內涵,但存在某些不足:一是忽視沈從文小說中的苗族民間歌謠與湘西傳統民間歌謠之間的精神關聯;二是偏重于苗族民間文化的研究角度,忽視沈從文游移于苗族民間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動態立場,無法深入挖掘其小說中民族性與現代性之間的復雜關系。德國藝術家格羅塞(Ernst Grosse)在《藝術的起源》中曾說:“在歌謠與舞蹈等活動里獲得的是一種統一社會感應力的文化功能,社會的一致性得以完成,民族群體的聚合與認同得以實現。”[1]民間歌謠本身帶有跨文本性與跨時空性,靜態或者孤立地在作品內部研究歌謠的價值意義是不夠的。本文旨在將苗族傳統民間歌謠與沈從文的具體作品相結合,通過分析作品中所引用民歌的特征,探討沈從文小說中歌謠人的主題的生成,進一步論證苗族民間歌謠的運用對小說的悲劇性起到的作用。
一、沈從文小說創作中民歌的性愛傾向
情歌作為苗族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在沈從文的小說中歌謠數量最多,據初步統計,沈從文小說作品中的民間歌謠共有89首,其中情歌64首,占了七成有余。[2]
作品中所引用的情歌,對于男女兩性的情欲表達比較直露,如在《阿黑小史》中阿黑唱的:“嬌妹生得白又白,情哥生得黑又黑;黑墨寫在白紙上,你看合色不合色?”在《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里,壯年水手成天在船上唱著:“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滾油煎。”在《雨后》中,男主人公四狗直接對阿姐做出“揉胸”這一動作,并唱起:“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對奶子翹翹底。心想用手摩一摩,心子只是跳跳底。”在《蕭蕭》中,花狗教小丈夫唱給蕭蕭的情歌:“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種豆莢,豆莢纏壞包谷樹,嬌妹纏壞后生家。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墳墳重墳,嬌妹洗碗碗重碗,嬌妹床上人重人。”在《媚金、豹子與那羊》中,媚金雖然身為小姑娘,卻毫不避諱對豹子的愛意:“紅葉過岡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風,把我成為婦人的只有你。”男子漢豹子真心地回應:“縱天空中到時落的雨是刀,我也將不避一切來到你身邊與你親嘴。”諸如此類的情歌還有很多,《山鬼》《巫神之愛》《鳳子》等小說作品里都有直接體現。
上述情歌中的男女雙方不避諱對愛情的渴求,并幾乎都會通過“身體”這一媒介進行愛的傳遞。這在傳統湘西苗族情歌中可以窺探到本源。在石啟貴整理的《情歌雜唱》中,隨處都能找到類似的句子:“手摸乖姣眼看色,似玉如花舍不得。若是是個紅桃子,一口吞吃免欠缺。”“面團體正又賢德,越看顏容心越熱。若是得伙同屋坐,早死夜埋也值得。”[3]同樣是通過大膽直露地描寫肉體觸碰,表達對情人的愛意;在龍秀海編著的《松桃苗族情歌選》中,無論是“贈物相約篇”里:“和心愛的人兒常來常往,迷戀到齒落發白不分開。”還是“野外幽會”中:“想你我的嘴唇少了血色,嘴皮薄得就像隨風擺動的箬葉。”[4]都通過身體大膽抒發男女之間深厚的愛情。
哲學家尼采說過:“如果我們站到這個陰森叵測的進程的終點……我們就會發現在社群之樹上最成熟的果實是主權個體,他重又逸出禮俗道教之外,是自律且超倫理的,簡言之,就是有自己獨立而長久的意志的人,可以許諾的人,——其中有一種自豪的,在所有肌肉中顫動的意識,對那個于此最終贏得的、在自己內部化為肉身的那個東西的意識,一種真正的權力意識和自由意識,一種根本上的人類完滿感。”[5]
沈從文在小說創作中喜歡引用帶有肉體或者器官意象的民歌,甚至是迷戀,主要原因是其中包含個體的存在,意象、場景、心理最終都指向青年男女的性與愛,它建構起沈從文以“原欲”為核心的生命動力學,這種動力學生產的是“自然人”,即自在自由的個體。這種個體與尼采上面所說的“主權個體”相類似,因為二者都“逸出禮俗道教之外”,而且是一種“自律且超倫理”的存在。在沈從文筆下,角色的“自律”與“超倫理”是不矛盾的,因為他們遵循的不是社會規則,而是情愛原則。“自由的個體”(主權個體)存在的標志首先是對自己身體比較自由地處置,這些都構成他作品中特有的身體敘事現象。
這種身體敘事最鮮明地體現在《雨后》中,四狗與阿姐的愛情過程,沈從文主要通過“肉體”與“野趣”兩個關鍵詞展現,小說情節的推進呈現為一種典型的性愛言說。身體、性與愛等諸如此類在苗族傳統民歌中被廣泛歌唱的因素,在沈從文的創作中得到傳承。這種對于愛意最單純直接的表露,反映出“性本能”在苗民身上的潛在力量。這種力量被弗洛伊德概括為“力比多”(即“性力”),心理學家榮格告訴我們:“力比多在生命過程當中表現自身,并被主觀地認知為斗爭與欲望。”[6]
榮格的話可幫助我們歸納出沈從文筆下苗族情歌“性欲→愛→自然”的邏輯線,這正好照應沈從文所追求的自然之美:“我用不著你們名叫‘社會’為制定的那個東西,我討厭一般標準,尤其是偽‘思想家’為扭曲壓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鄉愿標準。”[7]這種自然之美存在的最高境界就是沈從文小說中的“瘋癲”現象。
“癲子”在沈從文的很多小說中都有出現,如《阿黑小史》中的五明、《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中的號兵、《醫生》中的醫生,《山鬼》中的癲子,這些人物形象為追求愛情而變得“瘋癲”,變得好動歡樂、大膽直露,它帶來的不是病癥,而是人生本質。愛欲破開社會道德的束縛,歸于自然本真。由此可觀,沈從文不僅對苗族傳統情歌進行收集與利用,他還將自己自然人性之美的觀點與之進行有機結合,塑造出其作品中獨有的人性觀,即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
二、沈從文小說創作中民歌的自貶傾向
民歌的“自貶傾向”在沈從文的創作中第一個表現是:主人公常常會通過歌謠(以情歌和生活歌為主)貶低自己。
在《丈夫》中男主人公與水保會面后,感到自己與尊貴的人物談過話,進而想到妻子老七得了許多錢,便唱道:“水漲了,鯉魚上梁,大的有大草鞋那么大,小的有小草鞋那么小。”男人想到“大魚”“小魚”兩個對比意象,并在潛意識里將自己的身份歸于“小魚”這類,體現男主人公貶低身份意識的自覺性;同樣是在《丈夫》中,當水保離開,男主人公想起他腳上“閃閃發光”的靴子,手上“黃而發沉”的戒指,便唱起:“山坳里團總燒炭,山腳里地保爬灰;爬灰紅薯才肥,燒炭臉龐發黑。”這里的山坳和山腳分別對應二人居住地:黃莊和碼頭。在丈夫眼里,自己作為農民在黃莊只能靠燒炭維持生計,水保作為地方統治者卻可以靠“爬灰”這種不正當手段得到財富。雖然體現丈夫對水保某種意義上的戲謔,但丈夫對于財富與地位的仰慕在歌謠中仍然不經意地表露出來。
在《月下小景》中,小寨主見到姑娘后,為表達愛意,唱起情歌:“我不愿做帝稱王,卻愿為你做奴當差。”男主消解“寨主”這一象征權力地位的身份,更愿為心上人做奴隸,體現一種身份的錯位倒置。在《邊城》中,翠翠見到戴著“麻花絞的銀手鐲”的小女孩后,輕聲唱著:“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銀釧子,只有我三妹沒得什么戴,耳朵上長年戴條豆芽菜。”在這里翠翠以首飾為媒介,用豆芽菜與小女孩的貴重手鐲做對比,同樣體現對自己身份貶低的自覺。
類似的情況在苗族傳統民歌中也存在不少,如石啟貴所編著《民國時期湘西苗族調查實錄》中的“男女合唱”部分,男青年淪陷在姑娘的美貌中無法自拔,可女主卻唱自己:“蟠桃大會在天涯,姣是凡人若比它。姣如瘦地青辣子,瘟豬浪狗都嫌它。”通過鮮明的反差式夸張表達姑娘的有意自貶;在《唱佛歌》中,歌者先為人民祈福,又說自己“為愚不才初學手,言語粗糙莫記仇”,表達對于自身專業知識的謙卑與低調;在椎豬歌《你的大名四海揚》中,男主唱到自己的歌技時說:“今聽你唱口難開,甘拜下風投降你。”[3]這也是抬高他人貶低自己,為另一種貶低自身身份的方式。
除了身份自貶的意識自覺外,苗族民間歌謠還有一種對未來境況的自貶傾向,即對未來美好生活表示懷疑或否定。如龍秀海整理的苗族民歌《邂逅相逢》中,男女二人在相互迷戀的高潮時,女方卻疑心唱起了:“你對雪白淡香的花簇,激不起絲毫的興趣,你只是用甜言蜜語,故意把我的心兒灌醉。”使男方一再做出解釋;在《渴望牽手》中,女方迫切希望與男子結交婚戀,但又否定結交帶來的幸福:“結交擔心山水阻隔,愛戀又怕路程遙遠。野外相會讓你受累,你我最后不要交連。”[4]到歌謠最后甚至否定二人相愛的合理性。
沈從文作品中引用的民歌也有如此特征。如在《鳳子》中,男女主人公情投意合,可男人卻唱道:“我不問烏巢河有多少長,我不問螢火蟲能放多少光。要去你莫騎流星去,你有熱你永遠是太陽。你莫問我將向那兒飛,天上的宕鷹雅雀都各有巢歸。是太陽到時候也應回山后,你只問月亮明夜里你來不來?”以懷疑忠貞的口吻向女主表達另一種相互離散的可能性;在《媚金、豹子與那羊》中,媚金在與豹子定下婚約后向他唱到:“莫讓人笑鳳凰族美男子無信,你要我做的事自己也莫忘記。”顯示出對男子品行的一種假設性否定,為后文媚金的誤會埋下伏筆。這兩類在苗族民歌中經常出現的自貶傾向是苗族悲劇性文化心理的體現。沈從文筆下的《邊城》《丈夫》《鳳子》等文本都因為主人公的猶豫徘徊帶來一種“人為的悲情結局”。這種悲情結局與民歌中的自貶傾向交相輝映,打造屬于苗族本身的身份隱喻。苗族的俗語:“好花長在深山林,美人生在有鬼家”“強是人家的駿馬,富是人家的伙伴”[8]等都體現苗族人對美貌、財富的自覺疏離。這種疏離最后導致的是一種文化上對幸福生活與生俱來的遠離,“遠離”這個詞不僅體現在幸福感上,更體現在地域選擇上。
自古以來苗族都是一個在不斷遷徙的民族,沒有穩固的居住地與物質保障,所以一再遠離熟悉的事物,對先進的文化思想產生一種“滯后性”,形成僵硬的發展定式。這不可避免地加固苗民對生活的悲劇性體驗,即沈從文所說:“一切充滿了善,充滿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良善與單純的希望終難免產生悲劇。”[7]所以從這個層面來看,沈從文對這類情歌的引用不僅是對苗族人的書寫,還是有關苗族文化身份的寓言,折射出一定情景下自然人面對種種“不湊巧”所產生的精神困境。
三、沈從文小說創作中民歌的泛神傾向
從苗族的發展史中不難看出,湘西苗族民歌中無處不體現神性。“老天有意把我們下放人間,天公將我倆的頭發梳成一綹,雷公愿意讓我們成為一對”的神賦式;“假若落空就是命中注定,只怪老天瞎了一只眼睛。憂憤不惜年輕的性命,恨不得挖了天公的祖墳”的控訴式;諸如“等待天公為我報信”“不辜負天公的一片好意”[9]的祈求式。可見,從傳統湘西苗族民歌看來,神的旨意與命運的安排一切的因果,即神支配人民的生活,支配人民的命運。
正因為民歌中包含一種對于神的崇拜,沈從文得以借民歌的方式,將神在生命中的地位明顯地表露出來。《龍朱》有這樣的表達:“這個人,美麗強壯象獅子,溫和謙馴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權威。是力。是光。”令無數人向往神性的美并沒有使龍朱獲得想要的愛情,反而將他陷入無盡的孤獨中。要想擺脫這樣的困境,必須向心愛及逆行情感的傾訴——民歌對唱。沈從文雖然沒有具體寫出龍朱所唱的情歌內容,但從極具贊美性的評價中不難看出,龍朱在情歌中傾注自己四年最真摯最原始的感受——情愛。“龍朱所追求的,實際上是一種需求的補足及回歸原始人性的過程。”要想較完美地通過這一過程,無可避免地要進行神性的表達。
這一點與《神巫之愛》的情感表達相類似,兩者所不同的是,《神巫之愛》顯然更深入生活,不同女子對神巫的態度及愿望不一。文中從五羊、啞巴女子及神巫等多種視角展現神巫愛情。最后成就神巫與啞子寡婦愛情的,正是泛神傾向的民歌:“天堂門在一個蠢人面前開時,徘徊在門外這蠢人心實不甘。若歌聲是啟辟這愛情的鑰匙,他愿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天堂門本是西方基督教中高尚的人得以進入的地方,沈從文在這里加以運用,將傳統意義上的苗族情歌披上一層西方神話的色彩,既顯示神性的變體,又是神性在苗族中的真實寫照。
在《媚金、豹子與那羊》中,面對媚金大膽熱烈的表達,豹子直接說出“放心,我心中的最大的神。豹子的美麗你眼睛曾為證明”,將自己的戀人當作神,與神的愛能超越死亡,戰勝所有的困難。正因為這樣的泛神傾向,豹子才會因尋找白羊,誤了與媚金相約的時程,導致兩人戀愛的悲劇。他們以愛情悲劇的代價回歸最原始的人神共存,不僅引發對如今愛情現狀的思考,還寄托沈從文對于神性愛情與泛神性人格的向往。
情歌中隱含的泛神傾向,在儀式歌中同樣也存在。“你大仙,你大神,睜眼看看我們這里人!他們既誠實,又年輕,又身無疾病。他們大人會喝酒,會做事,會睡覺;他們孩子能長大,能耐饑,能耐冷;他們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雞鴨肯孵卵;他們女人會養兒子,會唱歌,會找她心中歡喜的情人!你大神,你大仙,排駕前來站兩邊。關夫子身跨赤兔馬,尉遲公手拿大鐵鞭!你大仙,你大神,云端下降慢慢行!張果老驢得坐穩,鐵拐李腳下要小心!福祿綿綿是神恩,和風和雨神好心,好酒好飯當前陣,肥豬肥羊火上烹!洪秀全,李鴻章,你們在生是霸王,人放火盡節全忠各有道,今來坐席又何妨!慢慢吃,慢慢喝,月白風清好過河。醉時攜手同歸去,我當為你再唱歌!”諸多因素中,不乏有圖騰意識與神性意識的表達。燕寶譯注的《苗族古歌》中與人類祖先姜央并提的有水牛:“蝴蝶媽媽與水泡談情說愛,后來生下十二個蛋,孵化出人類的祖先姜央與雷公、老虎、水牛、大象、龍等動物。”[10]雷公、水牛、龍等對應相應的神性圖騰崇拜,如湘西的“椎牛”(俗稱吃牛)“剖果”(舊譯“吃棒棒豬”)、接龍等。[11]將關羽、尉遲敬德、張果老、鐵拐李諸如此類的人物神化,表達湘西苗族最原始傳統的觀念理想——崇尚武力和祈求祥瑞。《神巫之愛》中神巫受族總囑托進行獻牲、祈福,借泛神傾向的儀式表達苗族人民對于族群生存的向往與展望。《邊城》中,作者讓翠翠唱這首迎神歌,目的在于賦予翠翠敏感而脆弱的內心世界中的神性,讓她的愛情前景與生命意識,通過在迎神歌中對神的祈禱表達出來。
由此觀之,沈從文借助民歌中神性的表達,不僅說明神是賦予生命價值的存在,還在潛意識上構建一種以生命原欲為核心的人性理念,既使神性充滿人性的道德價值,又將人性賦予神性的特征,以一種人神共在的方式闡述理想的生命形態,完成沈從文更高意義上的“人”的內核表達,達到對現代社會的反思與生命價值重建的目的。
四、結語
無論是沈從文小說創作中歌謠所體現的性愛傾向、自貶傾向還是泛神傾向,沈從文皆以一種反現代性的視角書寫苗族歌謠給其民族帶來的深遠影響,并將其擴展到更普遍意義上的人類書寫中,這本身是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寫作”。追溯本源,在苗族傳統歌謠中能找到相對應的文化心理與性格特征。一個民族的文化永遠是動態的,展現文化的媒介在不斷變動中。隨著改革開放后一大批新銳苗族作家的涌現(如向本貴、蒲玉等),通過苗族文化所引申的對人的書寫將越來越全面、具體與深刻,借助文學作品中的苗族歌謠研究苗族文化的趨勢將越來越多元化與動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