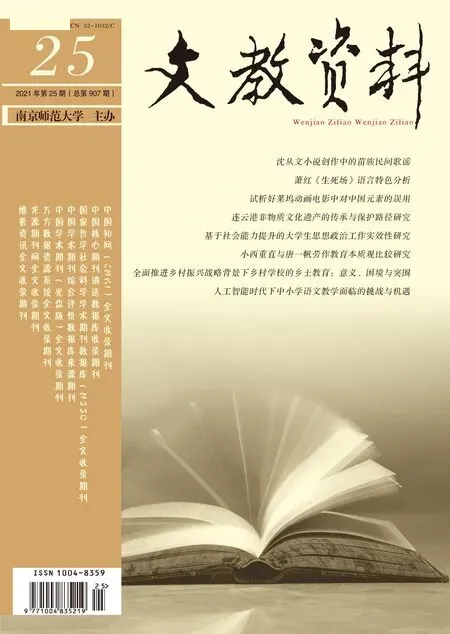小西重直與唐一帆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比較研究
張思偉 葉哲銘
(杭州師范大學(xué),浙江 杭州 311121)
小西重直(1875—1948),日本戰(zhàn)前教育家,山形縣人。1901年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xué)哲學(xué)學(xué)部,后留學(xué)德國和英國。1905年,小西重直回國,先后任教于廣島高等師范學(xué)校、東京帝國大學(xué)等學(xué)校。[1]1927年12月26日,小西重直任成城小學(xué)法人理事長,翌年2月9日至1933年擔(dān)任成城學(xué)園總長。[2]1933年3月至6月,小西重直出任京都大學(xué)總長。[3]他提倡“敬、愛、信”的教育精神,重視教育實踐,強(qiáng)調(diào)勞作教育是教育的本質(zhì),著有《勞作教育》等作品,對勞作教育在日本的興盛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唐一帆(1914—2007),福建仙游人,1933年畢業(yè)于上海新華藝術(shù)專科學(xué)校藝術(shù)教育系。[4]畢業(yè)后,他先后在仙游縣立文賢小學(xué)、縣立中學(xué)等地?fù)?dān)任教員。1939年8月至1941年7月,唐一帆在福建省立師范學(xué)校擔(dān)任勞作科教員、工場主任、級任導(dǎo)師和級任教員等職位。[5]1941年8月,唐一帆進(jìn)入福建省立師范專科學(xué)校擔(dān)任工藝科教師。[6]民國時期,唐一帆積極投身勞作教育,積累了豐富的教學(xué)經(jīng)驗,先后出版了《師范勞作教學(xué)新論》《勞作教學(xué)研究》兩本專著,并發(fā)表了《中國勞作教育的本質(zhì)》等20余篇文章,是民國時期名副其實的勞作教育專家。
小西重直與唐一帆均對勞作教育的本質(zhì)有著深刻的見解,相似的社會環(huán)境使得他們的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然而,由于教育背景、文化傳統(tǒng)等方面的不同,他們的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又各具特色。
一、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的共識
小西重直與唐一帆所處的社會與時期雖然不同,但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905年小西重直回國,日本進(jìn)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對人力資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一帆出生后,這一時期的資本主義獲得了較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對人才的要求逐步提高。20世紀(jì)初,公民教育思想、實用主義教育思想、自由主義教育思想等教育思想不僅在日本廣為流行,在中國也是風(fēng)靡一時,二人均受到了強(qiáng)烈的影響。相似的社會環(huán)境使得他們對于勞作教育的本質(zhì)有著相似的理解,都認(rèn)為勞作教育是身體與精神相統(tǒng)一的教育,是需要在實踐中進(jìn)行的教育,是對道德培養(yǎng)起重要作用的教育,是注重提升創(chuàng)造力的教育。
(一)勞作教育的本質(zhì)是身體與精神的統(tǒng)一
在古代,勞作教育被看成是對兒童身體進(jìn)行機(jī)械訓(xùn)練的教育。教育近代化開始后,人們發(fā)現(xiàn)勞作教育不僅對兒童身體的發(fā)展具有影響,而且對兒童精神的發(fā)展也起著重要作用。小西重直認(rèn)為勞作教育是靈與肉的交涉,唐一帆主張將勞心與勞力結(jié)合在一起,他們都認(rèn)為勞作教育是身體與精神相統(tǒng)一的教育。
小西重直認(rèn)為“靈為發(fā)生勞作之泉,筋肉則是勞作之流。勞作實為把靈與肉一元的結(jié)合之教育原理”。在勞作時,靈與筋肉是不可分割的,“離開了靈的作用,沒有勞作。離了精神的勞作之筋肉運(yùn)動,乃是機(jī)械的運(yùn)動,而不是真正的勞作。依借筋肉的勞作,而內(nèi)面的修煉,更為確實,但沒有內(nèi)面的修煉,則筋肉的勞作之發(fā)展,勢不可能”[7]。他提出在乳兒時代,嬰兒的運(yùn)動側(cè)重于肉的方面;當(dāng)嬰兒稍長,進(jìn)入自由游戲時代,靈與肉在游戲中相互促進(jìn),逐漸樸素地成為一元;當(dāng)兒童繼續(xù)成長,經(jīng)過自由游戲時代,靈與肉逐漸產(chǎn)生距離,形成對立姿態(tài),靈支配筋肉進(jìn)行勞作活動不再像游戲那樣簡單,“不能圓滑地安易地進(jìn)行”,兒童只有經(jīng)歷勞作的苦楚,才能發(fā)揮其教育意義,實現(xiàn)靈與肉的最終統(tǒng)一。[7]
唐一帆認(rèn)識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教育主張在我國社會盛行,“勞力”的教育長期被人們所忽視;“刻苦耐勞”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但人們受傳統(tǒng)教育的影響,只有勞力的精神,沒有勞心的習(xí)慣,在勞作的過程中缺乏思考,這樣的教育不是真正的勞作教育。因此,唐一帆接受了陶行知“從勞力上勞心”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勞作教育包括“勞力”與“勞心”兩個方面。他認(rèn)為一般的勞動人民已經(jīng)有了“勞力”的訓(xùn)練,不必再在“勞力”上下工夫,只需加強(qiáng)“勞心”的培養(yǎng);而知識分子雖然接受了教育,但傳統(tǒng)的教育并非真正的“勞心”的教育,因此知識分子應(yīng)接受“勞心”與“勞力”兩方面的教育。[8]
(二)勞作教育的本質(zhì)是實踐
勞作教育追求身體與精神的統(tǒng)一,最終都需落實到實際生活中,因此,小西重直與唐一帆都十分強(qiáng)調(diào)實踐在勞作教育中的地位。
小西重直指出:“教育在人之生活上,應(yīng)以精神生活為中心,而將其多樣豐富之可能性,盡量地求其發(fā)展。然今日的教育,則僅注意于一方面之偏倚地發(fā)展。從而兒童青年,均不以學(xué)校為他們自身的生活,而時欲求其滿足于學(xué)校以外。”[7]學(xué)校教育只將知識灌輸給兒童,忽視知識運(yùn)用能力的培養(yǎng),割裂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lián)系,導(dǎo)致兒童雖有豐富的知識卻依舊無法適應(yīng)社會。小西重直認(rèn)為:“今后的學(xué)校,必須將僅為觀念的教材之教授時數(shù),盡量減少,而置重勤勞的勞作或各種構(gòu)成的勞作以及其他實驗實習(xí)實演表現(xiàn)等上面,即在各學(xué)科的教授方面,亦非依據(jù)勞作的教育法不可。”[7]
唐一帆認(rèn)為勞作教育是一種“手腦并用”的教育,關(guān)鍵在于“做”,要“從做上去發(fā)現(xiàn)理論,從做上去印證理論,從做上去獲得一切知識、技能、習(xí)慣”[8]。唐一帆對勞作實踐的強(qiáng)調(diào)體現(xiàn)在方方面面,首先對待勞作教師的選擇,他強(qiáng)調(diào)勞作教師必須具有勞動的身手、敏捷的行動和實際的技術(shù),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指導(dǎo)兒童開展勞作活動。[9]其次,他認(rèn)為勞作是一種技術(shù)的學(xué)科,教學(xué)方法不同于一般學(xué)科,因此格外強(qiáng)調(diào)“實習(xí)”在勞作教學(xué)中的作用。再次,對于勞作科成績的考查,他將考查內(nèi)容分為“知識、技能、態(tài)度和結(jié)果”四個方面,知識和態(tài)度分別占20%,技能和結(jié)果分別占30%,可見相比于理論知識的學(xué)習(xí),唐一帆更加注重兒童動手能力的訓(xùn)練。
(三)勞作教育的本質(zhì)是道德的培養(yǎng)
小西重直與唐一帆認(rèn)為勞作教育不僅有助于兒童豐富勞作知識、熟悉勞作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夠培養(yǎng)兒童的優(yōu)良品質(zhì)、提升兒童的道德水平,使兒童真正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小西重直認(rèn)為,“凡百勞作,均預(yù)想著道德”。在勞作開始前,人們會事先確定目的、制定計劃;在勞作過程中,總會有不少困難出現(xiàn),需要人們盡力克服;勞作結(jié)束后,人們通常會進(jìn)行總結(jié)反思,這一過程中無時無刻不體現(xiàn)著人們的道德品質(zhì)。“無論個人的道德或社會的道德,在凡百勞作之中,皆得直接間接的修煉。”他認(rèn)為每一個人都存在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僅僅依靠精神的鍛煉是不夠的,也需要依靠筋肉之力實行各種勞作來培養(yǎng)。他把學(xué)校當(dāng)作一個勞作社會,在這個勞作社會中既可以實行個人的或小群的勞作,也可以實行共同的勞作。在共同的勞作中,個人的意見與全體的意見并非完全一致,兒童可以體驗到對立,也可以體驗到共鳴。這不僅使兒童的個性得到發(fā)展,社會性亦得到發(fā)展,“社會連帶心、相互扶助心、協(xié)同合作、容忍、寬大、友愛、秩序、規(guī)律遵循等諸德,均能由此教養(yǎng)之”[7]。
唐一帆也十分重視勞作教育對兒童道德培養(yǎng)的作用,他認(rèn)為勞作教育是一種道德教育的實踐。然而,過去學(xué)校中的勞作教育不能使兒童體會到勞動的辛苦與趣味,無法使兒童真正明白“勞動神圣”的含義,也就無法培養(yǎng)出真正的熱愛勞動的兒童。因此,唐一帆主張在選擇勞作教育教材、實施勞作教育時應(yīng)避免選擇引誘兒童墮落、養(yǎng)成兒童奢華習(xí)慣與自私自利的勞作內(nèi)容,而應(yīng)該選擇大眾化、民族化、科學(xué)化和時代化的勞作內(nèi)容,從而培養(yǎng)兒童良好的道德品質(zhì)。大眾化的內(nèi)容有助于兒童形成人人平等的價值觀,消除封建階級觀念;民族化的內(nèi)容有助于兒童了解民族文化,提升民族自豪感;科學(xué)化的內(nèi)容有助于兒童學(xué)習(xí)先進(jìn)的科學(xué)知識,養(yǎng)成嚴(yán)謹(jǐn)?shù)目茖W(xué)態(tài)度;時代化的內(nèi)容有助于兒童明了當(dāng)前社會的問題與需求,緊跟當(dāng)前時代的潮流。[9]
(四)勞作教育的本質(zhì)是創(chuàng)造
勞作教育不是技能的機(jī)械訓(xùn)練,也不是知識的簡單灌輸,它是一種培養(yǎng)創(chuàng)造力的教育。小西重直與唐一帆都十分重視兒童在勞作活動過程中創(chuàng)造能力的提升。
小西重直認(rèn)同小原國芳對“勞作”的闡釋,認(rèn)為“勞是勤勞,作非作業(yè)之作而是創(chuàng)作之作,‘勞作’即是勤勞而加以自己之力以從事于創(chuàng)造創(chuàng)作與構(gòu)成之意味”[7]。可見小西重直將勞作當(dāng)作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而非呆板機(jī)械的活動。他認(rèn)同自然的教育方法,認(rèn)為勞作是自然的語言,兒童通過勞作來表現(xiàn)自己,并在勞作的過程中反省自己,明了自身的不足,進(jìn)而對自身的認(rèn)識更為完善,這不是機(jī)械重復(fù)的過程,而是一種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兒童在其自己教育中,依從自然的教育法,自行實驗而充實的、勞作的、創(chuàng)造的從事發(fā)展”。他批判了當(dāng)時的學(xué)校教育,認(rèn)為當(dāng)時的學(xué)校教育是一種僅僅依靠“眼耳口”的教育,是一種注入式的教育,忽視兒童個性的發(fā)展,使兒童受到了嚴(yán)重的壓迫。[7]
唐一帆認(rèn)為人們的生活是在不斷改造的,勞作教育作為一種生活的教育,自然也應(yīng)特別注意改良與創(chuàng)造。[8]為此,他格外注重廢物利用的教學(xué),將無用的事物進(jìn)行加工組合,變?yōu)樵趯嶋H生活中供兒童玩耍、使用的事物,這種教學(xué)活動極易引起兒童的興趣,他認(rèn)為廢物利用的教學(xué)是最容易培養(yǎng)兒童創(chuàng)造的興趣與能力的方式。[9]然而,改良與創(chuàng)造的實現(xiàn)也并非易事。改良與創(chuàng)造需要立足實際,一方面應(yīng)符合當(dāng)下的實際,絕不能超脫現(xiàn)實進(jìn)行改良與創(chuàng)造;另一方面應(yīng)符合中國傳統(tǒng)的實際,絕不能一味效仿國外。此外,改良與創(chuàng)造也絕非易事,其前提是模仿,越精細(xì)的模仿意味著對事物的了解越透徹,基礎(chǔ)知識才能越扎實,最終才能實現(xiàn)改良與創(chuàng)造。改良與創(chuàng)造也是有前后的,創(chuàng)造雖好但并非人人都能進(jìn)行創(chuàng)造,在大部分情況下能做到改良已是不易。[8]
二、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的差異
小西重直與唐一帆身處的時代與社會雖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差異性也十分明顯的。小西重直信奉“敬、愛、信”的教育理念,他的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充滿了宗教的色彩;他更傾向勞作教育對精神方面產(chǎn)生的作用,強(qiáng)調(diào)勞作教育對“美”的重要作用。而唐一帆的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立足于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強(qiáng)調(diào)勞作教育對“生產(chǎn)”的重要作用,體現(xiàn)了唯物主義的色彩。
(一)宗教的勞作與唯物的勞作
小西重直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響,他的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建立在“動物是肉的,神是靈的,人不僅是肉,亦不僅是靈,他須依借肉與靈的交涉,始能盡其人之所以為人的使命”的人的本質(zhì)觀之上,他把人類的勞作看作“與神之圣的勞作交流而發(fā)生于靈肉交涉世界之勞作”。[7]在他看來,宗教生活是一切文化的泉源,宗教的虔敬是教育的出發(fā)點(diǎn),是教育的過程,也是教育的目標(biāo)。一方面,“宗教上之行”是宗教方面的勞作活動,有助于掃除人們心靈上的污物,實現(xiàn)心靈的凈化,有助于達(dá)到宗教中所說的虔敬生活,學(xué)習(xí)這類勞作是實施勞作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另一方面,世間所有事物都蘊(yùn)含著神的精神與人的努力,只有真正明了這其中的內(nèi)涵才能生出虔敬的態(tài)度,“接受材料的兒童,若能知道此事,那么,將先對人與神佛,而自然低下其小頭,其天真無邪的瞳中,亦將表現(xiàn)出真面目的態(tài)度”[7]。
唐一帆的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則與小西重直不同,他在人們實際生活與生產(chǎn)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自己對于勞作教育本質(zhì)的看法,并深入分析了勞作教育實施的心理基礎(chǔ)與生理基礎(chǔ),蘊(yùn)含著唯物主義的觀念。首先,唐一帆看到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國情上的區(qū)別,中國社會正在遭受列強(qiáng)的入侵、社會動蕩不安、生產(chǎn)落后、人民生活痛苦,在這種認(rèn)識下,他提出要實施勞作教育,勞作教育是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和國家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基礎(chǔ)。其次,唐一帆為了更好地進(jìn)行勞作教育教學(xué),對兒童的心理與生理進(jìn)行了觀察,發(fā)現(xiàn)兒童的年齡、性別、智力等方面的差異都會對兒童進(jìn)行勞作活動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9]
(二)美的勞作與生產(chǎn)的勞作
小西重直不僅認(rèn)為勞作的過程中處處充滿了美,而且勞作的美也能進(jìn)一步推動勞作的發(fā)展。首先,小西重直認(rèn)為人們在勞作的過程中處處存在美,人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身體呈現(xiàn)出的統(tǒng)一調(diào)和的姿態(tài)是一種美的勞作,創(chuàng)作過程中必然出現(xiàn)的鑒賞也和美的勞作不可分割。而從教育方面來講,其范圍就遠(yuǎn)遠(yuǎn)超乎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在借身體的運(yùn)動而行之一般廣義之構(gòu)成的活動上,亦能使其達(dá)于某種程度之美的構(gòu)成,故美的勞作,在一般的構(gòu)成作用上,是能多分的實現(xiàn)的”。其次,勞作多辛苦費(fèi)力,受人輕視,“要是能對其美化,那么,嫌惡之情自念不起,而能能動的進(jìn)而從事工作了。凡在能動的自發(fā)的從事時,工作與自己已是一致而調(diào)和了,故其心境,總是美的。而因心境是美的,故工作又易成為自發(fā)的”[7]。
唐一帆也看到了美在勞作教育中的作用,要求實施勞作教育的教師擁有美術(shù)的知能,然而相較于小西重直,唐一帆顯得更為務(wù)實,更強(qiáng)調(diào)勞作教育在生產(chǎn)方面的重要性。他認(rèn)為“勞作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是在于改良人類的生活,一方面是在增進(jìn)社會的生產(chǎn),故勞作教育的主張‘以勞作為生活的基礎(chǔ),以生產(chǎn)為生活的表現(xiàn)’”,“我們站在教育的立場上,應(yīng)該設(shè)法改良其生產(chǎn)的技術(shù),使其具有‘工業(yè)化’的傾向,換言之,即‘使一般純舊式手工生產(chǎn)轉(zhuǎn)變?yōu)檫M(jìn)步的手工制造,最后再轉(zhuǎn)變?yōu)槠餍档纳a(chǎn)’”。[8]人們在長年累月接受勞作教育后,將獲取豐富的勞作知識、實用的勞作技能、正確的勞作價值觀,對未來人們的生活和生產(chǎn)將產(chǎn)生巨大影響,這不僅影響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更重要的是將極大地影響人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們的生產(chǎn)素質(zhì),引導(dǎo)產(chǎn)業(yè)的前進(jìn)與升級。
小西重直與唐一帆對勞作教育的本質(zhì)進(jìn)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們都認(rèn)同勞作教育是一種手腦并用的教育,在勞作教育實施的過程中應(yīng)重視實踐的作用、重視道德的培養(yǎng)、重視創(chuàng)造能力的提升。同時,他們對于勞作教育的本質(zhì)也有自己獨(dú)特的見解,如勞作教育與美的關(guān)系、勞作教育與生產(chǎn)之間的關(guān)系,這兩種觀點(diǎn)也是今天我們教師在實施勞動教學(xué)時容易忽視的。此外,小西重直關(guān)于勞作與宗教關(guān)系的論述,雖然存在著一定的封建因素,不如唐一帆的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符合當(dāng)前的思想潮流,但小西重直思想中蘊(yùn)含的對大自然的敬畏也足以引起我們的思考。對二者的勞作教育本質(zhì)觀展開研究與比較,有助于加深今天我們對勞動教育的認(rèn)識,加強(qiáng)對勞動教育本質(zhì)的理解。
- 文教資料的其它文章
- 共生視角下粵北地區(qū)民間童謠在幼兒園的應(yīng)用現(xiàn)狀
- “互聯(lián)網(wǎng)+”背景下智慧課堂的構(gòu)建研究
- 課程思政視域下“社會保障概論”課程的教學(xué)設(shè)計與實踐
- 北京市遠(yuǎn)郊區(qū)義務(wù)教育小學(xué)階段經(jīng)典誦讀困境與對策研究
——以北京城市學(xué)院沙嶺實驗學(xué)校為例 -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課堂教學(xué)效果評價與優(yōu)化對策
- 借力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競賽,構(gòu)建設(shè)施園藝學(xué)第二課堂實踐教學(xu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