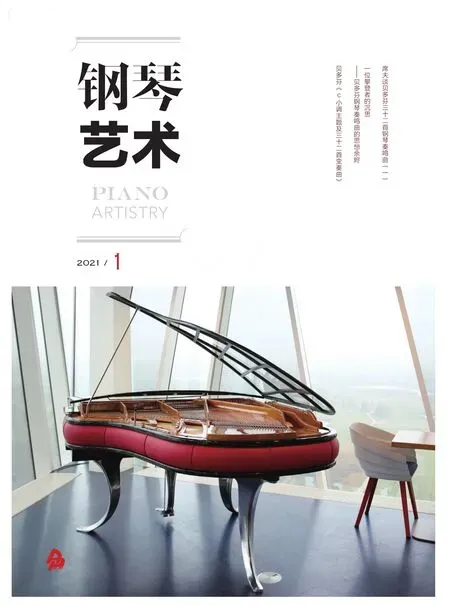一位攀登者的沉思
——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思想余燼
文/ 安德拉斯·席夫 編譯/ 谷宇飛

彪羅曾經(jīng)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比喻:如果說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是音樂的“舊約圣經(jīng)”,那么貝多芬的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可謂是“新約圣經(jīng)”——這句話洞見本質,且絕非虛言。這四十八首前奏曲和賦格憑借其統(tǒng)一與嚴謹,引發(fā)了我們關于“圣經(jīng)”的遐思。那么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究竟能喚起我們什么思緒呢?對我來說,這些作品就像巍峨雄偉的喜馬拉雅山脈一樣。其中千峰萬仞,各有千秋,或高聳入云,或重巒疊嶂,抑或袖珍可愛,這些作品都形成了邏輯上的統(tǒng)一,并構成了一個內涵豐富的整體。對于攀登者而言,登上這座高峰難于上青天。特別是對于學習這套作品并且希望能夠整套演奏的鋼琴家們來說,這就是他們所面臨的最艱巨的挑戰(zhàn)。由此看來,完成這項挑戰(zhàn)并非單憑體力就能夠勝任的。盡管克服體能問題并且葆有堅韌的耐力非常重要,但與智慧和情感方面的困難相比,更需要我們全力擔負起精神層面的責任和使命。
在將這套作品完整演繹過十五次之后(以后還會有更多詮釋),讓我來回顧一下這些漫長的音樂旅程。在貝多芬弦樂四重奏和鋼琴奏鳴曲中,我們可以洞悉他音樂的發(fā)展。這些音樂猶如兩條“命運的紅線”(此處的“紅線”象征主題線索,這個寓意來源于希臘神話中提修斯國王順著一條“紅線”走出了牛頭怪布置的迷宮。——譯者注),牢牢貫穿貝多芬的整個生命和存在。從鋼琴奏鳴曲Op.2到Op.111,從弦樂四重奏Op.18到Op.135,我們可以在其中分別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發(fā)展,甚至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蛻變。貝多芬不是神童,早年也并沒有聲名鵲起。相比較而言,他的生命歲月比莫扎特和舒伯特還要漫長,盡管如此,在創(chuàng)作生涯中,他還是不得不掙扎著寫出新作,才能開拓新的創(chuàng)作領域。在鋼琴奏鳴曲這一題材中,他所展現(xiàn)出的無窮無盡的多樣性令人驚嘆,幾乎沒有比這些曲目更獨特的作品了,而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則表現(xiàn)出鮮明的統(tǒng)一性。實際上,貝多芬多變的性格正是導致他的作品難以詮釋的關鍵,每首奏鳴曲都有屬于自己的面貌和獨特性,這些曲目之間的差異性比他們的共同點要鮮明得多。演奏者的真正使命就是揭示每首奏鳴曲的不同性、個性和獨特性,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我和其他有志向的鋼琴家一樣,在學生和青年時代多少彈過些貝多芬的奏鳴曲,但并沒有下太多功夫。雖然諸如《D大調第十五鋼琴奏鳴曲》(別稱“田園”奏鳴曲,Op.28)和《E大調第三十鋼琴奏鳴曲》(Op.109),對我來說似乎是得心應手,但其他作品,如《f小調第二十三鋼琴奏鳴曲》(別稱“熱情”奏鳴曲,Op.57),卻成為我難以逾越的鴻溝。我想用豐富的音響性賦予這首作品獨特的意義,但這似乎無法付諸實踐。最后兩首奏鳴曲令我崇敬之至,即《降A大調第三十一鋼琴奏鳴曲》(Op.110)和 《c小調第三十二鋼琴奏鳴曲》(Op.111),我將它們視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作品。當時我認為,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根本不配輕易觸碰這些“藝術豐碑”。在我早期的音樂生涯中,這種想法令我刻意去回避貝多芬的作品。只有一張唱片是個例外:我曾在布達佩斯國家博物館收藏的貝多芬布羅德伍德鋼琴上,演奏過Op.119、Op.126及其他幾首小品。
盡管如此,還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聆聽經(jīng)驗促成了我回歸貝多芬鋼琴音樂的靈感和誘因。首先,我要感謝安妮·費舍爾。這位出色的鋼琴家于20世紀70年代在布達佩斯完整演奏過貝多芬的三十二首奏鳴曲。幸運的是,我親耳聆聽過兩遍她所演奏的整套作品。許多年以后,我向她傾訴了我學習貝多芬的難處。她只是說:“那真是太遺憾了,這些音樂是如此神圣……”
1978年,我在佛蒙特州舉辦的“萬寶路音樂節(jié)”上結識了魯?shù)婪颉と麪柦稹乃抢镂覍W到了很多東西,例如,如何正確讀譜。對他來說,忠于樂譜是音樂的先決條件,他堅持一定要嚴格遵循貝多芬的指示。塞爾金的態(tài)度源于一種極為崇高的精神,在我心中他是楷模。不久后,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遇到了位頂級音樂家,名叫山多爾·維格。對我而言,能和他一起演奏音樂是我的榮幸。我們排練、表演并錄制了貝多芬的十首小提琴奏鳴曲。著名的維格弦樂四重奏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同時他也是這支樂隊出色的前任領導者。他對于貝多芬有著極為深刻的見解。他無拘無束的音樂精神最終將我從對貝多芬的恐懼等復雜情感中解脫出來,并賦予了我面對未來所需要的勇氣。
有人會認為自己出生得太遲,或者感嘆自己生不逢時,又或者抱怨自己時運不濟、錯失良多。對我們這代人來說,只有通過錄音才能了解阿圖爾·施納貝爾、埃德溫·費舍爾、威廉·福特文格勒、布魯諾·瓦爾特、奧托·克倫佩勒或布什四重奏的藝術。盡管如此,我們至少還有幸能聽到錄音!而這些音樂遺產(chǎn)正是詮釋貝多芬的準繩。
從1978年到2003年的二十五年間,我更側重于演奏巴赫、海頓、莫扎特和舒伯特的作品。這些好的學習經(jīng)歷,為后來研究貝多芬音樂奠定基礎。直到40歲以后,我才開始系統(tǒng)鉆研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其中大約半數(shù)已然成為我的保留曲目,而剩下的則需要我去逐一攻克。每年我都會準備兩到三首新奏鳴曲。最后,我習得了《“華爾斯坦”奏鳴曲》,接下來是最后兩首,也就是Op.110和Op.111。十年后的2003年,我將這些奏鳴曲全部消化并開始登臺演奏。對于年歲已然“成熟”的我來說,是時候開始計劃演奏整套貝多芬奏鳴曲的演出了。
這項龐大的計劃需要逐步去細化,從而解決各類問題,并逐一去面對。例如,我究竟該按照何種順序演奏這些杰作,又為何要如此刻苦鉆研呢?有那么多鋼琴家已經(jīng)演奏并且錄制過這些曲目。既然貝多芬奏鳴曲的詮釋已然如此豐富,我們還需要再增添一種演繹方式嗎?對于這些作品,我真的能夠呈現(xiàn)出獨一無二、不可或缺的詮釋嗎?以上這些都是需要我認真回答、如實自省的問題。這部作品是如此偉大、永恒且不朽,引領人們對它進行新的詮釋。的確,關于貝多芬奏鳴曲的嶄新演繹在不斷涌現(xiàn),正如圣經(jīng)被神學家們反復研讀那樣,貝多芬奏鳴曲也一次次向那些新的解讀和演繹方法敞開大門。正因如此,對于上述問題,我的回答毋庸置疑是“肯定的”。用貝多芬自己的話來說——“Es muss sein!”(“必須如此!”)。
接下來就需要考慮如何對每場演出進行細致的分工和規(guī)劃。近年來,音樂會的時長通常為兩小時,其中還包括中場休息時間(順便提一下,至于音樂會中場休息是否有必要保留,我們要聊的可太多了)。每首貝多芬奏鳴曲的時長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把它們拆分到七八場音樂會中來演奏。但是演出的具體順序該怎樣設計呢?針對這個問題,每個人的看法各不相同,幾乎有多少位鋼琴家就有多少種不同的觀點。我的大多數(shù)同僚們喜歡把貝多芬早期、中期、晚期的奏鳴曲混在同一場音樂會中演奏。與此同時,他們還會去審慎選用至少一部“熱門”作品。聽眾似乎更傾心于這種安排,大多音樂會的組織者也不反對這種做法,也許這樣更有助于提升票房。
不久前,我曾欣賞過一位著名鋼琴家的貝多芬專場音樂會。那場音樂會由《第九鋼琴奏鳴曲》(Op.14)、《第四鋼琴奏鳴曲》(Op.7)、《第二十二鋼琴奏鳴曲》(Op.54)和《第三十二鋼琴奏鳴曲》(Op.111)幾首作品組成,但組合在一起卻毫無章法、支離破碎,最后變得幾乎毫無意義可言。這幾首作品所對應的調性——E大調、降E大調、F大調、c小調——的順序本身就缺乏邏輯,它們之間也并無任何內在的聯(lián)系。自始至終我都堅信,按照創(chuàng)作的時間順序來演奏是最具說服力的。為什么呢?因為這樣就可以將這些奏鳴曲完美地嵌套進七八場獨立的演出中,就像手放進手套里那樣合適。如此一來,聽眾才能夠理解音樂間邏輯銜接的連續(xù)性,就像是閱讀一部長篇小說那樣。此外,作曲家以同一作品編號(如Op.2、Op.10、Op.14、Op.27、Op.31)發(fā)表的奏鳴曲沒有必要拆開演奏——事實上它們屬于同一系列。
毋庸置疑的是,音樂家首先需要有機會去演奏整套曲目。談到這里,我要感謝諸位音樂會的策劃者,是他們幫助我實現(xiàn)心中所想。這些“旅程”的經(jīng)歷印證了一點——那些本屬于“冷門”奏鳴曲的光環(huán),被所謂的“熱門”曲目不公正地掩蓋了。有趣的是,當那些觀眾本就喜愛的曲目和其相鄰曲目被一同演奏時,所營造出的聆聽效果更佳。大眾的審美品位本不應被低估。但愿他們走進音樂廳,并非是為了輕浮的娛樂,而是為了經(jīng)歷學習的過程并且共同體驗美好。演奏者更加應該關注理想的聽眾——那些整場音樂會中都始終追隨自己的人。如果僅僅因為碰巧在演出現(xiàn)場附近,在音樂會開始前五分鐘匆匆地買了張票,那么他(她)也許無法進入到合適的精神狀態(tài),無法去融入甚至聆聽貝多芬的音樂。因為貝多芬對觀眾的要求幾乎和對演奏者的一樣高。
首次在公眾面前演奏貝多芬奏鳴曲并不算什么大事。演奏者可以持之以恒地研究、分析和練習這些曲目,但只有經(jīng)過反復演奏才能達到爐火純青的水準。因此,對于演奏者來說,不止一次有幸在音樂會上演繹它,著實是一件幸福的事。經(jīng)歷過多次的演繹,演奏者才能收獲更多勇氣和自信;這樣的話,他們就有能力去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這樣一味地重復,是否會令演奏成為例行公事呢?我相信絕對不會,貝多芬的音樂是如此偉大,其深度永遠無法被我們全然探知。貝多芬的音樂內涵,就像大自然一樣取之不竭。
在演出過多場貝多芬奏鳴曲專場音樂會后,唱片公司的制作人 、音樂會的策劃者和我本人達成了一致共識:即在蘇黎世,以“現(xiàn)場”音樂會錄音的形式錄制下整場演出。蘇黎世市政音樂廳富麗堂皇,并且音響效果極佳,非常適合錄音。現(xiàn)場的觀眾不僅博學,而且相當安靜、懂規(guī)矩。正因如此,我才更傾向于在音樂會現(xiàn)場完成錄制工作,而非錄音室。正是一種一往無前的動力令貝多芬音樂重煥生機,而敢于冒險的精神是構成這種動力的重要源泉。在錄音室里,演奏者總是可以能隨時停下修改潤色,又隨即重新開始,這樣就可以完美無缺地把許多小樂段拼湊成一個更大的整體。但這常會導致音樂變得機械古板又刻意,這種情況不僅僅存在于貝多芬的音樂中。相比之下,貝多芬的音樂更需要大動干戈,以及音樂會現(xiàn)場所帶來的臨場感,前提是演奏者足夠走運。但倘若音樂會現(xiàn)場出現(xiàn)失誤怎么辦?我認為沒有必要總是追著一段差強人意的經(jīng)歷不放,甚至哪怕是徹底的失敗也無需過于憂心。我很樂意承認,這套唱片中最后三首奏鳴曲的錄音并非來自蘇黎世音樂會的現(xiàn)場。在音樂會結束的幾個月之后,在沒有觀眾的諾伊馬克特的雷施塔德音樂廳,我重新演奏了這些作品,這次的錄音更讓我滿意。不過專輯中剩下的二十九首奏鳴曲都錄制于蘇黎世的音樂會現(xiàn)場,只有很小幾處的改動是用排練時留下的錄音處理的。
在整套作品的詮釋中,我選用了貝森朵夫和施坦威兩個品牌的鋼琴,甚至還用同品牌中不同型號的鋼琴。至少對我而言,這些作品的風格和層次是如此多樣,以至于只選擇在同一架鋼琴上演奏是不可能的。此外,貝多芬的奏鳴曲也向我們展現(xiàn)了鋼琴發(fā)展的歷史。作為一名杰出的鍵盤樂器演奏家,貝多芬熱衷于參觀各大維也納鋼琴制造廠,并和一些制琴師成為朋友,同他們進行過深入且富有成效的交流。貝多芬時代的每一架古鋼琴都擁有自己獨特的品質。然而今時不比往日,幾乎所有的鋼琴家都在施坦威鋼琴上演奏。我認為這種全球化并非是好事,這種千篇一律、隨波逐流的現(xiàn)象對時尚和烹飪界同樣貽害深遠。在音樂領域,這種做法的危害更甚。大多數(shù)鋼琴家都喜歡平衡勻稱的音色,從而消除了音色的差異性和強烈的對比性。不足為奇的是,這導致如今大部分的演繹聽起來都如出一轍。相反,演奏者應努力尋求每首貝多芬奏鳴曲獨特的音質。一架好的施坦威無疑是優(yōu)秀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切。為什么我們不能更富有一些探索精神呢?
在演奏風格一成不變的同時,大眾的聆聽習慣也相應地被降低到了一個普遍的標準,導致現(xiàn)在只有施坦威鋼琴的聲音才能被聽眾所接受,而其他鋼琴的音色則會遭到質疑和猜忌。這真是太遺憾了!在過去,杰出的鋼琴家們演奏過各式各樣的鋼琴:例如,施納貝爾和巴托克更喜歡貝希斯坦;柯爾托喜歡普萊耶爾;也有其他的演奏家更偏愛博蘭斯勒和依巴赫。自1828年起,維也納的貝森朵夫公司就開始生產(chǎn)鋼琴,這種鋼琴以其溫暖歌唱般的聲音和具有主觀色彩的音色,成為維也納傳統(tǒng)的最佳代表。因此,舒伯特的音樂用貝森朵夫鋼琴來演奏絕對地道。許多貝多芬的奏鳴曲與舒伯特的奏鳴曲都有相似之處,舒伯特尊崇略年長的貝多芬,卻并不盲從。貝多芬是榜樣,又是舒伯特靈感的源泉。所以,我決定用貝森朵夫鋼琴和施坦威鋼琴各演奏半數(shù)的奏鳴曲。至于哪首曲目對應哪架鋼琴,這是個秘密。不妨請你猜猜看,不過事先請將那些先入為主的想法拋卻腦后,試著敞開心扉去毫無偏見地傾聽與感受。在理想情況下,我本希望借助早期鍵盤樂器來呈現(xiàn)第三種可能性。
偏見不僅體現(xiàn)在對樂器的選擇上,也體現(xiàn)在人們對音樂的思考和感知方面。人們了解這些奏鳴曲,或自以為了解了它們,因為已然聽過無數(shù)次了。現(xiàn)如今,對于這些名作,人們都有其各自心儀的演奏版本。這些詮釋最好不要被他人擅自推翻——請勿打擾!陳規(guī)要么把我們引向歧路,或者只是徒有其表,因為它并沒有經(jīng)過對音樂本身的深入探究。對于那些最受歡迎的曲目而言更是如此,演奏者務必與最荒唐的謬誤進行斗爭。《“悲愴”奏鳴曲》第一樂章中的反復部分從何處起始?我們該如何處理貝多芬在《升c小調奏鳴曲》中“非傳統(tǒng)”的踏板標記?在《“熱情”奏鳴曲》的第一樂章中,該用何種速度與節(jié)奏演奏才正確?(可以打賭,至少百分之九十的音樂愛好者會把這部作品的主旋律唱錯!)為什么《“槌子鍵琴”奏鳴曲》的演奏者務必要注意作曲家所寫下的節(jié)拍器標記,并加以認真地對待?究竟何時我們才會意識到“月光”這種會導致我們對作品特點做出錯誤判斷的昵稱,其實并非出自貝多芬本人之手?
馬勒曾經(jīng)說過“傳統(tǒng)就是打馬虎眼”(原話更精確的表述為“你們這些劇院的人口中所謂的傳統(tǒng)無非就是偷懶和馬虎”)。盡管傳統(tǒng)能夠將重要和有益的知識傳承下去,但馬勒此話也絕非虛言。音樂家就像一幅畫作的修繕者,在處理音樂時必須剝去污垢和已然硬化的舊塵——換句話說,演奏者必須根除不良的傳統(tǒng),以便在詮釋音樂時,能盡可能地去接近作曲家原本的意圖。
終登頂峰后,筋疲力盡的攀登者內心充滿了喜悅和感激。洞悉整座山脈的全貌對他而言是高山仰止,他所能做到的只能是越攀越高,越行越遠。正是這樣的經(jīng)歷,才讓生活變得更有意義。